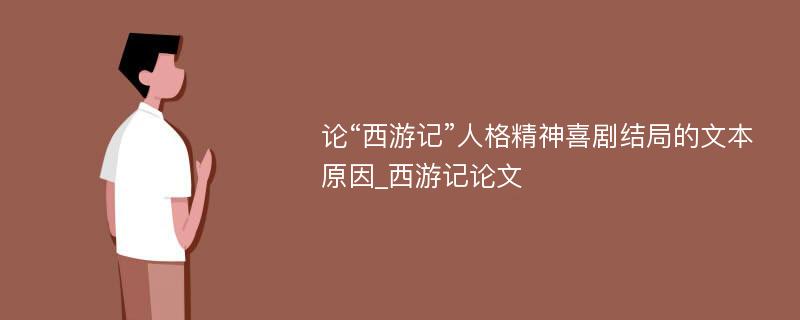
论《西游记》个性精神喜剧性结局的文本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游记论文,喜剧论文,文本论文,结局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2)02-0082-06
《西游记》与《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等不同,是一部以喜剧作结的作品。尤其是与其前的《水浒传》和其后的《金瓶梅》,在诸多方面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但在结局上却截然不同。也就是说,《西游记》与《水浒传》、《金瓶梅》,在对个性精神的表现方面,具有同一性,但其结局是相反的。
《西游记》的主题历来众说不一。但小说对个性精神的褒扬,应是没有问题的。取经僧众,西行之前,都是程度不同的离经叛道者。这种个性精神,在取经途中,除了沙僧、小白龙外,孙悟空、猪八戒和唐僧,也都有相当程度的表现,就是到了西天,也没有消失。
唐僧的前世“金蝉子”因不听如来“说法”,“轻慢我之大教”[1](P1064)(以下所引原文,只注回数),转世成人,又迷执天伦人情,执意为父报仇(“附录”),有违佛家教义。孙悟空大闹天宫,“欺天罔上”、“凌圣偷丹”(第七回),是“乱大伦”、“恶贯满盈”的大罪。猪八戒,先是好色,后则食人(第八回)。沙僧在流沙河食人度日(第八回),都属不廉不仁之举。小白龙“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第八回)违背了三纲五常中的“父纲”,犯了忤逆之罪。在等待取经人期间,同沙僧一样,也靠杀生度日(第十五回)。五人都算是离经叛道之辈。其中的“道”、“经”,无外乎儒家纲常、道规和佛戒,内涵虽异,但对个性精神和主体意识的束缚则是相同的。而“叛”之“离”之,反映的自然是一种立足个人维度的个性精神和主体意识(至于杀生行为,在超现实的神魔世界里,不宜拘泥理解)。
西行取经是一个“苦炼凶魔种种灭”、“五圣成真”(第一百回)的历程,同时,也是个性精神、主体意识张扬的载体。这种精神、意识,在相当程度上,贯穿于取经过程的始终。这在孙悟空、猪八戒和唐僧身上都有明显的表现。“西行路上的孙悟空,尽管被如来佛套上了那个拘束‘反性’的紧箍,但他的身上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异端’风采。”[2](P35)对神佛世界,依然保持着一种桀骜不驯的天性。腹谤观音,奚落如来,耍弄老君。见了玉帝,也只是“唱个喏”(第十五回)。为骗小妖,要求玉帝装天半个时辰。“若道半声不肯,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第三十三回)孙悟空这种对待神佛的态度,并非只是过过口瘾、争足面子而已。小说第二十四到二十六回,对不把他放在眼里的连观音也“让他三分”的“地仙之祖”镇元子,愣是被他逼得与自己称兄道弟,加倍的赔不是。取经路上的猪八戒是贪食好色的典型,面对美色,他是“心痒难挠,坐在那椅子上,一似针戳屁股,左扭右扭的,忍耐不住……眼不转睛,淫心紊乱,色胆纵横”(第二十三回)。唐僧在取经路上有过几次艳遇,虽没犯戒,但也是经历了难抑天性的心理煎熬,“是个坐怀心悸的正人君子”[2](P32),面对色诱,他“好便似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虾蟆,只是呆呆挣挣,翻白眼儿打仰”(第二十三回)、“战兢兢立站不住,似醉如痴”(第五十四回)。八戒的追求是主动的,只是苦无机缘。而唐僧的不免动情,则有戒律的勉强维持。二人虽程度不同,但本性是一样的。
取经僧众这种本能、个性,即使到达西天,也未被“灭尽”。孙悟空被封为“斗战圣佛”,其“争强好胜”,居然也能混入佛性。“‘斗战圣佛’并不是孙悟空修成正果的证明,而是作者对他英雄品格的肯定。”[3](P274)而且,孙悟空成佛之后,还念念不忘头上的“紧箍咒”,请求三藏“趁早儿念个松箍儿咒,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什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第一百回)。自由的心性一如往日。佛祖称八戒“保圣僧在路,却又有顽心,色情未泯,因汝挑担有功,加升汝职正果,做净坛使者”(第一百回)。色情未泯,无碍“成真”,还照顾到“口壮身慵,食肠宽大”,封个“净坛使者”。而唐僧的色欲本性,小说也没有着意安排他坐怀不乱的情节。看来,那点人性,也并没有因成就佛果而消失殆尽。
《西游记》的个性精神贯穿情节的始终,与《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等作品之仅见于情节开端和过程相比,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有理性支撑的、较为充分的自由精神。因此,喜剧性结局——“五圣成真”,使小说《西游记》最终成为一曲个性精神张扬的颂歌。
《西游记》个性精神喜剧性结局的形成,有多种因素,如作者的情况、市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等。但问题是,就作者情况而言,《西游记》其前的《水浒传》和其后的《金瓶梅》的作者,都具有个性精神和主体意识,但两书的个性精神都以悲剧作结。就时代条件而言,《水浒传》成书时期,在元明之际,或在明代弘治、正德年间[4](P274-276),个性精神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尤其是《金瓶梅》成书的明代后期,创作在精神自由度上,则远大于《西游记》,为何这些作品,都是以悲剧作结?看来,仅从外部思考其原因,还不够全面,有必要从小说内部即文本诸方面的特征入手,来讨论这一问题。
成熟的作品往往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容、形式、风格等因素,以一定的连接方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某一因素,与系统中其他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游记》个性精神得以张扬,与系统所呈现出来的多方面的特征如超实性、思想性和世俗性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游记》个性精神的喜剧性结局,既得力于其文本系统的超现实性、儒道佛既定理路,又获益于社会与道德的价值取向等。
一、超现实性
《西游记》的超现实性,包括浪漫性、童话性和游戏性等。浪漫的虚幻、童话的想象和游戏因矛盾而博人无所容心、忘怀得失的一笑,都使作品的形态,与写实有较大距离,呈现一种超现实性。这样,评价体系和创作状态,就有一个较大的自由度。
(一)浪漫性
《西游记》把个性精神隐寓于虚幻、浪漫性之中。《西游记》是一部幻想型的浪漫作品,如言:“《西游》幻极矣。”[5](P324)通过想象和夸张,使得“西游”世界,成为与写实世界迥然不同的突破生死,突破神、人、物界限的神奇世界。其环境是天上地下、仙地佛境、龙宫地府;其形象多是身奇貌异,神通广大,变幻莫测;其物是可大可小的一万三千五百斤的金箍棒、“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得熟”的人参果树和可以闻声拿人的昆仑仙藤上结的紫金红葫芦;故事是上天入地,翻江倒海,兴妖除怪,祭宝斗法等,奇境、奇象、奇物、奇事熔于一炉,构成了一个远离现实的幻想之域。
在这样浪漫的世界中,自由理想是易于充分表现的。法国作家雨果说:“浪漫主义其真正的定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6](P32)在写实环境中,则有较多局限。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乏其例,如元代郑光祖的杂剧《倩女离魂》和明代汤显祖的传奇《牡丹亭》等即是。《牡丹亭》第三十六出《婚走》杜丽娘就说:“秀才,比前不同,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7](P2196)“人物在梦境魂乡时,那一种泼天也似的自由精神便无所不在、无所不为;一旦梦醒还阳,便‘成人不自在’,小姐往往必须遵循人间的礼法,受种种无奈的束缚。”[8](P134-135)
《西游记》个性精神的张扬,是写实性小说在当时条件下做不到的。《金瓶梅》个性的恶劣膨胀不用说,即便是宋江谨小慎微、赎罪式的归正,在写实文学的政治逻辑中没有其适宜的位置。因为浪漫小说与写实小说遵循着不同创作规范。写实小说不论如何奇异,总要遵循现实生活的逻辑。浪漫小说不一样,它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的细节真实。它也要遵循一定的逻辑,不能胡来,但那是幻想的、理想的逻辑。《西游记》幻中之真,不同于生活之“真”,也与写实小说中所表现的“真”不一样。因此,《西游记》取经僧众与《水浒传》相类似的离经叛道,统治者的猜忌和惧怕,还不至于成为影响浪漫作品中人物结局的因素。《西游记》的浪漫性,助成了个性精神的喜剧性结局。
(二)童话性和游戏性
《西游记》将个性精神寄托于童话和游戏笔墨之中。《西游记》又是一部以童话性和游戏性为重要特征的小说。在一种轻松、愉快和玩耍的气氛中,个性精神得以凸显。
想象是童话的重要特征,是一种以具体情境为依据的非逻辑性的想象。《西游记》不少地方,情节和人物特征前后矛盾,就是因为“这种童话的想象方式……是一种非逻辑的关系。……儿童的想象常常只是相对于一个具体的情境而出现的,因此哪怕是对同一个人物的想像,也可能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出现前后不一致甚至完全矛盾的现象”[9](P109)。《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时,除了如来,所有仙圣神佛及其法宝(如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都奈何不了他;而取经路上,几个小妖精,一块破布袱,两只小瓶子,却把他折腾得死去活来。红孩儿的三昧真火,也能把他弄得“一身烟火,炮燥难禁……火气攻心,三魂出舍,可怜气塞胸堂喉舌冷,魂飞魄散丧残生”(第四十一回)等。这种不一致,却是童话的想象和逻辑。面对这种“幼稚”矛盾的故事,读者也只得姑且听之。这样,即使人物做出较为出格的事来,也被蒙上一层童话的色彩,人们也会一笑了之。
《西游记》是儿童式的游戏,同时也是一种与“经国大事”相对的游戏笔墨。这是古今共识。明人陈元之称《西游记》为“滑稽之雄”[5](P225)。鲁迅也说:“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10](P338)所谓游戏性,在《西游记》中,表现为“富有特色的矛盾性:或内容和形式之间的不和谐,或现象和本质之间的不协调,或想象和存在之间的不一致”[3](P260)。不该有人性的妖怪,反而有人情,矛盾成为产生游戏感的心理机制。
第四十二回,写孙悟空向观音菩萨借净瓶,观音要他“脑后救命的毫毛拔一根”作抵押,悟空不肯,观音骂道:“你这猴子!你便一毛也不拔,教我这善财也难舍。”其中“一毛不拔”是顺手点缀的“趣话”。观音尊者的身份,也如常人一般的逗趣。身份与世俗的心性、行为构成引人一笑的错位或矛盾。这间接体现了一种世俗的精神。天宫是神圣庄严的,却让一只极不正经的猴子去捣乱。形象的猥琐,颠覆了天宫的富丽堂皇。对于孙悟空和天宫来说,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都呈现矛盾状态。可笑,好玩,滑稽。一只胡闹的猴子,竟动用了十万天兵天将,却又无计可施。最后立头功者,不是托塔天王、二郎神,而是一条狗。狗在他脚脖上狠咬一口,再加上太上老君不光彩的“暗器”手段,才勉强抓住了孙悟空。可还是不能将其“明正典刑”,天宫却差点儿被烧掉。在一片好玩的笑声中,完成了对个性精神的表现。
在童话和游戏笔墨(包括浪漫作品)特殊的审美氛围中,创作心态是自由的,表现的内容和主题也易形成理想的形态。而且,面对这种姑且言之的游戏故事,读者和评论者也多是姑且听之。陈元之说:“若必以庄雅之言求之,则几乎遗《西游》一书”[5](P225),则是基于《西游记》“此东野语,非君子所志”[5](P225)。胡适说,《西游记》“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必深究。”[11](P366-367)鲁迅也说:“而且叫人看了,无所容心,不像《三国演义》,见刘胜则喜,见曹胜则恨;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鉴赏了——这也是他的本领。”[10](P338)欣赏游戏和童话时,人们是“无所容心”、“不必深究”的,无须以较为现实的标准予以思考和评价。在这种预设式、可期待的赏评方式的逆向作用下,创作也会因此多出一份自由的状态,个性精神的表现又多了一层宽松。作者不必太多顾忌到现实的规则,而能够自由地表现理想化的内容。诚如所言:“《西游记》游戏笔墨的特征……它给作家提供了摆脱世俗的拘谨和因循的束缚的机会,可以并要求天马行空般飞驰自己的想象。而作家的艺术思维既不能以一般事物的通常进程来衡量,他那神奇的笔墨也就像没有任何约束似的在任意抒写,所以,挥洒笔墨的结果,其内容似乎往往越出了常规,而形式常常会是无限的活泼。”[12](P122-128)《西游记》的童话性和游戏性,成为个性精神合“理”存在必要环境。一句话,《西游记》超现实特征,是五圣成真喜剧性结局形成的有利因素。
二、儒、道、佛的既定理路
《西游记》属思想、哲理小说,在明清六大章回小说中,理论色彩是最浓厚的。这势必影响到作者的构思,如人物性格发展的历程和结局的性质等。换言之,儒道释三家思想的逻辑过程和归宿,促成和支持了五圣成真的喜剧性结局。
《西游记》是一部累积型小说,儒、道、佛乃至于民间宗教、迷信、崇拜等,诸家杂陈,应有尽有。其中以儒、道、佛三家思想最为显著。
自《西游记》问世以来,探索其思想性,是研究的重要视角。较为流行的是儒道佛三家合一说。明清之际的袁于令说:“三教已括于一部。”[5](P223)清代刘一明认为读《西游记》“悟之者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5](P342)。现代《西游记》研究,多承此说。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只因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所以释迦,老君,观音,真性、元神之类,无所不有。”[10](P338)古今诸说,三家虽或有主次,但其思想杂陈糅合却一。这些符合《西游记》的实际情况。小说中孙悟空就曾给车迟国国王开过这样的治国良方:“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第四十七回)
小说第八回,观音一路东来,接连给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和小白龙指点迷津,劝其通过修行以成正果,则直接标明了离经叛道者由邪反正的佛、道、儒的既定理路。其中观音与孙悟空的相见,具有典型性:“大圣道:‘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情愿修行。’这才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那菩萨闻得此言,满心欢喜,对大圣道:‘圣经云: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你既有此心,待我到了东土大唐国寻一个取经的人来,教他救你。你可跟他做个徒弟,秉教伽持,入我佛门,再修正果,如何?’大圣声声道:‘愿去,愿去!’”
对于曾经违逆大伦的孙悟空,有善念,有善行,就能修成佛果,是佛家固有理路,也是小说显在的结构。在观音在劝言中,也引用了《周易参同契》中的“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13](P679)之语。意为有善念,天必从之,为五圣成真提供了逻辑理路。《周易参同契》的主旨,诚如所言:“后汉魏公伯阳以为还丹之道不可惑于邪说,必本诸《易》道然后可也。”(《四库全书·周易参同契发挥重刊序》)《周易》为儒家“五经”之一,又是道家“三玄”之一,为儒道共有的经典。《周易参同契》本诸《周易》,讲道教“还丹之道”,是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的道教论丹典籍。道教观念,在《西游记》中,比比皆是。不仅人可以成仙,修炼到家的动植物也可以成仙,甚至石头承受日月精华也可以成仙。这对五圣成真是一种理念上的支持。
儒家心学在《西游记》中表现尤为显著,在回目、诗赞、人物语言和结构等方面多有表现。第二十四回唐僧问孙悟空何时可到西天雷音寺,孙悟空答道:“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第五十八回孙悟空用乌巢禅师的《多心经》提醒唐僧道:“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
以孙悟空而言,全书内容的构架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压在五行山下;西天取经成正果。可依次隐喻为放心、定心、修心的心学理路。这种喻意在小说中多有提示,如在前七回,孙悟空上天入地大闹乾坤,即在回目上说他是“心何足”、“意未宁”(第四回);第七回被压在五行山下,就叫作“定心猿”;后来去西天取经,则常称作“心猿归正”(第十四回)等。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它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淛说的‘《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10](P338-339)
心学不仅提供了由心魔进入道境的理路,更重要的是,心学还提供了未被炼尽的心魔,在道境中取得合法地位的逻辑可能。这近于王学左派的思想。何心隐说:“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适,性也。”[14](P40)王守仁的先天“良知”,被加入声色情欲,以及百姓日用,本能被纳入“性”——道的范畴之中。《西游记》作者的构思与创作,应和了心学的逻辑。
作品的理论色彩与创作自由精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游记》作为理论色彩强烈的作品,与现实的关系,如果比作学术与现实关系的话,那么《水浒传》、《金瓶梅》等写实性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则可比作政治与现实的关系。虽然学术的内容、形式和规范等最终来源于现实,但毕竟比政治来得间接,因而,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必如政治亦步亦趋地紧跟现实。
同是离经叛道的宋江们,其人生历程与取经僧众较为相似。但由于其缺少诸家思想资源戮力而直接的支持,也即宋江们更多是生活在现实形态的社会之中。虽也有忠义儒家理论的支撑,但其突出性,显然逊于《西游记》。宋江们在走向圆满结局的当口,宿命般遭遇到了奸臣的不忿、惧怕和猜忌,结果归于悲剧。
朝廷对梁山的招安,是在无力剿灭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并非是在遵循某种有别于政治逻辑的理论理路。在奸臣与宋江私怨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政治逻辑上的排斥。这一点典型表现在宋徽宗身上。宋徽宗原是真心接纳反正者的,但也心存猜忌。“蔡京、童贯又奏道:‘卢俊义是一猛兽,未保其心。倘若惊动了他,必致走透,深为未便。今后难以收捕。只可赚来京师,陛下亲赐御膳御酒,将圣言抚谕之,窥其虚实动静。若无,不必究问。亦显陛下不负功臣之念。’上皇准奏。”[15](P914)《水浒传》是现实形态的小说,人物命运主要遵循现实的政治逻辑,而《西游记》遵循的是理论逻辑或者理想逻辑。
所以,五圣成真的喜剧结局,小说浓重的理论色彩及其逻辑理路,是一重要因素。
三、社会与道德的价值取向
小说《西游记》的审美价值结构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一方面是远离现实的超现实性和理论性,一方面又植根现实,秉持社会与道德价值取向,有显著的世俗性。诚如所言:“《西游记》则不同,它幻想的翅膀飞得高,而现实基础又扎得深。”[3](P314)现实与超越,犹如深厚地基与摩天大厦,呈现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个性精神、主体意识因此有坚厚的基础,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取经事业社会价值的取向和人物行为社会道德底线的设置。
西天取经,是佛教行为,又是救民水火、造福人类的社会行为,体现了俗世价值。个性精神因伴有社会性的内容,而易于为人们和社会所接受。这是个性精神最终胜利的必要保证。
三藏是取经队伍的灵魂。他的追求就是团体的目标。三藏是小说《西游记》中社会价值追求的一种象征。因为“那南赡部州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所以,如来让他去西天取经,“劝人为善”(第八回),是以达到普度众生为目的的。同时,三藏取经又是秉承李世民的旨意,以“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唐僧的决心是:“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第十二回)因此,其取经,又与儒家所追求的“平天下”,谋求社稷黎民福祉的目标相一致。这样,社会性成为个性精神的一种依托或调剂。
取经僧众的个性精神,还有一个为世俗所容纳的道德底线。《金瓶梅》和《西游记》,都有宣扬世俗人情的倾向。《金瓶梅》的写成期,是在较《西游记》思想更为自由的万历年间,人物结局却以悲剧作结。《西游记》虽写世情,反对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但同时又严守世俗道德的底线,反对纵欲邪淫,表现出健康文明的情欲观。唐僧取经途中虽有多次艳遇,却始终没有破戒。面对色诱,心里虽不免悸乱,但在行为上,尚属坐怀不乱的君子。八戒的色情心,诚然一路走来,未见泯灭。但始终只表现为一种本能,一种意念。“实际上他对两性问题倒是比较严肃的,负责的。”[2](P54)这与其前的《西游记》杂剧形成对比。杂剧中的猪八戒在女儿国与宫女偷欢,而小说《西游记》中进入佛门的猪八戒始终没有破过色戒。
小说《西游记》作者,一再提醒和警告人们要静心养德,不宜纵情贪欢。第二十三回说:“痴愚不识本原由,色剑伤身暗自休。”二十四回说:“色乃伤身之剑,贪之必定遭殃。”宋元以来,市井小说往往有道德规劝一类的文字,但是有意或无意,效果或目的多类似汉大赋的“劝百而讽一”,言行不一,至多是一种调剂、平衡。《西游记》与之不同,是言行一致的。看作者对情节的处理。八戒恨不得一夜做了三女之夫。结果被“绷在树上,声声叫喊,痛苦难禁”(第二十四回)。八戒于濯垢泉一顿忘形之后,却遭罹一番磨难:“原来放了绊脚索,满地都是丝绳,动动脚,跌个禋踵:左边去,一个面磕地;右边去,一个倒栽葱;急转身,又跌了个嘴躭地;忙爬起,又跌了个竖蜻蜓。也不知跌了多少跟头,把个呆子跌得身麻脚软,头晕眼花,爬也爬不动,只睡在地下呻吟。”(第七十二回)这样,《西游记》就摆脱了《金瓶梅》西门庆之流决海救焚、饮鸩止渴式的个性主义的恶性凸显。在表现个性精神的同时,又不至于触及社会道德的底线。这是五圣得以成真的世俗条件。
总之,《西游记》是个性精神胜利的赞歌。作品的超现实性、理论色彩,使个性精神得以较为充分的张扬,而世俗性又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便是《西游记》喜剧性结局的文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