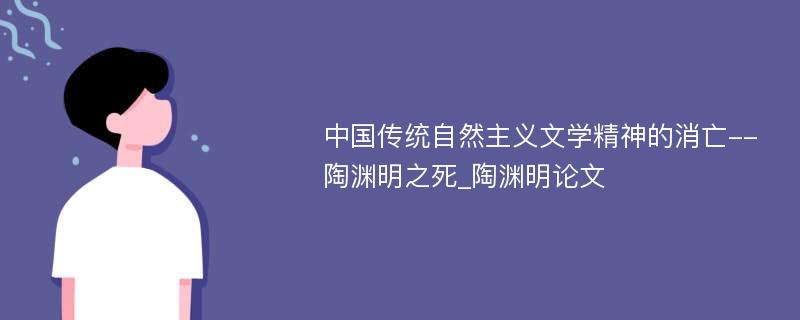
中国传统自然主义文学精神的消亡——从陶渊明之死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主义论文,中国传统论文,之死论文,陶渊明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1-0156-09
什么是陶渊明的文学精神?
晚年的梁启超在其专著《陶渊明》中,对于陶渊明的人品与艺术曾有如下评述:“渊明何以能够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文艺?一定有他整个的人生观在背后。他的人生观是什么呢?可以拿两个字来概括他:‘自然’。”“他并不是因为隐逸高尚有什么好处才如此做,只是顺着自己本性的自然。‘自然’是他理想的天国,凡有丝毫矫揉造作,都认作自然之敌,绝对排除。他做人很下艰苦功夫,目的不外保全他的‘自然’。他的文艺只是‘自然’的体现,所以‘容华不御’恰好和‘自然之美’同化。”[1]26这一段话中,梁任公竟一连用了七个“自然”,表达他对陶渊明“自然精神”不容置疑的肯定。
陈寅恪在1945年发表的一篇专论《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同样用了一连串的“自然”概括陶渊明的文学创作精神,并将其上升为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的“新自然主义”:“新自然主义之要旨在委运任化。夫运化亦自然也,既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为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如主旧自然说者之所为也。”“渊明虽异于嵇、阮之旧自然说,但仍不离自然主义。”陈寅恪因此认定,陶渊明不仅是一个“品节居古今第一流”的文学家,而且也是“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2]225。
两位近现代学术大师都把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看做陶渊明安身立命的根基、文学精神的核心,应当说大抵符合陶渊明其人、其文的实绩。
然而,在一部中国文学史中“自然”的观念与价值并非始终如一,随着“自然”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演替,关于诗人陶渊明的阐释评述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早先,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将中国文学史中“自然主题”的兴衰划分为“混沌”、“谐振”、“旁落”、“凋敝”几个阶段,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唐宋文学中得到高度的推重与成熟的表现;明清之际则开始旁落;进入20世纪之后,在现代中国,“当‘自然’成了‘进军’和‘挑战’的对象时,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自然’,甚至连‘配角’也当不上了,常常只能充当‘反面角色’”[3]。对照陶渊明的接受史,我惊异地发现,关于陶渊明文学地位与价值的评判,竟也与此息息相关:唐宋时期攀至顶峰;元代之后、明清以降逐渐旁落;延至现代当代几近名存实亡。目前已有的两部陶渊明接受史专著,仅只论及元代之前;[4]胡不归先生的《读陶渊明集札记》下篇“陶诗对后世之影响”带有接受史研究的性质,也只是到宋代为止。而在我看来,诗人陶渊明在元明清之后,尤其在现当代的处境际遇更为复杂曲折,也更具现实意义。
(一)
相对于唐宋时代关于陶渊明的评价,明清时期虽亦不乏赞誉推崇之辞,但重心已发生了明显的“位移”。概括地说,即由“自然”移向“世事”。由前人推崇的自然主义哲学精神偏向忠君不二的政治道德与经国济世的社会伦理。这固然与明清各时代诗歌整体的萎缩有关,更与时代价值观念的变迁、审美偏爱的走向有关。
按照通常的说法,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在唐宋达到鼎盛,从明代就开始受到新的经济形态的冲击,主要是城市商品经济的冲击,从而使社会结构、文化心态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内一些史学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发,认为从明代开始,中国社会内部已开始孕育出自身的“资本主义萌芽”。余英时先生并不同意这一判断,但也认为由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中国社会的内部变革,早在明清时代就以“渐变”的形态开始了,其在思想文化界的表现就是“15、16世纪儒学的移形转步”[5]189,在知识界则具体表现为文人的“弃儒就贾”,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民众的“崇奢避俭”,有些像今日的“文人经商”与“大众消费”了。余英时列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证实明代中期山西、安徽、江苏一带的商人已经达到相当的数量,其中一部分是儒生兼营的,一部分是商贾发财后又以数量不等的金钱购置了“监生”、“贡生”等“学历学位”加入儒者行列的,这在晚明时代的《三言》、《二拍》中均有精彩的表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元典精神已基本瓦解,义与利已经“合而相成,通为一脉”了。[5]219
与商业活动的扩展互为因果的,便是人们对财富、舒适、享乐的追求不但成为合理的,也成为必须的。余英时书中列举了明代学者陆揖(1515—1552)撰著的一篇反对节俭、鼓倡奢费的文章,该文认为奢可以刺激生产、扩大就业,从国计民生角度、从发展社会经济意义上肯定“奢侈”的重要性。“俭”与“奢”的道德意味被大大削弱,现代社会的“经济效益”理论在明代开始已被用来为“奢侈消费”正名。[5]221至于陶渊明身体力行的“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富贵非吾愿”、“转欲志长耕”的清贫自守志向已经不再受到社会的鼓励。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发出:“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的批评话语,也已经难以在此时的社会舆论中获得共鸣。宗白华先生曾经屡屡以渊明诗意为证:“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6]183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对于自然、对于友谊、对于哲理的探求全都一往情深,从内到外,无论生活上、人格上都表现出自然主义的精神。而明清以来日渐炽盛的“崇奢避俭”的物欲心态,必然壅塞了人们对于外在自然的感悟;而“弃儒就贾”的士林取向,又必然污染了心灵中内在的自然,在这样的社会与时代环境中,与自然同化的陶渊明其诗其文的失落也就无足为怪了。到了清朝末年,士子钱振鍠竟然说:“渊明诗不过百余首,即使其篇篇佳作,亦不得称大家,况美不掩恶,瑕胜于瑜,其中佳作不过二十首耳,然其所为佳者,亦非独得之秘,后人颇能学而似之。”[7]陶渊明作为诗坛“大家”的地位竟也被取缔了,这在以往的时代是从不曾见到的。
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日渐式微且日趋老化的中华民族的文化道统遭遇西方现代社会思潮的猛烈冲击,遭遇西方国家强权政治的严重威胁,古老的中国已经被推上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传统的儒家精神已无力支撑这一残局,传统的道家精神更无法挽回这一颓势。中华民族被推上了这样一种看似尴尬的选择:向自己深恶痛绝的西方学习,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以图自强,从而抗拒西方的入侵。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于此期间轰轰烈烈开展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无不基于这一转向。就社会普遍心理而言,放旷冲淡、归隐田园的素朴人生观就显得更加不合时宜。根据史学界的共识,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中华民族已经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进入“现代”阶段,被纳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西方的启蒙观念、工具理性开始了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这一宏阔过程。
从表面上看,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书写陶渊明的身价地位并未出现戏剧性的大变化,不像“五四”前后的“孔圣人”一下子被列入打倒之列。文学史提到陶渊明时,往往仍旧冠以“伟大诗人”的赞语,但若深入进去看一看,“伟大”的内涵已悄然发生变化,而且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变化愈来愈显著,远不止是余英时先生形容儒家的“移形转步”,陶渊明“形”未变,其内在的精神却被置换了,自东晋南北朝、唐宋以来广泛流布于诗苑文坛的陶渊明的精灵已经散逸,陶渊明的身躯内被注入另外的思想与观念。
在对陶渊明的精神实施改造的过程中,胡适、鲁迅二位新文学运动的先驱曾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胡适的“文学革命”首先是从“诗界”切入的,当然避不开陶渊明。他评诗的标准简单明了:好诗应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在他的半部《白话文学史》中,凡是白话的一律赞赏;凡是文言的,一律贬斥;即使同一个诗人,接近白话的诗就被赞为上品,用事用典的,难以解读的,便斥为败笔。其内在的理论支撑可以概括为“白话体”与“平民性”。平心而论,胡适在这一文学批评标准之下,的确发掘出一批民间的、散佚的、清新质朴的、朗朗上口的好诗,但也拒斥了许多诗意葱茏而用语隐晦的好诗。陶潜是被列为“大诗人”专节论述的,而且评价甚高:“陶潜的诗在六朝文学史上可算得一大革命。他把建安以后的一切辞赋化,骈偶化,古典化的恶习气都扫除的干干净净。他生于民间,做了几次小官,仍旧回到民间……他的环境是产生平民文学的环境;而他的学问思想却又能提高他的作品的意境。故他的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语却都是民间的言语。”[8]95胡适的这番话对陶渊明的推崇不可谓不高,其中不乏恰切肯挚之论,但话语的重心仍十分明显,胡适推重的陶诗“自然”,主要还是陶诗语言风格上的“天然去雕饰”、“轻描淡写,便成佳作”,可以印证其文学革命的理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自然的趋势,就是白话文学的冲动”,陶渊明的出现“足以证明那白话文学的生机是谁也不能长久压抑下去的”[8]96。且不说胡适的这段史述并不周严,因为陶渊明的诗文并不全都质朴如白话,陶的辞赋中也没有完全抛弃骈俪体的意思。更重要的是陶渊明的“自然”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文字与手法上,而是基于他“散淡旷放”、“委运任化”、“心与道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自然主义人生观,而胡适赞颂陶渊明的用意显然并不在这里。胡适所谓陶诗的“自然”,多半停留在文字表达的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上,应是其“科学”、“民主”精神在文学批评中的实践。
较之胡适,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另一位旗手鲁迅关于陶渊明的评论,其影响要复杂、重大得多。
《鲁迅全集》中提到陶渊明的地方有十余处,其中《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隐士》、《“题未定”草》(六)等篇中有较具体的讲述。与胡适相比,鲁迅的这些文章并非专题研究,多与当时的某些情事相关。如“魏晋风度”一文,原本是1927年夏天在国民政府举办的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的讲稿,他自己后来也说“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9]646。其话锋暗中指向国民党统治下的现实生活。《隐士》一文,意在嘲讽林语堂、周作人在《人世间》倡导“悠闲生活”及“闲适格调”小品文,顺手牵来“隐逸之宗”陶渊明借题发挥,杀猴给鸡看。尽管如此,鲁迅关于陶渊明的这些言论并非纯是嬉笑怒骂,仍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了鲁迅对陶渊明的态度。“魏晋风度”一文论及陶渊明处约800余字,其中前半说陶是一位“贫困”、“自然”、“平和”、“平静”的“田园诗人”;后半文字则反过来指出“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他还特别强调:“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10]515-517鲁迅这里对陶渊明所做的品评,虽没有什么突破性的创见,也大体符合陶渊明生平的实际状态。只不过他在这里着重强化的是陶渊明并未忘情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面,为后人寻此路径阐释陶渊明预留一片空间。到了《隐士》篇,由于索性把陶渊明与当时的论敌“隐君子”林语堂们捆绑在了一起,那用语就尖刻得多了:先是说“赫赫有名的大隐”陶渊明有家奴为他种地、经商,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接着又讲“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假使无法噉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11]223-224。他还又引出唐末诗人左偃的诗句“谋隐谋官两无成”[11]224,来拆穿隐士们的虚伪与奸巧。明眼人完全可以看出,后边的发挥已经不再指称陶渊明,而是针对“当代隐士”林语堂、周作人们的(至于林、周是否这样的人,则另当别论)。尽管如此,鲁迅对包括陶渊明在内的“归隐之道”的怀疑与不信任还应是真实的。
至于《“题未定”草》中论及陶渊明的文字,同为论战旁及。这次论战的对象除了林语堂,还有梁实秋、施蛰存、朱光潜。起因是施蛰存批评鲁迅《集外集》的文章应有取舍,不必全录。而鲁迅则认为要看清一个作家的真实面貌就不能看选本,更不能看摘句,一定要顾及整体,于是就举出陶渊明的例子,认为以往的选家由于多录取《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陶渊明在后人的心目中就成了飘逸的象征。“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11]422这里鲁迅强调的是论人要全面,不可偏执一端,虽然不免情绪化,仍可言之成理。《“题未定”草》之七是反驳朱光潜所说“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对此深为不满,不但花费许多笔墨重申了要顾及全文、全人的道理,最后他还申明了这样的结论:“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是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11]430如作为论战文字,鲁迅以陶为例阐发自己的观点,亦无可厚非;当然对方也可以说出“选本”与“摘句”的许多必要来。问题在于,鲁迅强调陶渊明的“金刚怒目式”,竟至得出陶渊明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才伟大的结论。虽然这一结论的得出有着与梁实秋、朱光潜论辩的具体语境,但给人的印象却是:鲁迅推崇的陶渊明是一名“金刚怒目式”的斗士。如果作为鲁迅一己的偏爱,别人仍无权提出异议;但假如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判断,别人或许可以质疑:陶渊明的伟大以及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究竟是因其关心政治的斗争意志,还是散淡放旷、委任运化的自然精神?而这个问题,恐怕是早有定论,假如一定要做翻案的文章,未必能有更多的空间。一个失败的例子是日本当代学者冈村繁,在《陶渊明李白新论》一书中,他强调他对于陶渊明的研究是沿着鲁迅指引的方向开展的,决心要挖掘出陶渊明“和旧说不同”的一面。令人深为遗憾的是,他在“从根本上”“重新审视”陶渊明之后,便不能不跌入“斗士”、“隐士”两极对立的逻辑陷阱,结果发掘出的竟是“深深蕴藏于陶渊明之后的,也可以说是人的某种魔性似的奸巧、任性、功利欲和欺瞒等特点”[12]34。他自谓看到了陶渊明这轮被人们美化、幻化了的月亮的另一面,与实际“全然相反”的真实的一面,“那里只不过是由岩石、砂土等构成的一片干燥无味的世界罢了”[12]127-128。被中国诗界历来崇仰的陶渊明成了一个“疏懒”、“怯懦”、“苟且求生”、“虚伪”、“世俗”、“卑躬屈膝”、“厚颜无耻”、“内心布满阴翳”的复杂人物。
冈村繁虽然明确强调自己的研究是沿着鲁迅指引的道路进行的,但我并不认为最终得出的这些“卑污”的结论应由鲁迅负责。我想,如果鲁迅在世,也不会同意冈村繁的这些论断。鲁迅之所以对陶渊明做出与众不同的评价,除了论战时的一时之需外,也是他个人心性的映射。鲁迅自己作为一位一贯主张“痛打落水狗”、“费厄泼赖应当缓行”的“猛士”与“斗士”,自然会更欣赏陶渊明的反叛性与斗争性,且无意间又将其夸张、放大许多。
如果往深处探究,我想,《鲁迅全集》中留下的那些论及陶渊明的言论,也许还和鲁迅自己当时的处境有关。从1912年到1926年十多年的时间,鲁迅一直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僉事”一职,1922年底至1931年底,又曾受聘于半官方的国民政府大学院任撰述员。为此,他曾受到对立派如陈西滢、林语堂们的猛烈攻讦。陈西滢曾发表文章讽刺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永彝’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13]3平心而论,鲁迅担任这些“官职”时曾为国民的文化生活做过不少有益的事,如普及艺术教育、清查图书、筹建图书博物馆等;但官差不自由,有时也不得不委曲自己参与一些并非本心所愿的官场应酬,如由国民政府举办的“祭孔大典”。[13]230-231鲁迅自己解释说,做官只不过是谋个饭碗,“目的在弄几文俸钱,因为我祖宗没有遗产,老婆没有奁田,文章又不值钱,只好以此暂且糊口”[10]228。针对陈西滢的文章中嘲讽的“在‘衙门’里吃官饭”,于是便有了前文提到的鲁迅所说的陶渊明的“闲暇”是因为“他有奴子”,做官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的议论,其中未必没有为自己辩诬的意气。鲁迅在教育部任僉事一职的薪俸是每月大洋三百元,对于鲁迅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家庭收入来源(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每月收入为八元)。鲁迅没有学习陶渊明,放弃这几斗官俸也无可厚非,历史上许多“诗人”同时也是“官人”,如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并不都要像陶渊明那样决绝地辞官种地。此时鲁迅若是再去赞颂陶渊明的“辞官归隐”、“不为五斗米折腰”,那反倒不正常了。可以作为参照的是,这一时期的鲁迅受到论敌攻讦的,还有他与女学生许广平的恋爱。鲁迅在论及陶渊明的《闲情赋》时,却并不否定陶渊明恋爱的狂态,甚至还特别为之开脱地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由此看来,鲁迅评价陶渊明的文字多与当时文坛论战的具体语境有关,也有鲁迅自己个性上的偏爱,并不是对于陶渊明的全面论述,甚至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判断。
(二)
可能是因为胡适、鲁迅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拥有的至高无上地位,也许还由于时代精神已开始为陶渊明铺设别样的色彩,所以从“五四”以后,胡适的“白话体”、“平民性”,鲁迅的“反叛性”、“斗争性”、“金刚怒目式”便成了评价陶渊明的基调。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替以后,鲁迅固不必说,即使作为政治营垒中的敌人的胡适,其对于陶渊明的评价实际上依然在大学的教科书中延续下来,并成为评价陶渊明的主要尺度。胡适与鲁迅的评价,上承明清以来经世致用的儒学,下启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阶级斗争文艺方针,加上胡适个人的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哲学、鲁迅永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文学研究界已经另立炉灶,为古人陶渊明灌注更多的现代理念。
完稿于1952年秋季的李长之先生的《陶渊明传论》为此率先做出贡献。作者在“自序”中表示,要从政治态度与思想倾向上对陶渊明进行新的阐释,落实鲁迅先生的夙愿,得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14]1。作者在阐释过程中一再摒弃青少年时代读陶时获得的真率的感性体验,而希望运用阶级的眼光、政治的眼光对陶渊明其人、其文做出理智的剖析,更由于坚执“和旧说不同”的先入之见,结果便真的塑造出一位新式陶渊明:就“人民性”而言,他虽然出身于没落仕宦家庭,曾经过着地主的享乐生活,后来由于家道败落,开始参加劳动,接触劳动人民,缩短了与劳动人民的距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在中国所有的诗人中,像他这样体会劳动,在劳动中实践的人,还不容易找出第二人。因此,他终于是杰出的,伟大的了”[14]129。在这篇仅仅六万余字的论著中,作者还花费大量的笔墨铺陈东晋、刘宋之际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而把陶渊明看做一位始终念念不忘政治斗争的孔门仕人,他的退隐只是出于“赌气”,出于“无奈”,并非“‘乐夫天命复奚疑’那样单纯”[14]69。他的沉默,不过是与政治的对抗;他的超然,不过是对现实的否定。由于受到“鲁迅的启发”,并且为了落实“鲁迅的指示”,证明“陶渊明是非常关怀当时的现实,而有战斗性”,作者甚至还从陶渊明那位身份不甚确定的曾祖陶侃那里,寻觅到陶氏家族凶暴善战的“溪人”(即“巴蜀蛮獠谿俚楚越”的谿族)血统;《桃花源记》中“秋熟靡王税”的诗句,也被认作“随闯王,不纳粮”的“同义语”。[14]138这实际上比之鲁迅已经走得更远了,还应当说正是那一时期的政治氛围左右了《陶渊明传论》一书作者的学术考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由学生与教师共同组成编委会)编著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于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次年修订再版,书中对于陶渊明的评价集中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主流意识形态。该书对陶渊明单独开列一章:“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对其多有正面评价,但“伟大”的内涵已不同于梁启超、陈寅恪当年的品评,而在于他自幼怀有济苍生的壮志,不肯屈服于黑暗势力,毅然与统治者决裂,回归陇亩,亲自参加劳动,接近下层农民,体验到劳动的重要性与民间疾苦;在于他以“金刚怒目式”的姿态、慷慨激昂的情绪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表现了坚贞不屈的精神;在于他作品的艺术风格多采用“白描的手法和朴实的语言”,自然质直、明白如话,反对选择惊奇的辞藻或雕镂奇特的形象。该书同时又对陶渊明思想中“消极落后”的东西进行了批判,批判的矛头不但指向“安贫乐道”的儒家思想,尤其集中指向他“与世无争”、“逃避现实”、“自我麻醉”、“借酒浇愁”、“屈服命运”、“放弃斗争”、“随顺自然,委运任化”的道家思想。
该书虽是“大跃进”年头北大文学系师生的急就章,书中评价陶渊明的模式却是早已制定了的,并在此前此后的文学教科书中渐次固定下来。如果非要细分,1949年前的文学史著中多突出陶渊明在“文体革命”方面的价值,如刘大杰撰写于1939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指出的:“陶渊明的作品,在作风上,是承受着魏晋一派的浪漫主义,但在表现上,他却是带着革命的态度而出现的。他洗净了潘、陆诸人的骈词俪句的恶习而返于自然平淡,又弃去了阮籍、郭璞们那种满纸仙人高士的歌颂眷恋,而叙述日常的琐事人情。在两晋的诗人里,只有左思的作风和他的稍稍有些相像。”[15]140这里关于两晋诗人的品评并不那么公允,其主旨无疑是沿袭胡适《白话文学史》的主调写下来的。而1949年之后的文学史著,如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则强化了阶级性、政治性的内容,其中往往少不了援引鲁迅关于“金刚怒目式”的说法。即便在刘大杰后来修订再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也增补进鲁迅关于“猛志固常在”的语录。反叛性、斗争性成了陶渊明精神的正面评价,而反叛性不足、斗争性不强成了陶渊明精神的负面评价。这一单纯从政治性、阶级性出发的评价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即使学力过人、涵养深厚且对陶渊明怀有诚挚感情的学者如逯钦立先生,也未能抵挡住“时代浪潮的冲击”。他在去世前留下的遗文《关于陶渊明》中,从退隐归田,到安贫嗜酒,从“游斜川”到“桃花源”,几乎全盘予以否定,文章中自然少不了反复引用鲁迅的话。这或许可以看做一个特殊时期对陶渊明进行政治性、阶级性、斗争性评论的极端例证。
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一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面世。单就陶渊明的评述而言,该书基本上是选用了余冠英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84年修订本的内容,单独列章,标题没有使用“伟大”的字眼,而是“田园诗人陶渊明”,对于陶渊明诗文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对其后世产生的影响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而且用语平和稳健,体现出学术大家的风范。但在对于陶渊明的基本评价上,仍然没有超越“五四”以来启蒙理念与革命政治的约束,思想方面尽量突出其对普通劳动人民的亲近、对于黑暗统治势力的拒斥与反抗及“有志难展、壮怀不已”的矛盾心态。艺术上则赞赏其朴素、自然、简洁、“全无半点斧凿痕迹”的创作风格。而“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则为陶渊明“消极思想”的表现,属于“陶诗的糟粕”。该书对陶渊明的评价,一洗多年来极“左”思潮强加于陶渊明身上的卑污之辞,起到了“拨乱反正”的效果。但这个“正”,仍不过是“五四”以来学界的通识,仍运行在由现代理性规约的文学河道中。
(三)
陶渊明何年出生,众说纷纭,至于陶渊明的卒年,几乎没有异议,《晋书》、《南史》、《宋书》都有明确的记载,确切地说是刘宋王朝的元嘉四年十一月,即公元427年冬天,距今已1584年。但此后千余年以来,由陶渊明的诗歌和人格所彰显的任真率性、放旷冲澹、任化委运、清贫高洁、孑世独立的自然精神始终如和风细雨滋养着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陶渊明并未死去,他的精神依然活着,甚至作为他的生命升华物的诗歌和文章仍然活着。
本文所说的“陶渊明之死”,该是诗人的第二次死亡。即不但肉体消失,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以及作为他思想象征的诗歌与文章也已经在现实世界中渐渐消泯。比起陶渊明一千多年前的那次死亡,他的这一次死亡,才是真正的死亡。
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陶渊明的研究虽然还在文学史的书写与学术会议的讨论中继续展开,甚至不乏貌似轰轰烈烈的场面,但是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包括现实文学创作界,陶渊明的身影却在不断淡化。即使偶尔登台露面,却又往往形象不佳,或灰头土脸,或下场悲惨。在我的记忆里,印象较深的就有这么两次。
一是1959年7月,共和国最高领袖毛泽东主席在《七律·登庐山》一诗中写到陶渊明:“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据臧克家、周振甫对于该诗作出的权威解释:“陶渊明已经过去了,在当时他可以到桃花源里耕田吗?不行,因为那是空想。今天中国的农村跟桃花源不同,今天的知识分子自然也跟(古代知识分子)陶渊明不同了。”[16]37照此说,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诗不但没有肯定陶渊明和桃花源的意思,反而认为陶渊明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可资佐证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陈晋先生在他不久前出版的《读毛泽东札记》一书中披露,毛泽东曾向他的文学侍读芦荻表示过对陶渊明的不满:“即使真隐了,也不值得提倡。像陶渊明,就过分抬高了他的退隐。”陈晋对此的解读是:“在历代社会,读书人不是总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吗?结果你却躬耕南亩,把说说而已的事情当了真,白白浪费了教育资源不说,忘却了自己更大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实在是有违于士子们的共识。再说了,如果真的像老、庄宣扬的那样,全社会都绝圣弃智,有文化有知识的人都陶然自乐于山野之间,文明的脚步还怎样向前?”[17]86与《七律·登庐山》一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主席于前五日(1959年6月26日)写下的《七律·到韶山》:“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诗句对人民公社给予高度赞誉。在后来毛泽东写给《诗刊》的信中,进一步坦诚地挑明了他写作这两首诗的心态与动机:“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这两首诗,也算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18]488-499在毛泽东主席的心目中,陶渊明大约也是一位“右倾”分子。或许还要更差,据朱向前先生主编的《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中披露:“毛泽东的原稿为‘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后改为‘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19]294改前的诗句显然流露出毛泽东对陶渊明更大的不满。从1957年开始,中国上下全都处于“反右派”、“反右倾”、“反保守”、“反倒退”、“反‘反冒进’”、“反厚古薄今”的政治风潮中,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更多人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贬职、罢官、劳教、流放、监禁。此时的陶渊明被划为“不向前”的右倾保守之列,恐已不仅仅是一个诗意的戏谑了。
接下来,在20世纪60年代围绕着陶渊明发生的一件“文学政治”的事件,就更加悲惨了。
事件源于陈翔鹤的一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四川重庆人,生于1901年,20世纪20年代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并与杨晦、冯至等人创办沉钟社,编辑出版《沉钟》半月刊。此人性情率真内向,喜欢养花,尤喜兰花,崇尚陶渊明,是共产党内一位有自己个性的文化人。《陶渊明写挽歌》是他发表在《人民文学》1961年第11期上的一篇短篇小说,问世后颇得圈子中友人的好评。以现在的目光看,这篇小说写得风致有趣、舒卷自如,有30年代文坛遗韵,深得陶渊明精神之况味:旷达中游移着丝丝感伤,愤世中又不乏旷达的自我解脱。小说写元嘉四年秋日,陶渊明上庐山东林寺见慧远和尚不欢而返,步行20里下山后一夜未能安眠。次日在与家人的闲谈中,论及佛门名僧慧远的矫情迎俗,达官贵人王弘、檀道济之辈的骄横跋扈,友人颜延之的患得患失,名士刘遗民、周续之的浅薄平庸,同时也表露了对新上台的皇帝刘裕的蔑视与憎恶,对前贤阮籍高风亮节的认同。陈翔鹤以其厚积薄发的文学才情,在不大的篇幅里全面展现了中国天才诗人陶渊明伟大的精神内涵:坚守率真自然,厌恶矫情作势;拒斥权力诱惑,保持人格独立;超然对待现实,旷达直面生死;不肯附和时代潮流,甘愿固穷守节、困顿终生。小说在颂扬陶渊明清贫自守的高风亮节、淡泊高远的人生志向的同时,也流露出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屡受强权整肃与政治迫害的抑郁心态,以及回归自然、从文学创作中寻求自我解脱的意向。《陶渊明写挽歌》如实表达了新中国如陈翔鹤一类知识分子从灵魂深处对陶渊明的认同,这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界,是颇为罕见的,应看做陶渊明精魂不泯的一线生机。
然而,这一线生机很快就被扼杀了。
从1964年开始,权力高层组织了对于《陶渊明写挽歌》的严厉批判,认定这是一篇“有害无益”的小说,充满了“阴暗消极的情绪”,“宣扬了灰色的人生观”,是“没落阶级的哀鸣与梦呓”。这里的“阴暗”、“消极”、“灰色”、“没落”,不仅指向小说家的创作心态,完全可以看做对诗人陶渊明的定性。当时文坛的绝对权威姚文元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指责:某些共产党员不想革命,却神往陶渊明的生活情趣。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有人将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与“庐山会议”放在一起(那也正是毛泽东主席写作《七律·登庐山》的写作背景),宣布《陶渊明写挽歌》是“为一切被打倒的反动阶级鸣冤叫屈,鼓动他们起来反抗的‘战歌’”,是“射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毒箭”。小说作者陈翔鹤因此受到残酷的迫害,于1969年4月22日下午死于接受批斗的路上。《陶渊明写挽歌》竟成了小说家为自己写下的“挽歌”!
(四)
“文革”结束后,“陶渊明研究”与其他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一样,一度出现活跃局面,并最终推出像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龚斌的《陶渊明传论》、胡不归的《读陶渊明集札记》以及关于陶渊明接受史研究的一些颇有分量的学术成果。然而,却难以挽回陶渊明精神渐趋消亡的时代命运。
中国诗人陶渊明在新旧世纪之交再次遇到严重挑战,这次的对手并不在学术界,甚至也不在政治界,而在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即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硬道理,市场经济、消费文化迅速占据了人们的公共空间乃至私人空间。“平面化”、“齐一化”的货币特性变成“现代社会的语法形式”,国内生产总值(GDP)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最高统帅,国人的注意力全被引向发财致富的金光大道,资本的魔性在我们这块曾经绝对革命化的土地上显得格外张狂。新的价值体系对国家财力的积累颇见成效,而对于高尚生活风格的形成却一无补益。被货币占领的社会生活界变得越来越“非人格”、“无色彩”,个人精神文化中的灵性和理想伴随着自然生态系统的恶化越来越干涸萎缩。面对蜂拥进城的农民工,还能说什么“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面对一脸渴望走进“公务员”考场的大学生、研究生,还能说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即使有人有心回归乡土,当下的中国农村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也已经失去了固有的价值与意义。
以往文学史书写中由胡适与鲁迅为陶渊明定格的“平民性”与“斗争性”,在当下其实也已经遭遇尴尬。“文革”结束以后,国家的决策层不再希望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持续下去,即使社会生活中“斗争”时有发生,也不再把“斗争性”作为每个国民必备的高尚品格,当初为政治服务而代陶渊明强化的“斗争性”已经失去现实的依托。至于胡适强调的“平民性”、“大众化”,情况更要复杂些。当一个社会真正进入现代化轨道之后,“大众化”真正的推手已经不再是文学艺术家,甚至也不再是政界的“英明领袖”,而是由资本与高新技术操纵的市场。在市场经济汹涌澎湃的今天,文化事业正在转型为产业和企业,作为市场精英的资本家完全有办法收买或扼杀那些已经背时倒运的文化精英。面对新世纪的文化市场,我们的伟大诗人陶渊明,也未能逃脱那些商业文化大腕、大鳄们设置下的一个又一个“大众化”陷阱。
到互联网上搜索一下,争先恐后扑进人们“眼球”的更多的“桃花源”,竟是房地产开发商们的广告,开发商们热衷于将自己的楼盘命名为“桃花源”,装扮成人间仙境。这里下载一例,为陶渊明的研究者们长长见识:
豪宅专家营造绝版“桃花源”;面积:963m[2];售价:4 500万元(4 6728元/m[2]);私家花园、室内游泳池、仿古长廊;周边环境:百老汇购物商场、沃尔玛购物超市;贷款总额:31 499 344.8(元);月均还款:193 512.5(元);契税:674 985.96(元);交易印花税:22 499.53(元);超级经纪人专业代理,多套供选,现房诚售!
这样的桃花源,当然已不再是“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桃花源,然而这样的“桃花源”对于现实的中国人却拥有更强烈的吸引力,陶渊明的桃花源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已被成功置换。
如果说陶渊明在后现代的艺术家那里只是被解构,那么,他在当代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那里遭遇到的却是被侵吞,连骨头带肉的一并吞噬。面对中国现实生活中从内到外的各个方面,陶渊明似乎已经整个地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赖以传布百世的自然主义生存理念、文学精神也已经死亡。在21世纪的中国,陶渊明已经完全成为这个时代的局外人,成为被这个时代消解、戏弄、遗弃的人。但也恰恰因为如此,陶渊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他者”,“陶渊明之死”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按照德里达“幽灵学”的说法,陶渊明的这一次死亡,才使他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幽灵”。我们现在重提陶渊明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面对当前人类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方面存在的种种繁难问题,人们能否向一个幽灵求助?德里达在其《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幽灵像是精神,却又不等于精神。或许可以把幽灵叫做“精神中的精神”,这是一种游移不定、绵延不绝、无孔不入的精神遗存。世界本身的现象兴衰史就是幽灵式的。“幽灵不仅是精神的肉体显圣,是它的现象躯体,它的堕落的和有罪的躯体,而且也是对一种救赎,以及——又一次——一种精神焦虑的和怀念式的等待。”[20]91用德里达的话说,幽灵具有“不可抵挡的作用力”和“原生力量”。[20]206幽灵似乎也成为“纵浪大化中”的一个精灵,成为“一个永远也不会死亡的鬼魂,一个总要到来或复活的鬼魂”[20]141。任何试图彻底清除它的举动,都只会让他以游魂的形式重新返回。德里达的“幽灵学”用语艰涩深奥,以我的肤浅理解,他的用意在于以他的幽灵说更好地解释精神现象,包括精神的流布与效应。从哲学的意义上讲,德里达认为他的幽灵说,已经将我们引向一个对于超越于二元逻辑或辩证逻辑之外的事件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讲,超越也是救赎,幽灵更由于拥有这种原生的与再生的力量,也就具备了参与救赎(非基督教的)的潜在能量。继海德格尔的诗性拯救之后,在德里达的幽灵学中,“幽灵”被再度赋予拯救艰难时世的力量。
传统中那些属于精神文化领域的东西是不会轻易被取缔的。当现实社会的滚滚红尘、滔滔洪水漫过人类的精神原野时,那些隐匿在人类思想与情感幽深处的精灵并不会全部席卷而去,它们还会守候在某些深潭、深渊中,游荡在某些山峦、林木间,会飘散在月光下,清风中,云里,雾里,文学评论的任务就是要寻觅并召回这些幽灵,让其在新的时代境遇中显灵、显圣,为人类社会调阴阳、正乾坤,让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品物咸亨、万国咸宁、逢凶化吉、共享太平。
收稿日期:2011-0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