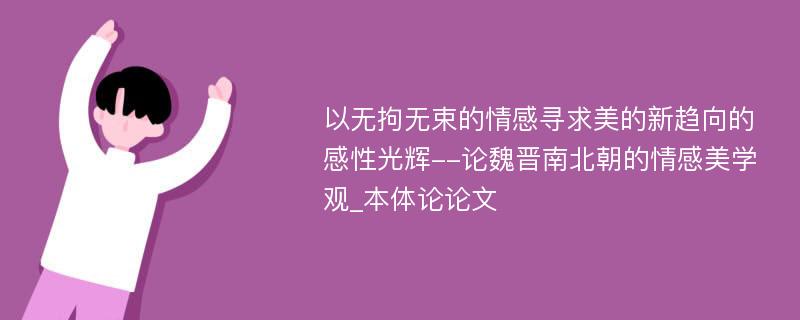
畅情求美新潮的感性光辉——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情感美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潮论文,美学论文,感性论文,光辉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0)02-0047-08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美学基本上是从本体论和审美学的角度来探讨情感问题的。这一时期的情感美学观主要是陆机的“缘情绮靡”说、三萧的“吟咏情性”说、刘勰的“理融情畅”说和钟嵘的“托诗以怨”说,共同构成内向化的畅情求美的时代美学思潮。
一 从曹丕的文情欲丽思想到陆机的“缘情绮靡”说
曹丕的文情欲丽思想包括两个互相关联的观念。他在《典论·论文》中首先明确提出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文气说是曹丕自觉地从文艺本体论角度来探讨艺术情感的。曹丕的文气论渊源于先秦以来哲学方面的元气论和美学方面的“乐气”说。从美学方面来看,《乐记》把“气”与音乐创造联系起来而提出“乐气”说,“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礼记·乐情》认为诗、乐、舞“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英华发外”。“情深”、“气盛”而外化为文(音乐韵律形式),“情”与“气”分列对举而为同一层次概念(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产之语:“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这里所指“好恶喜怒哀乐”六情生于“六气”,情与气是有着产生与被产生的因果关系的,因而在先秦还不是同一层次概念。)。这里的“乐气”有着情感的性质和审美性特点。曹丕所说的“文气”正是从“乐气”发展而来的,兼具形而上与形而下、抽象与具象的双重性质。从本体上看同为“气”,其体性有清浊之分,本性则自然氤氲。从具体上看“气”指创作主体的天赋个性、气质和才情,如“齐气”、“逸气”、“体气”,等等。从建安文学总体风貌特征来看,是“慷慨以气”(《文心雕龙·明诗》)和“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任气”、“多气”点明“本同”特色和情感激荡的特征。“文气”即是文情,指称文学的情感质素,确认艺术以情感表现为核心,把个体情感视为艺术主体存在,强调个性之情的自由表现。如果说“文气”说是从“本同末异”视界强调个体情感自由表现和辨别作家艺术风格的话,那么“诗赋欲丽”论则是从文体角度指明诗体的艺术形式美。“丽”作为纯粹美是内在情感自由表现的感性形式,“丽”指代艺术形式美规律(注:参详拙文《“丽”:对艺术形式美规律的自觉探索》,载于《文艺研究》1993年第1期。)。 如果把“文以气为主”和“诗赋欲丽”综合观之,则可以认为曹丕提出了文情欲丽的思想观点,致力于把情感美学与形式美学加以关联性思考的尝试。他把秦汉以来传统的艺术情感论和情感节制论(以理制情论)加以离析而弃置情感节制论,把两汉尚丽的形式美学与伦理规范加以分离而摈落伦理规范,把情感论和形式论重新组合,奏响了魏晋南北朝畅情美学的序曲,为陆机的“缘情绮靡”说作好了理论前导。
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美学新论,自觉地从艺术内在规律角度来观审情感与形式的关系。这一方面是对汉代以来正统理论“发乎情,止乎礼义”,“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辩证扬弃和彻底改塑,吸收其“发乎情”、“吟咏情性”的艺术情感论而遗弃其“止乎礼义”、“以风其上”的节制论和美刺讽谕论,也就是抛弃其教化中心主义和狭隘功利主义。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道家纯审美性情感美学观和屈原抒情求美的思想成分,吸收了《淮南子》情文相称的观点和《乐记》重视艺术形式美的思想,在曹丕文情欲丽思想的基础上推出缘情绮靡说,即把情感美学与形式美学圆融地统一起来,创造性地建构了与儒家正统理性美学观发情止礼论相对立的情感美学观,使其作为中国古典情感美学一大理论流派得以确立和形成。所谓“缘情”,是从艺术生成论的角度阐述艺术情感表现论的,强调诗歌因情感激发而创作,这里继承和发展了《乐记·乐本》“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和《毛诗序》“吟咏情性”意旨的。诗缘情的“情”字,虽然主要指情感心理,但并不排斥“志”即心理意向。陆机《文赋》谓“颐情志于坟典”,“情”与“志”是同位同义,都指主体内在情感心理意向而言。“绮靡”是指诗歌形式之美,辞藻美色彩美结构美在整体上给人以美丽动人之感。因此“诗缘情而绮靡”摈弃了“止乎礼义”以理制情的政教功能,强调了诗艺的审美形式化和美感特征,即以诗艺的审美功能取代教化功能,着眼于艺术内在规律,使得文学开始摆脱政教工具性能而具备独立品格,表现了文学的自觉意识,开启了情感的审美形式化和审美形式的情感化相统一的美学方向。因此,“缘情绮靡”说被后世视为一个独树一帜自足完善的纲领性情感理论,对后来情感美学观的发展演变影响深远,以至把缘情绮靡作为诗体的代称和诗评的标准。清代纪昀在《云林诗钞序》中强调发情止礼二者不可偏废,正是竭力维护儒家的政教工具论。他对于缘情绮靡内容本身不持异议,却指出陆机没有兼顾以理节情教化功能而陷入片面,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缘情绮靡”说对发情止礼的历史性扬弃和对文学独立品格的建树性确立。总之,曹丕与陆机将情感美学与形式美学密切结合起来,将情感美学观推进到一个新的认识阶段,开辟了诗歌理论新传统和新价值思维的未来指向,推动了对情感本体和艺术内部规律的深入探寻。
二 三萧的情感美学观——吟咏情性说
萧统、萧纲和萧绎,作为皇室贵族其权力影响和理论倡导举足轻重,左右文坛。他们的美学思想、美学取向和审美情趣代表了齐梁美学主潮。
三萧情感美学观的相同点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物感说的基础上,他们高度重视审美感兴和文学的情感质素。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认为自然景物触动创作主体的感兴和灵感而引起“兴咏”和激发创作欲望,并引述《毛诗序》“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极为重视审美感兴与情感外化的关系,其《答晋安王书》总结为“炎凉始贸,触兴自高,睹物兴情,更向篇什”。萧统将当时抒情体物的诗赋的审美功能概括为“入耳之娱”和“悦目之玩”,获得悦耳悦目悦心悦神的怡情效应。他在《文选序》中进一步将那些抒情性作品在理论上总结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沉思”指深沉的情感感受和独特的情感表现;“翰藻”指相应的艺术形式美,包括文辞、声律、对偶、用典的美感要求。
萧纲以情论文,突出艺术情感的中心地位。其《答张缵谢示集书》所言“沈吟短翰”,“寓目写心”,也是着眼于审美感兴和情感表现的。他在《与湘东王书》中批评当时京都文体背离了诗骚以来“吟咏情性”的优良传统:“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主张抒情写景诗赋之作不应模拟儒家经书的典雅雍容、质朴古奥的语言风格,而应做到情景交融、语言清丽,批评那种以经学论诗写诗的传统倾向。萧纲《答新渝侯和诗书》从文学新变论出发肯定“性情卓绝、新致英奇”的作品,并为抒发男女之情和描写女性美的作品张目。其《诚当阳公大心书》大胆提出情感放荡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即认为以礼义持身不妨碍为文自由放纵情感,这是抒情作品的内在需要。这种情感放荡说一反文学教化论传统观点,力主破除限制情感创造的清规戒律,要求率性而发任情驰聘,自由自在地表现个体的真情实感。这就阐明了艺术表现即情感表现、情感表现即自由表现的理论本质,极大地突出了文学的独特性自由性,具有标新立异的色彩和反传统的意义。萧绎《金楼子·立言》从“内外相感”的主客体关系角度进一步论证物感论,以捣衣情结为例具体阐析:“此是秋士悲于心,捣衣感于外,内外相感,悉情结悲,然后哀怨生焉。”其所谓“吟咏风谣,流连哀思”,是从情感内容美(包括悲怨之情和男女之情等)方面来立论的。其所谓“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则是从艺术形式美(包括文辞、音律、色彩等)方面来立论的。“情灵摇荡”,生动地体现出强烈的抒情性和巨大的感染力量。“吟咏风谣”,鲜明地表达了吸取民间歌谣(如吴声、西曲)艺术特色的创作要求。
第二,三萧都非常注重艺术形式美。萧统在《文选序》中提出编选的审美标准是“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纷呈“翰藻”,高度重视艺术形式美(包括文辞美、声律美、对偶美、用事美等),这既突现出萧统本人的审美趣味,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文坛那种注重藻采的创作风气和社会的尚美求美的世俗风向。但他也反对过分华艳,并未把尚于“翰藻”推向极化。萧纲对于追求形式美有一种理论自觉性,旗帜鲜明地提出讲求“篇什之美”。他特别强调抒情写景作品不可盲目模仿经书的语言风格,指明前者有着特殊的审美要求,讲究“丽辞”、“逸韵”。他评论裴子野有良史之才而无创作妙才,其作品缺乏艺术巧思且语言古质无文,因而“质不宜慕”。其《与湘东王书》认为那些卓有成就的作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标能擅美,各有特色,而且强调动人的情感力量和怡人的形式之美是构成作品永久魅力的两大基本要素。萧绎也十分重视艺术形式之美,所谓“绮縠纷披”,是指辞藻文采之美;“宫征靡曼,唇吻遒会”,则指声律和谐,具有音乐之美。
三萧都有意识地把情感内容和形式之美融合贯通起来,强调两者的内在统一。如萧统要求“沉思”与“翰藻”的统一,萧纲讲求“吟咏情性”与“篇什之美”的一致,萧绎注重“情灵摇荡”与“绮縠纷披”的合一。这种整合性认识和兼顾性思维还表现于语言风格方面。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提出“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的审美要求,注重翰藻文饰又反对过分华艳。萧绎《内典碑林集序》要求“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强调兼顾华丽与质朴、谨严与放纵的双向关系。三萧择取《毛诗序》“吟咏情性”的抒情观点并加以充实发挥,摒落“以风其上”的讽谏目的而以形式之美取而代之,构成情感美学理论的圆融机理和完整要求。三萧把陆机缘情绮靡的理论引向纵深思考,特别是萧纲的情感“放荡”说和“篇什之美”论,更是拓展了缘情绮靡说的力度和深度。萧纲还把情感内容视域从怨情拓展到艳情,并对情感表现的俗化倾向(民间歌谣特点)表现出特别兴趣。虽然萧统《陶渊明集序》重复过“有助于风教”的传统观念,萧纲《昭明太子集序》也讲过“成孝敬于人伦,移风俗于王政”,但这种装点门面的说法实质上并未能屏蔽“吟咏情性”的时代美学主潮和情感内容与形式之美相统一的整体美学趋向。三萧把对情与理关系的认识引渡到对情与形关系的认识,以对形式之美的高扬来取代对伦理理性的认同,在对艺术内部规律的认识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三 刘勰的情理美学观——理融情畅论
刘勰情感美学观的精神实质是理融情畅论。当时的情感生成论到了刘勰手里,对物感说的阐明更加深入和具体、全面。物色相召睹物兴情,所谓“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文心雕龙·诠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深刻揭示了情与物的审美感兴关系。自然物候的各种变化引起创作者“悦豫”、“郁陶”、“阴沉”、“矜肃”等不同的情感反映,由审美感兴而引起创作冲动。他在揭示审美情感发生机制的同时又指明了审美情感的非神秘性和可知性。刘勰情感理论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情感的本体化。刘勰不仅从认识论角度来观照情物关系,而且从本体论角度阐明“情文”观念。他从宇宙生成论角度来观审“情文”,对“情文”进行本体性界定,其“情文”概念则属于本体论范畴。刘勰《文心雕龙》称立文之道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情文、形文和声文共同构成“人文”,而“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文心雕龙·原道》)。情文作为一种本体性概念,具有普遍性根本意义。从广义来看,情文是指人文方面主体参与的一切审美创造;从狭义来看,情文是指审美创造的典型形态——文学作品。这里认证了文艺是情感表现的基本观点。情文为五性的载体,五性即是五情。(注:五性即五情。《大戴礼记·文王官人》释五性为“喜怒欲惧忧”。《文子》称:“昔者中黄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见《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注所引。)。情文概念揭示了文学的根源和本质内容。刘勰的情文观把人的情感作为艺术的内在规定和本体依据,艺术的构成必须以情感为本源和质料。情与文关系是道(本体)与文关系的一种生动体现,超过了质与文、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因而情文含有情感本体化的意义。“辨丽本于情性”,“情者文之经”,情成为立文之“本源”(《文心雕龙·情采》)。“五性发而为辞章”(《文心雕龙·情采》),“情动而辞发”(《文心雕龙·知音》),各种具体情感通过“文”有规律的感性表现构成文学作品。
二是情感的审美形式化。情感的表现必须外化为审美形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引用《易传·系辞上》“圣人之情见乎辞”的经典依据来强调“文辞尽情”,“情动而言形”。文采错杂成文的形式美感可使情感得以充分而生动地表现。他肯定“为情而造文”的创作正路而批评“为文而造情”的不良倾向,前者指“吟咏情性”、“述情必显”,后者指“情为文屈”、“繁采寡情”。总之,刘勰的情文观是以情为本,既要求“体情”、“依情”、“吟咏情性”,又讲求“情采”、“情辞”、“文辞尽情”,反对“情为文屈”,强调情感表现自觉地遵循艺术形式美规律,也就是情感的艺术形式化和艺术形式的情感化的统一。
三是理融情畅论。刘勰不但深入探究了情与物、情与形的关系,而且深入地探究了情与理的关系,提出了理融情畅论。在刘勰那里,“情”、“性”互释,“情”、“志”互文,“情”、“理”互渗。“情性”(或“性情”)、“情志”、“情理”指涉意义趋同。情感不仅与道(本体)相关联,而且与理相联结。如果说“情”是主体之心对道本体的感性体悟,那么“理”则是主体之心对道本体的理性认知。情与理属于同一层次范畴而互融互渗,情中有理的因素,理中有情的因素。从这一意义角度来看,甚至“理”与“辞”的关系可以置换为“情”与“采”的关系。在文学领域,如果说情兼具动力机制、创造机制和中介手段(就接受美学而言)的话,那么理则兼具“义理”(表现内容、创作旨趣),“思理”(艺术构思、艺术想象),“文理”(艺术规范、艺术规律)的功能值。情与理意义交叉而异又相通联。如所谓“情理实劳”,“情理设位”,“隐括情理”,“空引情理”,昭示了情理的同一性。他观审“情”时,在情感内容方面强调个体性情感与群体性情感的整合;在情感表现方面要求“情深而不诡”,防止“情失正”。他观审“理”时,在价值思维方面要求“理正”、“理圆”;在艺术规律方面则要求“辨理”、“分理”。在情理关系上鲜明标举“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由于情与理为同一层次范畴,都是对道本体的不同方式(直觉方式与认识方式)的把握,所以强调理融情畅。这种理融情畅论含有两方面意义,一是情感内容与伦理理性、道德规范的融合,因袭儒家的情理中和论,即所谓“诗人情性”,要求情不“失正”,志不“有偏”;二是情感表现与创作机理、艺术规律取得内在一致,所谓“情理同致”也含有这一方面的要求。理融情畅说的双重性特征即思想维面的保守性和艺术维面的开拓性同样显明。刘勰继承了汉代王充等人的情真说,提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情深而不诡”,进一步强调了情感真实论,但对情感个性论未能加以具体探讨。
四 钟嵘的情感美学观——托诗以怨说
钟嵘的情感美学观即是托诗以怨说,这是他对《毛诗序》“吟咏情性”说和陆机“缘情绮靡”论老新传统的合乎逻辑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六朝时代精神、美学思潮和审美理想的理论总结。钟嵘认为诗歌的性质或基本特征是“吟咏情性”即抒情骋情,并进一步从社会现实矛盾方面深刻地揭示了情感审美生成机制。其《诗品序》具体描述了心物交感,“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形成物—情—文的艺术发生论。在钟嵘看来,诗歌抒情的发生机制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人与物之心物交感,自然界四时气候景物推移变化感荡心灵,激发创作冲动,伤春悲秋而形诸吟咏;其二是社会生活不寻常遭遇使个体主体情感激荡而“托诗以怨”。《诗品序》曰:“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在这里,情感审美生成机制既包括物感说又包括事感说,这就使诗歌发生论具有明确而深刻的社会内容。从诗歌本质论来看,钟嵘确定诗歌的社会属性而偏重于“托诗以怨”。在诗艺功能观上,则强调情感的泄导功能,“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他在援引孔子“诗可以怨”观点时不提“事父”、“事君”的讽谏作用,择取《毛诗序》的“吟咏情性”话语而弃却“以风其上”的讽教观念,以诗歌的导情功能取代伦理教化功能,不再拘执于诗艺为政教服务的传统理性美学观。值得注意的是,钟嵘在情感表现内容方面把注意力从群体性的社会生活转向个体性的日常生活,“吟咏情性”被赋予新的表现内容。这样,钟嵘的长歌骋情说促使诗艺摆脱政治附庸地位和工具论特点而具有独立自足的品格。《诗品》的主导倾向是主张吟咏情性宣泄情感,并不特别注重有裨于政教。其在具体评论诸家诗作时,对诗歌联系时政和美刺讽谏取向只是一般性肯定,并不着重强调,倒是对魏晋以来诗歌创作的新趋向如侧重于抒写日常生活的个体情感及追求艺术美感加以关注和重视。
从情感表现内容和情感价值评判来看,与萧纲重视艳情的美感价值相比,钟嵘特别重视怨情的美感价值和对审美心理的感染力度。这种怨情深切反映出个体主体的不幸遭遇和不平之思而带有普遍社会性,在情感美学理论上被归结为“托诗以怨”。《诗品序》云:“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这种种个体不寻常社会遭遇,除去“扬娥入宠”一种之外,其他六种均属哀怨情类,均为“托诗以怨”的典型题材。《诗品》在评论汉代以来诗家作品时,情感价值评判以哀怨为主,表明以抒情为本位观念的成熟和个体悲剧性意识的强化。其评《古诗》“意悲而远”,“多哀怨”;称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谓班婕妤“怨深文绮”;评曹植“情兼雅怨”;谓王粲为“发愀怆之词”;称左思为“文典以怨”。钟嵘对秦嘉、徐淑、刘琨、郭泰、陆机、沈约等都提出其诗作所弥漫的那种“凄怨”、“孤怨”、“清怨”的情调和特色。这种挥之不去难以释怀的哀怨源自作者个体的不幸遭遇和悲凉感慨,如失意之叹、离别之怨、不遇之哀、磨难之苦、黍离之悲、死亡之恨,这种种悲剧性情感引起作者心灵激荡和灵魂骚动,激发创作冲动而加以倾诉宣泄以骋其情。这种怨情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个体性的“孤怨”,侧重于表现个体主体的悲剧性的身世遭遇和感伤性的情感感慨,它重在自我骋情的泄导功能,与汉儒要求的美刺讽谏政教目的大异其趣。这种孤怨在审美指向上以悲为美,自我抒情呈现出“悲”的美感价值特色,如“悲凉”、“感恨”、“惆怅”、“悲慨”、“悲怆”、“悲苦”等不同维度的情感色调。二是典雅性的“清怨”,怨而不失雅正,带有温柔敦厚之风。钟嵘《诗品》认为,所谓“情兼雅怨”,指情感表现是诗骚传统兼顾,雅正美和悲怨美兼备。“雅怨”即是“清怨”,是关于情感内容和文辞风格的雅化要求,即所谓“清雅”、“渊雅”、“文雅”、“闲雅”与俗化(趋俗偶俗)诗风如“质直”、“鄙直”、“古直”、“质羸”相区别,表现出重雅轻俗的倾向。其云“情兼雅怨”,“怨深文绮”,“文温以丽,意悲而远”,均是要求雅正和怨悱(情感二维)兼胜,情感和文采兼美,爽朗刚健的风力与华美绮丽的辞采的合至,反映出情感创造中对于诗骚美学传统的二维整合的时代审美要求和情感与形式相统一的时代美学趋向。另外,关于情感表现方法问题,钟嵘从“吟咏情性”的诗歌本质论出发,不仅要求以自身为目的的“穷情”、“骋情”,而且要求创作主体利用赋比兴并赋予表情体式的新意义,使其更有利于吟咏情性,要求三者交错运用,避免单调方法所带来的“意浮”或“意深”(晦昧)两种偏失,以达到情感表现的完美。
五 六朝情感美学观的三大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和文学独立的时代,也是缘情求美的时代。李谔《上隋高帝革文华书》说“贵贱贤愚,唯务吟咏”,吟咏情性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裴子野《雕虫论》云“天下向风,人自藻饰”,审美求美成为时代的兴奋点。这样就形成一个以情为本以美是尚的时代美学新潮,而畅情文学和尚情理论则是这一时代美学新潮的典型表现形态,这也是当时情感美学观的文化背景。
这一时期情感美学观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情感表现的本体论观照视角。六朝时期情感美学的发展进入大转折阶段,对于艺术情感问题的认识大大深化,开始注重和突出超出儒家伦理规范之情感本体论的意义和价值,重新确立情感本体论的新视角。同时,情感本体论的观照视角又受到当时玄学和佛学的深刻影响。玄学以无为本而提出人格本体论,佛学以佛性为本而提出精神本体论。玄学那种以无统有、执一御众的观照方式,大乘佛学那种心为物本、物为心应的观照方式,影响和促使理论研究凭借抽象理性思辩去建立一种穷本探原、把握事物终极依据的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式。情感理论和情理美学观也受到这种直探本原观照方式的直接影响,从本体论视角对情感美学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曹丕的《典论·论文》虽然产生于玄学思潮之前,但其文气说糅合先秦两汉的元气说(注:先秦《管子》一书提出精气说,汉代王充提出元气自然论,都把气作为宇宙构成的基本质料和宇宙生成的最终依据,因而具有本体论意义。)和《乐记》的“乐气”说而兼具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属性。文气说确认艺术以情感表现为核心,把个体情感视为本体存在和艺术主体,强调个性气情的审美自由表现。文气说从“文本同而末异”角度来立论,重在别共殊的辨异功能。气在“本同”而成为文艺创造的动力源和最终依据,气在“末异”而散变为诗人迥异的艺术风格。 他关于艺术风格辨异和文体特质辨异的思想正是以“本同”的本体论思维为前提的。钟嵘《诗品序》开篇即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把本体之“气”看成物感说、情感发生机制和艺术生成论的本原动因和最终依据,承续了曹丕的气本论视角。刘勰运用直探本原的思维方式来阐明美学新概念“情文”,认为道本体是“情文”生成的内在本源和最终依据,“情文”作为人类情感的审美表现形式是道本体的律动性表现而具有本体性属性。这样,文源于道文生于情两者在本体意义和终极依据上统一起来了。萧统也是从宇宙本体论视角来强调艺术情感表现论的,他在《陶渊明集序》中指明文学所抒个体之情与最高的道本体内在合一(“宜乎与大块而盈虚”),超越了伦理规范和事功目的,由此评论陶潜以诗抒情自在自乐而使“明道”(通达真理本体)和“重身”(重视生命情感)和谐统一而达到“道存而身安”。王弼的有情无累说是强调圣人体无通神而把握道本体,因而能在有限感性体验中实现超越性的情感美理想。这种情感超越论是基于本体论视角和辩证思维的。六朝情感美学为情感寻找形而上依据,把情感提升到至高无上的本体论地位,因而能够从本体论角度来高扬情感的价值和意义,导致对个性情感自由的普遍追求,并通过本体论视角而把物感说、艺术生成论和缘情论贯通起来,把情感表现的认识论、主体论和价值论统一起来。
第二,情理关系的一体化把握方式。本体论视角把情感本身和情感审美表现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和超越性境界,以情感超越论和人生目的论来取代“以情从理”论和伦理目的论。这种本体提升主体的直接结果是摒弃了情理关系上以理制情的传统模式,把情感从外在理性规范的束缚和压抑中解脱出来,由对情感的伦理价值标向转变为审美价值标向,高扬了个体情感自由表现的超越性及其独立意义和美学价值。从把握情理关系的思想方法来看,传统的以理制情论是运用中和方法即人统一于对象(社会伦理)的思想方法,是以伦理为本位和以客体为重心。玄学本体论则提出“体用如一”的思想方法,应用于情理关系上,就是达性(性指称“虚无之理”)畅情说(即王弼所谓“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在理性概念上,王弼是用本体层面的“道”(本体理性)来取代伦理层面的“德”(道德理性),把主体情感提升到与道合一的高度。在情理关系上,儒家美学是以理制情,玄学美学则是情理(道)合一论(或达性畅情论),情感在超越有限感性体验中获得自身本质的无限性而与宇宙本体同化同在,成为一种宇宙深情。王弼《论语释疑》中所谓“尽理之极”,沈约《齐竟陵王题佛光文》中所谓“理贯空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谓“神理之数”,这个“理”是指“自然之道”即本体理性。道本体能提升和升华个体情感,王弼要以达性畅情说取代“以情从理”论。然而,这种达性畅情论虽然讲求“体用如一”,但却以有无互异和辨异为前提,心与物、情与理还存在着差异和对峙,本体性虚无界外在于包容于感性界。而大乘佛学(特别是般若性空学说)的精神本体论执于“非有非无”、双遣双非的中道观及“体用不二”、“物我俱一”的思想方法,变有无互异为有无合一,强调物我同忘有无一观的和谐圆融境界。谢灵运《与诸道人辨宗论》“情理云互,物己相倾”,情与理(佛性本体)自由统一,因而导出“情理俱一”论。玄学的达性畅情论和佛学的情理俱一论成为六朝情感美学观把握情理关系的基点和参照系。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谓“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这里“情性”与“神明”(即道本体)相提并论,赋予情感与道合一的本体意义。《宋书·范晔传》所谓“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强调“情性”与“成理”的和谐统一,而“成理”则由本体理性概念嬗变为相应的客观事理和艺术法度,并要求独特性主体情感与普遍性审美形式规范的完美结合。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阐明“以情纬文”、“文以情变”的前提下,指出“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这里强调艺术形式(根源于内在情感)与规律理性相融合而成为妙造自然。刘勰《文心雕龙·养气》所谓“理融情畅”说(这个“理”指艺术理性,内涵包括“义理”、“思理”和“文理”),要求情理兼胜、情理圆融和“情理同致”,带有兼容会通、圆成圆融的特色。由此可见,六朝美学之“理”,包含有本体理性,自然理性(事物规律)和艺术理性(形式规范、艺术法度、艺术规律)的意义。在对情理关系的把握上,确立了情理一体化的思想方法,反对“以情从理”而提倡“情理俱一”,这种情理一体化是在玄佛“体用如一”、“体用不二”思想方法基础上强调内在自由的圆融统一。
第三,情形关系的兼美化审美指向。六朝情感美学既致力于解决文艺表现什么的问题,从本体论视角确立了情感在文学中的核心地位和情感自由表现的内在必然性,又致力于解决如何表现情感的问题。情感的如何表现可以分为两个关系向度,一是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一是情感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对于情理关系是坚持一体化的思想方法,在上文已作扼要阐析。对于情形关系则坚持兼美化审美指向,要求情与形兼胜兼美。情形关系即个体情感表现与形式美规律的和谐问题。六朝情感美学在目的论和功能观上对传统进行置换和扬弃,以人生目的论和审美功能论来取代传统的伦理目的论和教化中心观,以情感自由论来取代以理制情论,否弃了“止乎礼义”、“以风其上”的理性规范,改塑和更新了“发乎情”、“吟咏情性”的理论标度和美学价值,在继承《荀子》、《淮南子》“情文相称”和《乐记》形式规律论的基础上提出情与形完美结合的思想。其具体理论形态包括曹丕的抒情欲丽说,陆机的缘情绮靡说,挚虞《文章流别论》的“诗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的思议,萧统的“沉思”与“翰藻”兼胜的思想,《宋书·范晔传》范晔“情志既动,篇辞为贵”的论说,刘勰的情感与文采圆成的思想,钟嵘的风力(包括情感因素在内)与丹彩兼美的观点。《文心雕龙·情采》所谓“辨丽本于情性”;《宋书·范晔传》所谓“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点明了情感对形式的内在本源性关系和审美调谐性作用,以情为本而情形和谐统一。声韵音律为主体情感律动的审美物化形式,艺术形式是个体内在情感的外在感性表现。当时对于形式规律和形式美理想的探索具有理论的自觉性,热忱思考艺术形式本身的自足意味和美感效果。六朝形式美包括文辞美、声律美、对偶美、用典美。沈约的四声八病说及其于差异中求整一、于变化中求和谐的声律美学观,以及当时诗歌创作实践中“尚巧”的创作风气和“贵妍”的写作技巧,成为探究形式规律和追求形式美的典型表现。要求情感美和形式美的和谐统一兼胜兼美,必须反对寡情繁采和滥情乏采两种不良偏向。挚虞《文章流别论》所谓“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典正可采,酷不入情”,主要批评了寡情繁采的偏向。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则对两种不良偏向同时进行了深入批评,并要求把个体情感的自由表现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内在地统一起来。先秦两汉的理性美学观尽管讲求尽善尽美、文质统一,但形式美却依附于统一于伦理内容,形式美自身的审美属性和美学价值被理性内容的功利需要所压抑。六朝的情感美学观高度重视对形式规律和形式美理想的探讨,其对于情形兼胜兼美的自觉性追求与当时文学发展观、文学新变论相表里,标示了审美意识的独立和成熟。
六朝关于情感与形式完美结合内在统一的审美认识,昭示了时代的缘情求美的美学指向。从情美论的角度来看,六朝远祧屈原的抒情求美思想而标举缘情求美论,强调“真美”、“至美”,包括“情文”与美文、情感与美感的统一。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句“情用赏为美”,就揭示了情美理想(注:元代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四《胡师远诗集序》阐明“深于怨者多工,长于情者多美”;清代宋征璧《抱真堂诗话》提出“诗家首重性情,此所谓美心也”,进一步高扬了情美论。)。六朝的情美论在审美标向上,包括两大方面四个维度,即情感内容方面的以悲(悲情)为美和以艳(艳情)为美,在形式美感方面的以清为美(艺术风格)和以丽为美(艺术形式)(注:关于六朝时期情美论及其以悲为美、以艳为美、以清为美、以丽为美的审美取向,作者另外著文专题阐析,此不赘述。)。以悲为美、以艳为美反映了对文学抒情性和情感个体性的深刻把握和对人性美(包括性爱美女性美)的深层挖掘,它是对传统以和(中和)为美与以理节情论的突破。以清为美、以丽为美则标示了文学的独立自足品格的确立和回归于瞩目于文学自身的审美特质和美学价值,它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创造。
收稿日期:1999-01-11
标签:本体论论文; 美学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读书论文; 毛诗序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诗品论文; 乐记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