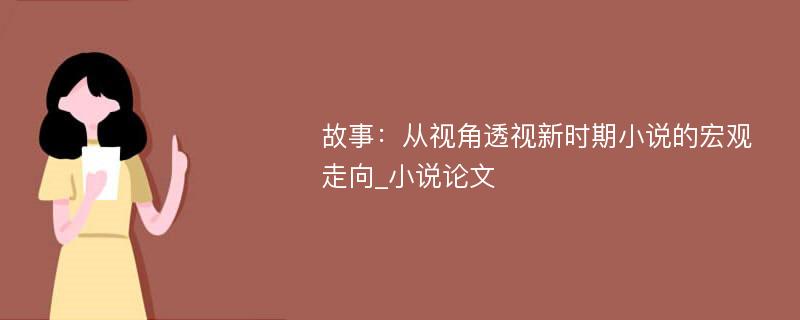
故事:从一个角度透视新时期小说的宏观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透视论文,角度论文,走向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后新时期”的提法已被广为接受,为表述方便起见,本文仍将90年代以来的文学统称为新时期文学。在短短的新时期小说历程中,故事这个小说要素在受青睐遭冷遇到再被注目的荣辱变迁中“走”过了一条螺旋形的道路。这条标识着新时期文学运动轨迹的道路一览无余地显示出:故事,曾经像一只闪闪发光的金苹果被小说家们视为宠物;而在各种新思潮新观念新方法的狂轰滥炸之中,故事又一度被视为一个古典概念遭到拒绝;随着新潮小说的式微,更年轻的小说家们又开始温情脉脉地回望故事这块古老的领地,忘情于在故事营造中奉献他们的睿智展示他们的才情。这种意味深长的变化当然不会只是一种简单的回归,也就是说,我们声称“一览无余”地看到的现象仅仅是一种表面的现象。透过这个现象,我们能看到更诱人的景观吗?在这寻根究底的时刻,回味一下英国现代杰出的小说理论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斩钉截铁写下的那段话--“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这是所有小说都具有的最高因素”①--我更有理由认为,以故事为切入点,透视眼花缭乱的新时期小说,无疑拥有了一个洞若观火般的窗口。而且,从研究现状看,在对新时期小说创作整体趋向的总体考察中,从主题意蕴、结构形态、叙述方式、语言传达等角度入手所作的探索,都已相当深入,而这些角度又都与故事这个小说的基本层面唇齿相依。当然,本文的宗旨不在于勉强地进行理论平面上的创新,而在于对似乎一目了然的现象的描述中,厘清潜在的逻辑,从而为把握新时期小说的宏观走向提供一个清晰的角度。
一
回头审视一下新时期初始阶段的小说,涌现在我们面前的多是一个个剑拔弩张荡气回肠的故事。《伤痕》、《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李顺大造屋》、《绿化树》、《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这些轰动一时的作品几乎都充斥着波诡云谲的矛盾和喷薄欲发的冲突。现在面对这些作品,我们除了领略一番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似乎再也“看”不到别的什么动人的东西了,曾经被兴奋的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深度”早已在岁月的轮转中沦为平面。而且,即使从共时态看,同一深度作品的大批量生产本身就导致了深度的平面化。卢新华的《伤痕》一出,文坛随即涌现出数不尽的伤痕累累的故事。十年浩劫,有多少人幸免无伤?于是编一些故事让不同境遇的人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受伤,成了这个时期小说家们的首要任务。像李顺大脸上深深的皱纹总是在农村的政治风云变幻中凸现出来一样,被文革梦魇所缠绕而创作出的小说,其人物命运沉浮都与政治运动息息相关。小说家们所要达到的深度大致相同,只不过奔向这个深度的途径不同罢了。新时期初始的小说家在竭尽心智地编故事;这个阶段故事性在小说创作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高扬,小说家们对故事的重视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实际的情形远非如此。
作家们之所以兴致勃勃不约而同地把工人、农民、军人、学生、知识分子、大小官员,甚至和尚尼姑们在那段岁月实际经历的不幸和“理该”或可能会经历的不幸分门别类地倾倒和挖掘出来,并非源于对故事的激情,而是故事所承载的控诉和宣泄功能使他们激情荡怀地开始故事的旅程。在兢兢业业地编故事时,故事中人物的命运遭际当然也程度不同地感动着作者,但真正让他们激动不已的是通过故事说明什么反映什么的激情。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解放初期的小说。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使小说家们沉浸在对先烈们感恩戴德的缅怀中激动不已地编着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战争故事,那种按捺不住的表达欲和汹涌澎湃 的宣泄欲与新时期文学初始阶段何其相似!两者的差别在于,一个是歌功颂德,一个是控诉批判。过于汹涌的激情使这两个阶段的小说都带有很强的情绪化和观念化的特点。很多作家甚至怕故事本身抵达不了期待中的深度,急急切切地在作品中留下说书人即兴评点式的毫不含蓄的议论。比如,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故事!)最后一节的小标题是:“记住吧,人们!”而小说的结尾是:“活着的人们啊,争取用较少的代价换取较多的智慧吧!”类似的直抒胸臆的论说语式在同阶段的小说中俯拾皆是,从这就不难看出,作家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故事本身。他们不能像山鲁佐德姑娘给阿拉伯君主讲故事一样专注于故事本身的吸引力,对故事所要揭示的哲理、观念的刻意追求使他们的创作意识中浸染着刻骨的浮躁,导致了这些表面上非常重视故事的小说实际上“故事意识”并不强。这甚至在根本上铸定了这个阶段的小说文体上的稚嫩和美学意蕴上的单薄。虽然一系列“受难”和“忏悔”的故事凝聚着作者、叙事者以及人物的所有在生命意义上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体验,但是,由于时时刻刻支配着故事进程的观念(预期中的故事所要诠释的观念)过于强大了,套用一句伍尔芙的话,它像一个“强大的专横的暴君”,无所不在地统治着故事,这样,观念的主导性强硬地干扰和堵塞了小说的审美空间。在导向预定的深度过程中,作家“不是被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是被某个奴役他的强大专横的暴君逼着去提供故事情节”②,那些涌动于作家内心的潜波暗流和诗性感悟都慑于观念的威力而侧身故事的边缘以至于永远胎死腹中。这种情形颇似目的相当明确(争夺冠军)的马拉松长跑运动员,不管沿途的景致有多么地迷人,他也是无暇欣赏的,整个单调乏味的长跑过程在那闪光的奖杯映衬之下遂成伟大壮举。而现在我们面对新时期文学初始的那些小说,我们漫长的阅读过程所得到的报偿是领悟故事背后的深度,而当这个深度像过时的记录不再激动人心之时,故事的鉴赏者无疑像与奖杯无缘的长跑者一样难免失望。
二
1985年前后,新时期文学进入到一个空前活跃的新阶段,小说创作更是打破了传统封闭型故事的一体化局面而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心理结构、意向结构、自然空间结构、文化空间结构等等小说新样式层出不穷,小说的诗化、散文化、抒情化、情节淡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现代派”小说登堂入室,传统与现代的论争更是搅得文坛沸沸扬扬,马原、刘索拉、徐星、残雪、莫言、阿城……一大批出手不凡的年轻小说家仿佛从天而降。他们标新立异的姿态和咄咄逼人的架势旋风般征服了整个文坛,评论界的喝彩的诘难越发变本加厉地铸就了小说改朝换代的神话。新崛起的一代作家对小说艺术的革新确实称得上是一场革命,我要强调的是,面对这种翻天履地的变革,小说创作发展过程中的“断裂带”在一片惊呼声中被不知不觉地夸大,以至于我们评论界沉浸在革命的“狂欢”(惊喜或者愤怒)中,没有了足够的耐心细细体察革命前后的种种隐秘。就故事这一小说的基本层面而言,在摧枯拉朽的小说艺术革新中,它首当其冲地遭受贬抑,新一代的作家完全摒弃了有头有尾的传统故事套路。指出这一史实是容易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在操作层面上故事不再凸现为醒目的小说外观,就把故事这个小说的基本层面游离于小说研究的视界之外。其实,从创作意识上看,故事阴差阳错地成了小说创作的中心,也就是说,恰恰是对故事不屑一顾的时候,新时期小说创作以否定的方式开始了对故事的史无前例的关注。整体走向上,与操作层面上的“故事--反故事”相对应,小说创作意识中开始了“观念--故事”的革命性转变。像“文革”十年的强大负面价值时刻牵动着新时期初始阶段的小说家一样,故事亦成为强大的负面像幽灵一样缠绕着处身转变之中的小说家的创作意识。我们检视一下新一代小说家的“革命”成果,能更触目地看清故事这个阴魂不散的幽灵“游荡”于小说艺术变革过程中的具体情态。
我们先看看在小说艺术革命中独领风骚的马原。他的《冈底斯诱惑》、《虚构》等小说确实以焕然一新的面目出现在文坛。《冈底斯的诱惑》开篇就得意洋洋地宣称:“当然,信不信都由你们,打猎的故事是不能强要人相信的。”《虚构》则如此夫子自道:“我只是要借助这个住满病人的小村庄做背景。我需要使用这七天时间里得到的观察结果,然后我再去编排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马原经常这样在小说中插入对自己和自己的故事的评价,插入与读者的对话,以及故事正被叙述和编撰时的种种状况。马原以他恶作剧般的独特文体宣告了一个其实很简单的事实:再怎么动人再怎么真实的故事都是作家在白纸上编出来的。他在发表于1985年的《西海的无帆船》中直言不讳:“你郑重其事和嘻皮笑脸没有本质不同。你无论如何,都不过是在讲一个故事。”这样的“创作态度”与新时期初始阶段的小说家相比真可谓相别天壤。当初卢新华、刘心武们投身创作时的面部特写是那么的神圣那么的庄严那么的激动,他们信奉故事的真实性。那时候你要是称他们写小说是在“编”故事,定有冒犯之嫌。这种背景下,仅仅是马原将炮制故事的隐秘半真半假地拱手相告,亦够惊世骇俗的了。而从故事这个角度看,马原跨出的步子实际上算得上平缓,其留下的足迹相当清晰。吴亮曾一语中的地指出过,马原的小说“不是叙述了一个(或几个片断的)故事,而是叙述了一个(或几个片断的)故事”③。马原的秘诀就在于他变着法子编故事,他要“打倒”的不是故事,而是故事的完整性、逻辑性和神圣性。事实上,撇开种种叙述技巧不说,单是马原作品中那些关于天葬、手术猎、麻疯病的故事也是独具魅力的。可以说,从“反故事”的意义上看,马原的所作所为还是比较谨慎的。而且,正是从马原开始了对“怎样讲”(写或编)故事的真正关注。
相比之下,刘索拉、徐星、残雪、孙甘露等走得更远。与马原的变着法子编故事相比,他们是企图变着法子不讲故事,就像航船的舵手想方设法要绕过礁石一样,他们以各自的绝招实践着逃离故事的突围表演。刘索拉、徐星倾心零售着从域外批发来的荒诞意识,残雪醉心于凌乱不堪的梦境,孙甘露沉浸于语言乌托邦……“小说什么都写,就是不写故事”一时成为实验小说的标签(当然,真正要在小说中彻底地不写故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列,另当别论)。但是,越是不写故事,故事越是要缠绕作家。就像“哪里都可以走,就是不能撞礁石”的舵手,在空茫茫的大海上选择行船路线时,那唯恐避之不及的礁石实际上“盘踞”于舵手的意识之中挥之难去,成了他思维的焦点。故事与实验小说家们的情形大致与此相似:他们不得不像舵手重视礁石一样重视故事。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故事在“反故事”的操作过程中成为作家创作意识的中心。即使我们从史的角度给实验小说定位时,也少不了要以此前的传统故事型小说为绝对的参照。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曾说:“诗(文学)的影响是一门玄妙深奥的学问。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还原为训诂考证学、思想发展史或者形象塑造术。”④传统故事型小说对实验小说的“影响”实则意味深长。现在看来,兴奋的评论界从那些标新立异的作品中提炼出的颇具现代派流风余韵的新观念在时间的流逝中日益失去光彩,而从故事这个角度去透视,转型期打下的死结所昭示的文体变异痕迹倒没有随着文学史链条的延长而显得微不足道。
稍后出来的以方方、池莉、刘震云等为代表的蔚为壮观的新写实主义大军亦可归入“反故事”的阵营中。他们在“还原生活”的口号下报流水帐似的叙写着种种鸡零狗碎的生活琐事。细枝末节的纤缕毕现,使新写实小说总体上在文体上呈现为松散杂沓,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没有集中紧凑的故事。而且,方方们低格调的对现实的无力对人生的无奈取代了刘索拉、莫言们高姿态俯视生活的不可遏止的自信和冲动。新写实的一时“得逞”似也不难理解,日常生活中确实没有那么多前因后果步步相随的结果,多的是一块豆腐发臭了小夫妻开始相互埋怨争吵不休这样的琐事。与那些精心编制的环环相扣的故事相比,新写实小说漫不经心地将生活中甜酸苦辣原汁原汤地和盘端出,可谓真实地还原了生活。这样,以颇具蛊惑力的“真实性”这把标尺来衡量,以题材的日常性和行文的随意性忠实还原生活的新写实小说倍受称道,就在情理之中了。问题是,“真实”地还原(反映)生活并不是小说(文学)的全部存在理由。当新写实小说漫不经心的文体作为对故事虚假性的反拨渐渐失去尖锐的警策作用时,其无章法不节制的写作姿态越来越凸现为难以容忍的缺憾。这甚至从根本上注定了新写实小说无力回天的命运:扯开大旗轰轰烈烈地登台,亮相不久就悄无声息地偃旗息鼓。
陈平原在谈论学术史变迁时说过:“原来只考虑如何打败对手,所有的奇招都依此而设计,一旦对手不在场,‘奇招’演化成为‘表演项目’,就显得相当偏颇。”⑤故事作为不在场的对手近在咫尺时,反故事的种种绝绍还能在虽看不见但显然很容易感受到的“张力”中较劲,一旦距离(文学史链条的延长)渐渐拉开,表演起来不仅偏颇而且由于对手的远去而意味索然。或许正因为如此,实验小说家们如日中天炙手可热的时候,“反故事”的种种策略反而因语境的变化而失去意义。况且,对“对手”的估价本身又存在着问题。我们现在可以明确指出,实验小说家们把故事作为小说革新的假想敌实在是一种历史的误会。此前小说的稚嫩不是太注重故事而是太注重观念的传达而没能写出好故事。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实验小说(新潮小说)看起来与新时期初始的小说势不两立,而背后却又有着惊人的一致:都为着一种明确的观念而写作,都没能写出堪称经典的故事。徐星、刘索拉们反抗秩序抗拒平庸的愤世嫉俗的剧烈程度与卢新华、张一弓们对十年浩劫畸形政治的痛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潮小说的式微和新写实的危机是否预示着小说家们要开始重新审视故事?
三
9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巨变(变化很大却没有以往张张扬扬的标榜和随之而来的轰动)。以《褐色鸟群》名满文坛的格非写出了《敌人》(1990),写过《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的苏童写出了《米》(1991),写过《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余华推出了《活着》(1992),以《烦恼人生》独占鳌头的池莉写出了《预谋杀人》(1992)……对照他们的前后作品,其差异之大简直判若两人。他们开始一反常态地醉心于讲述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故事。这种不约而同的契合绝非偶然。莫言在1991年曾明确表示:“我一直在思考所谓的‘严肃’小说向武侠小说学习的问题,如何吸取武侠小说迷人的因素,从而使读者把书读完,这恐怕是当代小说唯一的出路。”⑥池莉在1992年强调“名著的标准之一就是不仅仅专家读,关键在于要得到最广大读者经久不衰的热爱”⑦。类似的公开陈述,在90年代的小说界已不是个别现象。周大新在《文学评论》发表题为《漫说“故事”》的长篇创作谈,格非在《上海文学》发表长文《故事的内核和走向》,作家们对故事的理论兴趣足以表明,“反故事”的喧嚣过后对故事的回归是缘于作家们创作策略的自觉调整。
如果说新时期文学的初始阶段,小说家们为了一个明确的观念(如控诉、批判)气喘吁吁地编故事,1985年以后小说家们开始为了一个明确的观念(如反抗秩序,如还原生活)信誓旦旦地抵制编故事,那么,到了90年代,小说家们才真正开始为了编好故事而从容不迫心安理得地编故事。
显然,格非、余华们进入90年代后所编的故事与新时期初始的小说家所写的故事已有着天壤之别。格非们放弃了再现现实的意图,更多地侧重于表现感觉的真实,在建构故事时,为故事的叙述结构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在讲述故事时,不再依赖时间上的延续和因果承接关系,更多地依据心理逻辑。⑧这样,故事不再仰仗观念骨架的支撑,它靠自身的生命和逻辑显示出勃勃生机。新时期小说发展到这一步,故事这个小说的基本层面才开始真正焕发出迷人的魅力,或者更直接地说,只有到了这个阶段,故事才秉赋了自主性和自足性成为生生不息的动力源真正位居小说创作的中心位置。
故事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用格非的话说即“故事早就不是目的,甚至也不是某种思想观念的载体,它实际上已成为感觉中的世界本身”⑨)总体上提升了小说的美学深度,我们无法再以“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反映了什么”的单一的线性逻辑思维去一劳永逸地诠释故事。故事不再植根于历史文化的深层模式中,它所可能抵达的深度也已“降格”为副产品。故事的发生也不再必然地赋予特定的历史动机和文化意蕴,它的每一个环节都拥有饱满的动机。像苏童的长篇小说《米》,那个农村流浪汉五龙进城后的种种遭遇,固然也有其现实依据,但所有源于现实(历史)的依据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五龙居然经历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件,而苏童居然那么不可思议地把这些事件写得那么彻底!故事的强大冲击力扑面而来,似乎任何道德观念和逻辑推理都无法阻挡故事的进程。读这类作品,我们多少可以意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洛德·西蒙所说的一句挺让人费解的名言:“当我们想写一部小说时,当我们开始想要叙述一个故事时,实际上这故事已完结。”⑩(陈村说过类似的话:“作家也许在心里打算着给读者讲述某一个类型的故事,但是,我们用不着替故事担忧,故事自己会往前走的。”(11)故事不再是现实(历史)的象征容器,它本身就是一种绝对的现实。面对那一个个命定般铸就的故事,我们在被震惊之余,甚至只能小心翼翼地逼近它们,所有的了悟和洞悉似乎都显得过于自信。这样说并非故作神秘,美国作家尤多拉·韦乐蒂曾说:“每一个好的故事都有神秘性,不是迷惑性的那种,而是诱惑性的神秘,在我们更好地理解故事的同时,那种神秘不一定会减退,而是确定地变得愈来愈美。”(12)近年来小说创作回归故事的同时伴随着一股不小的神秘潮(13),也就不是什么悖理的事。其实,神秘本身并不神秘,它无非昭示着人的认识界限。故事的神秘性或许正表明,优秀的小说秉赋的丰厚美学意蕴越过了我们现有的理性认识。
因此,我们可以说,新时期小说创作向故事的回归,其意义远远不止是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便利。仅就文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小说家解除了观念的束缚“心无旁鹜”潜心写故事,回归后的故事更为精致;另一方面,因为故事只遵循自身的原则(所谓自主与自足)向前推进,远离了主题、道德、感情等的牵制,“行程”又更加自由,我们也就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脱离叙事意念“约定”的情愫韵致在故事的间隙里随意蔓延。而这些有时甚至在无关紧要的细节处停留下来横生枝节地催化出的诗性感悟,往往与习惯的感觉方式很不相同,其突兀的陌生化策略又无疑在迷惑视听的外表下,增加了作品的审美信息量。总之,故事,作为小说试验的最后一块停泊地(或现在的暂时栖息地),“承担”着小说艺术革新的种种后果。
注释:
①福斯特:《小说面面观》P21,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②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下册)P616,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③吴亮:《马原的叙事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④布鲁姆:《影响的焦虑》P6,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⑤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p21-2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⑥莫言:《谁是复仇者?--〈铸剑〉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
⑦池莉:《预谋杀人·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⑧⑨(11)格非:《故事的内核和走向》,《上海文学》1994年第3期。
⑩克洛德·西蒙:《弗兰德公路》p267,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12)转引徐岱《小说形态学》p117,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3)参见洪治纲《追踪神秘--近期小说审美动向》一文,《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