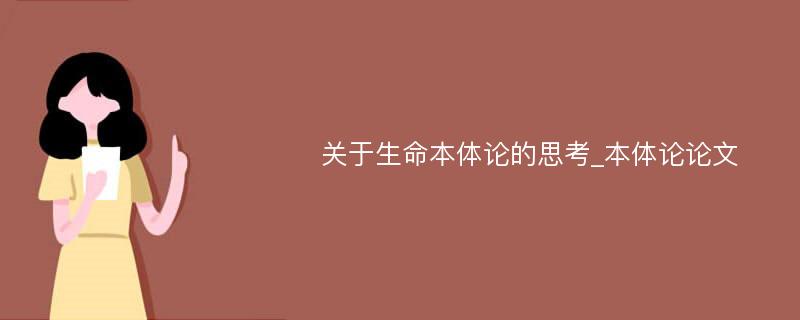
生命本体论反思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至今日,尽管确如有的论者所言,在文艺学、美学论著中“‘本体’的滥用仍然我行我素”〔1〕,但与八十年代中后期相比, 九十年代以降,文学本体论“热”已然大大降温。不过,这恐怕并非真正反思的结果,实际只是一种追逐时髦的热情的消退。而由于文学本体论曾对文坛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记录了我们曾经怎样走过的一大段路程,故于下一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对文学本体论认真进行一番反思,无疑是必要的。
关于文学的本体论,名目繁多。然而真正从“本体”意义看,文学本体论其实主要是三种,即形式本体论、语言本体论、生命本体论。其它种种都可以为它们所概括。三种之间,当然不无交叉和渗透,但又以生命本体论为核心。因此,这里拟就生命本体论进行反思,以期从一个方面获得对于文学本体论的重新认识。
一、生命本体论“三部曲”
文学的生命本体论,开始是以人类学本体论形式出现的。彭富春、杨子江首先提出,“艺术的真正本体只能是人类本体”,文艺理论必须“建立在人类学的基础上”。由于“一方面,从人的生存出发,我们必然走向艺术;另一方面,从人的艺术出发,我们不得不深入到人的生存”,因而只有立足于人类学本体论,“我们的理论的触角才真正地开始进入到艺术存在的本体;艺术也才会真正显露它的自身的本体”〔2 〕。紧接着,在《文学评论》组织的笔谈中,彭富春又一次强调,“文学是什么,在于人类是什么”,“我们如果要建立文艺本体论的话,我们必须建立美学本体论;我们要建立美学本体论的话,我们必须建立哲学本体论。这个哲学本体论只能是人类学本体论”〔3〕。
那么,人类学本体论又将落脚到何处,或者说人类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呢?彭富春等进一步指出,“生存就是生命……你是肯定生命的,那你就是有意义的,你是否定生命的,你就是无意义的。所以,理性与非理性之争后面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东西,即生命本体”。于是得出结论:艺术的意义、价值就“在于纯粹的生命意识。它是生命意识的觉醒”,就是“要唤醒你的生命意识,任你的生命本性的自然而运动,从而使你在生存之网中获得解放与自由”〔4〕。这样的见解, 很快引来了诸多论者的认同,各种类似的表述纷纷出现。如认为文学“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表现”,“体现为这种自由的生命活动之无限展开的过程”〔5 〕;“艺术作品决不是别的什么,它仅仅是不可重复的个体生命的不可重复的纯粹形式,是作家独特生命的形式化”〔6〕; “艺术本体与人的生命是同构的,文艺活动的过程和文艺的本体存在都只能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寻求解释”〔7〕; “一个新的口号必须呼喊出来:文学艺术必须体验生命”〔8〕; “把生命解释为人的价值存在,人的超越性生成,这才是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本原”〔9〕; 甚至大声疾呼:“一切依据都在于生命形式!”〔10〕由此出发,有论者还对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开始持以怀疑或否定态度,提出:“在理性已牢固确立的物质时代,强调物质世界的第一性有何意义?”〔11〕认为“脱离了生命,脱离了时间,世界便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物质”,因而“文学的特性,决定了文学家、文学理论家必须把万事万物作为有生命的存在——都有着生命的冲动”〔12〕。甚至断言:“从文学来源于心还是来源于物的角度讨论文学,从文学的本质是反映还是表现来讨论文学,往往是徒劳无益的。”〔13〕这样,文学的人类学本体论,便推演到了生命本体论。
生命本体论的提出,似乎与精神本体论、更与文学主体论不同。彭富春等就曾批评刘再复那名噪一时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依然是从一种外在于艺术的哲学理论出发的”,“是对某种哲学框架的图解”,而使“我们仍然不知道文艺是什么”〔14〕。然而正如后来有论者所说,主体论“这种见解,显然不仅是一种以人为文学本体的理论,而且是一种以人的精神为文学本体的理论”〔15〕。而生命本体论一经展开,就可以被发现,它其实并没有超越主体论,仍然是“某种哲学框架的图解”,即以精神或意识为指归;即使表示不屑于从来源于“物”或“心”的角度谈文学,企图超越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却一旦谈论生命的本质,也还是未能跳出以精神或意识为第一性的樊篱。如有论者强调,不能“把意识只看作是物质存在的反映而忽视它作为生命存在的本体论意义”,由于“在传统反映论模式中,精神的这种本体意义消失了:它仅仅是对物质存在的反映”,结果“精神价值受尽了委曲(屈)”〔16〕。或者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人类渴望认识自己的生命冲动的精神家园”,因而只有“主体对自我意识的发掘和表现才能在超越对象意识中展示永恒的人生奥秘”〔17〕。还有论者联系创作实际,特别推崇“第三代诗人”,称赞他们的诗作“是内在生命体验的真切表达,是潜入到深层心灵去窥探人生的奥秘,谛听生命的呼吸与律动,使诗最终与人吻合成为一体”;同时批评“中国相当一部分存活率极高的诗歌”虽“永居诗国”,却“不再是人的内在生命的律动的本体体验”,“无法与生命的内在构成化合”〔18〕。这样,生命也就与意识、精神、深层心灵等同起来,使生命本体论在实际上变成了意识本体论,亦即精神本体论。回顾刘再复,令人感到他确乎秀出班行,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命本体论,却已预先守候在生命本体论必然推演行程的途中了。
然而毕竟还有后起之秀。他们把意识或精神又进一步归结到了非理性的直觉、体验、心理或生理的本能冲动。这是对意识本体论的超越,也是对刘再复的超越。一些论者,断言“作家创作活动的深层动机原本就来自生命需要的本能冲动”,因而“当主体的这种生命本能的冲动尚在理论的视野之外时,理论永远不能夸口它完全认识了文学”〔19〕;认为“诗所要传世的,就是人的原初意识或超前意识”〔20〕;推崇“原始的情感”“还未经过政治的、道德的标准的切削,还未拿到社会生活中加入一个潮流,带有最大的自然性”,因而“是最真实的”,会“带给人全新的感觉”〔21〕等等。一个时期里,这种对于非理性的导扬此起彼伏,以至形成了一股思潮。这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刘晓波。他不仅认为“作家只是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与自己的灵魂进行自我对话,他是个‘为艺术而艺术’的非社会化的人”,而且论定,“进入创作过程的作家沉醉于迷狂之中”时,“打碎了一切理性的束缚”,“是纯粹的、本真的生命呈现”〔22〕。他甚至明确宣称:“要大谈本能,谈非理性,而不能谈社会,不能谈理性”〔23〕;“我的文学观就是没有什么理性可言,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都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文学的审美的纯洁性。在中国就是不能谈什么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这类字眼”,“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不如此,“文学就没有真正发展的一天”〔24〕。
不仅如此,有些论者还将生命的本质完全归结为性意识、性本能,彻底回到了弗洛依德的泛性欲主义,把性当作了分析生命现象、文艺现象乃至全部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并与道德完全对立起来。如有论者就断言“性意识是生命意识的核心内容”〔25〕;或通过作品评论,认为性欲的满足使男人和女人“都真正意识和醒悟了活着的意义”〔26〕;甚至说“一部无人撰写的‘性’的历史,几乎包容了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27〕由于性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必然被赋予道德的评判,所以又有论者不惜对“恶”大加肯定和抬举,如宣称“被压抑着的罪恶恰恰是最真实的部分。因此,性意识的公开呈露对于诗走向生命真实的全部迈开了一大步”,宣称“强化情感的非理性、隐秘性一面从而进到情欲性感的突现,实在是冲破伦理有序空间最为辉煌的一次进击”〔28〕。还有刘晓波,不仅强调“我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标准视之为‘恶’的一切,正是人的生命本身,而审美也就必然忠实于这种‘恶’”〔29〕,而且提出:真善美对艺术来说是“有点可悲的”〔30〕。这样,意识本体论便又被推演成了以直觉、体验、本能直至更彻底的“性”、“恶”为内涵的非理性本体论。
生命本体论——意识本体论——非理性本体论,这就是在文学即“人学”标题下奏出的“三部曲”,而最终归结到非理性,正是这生命本体论三部曲的真正的主题。
二、生命本体论的西方“原型”
在西方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中,许多哲学流派都十分热衷于对生命问题的研究,其中特别是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受此影响,在现代西方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方面,也有相当多的流派,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小说等,都把生命、自我、主观经验、内心体验乃至直觉、幻觉、梦境、本能、无意识等作为所关注、所强调的中心,把它们视为世界和艺术的根本,视为一种“最高的真实”。
具体说来,现代西方的生命本体论首先是把“生命”或“自我”看作一种最直接、最真实的存在,是全部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世界万物,无不以此为本体、为本原。如德国生命哲学的创始人狄尔泰(1833—1911)认为:“生命本身、我们所不能深透的生命力,包含着揭示一切认识和一切思维的联系。一切认识的可能性的关键即以此为基础。”〔31〕另一位德国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席美尔(1858—1918)也认为:“生命看来是最最客观的东西,……它是主体的最深刻和最坚实的客观化。”〔32〕法国生命哲学的主要代表柏格森(1859—1941)则说,“唯一实在的东西是那活生生的、在发展中的自我”,而“自我”就是一种“生命冲动”,此外的物质世界,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鬼影”〔33〕。至于存在主义,虽然没有象生命哲学那么多地直接使用生命的概念,但其理论显然与生命哲学相通。如德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海德格尔(1889—1976),在著述中曾大量使用“在”、“在者”、“亲在”等十分晦涩的术语,对此,法国存在主义者华尔曾较为通俗地解释说:“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我们所真正接触的唯一的本体的形式是人的存在。……只有人是真正存在的。”〔34〕可见海德格尔也是以个人生命的存在,来作为世界万物存在的前提的。与此相仿,德国存在主义另一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1883—1969)认为,“一切现实的东西,其对我们所以为现实,纯然因为我是我自身”〔35〕;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1905—1980),则在他颇有影响的《存在与虚无》一书中,认为世界依赖于人的存在,否则就是什么也说不上的“巨大的虚无”;等等,也都表达了相近的意思,正如美国存在主义者蒂利希(1886—1965)所说,“生命哲学包含构成存在哲学的大部分特征的主旨”〔36〕。
接着,这种现代西方的生命本体论又将生命归结到了意识或精神,即不是生命产生意识,而是意识产生生命。如柏格森就明确指出,“意识并不是由大脑产生的”,相反,“生命是心理的东西”〔37〕。按照柏格森的解释,生命既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又是一种作为宇宙意志的“生命冲动”创造的结果。“生命冲动”向上喷发,产生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一切生命形式;“生命冲动”遇阻向下坠落,产生一切无生命的物质事物。这就同唯意志主义认为世界万物都以“生存意志”或“生命意志”为基础、为本质一样,将“生命冲动”当作了包括有机界、也包括无机界在内的世界万物的本原。那么,“生命冲动”又如何被证明其存在呢?柏格森认为,这就要靠“内心体验”,即二者是同一的。如他所说,“当我们自由地活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亲身体验到这种创造”〔38〕。这样,所谓作为宇宙意志的“生命冲动”,就又回到了人的意识或精神,也使整个生命哲学又由客观唯心主义跳回了主观唯心主义。柏格森曾标榜生命哲学“超出于唯心主义和实在主义之外”〔39〕,亦即超出了传统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范围,但事实却表明这不过是一种神话。存在主义强调“个人”或“自我”,但同样认为真正的真实存在还应更进一层,这就是人的主观意识和心理体验。如雅斯贝尔斯就认为对于人的社会历史进程及其特点,都应该“到人的存在的内在世界中去寻找”〔40〕。萨特则利用了笛卡尔(1596—1650)的“我思故我在”的公式,强调“世间决没有一种真理能够离开‘我思故我在’。我们凭此可得到一个绝对真实的自觉意识”;他还概括不同存在主义的共同点,就是“都认为存在先于本质,或者说,必须以主观为出发点”〔41〕。可见,存在主义不仅把人的存在、或者说人的生命的存在当作了全部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且也进一步把人、人的生命归结到了人的心理意识、精神生活。由此也可以看出,不论生命哲学还是存在主义,其实又都把生命本体论推到了意识本体论。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深受这种理论的影响。如英国女小说家伍尔芙(1882—1-941),就要求作家“表现出我们借以生活的精神,就是生命本身”〔42〕;奥地利诗人里尔克(1875—1926)则劝人“与世隔绝”,“深入你的内心世界,探索你的生活源泉”〔43〕。还有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1871—1922),认为艺术家的职责就是“‘解释’早已存在于我们各自心中的印象”〔44〕;德国作家埃德施米特(1890—1966)提出,“一定要纯粹确切地反映世界的形象,而这一形象只存在于我们自身”〔45〕;等等,都可见所受生命即意识或精神这一观点的影响之一斑。
再进一步,西方的生命本体论又把意识、精神完全归结到了神秘的、非理性的直觉、体验、本能冲动,从而对生命乃至世界的本体、“最高真实”作出了最后的回答。如狄尔泰就说,“生命是最初的也是最后的,而且生命没有体系,没有理性,它之出现是为了它自己和由于它自己”〔46〕;柏格森也说,“生命冲动”“是一条无底的、无岸的河流,它不借可以算出的力量而流向一个不能确定的方向”,只有直觉才是“能够朝向事物的内在生命的真实的运动”,因而“意识,或毋宁说是无意识,是生命之源”〔47〕。对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公式,萨特所承袭的是它的唯心主义,而对其中的理性因素则掷之一旁。他认为“自觉意识”只能是超出感觉和思维的心理本能活动,“每一个人是作为一种深秘而孤立的存在”,甚至认为只有“被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歇斯底里病,才能说明真正的社会现实”〔48〕。这样,人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无论生命哲学抑或存在主义,在人与世界之间、人的精神存在与肉体存在之间、人的非理性直觉、体验、本能与理性意识之间,都是以前者为第一性、后者为第二性的,从而构筑起了生命——意识——非理性心理意识这样一种三部曲式的生命本体论。在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一些引人注目的非理性主张,如普鲁斯特认为唯直觉“才是判断真理的标准”,“才能够使真理更臻完美”,因而“艺术家应服从他自己的本能”〔49〕;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1883—1924)表示“我尽可能抛开理性而生活”〔50〕;超现实主义理论代表、法国作家布勒东(1896—1966)宣称文学就是“无意识写作和记述梦境”,强调超现实主义的要旨就在于“纯粹的精神的无意识活动”,“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51〕;等等,都显然是这种生命本体论的最后一曲的回声。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见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生命本体论,其实正是以现代西方的生命本体论为“原型”,并同样踏着三部曲的节拍亦步亦趋的。实际上,有些论者对此也不讳言,如有人就表示“新哲学强调生命世界的本体性和生命的世界本体性,提倡艺术家体验生命的学说,实际上是以这种哲学本体论观念为其基础”〔52〕。还有论者更坦率:“八十年代诗人所意识到的深刻的东西莫过于文化与人的冲突了。于是他们身不由己地接受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启示:尼采、叔本华、柏格森、萨特、海德格尔……”〔53〕,这就一语道出了我国文坛的生命本体论“热”之所由来。只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宣扬反社会、反文明的动物性和疯狂性方面,我们比现代西方的生命本体论走得还远。
三、生命本体论“热”之因:三种“匮乏”
弹指十年间。如今回首生命本体论,对其利弊得失,即使不作详细论证,大概也可以感受得比较清楚。需要指出,文艺理论批评中的各种主张或观点,并非凡以西方理论为蓝本便必定得其咎。对于西方理论中的合理因素,我们无疑应当加以借鉴。但关键在于这些西方理论从根本上看是否科学。应当肯定,西方的生命本体论对于“生命”或“自我”,对于意识或精神,以及对于非理性的直觉、体验、本能的重视,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并非对这些东西一概予以拒绝。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论道“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4〕。马克思不仅强调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55〕,而且批判旧唯物主义“对事物、现实、感性”“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56〕。恩格斯甚至还曾明确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57〕。然而,生命本体论是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哲学的几乎一切领域来立论的,这就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一系列显得十分简单的问题都摆在眼前:宇宙之间,是先有物质世界,还是先有人的生命?如果无法否定是先有前者,那么为何以生命为本体?如果说物质世界也是“生命冲动”的结果,那么“生命冲动”作为一种宇宙意志,它是从哪里来的,又如何证明它的存在?如果说这一切都只能到人的内心世界中去寻求答案,那岂不就是把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拼接、杂糅到了一起吗?至于把生命仅仅归结为意识或精神,又进一步把意识仅仅归结非理性的直觉、体验、本能、冲动等等,实际就连现代西方美学和文艺领域中的某些有识之士,也都大不以为然。如美国哲学家、美学家苏珊·朗格女士(1895—1982),就明确反对假“洞察”或“直觉”之名,“向荒谬、向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投降”〔58〕。再以文学论,视生命为文学的本体,其实也没有真正把握其本性,因为这尽管可能获得对于人类生命活动的一般认识,却无法回答作为人类生命活动形式之一的文学艺术的特殊性问题。除将创作引向非理性,对于真正的文学理论建设,很难说究竟能够推进多少。
如今,包括生命本体论在内的文学本体论“热”在我国已经降温。推想当年的高扬生命本体论者,很可能在观念上也已程度不同地有所改变。然而我们不能没有自省和检讨:对于在今天看来纰缪十分明显的生命本体论,为什么当年竟那样地崇尚、热衷,以至奉为圭臬;否则,以盲目性为特点之一的“热”,就还会以其它形式出现。九十年代以来,文坛又有追“新”冠“后”热、国学热;在对人文精神的倡导中,也有论者重新表现出对抽象的“人性”、“永恒”的极大热情。而且文学本体论是否会“东山再起”,也未可知。因而对生命本体论的反思,或可使我们得到一些启示。生命本体论的“热”之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我以为在于三种“匮乏”。
一、价值论的匮乏。自八十年代初人们开始关注文学的本性问题,以至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本体论的提出,应当说目的还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使文学摆脱政治的束缚。但是,我们的可悲在于只知摆脱束缚,却不知摆脱束缚之后到哪里去。也就是说,并没有真正弄明白文学为什么而存在、文学应当怎么样的问题,没有寻找到文学的价值定位,目标变得茫然。于是,我们就只有在创作上不断翻新,在理论批评中不断强调文学的本性,以期形成一种与政治相疏离、相抗衡的力量。然而正由于没有明确的价值目标,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所以创作上的翻新,就变成了对西方的模仿,以至被称为十年间走过了西方一百年的路;理论批评中对文学本性的强调,也同样变成了以西方理论为主的各种理论的竞相登台,以至目的已无所谓,过程就是一切。当时,有论者曾鼓吹文学批评“超越一定的功利目的,完全是为了试验思维的可能性”,并提出:“我们能否使自己的理论思维渗透着一种智力游戏的精神?”〔59〕这种把精神思考的过程当作理论研究的价值本身,而将目的的明确性视为“功利”并加以弃置的做法,其实正表明不知真正的价值在何处。于是,尽管对西方生命本体论的舛误未必没有觉察,但价值目标茫然,耳食之学与稗贩之学大行其道,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有意思的是,重过程轻目的本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与对于本体的追寻这种现代性的思考是相互矛盾的,但在我国文坛对生命本体论的高扬中,二者却就是如此奇特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方面说明生命本体论在我国实际上并不具有西方那样的彻底性,一方面说明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在我国虽于九十年代才被传扬,但其心态准备,却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即已开始。
二、方法论的匮乏。这里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缺少辩证法。生命本体论的推演,由生命而意识而非理性,其片面性、极端性之弊显然可见,及至完全归结为性,并公然为恶张目,则更令人惊听回视,瞠目结舌。很难相信,论者在高谈阔论之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理论”的纰漏和荒谬。然而由于价值目标的模糊,理论思维已被感觉化,跟着感觉走,所以片面性、极端性也已不再为理论研究所避忌,相反倒成为一种时髦,而要求两点论,要求全面看问题,却被视为观念的迂腐和陈旧,如是严肃的科学探索,终于变成了竞相争比出言的狂放和胆大,以至连起码的逻辑和事实,都已被置之于不顾。平心而论,认识过程中的片面性乃至极端性,确乎难以完全避免,因而不应求全责备;问题是明知其误或至少也已估计到可能有误而仍振振有词,这就另当别论。这种情况的形成,当然与迎合时尚、追逐时髦、显示“理论勇气”、以求“轰动效应”等心态有关,而从方法论看:则应当说是作为“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60〕的辩证法正在被放逐。若再进一步探究,又可以发现,舶来的“深刻的片面”、国产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其实正是其理论的渊源。
方法论的匮乏,还体现于我们并没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前问题”,尚未首先得到解决。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有论者已经指出的:“‘文学本体’作为一个范畴是否科学,仍是一个疑问。”〔61〕对于“本体”的概念,我国诸多论者在理解上颇有不同:存在、本质、本性、本原(“本源”)、核心、基础、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事物本身,等等,而对“文学本体”,更有论者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多”。但是,如果回到最早提出本体概念的哲学领域,则大约理解为宇宙万物最高、最抽象的“终极存在”,才与原有的涵义较相吻合。如是,当我们高扬文学本体论的时候,就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眼前:一、宇宙万物,究竟有无“终极”?二、具体事物是否也可言“终极”?抑或它只在自身的现象中包含着自身的本质?这些问题,当然难以轻易作答,但本体论者既然高扬本体论,就理应先把它们搞清楚。粗看起来,包括生命本体论在内的文学本体论,一般是承认终极存在的;然而细加推究,却可发现其立场并不坚定,往往若明若暗,闪烁其词。不同论者对于“终极”的不同认定是无可厚非的,而同一论者的含混游移、左支右绌就不免显得尴尬。譬如生命本体论由生命推到意识再推到非理性的直觉、体验、本能冲动,便必然会引来这样的质疑:它们究竟是文学的本体,还是同时也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如系前者,那么是否任何具体事物都有本体亦即终极可言?而对各种各样的具体事物,能否一一指出它们的本体或终极是什么?而且,所谓本体或终极,不是本应作为宇宙万物最高最后的抽象吗?怎么又变得只在如此局促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如系后者,即文学与宇宙万物的本体、终极是同一的,那么,难道能把宇宙万物的本体、终极也归结为生命、意识乃至非理性的直觉、体验、本能么?或许也有论者真同柏格森一样如此推论,但不要说他人,就是自己,是否就真的相信呢?又如有论者将文学的本体既归结为语言,又归结为生命〔62〕,亦即同时存在两个本体、两个终极;或认为文学本体不仅是“宇宙、自然、世界、人生、社会、生活、人类的精神世界”,而且也是“文学作品、文学宝库本身”〔63〕,亦即成为“无边”的本体论;就都更令人不知究竟孰为本体或终极了。显而易见,“前问题”不首先解决,则再多的本体“论”,也只能是数量上的延展,徒然令人眼花缭乱,却很难产生真正的理论价值。倒是后现代主义很干脆,它根本否认“终极”、“本体”的存在,而且连“本质”也一起拒绝。这当然同样值得探讨,但无可否认,对于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本体论,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进入九十年代,文学本体论走势低迷,一个重要原因,也就在这里。
三、唯物论的匮乏。当然不能说所有关于本体、文学本体的谈论都远离了唯物主义。但在文学本体论思潮中,相当多的观点、观念与唯物主义相悖,却是不争的事实。
生命本体论对物质第一性的否定,对人的生命活动与社会实践的剥离,甚至连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物质决定精神等一些基本常识也全然不顾,可以说不论是否自觉,实际都站到了唯心主义麾下,与唯物主义对垒。当然,唯心主义绝非一无可取,但在“物”与“心”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其谬误却早已为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所证明。如今,我国的一些本体论者覆辙重蹈,使唯心主义如此直接、公开地表现出来,以至为几十年来的文艺理论批评领域所罕见,这对于生命本体论以及整个文学本体论“热”来说,毋需词费,也显然可见是一重要原因。
注释:
〔1〕黄力之:《“本体”的滥用及其文化意义》, 《文艺报》 1995年10月27日。
〔2〕《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1期。
〔3〕见《我们的思考与追求》,《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
〔4〕《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
〔5〕陈宏在语,见《我们的思考与追求》。
〔6〕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7 〕林兴宅:《出路:生命自由意识的觉醒》, 《福建文学》1988年第12期。
〔8〕〔11〕宋耀良:《体验生命——一种新的创作论观点》, 《文学评论家》1989年第4期。
〔9〕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
〔10〕李震:《从文化文本到非文化文本——中国新诗本体的觉悟》,《艺术广角》1989年第5期。
〔12〕程文超语,见《我们的思考与追求》。
〔13〕林岗:《符号·心理·文学》,花城出版社,第167—168页。
〔14〕《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
〔15〕严昭柱:《关于文学本体论的讨论综述》,见陆梅林等主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上册,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16〕吴兴明:《精神价值论——文艺研究的逻辑起点》,《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
〔17〕孙文宪语,见《我们的思考与追求》。
〔18〕夏永刚:《诗的挣扎——论第三代诗人的生存意识》,《艺术广角》1989年第5期。
〔19〕孙文宪语,见《我们的思考与追求》。
〔20〕邵进语,转引夏勇刚:《诗的挣扎——论第三代诗人的生存意识》。
〔21〕孙桂贞:《关于新诗创新的一点体会》,《诗神》1985年第5期。
〔22〕刘晓波:《创作论的窘境》,《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5 期。
〔23〕见《南北青年文学评论家对话》,《语文导报》1986年第11期。
〔24〕刘晓波《危机! 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 《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
〔25〕见《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26〕刘敏:《天使与女妖》,《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4期。
〔27〕叶砺华:《跪在现实面前的“性”文学》,《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5期。
〔28〕夏永刚:《诗的挣扎——论第三代诗人的生存意识》。
〔29〕《选择的批判》,第28页。
〔30〕《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
〔31〕转引自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
〔32〕转引自黄力之:《生命意识:近年文学思潮之一瞥》,《文艺报》1991年7月6日。
〔33〕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商务印书馆1958 年版, 第120、159页。
〔34〕〔35〕〔36〕转引自《现代西方哲学》第552页;第552页;第544页。
〔37〕转引自《现代西方哲学》,第198、197页。
〔38〕转引自《现代西方哲学》,第201页。
〔39〕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5页。
〔40〕〔41〕转引自《现代西方哲学》,第569页;第553、555 页。
〔42〕〔43〕〔44〕〔45〕转引自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第165页;第133页;第152页。
〔46〕转引自黄力之:《生命意识:近年文学思潮之一瞥》。
〔47〕〔48〕转引自《现代西方哲学》,第206、214、197页;第585页。
〔49〕〔50〕〔51〕转引自《现代西方文论选》,第130、365页;第383页;第175、169页。
〔52〕宋耀良:《体验生命——一种新的创作论观点》。
〔53〕李震:《从文化文本到非文化文本——中国新诗本体的觉悟》。
〔54〕《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55〕《189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56〕《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18页。
〔57〕《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0页。
〔58〕转引自蒋孔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59〕李陀:《文学批评与智力游戏》,《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1期。
〔6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521页。
〔61〕严昭柱:《关于文学本体论的讨论综述》,见《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上册,第821页。
〔62〕见李震:《从文化文本到非文化文本——中国新诗本体的觉悟》。
〔63〕王蒙:《读评论文章偶记》,《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标签:本体论论文; 文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存在主义文学论文; 生命哲学论文; 文化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本体感觉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