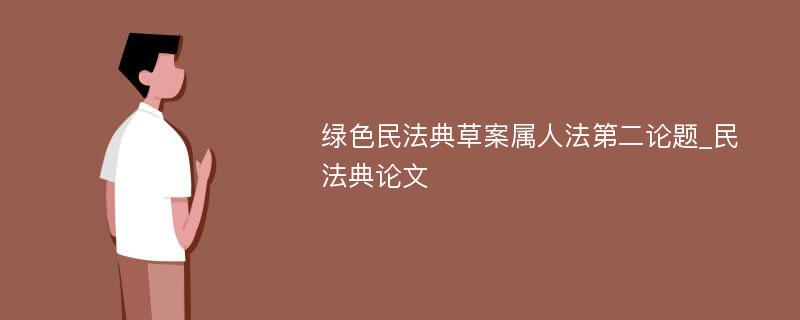
《绿色民法典草案》人身法二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法典论文,草案论文,人身论文,法二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目前有5个民法典草案,将来可能达到8个。已有的5个是,王汉斌委托9位专家完 成的学者建议稿;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人员以此稿为基础加工成的所谓“室内稿”;梁慧 星教授及其同事利用自己起草的前述学者建议稿中的有关编外加自己补写的编构成的“ 补全稿”[1];王利明以同样的方式完成的补全稿[2];出于谦虚最后谈到的是我们的洋 洋90万言的《绿色民法典草案》[3]。将来可能产生的3个民法典草案分别为:一,将作 为王利明教授承接的教育部重大人文社会科学联合攻关项目“中国民法典的体系和重大 疑难问题研究”的最终成果的民法典草案。二,在分配这一项目时,中国政法大学民商 经济法学院与人民大学联合中标,分得80万元科研经费中的15万元,该学院打算利用这 一经济资源起草一部自己的民法典草案。三,同属于广西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孟勤国教授 也打算搞出一部自己的民法典草案。由此,中国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法典起草繁 荣期。各个草案的作者彼此竞争,比较优劣,或褒或贬,属于人性的正常表现。基此, 本文试图显扬我主编的《绿色民法典草案》中的两个新规定以证明该草案的先进和优越 。
一、关于人身计划权的规定
在《绿色民法典草案》中,我们规定了101种人格权,其中人生计划权最为引人注目。 第一分编自然人法第331条规定:“以生命健康权(注:根据现在的已提高的认识,人生 计划权与生命健康权没有什么联系。特此更正。)或自由权为基础,自然人享有人生计 划权”。本条确立了一种新型的人格权——人身计划权。这是参考泛美人权法院(注: 该法院成立于1979年。See Antonio Augusto Cancado Trindade,Current State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Inter-American System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t the Dawn of the New Century,In Tula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Spring,2000.)于1997年9月17日对Maria Elena Loayza Tamayo v.Peru一案做出的 判决做出的规定。了解了这一外国判例,有助于读者明了人身计划权的产生背景和在我 国的可能适用情况。因此,我拟主要根据从网上获得的秘鲁法学家卡洛斯·费尔南德斯 ·塞萨雷戈(Carlos Fernandez Sessarego)在1999年的《民事责任与保险杂志》(Revista de Responsabilidad Civily Seguros)上发表的“新近泛美人权法院判决中体 现的人生计划损害”一文,补充其他材料介绍这一案例及学者的分析,就我国可以赔偿 人生计划损害的情形提出自己的见解。
Maria Elena Loayza Tamayo一案的案情是:塔玛育曾经在秘鲁的军事法院因叛国罪( 严重的恐怖主义行为)受审判,被无罪开释,但后来她又因恐怖主义行为受到了普通法 院的审判。于是,塔玛育向设在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的泛美人权法院控告秘鲁政府违反 了泛美人权公约(注:该公约制定于1969年。See Antonio Augusto Cancado Trmade,op .cit.,.)第8条第4款关于因生效判决被无罪开释的人不得因同一行为再受审判的规定。 请注意,她并非因为她被误认为是恐怖分子起诉,而是因为一事两审起诉。从纯粹的理 论可能性来看,塔玛育仍然可能有过恐怖主义行为,但基于审判的终局性原则(
Finality)(注:这是中国的司法程序中最缺少的一个要素,一个案件可以因为上诉、申 诉、信访等途径无限地审下去,只要当事人有足够的韧性。),即使放错了她也不得再 行起诉。由于她确有理由,她获得胜诉。泛美人权法院责令秘鲁政府在合理的期间内释 放塔玛育,同时要求它“合理地赔偿受害人及其家人并填补已发生的费用”(注:Véase Carolos Femandez Sessarego,El dano al proyecto de vida en una reciente sentencia de la Corte Interamericana de Ferecho Humanos,En http:/// www.alterini.org/fr_tonline.htm.p.1.)。确实,塔玛育在5年的时间内被误认为有恐 怖主义犯罪行为,其学习被中断,人被转移到外国,远离其谋生手段,处在孤独和经济 上的贫困中。由于被拷打,心理和生理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折磨。其人身遭受了各种侵害 ,其人格和职业的可以合理确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对她做出赔偿完全有理由。
这一判决确立了一项新的人权和民事权利:人生计划权。该判决认为,人生计划,就 是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实现的个人的和职业的发展。对它的破毁、延滞或减等,构成必须 赔偿的侵害(注:Véase Carlos Fernandez Sessarego,op.cit.,p.2.阿根廷人对这种 损害的定义是:“或多或少地挫折人生计划造成的损害,由此受害人被阻碍了其人格的 发展”。Véase Ramon Daniel Pizarro,Dano moral,Jose Luis Depalma,Buenos Aires,1996,p.61.)。具体讲,它是第三人损害的“每人有意无意地选择的生活方式以 及所有人都享有的确定我们的生活计划,按我们现在的样子而非按第三人强加的不同方 式生活的自由。”(注:Véase Ramon Daniel Pizarro,op.cit.,p.61.)法院认为,人生计划是与个人实现的概念相连的概念,它维护主体对其生活方式的考虑权以及实现其提出的目标的选择权。它还承认,人生计划权是一个已存在于学说上和新近的判例中的概念。因此,它在判决中援引这一权利并非首创,不过是利用现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而 已。事实上,从1985年起,在秘鲁和其他国家都有关于“人生计划”的作品问世。它们 多数都未使用人生计划的术语,第一篇使用这一术语的论文是1995年在利马的杂志《正 义女神》(Themis)上发表的《关于人生计划损害与心理损害之区别的笔记》的论文;19 96年产生了《存在一种人生计划损害吗》的论文,发表在意大利;同年还有秘鲁著名的 人法专家卡洛斯·费尔南德斯·塞萨雷戈的《人生计划损害》问世,但到了1998年才发 表(注:Véase Carlos Fernandez Sessarego,op.cit.,p.18.)。也有人把这一问题的 历史追溯得更早,认为人生计划权的观念完全来自1948年的美洲宣言,该宣言把精神提 升为人的存在的最高目的和最高范畴(注:Véase Carlos Fernandez sessarego,op.cit.,p.15.)。
人生计划权的提出受到了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构成哲学观念转化为法上的权利的一 个实例。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人是自由的、时间的或非永恒的生灵。自由把 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在主观向度上表现为人有作决定的能力。这种产生在主观世界 中的内在决定意味着主体可以在世界提供的既存可能性中做出一种确定的选择。由于其 自由的属性,人类还是计划的动物。事实上,人都是在时间中按计划生活的。
在自由的客观的向度上,人们主要以主观决定为依据塑造了“人生计划”,它使人的 完全发展成为可能,让人选择试图在其生存的时间内实现的目标。
以上是从自由的人的本体论属性对人生计划做出的说明,接下来从人是时间的属性来 进一步说明同样的主题。人以过去为支撑,从现在出发规划未来[4](P41-)。但人都是 暂时的或曰匆匆过客,都要以死亡告终,因此,人的自由决定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 ,否则就会失去机会,从而造成对自由权的客观表现的人生计划的损害。在这个意义上 ,对人身计划的损害也是对人的自由权的侵犯。对人生计划权的保障就是对自由权的保 障。人生计划代表了人的最高追求,此等计划决定了人在将来的“存在”,此种选择是 存在的最高价值。保护人生计划权,就是保护人的自由的最有意义的客观的或现象化的 表现。因此,对人生计划的破毁、延滞或减等,意味着有形地减少人的自由,导致主体 价值的丧失。按坎萨多·特林达德(A.A.Cancado Trindade,巴西籍)法官的说法,由此 引起的损害是人所能承受的最重的。
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区分人生计划损害与直接损害、丧失的利益和精神损害。实际上 ,泛美人权法院就塔玛育案件做出的判决已区分子它们。直接损害是由行为造成的直接 或间接的财产减少;丧失的利益是丧失的经济收入等,它们都可以以某种方式量化,而 人生计划损害的对象是人的完整实现,必须考虑受害人的职业、能力、环境、潜力和追 求才能确定。
研究者认为,人生计划损害是一种与精神损害不同的损害,前者的侵害对象是人的本 体论上的自由,具有持续性。后者的侵害对象是人的心理,严格说来是人的感情,其伤 害可通过时间的流逝消失或减轻。前者不限于受害人的感觉,而是要影响到他的未来( 注:Véase Ramon Daniel Pizarro,op.cit.,p.60.);它是对人的生存条件的改变,即 “受害人的客观环境及他与他人的关系的改变,此等改变通常会在加害行为引起的痛苦 或悲哀终止后延续很长时间”,例如受害人中断职业活动就是改变其生存条件的一种形 式。精神损害并不导致人的生存条件的改变,它是受害人承受的主观痛苦或折磨,可以 通过慰抚金弥补(注:Véase Carlos Fernandez Sessarego,op.cit.,p.12.)。精神损 害可以首先通过侵害人的身体造成,例如,造成伤口或伤残;也可以通过首先侵害人的 精神造成。这些精神——肉体的损害最终都造成受害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损害。正如人 所共知的,肉体的伤害最终都会干扰心灵,反之亦然。所有的心理——肉体损害都导致 对人的健康的损害,影响人的舒适,受害人因此应得到赔偿(注:Véase Carlos Fernandez Sessarego,op.cit.,p.8.)。而人生计划损害与心理——肉体损害极为不同 ,它损害的对象是人格的自由实现,尽管此等损害也有身体和精神的方面,但它是一种 独立的损害。
按泛美人权法院法官鲁克斯·仁希福(Roux Rengifo)的观点,并非所有的生存条件改 变都要赔偿。该赔偿的“应该是非常实质性的,例如根本搅乱了家庭生活发展的感情和 精神框架的改变,或搅乱了已花费巨大努力和精力的职业的进步的改变”,而一般的绝 望等,不在赔偿之列。塞萨雷戈也认为,只有“其后果顿挫人的整个生存围绕着它旋转 的中心和决定性的轴心,扼杀了人的目的,使之丧失了生存的意义的”的人生损害,才 应该赔偿,以避免这一制度被滥用(注:Véase Carlos Fernandez Sessarego,op.cit.,p.13.)。
人生计划损害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根本损害或人生整体受挫,例如,著名的钢琴 家或外科医生在一场事故中失去了一只手的情形;其二,人生计划被顿挫或取消,导致 明显限制或迟滞主体的正常发展,例如塔玛育一案的情形。当然,遭受人生损害的人并 非完全不可能获得新生活,只是从损害的深度和根本性来看,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而已 (注:Véase Carlos Fernandez Sessarego,op.cit.,p.13.)。
由于人生计划损害的出现,损害的类型变成三足鼎立的格局:物质损害、精神损害或 主观损害、人生计划损害,后两者共同属于“对人的损害”的属概念。人生计划损害是 否可以金钱赔偿?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这种损害应该通过恢复被害人的尊严来 弥补,但审理塔玛育案件的泛美人权法院仍授予原告124190.30美元的物质赔偿。学者 们认为,为精神损害可以物质赔偿提出的理由多数都可适用于人生计划损害赔偿。不过 ,在Cantoral Beavides v.Peru一案中,泛美人权法院仅判令秘鲁政府赔偿原告一笔奖 学金,使他能够回到大学完成其高等教育,实现其人生计划(注:See Megan Hagler
and Francisco Rivera,Bamaca Velasquez v.Guatemala:An Expansion of the Inter- American System's Jurispru on Reparation,In Human Rights Brief,Spring,2002.) 。
当然,侵权行为可以导致受害人本人的人生计划损害,实际上,其亲属的人生计划也 难免受到影响。泛美人权法院在塔玛育诉秘鲁一案的判决中已经反映出受害人的人生计 划与其家人的同样计划的牵连性(“合理地赔偿受害人及其家人”)。2001年11月28~29 日,泛美人权法院却在Bamaca Velasquez诉危地马拉一案中做出了否定性的判决。巴马 卡·贝拉思圭兹是危地马拉革命阵线的玛雅人游击队司令,于1992年3月12日被政府军 捕获。军队秘密地拘押并拷打他达1年之久,并于1993年9月将其杀害。但其妻子杰尼弗 ·哈勃里(Jiennifer Harbury)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为了找到其丈夫,她求诸人身保护 令,提起了几个刑事诉讼;在危地马拉武装力量总部和美国白宫前进行过绝食(其中一 次长达32天)。直到3年后,她才得知丈夫已死。从此,她为得到其丈夫的遗体而努力。 由于尸体被埋在军营内,她的要求遭到了危地马拉政府的拒绝。最后,她于2000年11月 25日在泛美人权法院起诉危地马拉政府,被告败诉,法院判处它赔偿巴马卡、哈勃里及 其亲属的物质损害、精神损害共计498000美元。在人生计划损害赔偿问题上,被害人的 代表“司法与国际法中心”(Center for Justice and International Law)却主张要赔 偿的是哈勃里而非巴马卡这方面的损失,因为她的生儿育女以及与其丈夫度过余生的人 生计划被破毁了。由此提出了直接受害人的家属由于犯罪行为成为间接受害人后要求赔 偿人生计划损害是否可行的问题。这一请求遭到了泛美人权法院的拒绝(注:See Megan Hagler and Francisco Rivera,op.cit.,)。我想这是为了限制政府责任的范围。
让我们回到人生计划权问题的理论方面来。塞萨雷戈认为,人生计划权的设立,意义 在于确定了人在法中的中心地位,因而是一个法律人文主义的举措。在这个场合,他采 用了与中国的相关讨论差不多的术语谈论“人”与“财”的先后轻重问题,确认“人的 这种地位体现了法的本色,因为它是优先保护人,其次才保护人的财产的”(注:Véase Carlos Fernandez Sessarego,op.cit.,p.15.)。这种观点与尹田的保护了财产 就保护了人的观点[5]形成鲜明的对立。该人的观点显然属于塞萨雷戈猛烈批评的“个 人——财产优先的法律观”或“法的惟一经济观”。看来,在中国发生过或还在发生的 人文主义与物文主义的民法观的交锋,至少在秘鲁也发生过。对此有我国的拉丁美洲法 专家徐涤宇的研究可证:“在其他所有法典中,‘拥有’(To have)在位阶上高于‘存 在’(To be),即财产权被界定为人本身权利之上的‘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对其保护优于对人本身的保护,而秘鲁民法典正好相反”[6](P277-)。
由于人生计划权的合理性,它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1999年8月4日至7日,在秘鲁的 阿雷基巴(Arequipa)举行了“第二届国际民法大会:秘鲁和阿根廷民法典改革委员会聚 会。秘鲁民法典15年及其改革进程”。在这个会议上,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和波多 黎各的民法典改革委员会联合制定了一个“阿雷基巴纲领”,宣布,无论是制定新民法 典还是修订已有民法典的签字国,都要遵守若干基本原则,其第26项原则就是“明确规 定对人身或对人生计划的损害的可填补性质”。基于这一纲领,1998年的阿根廷民商合 一的民法典草案第1600条第2款规定,干扰人生计划是非财产损害的一种形式,它通过 身体的或精神的途径,损害或阻碍完全享受生命的实施(注:Véase Proyecto de
Codigo Civil de la Republica Argentina Unifieado con el Codigo de Comercio,
La Ley,Buenos Aires,2000,p.413.)。阿根廷以此举兑现了把“纲领”内国法化的诺言 ,而且自觉地接受了人权法院的一个判例确立的原则。
不难看出,人生计划损害可以由政府引起(注:尽管人们都是从国家责任的角度谈论这 一问题的。See Ben Saul,Compensation for Unlawful Death in International Law:An Focus on the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In Law,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19,2004.),这是塔玛育案件的情形;也 可以由私人引起,例如在钢琴家或外科医生因为事故断手的情形。在前种情形,人生计 划权是抗御政府的公权力滥用的工具。这样的纵向的人生计划损害的发生概率真是太大 ,书不胜书。从西方国家的情形来看,二战期间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迁入集中 营、剥夺全部财产、强制劳动甚至处死——造成的是地地道道的人生计划损害;珍珠港 事件后美国政府把大量无辜日侨赶进集中营的恶劣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也是人生计划 损害,因为他们的人生计划被顿挫或取消,其发展被限制或迟滞。从我国的情形来看, 基于同样的理由,“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受害人造成的也是同样性质的 损害。看到这一点,可以感受到人生计划的概念尽管产生在外国,却离我们一点都不遥 远。从私人造成人生计划损害的可能来看,输血使人感染爱滋病的、错误手术致人残疾 的,都有此等效果。实际上,齐玉苓案件不过是私人侵犯人生计划权的一个实例。我认 为,在此案中,齐玉苓被侵犯的不是受教育权,而是人生计划权。她由于一次冒名顶替 终身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并据此成为城市人的机会,丧失了在有限的人生期间的自由选 择权。如果我们充分明了我国城乡间的巨大差别以及农村人把自己转化为城市人的途径 之有限,就可理解齐玉苓遭受的人生计划损害之巨大。过去,我国法院的武库不够丰富 ,只能选择受教育权保护齐玉苓。《绿色民法典草案》引进了拉丁语族国家的人生计划 权理论,我国法院就可运用新武器保护类似齐玉苓的人生计划受害者了。并且,人生计 划权的引入导致了损害——赔偿由过去的物资——精神两分法转化为物资——精神—— 人生计划的三分法,这要求我国的立法和司法解释进行相应的变革。而且,人生计划损 害的赔偿最重,对这种损害赔偿的承认将极大地提高侵权人的行为成本,促使他们谨慎 运用自己的权力或行动,避免承担高昂的责任。
从某个角度看,我国人民在自己的法律实践中已有了人生计划权的观念,例如分手的 恋爱者或离婚者一方(尤其是女方)提出的赔偿青春损失费要求,就隐含着人生计划损害 的性质。因为轻率地抛弃她们的人改变了其人生计划,给其未来生活的安排带来了难以 弥补的损害,人们在自己的法意识里认为这样的损害是必须赔偿的。由此可以得出外来 的人生计划权观念与我国的本土文化契合的结论。因此,我们的《绿色民法典草案》对 这种新型权利的移植,还有一定的本土资源支撑。
二、关于民事结合的规定
第三分编婚姻家庭法第2条第3款规定:“同性人彼此之间缔结的民事结合,在性质相 宜的范围内,适用本分编的一切规定”。
本条的意义在于追随世界潮流承认了同性婚姻,对之准用关于异性婚姻的一切规则。 要理解本条的意义,就必须先了解同性恋者地位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改善。
同性恋一词是德国医生贝尼基脱于1869年创造的,1890年由性学家哈未劳克·爱利斯 引入英语世界。20世纪70年代,Gay一词普及,原意为“快乐人”,现用来指一切同性 恋者。到了70年代末,女同性恋者认为Gay一词以男性为中心,所以坚持以Lesbian为自 己的名称[7]。欧美的同性恋者有受刑罚、受迫害、受歧视的历史。但到了上个世纪下 半叶,由于人权意识的加强以及对同性恋的自然倾向性的发现,同性恋者的地位日渐改 善,其性行为逐渐被合法化。2002年秋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当福布莱特访问学 者,惊异于电话号码簿上有同性恋者联系方式的介绍;在Inside in New York这样的指 南书中也有这样的介绍(注:参见该书第216页及以次。),而且人们把保护同性恋者的 权利当作民权运动的前沿问题,政客们以标榜自己在这方面的作为吸引选票(注:这是 我于2002年9月至2003年6月居住在纽约期间观察到的。)。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各国 从宪法、刑法和民法三个方面保护同性恋者的权利。下面从简介绍对他们的宪法和刑法 保护;从详介绍对他们的结合的民法承认。
先说宪法保护。1994年2月8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关于禁止基于不同的性取向导致欧 洲公民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决议。经过1997年阿姆斯特丹条约修改的欧洲联盟条约第13条 规定了类似的原则。2000年12月7日通过的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明确规定禁止一切基 于性取向的歧视[8]。1998年经修改的厄瓜多尔宪法第23条第3款明示禁止因性取向的歧 视。新西兰的人权法案也禁止因为性取向在就业、教育、接近公共场所、提供财产和服 务、享受医疗服务方面实行歧视。斐济共和国宪法也禁止因为性取向的歧视。南非宪法 有同样的规定。1999年4月18日,瑞士通过了新宪法,其中规定禁止因生活方式受歧视 ,其含义就是禁止因性取向歧视人(注:Véase Graciela Medina,Los Homosexuales y el Derecho a contraer matrimonio,Rubinzal-Culzoni,Buenos Aires,2001,pp.58s.)。
在刑法上,丹麦、芬兰、法国、挪威、荷兰、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德国、巴西、哥 斯达黎加、瑞典、佛蒙特的刑法典或刑事特别法都禁止因为性取向的歧视(注:Véase Graciela Medina,op.cit.,p.59s.)。
在民法上,世界上承认了同性恋婚姻的有丹麦、挪威、瑞典、冰岛、匈牙利、荷兰、 比利时、西班牙的部分地区、法国、德国、瑞士的一些地方、加拿大(包括魁北克)、佛 蒙特、马萨诸塞州(注:马萨诸塞州高等法院于2003年11月承认同性恋者的结婚权。200 4年2月4日又做出判决,称同性恋者不仅可以组成名义上的家庭,而且也可以享受完全 平等的婚姻权利,并认为这样才符合美国宪法的要求。参见《厦门晚报》2004年2月5日 第19版。1996年,美国高等法院宣布同性恋者享有宪法保护的平等权利。2000年,佛蒙 特州允许同性恋者结成民事结合。2003年,最高法院推翻德克萨斯州的反鸡奸法,承认 同性恋行为合法。2001年,联邦判决支持同性恋者领养孩子。)、阿根廷等法域。丹麦 是第一个赋予同性伴侣同居法律地位的欧洲国家。1968年由丹麦社会党提出第一个立法 案,建议允许同性恋结婚,最终因反对强烈而流产。立法者于是改变策略,成立了一个 “非婚姻同居”委员会草拟新的立法方案,终于在1989年6月通过了丹麦王国的登记同 居伴侣法,并于10月1日实施。登记为同居伴侣的条件基本上与结婚相同;并且,在除 了收养权、人工辅助生育权、父母子女间的亲权之外,在登记伴侣间产生类似于婚姻的 法律效力[8]。挪威继丹麦之后于1993年4月30日通过自己的相应立法,8月1日实施。瑞 典1994年6月23日通过了这方面的法律,于1995年元旦实施。冰岛于1996年6月12日通过 了这方面的法律,于同年6月27日实施。引人注目的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于1996 年修改其民法典,允许同性同居伴侣获得类同于异性同居伴侣的地位。荷兰于1997年7 月5日通过登记同居伴侣法,于1998年元旦生效实施。与前述的北欧及受其影响的国家 不同的是,荷兰法不仅仅是针对同性恋伴侣的,而是不问其性取向、对所有同性或异性 同居伴侣开放。这是最早提出的民事结合制度。更为值得关注的是荷兰人很快就走出了 另外一大步:1999年7月8日议会开始审议开放婚姻法,允许同性恋结婚。经过两院先后 审议通过,2000年贝阿特丽斯女王批准该法,于次年4月1日生效。就法国而言,1999年 11月15日,法国议会通过的第99—944号关于民事团结契约(pacte civil de
solidarité)的法律作为法国民法典的第一编的第十二章,标题为“关于民事团结契约 和同居关系”[8]。它规定,PACS(即pacte civil de solidarité的缩写)制度介于隆重宣告的婚姻和合伙人之间缔结的合伙合同两种制度之间,其成立需要起草一个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PACS契约,最终又可以基于各方决定而解除之。到2002年11月16日,据法国《世界报》的统计:全法国登记备案的PACS契约共计65000个。比利时于1998年3月19日通过关于共同生活合同和建立合法同居的法律,于2000年元旦实施。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于1998年6月30日通过稳定同居法,承认同性、异性间同居的法律地位。阿拉贡省于1999年3月12日通过类似的非婚姻的伴侣法。德国于2001年8月2日通过了生活伴侣法;瑞士的日内瓦和苏黎世于2002年9月22日通过了类似的法律。2003年夏,加拿大总理宣布将修改有关法律,将同性伴侣婚姻合法化,计划先拟定法规交最高法院听取意见,然后送交国会投票表决。该法规以C-250草案的名称在国会以216票对55票获得通过。2003年6月20日,在司法委员会以9票对8票得到通过,不过在该法案的通过过程中存在对立观点的冲突[7]。就阿根廷而言,2002年12月13日,布宜诺斯艾利斯议会通过5小时的辩论,通过了民事结合法,承认了同性婚姻和异性同居为合法,在保守的、天主教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开了这方面的先例[9]。芬兰、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捷克、斯洛文尼亚和卢森堡正在准备制定相应的立法。看来,制定承认民事结合的法律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在我国,由于李银河教授的辛勤工作(注:她在1993年出版(合著)了《他们的世界—— 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书;在1998年出版了《同性恋亚文化》( 今日中国出版社)一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人们过去有的对同性恋者的偏见。), 我国同性恋者的状态日益宽松,人们对他们的看法由犯罪转为病态,由病态转为正常, 不排除将来被视为美德的可能,这是因为他们的结合不生养孩子,不会造成进一步的人 与资源关系的紧张使然。不妨可以把此等结合按照《绿色民法典草案》的术语说成是“ 绿色结合”[10]。
那么,什么是民事结合呢?法国民法典第515-1条的定义为:“PACS是两个异性或同性 的成年自然人为了组织其共同生活缔结的合同”[8]。阿根廷的民事结合法的定义为: “两个人不论其性别或性取向的自由结合,在义务、权利和福利上与普通夫妇享受同等 对待”[9]。由此可见,民事结合不以同性恋婚姻为限,它包括异性间的同居或曰事实 婚。因此,民事结合制度另一方面的意义上承认了事实婚的效力。这实际上是在传统的 异性婚姻旁开辟了一种新的婚姻:一方面,这种异性配偶间享有传统配偶间的一切权利 ,承担一切义务;另一方面,这种结合很容易解除,与解除一般合同的程序差不多,没 有解除婚姻那样的“离婚战争”问题——要记住,在法国,配偶要别居6年才能离婚。
我们的《绿色民法典草案》为何要承认民事结合?因为同性结合是私人的、隐秘的事情 ,只要不以同性恋腐蚀未成年人、卖淫、乱伦,无必要干预(注:Véase Graciela
Medina,op.cit.,p.63.)。我承认同性婚姻还有另外的理由:贯彻绿色生育原则。因为 同性恋婚姻不会产生后代,有利于缓和人口危机。那么,我国是否要把异性间的事实婚 和同性婚姻统在民事结合的共同名目下呢?我认为无必要,因为我国的离婚程序不复杂 ,无必要以民事结合把事实婚合法化,因此,我们的《绿色民法典草案》仅把民事结合 规定为同性婚。
关于民事结合的成立手续,各国有不同规定。在法国,民事结合登记不进入民事身份 登记簿,在另外的登记簿登记,以使其解除程序较解除婚姻简便。而在魁北克,婚姻和 民事结合都在民事身份登记簿登记(第121条附1条)(注:See Civil Code of Quebec,
Baudouin·Renaud,2002-2003,Montral,p.52.)。我们的《绿色民法典草案》把一切关 于婚姻制度的规定都准用于民事结合,因此,民事结合的当事人要到民政机关进行民事 结合登记。民事结合的效力基本同于婚姻,不过解除比较容易。此等效力有配偶间的权 利义务、亲属关系之发生、继承权之发生等。
三、结论
在目前的5部民法典草案中,绿色民法典草案的编纂者最自由。尽管是1998年的司法部 项目,但其编纂未受过任何官方意志影响,编纂者们没有义务考虑从而也没有考虑过它 在适用上的可操作性,因此赢得了把世界上最先进、最新颖的规定吸收进来的自由。我 们试图把它搞成一部世界上最新的民法规定的综述,上面就是它综述的两项对国人为新 的制度。它们可以成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者的参照物,或迟或早地对未来的中国民法典 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