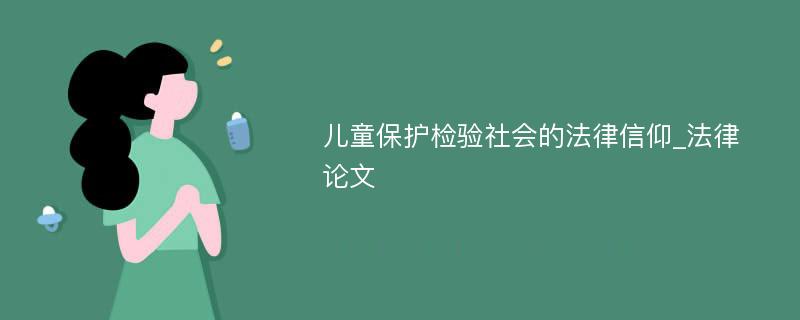
儿童保护考验社会的法律信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儿童论文,法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哈罗德·J·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提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就这个意义而言,法律并不主要来自于国家的立法权,而是出自于许多个人和群体在其日常生活中频繁进行的相互交往的关系,公众和社会的需要应当是法律的主要渊源。所以是在家庭、劳动组合、各类交易行为、父母和子女、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互动基础上,形成了各种法律制度,国家的司法职能最终要体现为维护民间法律关系的权利和责任。
一、信仰决定法律
现代社会的法律体制机制重点在于:司法权在政权结构里的位置,司法权的内部构造以及公民的权利。这样的法律制度有利于提高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行为的可预期程度,使普通民众不仅可以根据明确而稳定的规则来规划和安排自己的行为及其生活,而且对于纠纷发生后会得到怎样的裁决,也可以有合理而稳定的预期。现代法律制度由此既为社会成员提供最为明确和便利的生活秩序,也使社会的价值信仰制度化为共同的心理认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立法是公共权力、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的综合体,是对政权组织和个人按照社会正义原则进行权力及义务的安排和分配。立法的实质和有效性不在于强力,而在于其目的的合理性,即是否体现了社会正义原则。社会正义即社会制度的正义,其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体现在社会基本结构中的社会正义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解决各种社会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分配的问题,即“分配正义”;其次是如何解决社会争端和社会冲突的问题,即“诉讼正义”。然而,在检验有关儿童权益的法律设计时可以发现,由于儿童无论在社会资源、社会合作,还是在社会争端以及社会冲突中都不能成为参与博弈的主体,进而凸显出现行法律制度在对儿童保护上的软肋。四川省自实施《四川省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以来,降低儿童死亡率、提高儿童健康水平、巩固九年义务教育3项目标成效明显,但是在发展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改善儿童生存的自然环境、保护处于困境中的儿童、依法保障儿童合法权益4项目标上则有相当的困难。在有关儿童法律、法规趋于完善,全社会保护儿童权益的观念日益增强的情况下,上述4方面的目标还存在实施中的困难说明了什么问题?
无论是发展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改善儿童生存的自然环境,还是保护处于困境中的儿童、依法保障儿童合法权益,都将涉及儿童生存、生活资料的实质承担者与社会组织机构的交换关系。而儿童权益在现有制度设计中,也只有在这种交换过程中才能受到法律机制的“分配正义”和“诉讼正义”的调控。如果儿童生存、生活资源的承担者因交换成本等因素退出与社会组织的交换程序,那么法律的调控作用则将随之而减弱,甚至退出。所以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二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前款所列行为,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照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的规定,另行确定监护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此款规定确实存在难以实现的问题。所以,保护处于困境中的儿童、依法保障儿童合法权益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制度建设。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社会运行主要形式的市场经济,其本质特点不是公平交易而是自愿交易,市场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在自愿交易的基础上遵守信用,自愿交易与遵守信用互为因果关系。如果仅仅把法律认定为是一种有强制力保障的社会组织方式,那么很可能会陷入将“自愿交易”规则扩大化的困境。在涉及儿童权益问题上,反而将其监护人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作为首要的标准,将体现社会正义的救援干预放在从属于“自愿交易”的位置,儿童权益事实上成为各方利益博弈的筹码。特别是如果仍将对孤儿、流浪儿童等处于困境儿童的救助还限于慈善事业的范围,反映出的则是在有限的法律制度背后的法律信仰的缺失。
信仰的高度决定了法律的高度。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在《礼记·礼运》“大同篇”中就从理想社会的角度,提出了实行社会管理的设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他1516年出版的《关于最美好的国家制度及其乌托邦岛意趣盎然的全书》(后被称为《乌托邦》)中对儿童集体教育、免费医疗、为残疾人提供救助等未来的社会公共服务作了描述。制度的脚步声总是要在思想的光圈内响起。尽管系统的公共服务作为社会制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但是沿着先哲们预期的思想脉络,我们可以感受到寄希望于动员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人类长期以来不懈的追求。将保障包括儿童在内的公众权益规定为政府责任首先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地英国,16世纪英国在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社会分层剧烈变动,出现了大批因圈地运动而流离失所的贫民,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上升。为解决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除了1530-1597年英国政府通过的13个有关处理流浪者的法案外,1601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原有法案的基础上颁布了《济贫法》。直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议会颁布了新《济贫法》,明确规定要求社会救助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实施社会救助是政府应尽的义务的原则。从而构成了以人人有生存的权利、政府有保障公民生存的义务为目标,确定社会救助是一项专门的政府职责、有立法为依据的社会制度。政府承担社会救助的社会责任,既是英国在工业革命的发展需求推动下产生的社会制度创新,更是对于健全社会和界定政府职能的认识创新。人类天然就是群居生活的群体,人类的聚集状态被称之为社会,无论什么样的生产方式都不能改变人类的聚集状态要符合人类共同的生存需求这个规律,政府正是基于此而产生的。所以著名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第三条就写到“政府应当是为了保证人民、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安全而设立的;在不同形式的政府之间,最好的政府是能够提供最大幸福和安全的政府,是能够最有效地防止弊端危险的政府”。《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第二条也规定“所有的权力都源自人民,因而也都属于人民;管理者是他们的受托人与仆人,无论什么时候都应服从于人民”。因此,法律的价值取向不仅是要保障市场交易,更重要的是要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这就是现代法律制度必须要体现的工具性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合理性内涵,前者是指手段的可行性,后者则是对于秩序、条件和规则的认定,是社会化的理性和理智的法律诉求。有关儿童的法律、法规设计,体现的是将政府界定为是主动的责任承担者,还是相对的利益仲裁者的法律视野,体现了社会公正作为法律信仰的条件和程度。当有儿童流浪于街道而庞大的法律体制及其机制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无能为力,那就很难让人感受到正义是现实的、有作为的社会力量。
二、本土资源影响司法机制
中国现代法律制度的建立是清末社会改革与以实力为背景的中西文化对接的成果。所以,在现行法律制度以及运行机制的设计中,仍然可以看到两种司法文化混合存在的印迹。
汉语“司法”本是古时官名,唐代的州、县分设“司法参军”、“司法”。而英文中的“judiciary”是指掌握审判的权力和机构,并不是官职。古汉语中“司”是掌管、主持的意思,司法在中国传统社会则是主管审判、法律的官员。统一行使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政治体制,由皇帝总揽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力成为数千年来各个朝代的体制特征。直到清末将司法与行政权分离,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倡行“五权宪法”才有所改变。可见国家行政权力对于司法活动的影响具有历史的惯性。
统一行政与司法权力并不等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增加。特别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始终存在中央政权集中管理的整个统治空间地域的扩大和官僚系统职能运作效率日趋低下的矛盾,所以地方社会则是通过宗族、乡约等组织从“道德化”的角度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社会组织方式如黄仁宇所言“因采取中央集权制,事无大小,悉听朝廷号令。……因此皇室威权,虽广泛无涯,但其行政技术低劣。政治之安定,并非经常在法律及经济上求改革;而有赖于支持儒家思想,由家族社会之安定性所促成”。政府只注意有关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对儿童权益等并非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问题则脱离于政府行政管辖序列之外,是那些时期的共同特点。
当在现代司法的制度要素基础上建设中国法律体系时,人们特别注意的有:一是司法独立原则。即审判不受立法、行政等其他权力的干涉,司法机关通过案件审查立法、行政等是否合宪合法,从而形成分权制衡、尊崇法律的宪政体制;二是建立合理的管辖与审级体系,统一实施法律。建立严格的法官任免制度,确保法官具备公平审判所必需的知识技能;三是建立和完善“有权利就有救济”的诉讼制度,为受到侵害的各项权利提供救济,强调司法程序中当事人的权利,用公民权利构造正当程序。但是也要看到,在有关司法实践中,儿童权利救济还显得非常薄弱,传统社会的家族、亲缘承担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了下来。然而,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引起大量家庭、亲缘模式的不确定性变化,熟人社会对于家庭、亲缘责任、义务的道德监督压力也不复存在等问题,却在司法理论和实践中反应缓慢,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都是不同的,司法体制的现代改革,是否也应当包括法律机制对于本土化资源的救助和补充,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观,应落实于制度的可操作性、可信任性之中。
三、社会资本规定司法能力
以现代司法制度构建公平的、有效率的社会是普遍的理想。然而在现实中,司法体制与司法能力似乎并不一定就会同步发展。尽管保护儿童权利是已被人所熟悉的社会目标,但是离共同信仰主导下的共同行动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所以历年有关儿童权利保护的研究和政府报告,都提出要提高全社会对于儿童问题的认识。司法制度具有可借鉴可移植的特征,但是要使一种司法制度发挥预期的效力,即司法能力,则取决于社会资本给定的条件。
社会资本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结构型社会资本,另一种是认知型社会资本。结构型社会资本主要是指社会组织机构,认识型社会资本主要是指观念价值。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说:“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收益”。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权威的定义,但是一般都认为社会资本是继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与人力资本之后的一种新的资本形式,是一种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于“马背上的法庭”的司法效力,正是现代法律理念依托乡土情感网络而形成了新的社会道德责任感。这类送法上门的机制效应,不仅降低了农民的诉讼成本,更重要的是以法律信仰充实日常的道德制约关系,从而实现了社会资本的增值,提高了司法能力。所谓好的法律制度并不是只依靠技术专家就能有效地运行起来的,社会信任和体现社会信任的各种非正式组织网络是否与司法运作程序和目标连接,往往是制约司法能力的重要因素。目前在儿童权利的司法设置中,已经考虑了相应的法律规定和程序,但是缺乏对于利用社会资本的普遍安排,如各类民间性质的儿童保护组织具有什么样的法律地位以及如何在体制内发挥作用,还无法从体制的稳定性上形成与司法活动的有效互动。一般而言,弱者总是愿意求助于法律,以便能更好地约束强者,但是因为儿童的依附性社会角色,如果没有来自社会主动的、有组织的关注,司法体制在缺少监督压力的情况下,往往是低效率的。社会资本是促进人们合作行为的规范,对于社会资本的判断,也在一定意义上是垄断司法资源,还是让人们信仰法律的公开性、正义性的体制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