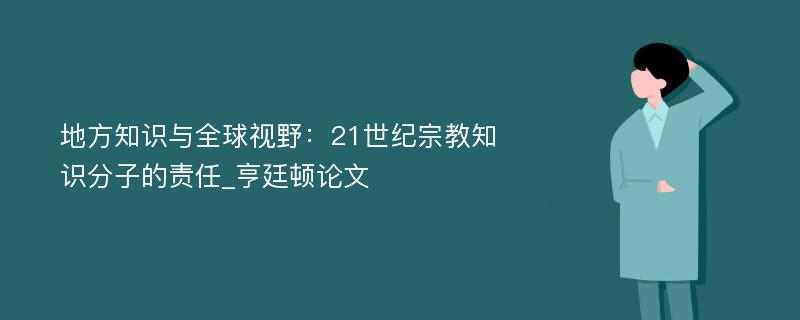
地方知识与全球视野:21世纪宗教知识分子的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视野论文,宗教论文,地方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6)05-0028-09
1994年,我和伊斯兰学者赛义德·胡赛因·纳萨尔(Seyyed Hossein Nasr)共同在哈佛召开过一个小型的关于伊斯兰和儒家的学术对话会,一共有10余位学者参加。1995年,马来西亚大学提议举行同样的对话,我们同意了。马来西亚当时的一位副总理亲自主持了这场上千人的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为“伊斯兰和儒家”的学术对话,会后已经出版了两本书。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后,在学术界引起的震荡远远没有在其他领域大,特别是没有在政治界和地缘政治领域引起的震荡大。为什么呢?1989年时,我离开了哈佛1年,在夏威夷的东西中心文化传播研究所做研究,在那里发展了两个论域,一个是“文化中国”,另一个是“文明对话”。当时主要是谈文明之间的对话,即世界七大宗教——南亚的印度教和佛教、中国的道家和儒家、希腊文明和中东的犹太教,以及后来发展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对话。同时,这种历史的宗教传统也和各个不同地方的原住民进行过对话,包括日本的神道,美国的印第安传统,即美国的本土传统和夏威夷本土的传统。这个对话在宗教界、哲学界已经进行了很多年,而且获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1993年以后,这个问题不仅引起了全世界的学术界、政府、媒体、企业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关注,还引起了不同的社会运动的领导人的长期关注。
一
1.文明对话的背景
1999年,在纽约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首脑会议上一致投票赞同1999年为“和平文化年”, 2001年为“文明对话年”,充分显示了“和平”和“对话”是世界各国乃至全人类的共同意愿,这个文明对话是伊朗当时的总统哈塔米先生所提出的,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冲突和抗衡的残酷事实。地球村(global village)这个概念是加拿大一位传播学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Global village的出现,带来了全球生命共同体的曙光,大家从生态环保了解到,这个地球就是我们的救生艇,和我们自己的生命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从科技、信息、金融、资本、贸易、投资、交通、旅游、移民等,还是各种疾病、犯罪、恐怖活动等的负面传播。地球村显然有助于世界各国落实休戚相关的共识,人们已经不会再孤立地考虑问题,一旦甲地出现的情况,大家会认为与乙地、丙地乃至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密切的联系。但是我们人类社群并没有促成天下一家的现代社会,摆在眼前的现状是,全球化并没有实现东西南北整合融会的大同世界,而在世界的很多地方正好相反,异化、分离、差别和歧视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可见,亘古以来,人类全体同舟共济的必要性没有比今天更为迫切,而国际社会的分歧也没有在今天这样特别的严重。这个分歧不仅是国际上的分歧,是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乃至每个地方的贫富不均。有的地方能够掌握信息的资源,有些还生活在前现代,这种情况非常普遍。那么,面向21世纪如何消解这种矛盾,是每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所必须认识和面临的挑战。
2.地方知识的重要性
为什么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之中,我们要来考虑地方知识?1995年,联合国在丹麦的首府哥本哈根举行了一个社会发展高峰会,集中讨论了三个议题——贫穷、失业和社会解体。地球村的出现不仅没有为全球社区的整合创造条件,而是导致了家国天下。前面已经提到各个层次都出现有社会解体的危险,因此,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大课题。所以我们曾指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正激烈的加深根源意识并导致本土的回应。所谓本土的回应,其实是健康的,不只是原教旨主义,也有很多非常深刻的认同价值。全球化和现代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全球化就是西化和现代化的加速发展,但全球化和现代化最大的不同是全球化加深了区域化和地方化的步伐。
在20世纪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出现的时候,很多学者认为现代化可以把文化的差异性、种族的差异性消解,甚至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同质化(Homogenization)的过程。可是全球化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我曾参加过世界经济论坛,有的人说经济论坛体现一种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确实有趋同乃至同质化的特征。但是文化全球化情况不同,波士顿大学一位很有名的社会学家Peter Burgen教授在很多年前组织过一次关于文化全球化的讨论。在正式进行个案调查之前,他请了几位学者一起探讨文化全球化的特点。当时,他提出了一些很有挑战性的观点,这些观点是从马克斯·韦伯了解新教伦理和这个体系的形成的这一理念发展而来的,也就是从现代化理念所发展出来的。他知道这个提法有问题,但他有意要提出这个看法。当时我就表示反对,他说没有关系,我们还要作实证调查,调查完后我们再来考虑。他认为文化全球化其实和经济全球化是同步的,也是一个同质化乃至趋同的大同。从语言方面来说,他认为世界将来最重要的只有一种语言,其他语言逐渐都变成地方语言。美国的一位哲学家Richer Wurgen今天还有这种观点,他没有到中国访问之前,他说世界上将来只有一种语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语言。来中国访问之后,他说也许有两种语言,其他的语言——法文、德文、日文等基本就退潮了,而且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没有它的内涵和特点,只有一种会在世界各地成为流行文化,这就是杂交文化。他认为,你的文化就是我的文化,你的传统就是我的传统。比如说到上海,到纽约,到东京,特别是看年轻人,他对任何文化传统的认同都很淡漠,特别在电脑、互联网上,他可以和千里以外的人交朋友谈恋爱,反而跟他附近的人完全没有关系。大学里面的教授和他的同事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但是和千里以外的同行可以一起讨论问题,这个现象非常明显。所以,Richer Wurgen讲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1)素食、娱乐、电视和歌曲各方面
这方面我有一些经验,如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做完报告以后,我们从操场步行到餐厅就餐,突然由学校的广播里播放出一支曲子,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英文叫Rap,就是用讲话的方式来传达信息。像绕口令又不完全是。当时,我说我根本听不懂,人民大学教授也说听不懂,大部分同学也听不懂,但是那个调,那个味道振奋人心,大家很喜欢。仅从对这首歌曲的接受来看,文化趋同的现象就越来越明显。另外还有一种预言,即认为将来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是基督教的新教,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根据韦伯的观点提出来的。之后,他对巴西、德国、台湾地区、英国、日本、美国等10个地区的两三年研究后,在华盛顿发表了系列论文了,并编辑成书,书名为《多种全球化》(Many Globalizations)。
Peter Burgen说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不同,哲学家如果他的思考和理论出了问题,那会让他在哲学这一职业上面临更大的困难;社会学家可以提出先理论,理论被别人改正了,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可以马上承认错误,然后重新修订,这点对社会学家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他会公开承认原来的设想是错误的。文化全球化是走向多样性的,虽然经济全球化有本质的单一性,经过分析以后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描述,这中间的很多细致的问题很难讨论。我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有的根源性问题不仅没有被消解,而且突出了,也就是现在流行“认同”,或者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哪一些是人类的根源意识呢?根源性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族群。如果族群的问题处理不当,美国是不能维持成为一个共和国的。美国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家阿克斯·莱克斯·朱丽安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如果黑白的族群问题,包括美国和西班牙语系的族群不能取得协调,那United States(合众国)就会变成Issue States(问题国),变成Issue(问题)共和国了。
(2)语言问题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亨廷顿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最近的一段时间,他所关注的是美国的认同问题,而更关注的是语言问题。许多人都在担忧英文的力量是不是太大了。他作为一个美国学者,担忧美国的文化认同,感觉到因为英文不是美国的宪法规定的国语,在美国最大的州——加州,50%以上居民的母语都是西班牙语。在新墨西哥州,在布什总统的家乡德克萨斯,或者是在佛罗里达,西班牙语有一定发展的趋势。而加拿大,如果不能处理好法文和英文的关系,加拿大有可能分裂,魁北克分裂的意识就非常强。在欧洲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叫鲁文大学,这所大学因为语言的关系分裂成两个大学,一个是French Luven(音),另外一个是Flemish Luven(音),基本上是分开了,根本不可能或很难在近期合二为一。
(3)性别问题
在过去50年的女权运动中,特别是要求平等权的运动在西方国家和世界各地对人类社群的家族体系、人际关系和家庭组合的基本形式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使原来严重的性别有了很大的改观。
所以,语言、族群和性别在认同政治中都起到非常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成为大家不可忽视的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地域问题,就是平时所指的出生地,也就是各种不同主权运动。比如说夏威夷有夏威夷主权运动,世界各地特别在欧洲都有主权运动,在西班牙有巴斯克主权运动,在土耳其有库尔德的主权运动,在各个地方都有原住民的地域。
(4)阶级问题
阶级就是阶层。目前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矛盾非常突出。一个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和一个出生在贫穷的家庭的人,日常生活的经验是根本不同的,这中间的矛盾冲突有的时候比族群、性别、语言的矛盾冲突更大。大家知道,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都有所改善,可它的贫富不均问题也更突出了,现在已经超出美国。贫富差距很大,就会出现非常让人担忧的问题——仇富的心理或者赤贫的心理。这种心理在各大都市已非常明显,虽然社会需要和谐、希望和谐,但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社会又会变得很难和谐。
(5)年龄代
以前我们认为一代人是30年,现在大概是10年,有时三五年。因为社会、经济、信息发展太快,就会以代沟的形式出现,这又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大问题。一个年龄代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新的发展方向。1980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住了1年,和七七、七八、七九级“文革”以后考进大学的头三届学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北京师范大学给了我一间办公室,我可以在办公室里和一两位或者十几位学生一起讨论问题。当时这三级同学组织了一个社团,是由18个院校合作组建的,他们出版一份《这一代》(This Generation)杂志,这份杂志对他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特殊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当时我感觉到,这三级大学生可能代表中国文化和政治发展的希望。
(6)信仰
另外一个更重要方面,就是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信仰。信仰分为各种不同的社群,前面所提到的七大信仰,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0世纪所发展出来的各具特色,又相互碰撞,相对独立的各大文明。卡尔·亚斯贝尔斯在1948年提出,这几大明即使到二战以后,在塑造人类发展过程都还会起到巨大作用,他同时还提出,对人类文明有塑造意义的四位典范性的人物——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和耶稣。当时我觉得是他的个人偏见。而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里,一定要包括穆罕默德、老子、摩西这些人物。
二
正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加强了区域化和地方化,所以根源意识特别重要,各种不同的地方性知识,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体验和经验,它对丰富人类的文明,丰富全球化,特别是从文化的角度应该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但是,在最近二三十年,特别是在西方出现了所谓“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的观点。历史终结论提出者福山直到目前还没有完全改变他的看法,不过最近他开始在考虑信仰问题,讨论信赖问题,他觉得将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可能只有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他认为就是西方模式,甚至有人认为是美国模式。何谓美国模式呢?就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个人的尊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受到一位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伊斯兰教但成就不算突出,就是经验特别丰富、学识特别宽广的学者Wunaluns(音)的影响,他曾经在1992年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伊斯兰的愤怒》(Rage of Islam)。亨廷顿就是根据这一观念提出他的“文明冲突论”的。本来在他的学术著作中主要是讨论从量化的角度来看民主化的进程,并没有把文化因素考虑在内,他把文化因素考虑在内,基本上是一个策略和工具理性的方法,而并非相信文化的重要性。这中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就是这位专门研究伊斯兰教的 Wunaluns教授,在美国有很多学者以他的观点作为对象,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因为这位学者虽然一生在研究伊斯兰教,但是对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同情和了解,而且很鄙视。为什么?他本身就是犹太血统!他虽然研究伊斯兰教,但是对伊斯兰教不了解。但具有讥讽意味的是,他同情巴勒斯坦,也最同情爱德华·赛义德。他是在黎巴嫩基督教传统中培养出来的,他基本上不懂阿拉伯文,对伊斯兰教本身也没有一些体验,他赞同巴勒斯坦,并同阿拉法特很熟悉。他虽然一生都在从事伊斯兰研究,但他不了解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教教义,却对伊斯兰教进行非常狠毒的攻击,这在欧美学术界造成很多不良的后果。
1.文明冲突论的实质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主要是担忧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对西方文明,也就是美国文明提出的挑战,表明上看似乎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同,好像更有文化多样性,其实这是不对的。他只是说在福山所讲的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间,西方文明涵盖了世界。美国文明涵盖世界可能会受到两种阻碍,一种是近期的,就是伊斯兰,一种是远期的,就是儒家文明。而儒家文明也成为美国所谓“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背景。幸好,这种观点虽然影响到美国政府的政策,但美国最强大的而且将来发展中最有意义的力量却来自民间社会,也就是市民社会的知识分子、媒体,非政府组织中接受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少,虽然大家对文明冲突有所误解,但是很想接受福山的“历史终结”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2.国际化与本土化
此外大家还有一个愿望——希望和平,这是从很多具体事实分析后的结果。“9·11”事件以后,亨廷顿本人放弃了他的文明冲突论,因为“9·11”事件所代表的不是文明冲突。无知会造成冲突,但文明不会冲突。“9.11”所代表的悲剧,在很多地方表明的事实就是伊斯兰世界的愤怒。其实这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因为无知和傲慢有密切的关系,这只代表美国社会的一个侧面。布什现在所得到的国内认可率已经降到了31%,可能还会继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文化多样性和文明多样性这样一种观念,甚至说因为全球化导致了区域化,区域化的情形非常明显,像欧洲有欧盟作代表。还可以日本做例子,我去年在日本3个月,主要在东京大学从事学术研究。我觉得日本现在的知识界受到的挑战非常严峻。日本的福泽一平(音)在20世纪初期提出一个“脱亚入欧”论,他想离开亚洲进入国际社会,所以日本走的是国际化道路。但日本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配合得比较成功,就是越国际化就越日本化。在日本旅行就可以看到,建筑、生活习惯、日常生活和日本优良的传统,如日本的书道、茶道,各种古老的传统如相扑等都保存下来了。这和中国“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的摧残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日本国际化和本土化非常成功,但近来也意识到再亚洲化或再区域化问题,即日本需要回到亚洲,要面对韩国乃至中国所提出的问题。
3.区域化与地方化
除了区域化以外,还有地方化问题。地方化的问题和多元现代性有密切的关系。什么是多元现代性问题,到底现代性是一种模式就是美国和西欧模式,还是有跟美国西欧不尽相同的其它模式,比如说东亚模式,或者南亚模式、拉美模式、俄罗斯模式、东欧模式,乃至非洲模式,这都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从人类发展的长远来看,亨廷顿在谈论人类文明冲突的时候,他的世界地图完全是美国中心主义的世界地图,他所担忧的只有伊斯兰世界和儒家世界,因为这两个世界可能会对美国有所威胁。他基本上把日本划在儒家文化之外,这也与一般学者的观点不同。亨廷顿把日本划出来,认为一定要日本和美国的联合,这样华盛顿的统一观才能继续进行,如果日本也属于儒家文化圈,那么西方的力量相对就减少了。另外,他很不重视南亚,也忽略了印度,其实,印度现代的情况已经不同了,他们正在起飞。亨廷顿更是忽略了非洲,这完全是地缘政治强权观念,没有真正深刻的文化内涵。
4.文化多样性与现代化多样性
如果要说文化多样性,或者现代化的多样性,这里有两个基本的预设,可以提供讨论:第一个就是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traditions in modernity),我曾经编过一本书后来在哈佛大学的出版社出了,是讨论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 (the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Asia modernity),而这一儒家传统是多样性的。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世界各地所出现的所有的现代性,几乎没有一种不和特殊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法国的现代性和法国的革命传统有密切的关系;英国的现代性和英国的不注重宗教、注重传统、注重实证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德国现代性和德国的民族主义有密切关系;美国的现代性和美国的市民社会有密切关系。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在欧洲讨论到市民社会的学术讨论会,欧洲的许多学者认为欧洲的市民社会不管是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都不很发达。比如说今天的法国大概40%、50%以上的工人都是为政府服务的,政府的力量非常大。在德国也如此,大学没有私有化和公有化之别,所有国立大学的教授和职员都是政府官员。日本最近才有国立大学法人化的运动,在这之前,国立大学的教授都是由文部省根据政府官吏的方式来支持。这些社会都不像美国的市民社会。所以不同的西方社会有不同的现代性和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还有一个预设问题。我想也可以证明这个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也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当然有西欧的模式,有美国的模式,甚至可能有东亚的模式。很明显东亚社会包括日本、南韩、中国及台湾和香港地区,特别是中国的沿海一带,在很多地方,不管你用哪一种指标来看它都是现代的,它的现代性非常强,但是它的生命形态和文化形式和欧洲、美洲则有所不同。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本身就出了问题,比如说西方最重要的价值是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的尊严,现在都说是普世的价值。但是自由如果没有公义,我觉得在伊斯兰世界如果你要问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可能是justice(公义或正义)。公义和理性可以相提并论,也属于普世的价值,它是同情或者移情,或者慈悲。如果在佛教世界,在东亚,同情的观念则非常重要,它和法制可以互相配合,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让。所谓的礼让,与权利有密切关系,那就是责任和个人的尊严配合起来,那就是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公义、礼让和责任,当然也是普世的价值。可是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有所不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尊严是一个大的潮流,它们普及世界各地,所以也是不可忽视的。它们之间有非常复杂的互动,因此,有些学者说我们现在进入了第二个轴心时代,就是在公元前所出现的大的传统,对现在的每一个大的传统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印度教在印度的影响力,伊斯兰教不仅在中东,而且是在世界的影响力。其实,伊斯兰国家多半是在亚洲,最大的是印度尼西亚,其次是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孟买的穆斯林人口也比较多,中国的穆斯林人数也非常多,有10个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
基督教本身又分成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派,这三派的整合非常重要。新教以美国或者德国为代表,但是天主教以意大利(包括拉丁美洲在内)为主,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有很多矛盾冲突,已经去世的教皇保罗,他最担忧的是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徒变成新教徒。此外还有东正教,主要是俄罗斯和东欧。保罗教皇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罗马教廷代表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实现对话。但是他访问过世界很多地方,就是没有办法去俄罗斯,因为东正教不愿意和基督教、天主教融合,它有自己的发展策略。
除了这两大宗教以外,儒家文化圈将来发展的动向又如何呢?在儒家文化圈里,像南韩现在已有30%以上的人是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但是如果你看整个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地区,日本的基督徒没有超出3%,台湾地区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基督徒占3%到5%。但在台湾地区影响最大的仍然是佛教,而当地的佛教是特殊的佛教,就是太虚所说的人生佛教,后来发展成为人间佛教,到了台湾以后就是星云和慈济功德会,或者法比山的圣严,又叫做人间净土,这些都是入世的佛教。这种入世传教的发展非常迅捷,将来在东南亚和中国大陆也一定会有发展。
三
“二一三四”的分法在学界较流行,我认为这种分法较为片面。“二”是指全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过去的对抗。“一”就是一个超级大国掌控一切。“三”(或“四”)就是很多中国学者认为将来世界是三极化,北美、欧盟和东亚。但是谈到这个三极的时候,大家发现印度正在崛起,所以有学者说也许是四极,我觉得很有可能。俄罗斯有那么多的石油,普金所代表的俄罗斯会坐等着其他地方发展吗?不可能。如果油价增加一块钱,俄罗斯的收入就会增加56亿。俄罗斯地跨欧亚两地,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它的经济肯定会兴起的。拉丁美洲,也就是西班牙语文化的代表,整个伊斯兰世界,甚至非洲,将来在世界舞台上都有它们各自的地位,特别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它们可以为丰富人类的文化做出积极的贡献。我们不应该用一种狭隘的,即“钱”和“权”这两种力量来判断世界的一切。其实儒家文化能够在先秦发展,主要是孔子和代表他的弟子们,直到后来的孟子、朱子。对于既没有钱又没有权的这一批人,可以通过教育,通过文化的理想,通过智慧来逐渐改变他们。如果看卡尔·亚斯贝尔斯提出的重要的人物,不管是孔子、释迦牟尼,还是穆罕默德,不管是老子或者苏格拉底,基本上都不是从“钱”和“权”来出发的。所以我们不要把数据(data)和信息 (information)混为一谈,不要把信息和知识 (knowledge)混为一谈,更重要的是不要把知识和智慧混为一谈。面向21世纪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信息和知识,而是人类如何和平共处的智慧,这些智慧常常是在一般人认为没有现代性、没有价值、不可能在世界舞台上起很大作用的原住民所带来的。现在世界上有各种宗教组织,有很多原住民所代表的各种生活形态,从新石器时期到现在,它们和自然界就有了一种和谐的关系。我们现在人的已经没有办法听到地球的声音,他们可以听得到,我们和自然的关系和他们的感受不同,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地方知识里面找到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
在世界经济论坛上,长期以来都是以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为主导的。从公元2000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突出了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认同问题,另一个就是宗教问题。我被邀请参加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我对经济基本是外行。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21世纪的宗教问题是世界的宗教问题。这在东方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儒教文化的中国地区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曾经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这个思路是从孔德开始的,就是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从迷信的宗教经过形而上的哲学进入科学理性的,到了科学理性后,形而上的哲学就过时了,宗教则根本就不灵了。一直到了今天,主导中国的思想是一个所谓的科学主义。我们大家都非常佩服朱镕基先生,但他在提出“科教兴国”的时候,他常常错误地讲成“科技兴国”,好几次有人提出是“科教兴国”,教是教育,包括人文,包括社会,不是单一的技术而已。但他总是说,我就是说“科技兴国”。“科技兴国”是很难的,还要有“科教兴国”这个“教”,它的范围才够大,才有包容性和普适性。
21世纪的领导人一定要在积累经济资本外,还必须有现代一般人所谓社会的资本,也就是如何运用软实力(Soft-power)的关系。而这个软实力是通过对话、和平相处、沟通、辩难所发展起来的。一个社会,一个学校,甚至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对话的机制,就不能够积累社会资本,即使有很大的经济力量,它也不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就以一所大学来说,它的硬体建筑和经济条件非常好,但是它的学风不好,教授和教授之间没有对话,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对话,教授与行政单位没有对话,它就没有社会资本,而这个学校即使有很大的经济资本,它也不是一所朝气蓬勃的学校。
除了科技能力以外,一个国家还必须有文化。没有文化能力的世界超级大国是不可能存在的,文化能力至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史、哲。没有历史的记忆,没有哲学反思的能力,没有精致的语言来表现人最内在的感情,没有对宗教体验的重视,这些国家不可能成为领导世界的主人。在中国的实业界曾经有过这种反思,一年前,参加过一个“儒家传统与世界级大企业”的学术讨论会,会上提出,如果儒家的世界要创造出特别的品牌,只是学习人家,学习其他外来的观念,就永远走不出你自己的品牌,也很难成就自己的企业。儒家的学术界也一样,假如我们学术界所用的观念、价值、理念、理论都来自西方,而自己的本土不能开发出一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我们同样也很难在国际上成为真正对话的对象。在“五四”时代,中国极杰出、极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像冯友兰和胡适,他们和杜威的关系,绝对就是师生关系。杜威从1917年到1919曾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其间他发表过多次演讲,每一次演讲大家都非常认真地记录,对中国的教育,对中国的社会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杜威在中国所发表的言论对杜威哲学在世界上没起到很大的作用。1972年,有一批学者在夏威夷把杜威在中国的演讲精华部分翻译成英文,但对整个英语世界的杜威研究也没有多少影响。可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在西方进行学术交流,那就不是师生的关系了,主要是一种朋友关系,可以以一种和平互惠的方式来讨论问题,包括我的指导教授,也许年纪比我大一些,可是我可以从儒家的传统、集体的观念,他可以从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提出一些观点,我们可以同时讨论世界上的各种不同的大问题,可以根据不同的资源来讨论,这样能够建立一种互惠的关系。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对话的情景下,宗教在 21世纪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弱,而且越来越重要。
除了社会资本和文化能力外,智商中应该有伦理智慧,有人说还有情商。除了物质条件之外,当然还有精神价值,而这些精神价值、伦理智慧、文化能力乃至社会资本,事实上都和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20世纪的下半叶,特别是到了80年代90年代面向21世纪时,宗教的重要性更显得非常之重要。我甚至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真正的国家领导人,尤其是21世纪的领导人,必须对宗教有很强的敏感性。韦伯曾经说过,他对宗教来讲是“音盲”(unmusical)。21世纪的国家领导人不能对宗教“音盲”,需要去了解宗教,如果不去了解宗教,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宗教的派别,就可以弄得你无所适从,很难处理。如果你对宗教没有正确的理解,要让宗教正常地发挥它积极调节社会和谐、激发人类向上、向最高价值推进的那些健康的力量的功能就不一定能够实现。因为宗教在受到种种的误解或曲解,甚至迫压时,往往会做出极强烈的反弹,这种可能性很大。所以了解宗教是非常重要的。
从事于宗教学研究的人,有的当然是实际的宗教领袖,有的则是从事宗教研究的知识分子,大家都以新的责任来面对21世纪。去年在日本曾有一次世界宗教史大会,每5年开一次,大概有600位世界各地来的学者,日本国内也有900位学者参加。在这个大会上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宗教学界应该发展两种语言,也就是两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和他自己宗教特性有关系的语言,如基督教有基督教的语言,佛教有佛教的语言,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语言。但同时要发展一种世界公民的语言,为什么要发展世界公民的语言,因为世界公民的这个观念是从20世纪到21世纪才特别引起大家关注的,以前是没有的。哲学家维根斯坦(19世纪20世纪初期的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的意义要死了以后才真正知道”。因为我们还没有死,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完全掌握人生的意义,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他又说了一句,“没有离开地球的人永远没有了解地球。”从1960年以后,通过太空探险,人类离开了地球,而且成功地返回来,所以现在我们肉眼可以看到地球的全貌。从物质条件来看,地球的矿物、水源、土地土壤和空气都可以量化,全貌都可以看到,至少现在的太空探险,还未发现另外一个像地球一样的蓝体,也就是适宜于人类生存的地方。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世界各大宗教面对人类所共有的问题,不仅是生态环保的问题,也有失业的问题,社会解体的问题,大家都经过了调节。怎么调节呢?基督教不可能只说我们关注就是未来的天国,而现在的世界怎么样做我都没有兴趣,佛教不能说我们所要求的是净土,现在不过是红尘,红尘让它污染,对我没有影响。
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宗教领袖,对现代人类所遇到的问题——地球的问题,人类的存活问题,社会和谐的问题,极端贫穷的问题,失业的问题等,都应该有所关切。在这个意义下面,宗教领袖不仅是对他自己的宗教社团负责,应该有更宽广的世界公民的责任和世界公民的义务。 2000年,在联合国支持下举行了一次,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宗教领袖和精神领袖的国际大会,会议在纽约联合国开幕,法国也参加了筹划,这是我感觉到最失望的一次会议。参会的世界各地的代表都是非常杰出的宗教领袖,但大家利用联合国这一个舞台,大多在陈述自己宗教的优越性,彼此之间根本没有对话。有一批印度来的宗教领袖,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一个教派,他们不能看到任何女士在他们的眼前出现,因为这是不符合他们的宗教传统,所以他们就排在第一排,回避任何女士,结果上台发表演讲的就有不少女士,他们又不能回头,又不能走,显得非常尴尬。很多其他的宗教刚刚谈到宗教应该和平,宗教应该互惠,突然有一位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徒起来发表看法,他说假如你不信上帝、假如你不信基督教,那就绝对进地狱。会议中间的很多观点,我不能接受,在宗教上的排他性和包容性我们也不能接受,包容性比如说叛教,佛教对叛教的包容,儒家也有包容性,基督教也好,伊斯兰教各种教派也好,但我认为最后和最高的境界是佛教。儒家传统比如像唐君毅先生提的九大心灵境界,对基督教等每一家都给予非常的认可,但是最高的“天德流行”那就是儒家,我对这个观点现在也很难接受。我们必须有一种多元的观点,多元观点的出现要靠对话,宗教界的对话是宗教领袖们应该推动的,特别是要推动与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社会之间的对话。开展这种对话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容忍,没有容忍(tolerance),就不可能有对话。但容忍是最低的要求,只有容忍也不能够形成对话,还要承认(recognition)对方。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血债为例,双方现在不得已至少是互相承认,就是承认对方会存在,我必须跟他对话。除了容忍外,还要承认与他的对话,承认才可能有尊重,有了尊重才可能把对方当作你的参照,能够参照才能把对方当作你学习的对象,能够互相学习才能够尊重对方的“他者”、“异者”。
从儒家传统的角度来看,如果和基督教对话,一个基督教徒不会因为和儒家的对话而变成非基督教徒,通过这种对话可以使双方对各自传统的缺点和长处有了更全面的理解。所以真正的对话,尤其是在宗教之间的对话,并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使对方来接受你的教义,不是传教。但遗憾的是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基督教的传统下,其传教的意愿太强烈,所以有很多的穆斯林学者不愿意和基督教徒对话。不应该在对话时进行传教,也不能利用对话的机会来特别强调其的价值,陈述其的观点,或者厘清人家的误解,这都不是对话的目的。对话目的的先决条件首先是聆听,认真听取对方的声音;第二就是增加自己的视野,通过扩展自己的视野来加强自己的反思反省能力。这才是真正的对话的目的。人类文明差异那么大,要想随意进行对话是不行的,但是如果要发展人类的和平文化,宗教界的领袖要能够发展出一套对话的机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三年前,我和日本的池田大作(他也算一位宗教领袖)进行了对话,所谈的内容是“冲突”与“和谐”的问题。我当时就提了一个意见,不要再说冲突,我们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就是“面向对话文明” (towards civilization of dialogue)。“面向对话文明”就是说,如果这个文明能成为一个对话文明,那么和平的机制就可以发展,也许过于理想性,但是它也有现实性。结果我的意见被池田大作和他的一些同事接受了,所以我们进行了比较和谐的对话,基本上是笔谈,后来在日本的一份叫《第三文明》的杂志上发表了。已经连续刊载了一年半,每一期发表一段,将来肯定会汇编成书。
为什么“文明对话”有可能呢?我相信只要我们秉持一种开放性,能够了解多元,不以自己狭隘的观点强加于人,也就是既要以儒家传统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是“己所欲,施于人”,又能够以“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的消极和积极的心态来进行对话,就可以逐渐发展出一个具有深刻的地方经验的普世意义文明的对话局面。在这中间能够扮演积极角色的就是宗教领袖,也就是从事宗教研究的知识分子。所谓的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绝对不是一个精英主义的提法,而是一个非常普世的提法。所以,中国现在的所有大学生都是知识分子,都可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也应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呢?定义非常简单,就是凡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并对宗教具有敏感性的所有知识分子。如果从事宗教研究,宗教界的领袖能够发挥作用,他不仅能推动自己的语言,他对世界也有公定的语言,那就能够使世界上绝大多数没有宗教信仰,完全是经济人或者政治人、社会人、对宗教没有敏感的人,都能够尊重宗教在社会上所起的积极作用,而且能够逐渐寻找到他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假如宗教界的领袖和公元2000年我在联合国所碰到的领袖那样,只以他们自己的宗教传统作为惟一的价值判断,那么大家所得到的只是各种不同的观点,彼此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横向对话。所以,我认为现代从事宗教研究乃至宗教界本身的知识分子,都肩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特别说明:本文系杜维明教授2006年6月16日在南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与云南大学联合在昆明举办的“文明对话国际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报告,作者授予《思想战线》发表权,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陈松涛根据录音整理、姚继德教授修改审定,未经作者审阅。
收稿日期:2006-05-12
标签:亨廷顿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美国宗教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全球化论文; 经济论文; 现代性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