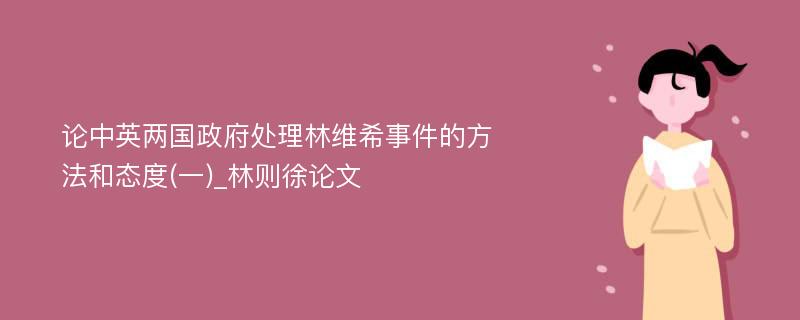
论中英两国政府处理林维喜事件的手法与态度(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国论文,中英论文,手法论文,态度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绪论
清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838年12月31日),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走私活动,并且对林则徐所严厉执行的禁烟和销烟政策寄予厚望。自此以后,中英两国间维持了近二百年之久的和平关系日趋紧张, 最后陷入了对抗的局面。 次年五月二十七日(1839年7月7日)在九龙尖沙嘴村发生的林维喜(注:这是林维喜的英文姓名译音的最初版本,见于《义律海军上校致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函》,1839年7月15日。胡滨泽《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 中华书局,1993年,428页。 英国外交档案中常见的其他林维喜英文姓名译音还包括Lie-wy-hee、Lie-wy-he、Lin Wie hee和Lin-Weihe 等。)命案,对已经恶化的两国关系更是火上加油,使战争危机加深。
过去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中,对林维喜事件的论著并不多见,看法亦人言人殊,然而此案对发生第一次鸦片战争却殊为重要。首先,义律与林则徐为了交出凶手而引发的争端,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埋下伏线;其次,在确认英国公民于中国领土上拥有领事裁判权的《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1843年签订前(注:《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为《虎门条约》的一部分,由清廷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驻华公使璞鼎查爵士议定,作为《南京条约》的善后条款,其内容于1843年7月22 日在香港公布,10月8日在虎门正式签订。 此章程确立了英国人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这是凶手涉及英国公民的最后一件命案,案情亦是较为严重的一次;再者,自1833年英国颁布枢密院令,以容许驻华商务监督拥有设置刑事和海事法庭的权力开始(注:"Orders in Council
at the Court of Brighton,9 December 1833",in Additional PapersRelating to China,No.1,in J.J.O'Meara( ed.) ,Irish UniversityPress Area Studies,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31,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Shannon: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pp.25—28.), 这是首宗依据有关条文而开设海上法庭进行审判的案件,亦是香港有史以来首宗由英国刑事法庭审讯的案件;由于这次审讯是在中国领海上进行,侵犯了中国的司法自主权,所引起的司法冲突问题也是较以往同类事件更为严重的。
从表面上看,林维喜事件只是一宗普通的命案,案中一名中国人林维喜被杀,凶徒涉及数名酗酒闹事的英国水手。清朝自立国至林维喜案发生前的二百年间,这类案例屡见不鲜(注:两广总督阮元曾向道光皇帝上奏谓:“查各夷船日久停泊粤洋,与民人争殴伤毙,事所常有。”参看《两广总督阮元奏审办咪唎坚夷船水手伤毙民妇一案折》,道光元年十月十四日,收录于故宫博物院辑《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1 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8页,总23页。英国布利斯特市(Bristol)的商人在致外交大臣巴麦尊的函件《下列布利斯特签字商人致外交大臣巴麦尊子爵》(1839年10月10日)中亦提及:“又以英国的不法商人来中国的日渐其多,许多快艇小船,阑入珠江,船主水手,不遵守任何法律,不服从任何权威,常常斗殴争打,以致逞凶杀人,无法无天。”见齐思和译《英国蓝皮书——和对华贸易有关的英商呈英政府文》,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2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642页。),同时亦离不开三种常见的情况,或者是洋人杀了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杀了洋人,又或是洋人自戕同类。西方殖民主义者来到中国进行通商贸易,原是无可厚非,但对于上岸酗酒生事的水手疏于管束,最终酿成命案,水手所属的船公司、船主甚至该国领事,应是难辞其责的。
英国人不惜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进行贸易,首要考虑的当然是通商之利,但是在推广贸易之余,还是需要尊重别国的法律和司法权力的完整性。义律作为鸦片战争前夕英国驻华最高级官员,他亦先后对邓廷桢和林则徐声称,英国人到中国进行贸易必遵守中国的法例。义律给邓廷桢的照会声言:他受本国政府的委任“把到这个港口进行贸易的英国船只和臣民置于他的管理之下。他有责任尽一切努力使到过这些范围内的所有英国人尊重帝国的法律和习惯”;他向邓廷桢保证,他“将永远积极致力于那些目的。”(注:《义律海军上校致两广总督照会》,1837年9 月25日,《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233页。 )又谓:“所论别国之人到英国贸易,必遵英国例禁。而英国之人到天朝贸易,亦须恪守天朝法度,其例甚是。可见要在粤省贸易者,自必遵例而行。”(注:《道光十九年第2 号——义律要求宽限新例取结一事之禀说贴》(标题为笔者所加),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东京岩南党书店,昭和42年,162页。 当时英国的首相Viscount Melbourne亦认为:“该国(指中国——笔者按)法例如已知悉,是必须受到尊重的,没有国家会鼓励或煽动其国民去违反这些别国的法例。”引自Viscount Melbourne,"War with China",12 May,1840,in No.I,Subjects of Debates in the House of Lords,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Third Series,Vol.LIV (54) (London:Thomas Curson Hansard,Paternoster Row,1840),p.27。)
义律的一番言论表明,在中国进行贸易的英国臣民会遵守中国法律。而这些英国人亦清楚知道“除了发生杀人事件外,中国政府对于维护英皇陛下臣民与他们本国人民之间或英皇陛下臣民相互之间的和平根本不进行干预。”(注:《义律海军上校致巴麦尊子爵函》,1837年9 月26日,《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221页。 )可惜义律所代表的英国政府在林维喜案发生后,并没有依据上述原则来处理这一事件,对于中方要求交出凶手,义律亦托辞拖延,敷衍搪塞。故此义律和林则徐对是案的处理手法和态度是否正确,及其引申的国际法和领事裁判权问题,以至义律是否称职等等,实有深入探讨和弄明真相的必要。
二 关于林维喜事件的报导与评述
1839年12月16日,林则徐在广州的天后宫接见了因遇到台风而沉没的英国三桅船“杉达”号(Sunda)的15 名生还船员(注: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集·日记》,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华书局,1962年,362 页。 ), 其间他与喜尔(Hill)医生的对话,“谈到中国人林维喜被杀害的事件,对于迄未交出凶手一层,表示非常不满。他不能理解何以我方(指英国政府——笔者按)会找不到凶手,尤其是我方知道有五个人是参加这场凶殴的,这五个人之中理应有一个被交出抵罪。”(注:撷·义律·宾汉(J.ElliotBingham)撰《英军在华作战记》,寿纪瑜、齐思和合译, 《鸦片战争》5册,324页。)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林维喜的命案虽然已发生了接近半年的时间,但钦差大人仍未能结案惩凶,究竟中英双方争执的焦点是什么呢?
在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里,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Frederic Wakeman,Jr.)对中国政府官员处理林维喜事件,有以下一番话:“杀人案虽仍未解决,但只要派水师提督关天培的水勇登上停泊于香港的某只商船,随便捉拿一个外国人作为人质来代替被义律包庇的真正罪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结案。”(注: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208页。 )韦氏似乎建议中国政府在未查明事件的真凶之前,便可随意胡乱抓人顶罪。这样轻率的论断,竟会出自一位学者之笔,委实令人惊讶和不安。对于这一事件的起因和经过的评述,案发当时确实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当时的报导纵使错误百出,荒谬绝伦,但是因为能够减轻英国政府在这件命案上所负的责任,结果仍为其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一些中外历史学家所采纳。在这一节里,我们将对这类当时的报导或事后的评述略加介绍。
Hugh Hamilton,Lindsay (1802 —1881 )所著的Remarks onOccurrences in China Since the Opium Seizure in March 1839 tothe Lastest Date一书,于1840年在伦敦出版,书中记述这件刚于上一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可说记忆犹新。作为一名曾经侨居中国多年的前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H.H.Lindsay 的陈述是否能够忠实反映事情的真相,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对于林维喜事件的起因以及他的死亡经过,这本书提供了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指出:“一名水手正横躺于地上,似是刚打斗过后等待恢复元气又或是喝醉后正在休息,他察觉到两名持着长刀的中国人站于他的身旁,这名水手只好仍保持他的睡姿,并假装死亡,但他仍张开半只眼睛张望,他发现这两名中国人正准备向他的咽喉随意地刺过来,这名水手立即跳起,并抢去其中一把刀,他因此被敌人追逐,直至他爬上一道墙。林维喜就是在爬过这道墙时,失足跌下而被打伤致命。”(注:H.H.Lindsay,Remarks on Occurrences inChina Since the Opium Seizure in March 1839 to the LatestDate (London:Sherwood,Gilbert,and Piper,1840),p.7.)
另一个说法多年来常被一些西方历史学者沿用。H.H.Lindsay 在他的著述中这样说:“义律上校不止一次地声称当日在岸上还有美国的水手,他们也同样牵涉于骚乱的行为之中。这些人(指1840年4 月返回英国而曾在林维喜案中受审和被扣押的英国水手——笔者按)断言当日登岸时遇到一群美国人,这些美国人曾经与附近村落的村民发生争吵,且进入过一间供奉神像的屋宇或寺庙,并且粗暴地触摸这些木制的神像,大概还将装饰在神像头上的金叶拿走。由于村民误将英国人当做捣乱的美国人,以致鲁莽地对漫步经过的英国水手施以木棍和石块的袭击,从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结果是中国人输了,奄奄一息的林维喜被运送至海滩,并搁在那里。我们应否相信这些人的叙述,因为这个版本对这件事件提供一个不同的看法,那些中国人则被视为攻击者。”(注:Ibid.p.8—9.)
在P.C.Kuo(郭斌佳)的著作A Critical Study of the FirstAnglo-Chinese War with Documents中,明显就是沿袭了H.H.Lindsay的说法,指出有理由相信一些美国水手才是导致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注:P.C.Kuo(郭斌佳),A Cri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 With Documents(Taipei:Ch'eng Wen Publishing Co.,1970,Reprinted Edition),pp.119 —120.)。 至于在Winifred
A.Wood、Maurice Collis和Arthur Waley等人的著述里, 虽然对于事件的发生经过没有像H.H.Lindsay所描绘得那样绘影绘声,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同意在林维喜命案发生当日,除了英国水手外还有美国水手在岸上生事(注:Winifred A.Wood,A Brief History ofHong Kong(Hong K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Limited,1940), p.19;Maurice Collis,Foreign Mud:Being an Account of the OpiumImbroglio at Canton in the 1830's and the Anglo- Chinese Warthat Followed (London:Faber and Faber Ltd.,1946),p.242; ArthurWaley,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 London:GeorgeAllen & Unwin Ltd.,1958),p.55.)。
这些学者都不期然地当上了义律的助手,为他所提供的“实情”编造故事。义律在案发后不久曾经致函林则徐所委派负责调查该命案的官员,并谓:“经调查,看来有好几名船上的水手,包括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内,曾经获准上岸,正像人们所说,他们是为了洗澡并在海滩上进行锻炼。”(注:《义律海军上校致钦差大臣所派官员函》,1839年7 月13日,《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36页; 另参阅《道光十九年第87号——义律致钦差大臣所派委员之声明》(标题为笔者所加),《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219页。 此处谓花旗国及英国水手曾容许上岸沐浴及海边散步。)义律还向其上司外交大臣巴麦尊子爵表明他的信念谓:“美国船只的水手实际上与我们本国的水手一样,常常地被卷入了7月7日的骚乱;就我所掌握的证据来说,我可以补充一句,他们也被卷入了由那次骚乱所引起的令人悲哀的和不幸的事件。如果他们的领事确实不承认美国公民与这些事情的联系,那末,他冒险使他的说法不符合真实情况。 ”(注:《义律海军上校致巴麦尊子爵函》, 1839年9月,《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32页。)其实整个事件的真实情况经义律多番掩饰后,已变得愈来愈含糊。义律究竟掌握了什么证据呢?事件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美国水手是否涉案呢?中方官员怎样循此彻查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在本文下一节将有所交待。
Arthur Waley仍强词夺理地为林维喜的致命原因争辩,他认为根据中国地方官员的验尸结果,林维喜是由木棍重击胸部致命的,但是死者曾被击打多次,故此不能明确地断定是由于哪一个水手给予致命的一击。作者还强调说:“一个健全的人是不可能因棍击胸部而丧命。”(注:Arthur Waley,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p.62.)凡此种种推测之言都与义律的狡辩相互呼应。
学者们除了对林维喜事件的起因有不同的说法外,关于命案的发生日期和义律的善后情节,以至使用何种货币悬赏缉凶等事项,都出现多种错误的记述,故此亦需略作澄清。林维喜的命案发生于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1839年7月7日),Arthur Waley所指出的案发日期是6 月27日(注:Ibid.p.57.);而在Jack Beeching 的The Chinese OpiumWars和Immanuel C.Y.Hsu(徐中约)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二书中,皆误记为7月12日(注:Jack Beeching,The Chinese Opium Wars(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5),p.87; Immanuel C.Y.Hsu,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1995,Fifth Edition),p.183.);Jack Beeching 还声称登岸的英国水手为数约三十人之众(注:Jack Beeching,The Chinese OpiumWars,p.87.),这个数字并无引述资料来源,观乎中英两国的外交档案,只见义律在所拟向中国人发布的声明草稿中提及“有好几十名外国水手被卷入进去”(注: 义律: 《所拟向中国人民发布的声明草稿》,1840年3月31日,《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634页。)。此数字是否可信,有待进一步查证。
姚廷芳编著的《鸦片战争与道光皇帝·林则徐·琦善·耆英》一书在论述林维喜案发生与义律的紧急善后措施时,曾经这样说:“又找一位中国证人,以一百元墨币代价,请证人写一字据,证明林维喜不是被打死而是死于意外,以卸去英国水手的责任。”(注:姚廷芳编著《鸦片战争与道光皇帝·林则徐·琦善·耆英》上册,台北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70年,191页。)这段评述有一半是正确的, 另一半恐怕是无中生有。义律的确找到林维喜的儿子林伏超立下字据,证明其父是死于意外,与洋人无关(注:《道光十九年第85号——林维喜之子林伏超所立的字据》(标题为笔者所加),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218页。),但他并没有付出这100元的墨币找人向林家说项, 因为他已答应给予死者家属1500 元的抚恤金。
但是在Gerald S.Graham的著述中,这笔抚恤金又变为2000 元了(注:GeraldS.Graham,The China Station:War and Diplomacy 1830 — 186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95.)。 至于悬赏缉凶,义律曾公布以200元(一作200镑)作为赏金,以助缉拿凶手,而这些钱是以墨西哥银圆或是英镑支付,现时尚难弄明白(注:例如义律在给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的函件内说明:“我已建议由女王陛下政府方面悬赏二百元给任何提供证据的人或人们,那些证据将证明任何其他的人或人们(女王陛下的臣民)犯了杀害那个人的罪行。”而义律在给钦差大臣所委派的官员信件中则谓:“他在英国船只中发布一份通告:如有任何人愿揭发可能杀害当地那名中国人的人(不论是否意外杀害),则给予二百镑的奖赏”。对于赏金以何种货币支付,义律本人也有前后不同的两个说法。参看《义律海军上校致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函》,1839 年7月15日,及《义律海军上校致钦差大臣所派官员函》,1839年7月13 日,《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28、436页。)。魏源在《夷艘入寇记》中说成“悬赏格银千圆,购告殴犯之人”(注:魏源:《夷艘入寇记》,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1974年,7页。); 姚薇元在其《鸦片战争史实考》一书中,又把赏金说成2000元(注: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人民出版社,1984年,39页。这个说法,中英两国的档案资料皆有其出处,但与义律最初所悬赏的金额相差10倍。)。Maurice Collis 在Foreign Mud:Being an Account of the
OpiumImbroglio at Canton in the 1830's and the Anglo- Chinese Warthat Followed一书内所提供的数字更与档案资料完全不符(注: 根据Maurice Collis的陈述,义律为林维喜的家人提供了300 镑作为抚恤金;另提供125镑以应付一些中国官员的敲诈;又在村落里分发了25 镑。见Maurice Collis,Foreign Mud:Being an Account of the OpiumImbroglio at Canton in the 1830's and the Anglo- Chinese Warthat Followed,p.242.这种说法与1839年7月15 日所发出的《义律海军上校致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函》互相对照,就会发现很明显的差异。)。这些错误的资料已经流传了多年,但是提出质疑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从前文的讨论和介绍,可以得知多年以来一些对于林维喜事件的报导和评述,都存在观点偏差和资料失实的情况,然而绝大部分的史家皆没有认真考证有关史实的真确性和更正那些十分明显的资料性错误。历史记录要靠真凭实据来支持,若单凭推想臆测,是站不住脚的。此外,不少以中国近代史和香港史为题的专书,根本未有重视这一事件,有些更只是轻轻带过,评述的篇幅亦十分有限(注:举例而言,以下关于中国近代史和香港史的著作对林维喜事件的评述都较为简单,如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9版,25—26页;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3版,55—56页;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39—40页。Alexander 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the Victorian Era,Vol.1(London: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1900);pp.57—58;Immanuel C.Y.Hsu,The Rise of Modern China,pp.183—184;Jonathan D.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90),pp.155 —156.G.B.Endacott,A History of Hong Kong(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Revised Edition),p.13。)。例如在陈胜粦等编著的《对西方挑战的首次回应——鸦片战争》一书内,作者就没有将林维喜的命案放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鸦片战争的大事年表内(注:陈胜粦、廖伟章及李才垚合著《对西方挑战的首次回应——鸦片战争》,文物出版社,1990年,206页。原书无页码, 此处为笔者按页点算所得。)。
事实上中英两国关于林维喜事件的原始档案资料,经学者多年来的努力,不少已结集成书或辑成提要,成为了解这宗命案原委的重要依据(注: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Third Series,Vol.LIIIto LIV(53—54),(London:Thomas Curson Hansard,Paternoster
Row,1840)。《鸦片战争》1至6册;《林则徐集·日记》;《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林则徐集·奏稿》中册;《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6部,道光十九年文书,162—250页;Lo Hui-min (骆惠敏),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apers Relating to Chinaand Her Neightbouring Countries 1840—1914 with AdditionalList 1915—1937(Paris:Mouton & Co.,1969) ,pp.41 —42; J. J.O'Meara (ed.),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30—31,Opium War andOpium Trade;J.Y.Wong(黄宇和),Anglo-Chinese Relations 1839 —1860:A Calendar of Chinese Documents in the British ForeignOffice Records 《鸦片战争时代中英外交文件提要》( 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45—47.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陈锡祺主编《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下册。这些书籍都是研究林维喜事件的极佳参考材料。)。本文将参考这些重要的原始档案资料,重构林维喜事件的主要部分的真相,并探讨中英两国官员在处理此事件过程中的手法与态度是否合乎法理,公正无私。
三 中英两国政府对命案的处理手法与态度
当我们论述义律如何运用其“公正”的原则来处理林维喜的命案时, 首先不妨阅读一则来自《中国丛报》的最早的报导, 它这样说:“1839年7月7日,星期日,在香港船舶下锚地邻近一个称为尖沙嘴的村落,发生了一场十分严重的骚乱,当时有一大群外国水手集结岸上,一名叫林维喜的中国人在第二天,亦即是星期一,气绝身亡;一份关于这件事件的报告在当天黄昏送达澳门,义律上校在星期二的早上前往香港……虽然在香港正当这场骚乱发生时,以及在第二天这名男子死亡时,我们都只能确定以下一些事实:当时有一大群水手在岸上喝醉和制造乱事;他们与村民发生激烈的打斗;数名中国人被打,当中一人受伤严重,在次日,亦即是7月8日死去……只有极小部分事件的详情获得公开。在法庭上目击者所提供的证据,以至那些被控告有罪的被告姓名,都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注:ART.Ⅱ."Affray at Hong Kong; death of aChinese,Lin Weihe; court of justice with
criminal
andadmiralty jurisdiction instituted; its proceedings; CaptainElliot's address to the grand jury; his address to theprisoners,with sentence of the court passed on the same",in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V Ⅲ,August,1839,No.4,pp.180— 181.)
从上述报导,可以得知英国政府最初希望低调处理这宗命案,基于保密的原则,民间对于这一事件的真相所知不多。这种做法当然最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逃避交凶的责任。义律是一个行事细密和擅于辞令的人,所以在命案发生后的第三天已在香港展开调查(注:《义律海军上校致钦差大臣所派官员函》,1839年7月13日,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36页。此处所记义律前赴香港的日期是7月10日,与前注The Chinese Repository所述晚了一天,此处以义律的记录为准。),当他知道这次冲突是与英船“卡纳蒂克”(Carnatic)号和“曼格洛尔”(Mangalore)号的水手有关时, 只好在案发当地利用金钱收买人心,布下利诱死者亲属之局。他曾多次强调自己的处事原则是公正的,因此他为死者家属提供了1500元的抚恤金;另以400 元作为应付一些低级地方官吏的敲诈;对那些蒙受损害的村民给予100元的赔偿。 他还宣布了两项悬赏,包括如能提供证据指证凶手者,赏200元; 如能提供证据指证骚乱的罪魁祸首者,赏100 元(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28页。)。 最重要的是他用钱换取了死者之子林伏超所立的字据,证明其父是死于意外,与洋人无关(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28页, 义律在信中谓:“死者的亲属给我送来了一封信,声称,他们认为他的死亡是一个意外事故,而不是人们故意造成的。”另参看《道光十九年第85号——林维喜之子林伏超所立的字据》(标题为笔者所加),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218页。 该字据对林维喜的死因有这样的描述:“父亲维禧(喜——笔者按),在于九龙贸易生意,于五月二十八日出外讨账而回,由官涌经过,被夷人身挨失足跌地,撞石毙命。此安于天命,不关夷人之事。”)。义律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平息事件,他还为收买死者家属之事托辞掩饰谓:“无论是意外事故或故意杀害,他(指林维喜——笔者按)不再在这里照料他们(指林维喜的家属——笔者按);因此,义律认为应当对他们提供援助。这是公正的。”(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28页。)既然林维喜之死, 与英国水手无关,义律何须收买林氏家人。林氏家人既然认为其父死于意外,又何须立据以证明“不关夷人之事”。这不是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么?义律所谓“公正”,其实是做贼心虚的一种表现。
义律首次向巴麦尊报告这宗命案时,他还承认:“那两艘英国商船的水手被很不适当地允许在香港登岸,从而被卷入一场骚乱,不幸带来人命的伤亡”(注:《义律海军上校致巴麦尊子爵函》,1839年7 月18日,《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26页。)。 但不久之后,义律却改变了口风,他还向林则徐所委派负责调查这宗命案的中方官员指出,当时获准上岸的水手,除了英国人外,还包括美国人,他们上岸的目的是为了洗澡和在海滩上进行锻炼(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28页。)。 这种做法无疑是想扰乱中方官员的调查视线,亦希望减轻英国政府在这宗命案所负的责任。义律其后向外交大臣巴麦尊报告时,也是坚持这个说法(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32页。)。
在命案发生后数天,林则徐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述:“六月初二日(1839年7月12日)……闻尖沙嘴夷船水手有殴伤华民身死之事, 拟委员往办。”次日又载:“早晨赴抚署会商委员验讯命案、缉拏凶夷事。”(注:《林则徐集·日记》,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二日及六月初三日,346页。)林则徐很快就委派了地方官员前往案发地点, 搜集证据,追查事件真相,并希望缉拿凶徒,按照中国的律法进行审判治罪。
经过新安县知县梁星源和署理澳门同知蒋立昂等官员的调查后,林则徐将案件的侦查结果以告示的形式在澳门的大码头(Praya Grande,Macao)张贴,告示中表明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众多夷人上岸酗酒, 强进尖沙嘴村,并将适逢路过之林维喜殴打重伤致死。 ”(注: ART.V."Proclamation from the high imperial commissioner,concerningthe murder of Lin Weihe",Taoukwang,19[th]year,6[th]month,23[rd]day (2 August,1839),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I,August,1839,No.4,p.213.原文抄录自Canton Press,并没有注明期号或出版日期。)而对验尸及盘查证人的结果则有这样的记述:“新安知县对林维喜之尸首经切实验明,是多处受棍殴伤,在其禀报中已详述,同时会同当地武官,拿获从事收买尸亲以图掩饰真相之刘亚三。滋事当日,若干水手上岸?彼等属何船只?彼等用以打伤林维喜至其倒下之棍棒从何而来?何时,某船长带一夷医去看望救治伤者?何时彼等将林维喜移至海滩?何时断气?何人嘱咐用钱收买尸亲以掩饰真相?当场付钱若干?何人诱骗死者亲属出具字据,证明林维喜乃死于意外?何人签写未付余款支付约据?其中全部应付尾数多少?凡此每一详情细节,刘亚三一一供认,历历如绘。再则,死者亲属业已交出约定付款字据,该字据已译成中文,其中记下船长姓名、船名、金额、应付款日期、何人担保,均与刘亚三之供词完全符合。”(注:lbid.pp.213—241.)
林则徐和邓廷桢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内,更进一步确认上述的调查结果,并谓:“经新安县梁星源验明(指林维喜的尸体——笔者按),顶心及左乳下各受木棍重伤。讯据见证乡邻,佥称系英咭唎国船上夷人所殴,众供甚为确凿。”(注:《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林则徐集·奏稿》中册,674页。)对于义律声称命案同时涉及美国水手一事, 中国政府官员的处理态度亦绝非草率。为找出事实真相,林则徐和邓廷桢曾向美国领事吐哪(Warren Delano Jr.)札谕求证:“义律至今尚称米国人一同在场,本大臣、部堂均未接据吐哪查禀,此一节关系紧要,亦应令其确切禀复,以凭立案。”(注:《咪夷吐哪禀复遵札由》,道光十九年八月十八日,《鸦片战争》2册,319页。)而美国领事其后的回复已直接否认其事,谓:“七月十一日(1839年8月19日), 领事在澳门得接余、李二委员札一道,办理此事,领事即付信下尖沙嘴,查问米国船主等殴毙人之事,十五日即已回复委员毙人命之事,是时本国人并无登岸,亦与本国人无涉,彼时委员察看,亦已知之。本国人并无滋事,闻之心亦甚安。”(注:《鸦片战争》2册,319页。)由此可知义律所谓凶案涉及美国水手的狡辩,明显已站不住脚。中国政府全面掌握了凶案的实情,要求义律交出凶犯,是完全合理和正确的。
而事实上,当林则徐接手推行禁烟行动之际,他对国际法已有初步的了解,在1839年4月8日一封回复义律的公函中,林则徐就谈到:“你所代表的国家自有其法律,这只是在你的国家才会生效。但是自你前来广东进行贸易以后,甚至你的国主也会命你遵守天朝的律例和法令。你怎可能将自己国家的律例行使于天朝呢?”(注:A Digest of theDespatches on China with A Connecting Narrative and
Comments,8 April,1839(London:James Ridgway,1840),p.125.未见中文原件。)林则徐抵达广州后不久,即从任职翻译的幕客袁德辉处得知瑞士法学家滑达尔(Emerich de Vattel)的《国际法》(Le Droitdes Gens )是一部论述国际交往准则的权威著作,林氏对此书十分重视,还请袁氏译述其中的资料以备每日阅览(注:张劲草、邱在珏和张敏合著《林则徐与国际法》,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85页。),他深知要成功地与洋人交涉,不能不了解洋人的法律观点。林维喜事件发生后,他马上经由中国行商伍敦元(原名伍秉鉴,外人称伍浩官),转请美国传教士伯驾医生(Rev.Peter Parker)译出有关战争及随之而来诸如封锁和禁运等敌对措施的条文(注:吴德铎:《林则徐与伯驾——鸦片战争的回响》,《历史月刊》31期(1990年8月),63页; 另参看王维俭《林则徐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考略》,《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1期,60页。 ),以便更有效地与义律展开交凶的交涉(注:杨国桢:《林则徐对西方知识的探求》,宁靖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327页。)。这些译出的文献, 现在有部分还收录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可以说,林则徐处理林维喜案已做到遵从国际法标准行事。义律拒绝交出凶手更显出其理屈词穷的一面。
义律本以为用钱就可以收买人心,而且将美国人也牵涉在内,可以收分散视线之效,这样做对英国水手来说,绝对是有利的。然而,事实证明他的卑鄙伪善行径还是掩饰不了的。此外,他亦早已为挑战中国的法律和司法自主权埋下了伏线。约在林维喜命案发生前的半年,义律曾经为如何管制其本国的侨民行为而感到困扰,因此,他写信向英国政府寻求指示,在致巴麦尊的公函内,义律声称:“无论如何,由于我深信急迫需要通过英国法律或中国法律加以控制,所以我最恭敬地把这些意见提交女皇陛下政府仔细考虑。当我通知阁下,在我接奉不同指示之前,我认为我有责任对于按中国法律逮捕和惩罚一名英国臣民(不论他犯有什么罪)一事抵制到底时,我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焦急情绪将是更加可以解释的,最近具有最严重性质的犯罪行为每天都很可能发生。”(注:《义律海军上校致巴麦尊子爵函》,1839年1月2日,《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3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