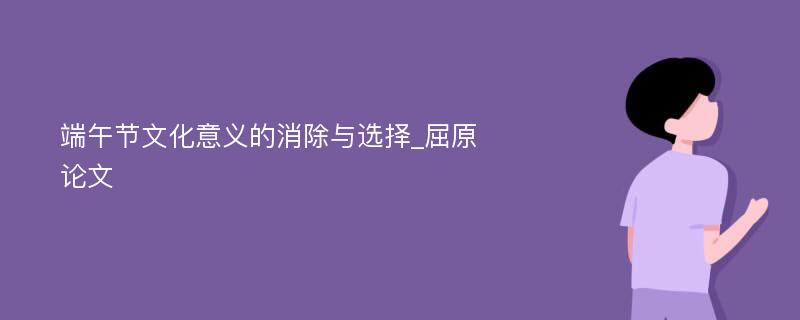
端午节文化意义的淘汰与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端午节论文,意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在荆楚地区是仅次于春节的隆重的传统节日,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岁时节日。今天端午节的形式与文化内涵,是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间的多种文化因子相复合的产物。它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较之其它任何一个节日都要复杂,因此,我们并不打算对其作全面论述,只将端午节在历史发展变化中文化意义的淘汰与选择,作为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
1
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端午节又名端阳节、蒲节、重五节等。《太平御览》卷三十引《风土记》:“仲夏端午,端者,初也。”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引《岁时杂记》:“京师市廛人,以五月初一为端一,初二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午。”《月令广义》云:“五月五日为端阳节。”《幼学琼林》又云:“端午却为蒲节。”仅以所引诸多命名,就可见端午节起源之复杂,但就其命意而言,则显得极为单一。端午,就是五月初五;端阳,因当日炎阳当空,故名之;蒲节,也是因荆楚人喜欢于此日挂菖蒲之类的植物以避毒驱邪而得名。
一般来说,年节习俗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日期,二是仪式活动,三是叙述这一习俗由来的富有某种文化意义的传说。端午节的日期是每年的五月五日,其活动内容有裹粽子、划龙船、挂菖蒲艾蒿、饮雄黄酒等,而作为代表其节日文化意义的传统故事则有多种说法。罗列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纪念屈原。持此种观点的占绝大多数,可谓妇孺皆知。梁代吴均《续齐谐记》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及五色丝,皆汨罗水之遗风。”宗懔《荆楚岁时记》亦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并命舟楫以拯之。”
二是纪念越王勾践。《记纂渊海》引《岁时记》云:“越地传云竞渡起于越王勾践。”西汉《越绝书》说得更具体,认为越王勾践为国雪耻而忍辱负重,于五月五日操练水军,最终复国,越人便以五月五日作为纪念他的节日。
三是纪念吴国忠臣伍子胥。东汉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故以端午节纪念他。
四是纪念孝女曹娥。据《会稽典录》载:“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迎伍君神,溯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遂自投于江而死。”这里又把端午习俗解释为对孝女曹娥的追念。
五是纪念介之推。在《艺文类聚》岁时部“五月五日”条下,有一条出自《琴操》的记载:“介子绥(介子推)割其腓股,以啖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原来与寒食节联系着的介子推故事,竟和端午节也联系起来而具有了纪念介子推之死的意义。
六是源于祭图腾龙。闻一多先生在他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等文中作了详尽的论述说明,认为:“端午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目……端午是个龙的节目。”(注:《闻一多全集》卷五,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七是端午源于恶日的忌讳。五月五日,被古人视为恶日,故《风俗演义》、《论衡》、 《后汉书·礼仪志 》等书有“不举五月子”的记载。
八是端午节由夏至演变而来。因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载有夏至食粽的习俗,隋人杜台卿的《玉烛宝典》亦云龙舟赛为夏至节的主要活动内容。至于为何在夏至节有这些活动,其传说故事已不可考。
以上说法虽然众说纷纭,但以现代大众对端午节所熟知的意义而论,人们大多认为是为了纪念屈原,而我们感兴趣的并非是对端午节的源流作出考辨,而是考察这种选择是如何发生、演变、归一的,也就是说,在相关的人物与传说之中,这种文化意义的选择、走向和定型是如何完成的。
闻一多先生详细考证后得出结论,端午节远在屈原出生之前就已存在,而端午节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龙舟竞渡早于屈原时代一千多年,吃粽子的风俗恐怕在四五千年前就已形成。继而闻一多先生指出,端午是源于吴越民族的祭图腾龙。在远古时代,龙是人们由产生恐惧感而产生崇拜信仰的对象,龙舟是想象中的龙的具体形象化,这反映出尊神的时代,人类对自然认识的程度还很落后,他们无法理解大自然,只有凭借想象并把想象转化为一种变形的现实。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并揭示大自然的面目,于是,龙舟竞渡从对龙的祭祀仪式演变成了端午节的民众娱乐习俗。然而,一种年节习俗如果逐渐失去原有的文化意义,如果不被另一种新的文化意义所代替,那么,这种年节习俗就会在时间中消亡,许多古代习俗之所以不再流行于现代民间生活,也正是因其原有文化意义逐渐在民众中淡忘所致,至于像寒食节风俗相传是为纪念被烧死的介之推,而现在清明节取代寒食节,人们在这一天为烈士或去世的亲友扫墓,以表示纪念之情,很自然地完成了其节日的文化意义转换。实际上端午节并没有因意义转换而流于娱乐性习俗,而是逐渐从对神的崇拜转化为对英雄式人物的纪念。于是,就有了前面所述几种对人物纪念的说法。
2
在关于端午节纪念人物的说法中,牵涉到五个被纪念对象:屈原、勾践、伍子胥、曹娥、介之推。当我们考察有关这五个人物的传说故事时,可以发现两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
其一,他们都是悲剧性人物,都带有或强或弱的悲剧色彩,最典型而悲剧性最强烈的是屈原。屈原寄楚国的振兴于楚王,以图统一中国,他担负着一个体现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大势,而又不得不归于失败的历史使命。历史的必然要求(统一天下)和承担这个要求的英雄实际上又不可能将它实现,这使愿望和效果、使命和前途、个人与历史之间产生激烈冲突。冲突中,屈原对自己的愿望抱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要将其付诸现实,为自己的“美政”理想上下求索,哪怕是经受无数次的挫折和打击,而始终不渝,这更加重了悲剧的浓烈色彩。忠臣伍子胥遭受诬陷,自杀身亡,被吴王夫差将尸体抛入钱塘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悲剧,“敌国破,谋臣亡”的悲剧命运无可避免地落到了伍子胥的身上,以龙舟竞渡的形式来纪念他,表达了人民对遭受悲剧命运的忠臣的同情。越王勾践体现了悲剧中的崇高精神,他在国家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体现了人物身处苦难,矢志复仇的韧性美。介之推被活活烧死,本非晋文公之所愿看到的结果,但有功之臣不被赏,其生命却遭到被摧残而毁灭的悲剧。曹娥的悲剧色彩相比之下也许会淡些,但不可否认在她身上也体现出悲剧性,她异乎寻常的执著孝顺曾震撼过许多人的心灵。选择悲剧性人物作为端午节的纪念对象,暗示着民众的集体无意识选择和这一节日文化主题的变奏:即由对神性的崇敬向人性的尊重的转变,由祭图腾龙到纪念世俗性人物的转变。其二,由于人物的悲剧性品格中加注了新的社会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在历史嬗变中演化为相对稳固的价值观念形态,而他们正是这些价值观念形态的现实载体,他承载了历史的文化积淀以具体代替抽象的存在。屈原爱国、忧民,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楷模,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诗人像屈原那样被人们热爱过,这种热爱的前提来自屈原对人民、对国家的强烈热爱之情。在爱国忧民前提下寄希望于君王的忠臣形象也适合了统治者的心态,在封建权力话语系统和民众话语系统中都占据着显著的地位。伍子胥的忠诚、勾践的奋斗精神、介之推的至死不渝、曹娥的孝顺,历来都是为人们所称颂的。在民众心中,人物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同位语,人物所固有的可感性和形象性有利于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接受,这就使端午节文化意义的转换与选择显得非常顺利。
然而,当端午节的文化意义转换过程完成之后,它不可能容纳形形色色的传说故事,文化意义的归一化趋势必然出现。既然上述人物都象征着某种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和历史社会以及传统文化紧密相联系,体现出极强的价值张力,那么,它必然最大限度地融汇各个时代对此种价值观念新的理解和看法,为适应归一化的趋势,每个与端午节相联系的人物之间,也必然产生其所象征的文化意义的竞争、淘汰与选择。
上面已经论述到,屈原最突出的精神品格是爱国忧民,这种精神品格是建立在广泛而坚实的民族性基础之上的。上自以帝王将相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自然地接受了屈原并加以褒扬,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话语,对于加强和巩固屈原在端午节文化意义中的地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至庶民百姓同情屈原的不幸遭遇,充分接受并赞扬屈原,是因为他代表了民众内心深处对自己所属民族的依恋与热爱,以及彼此之间的信赖和帮助,屈原爱国忧民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成为唤醒民众对这类情感体验的催化剂。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者,他也自然受到了历代儒生的大事宣传阐扬,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屈原的崇敬与赞扬成为了深入人心的千古定论,屈原精神已化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真、善、美,代表着崇高与伟大。
我们再来看其他几位人物。伍子胥最突出的精神品格是忠,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忠是建立在对封建君主的愚忠之上的,他的忠指向的是一个统治着吴国的君王。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对忠的选择并非是盲目的,如果君王不仁或昏庸,那么,忠就失去了价值依附,他的忠便不能在民众中得到多大的响应。因而他所体现的文化意义在竞争中就显得苍白无力,所以,以端午节纪念伍五胥也只能是一时一地的做法而已。勾践身上也有一种鲜明的精神品格,他一生之中,曾兵败国亡,又曾卧薪尝胆,忍辱复国。尽管他也成为了历代人们所称赞的人物,但同样我们注意到勾践是一个封建君主,他卧薪尝胆乃是受一种强烈的复仇意识所驱动,而不是把人民放在首位的。范蠡曾指出:“越王(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共乐。”(注: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他逼迫功臣文种自杀就自然暴露出他残暴的本性和狭隘的心灵。他的内心深处带着极强的自私怨恨情结,为消释其怨恨,人民成了他实现复仇目的而被利用的工具。曹娥的孝代表的是一种对血缘亲情的注重,源于原始氏族社会血缘基础的人伦精神,在曹娥身上表现出壮烈而震撼人心的力量,虽然她的表现得到了特别重视伦理观念的我国大多数人的表彰和赞赏,但较之屈原,她的文化意义指向显得太单一化,缺乏屈原精神品格的完美与丰厚。至于介之推所代表的义的精神品格,除了意义的单一性外,他死于火的事实,使他不可能与端午节的水性文化特征顺利融合,因而,以端午节纪念介之推就显得牵强,迫使之自然最早地退出这场文化意义的竞争,转而在寒食节中获取他应有的位置。
在屈原与其他几个人物的比较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人物精神品格的差异性决定了他所代表的文化意义的宽、狭或丰厚、单薄之分。无论伍子胥的忠、介之推的义、曹娥的孝,还是越王勾践的复仇意志,所含蕴的文化意义都缺乏民族整体文化价值取向的支撑,也就难以与屈原所代表的文化意义相媲美了。虽然如此,也并非意味着这几个人物在短时间内完全失去其影响作用,从唐代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在其中“五月五日”条下同时收进纪念屈原、纪念介子推和纪念曹娥三说来看,屈原故事最终“独占鳌头”,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过程。
至此,我们有必要指出:光耀千古的屈原精神是在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土壤中孕育而成的。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思想和文化空前活跃的黄金时代,地方千里的楚国是四方百族文化的并汇之处,楚文化以开放的姿态融聚百家各族的文化精髓,代表着当时中国文化的巅峰。文崇一先生赞颂楚文化道:“这是一个狂飙式的文化,有最温柔的诗篇,也有最强大的武力。”它敢于同大国争雄,又勇于接受小邦文化,正因为“它拥有最多的人民、土地和财富”,又具有博大的胸怀,进取的雄心,创造的勇气,所以能产生彪炳史册的人物——屈原(注:文崇一《楚文化研究·序言》,台湾省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十二,1967年,第1页。)。 苏仲湘先生指出:荆楚“成为广阔的中国南方各族融合的中心,是当时民族联结和融合的一个典型。”(注:苏仲湘《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楚历史与文化》,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 )楚文化除包含着周文化和南方固有文化传统之外,它还包容了东方夷文化因子,商文化因子以及西北文化因子等。众多的文化复合成楚文化的雄浑、深厚。同样,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对周边地区文化也发生着深刻的影响。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便不难明白为什么以端午节纪念屈原不只是楚国,他已属于全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依托,代表着中华民族最完善的精神品格。屈原也正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代表着楚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性格的多样性、丰富性。概而言之,屈原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性、道德精神和诗性智慧。屈原首先是位政治家,对内同楚王商议国事,发布命令;对外接待宾客,应对诸侯。他极富有政治天才,又始终把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保持高尚节操正道直行,对“美政”理想执着追求,九死而不悔,批判邪恶势力,也敢于同他们作毫不妥协的斗争,甚至对楚怀王的昏庸与失信,也敢于指斥,而这一切表现,都只出于一个目的,这就是振兴楚国,使人民幸福,最终统一中国。同时,屈原也是一名伟大诗人,他具有最典型的诗人品格。他融合提炼楚地的语言,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形式——楚辞。《楚辞》的形式是符合人民大众审美倾向的艺术形式,其中《九歌》是对民间祭祀歌辞的艺术加工,而又回到了民间,成为民间长期流传的歌辞;《天问》也是采用民歌中惯用的对答形式,其中有的内容可能就是民歌歌词的记录,玄妙瑰丽的色彩,宽广深厚的思想,独特的艺术创作形式,使屈原的作品极富有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屈原作为一个坚贞而忠诚的利他主义的楷模,一个睿智而憧憬美好政治理想的政治家,一个遗留下大量感人至深且极具影响力的诗歌作品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诗人,他成为了楚文化土壤孕育出来的,将政治理性、道德精神和诗性智慧高度结合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伟人。那么,屈原成为端午节文化意义竞争中的唯一被选择者,并非是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民族文化精神选择的必然。屈原精神融会了我们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伦理观念,乃至社会政治理想而形成于我们民族的精髓之中。屈原之后的每一个时代,人们都可以从屈原的悲剧故事和文学作品中,重新唤起意识深层的集体无意识,并使之“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注:荣格《集体无意识和原型》,载《文艺理论译丛》第1 辑。)
3
年节习俗本身的仪式活动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作为一种独特民俗文化景观的端午节,其仪式活动在原初阶段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龙舟就有象征神灵的意义,这一点从各种资料中都可以找到有力的佐证,而竞渡过程中也有诸多的宗教性。端午插菖蒲挂艾蒿是为避邪消灾。在历史嬗变中这些仪式的宗教性并没有得到加强,反而越来越淡化,最终变成社会性的世俗活动。这与中国文化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不无关系,社会世俗性取代宗教的神圣性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屈原精神所具有的最广泛的社会性更是为仪式提供了强有力的背景支持。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性的仪式活动是传统文化及相关因素的现代载体,这种载体体现出文化内在演化的轨迹。仪式的现代性转换回应着端午节文化传承中固有的活动方式,这些仪式也是对古代民族性的一种现代主义表达。如龙舟竞渡成为现代体育竞赛项目和旅游活动内容等等,可见端午节举行的活动,已浸染了浓厚的现代文化色彩,那么,它在现代文化环境中,是否会逐渐丧失其原有的传统文化精神品格呢?我们在现实的景况中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端午节的活动在一些地区也卷入了“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创造环境,繁荣经济”的热潮,利用端午文化进行龙舟经济交易会和旅游活动,已成为端午节的重要内容,端午节明显地反映出商品经济时代的文明进步,对这种新的端午现象,作出决然的反对难免有不符合现代文化要求和反对进步的嫌疑,但我们所更为注重的是端午节习俗中的文化价值而不是其商业价值。极易被忽略和掩盖的文化价值是无形的看不见的,但却具有超越时空的存在意义。商品经济价值却是一时一地的,具有片段性和瞬间性,它带给人类的往往只是物质上的而不是文化意义上的价值,事实上,这种原本带有强烈审美性的仪式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浸染了世俗功利性,如龙舟这一文化符号在一些地方成了商业广告的宣传材料,有些地方将龙舟本身也变成商品,饮雄黄酒成为某些商人推销其商品的借口。这里,不仅仅是文化意义的淘汰与选择,而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为维护自身而作出的种种回应和努力,但能否使传统的文化意义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得以延续和发展而不被异化,这取决于多种因素如活动方式的可操作性,传统文化的自下而上的影响力以及对现代文化语境的阐释范围和表达结果。闻一多先生在他的《人民的诗人——屈原》一文中带着肯定的语气说:“惟其端午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和中国人民同样的古老’,足见它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可分离,惟其中国人民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如何重大的作用。也惟其远在屈原死后,中国人民还要把他的名字,嵌进一个原来与他无关的节日里,才足见人民的生活里,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注:《闻一多全集》卷五,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根据两千年来屈原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所确立的不可移易的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端午节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其根本的文化意义不会被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