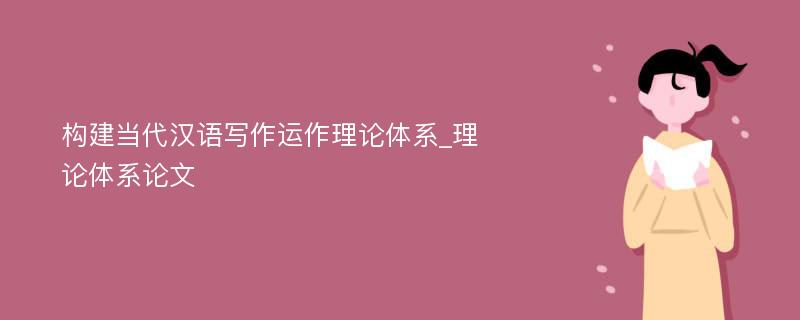
建设中国当AI写作作学的操作性理论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操作性论文,中国当代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应该承认,中国当AI写作作学至今仍然未能形成自身的学科理论体系,因而仍然停留在学科建设的草创阶段。草创阶段的学术理论其最明显的标志是学科范畴缺乏稳定内涵,并且处于各自独立的状态,不能构成自洽性,亦即不能互相补充,互相说明,互相支持,达到有机的统一,形成理论上的层递性和系统化。任何成熟的学科理论其基本概念,或者基本范畴都应处在一种严格的逻辑关系之中,既不能任意抽出,也不可随意插入。很明显,中国当AI写作作学的基本概念距离学科体系的基本要求相去甚远。
虽然,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写作学的各类教材纷纷出版,据估计已达数百种,可能是人文学科中教材数量最多的。但是数量的众多与学科理论水平之低下,正好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是因为中国当AI写作作学缺乏必要的学术研究基础,至今在偌大的中国仍无一个写作学术研究的专业刊物,而在各大学的学报上,称得上写作学的学术论文寥寥无几。即使有些青年学者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也未得到充分的鼓励和必要的批评,而客观形势对于写作学又空前迫切需求,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写作教材在低水平上不断重复生产的现象。①
造成中国当AI写作作学这种状况的历史原因自然很多,但是就理论本身而言,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缺乏写作学科的自觉性。相对于语言文学等等学科,写作学科是比较后起的,因为后起,不免借鉴,由于借鉴不慎,竟至变成了依附。
这种依附性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把写作教材当作一种知识,这大概要从六十年代初期北京大学汉语教研室出版的《写作》算起②。直到新时期刘锡庆主编的《写作基础知识》仍以传授知识为己任。应该承认,这是一种基本观念的错误。定作不同于文学理论、语言学、逻辑学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一种传授知识的学科,在这一点上不清醒,遂导致写作学的架空。写作学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实践的学问,而实践的学问是不能靠理论的演绎来完成,而是需要一代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从实践过程中进行理论概括的。中国当AI写作作学的贫困,本来需要比文艺学、语言学逻辑学更具原始创造力的人才,像许多学术领域的开山大师一样,直接从经验、直觉和原始素材、历史资料作出第一手的抽象的,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高等学校各学科的竞争中流落到写作学科来的却大多数是缺乏原创性的人才。正因为这样,写作学就非常方便地依附于邻近学科的知识。讲授知识之所以在一段时期中被广泛接受,其原因盖在于从教学队伍的素质来说:别无选择。
从理论上说,这是一种让步,当然会导致日后学科的危机;从实践上说,好像是一种权宜。但由这种权宜带来的危机更为严重。因为在大学课堂上,这种“写作知识”来自文学理论语言学、逻辑学,又比文学理论、逻辑学和语言学零碎而粗浅。最明显的莫过于关于“主题”的范畴,写作知识从文艺学中抽取了一些贫乏的僵化的结论:主题是客观的反映,主题又是作家主观的思想,接着又列举了许多大作家对于主题重要性的论述。所有这一切都充满了知识性,但却缺乏大学课堂讲授的生命:可讲性。教师没有什么可讲的,学生没有什么可听的。
这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学科依附现象。本来,主题范畴并非文学所固有,乃来自音乐,主题是乐章之主要旋律,相对于变奏而言。文学理论在借用这对范畴时本身就不够严谨。在音乐中,主题和变奏是旋律本身的一种结构,主题是丰富曲调中的贯穿始终、变化很少的部分,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基调。文学理论把它变成贯穿中心处于领导地位的观念、思想,本来就有点粗浅了,写作学在借用文学理论这个范畴时,却对这种不成熟现象没有起码的批判精神,因而写作学对文学理论的依附,不是依附文学理论比较深刻严密的部分,而是依附文学理论比较幼稚比较简陋的部分。当然,也有些写作知识,还作了一些努力,例如,把主题说成是“文章的灵魂”。灵魂相对于肉体而言,这有点像主题与变奏的对立统一,但很可惜的是,这仅仅是一个比喻,而比喻本身的内涵如果不加阐释的话,是不能成为一种科学的阐述的,任何科学范畴都不可能仅仅借助于比喻而深化。
缺乏理论基础自然引起了写作学界广泛的焦虑,于是就产生了中国当AI写作作学科建设的第二阶段,向新兴学科借用理论向新引进的学科借用概念和原理。在八十年代中期,写作学在文学理论的带动下,投入了引进新理论的热潮。一时风云际会,从科学主义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到人文主义的存在主义、性心理学、话语理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由此还产生了一本笔者也有幸参加的《高等写作学》。这本多所大学联合编写的教材,满足了写作教学队伍追求理论的虚荣心,但是五花八门的“理论”,来得快,消失得更快,今天还有谁相信,只要挂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招牌,文学艺术的奥秘就昭然若揭了呢,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本身的薄弱并不能因为时髦的理论招牌而突然变得充实而深厚起来。写作学的基本范畴较之文学理论更为空疏,因而那怕再尖端的理论也只能成为空洞的框架。
这一回写作理论的依附性,不但表现在它对文学理论范畴的生搬硬套上,而且表现在对文学思想更迭的潮流缺乏独立的批判性上。
新时期十多年的写作理论追求说明,对于写作学科的建设来说,目前所缺的不是一本又一本的教材,而是站在写作学本身立场上对已有的写作学教材的总结和批判。当前最缺乏的是写作学的学科自觉性。最迫切需要的是立足于写作学科自觉性的基本范畴的重建。
大学教材,那怕是百科全书式的教材,充其量也都是一种高级的普及著作。其普及的内容乃是学术研究的公认的稳定的成果。在学术研究成果缺乏起码积累之时,教材也就缺乏普及的内容,因而也就只能停留在对邻近学科的依附上了。
写作学科长期以来之所以缺乏独立的学科意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找不到写作学科的根本的特点。纯知识的传授和纯理论的追求都不是写作学科的特殊规律。写作学最大的特点,写作学科的生命就是它的实践性。它不同于文学理论,也不同于逻辑知识之处,就是它的可操作性。知识也好、理论也好只有成为操作能力的一环,通向有效地阐明操作的规律,提高实际操作水平,才算是写作学科一个组成部分。照搬知识和其它学科理论,或者把其它学科改头换面,并不能说是进入了写作学科体系的创造。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特殊的目的性、特殊的思路、特殊的切入方式。对于同一现象,不同学科,由于目的、思路切入方式不同,应该而且可能产生不同的范畴。不同学科共用的范畴长期不在内涵上分化,只能导致低水平的混淆。如哲学把世界划分为主观与客观两个世界,艺术就不能满足于这种哲学范畴的基本划分。文学理论的特殊目的在于文学写作的普遍规律,而写作理论则比文学创作更广泛,其特殊目的在于将文学与非文学的理论付诸实践,具体化为可操作性的原理。
本来,最理想的途径就是写作学另外建立一系列相应的概念和范畴,但是,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在学科草创阶段,经采用折衷的办法,亦即借用相邻学科的理论,尤其是那些已被广泛接受的范畴。但是由于文学、语言、逻辑学具有学术优势,因而必须高度警惕借用变成套用,而套用则必然妨碍写作学本身内涵的发生和发展。不借用就等于说是从零开始,凭空产生,这是十分艰难的。借用的目的,仅仅在于利用概念的形式来孕育新的内涵。但学科概念往往比较稳定,比较严密,对新内涵的发生又有相当的抑制作用。如无强烈的学科独立意识,必然造成惰性,亦即学科依附性。
就以主题范畴而言,写作学要求的操作性是文学理论的描述性所没有的,倒是在音乐理论中,主题与变奏的对立还包含着某些操作的基础。这时,对于有志于写作学科独立的学者,就不应该对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再抱过大的希望,而应该面向直接操作经验,作第一手概括。
对于任何一个具有写作操作经验的人来说,提炼主题的第一个大障碍是素材、资料、思绪的芜杂,如果任其芜杂,则无主题可言,故从操作性来说,主题就是在芜杂而丰富的素材、资料,思绪、思想中去寻求其内在的单纯的深刻联系。简而言之,主题产生于素材与思绪的脉络的凝聚,再按凝聚起来的闪光的、独特的、深刻的观念或体验的秩序,重新同化、调节、提纯、剔除,重新创造一种准则。从正面来说,主题是一种选择的目的性,从反面来说,主题又是一种排除的标准。任何对于这种准则的违背,都只能导致主题的损害,不是过分狭窄、乾枯,就是主题的模糊甚至转移。
对于行文的过程来说,主题不但是一种终极的目的,而且是一思绪的结合和展示过程。这里有连续、跨越、遥远和深化的控制问题,也有对于主题徘徊、浮泛的防止问题。
对于不同文体不同风格的作品来说,主题有不同显示的方法和要求,是开门见山,还是卒章显志;是政论语言的鲜明强烈,还是艺术语言的弦外之音,都是主题在操作过程所遇到的问题。而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的经验就是主题范畴的特殊内涵的基础。
当AI写作作学要形成自身独立的主题范畴,不应指望从任何相邻科学去搬用,而应该从自身活生生的经验中去概括、去提炼,去作理论化的第一手抽象。
如果不作这样的艰苦努力,不但任何写作学科的独立体系都是空谈,而且一切大批量引进的科学主义或人文主义的西方理论都只能是华丽的包装而已。写作学要解决的是在操作过程中面临的矛盾,以及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的一般规律,还有解决这矛盾所应防止的偏向。把这样的操作经验理论化并不十分神秘,只要有实事求是之心,而无哗众取宠之意就成。一切邻近的学科理论、西方的尖端文论都要与写作本身的操作性要求结合起来,或者说得粗暴一点,都要经过写作学科操作目的性的严格批判、化解和扬弃。
对于中国当AI写作作学来说,目前最缺乏的并非是对于相邻学科现成范畴的借用,也不是西方文论体系的批发,而是以写作操作性基本范畴去积累研究成果。以中国写作学目前的学科水平,远远还没有达到建立自给体系的火候。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至少需有两个条件,第一,各个方面基本范畴的确立。首先是内涵的稳定,其次是相互关系的严密。第二,写作学基本原理的完善。完善与否,必须经过学术研究的反复考验,而不是多种教材批量生产的重复。
中国现AI写作作学目前许多广泛流行的说法,还根本没有经过学术研究的考验。没有经过学术研究考验的理论,却匆匆忙写进了教材,就免不了产生一种停留在常识水平上的准理论或者亚理论,这种理论的特点是理论与常识的矛盾没有得到充分揭露,充满了片面的表面的、零碎的、乃至歪曲的经验。许多广泛得到认同的“原理”,往往连起码的矛盾都没有揭示,连初级层次的内在联系都没有展开。因而造成某种低水平的随意性。
就以写作学中非常重要的“论证”而言,本来,不言而喻的,最重要的是论点的形成和确立。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中国当AI写作作学至今仍然连这样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提出来,就匆匆忙忙地强调议论的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并且不约而同地在大学写作教材中把根据现成论点组织与之相符的材料加以印证叫做论证。光是这一点,就足以暴露中国写作学学术研究的薄弱了。象这样的说法,只能说停留在直觉和印象水平上。而科学和学术,却始于对直觉、印象、常识的批判。
本来,对任何相邻学科的借重,都应该取其最深刻的部分,中国写作学对于小逻辑中最富生气的防止孤证和轻率概括的部分恰恰忽略了。至于在新引进的西方文论的过程中,这种情况更是比比皆是。从1985年以来,我们引进了那么多西方学术流派,可是在作为写作学基础的论证范畴中有什么实值性的吸收呢?很少。其实,在热闹了好一阵的波普尔的“证伪说”中就有许多值得我们的“论证”范畴吸收的营养。波普尔把证伪看得比证明更重要,认为一切论点都不可能通过不管多少肯定的例证得到证明,相反一切真理只有通过证伪才能得到发展。他的著名例子,如有一论点:一切天鹅都是白的,不管你举出古今中外多少天鹅都是白的,你都不可能证明,“一切”天鹅都是白的,因为一切是无限的,而人们的研证,也就是人们直接和间接的经验是有限的,有限的不断相加仍然是有限,不可能得出无限的结论③。波普尔说,倒是如果人们发现了一只黑色的天鹅,便可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并非一切天鹅都是白的。由此波普尔引出一个原理说,一切的论点都是一种“试错”,试错由于证伪而接近真理。因而他把他的著作称之为《猜想与反驳》。他特别强调了论点的探索性,以及反驳比证明有更重要的意义。他认为一切理论的形成都需经过自我非难的“免疫”过程。自然,波普尔的学说自有其偏颇之处,但是他所强调的反证无疑比我们所迷信的根据论点选择论据在学术理论上要高出许多层次。不讲别的,就是其中直接关涉到论证的思想材料和骇世惊俗的思路就有十分宝贵的学术价值。然而,十分令人奇怪的是,波普尔的这种学说,在我国当AI写作作界居然没有引起学术上的反应。倒是在写作学界以外却引出一些深思熟虑的学术论文。而这时,中国写作学界正忙于追随文艺美学引进了许多文论,然而没有一种文论最后是落实到中国写作学基本范畴的确立和深化上的。
中国写作学的草创性质,不但表现在基本范畴的贫困上,而且表现在对基本范畴的漠视上。至今,许多学者仍然疏于或者不善于对写作是基本范畴作高度抽象的思辨,这是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中国古典哲学缺乏思辨传统的。因为,同样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反向思维传统在中国当AI写作作学中也没有得到长足的继承。
中国当AI写作作学之所以难于作基本范畴的思辩,其原因,第一,在于直接从经验上升的抽象力的薄弱;第二,间接对固有前提的批判力的缺乏④。如广泛得到认同的“论证的原则是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就没有什么人对之从哲学上和经验上加以批判性的推敲。
从哲学范畴来说,任何文章的论点与材料都不可能完全统一。因为论点是普遍的,而材料是特殊的,普遍与特殊的对立是永恒。在任何文章中任何特殊材料都不可能满足论点普遍性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材料从外延上总是小于观点所要求。反过来说,任何普遍观点的内涵,又只能是特殊材料属性的一部分,正等于水果的内涵只能是香蕉属性的一部分,从逻辑学来说概念的外延越大,其内涵就越小,概念的外延越小,其内涵越大。具体的香蕉外延自然比之抽象的水果外延小,其内涵自然要大于普遍概念水果,因而从理论上来说把二者的统一,笼统地作为一种理论准则只是一种常识性的印象,是不能作为学科理论基础来看待的,然而由于写作学术研究的幼稚,这一说法居然戴上了权威的光环。
传统的“观点与材料统一”的原则,其最致命的缺陷乃是把观点预设为绝对完善的论述,论证的任务不过为之寻求理由和证据。其实,这只适合中学生做作文练习,如果把它扩大为高级论证或学科研究的原则,就会变成宗教式的愚昧。学术研究的生命在于不断突破有限的认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完备的论点、绝对真理只能无限接近而不可能穷尽。理论的最高目的不是证明某种观点绝对正确,而是发现某种观念,即使正确,也只在有限的地点、时间、条件之下可行,到了爱因斯坦的世界,牛顿力学也得作出修正。
对于深化论点来说,最方便的莫过于抓住现成的(权威的)观念与事实之矛盾了。对于追求创新的学者来说,一旦发现了任何事实材料为固有的权威理论所不能解释之时,那就意味着遇上了提出问题的机会了。而提出问题正是发展论点的第一步。
不论从理论上来说,还是从操作上来说,观点与材料的统一都是属于低层次的原则,而抓住观点与材料不统一之处不放才是更高层次的创新论点,提高论证严密度的原则。
长期以来,中国当AI写作作学满足于传统的描述性,对于操作性特点十分漠视,导致了其学科方向的模糊。这种模糊更造成了它的恶化的依附性,而长期恶化的依附性几乎完全窒息了它本来就存在的某种操作性倾向。写作理论必须超越描绘性,才能上升为操作性,而操作性必须超越零碎的技巧(如中国的小说评点)层次,才能上升为概括性的理论。
以情节结构为例。传统理论以描述性为特点,认为由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构成。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也认为情节是一种结果和原因之间的关系⑤,即为这样的论点寻求与之相一致的材料是很容易的,中国和西方的许多古典小说戏剧作品都可以作为例证。
但是这样的证明有什么意义呢?且不说它的理论意义,就说它的操作意义也很渺茫。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有结有解的情节并不一定是引人入胜的情节,相反引人入胜的情节并不一定均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结无解的小说,同样产生了杰作。更要命的是这样的理论并没有告诉你如何去构成引人入胜的情节。
描述性和操作性是互相矛盾的,描述性理论有很强的优势,因而它很容易抑制模糊操作性。这是因为,心理定势的强大惯性作用要改变这种定势就需要有特别明确的操作性目标意识,只有操作性目标意识强大到足以克服描述性心理定势以后,才有可能产生一种既具操作性又富于理论性的理论。
任何理论的创新其原因不外在于视角(思路)的变化,或者材料的发现,从描述性到操作性思路(视角)是一个很大跨度的变化,由于思路的变化使一些原本缺乏重要性的旧材料变成了新材料。
从操作性的思路来看最重要的是如何创造高潮,或者如何在后果严重的“结”下面揭示奇妙的“因”。根据这个要求,本来极不受重视的左拉的“实验小说”理论就具备了崭新的意义。左拉认为,文学家和科学家在一点上是相通的。科学家把物质放在试管中改变其正常状态,加温、加压、加上不同试剂,以观察其有无特殊的变化,而文学家不过是把人物的情感放在试管(特殊环境)中,改变某种条件,而看其有无特殊变化⑥。他还举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为例,说明高明情节产生的关键在于使人物越出常态。
文学的任务在于探索人类的内心奥秘,可是在常态中人的外部关系迫使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人的深层心理“被人格面具”掩盖着,只有把人打出常轨,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层,包括潜意识层才可能浮现出来。正如贵族夫人于洛太太本来是坚决拒绝暴发户花粉商的引诱的,但到了她丈夫在名誉和财产上都面临灭顶之灾时,这位贵族夫人才不得不考虑以身相委。这在《贝姨》中是很精彩的情节。
从操作性思路观之,情节的构成并不一定需要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具备,也不一定忙着为结局去寻求原因,只要把人物打出常轨,让他老是掩着自己的人格面具来不及变换,他的真面目就暴露无遗了,他的心理奇观就令人惊叹了。因而所谓情节的操作也就是把人物从常轨环境打入例外环境。例如,把武松送到老虎面前,把白骨精放到孙悟空和唐僧面前,在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安插一个薛宝钗,让一心读书的知识分子章永璘当了右派,在他饥饿不堪时,一边安排一个破鞋给他吃饭,另一边放上一本《资本论》,作者的任务就是在改变了的人物关系和社会环境中去展现心灵各个层次各个侧面的奇观,在操作中,高潮和结局、解和结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这样就不但有了操作性,而且有了理论的独创性。为在理论上把弗洛依德性心理分析法与小说戏剧情节结构结合起来开辟了途径。由此,我国当AI写作作理论家再不必因其它学科又引进了与弗氏性心理学说相对立的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而自卑了。
中国当AI写作作学在引进任何新学说时必须步步为营,力戒浮躁,不能象东北民间故事中那个黑瞎子(熊)那样,来到苞米地里,十分贪心。搿了一个夹在腋下,又去搿另一个,也而腋下那个已经掉了,如此反复,以至折腾良久,仍然只有一个。任何一种西方或东方的学说,都只有在与中国当AI写作作学的操作追求发生关系以后,才能说是有效的引进。在这里,任何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和满足于新招牌都不可能担负起建设中国当AI写作作学科理论的重任。
注释:
①自然,也有一些专业性的写作教材如公文写作、司法文书写作、经济文书写作等等,也非一无是处,至少也为此类专业写作学术理论基础设施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而不是抄来抄去的素材。但是从理论上看这些教材的水准仍然是很低的。
②本文论述的范畴系中国当AI写作作学,其时限为五十年代至今,四十年代以前之写作理论及教材,重要如叶圣陶、夏丐尊等之《文章作法》、《文心》均不在论述之列。本文论述的地域本当包括台港,由于资料缺乏,暂且从略。
③其实波普尔在此陷入悖论,他所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肯定他的论点的,按他的证伪理论,是不能起证明作用的。
④参阅孙绍振《论科学抽象》,1986年第三期《福建师大学报》(人文版)。
⑤其实福斯特的这种说法源自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在《诗学》中亚氏把情节归结为“结”(结果)和“解”(原因)。
⑥参阅《西方文论选》(下)第2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