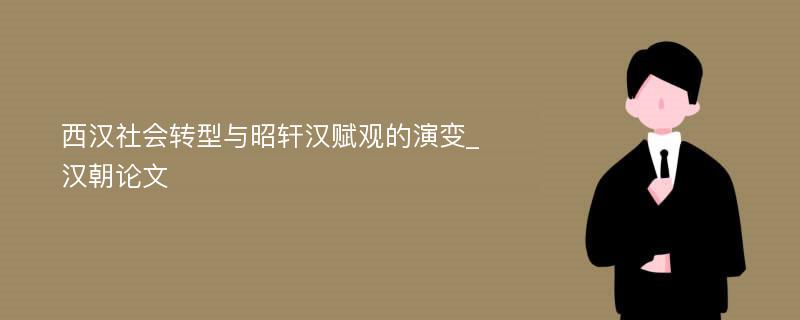
西汉社会转型与昭宣时期汉赋观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赋论文,西汉论文,时期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汉时期,汉赋由六艺附庸蔚成大国,汉赋理论总结也随之发生发展。景帝时期,枚乘对赋的体物铺陈方法作出了“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①的概括;武帝时期,司马相如对赋的艺术构思提出了“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②的要求,司马迁则通过对司马相如“《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③的评价,表达了对赋之“讽谏”政治功用的肯定;宣帝时期,宣帝对赋的功用与艺术效果作出了“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④的评价;成帝之后,扬雄就赋的艺术与功用指出,“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⑤,并出于对“丽以淫”的赋的社会功用极度失望而发出了“壮夫不为”⑥的感慨。由这些评论不难发现,西汉时期的汉赋观大致经历了一个由重艺术经验探索到重社会功用总结,再到重视如何处理艺术技巧与社会功用的矛盾问题的历程。而在西汉赋观念的发展演进历程中,受盐铁会议引发的社会转型的影响,昭宣时期人们对文艺特性以及赋的审美功能与社会功用作了反思讨论,对两汉赋观念的发展演进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学术界对此问题虽有相关讨论,如踪训国《汉赋研究史论》讨论了汉宣帝与司马迁、扬雄、刘向父子等文人的汉赋观,认为汉宣帝揭示了汉赋具有三种社会作用:讽谕教化的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娱乐功能,“已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⑦;张海楠《〈盐铁论〉的主要思想及其文学价值》论及了桑弘羊重质轻文、以素璞为美、反对道古害今、肯定郑卫之音的文艺思想⑧,王永《〈盐铁论〉研究》提到汉宣帝对汉赋的评价“进一步刺激了知识界对汉赋的关注,同时也刺激了知识界形成以赋的创作、欣赏、评议为主要内容的学术风气的空前弥漫”⑨,但这些成果限于各自的研究目的,并未从社会转型视野下去观照昭宣时期汉赋观的发展嬗变及其意义。因此,下文将汉赋观的发展放在盐铁会议引发的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考察,略陈管见。
一 盐铁会议中朝野士人对文艺特性的反思
征和四年(前89),鉴于军旅连出、奢侈浪费导致的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巫蛊之祸导致的戾太子刘据自杀、政治危机重重,汉武帝借答复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屯田轮台的奏请,作《报桑弘羊等请屯轮台诏》深陈既往之悔,下令“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⑩,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示休息养民。但由于专制帝王维护自我权威的需要及其复杂性格的因素,武帝追悔并不彻底,除不复出兵外,其余政策仍在延续。后元二年(前87),武帝崩,年始8岁的昭帝继位。武帝临终前委命的四位辅政大臣中,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倾向于继承武帝轮台诏精神,“轻繇薄赋,与民休息”(11);御史大夫桑弘羊则倾向于“君薨,臣不变君之政;父没,则子不改父之道也”(12),力图维护武帝战时制定的各项统治政策。两种不同的治国思想必须抉择。在此情况下,昭帝始元六年(前81)盐铁会议顺势召开。会议以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为中心议题,由丞相、御史大夫及其属官跟各郡国荐举的六十余位修习儒学的文学、贤良在朝中展开辩论,对武帝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政策进行了反思清算。尽管这次会议不曾专门讨论文艺问题,但其中涉及对文艺特性的反思。这些反思随着盐铁会议引发的社会转型,对昭宣时期乃至东汉的汉赋观均影响深远。
根据《盐铁论》记载,盐铁会上,朝野士人对文艺创作的文与质、审美娱乐与政治教化、颂美与怨刺、崇古与重今等关系问题,都作了反思。
关于文艺创作如何处理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朝廷官吏提出:“文学言治尚于唐、虞,言义高于秋天,有华言矣,未见其实也。……故玉屑满箧,不为有宝;诗书负笈,不为有道。要在安国家,利人民,不苟繁文众辞而已。”“歌者不期于利声,而贵在中节;论者不期于丽辞,而务在事实。善声而不知转,未可为能歌也;善言而不知变,未可谓能说也。”(13)“至美素璞,物莫能饰也。至贤保真,伪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画。”(14)认为诗书歌论应具有安国家、利人民、中节律、至美保真、务在事实的实际内容,反对繁文众辞、利声、虚饰,表现出重质轻文的倾向。以文学为代表的在野文人则提出:“非学无以治身,非礼无以辅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宝也,待礛诸之工而后明。毛嫱,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泽脂粉而后容。周公,天下之至圣人也,待贤师学问而后通。”“西子蒙以不洁,鄙夫掩鼻;恶人盛饰,可以宗祀上帝。”(15)认为宝玉、美人需要装点文饰才能昭显于世,文饰的好坏甚至可以改变对象的本质,使本质美的遭遗弃,本质丑的获认可,表现了重文的观念。文学还提出:“师旷之谐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宫商调。”(16)认为师旷这样高明的乐师弹奏乐曲,是将宫、商、角、徵、羽等五个音级与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等六种高低清浊的节律协调在一起,从而奏出五音六律谐美的音乐。可见在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上,文学更强调文与质的和谐美。这既是对孔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7)思想的继承,更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对文艺修饰美的积极肯定,体现了西汉中期文人对文艺创作美的自觉追求和昂扬自信的时代风貌。
关于文艺的审美娱乐与政治教化的关系问题。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朝廷官吏出于享乐需要,继续汉武帝好新声曲的艺术趣味,追求文艺的审美娱乐功能。桑弘羊提出:“橘柚生于江南,而民皆甘之于口,味同也;好音生于郑、卫,而人皆乐之于耳,声同也;越人子臧、戎人由余,待译而后通,而并显齐、秦,人之心于善恶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鸟下翔;师旷鼓琴,百兽率舞。”(18)认为郑卫之音、曾子悲吟、师旷琴声都值得欣赏,原因在于它们都能够愉悦耳目、感动人心。并认为:“炫耀奇怪,所以陈四夷,非为民也。夫家人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乐,而况县官乎?”(19)肯定了用新奇而娱乐性强的乐舞百戏招待外宾的正当性,表达出雅俗兼综、追求文艺审美娱乐特性的观念。文学、贤良则针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继承儒家重视乐舞政教功能的传统,坚决反对乐舞享乐。贤良指出:“今万方绝国之君奉贽献者,怀天子之盛德,而欲观中国之礼仪,故设明堂、辟雍以示之,扬干戚、昭《雅》、《颂》以风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虫不畜之兽,角抵诸戏,炫耀之物陈夸之,殆与周公之待远方殊。……目睹威仪干戚之容,耳听清歌《雅》、《颂》之声,心充至德,欣然以归,此四夷所以慕义内附,非重译狄鞮来观猛兽熊罴也。”(20)这是针对桑弘羊观点,力倡《雅》、《颂》之乐,认为包孕德、礼的《雅》、《颂》可使少数民族君长受到熏陶自来归附,体现了对乐舞感化人心、辅助政教的社会功用的追求。基于此,文学、贤良还对当权者乐舞享乐导致世风衰败给予了猛烈批判。如《盐铁论·刺权》中,文学历数桑弘羊等当权者凭战时经济政策攫取巨额财富、奢侈享受时,就批判其“中山素女抚流徵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致使“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伪而罕归本也”,认为当权者追求乐舞享乐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弃本逐末、世风败坏。《盐铁论·散不足》中,贤良还抨击了当时社会普遍追逐声色玩好、耽于乐舞享乐、在祭祀、丧礼等场合僭越用乐等现象,认为这造成了社会的财尽政怠。《盐铁论·力耕》中,文学甚至还将耽于女乐视为亡国的重要原因:“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薄,而女乐终废其国。”朝野士人对文艺功用的这些评价,或着眼于维护自身利益,满足一己之情;或着眼于中下层百姓利益,关注民生疾苦。尽管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但都对此后汉赋观与创作影响深远。
关于文艺的颂美与怨刺问题。在盐铁会议上,朝野士人都通过对《诗》、《书》等经典创作目的的阐释,表明了对文学创作目的的思考。尽管他们都认为文学是为美刺政治而作,但由于各自出发点不同,得出的具体结论也不一样。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在朝官吏站在维护既得利益的立场,主要借阐释经典创作的美刺问题,维护现行政治。如《盐铁论·忧边》载桑弘羊语:“《春秋》讥毁泉台,为其隳先祖之所为,而扬君父之恶也。”认为《春秋》记载鲁文公毁泉台之事,目的在于讥讽其变更先祖施政方略的不孝行为,以此为奉行汉武帝的战时经济、军事政策辩护。《盐铁论·繇役》中,桑弘羊还借阐释《诗经·大雅》中《六月》、《出车》皆为颂美周宣王、仲山甫征伐戎狄、猃狁的武功而作,来证明武帝对外征伐、筑西北四郡以备边的军事政策的正确性:“及后戎、狄猾夏,中国不宁,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诗》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无征伐而服不义,不能无城垒而御强暴也。”又《盐铁论·诏圣》载御史云:“其后,法稍犯,不正于理。故奸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诗》刺彰,诸侯暴而《春秋》讥。”《甫刑》,即《尚书·吕刑》。此借阐释《甫刑》为惩罚奸伪而作,《诗》为刺王道衰,《春秋》为讥诸侯暴虐,来肯定武帝为保证战时经济政策的推行而实施严刑峻法的合理性。文学、贤良则站在为民请命的立场,借阐释经典的创作目的批判现行政治,要求改良。在文学、贤良看来,《诗经》颂美诗是为歌颂统治者仁义有道而作的,“周公抱成王听天下,恩塞海内,泽被四表,矧惟人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诗》云:‘夙夜基命宥密’”(21)。因此,他们往往借阐释《诗经》颂美诗,批判武帝事征伐、重徭役、与民争利的弊政。如《盐铁论·未通》载文学语:“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适其所安,安而不扰,使而不劳,是以百姓劝业而乐公赋。若此,则君无赈于民,民无利于上,上下相让而颂声作。……《灵台》之诗,非或使之,民自为之。”认为《大雅·灵台》这类颂美诗是为歌颂周文王施行德政、安民轻赋而作,借此批判武帝时“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致使百姓纷纷流亡的黑暗现实。在《盐铁论·繇役》中,文学还分别借阐释《诗经》美刺诗的创作背景,表明了统治者当以德服远、反对徭役扰民的观点:“舜执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怀四夷。《诗》云:‘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伦,莫不引领而归其义。”“古者,无过年之繇,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为作也。”值得注意的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在朝官吏往往借解释经典作者的创作意图,借美古以美今,崇尚武力、刑法;而文学、贤良则主要借阐释经典作者的创作动机或借美古以刺今、或借刺古以刺今,崇尚节俭、仁德、宽政。
关于文艺创作的崇古与重今的问题。可以说,这一问题是伴随着朝野士人对现行政策的认可程度产生的。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在朝官吏依靠权力优势,在辅佐汉武帝推行盐铁专卖等经济政策时攫取了巨额财富,因而对武帝政策的认可程度高,认为武帝的经济、军事等政策都是为定边安民、国富民饶而实施的,并取得了如《周颂·良耜》所说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的重大成就(22)。而文学、贤良等文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当时虽不是最低,但都如桑弘羊讥讽,“禄不过秉握”、“家不满檐石”,“皆贫羸,衣冠不完”(23),因此,他们最能感受到弊政给百姓的痛苦,对现实政治的认可度也比较低,渴望改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受先秦儒家法先王的思想影响,他们往往或用古代圣王治世与武帝以来的政治作对比,或用文帝无为政治与武帝有为政治的不同效果作对比,否定现实政治,正如桑弘羊所批评,“文学结发学语,服膺不舍,辞若循环,转若陶钧。文繁如春华,无效如抱风。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24),表现出鲜明的崇古倾向。但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对武帝政治的批判,则推动了昭宣时期“过武”文学主题的形成。
盐铁会议中的朝野士人对文艺问题的认识虽有分歧,但都表现了对文学美刺时政的政教功能的重视;其对崇古与重今问题的讨论,实际也是围绕文艺如何服务于现实政治展开;而对文与质、文艺是否应具有审美娱乐特性的讨论,则一定程度代表了当时人们对文学艺术形式美的思考。尽管这些讨论都是依附在治国方略问题的讨论中,不是专门的文艺探索,更不专门涉及汉赋问题,但都启发了后人对赋的艺术表现技巧与社会功用等关系问题的思考。在西汉昭宣时期社会转型历程中,盐铁会议对武帝政治的反思,为宣帝政治、经济的中兴起到了肃清思想、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而这次会议对文艺特性的讨论,也因此影响深远。
二社会转型影响下宣帝时期汉赋观的特点及嬗变
据《汉书·昭帝纪》载:盐铁会议后,“秋七月,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似乎这次会上虽然“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25),讨论极热烈,却只是得到了罢酒榷的结果,而文学、贤良强烈反对的汉武帝时期的备边等政策仍在延续。桓宽还在《盐铁论·杂论》中感慨文学、贤良的陈词“终废而不行”,似乎会议收效甚微。然而,只要将会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考虑,即可发现这次会议对昭宣社会转型意义重大。其中值得重视的是,元凤元年(前80),坚持维护武帝战时政策的桑弘羊就受上官桀父子、燕王刘旦、鄂邑长公主谋反事牵连被杀,执行武帝轮台诏精神的最大障碍被铲除。尽管霍光辅政期间没有罢除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并一定程度加强了边备,但正如《汉书·昭帝纪》赞云:“光知时务之要,轻繇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盐铁会上文学、贤良呼吁的一些经济、军事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汉书·食货志上》还记载:“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文学呼吁的流民问题也有所缓解。这些都昭示了盐铁会议对昭宣时期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重要影响。
在学术文化上,从盐铁会议论辩双方引用典籍的情况看,汉昭帝时期,儒学获得了空前重视(26),这与武帝以来实施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有关,更与昭帝时期儒者获得统治者欣赏有关。始元五年(前82)夏阳男子张延年假冒卫太子诣北阙,时丞相、御史、中二千石官员都不敢表态,隽不疑依《春秋》义将其收缚,平息了这一事件,霍光由此感慨:“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27)。又元平元年(前74),夏侯胜以《洪范传》推测“臣下有谋上者”,由此劝谏刘贺,使当时正在谋划废黜刘贺的霍光和张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28)。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对盐铁专卖等经济政策、征伐匈奴等军事扩张政策的猛烈抨击,更是有力打击了桑弘羊的政治威望,使霍光得以在会后顺利铲除政敌。这一系列事件,促使霍光乃至宣帝在用人问题上注意选拔儒士。尽管宣帝治世秉持汉家制度“霸王道杂之”,但受昭宣时期政局演变的影响,亦需借助儒学维护皇权独尊,巩固既得政权,因而较重视选拔魏相之类通达的儒士任职,从而推动了宣帝时期文人群体进一步儒士化。这有《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为证:武帝时期“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相比之下,宣帝时期以儒术进者数量较武帝时期明显增多。
在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政局稳定的情况下,汉宣帝修武帝故事,仿效武帝搜罗文人为其润色鸿业,促进了这时期宫廷文人群体的生成与汉赋创作的繁荣,也推动了这时期汉赋观在继承前代探索的基础上,呈现出了新的时代风貌。
据班固《两都赋序》:“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29)可知宣帝时期的汉赋作家跟武帝时期一样,有言语侍从王褒、刘向,还有公卿大臣刘德、萧望之。另据《汉书·王褒传》:“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可知宣帝时期赋家还有言语侍从张子侨、华龙、柳褒等人。这些言语侍从构成了宣帝时期宫廷文人群体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今存文献,宣帝时期赋家生平可考者多兼具赋家与儒者双重身份。如刘德与刘向父子为楚元王刘交之后,家庭有习《诗》传统,刘向还曾受宣帝之命修习《榖梁春秋》,在甘露三年(前51)讲论《五经》于石渠阁,被王充称为“鸿儒博生”(30);萧望之治《齐诗》,为一代儒宗;王褒学术渊源虽未能详考,但其作品多引用儒家经典,可推知曾熟读经书。而汉宣帝本人也曾“师受《诗》、《论语》、《孝经》”(31),并因思念祖父刘据而好《榖梁春秋》。文人群体的儒士化与帝王娴熟儒家经典,势必促使当时人们较武帝时期更重视赋美刺讽喻的政教功能。
尽管这时期没有出现《两都赋序》这样的赋学专论,但由史料记载和这时期的作家创作,仍可寻绎出此期汉赋观的基本特点。《汉书·王褒传》即有一段记载: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顷之,擢褒为谏大夫。记载反映了汉宣帝时期两种不同的汉赋观。一种是以“议者”为代表,反对追求赋的娱乐功能。宣帝修武帝故事,令王褒、张子侨等作家在侍从游猎行幸之际作赋,并论作品高下赐帛,这行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与竞技性。由宣帝对辞赋的辩护,不难发现“议者”以赋为“淫靡不急”的批评实际是针对王褒、张子侨等侍从臣的辞赋而发,主要指向辞赋的内容。这种批评与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反对统治者乐舞享乐的观点是一致的。参以《汉书·王吉传》,《韩诗》学者、谏大夫王吉曾因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劝宣帝“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视天下以俭”,可推知这些“议者”当为王吉之类修习儒学的文臣。一种是以宣帝为代表,认为赋具有“辩丽可喜”的形式与“仁义风谕”的内容,欣赏赋可在娱乐中获得道德熏陶、增长学识。应该说,这两种观点尽管有不同,但并不构成矛盾关系,都体现了儒家追求文学社会功用的政教文学观念在汉赋领域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汉宣帝的汉赋观更具包容性。他在驳斥“议者”观点时,延续了桑弘羊“好音生于郑、卫,而人皆乐之于耳”的追求文艺娱乐功能的观念,肯定赋的艺术形式美,同时也认同盐铁会议论辩双方提出的文学应具有美刺时政的政教功能的观点。这是一种对雅与俗的艺术形式美、对审美娱乐与政治教化两种艺术功用兼容并包的新的汉赋观,体现了封建社会强盛期人们对自身艺术创造美的积极肯定,洋溢着一种昂扬自信的气势。另外,从宣帝对辞赋的评论看,他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将优秀赋作与当时被视为经典的古诗相提并论,高度肯定了汉赋的文学地位,并触及了汉赋的来源问题。这对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总结当有启示意义。
如果说汉宣帝和“议者”是从读者角度对汉赋的内容与形式问题作出评论的话,那么,王褒与刘向则是从作者角度总结了他们的汉赋创作经验。
王褒是宣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赋家,《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十六篇。他在《圣主得贤臣颂》、《四子讲德论》、《洞箫赋》等作品中都透露了其汉赋观。《圣主得贤臣颂》开头云:“今臣辟在西蜀,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无有游观广览之知,顾有至愚极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应明指。虽然,敢不略陈愚而抒情素!”(32)说明其作颂目的是抒发内心情感。而人的内心情感包括社会政治情和个人情。从王褒对赋的评论及其创作实践看,他更多抒写的是社会政治情。在《四子讲德论》中,王褒借浮游先生之口,面对斯微文学“何必歌咏诗赋可以扬君”的质疑,提出了诗赋应当歌颂盛德的观点:
昔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吉甫叹宣王,穆如清风,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伪臣虚称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伤乎王道。故自刺史之来也,宣布诏书,劳来不怠,令百姓遍晓圣德,莫不沾濡。……于是皇泽丰沛,主恩满溢,百姓欢欣,中和感发,是以作歌而咏之也。(33)
在此,王褒借阐释周公作《清庙》颂文王之德、尹吉甫作《烝民》赞周宣王之功,明确提出作家在世平道明的时代有歌颂君王统治业绩、令百姓遍晓圣德,以辅助君王教化百姓、稳定政权的义务。其《甘泉宫颂》还写到:“窃想圣主之优游,时娱神而款纵。坐凤皇之堂,听和鸾之弄。临麒麟之域,验符瑞之贡。咏中和之歌,读太平之颂。”(34)描写了汉宣帝在优游赏观之际,欣赏具有中和风格与太平内容的诗赋,此中也透露了王褒以赋颂德的汉赋观。正如班固《两都赋序》所总结,武宣之世的赋皆“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35),在王褒那里,他除了提出诗赋当颂盛德外,还通过其创作实践表达了以赋委婉劝谏抒下情的要求。如《圣主得贤臣颂》云:“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认为君臣相得才能建立更大功业,委婉劝谏宣帝选用贤能。此颂篇末还说:“是以圣王……遵游自然之势,恬淡无为之场,休征自至,寿考无疆,雍容垂拱,永永万年,何必偃卬诎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侨、松,眇然绝俗离世哉!”班固就此解释:“是时,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36)说明王褒也继承了枚乘、司马相如以来以赋讽喻的精神。
王褒除重视以赋抒发社会政治情感外,还非常重视赋的辞采美。如其作《九怀》,据王逸《九怀章句》:“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执握金玉,委之污渎,遭世溷浊,莫之能识。追而愍之,故作《九怀》,以裨其词。”(37)可知见王褒在同情屈原身世之际,对屈原作品“藻采敷衍”也非常叹赏。而所谓“裨”,有弥补、补益之意。说明王褒作《九怀》不独追愍屈原,还有暗地里比拼藻采之意。这恐怕与他侍从宣帝时,宣帝令他与张子侨等人作赋,“第其高下,以差赐帛”,形成了竞技逞才的创作意识有一定关系。追求汉赋的辞采美,在刘向那里也有体现。《九叹》中,刘向表明其创作目的是:“垂文扬采,遗将来兮。”王逸注:“言己虽不得施行道德,将垂典雅之文,扬美藻之采,以遗将来贤君,使知己志也。”(38)这样的创作理念,与司马迁“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39)的创作观相似,突出表现了对作品辞采美的追求。尽管刘向《九叹》并非作于宣帝时期,但据《汉书·楚元王传》:“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既冠,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40)刘向的赋创作活动主要是在宣帝时期。因此,可以说,在宣帝用物质赏赐与精神鼓励来论赋之高下的手段刺激下,王褒、刘向等赋家形成了一种竞技意识,促使他们在赋的艺术形式美方面进行了探索。
此外,由《洞箫赋》对音乐的描述,还可窥见王褒对汉赋的内容与艺术形式美并重的观念:“赖蒙圣化,从容中道,乐不淫兮。条畅洞达,中节操兮。终诗卒曲,尚余音兮。吟气遗响,联绵漂撇,生微风兮。连延骆驿,变无穷兮。”“中道”,李善注云:“中于道德。”(41)这几句前半段着眼于音乐的内容:合于道德、乐而不淫;后半段着眼于音乐的形式:条畅中节而变化无穷。这些既是王褒对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要求,也可视为王褒对赋的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创作体验。而同样观念在刘向那里也有体现。刘向《雅琴赋》:“观听之所至,乃知其美也”(42)、“穷音之至入于神”(43)、“游予心以广观,且德乐之愔愔”(44),同样也表达了对优美动人、道德深蕴的音乐艺术的欣赏。但相比之下,王褒强调音乐“变无穷兮”,更具创新意识。这样的音乐观其实也融入了王褒赋的创作中。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点评汉代十大赋家的各自特点时指出:“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即特别抓住了王褒赋“穷变”的特点。就《洞箫赋》为今存赋史上第一篇独立成篇的乐器赋看,此评可谓知言。
刘向也是汉宣帝时期的重要赋家,《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三十三篇。但由于他历仕宣、元、成三帝,且其创作于宣帝时期的赋作多散佚或仅存残句,蕴含其汉赋观的《九叹》、其校书所作的《别录》、《书录》都作于元、成时期,故此不作详论。
由以上对宣帝时期汉赋观的清理不难发现,盐铁会议之后,汉宣帝时期的汉赋读者与作者都参与了对汉赋的社会功用与艺术表现技巧的讨论。以“议者”为代表的儒臣站在尚节俭、重政教的立场,反对汉赋的娱乐功能;汉宣帝站在稳定政权、个人喜好的立场,既强调汉赋“仁义风谕”的政教功能,又重视汉赋“辩丽可喜”的艺术形式美;以王褒为代表的赋家站在为帝王服务、为盛世谋划的立场,提出了文学当歌颂盛德、辅助政教的创作原则,追求汉赋文与质的统一,重视赋的辞采运用,具有以赋逞才的倾向。尽管他们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汉赋的具体看法也不同,但总体而言,都反映了这时期人们对汉赋社会功用的积极关注,体现出西汉中兴期士人对社会政治的热情关怀。汉宣帝将优秀辞赋与古诗等同视之,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汉赋的社会地位;王褒重视赋的辞采美、追求“变无穷”的艺术境界,则反映了昭宣时期社会转型下汉赋作家的创新意识。可以说,经过盐铁会议的反思,宣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相对于武帝时期有了调整,社会呈现出转型样态,如变政治上的外儒内法、重用酷吏,而为德刑并用、重用循吏,变经济上的与民争利而为休息养民,对武帝时期方略,否定的同时也有吸纳。宣帝时期政策上的变通兼容,取得了《汉书·宣帝纪》赞称道的“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单于慕义,稽首称藩”的巨大成效。这些成效必然会对当时的文艺观念带来冲击。从盐铁会议上朝野士人对文艺特性的讨论,再到汉宣帝时期的汉赋读者和作者对赋的社会功用与艺术形式美的探讨,不难发现,随着社会转型带来的国力复兴,宣帝时期人们的心态在沉稳中充满自信,与此相应,这时期的汉赋观也呈现出了由盐铁会议前的各持一端向兼容并包、逞才求新的方向迈进的恢弘气象。
三 昭宣时期汉赋观的影响
汉昭帝时期对文艺特性的探讨,汉宣帝时期对汉赋的讨论,既有对赋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如何结合的思考,又有对赋的政治教化与审美娱乐功能如何侧重的反思,其中特别强调了赋美刺讽喻的政教功能,这些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对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等作家创作追求的继承与总结,并直接开启了西汉末年刘向、扬雄等人的汉赋批评。
黄龙元年(前49),宣帝崩,元帝即位。宣帝病重时就委命史高、萧望之、周堪辅政,领尚书事;与此同时,宣帝生前还信用宦官弘恭、石显,以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仆射。元帝即位后,由于身体与个性原因,将政事委以石显,由此造成了宦官、外戚、儒臣共同辅政的局面。在皇帝优柔寡断无法平衡三种势力及其利益的情况下,势必引起激烈斗争,斗争结局以萧望之为代表的儒臣失败告终。元帝初元二年(前47),萧望之、周堪与刘向遭谗下狱,萧望之被迫自杀;永光四年(前40),周堪被排挤病死、张猛被石显谗杀,刘向被废居在家十余年。成帝时期则进入了王氏外戚专权的时期,西汉政权也由此在外戚把持朝政下走向灭亡。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幻,皇权的日渐式微,极大程度消磨了文人歌颂现实政治的热情。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再次被提起,人们对赋的认识则在昭宣时期对赋美刺时政的政教功能的探索基础上,更进一步倾向于对赋的抒情讽谏功能的追寻。
作为一位经历宣帝中兴的赋家,刘向仕途偃蹇,而儒者兼刘氏宗室的身份又使他特别关注社会政治,期望皇帝能采纳忠谏有所作为。尽管他曾劝成帝“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45),主张创作雅、颂那样的作品施行礼乐教化,但在其实际创作与对前代赋的评论中,他更倾向于以赋抒情讽谏。如其《九叹》继承了《惜逝》、《哀时命》、《七谏》等汉人拟骚作借解读屈原作品以自伤的传统,并借阐释屈原作品表明了以赋陈情讽谏的创作目的:“舒情陈诗,冀以自免兮”、“兴《离骚》之微文兮,冀灵修之壹悟”(46)。又如周堪、张猛死后,刘向“伤之,乃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47)。尽管无法考究《疾谗》等八篇作品的体裁,但由《汉书》对其“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的内容与写作手法的叙述,可能为诗赋类抒情作品。刘向对前人赋作的评论,同样也着眼于阐释这些赋的抒情讽谏功能。如其《孙卿书录》云:“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48)这是从读者角度对赋进行审视,解释了荀子歌、赋创作的讽刺目的。又如其评贾谊作《吊屈原赋》是“因以自谕自恨也”(49),不仅解释了贾谊以赋抒情的创作目的,而且还触及赋的创作方法问题,即重视依托古人古事表达情志。此外,刘向还重视赋的艺术感染力。如《艺文类聚》卷四十三引其《别录》:“有《丽人歌赋》。汉兴以来,善雅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盖动梁尘。”(50)《丽人歌赋》已失传,但由刘向对鲁人虞公的歌声充满赞赏的描写,可以窥见其对此赋再现丽人歌的高超描写技巧的欣赏。
扬雄历仕成、哀、平三朝,因作赋似司马相如被汉成帝召见待诏,《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十二篇。作为一位汉赋大家,他欣赏司马相如赋弘丽温雅的风格,并常拟之为式,但他更重视发挥赋的讽谏功能。据《汉书·扬雄传》记载,他作《甘泉赋》是为讽戒成帝耽于宫馆游乐、宠幸赵昭仪;作《河东赋》是为劝导成帝以实际行动励精图治;作《校猎赋》是讽劝成帝尚节俭、还苑囿于民;作《长杨赋》是讽谏成帝为向胡人炫耀汉廷多禽兽,而命右扶风征发百姓入南山狩猎以供游乐的扰民举措。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等赋相比,扬雄赋的篇幅相对短小,但讽谏范围有所扩大,讽谏力度也有所增强。然而,汉成帝对扬雄的赋只是感觉奇异,并未接受其建议,照样“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51)。在作赋目的与实际效果严重背反情况下,扬雄对赋做了深刻反思: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髠、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52)。
在此,扬雄根据他对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前代赋家作品的理解,对赋的社会功用与艺术表现技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赋的社会功用就是讽谏,“赋者,将以风也”。赋特别重视艺术表现技巧,写作思路上必当“推类而言”,运用联想类推的思维方式;语言运用上“极丽靡之辞”,词藻丰富华美;艺术风格上“闳侈巨衍”,巨丽而气势恢宏;结构安排上“既乃归之于正”,卒章显志。由此,扬雄抨击赋实际是一种因过度追求艺术形式美而淹没了讽谕意义的文体:“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53)认为赋过度追求丽靡辞藻,就欲谏反劝,不仅达不到讽谏效果,反而使赋沦为俳优戏谈,成为仅供帝王游戏取乐的工具。他“辍不复为”赋,则是以一种极端行动表明了对赋的社会功用在现实中遭到漠视的抗议。可以说,扬雄这些反思主要是建立在对赋的社会功用的认识基础上的,他强调赋的讽谏功能,更期待赋的讽谏效果。这样的汉赋观与宣帝时期的“议者”是相通的,并与盐铁会议中桑弘羊的尚质轻文、文学强调文艺政教功能相一致,亦可视为昭宣时期汉赋观的余响。
总之,从汉赋观的发展历程看,自司马迁肯定司马相如赋的讽谏意义,并将其与《诗》之讽谏等同视之后,经过昭宣时期的汉赋读者与作者的探索,西汉人对赋的讨论就基本是立足于汉赋的社会功用展开了。这些讨论涉及赋的内容与艺术形式、审美娱乐与政治教化、颂美与讽谏等关系问题。尽管由于西汉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同,但人们对赋的认识大体上呈现出由重视赋的艺术表现技巧,到艺术表现技巧与政治教化功能并重、再到侧重于赋的讽谏功能上。在汉赋观的发展嬗变历程中,昭宣社会转型期对文艺特性与汉赋问题的讨论无疑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时期强调文艺的政教功能,重视赋仁义讽谕的社会功用,不仅影响了刘向与扬雄的汉赋观,而且还启发了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对汉赋的来源与内容特点的思考。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的理论总结,亦可谓与这时期的汉赋观遥相承传。
由西汉社会转型对汉赋观演进的影响考察说明,西汉时期汉赋观的形成、发展、嬗变跟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有紧密关系。当社会经济强盛、政治稳定之时,士人们就普遍主张文艺讴歌时代,以赋颂德;而当社会经济问题突出、政治昏暗之时,士人们就普遍强调文艺干预政治、以赋讽谕。这样的汉赋观的形成、发展与嬗变固然与儒学成为当时官方钦定的统治思想、人们普遍接受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有关系,但从中也可看出那个时代的士人对现实政治的热情关怀。正如《礼记·乐记》所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与文学观的形成、发展与嬗变,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反过来,结合社会政治状况,也可更深入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与文学观的形成、发展与嬗变的深刻原因。
注释:
①(29)(33)(35)(41)(42)(43)(44)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三十四第480页,卷一第21页,卷五十一第713页,卷一第21页,卷十七第246页,卷四张衡《蜀都赋》注第81页,卷二十九《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注第410页,卷十八嵇康《琴赋》注第259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②葛洪《西京杂记》卷二,古本小说丛刊《燕丹子西京杂记》,第1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③(49)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裴骃《集解》引,第3317页,第2494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32)(36)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下《王褒传》,第2829页,第2822页,第282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⑤⑥汪荣宝《法言义疏·吾子》,第45、49页,第4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⑦踪训国《汉赋研究史论》,第119—120页,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版。
⑧张海楠《〈盐铁论〉的主要思想及其文学价值》,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40—43页。
⑨王永《〈盐铁论〉研究》,第23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⑩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第391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11)班固《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3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12)(16)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二,《忧边》,第162页,《刺复》,第130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13)(14)(15)(18)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五,《相刺》第254—255页,《殊路》第272页,第272页,《相刺》第254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17)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六《雍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79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19)(20)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七,《崇礼》,第437页,第437—438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21)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三,《未通》,第193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22)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一,《力耕》,第28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23)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四,《地广》,第209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24)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五,《遵道》,第291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25)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十,《杂论》,第613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26)参阅龙文玲《〈盐铁论〉引书用书蠡测》,《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1期。
(27)班固《汉书》卷七十一《隽不疑传》,第303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28)班固《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第315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30)黄晖《论衡校释》卷三《本性篇》,第141页:“自孟子以下,至刘子政,鸿儒博生,闻见多矣,然而论情性竟无定是。”中华书局1990年版。
(31)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3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34)(50)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居处部二》、卷四十三《乐部三》,第1115页,第771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37)(38)(46)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69页,第285页,第295,30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39)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273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40)(47)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4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45)班固《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103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48)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58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51)班固《汉书》卷十《成帝纪》,第330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52)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下》,第357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53)班固《汉书》卷五十七下《司马相如传下》,第2609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标签:汉朝论文; 九怀论文; 西汉论文; 文化论文; 春秋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盐铁论论文; 桑弘羊论文; 读书论文; 武帝论文; 两都赋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