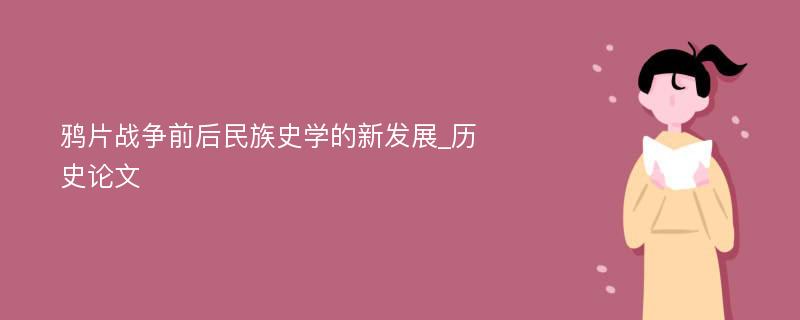
鸦片战争前后民族史学思想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史学论文,新发展论文,民族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07)01—0103—05
一、对传统夷夏观念的突破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夷夏观突出地表现为华夏中心主义,认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四周不过是些“蛮夷”小邦。当西方国家完成工业革命,要求打开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时,乾隆皇帝仍坚持“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 嘉庆帝1808年谕旨中论及中英两国地位时还说:“天朝臣服中外,夷夏咸宾,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2](p287) 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看法尚且如此,更毋论一般士人的识见了。朝野人士普遍拒绝吸收域外先进的东西,甚至不能容忍利玛窦所献《万国舆图》中的中国处于稍微偏西的位置。
鸦片战争的失败,对于中国各阶层都无异于醍醐灌顶。“天朝上国”竟然惨败于“蛮夷”小邦的奇耻大辱,把一批仁人志士推向了“睁眼看世界”的时代前列。研究中国边疆和域外史地的学者,如林则徐、魏源、夏燮、徐继畲等人,开始从中国与西方国家之角度分析“夷情”,他们要求学习西方,御侮自强。传统的夷夏观念开始发生转变。夷夏问题不再仅是中原农耕地区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而主要演变成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
第一,史地学者认为夷夏问题主要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林则徐是当时较清醒认识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四大洲的最早的一位官员型学者。他重视对地图等西书的搜求,当时已获悉英国本土及澳门售有《地理图》、《地理志》、《唐蕃字典》(汉英字典)、近代中西历对照表等。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公然翻译西书、西报,探求海外“奇技淫巧”等新知,这在当时确为惊人之举。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尽管林则徐对西方文化知识的了解和接受仍是有限的,但是林则徐对西方近代文化思想的引进,表明了他在思想上已初步突破了“夷夏之防”和“夷夏之辨”的禁区,主张中国向西方国家学习的态度。
魏源认为,夷狄问题应作具体分析。西方国家中也有知书达理、学识渊博之士,不能千篇一律地称之为夷狄,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夷狄问题。他说:“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未知王化者言之。故曰先王之待夷狄如禽兽然,以不治治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且天下之门有三矣,有禽门焉,有人门焉,有圣门焉。由于情欲者入自禽门者也,由于礼义者入自人门者也,由于独知者入自圣门者也。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3] 魏源从世界整体之角度分析不同国家的情况时,已经注意到西方国家的先进之处,并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去加以学习,反映了他对传统夷夏观中民族偏见的某些突破。
鸦片战争期间,姚莹在台湾登上英人的兵船对西方的长处进行深入了解后,深切地感到由于固步自封造成了中国与西洋诸国的现实差距。他不无感慨地说:“余尝至英夷之舟中,见其酋室内列架书籍,殆数百册,问之,所言亦与回人相似,而尤详于记载各国山川风土,每册必有图。其酋虽武人,而犹以书行,且白夷泛海,习天文算法者甚众,似童而习之者。盖专为泛海观星,以推所至之地道里方向远近,必习知此,乃敢泛海舶纵所之也。吾儒读书自负,问以中国记载,或且茫然,至于天文算数,几成绝学,对彼夷人,能无泚然愧乎?”[4] 夷人重视自然科学和舆地知识,孩童时即学习天文算法,英酋武人泛海远行还在舟中置书数百册。相反,中国的士大夫们虽自视甚高,历史地理知识却极为贫乏,自然科学“几成绝学”。面对这种危险局面,姚莹主张“尽取外夷诸书与留心时事者,日讲求之”。[4] 尽管姚莹仍用“英夷”“外夷”等指称英国和西方国家,但他所谈的在夏燮看来,“夷”主要是指西方国家,他说:“自壬寅通商后,五口之间,华夷错居,衅端叠起。”[5] 夏燮在《中西纪事》中亦主要从中西关系的角度谈夷夏问题。如他论及《南京条约》中天主教受条约保护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后果,说:“约内载传习天主教者,中国官须一律保护,不得刻待禁阻之语。查天主教自明季入中国,国初,杨光先著《不得已》书攻之,……今又载入约中,将来白昼公行,何所顾忌,用夷变夏之渐,不可不防。”[5] 这里的“用夷变夏”也是针对西方国家来说的。
第二,史地著作中的西方译名、称谓等出现变化。传统的夷夏观念把边疆地区的诸游牧民族,视为不开化的野蛮部落,以带有明显贬意的“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字眼称之。抱着这种“以尊临卑”的心态与西方人交往的初期,英国人被中国官方称为“英夷”,把办理外交叫做“夷务”,按照一切远离中华文明的民族都是“化外之民”的逻辑,西方人自然不属于文明的范围,因此中国在给外国人的译名时也多反映出“华夷之辨”的观念。如用贬义词狄妥玛(今译托马斯·迪克,在中国海关任税务司的英国人)、吓厘士(今译哈里斯,美国外交官)、渣甸(即查顿)、马赖(一译马奥斯多,法国传教士);或在汉译名一律加“口”字旁。“口”在汉语里有计数牲畜的意思,以此引伸为野蛮的禽兽。如吗咃仑(今译马他伦,英国水师副提督),喇吃呢(今译拉萼尼,法国外交官)、喳噸(今译查顿,鸦片贩子)。陈旭麓指出,用“夷”来泛称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6](P101) 这种情况到鸦片战争前后已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
随着与外人接触、交往的不断增加,一些留心时务、通达外情的开明人士逐渐舍弃对外人的蔑视称呼——夷,而代之以“洋”。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一书的正本中,魏源把抄本中“夷”字,通统改为“洋”字。如“夷艘”、“夷人”、“夷商”皆改作“洋艘”、“洋人”、“洋商”。徐继畲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手稿《瀛环考略》中,“夷”字比比皆是,此后几稿“夷”字渐次减少,被删去或改换成其它词,如“夷目李太郭”改为“英官李太郭”,“山之尽头,夷为之岌”改为“山之尽头,番为之岌”。《瀛环考略》手稿英吉利一节仅2429字,就有21个“夷”字,而《瀛环志略》刊本同一节长达7620字,却不见一个“夷”字。
译名不仅是一种传达命名信息的手段,也是表达译名者思想的一种方式。1848年刊行的《瀛环考略》中很少使用“夷”的译名,也很少采用另一些“胡”、“狄”等带有贬义性的译名。① 而更多地使用了“泰西”、“西洋”、“西土”、“西国”这些属于中性的描写词,甚至在许多官方文献中被斥为“夷酋”的李太郭,《瀛环志略》中被尊称为“英官李太郭”。1858年6月26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1款才明确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7](P174) 而徐继畲在鸦片战争后对西方已逐渐形成比较客观的认识,反映了他对夷夏问题的卓越见识。在《中西纪事》中,夏燮混用“英夷”、“英人”、“夷舟”、“英舟”、“洋艘”的现象很为普遍。如卷十一“五口衅端”即有这样的话:“沪中通商,遂为五口之首,外洋贸易之暇”。书中很多地方,都能看出夏燮对西方认识的某些突破。在他看来,西方各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许多用“夷”的表述,则明显带有敌忾之意。如夏燮说:“大西洋之强国足以抗英吉利者有三:曰法兰西,曰弥利坚,曰俄罗斯,此三国者皆英夷世仇也。”[5](卷十二)
鸦片战争前后,从普遍称西方国家和西方人为“夷”,到逐渐减少这一由古代沿用而来的轻蔑性字眼,从“夷务”到“洋务”的变更,由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夏中心观念开始在动摇。林则徐编撰《四洲志》、魏源继之完成《海国图志》,徐继畲又出版了《瀛环志略》。这些书尽管一般还比较粗浅,甚至有谬误之处,但它们毕竟向长期处于孤立、闭塞环境的中华民族,最初展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改变中国人历来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
二、珍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
在如何面对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上,祁韵士、张穆、姚莹等史地学者普遍从安定少数民族的民心,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高度出发,阐发了他们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
其一,史地学者重视民族友好交往的记载。史地学者非常重视对历史上民族间友好交往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史地学者都对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了记载和评述。
祁韵士记录了有关“御制优恤土尔扈特部众”的情况:“御制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曰:归降、归顺之不同既明,则归顺、归降之甲乙可定。盖战而胜人,不如不战而胜人之为尽美也,降而来归不如顺而来归之为尽善也。然则归顺者较归降者之宜优恤,不亦宜乎”。[8](卷十四)
张穆于《蒙古游牧记》卷十四对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的事迹详为记述,并在注文中征引了乾隆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以丰其记,其中有几句话是:“始逆命而终徕服,谓之归降;弗加征而自臣属,谓之归顺。若今之土尔扈特携全部,舍异域,投诚向化,跋涉万里而来,是归顺,非归降也。”
为消除人们对土尔扈特部的误会,俞正燮作《书〈西域闻见录〉后》一文,详细考订了该部的世系,说明土尔扈特部“弃俄罗斯而来”,并非“其部众不思勤俭立业”,[9](卷六) 而是因为他们与祖国有着血肉联系。他指责椿园《西域闻见录》拾西人之牙慧,记载不实,于是他搜检官私著述,详加考订,充分表现了他希望祖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对于土尔扈特的归来,俞正燮认为:“我于俄罗斯,不为纳其属部。俄罗斯于我,亦非绝置属部于不言。”[9](卷九) 表明了他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严正立场。
对于土尔扈特重返祖国的重大事件,何秋涛不仅在“圣训”“圣藻”中论及,更特辟《土尔扈特归附始末》专篇记述其回归原因和过程。如该文记载曰:“土尔扈特司蒙古俗,务畜牧,逐水草徙;而俄罗斯城郭居,风俗既异。土尔扈特重佛教,敬达赖、喇嘛,而俄罗斯尚天主教,不事佛,以故土尔扈特虽受其役属而心不甘,恒归向中国。”[10](卷三十八) 迁往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蒙古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上与俄罗斯多有不同,惨遭沙俄的奴役,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历经艰辛,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受到乾隆帝的盛情接待。对这种决不屈服于外力威胁的爱国行为,何秋涛不仅详述其始末,而且对此事的重大意义深致其意,热情赞颂,充分体现出他珍视祖国各民族团结的深厚感情。
姚莹在自己的书中屡次提到唐与吐蕃间和亲友好之事,对土尔扈特重返祖国的爱国行动,也作了记述。[11](卷四)
由上可见,史地学者对土尔扈特的爱国之举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反映了他们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高度重视。对于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行动,他们普遍认为是“归顺”,而非“归降”。这种提法,应当说不仅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有利于民族间的和睦相处。我们认为,史地学者在国内民族关系的看法上,实际上是对中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的新发展,主要是因为,这时他们对民族关系的高度重视明显有着反对沙俄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目的,故而,他们的民族思想赋上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二,史地学者民族和睦的安边主张。新疆地区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境内有维吾尔、回、汉、满、哈萨克、布鲁特、锡伯、索伦、蒙古等民族,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是史地学者尤为关注的问题。
龚自珍严厉谴责驻乌什领队大臣素诚处理民族关系的做法,结果造成“乌什之叛”。他说:“吾师亦知乌什往事乎?素诚者,旗下役也,叨窃重寄,为领队大臣,占回之妇女无算,笞杀其男女亦无算,夺男女之金银衣服亦无算,乌什杀素诚以叛;乌什之叛,高宗且挞伐,且怜哀,圣谕以用素诚自引咎。御制诗,时以激变为言,谓素诚死有余罪”。[12](P310) 龚自珍认为, 驻疆的大臣应以平等的态度与适当的措施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才能赢得少数民族的信任,维护民族间的安定与团结。他说:“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驼羊视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又说:“故今日守回之大臣,惟当敬谨率属,以导回王回民,刻刻念念,知忠知孝,……耕者毋出屯以垦,牧者毋越圈而刈。上毋虐下,下毋藐上,防乱于极微,积福于无形。”[12](P311—312) 这里,龚自珍论证了民族间“安”与“信”的重要性。龚自珍重视边疆政策研究与民族政策的结合,主张建立一种相互和谐的民族关系,表达了他对民族间和睦相处的高度关注。
沈垚认为,要保持边疆的的长治久安,除了加强兵备、屯田积谷外,还须慎重处理民族关系,主张加强民族和睦。他指责清廷驻疆官员不知体恤维吾尔族民情,与当地维族上层分子相勾结,“恣为贪酷,侵夺其财货,虏辱其妇女,以积其愁苦冤怨之气”,引起维族人民不满,使张格尔那样的少数“桀黠凶悍之人,乘机鼓扇”[13] 分裂叛乱。他还指出造成边疆动荡的原因是镇守诸臣缺乏安边柔远之心,“故欲使西陲无事,必自镇守诸臣能仰体皇上安边柔远之心始。”[13]
魏源也指出清廷某些驻疆大臣“素愦愦不治事,又酗酒宣淫”,[14](卷四)认为这是引发边疆极少数叛乱分子乘机启衅的原因。
林则徐服戍新疆期间,承担了勘查南疆荒地的任务。在分配土地问题上,林则徐主张将大部分土地交给维民垦种,驳斥了防范维民、不分给他们土地的谬论,充分体现了他从大局出发,要求少数民族的发展经济,维护民族团结的良好愿望。
姚莹认为加强民族间的交流融合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说:“今土司之地,汉人日渐繁多。蕃夷渐慕华风,更千百年皆将用华变夷,势使然也”。[4](卷四) 姚莹还认为少数民族保存了一些中原地区已经断续的古代礼节,从而打破了人们视边疆少数民族野蛮、落后的传统陋识。姚莹说:“蕃人有合古者数事。女衣裳前著幅,一也;蕃僧见人必以哈达,即古之束帛,二也;蕃见官长必偻背旁行,即古一命而伛,再命而偻,循墙而走之义,三也;官长有问,必掩口而对,四也。礼失而求诸野,不其信乎”。[4](卷八)
姚莹还认为边远地区的社会也在不断的进步中。他说:“台湾自明季始为红毛所据,郑氏父子驱逐红毛而有之。本朝康熙二十七年入版图,至今得沐圣化,教养近二百年,已变革盱睢,富庶若此。更百余年山后之地尽辟,岂非海外一大都会耶?吾人生居中土,但见盛世文物声明如书籍所载。太古淳朴、陋野之风徒存想像。以余所见台湾生蕃,则已身游洪荒之世矣。今又来兹异域畅览夷风,然后知六合之内,人物由朴而华”。[4](卷十二) 这里,姚莹以台湾为例,说明了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的巨大变化,从中亦可看出他对发展边疆地区民族经济、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视。
总之,在民族政策上,史地学者指斥了驻疆大臣压榨少数民族的做法,认为这是导致边疆动荡不定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尤为关注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凡此,无不体现出史地学者民族和睦的安边主张。
其三,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清代,青藏高原、大漠南北和天山北路的蒙族民族大多信奉藏传佛教,而天山南路的各民族则信奉伊斯兰教。在边疆地区,这两种宗教有着巨大的传统影响和社会势力,有着强烈的民族性。宗教问题往往同民族问题、边疆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边疆地区的稳定。
姚莹认为应从具体情况出发提出治理措施,他主张,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能强求一致,应当采取“因俗而治”[4](卷三) 的策略。 “国家抚驭外藩,封止其王。若其部属如何,制度皆听之为之,各因旧俗,不为区处而变易之也。有不服或阙贡,大则六师讨之,小者畺吏移文责让之而已”,这样,可以起到稳定人心,巩固边防的作用。[4](卷八)
对于藏族“赭面”、“妇人辫发”之民情风俗,姚莹有这样一段述评:“《新唐书》言吐蕃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荣之。余按:妇人辫发至今犹然,赭面之俗则唐时已革。盖自赞普娶唐公主,公主恶其人赭面,赞普不得已令国中权罢之,遂至今矣。巴勒布人至今眉额间犹赭之,是其遗俗,亦犹中国妇人之傅粉也。赭白虽殊习,则尚之何足评乎。《新唐书》又谓其吏治无文字,以细木为笔,引墨横书,如发字皆右行,谓之唐古忒字,略如西洋夷书,不知始自何代何人为之,大约宋元间也”。[4](卷九) 在姚莹看来,藏族特有的民族习俗是历史形成的, 别人不应有什么非议。他还提出:“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4](卷三)
如何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姚莹认为:“自道术分裂,儒分八、墨分三、释道亦各分数支。同中立异,门诤坚固。于一教中且自相胡越,况欲并包殊方,泯其畛域,会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数。广谷大川异俗,民生其间刚柔轻重迟速异齐。皇清能并回部,不能使天山南路舍回教而被儒服;能服蕃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黄教而诵六经。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而不能使白帽黄帽之方尽奉天主。故曰: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4](卷十三) 在他看来,对于精神领域内的宗教信仰,仅靠武力征服是行不通的,只能在尊重他们传统信仰的前提下,采取因势利导的办法进行统治。
何秋涛也认为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不能强求一致。从他对俄罗斯民族政策的评价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说:“俄罗斯能兼并西北诸部,而不能使黄衣白帽之徒尽奉天主,此以知嗜好所在,非威势所能变也。古人有言曰:‘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10](卷二十八) 何秋涛认为沙俄的民族压迫和宗教压迫行不通,“因俗而治”才是良策。他还主张“边裔之地,治贵易简”,[10](卷九) 这是阐发的民族、宗教政策,其核心还是应当根据边疆地区的具体情况,力求采取简单易行的治理方略,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
总之,在习俗、信仰方面,鸦片战争前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就变化,史地学者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这是他们珍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在史学方面的反映。
[收稿日期]2006—09—20
注释:
①个别的贬辞仍存在,如卷八有“黑番愚懵”等语,估计是受西方殖民主义观点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