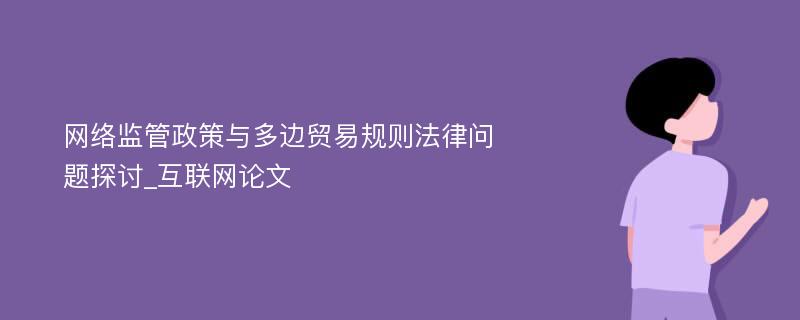
互联网监管政策与多边贸易规则法律问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边贸易论文,互联网论文,探析论文,法律问题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在1994年达成“一揽子协议”之际,互联网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互联网与多边贸易规则之间的关联似乎还十分遥远。然而,此后20年时间内,互联网不仅对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律体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问题。例如,一国基于国内法实施的互联网监管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将构成影响国际贸易的壁垒?这些监管措施是否符合WTO所管辖的多边贸易规则?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以不同方式对互联网进行监管是各国的普遍做法,由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往往被推至相关讨论的风口浪尖。2010年谷歌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爆发的冲突,以及2011年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向中国提出的“问题清单”,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问题对于中国的特殊重要性。本文着重结合中国的相关立法和实践,对互联网监管政策与多边贸易规则的相关法律问题加以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的对策建议。 一、中国互联网监管政策引发的风波:2010年“谷歌事件”和2011年“问题清单”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袭击、网络犯罪、网络间谍、网络军备竞赛等网络安全威胁日益引发关注。同时,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对各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把网络安全作为国家信息安全乃至战略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不同措施对互联网加以监管。例如,美国是互联网最早起源的国家,也是大力标榜和倡导“互联网自由”的主要国家之一。但是,“911事件”以来,为了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先后通过了《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法》、《保护美国法》等多部法律,授权联邦调查局等政府部门对互联网通讯和信息进行监控。① 尽管采取不同措施对互联网进行监管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各国普遍做法,基于各自法律传统和现实国情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在监管方式和严厉程度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就中国而言,内容审查(包括对境外网站的屏蔽和信息过滤)是我国使用较多的管理手段之一。②而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在世界范围内技术最为先进、范围最为广泛,其审查技术和手段正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再加上中国庞大的网民数量,中国已经成为除美国外对互联网的未来影响最大的国家。③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将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视为“眼中钉”,多年来一直通过不同渠道加以批评和施压。④2010年“谷歌事件”,进一步将中国互联网监管政策推向风口浪尖。⑤ 2010年1月12日,谷歌公司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受到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同时对中国政府有关互联网信息过滤的要求加以质疑,并声称如果中国政府不同意其使用无需过滤的搜索引擎,谷歌将考虑退出中国市场。⑥“谷歌事件”由此引发。 在上述声明未能迫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的情况下,谷歌公司又决定:自2010年3月23日起,通过“google.cn”和“g.cn”这两个域名向中国大陆提供的网页、图片和资讯搜索服务,将自动重定向至谷歌香港的域名“google.com.hk”,以实现使用其在香港的服务器来进行不受审查和过滤的搜索。⑦然而,中国政府对这一做法并未予以接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发表称:谷歌公司违背书面承诺、停止过滤并就黑客问题指责中国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将商业问题政治化”。⑧ 在几个月的僵持之后,因谷歌中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ICP)执照将要在2010年6月底到期,谷歌不得不作出妥协,通过在“google.cn”上创建一个“着陆页面”,向用户提供谷歌香港网站的可选链接,而不再把中国大陆用户自动转往谷歌香港的网站。⑨2010年7月9日,谷歌宣布其ICP执照通过了中国政府的年检。⑩因谷歌威胁退出中国市场而引发的“谷歌事件”,由此而戏剧性地告一段落。 中国政府和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之间围绕中国互联网监管措施的上述纷争,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这一事件前后,美国国会和政府多次对谷歌公司加以声援,同时对中国政府进行多方指责和施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声称,位于美国的邮件服务器受到黑客攻击及偷窃代码事件引发了“严重的担忧和问题”,并呼吁中国政府对此作出解释。(11)克林顿国务卿还在2010年1月和2011年2月发表了两次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著名演讲,将推动“互联网自由”上升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层面。(12)而中国政府也多次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强调中国依法管理互联网,有关管理措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13) 在“谷歌事件”前后,要求将中国互联网监管政策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这一直是美国国内一股强烈的声音。2010年1月以来,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第一修正案联盟”(California First Amendment Coalition)等多个非政府组织先后致函美国政府,要求向WTO起诉中国的网络审查措施。(14)谷歌公司在2010年11月发布的一份政策文件中也称:“一系列贸易协定——特别是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可以并应当在有必要时用来反对限制与阻扰通过互联网发送的信息。”(15)但是,美国政府除了发布声明对谷歌公司加以声援外,最终并未直接诉诸法律行动。不过,美国政府在一年多后采取了与之相关的另一行动。 2011年10月17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柯克致信中国常驻WTO代表易小准大使,根据GATS第3.4条的相关规定,要求中国政府就其互联网监管政策提供相关的详细信息。(16)在这一信件中,柯克声称:“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并使之能够在中国被看到,这是服务提供商向中国消费者和企业提供服务时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因素。由于其网站受到中国国家防火墙的屏蔽,一些中国之外的公司在向中国消费者提供服务时面临着挑战。这一状况,对那些试图通过跨境方式提供服务的公司特别是中小企业构成了障碍。”(17)该信件的附件中,分为四个部分提出了25个问题(以下简称“问题清单”),涉及了中国互联网监管政策的方方面面,例如: ——在中国,是由谁或是哪个部门负责决定外国网站是否以及何时应当被屏蔽? ——阻碍连接到外国网站的指南和标准是什么?这些指南和标准多长时间修改或公布一次?有关指南公布于何处?是不是在实施之前被公布?负责起草这些文件的是哪些部门? ——对特定网站实施限制是通过何种程序?相关部门如何决定一个网站是应当被完全屏蔽还是仅屏蔽其中被认为非法的服务或内容? 这一“问题清单”,是美国政府直接依据WTO规则(GATS)采取的一项措施,为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投石问路”的意味颇为浓厚。显然,从试图求助于多边贸易规则来规制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而言,“问题清单”与“谷歌事件”有很大的延续性和一致性。不过,“谷歌事件”主要涉及谷歌在通过其在华分支机构提供互联网搜索等特定服务时,可能受到中国互联网监管措施的影响;而“问题清单”则主要是针对中国之外的公司在通过互联网向中国消费者提供传统服务(如咨询服务、销售服务等)时,可能受到的影响——此时,互联网主要是体现为一种提供服务贸易的手段(即后文将述及的GATS所指“模式一”)。必须看到,由于二者所指向的具体问题存在较大差异,结合WTO规则进行的相应讨论也将不同。(18) 二、互联网监管政策的货物贸易法律问题 2010年“谷歌事件”和2011年“问题清单”,提出了一系列的WTO法律问题。就国际贸易而言,互联网通常被认为是与特定服务的提供相关联;以往涉及互联网监管政策与多边贸易规则法律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从服务贸易即GATS的角度加以探讨。不过,互联网监管措施是否也会带来货物贸易领域的法律问题,从而导致WTO货物贸易法律规则(主要是1994年《关贸总协定》,一般缩写为GATT1994)的适用?这是一个需要加以考量的问题。 (一)GATT1994的可适用性问题 为了明确互联网监管措施是否会产生GATT1994下的法律问题,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作为WTO货物贸易主要规则的GATT1994和作为WTO服务贸易主要规则的GATS,在适用中是相互排斥还是可能叠加适用?换言之,对于某一被投诉的贸易措施,GATT1994和GATS是否可能同时适用? 这一问题,在上述两个协定以及其他WTO法律文本中都没有加以规定。在“欧共体—香蕉进口、销售和分销案”(EC-Banana III)中,厄瓜多尔等投诉方认为欧共体的香蕉进口、销售和流通体制既违反了GATT1994,同时也违反了GATS的有关规定。欧共体则主张上述两个协定的适用范围各不相同,不会叠加适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最终支持了投诉方的观点。上诉机构在该案中更是明确指出:尽管这两个协定的适用范围各不相同(分别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但根据所涉措施的性质不同,这两个协定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叠加适用;具体而言,“有的措施仅影响单纯作为货物的货物贸易,因而只适用GATT1994;有的措施仅影响单纯作为服务的服务贸易,因而只适用GATS。但也存在着GATT1994和GATS可同时适用的第三类措施,这类措施会对与特定货物有关或与特定货物同时提供的服务产生影响。在因第三类措施而产生的所有案件中,可同时适用GATT1994和GATS对相关措施加以审查。当然,尽管同一措施可以分别由这两个协定来加以审查,该措施在这两个协定下所审查的具体方面并不相同。在GATT1994下,审查的重点在于被诉措施如何影响所涉的货物;在GATS下,审查的重点在于被诉措施如何影响所涉的服务的提供或所涉的服务提供商。一项影响与特定货物相关的服务的措施是应当适用其中某一个协定还是同时适用这两个协定加以审查,这个问题只能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回答。”(19) 那么,一项针对互联网的限制措施究竟应当适用GATT1994还是CATS?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Tim Wu教授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此进行了讨论。在他看来,学界对这一问题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第一,通过互联网购买的货物(例如,一个中国消费者在亚马逊网站从美国的零售商购买纸本书)仍然涉及货物的流通,因而会导致GATT1994的适用;第二,完全不牵涉任何物品的下载或存储的在线服务(如使用搜索引擎)是单纯的服务,只适用GATS。至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另一种类型——以电子形式下载和存储传统的货物(包括电子版的报纸、音乐、软件、书籍等),学者们对于应当适用GATT1994还是GATS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WTO也没有相应的判例。(20)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还有部分值得商榷之处: (1)那些不牵涉任何物品下载或存储的在线服务(如使用搜索引擎)只产生服务贸易法律问题,针对这类服务的互联网限制措施仅适用GATS,这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2)但是,根据前述WTO上诉机构在“欧共体—香蕉进口、销售和分销案”中的立场,通过互联网购买传统货物应该既涉及货物的流通又涉及服务的提供(具体而言是互联网销售服务,即通称的“网购”),应当既适用GATT1994又适用GATS。 (3)至于以电子形式下载和存储传统的货物,尽管Tim Wu等学者倾向于适用GATT11994,但笔者认为适用GATS更为合理。Tim Wu等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适用GATT1994可以避免因货物载体的不同而导致的逃避关税,也可以避免对不同载体的“相同产品”的歧视问题。(21)但问题在于,对电子形式的“货物”征收传统的关税是否有足够的可行性?而且,将这种“货物”纳入服务贸易框架内并适用GATS加以规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动WTO的贸易自由化宗旨。 基于以上的简要分析,笔者的结论是:互联网监管措施主要涉及的是GATS框架下的服务贸易法律问题,但如果此类措施对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有形货物买卖产生影响,GATT1994和GATS应当可以同时适用。 (二)可能被指控违反的条款及抗辩 如果一项互联网监管措施对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国际货物买卖产生影响,在GATT1994下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是该协定第11条关于数量限制的规定和第3条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被投诉方的主要抗辩依据则是第20条关于一般例外的规定。 1.GATT1994第11条(普遍取消数量限制) 为了约束贸易壁垒和推动贸易自由化,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专门就缔约方采取的数量限制措施加以严格管制,规定除关税、国内税或其他费用外,不得对从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进口的产品或向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出口或销售供出口的产品设立或维持任何禁止或限制,无论这类禁止或限制是通过配额、进出口许可证还是通过其他措施来实施的。该条款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它适用于除了以关税、国内税或其他费用的形式采取的措施外,一缔约方所设立或维持的禁止或限制出口、进口或销售供出口的产品的所有措施”。(22)在1999年“土耳其对纺织品进口采取的限制措施案”中,专家组曾经肯定地指出:“禁止使用数量限制是关贸总协定体制的一项核心要求”。(23) 那么,一项对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国际货物买卖产生影响的互联网监管措施是否可能违反第11条呢?尽管WTO迄今没有相关判例,但在“美国—影响赌博和博彩服务的跨境提供的措施案”中,美国采取的禁止通过互联网跨境提供赌博和博彩服务的措施,被定性为相当于采取了一种“零配额”限制,从而构成了对GATS第16条有关市场准入之规定的违反。(24)依照这一逻辑,如果一国采取措施对特定境外货物生产商或销售商的网站加以屏蔽和信息阻隔,这似乎也可被解释为一种数额最低为零(在完全屏蔽某一网站的情况下)的配额,从而构成与第11条不符的数量限制。 2.CATT1994第3条(国民待遇) 非歧视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地位极为重要。对货物贸易而言,其内涵主要体现在最惠国待遇(GATT1994第1条)和国民待遇(GATT1994第3条)两方面:最惠国待遇禁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产品加以歧视,国民待遇则禁止使任何进口产品相对于本国产品而言受到歧视。WTO上诉机构曾经指出:“非歧视义务的精义在于相同产品(like products)应当享受同等的待遇,而无论有关产品产于何地。”(25) GATT1994第3.4条规定:“任何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进口至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时,在有关影响其国内销售、标价出售、购买、运输、分销或使用的所有法律、法规和规定方面,所享受的待遇不得低于同类国内产品所享受的待遇。”以往判例已经确立,一项违反该条款的措施需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所涉及的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属于“同类产品”(like products);第二,被诉措施构成“影响国内销售、标价出售、购买、运输、分销或使用”的“法律、法规和规定”;第三,进口产品所享受的待遇低于或差于同类国内产品所享受的待遇。(26)境外学者一般认为,我国的互联网监管措施往往对于国外网站的审查和防范比国内网站更为严格。(27)不过,由于我国互联网监管政策中的很多具体规定和做法难以从官方渠道获得,这使得对一项监管措施是否违反国民待遇条款加以较为客观的评判颇为困难。至少从理论上说,如果其他国家能够证明销售某一产品的境外网站受到屏蔽或信息阻隔,主张该屏蔽或信息阻隔措施使有关境外产品相比中国境内同类产品受到与第3.4条不符的歧视是有可能。当然,这一理论上的推断究竟是否成立,还需通过进一步的事实来加以检验。 3.第20条(一般例外) 在GATT/WTO法上,第20条素以复杂难解而著称。该条包含一个引言和10款,与互联网监管政策有关的主要是关于维护公共道德的(a)款,其规定如下: “本协定的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国采用或实施以下措施,但对情况相同的各国,实施的措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歧视,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a)为维护公共道德所必需的措施;……” 鉴于后文还将涉及对GATS第14条中的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分析,而后者与GATT1994第20条(a)款的措辞、分析步骤和要件等几乎完全相同,此处暂不加以展开。 (三)小结 从本部分的分析来看,互联网监管政策可能涉及WTO法律体系中的货物贸易法律问题,一项监管措施有可能违反GATT1994第11.1条(构成数量限制)、第3.4条(对外国产品的歧视),而难以用第20条中的公共道德例外来加以抗辩(此点详见第四部分相关分析)。 三、互联网监管政策的服务贸易法律问题之一:GATS的可适用性 以1995年GATS的生效为标志,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第一次将服务贸易纳入了其管辖范围。GATS第1条第1款规定:“本协定适用于各成员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据此,无论是在2010年“谷歌事件”还是2011年“问题清单”中,GATS能否适用于中国所采取的互联网监管措施,关键在于判断这些措施是否构成了“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 (一)GATS所指的“措施” GATS第1条第3款规定:“就本协定而言,‘成员的措施’是指:(1)由中央、地区或地方政府和当局所采取的措施;(2)由中央、地区或地方政府或当局授权行使权力的非政府机构所采取的措施。”该协定第28条进一步指出:“‘措施’指一成员的任何措施,无论是以法律、法规、规则、程序、决定、行政行为的形式还是以任何其他形式。” 自1994年以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与互联网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等。(28)这些法律法规所体现的中国互联网监管政策及相应的实施手段,就是“谷歌事件”和“问题清单”所共同指向的“措施”,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我国立法中禁止特定互联网信息的规定(29),以及我国公安、国安等部门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制定的部门规章和采取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二类是互联网的行业自律性规定和由行业组织采取的措施。例如,成立于2001年5月的中国互联网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互联网行业组织,它先后制定、发布了包括《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互联网站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抵制恶意软件自律公约》、《博客服务自律公约》、《反网络病毒自律公约》、《中国互联网行业版权自律宣言》等在内的自律规范,有关门户网站、电信运营商也依法采取了各种对互联网信息进行监管的措施。 上述第一类措施属于GATS第1条第3款所指的“由中央、地区或地方政府和当局所采取的措施”,这应当没有疑问。至于第二类措施是否属于第3款中所指的“由中央、地区或地方政府或当局授权行使权力的非政府机构所采取的措施”,似乎不应一概而论。当然,尽管笔者暂未查找到我国法律法规中向有关行业组织“授权行使权力”的具体依据,但对于行业组织采取的大部分措施来说,要证明这一点应当问题不大。(30) (二)“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 GATS要适用于某一项措施,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该措施构成GATS意义上的“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上诉机构曾经在“加拿大影响汽车业的某些措施”案中指出:“为了确定某一措施是否构成‘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至少需要分析两个关键的法律问题:第一,是否存在GATS第1条第2款所指的‘服务贸易’;第二,争议措施是否在第1条第1款意义上‘影响’了相关服务贸易。”(31) 1.“服务贸易”的存在 关于是否存在GATS第1条第2款所指的“服务贸易”,上诉机构认为,这要看在某一个案中是否存在通过谈判达成的具体承诺,或者在没有具体承诺时,是否涉及作为一般性义务的最惠国待遇。(32)由于“谷歌事件”和“问题清单”并未涉及最惠国待遇(即不同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差别待遇)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对于“谷歌事件”中谷歌所从事的业务和“问题清单”中外国公司通过跨境方式向中国市场提供的服务,中国政府是否在GATS下做出了相应的具体承诺? 与WTO的相关货物贸易协定相比,GATS的一大特点是它采取的“积极清单”(positive list)自由化模式:WTO各成员只是在它们通过具体承诺表,按照GATS第1条第2款所规定的“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存在”等4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针对某一服务行业承诺了具体义务后,才需要在该行业遵守关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规定。(33)当然,对于载入承诺表的部门,有关成员仍可针对不同的服务提供方式,在承诺表中列入有关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条件和限制。以下结合中国加入WTO时所达成的《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 (下称“《中国承诺表》”),对“谷歌事件”和“问题清单”中可能涉及的服务及中国做出承诺的情况加以分析。 (1)“谷歌事件”可能涉及的服务。GATS一共涵盖12个服务贸易部门、143个子部门,其中第2个部门(通信服务)下的子部门2.C(增值电信服务)列有7个小项,第3项和第7项分别是“在线信息和数据检索”和“在线信息和/或数据处理(包括交易处理)”,这也正是谷歌所从事的主要业务。(34)《中国承诺表》没有就子部门2.C中的“跨境提供”这一服务贸易提供方式单独作出市场准入承诺,但对“商业存在”这一服务贸易提供方式作出了这样的承诺:“将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在上海、广州和北京设立合资增值电信企业,并在这些城市内提供服务,无数量限制。合资企业中的外资不得超过30%。……中国加入后两年内,将取消地域限制,外资不得超过50%。”在“国民待遇”一栏中,对应的表述则是“没有限制”。(35)据此,外国相关服务贸易提供者无权以“跨境提供”的方式,从其他成员的领土(包括通过位于其他成员领土上的服务器)向中国领土内提供有关服务,(36)但可通过在中国设立外资股比不超过50%的合资公司,以“商业存在”的方式来提供上述服务,并在此范围内享有完全的国民待遇。“谷歌中国”就是根据中国国内法和我国在GATS下的上述承诺,由谷歌公司与北京飞翔人信息有限公司(赶集网)共同出资设立的一家合资企业(其全称为“北京谷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两个出资方各占50%股份),它在2007年9月取得由中国信息产业部颁发的新ICP牌照,并通过www.google.cn在中国大陆提供相关服务。由此可见,“谷歌事件”所涉及的服务贸易是:谷歌公司通过设立“谷歌中国”,以商业存在的形式在中国大陆提供的互联网“在线信息和数据检索”以及“在线信息和/或数据处理(包括交易处理)”等服务。(2)“问题清单”中可能涉及的服务。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的信件可以看出,“问题清单”主要针对中国之外的公司以“跨境提供”方式,通过互联网向中国市场提供的相关服务。从《中国承诺表》中不难看到,在GATS所涵盖的大多数部门或子部门,中国对外国公司以跨境提供方式来提供服务都没有加以限制。例如,在第1个部门(“专业服务”)中的“法律服务”(CPC861,不含中国法律业务——原注)这一子部门,中国对第3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即“商业存在”作出了限制,(37)但对第1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即“跨境提供”,《中国承诺表》载明的是“没有限制”,这就意味着,中国允许外国法律专业服务机构通过包括互联网等方式,跨境向中国消费者提供除中国法律业务外的其他法律业务。因此,“问题清单”中所涉及的服务贸易主要是:普通外国公司以跨境提供方式向中国市场提供的、《中国承诺表》中对该方式没有加以限制的各种服务。 2.“影响” 何种措施可以构成“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上诉机构在“欧共体—香蕉进口、销售和分销案”中指出:“GATS第1条第1款中对‘影响’一词的使用,表明了起草者赋予GATS广泛适用范围的意图;‘影响’一词的通常含义是一项措施对某事产生影响(have an effect on),其适用范围是很广的。”(38)在后来的“加拿大一影响汽车业的某些措施”案中,专家组曾经主张,对某一争议措施是否“影响”服务贸易的判断,需要首先认定相关措施是否违反GATS某一实体义务。但是,上诉机构推翻了这一立场。上诉机构强调指出,确定GATS能否适用于某一争议措施(包括该措施是否“影响”了特定服务贸易),必须在评判该措施是否与GATS的某一实体义务相符之前作出。(39)换言之,某一措施是否属于GATS所指的“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与该措施是否“违反”GATS相关义务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影响”是“违反义务”的前提,但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并不必然会违反GATS的义务。 如果一国对特定服务贸易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全部或有条件地加以禁止,这显然会对相关服务贸易的提供产生“影响”。在“美国—影响赌博和博彩服务的跨境提供的措施案”中,美国所采取的禁止通过互联网跨境提供赌博和博彩服务的措施,被上诉机构认定属于GATS第1条第1款所指的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40)同样的,中国采取措施对特定互联网信息予以过滤以及对特定境外服务贸易提供者的网站加以屏蔽、信息阻隔(如果中国政府不能证明这种情况不存在),这会“影响”有关服务的提供,应当是不难加以认定的。 (三)小结 如前所述,在“谷歌事件”和“问题清单”中,都存在GATS第1条第1款所指的“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因而GATS可以得到适用,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上述认定并不必然意味着我国的有关措施“违反”了GATS的义务。对于后一问题,下文将加以分析。 四、互联网监管政策的服务贸易法律问题之二:监管措施与GATS的相符性分析 在确定了GATS可以适用于一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后,更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其他WTO成员将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可能被指控违反GATS下的哪些义务?又能否援引相关例外规定成功加以抗辩? (一)我国可能被指控违反的相关义务 1.中国《承诺表》下相关具体承诺 具体而言,在“谷歌事件”中,有关国家可以主张:对于子部门2.C(增值电信服务)特别是其中的第3项(“在线信息和数据检索”)和第7项(“在线信息和/或数据处理(包括交易处理)”),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措施与中国针对“商业存在”做出的承诺不符。在“问题清单”中,有关国家则可以主张:对于所有在《中国承诺表》中没有针对第1种服务贸易做出限制的服务贸易部门和子部门,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都与中国做出的承诺不符。 2.GATS第3条(透明度) 该条规定:“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各成员应迅速并最迟于其生效之时,宣布所有普遍适用的有关或影响本协定实施的措施……”(第1款);如该款所指的公布不可行,则“此类信息应以其他方式公之于众”(第2款)。 透明度原则,是WTO法要求各成员在管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领域应当遵守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我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而言,尽管我国立法机关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都依法进行了公布,但在实践中,这些法律法规往往需要通过各种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来加以细化(美国在其“问题清单”中,也提到阻碍连接到外国网站的“指南”和“标准”)。而这些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不是都得到了及时的公布,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3.第6条(国内规制) 该条是WTO成员涉及服务贸易的国内管理措施的主要规则,共包括6款,其中第1款规定:在已作出具体承诺的部门,每个成员应确保所有普遍适用的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以合理、客观和公正(reasonable,objective and impartial)的方式实施。那么,我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是否符合该条款的规定? “以合理、客观和公正的方式实施”的含义是什么?GATS中没有对此加以澄清,WTO的以往案例也几乎没有涉及这一问题。不过,GATT第10条(贸易法规的公布和实施)的措辞和精神与之非常相似,尤其是其第3款(a)项规定各成员法律、法规、判决和裁定应以统一、公正和合理(uniform,impartial and reasonable)的方式实施。因此,有关该条款的案例将为GATS第6条第1款下的贸易争端提供重要参考。(41)具体而言,在涉及GATT第10条第3款(a)项的案例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主要是着眼于对个案具体事实的分析,来裁定“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实施”的要求是否得到了遵守。以下几点尤其需加以注意: 首先,在“美国—影响赌博和博彩服务的跨境提供的措施案”中,专家组明确指出:GATS第6条第1款并不涉及有关国内措施的实质内容,而仅仅针对其实施程序。(42)在有关GATT第10条第3款(a)项的案例中,专家组也持类似态度。由此可见,其他国家很可能无法通过该款对我国互联网监管政策的实质内容(例如,哪些信息应当受到审查和过滤)加以投诉。 其次,在“阿根廷—牛皮和皮革案”中,专家组曾经强调指出:“在适用GATT第10条第3款(a)项时,要求就某一措施对商业领域的贸易者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考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需要证明存在贸易上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那些违反GATT1994的行为而言,这种损失的证明并不是一项要求。但是,有可能需要分析的是,由于海关规则、法规、决定等的实施被投诉不公正、不合理或缺乏统一性,因而可能对竞争关系产生了影响。”(43)根据这一分析,在涉及中国互联网监管政策的争端中,投诉方需证明中国监管政策的实施方式的确使其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受到了不利影响。而从中国政府的角度看,如果能够证明我国互联网监管政策的实施方式与世界上大多数或者相当一部分国家类似,无疑有助于避免本国措施的实施被视为不合理、不客观、不公正。 最后,在“美国—对来自阿根廷的石油管反倾销措施的日落复审案”中,上诉机构提出:投诉一个WTO成员的行为不公正或不合理,这是一种严重的指控,因此,“依据GATT1994第10条第3款(a)项提出的投诉必须用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投诉的性质、范围和用以支持该投诉的证据应当与根据ATT1994第10条第3款(a)项所提出投诉的严重性相一致。”(44)同样可以预见的是,投诉方根据GATS第6条第1款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指控,应当进行与这一指控相一致的充分举证。 4.第16条(市场准入) 该条一共包含两款,其中第1款规定:就GATS所规定的4种服务提供方式而言,“每一成员对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给予的待遇,不得低于其在具体承诺表中同意和列明的条款、限制和条件”;第2款进一步要求:除在承诺表中另有列明者外,WTO成员在其作出市场准入承诺的部门中,不得就服务提供者的数量、服务交易或资产总值、服务业务总数或服务产出总量、特定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可雇用的自然人总数、服务提供者作为法律实体的类型、外国股权最高百分比或外国投资总额等6个方面维持或采取任何限制性措施。 其他国家可以主张,对于外国公司以“跨境提供”的方式(包括通过互联网)向中国境内消费者提供服务,中国在《承诺表》中没有做出限制而又通过互联网监管政策妨碍了这些外国公司的市场准入,从而违背了该条第1款的要求。 5.第17条(国民待遇) 该条规定:在遵守承诺表所列任何条件和资格的前提下,各成员对于列入承诺表的部门,“在影响服务提供的所有措施方面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本国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美国的“问题清单”中,的确有几个问题直接涉及国民待遇问题。例如,第四部分第3个问题是:“中国境内和境外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获得的应被过滤的词语是否相同?”第5部分第6个问题是:“针对境外互联网内容的不法信息监控程序是否与针对境内互联网内容的监控程序是否不同?如果不同的话,那么这两个程序的区别体现在哪里?”在“谷歌事件”中,境外研究者也对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歧视作为美国公司的谷歌而有利于百度等本国企业颇有指责。(45)但是,由于无法从官方渠道获知中国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具体做法,因而难以对我国互联网监管措施是否违反国民待遇条款作出确切的回答,而只能假设如果美国提出的上述问题属实,我国将难以证明有关做法符合国民待遇义务。(46) (二)中国可以提出的抗辩 1.第3条之二(机密资料的公开) 该条规定:“本协定的任何规定都不得要求任何成员提供那些机密资料。”但是,如果中国援引这一条款,就需要证明我国互联网监管方面未公开的相关标准、指南、内部文件属于该条所定义的机密资料,这些资料“一旦公开会阻碍法律的实施或违背公众利益,或损害特定公营或私营企业合法商业利益”。尽管WTO争端解决实践并没有对这一条做出过权威的解释,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容易。 2.第14条(一般例外) 该条规定:“只要这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况相同的国家间构成武断的、或不公正的歧视,或构成对服务贸易的变相限制,则本协定的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成员采用或实施:(a)为保护公共道德或维护公共秩序所必需的措施……”、该条款已在WTO争端解决实践中多次被援引,另外,针对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几乎完全相同的措辞,WTO争端解决实践中已有大量判例。根据相关判例,中国要成功援引GATS第14条,存在两大障碍: 第一,证明我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属于该条(a)项所指的“必要性”检测。由于WTO争端解决实践已经澄清,援引一般例外条款的国家有权确定本国认为合适的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保护水平,中国有可能能够成功主张,要达到我国所设定的保护水平,除了现行的严格监管措施(或者至少对其中的相当部分措施而言)外,没有其他可以达到同样保护水平而又贸易扭曲效果较小的替代措施。(47)当然,其他国家也可能就援引该项例外的一个前提问题提出质疑:中国的监管措施是否都与保护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有关?鉴于中国互联网监管措施的复杂性,这里不一一展开分析。 第二,证明我国被投诉措施的实施没有“在情况相同的国家间构成武断的、或不公正的歧视,或构成对服务贸易的变相限制”。WTO争端解决实践已经明确,一般例外条款中的这一引言,主要是针对被投诉措施的实施方式而不是其实体内容的。(48)如果其他国家能够在此前有关透明度(第3条)、国内规制(第6条)等条款上,证明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措施至少部分不符合这些条款,那么中国的被诉措施将很难通过这一引言的审查。 3.第14条之二(安全例外) 该条规定:“本协定不得解释为:(a)要求任何成员提供其认为公开后会违背其基本安全利益的任何资料……”这一条款源自GATT1994第21条(安全例外),二者措辞几乎完全相同。 笔者认为,该条是中国较有可能成功援引的抗辩,因为它在允许WTO成员拒绝提供公开后会违背其基本安全利益的任何资料时,用“其认为”的措辞将判断权交给援引这一例外的成员。据此,中国可以主张,有关中国互联网监管政策的某些具体资料如果公开,将会损害中国的基本安全利益。但是,即便如此,该条为中国提供的抗辩也仅仅限于特定资料的公开方面,而如前所述,其他国家可能用来投诉中国的条款和义务并不限于此。 (三)小结 尽管“谷歌事件”和“问题清单”所针对的都是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和措施,但在WTO规则下,二者所涉及的服务贸易法律问题有一些重要的区别。前者主要涉及我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对谷歌公司所从事的互联网搜索等服务的影响,问题性质相对单一、具体;后者则涉及我国的监管措施对外国公司以模式一(跨境提供)向中国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影响,波及的企业和服务种类更为广泛。而且,美国在“问题清单”中提出的有关问题层次清楚,目的明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由此不难看出,美方对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和可能涉及的WTO法律问题都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尽管笔者目前获得的信息并不足以在本文中作出完整和深入的分析,但大体而言,中国要证明我国的互联网监管措施完全符合WTO义务,面临的任务将十分艰巨。(49) 五、几点结论性认识和对策建议 鉴于互联网在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包括对国家战略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主权国家有权基于各种正当理由,对互联网进行监管。在实践中,当今世界的几乎所有国家,都以不同方式对互联网的使用加以监管。事实上,互联网监管本身在国际法包括WTO法上并未受到禁止。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一国是否对互联网进行监管,而在于该国特定的监管程度和监管方式。 在中国获准加入国际互联网的1994年,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揽子协定则尚未生效。不难设想,在WTO所管辖的多边贸易规则谈判和生效之时,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互联网将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更难以预见的是,一国互联网监管政策会成为WTO法上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但事实上,正是在“不经意”中,WTO规则已经成为国际法上评判(进而约束)互联网监管政策的主要标准。 (一)互联网监管政策涉及一系列多边贸易规则下的重要法律问题,我国应对此加以重视 前文着重结合2010年“谷歌事件”和2011年“问题清单”的分析表明,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一国实施的网站屏蔽、信息过滤等互联网监管措施有可能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这类措施是否构成与多边贸易规则不符的贸易壁垒,已成为一个值得探讨和澄清的新议题。根据前文研究,互联网监管措施涉及一系列多边贸易规则下的法律问题,例如: ——如果说互联网监管措施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影响相对易于证明,那么,这类措施是否也可能对国际货物贸易产生影响,从而产生GATT1994下的法律问题?更具体地说,GATT1994的哪些条款、在何种情况下对互联网监管措施适用? ——在GATS框架下,如何对通过互联网提供的特定服务加以分类?例如,谷歌作为互联网公司提供的服务涉及GATS下的哪些服务贸易部门和子部门?毕竟,确定国际服务贸易部门和子部门的基本文件——《服务行业分类表》(50)在1991年由原关贸总协定秘书处制定时,还根本无法对随后出现的互联网相关服务加以预见和明确规定。今天,应当如何根据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法律文件加以解释? ——在“谷歌事件”和“问题清单”中,互联网监管措施可能具有的歧视性和对国民待遇原则的违反都被提出来了。那么,如何证明一国的监管措施对境外服务或服务提供者进行了比对本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更为严格的监管?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境外服务或服务提供者与本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是“同类”(like)的?一定的差别待遇本身是否必然违反GATS的国民待遇条款? ——在某种互联网监管措施被指控违反WTO规则的情况下,实施该措施的国家往往会援引GATT1994第20条或GATS第14条中的公共道德例外。那么,该项例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特定的互联网监管措施提供抗辩?该例外中的“必要性”和引言要求应如何加以解释?等等。 尽管至少在“谷歌事件”出现后,这些法律问题已经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由于种种原因,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客观的分析和澄清并非易事。首先,互联网监管政策涉及的主要WTO规则——GATS是一个存在不到20年的新协议,涉及该协定的贸易争端也远远少于GATT1994下的争端,这使GATS的很多条款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和适用;其次,从多边贸易规则角度对互联网监管政策的探讨还是一个较新的问题领域,相关研究和前人成果都较为薄弱;再次,不少国家的互联网监管政策和相关实践缺乏必要的透明度,这进一步加大了研究的难度。 有鉴于此,本文的第一条对策建议是:作为“谷歌事件”和“问题清单”主要当事国,中国应当未雨绸缪,高度重视互联网监管政策与多边贸易规则法律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认真研究WTO法相关规则、判例的法律内涵和演变趋势,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谈判,使未来的国际规则更好地反映我国的利益和需要。 (二)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处理互联网监管政策的“贸易与人权关联”,是否合适和有效值得怀疑 西方国家对中国互联网监管政策的关注,呈现出政治(人权保护)和经济(商业利益)两个不同层面,二者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其中,在前者即与互联网有关的人权特别是言论自由问题上,西方国家关注较早,但偏重于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美国相关国内法的角度加以质疑,但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国际法依据。相比之下,在后者,即贸易和市场准入问题上,西方国家尽管发声较晚,却一开始就是以具有权威性和普遍性的国际法(具体而言是指WTO法)规则为依据,而且调门不断提高,“政治问题商业化”的策略不断彰显,并在“谷歌事件”和“问题清单”中折射出一种新的“贸易与人权关联”(trade and human rights linkage),需要加以高度重视。 在西方学界和媒体的推动下,国际贸易和人权保护这两个长期彼此孤立的领域,自东西方冷战结束特别是1995年WTO成立以来开始“挂钩”。尽管人们对于两者的关系有着各种不同的认识,但是,这一时期的“贸易与人权关联”包含着以下重要理论假设:那些“侵犯或无视人权的国家”不应被国际贸易体制所接受;对这些国家的“惩罚”(包括通过WTO进行贸易制裁)可以迫使这些国家改变政策,从而推动人权保护。(51)当然,这一立场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很少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主张,其“利益偏向”显而易见。(52) 在“谷歌事件”前后,一种新的“贸易与人权关联”开始形成。在围绕互联网监管政策的纷争中,西方国家极力鼓吹以自由贸易为手段推动所谓的人权议程,这与以往的“贸易与人权关联”倡导通过对“侵犯人权国家”实施贸易制裁手段来维护人权不同。关于这一点,一位学者在2008年美国国际法年会上,就“互联网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Internet)专题做出过如下的直白表述: “人权的倡导者时常发现他们与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存在争执。推动生产效率更高的货物自由跨境流动这一愿望有时在关注工人权利和环境保护方面存在欠缺。然而,网络空间可以提供一个使自由贸易的愿望和推动政治自由的想法携手并进的场所。通过网络空间的贸易自由化,国际贸易法可以推动原本受‘专制体制’控制的信息流动。……始料未及的是,GATS可能成为一份人权文件。”(53) 在“谷歌事件”和“问题清单”中,西方国家借助WTO规则对中国政府奉行的互联网监管政策发难,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国家所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利用互联网推动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54)从这一点看,新的“贸易与人权关联”有着与以往如出一辙的“利益偏向”。但不能不看到的是,通过推动自由贸易和人权议程的“携手并进”(而不是如过去那样,以保护人权的“矛”攻自由贸易的“盾”),西方国家的主张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者和更大的道义吸引力,并因此而产生更大的攻击性和威胁性。 但是,这种“政治问题商业化”的做法,是否有利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健康发展?又是否有利于加强中国、美国等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和战略合作?这些问题无疑是值得思考的。2013年“斯诺登事件”表明,美国在互联网监管问题上经常奉行双重标准。(55)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为中美等国之间就互联网监管问题进行平等对话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的另一对策建议是:中国应当推动通过WTO以外的场所和手段来解决不同国家围绕互联网监管政策的分歧,如通过业已建立的中美、中欧等互联网双边对话机制和联合国、“伦敦进程”等多边网络进程,来推动有关网络空间治理包括互联网监管政策的国际合作,在合理平衡“互联网自由”与“互联网主权”等不同关切的前提下力求达成若干政治共识,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制定有关互联网监管的国际法准则。 (三)推动我国互联网监管政策进一步走向法治化,这符合我国长远的国家利益 迄今为止,中国加入WTO已有近15年。经过与多边贸易体制多年的磨合与适应,中国将迎来更多机遇和更大挑战同时并存的复杂格局,牵涉不同国家之间社会制度差异的贸易摩擦将越来越多地出现。(56)由此带来的问题之一是,单纯从经济和贸易角度研究WTO法律问题(包括贸易争端),将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新需要。在笔者看来,如何切实有效地反对“贸易与人权关联”,将是我国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但与此同时,在互联网监管问题上,如何科学地借鉴其他国家成熟和具有普适性的社会管理经验,使互联网更好地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进器,这同样值得我国政府和学界深入探讨。 中国政府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重要文件中宣示,将致力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包括“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57)这里,“依法治国”必然包括“依法治(互联)网”;(58)而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奉行的法治,不仅包括我国的国内立法,还包括中国加入、接受的国际条约和其他国际法,这一点也应当予以明确。(59)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恰恰反映了WTO法对于推动中国互联网监管政策进一步走向法治化的潜在作用。 法治的基本目的之一,在于约束对公权力的滥用和确立对私权利的必要保护。过去十几年中,我国已经制定一大批关于互联网监管的法律法规,这为我国依法治理互联网奠定了基础。但在实践中,我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和相关具体措施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法治的要求?是不是具有可持续性?是不是符合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的第三条对策建议是:我国政府应当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本国核心利益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借鉴其他国家互联网管理的成熟经验,大力完善我国的相关国内立法和措施,使我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在法治理念的指引下,向更为透明、更为合理、更为“必要”的方向迈进。切实奉行“依法治网”、推动我国互联网监管政策进一步走向法治化,这也完全符合我国长远的国家利益。 注释: ①张恒山:《美国网络管制的内容及手段》,《红旗文稿》2010年第9期,第33-34页。 ②有关境外学者对我国互联网监管手段特别是所谓“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的研究可参见:Cynthia Liu,"Internet Censorship As a Trade Barrier:A Look at The WTO Consistency of the Great Firewall in the Wake of the China-Google Dispute",42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207-1211(2011). ③See Fredrik Erixon & Hosuk Lee-Makiyama,"Digital Authoritarianism:Human Rights,Geopolitics and Commerce",ECIPE Occasional Paper No.5/2011,p.5,http://www.ecipe.org/media/publication_pdfs/digital-authoritarianism-human-rights-geopolitics-and-commerce.pdf,last visited on 22 September 2014. ④早在2006年,美国众议院就提出一个所谓的《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Global Online Freedom Act,简称为GOFA)草案,计划对美国公司在“限制网络自由的国家”参与实施网络审查制度的行为加以惩罚,还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发布报告,指明哪些国家限制网络自由;并对那些有网络过滤功能的软件和硬件进行出口管制,禁止这些产品流通到“限制网络自由”的国家。随后,美国众议院又分别在2007年、2009年、2011年4月和12月、2012年6、2013年2月以及2014年11月多次推出该法案几个不同的新版本。See e.g.David Fidler,"The Internet,Human Rights,and U.S.Foreign Policy:The Global Online Freedom Act of 2012",16 ASIL Insights,24 May 2012,pp.1-2,http://www.asil.org/sites/default/files/insight120524.pdf,last visited on 15 August 2014. ⑤下文关于“谷歌事件”的介绍和法律分析,可另参见黄志雄、万燕霞:《论互联网管理措施在WTO法上的合法性——以“谷歌事件”为视角》,载孙琬钟主编:《WTO法与中国论丛(2011年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294页。 ⑥Google,"A New Approach to China",http://www.google.com/press/new-approach-to-china/,last visited on 3 March 2012. ⑦谷歌公司:《关于谷歌中国的最新声明》(2010年3月23日,中文版),http://www.google.com/press/new-approach-to-china/update.html,2012年3月10日访问。 ⑧《国新办网络局负责人就谷歌退出中国内地发表谈话》,http://news.china.com.cn/txt/2010-03/23/content_19661008.htm,2012年3月10日访问。 ⑨《关于谷歌中国的最新声明》(2010年6月28日,中文版),http://www.google.com/press/new-approach-to-china/update_0610.html,2012年3月12日访问。 ⑩See Geoff Dyer,"China Renews Google Web Licence",Financial Times,9 July 2010,http://www.ft.com/cms/s/2/32d48ae2-8b5b-11df-a4b4-00144feab49a.html,last visited on 8 March 2012. (11)维基百科:《谷歌退出中国事件》,http://wapedia.mobi/zhsimp/%E8%B0%B7%E6%AD%8C%E9%80%80%E5%87%BA%E4%B8%AD%E5%9B%BD%E4%BA%8B%E4%BB%B6,2012年4月17日访问。 (12)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on Internet Freedom",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519.htm,last visited on 5 January 2014; Hillary Rodham Clinton,"Internet Rights and Wrongs:Choices & Challenges in a Networked World",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2/156619.htm,last visited on 5 January 2014. (13)姜瑜:《中国互联网管理措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10/01-14/2072935.shtml,2012年3月10 13访问。 (14)David Coursey,"US May Use WTO to Resolve Google-China Dispute:Obama Administration to Help Google in Censorship Batde",http://news.techworld.com/networking/3214222/us-may-use-wto-to-resolve-google-china-dispute/? olo=rss,last visited on 11 July 2014. (15)Google,"Enabling Trade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Breaking Down Barriers to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15 November 2010,http://googlepublicpolicy.blogspot.com/2010/11/promoting-free-trade-for-internet.html,last visited on 24 May 2013. (16)USTR Press Release,"United States Seeks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China's Internet Restrictions",19 October 2011,www.ustr.gov,last visited on 20 May 2013.GATS第3.4条规定:“对于任何其他成员关于提供……任何普遍适用的措施或国际协定的具体信息的所有请求,每一成员均应迅速予以答复。” (17)Ibid. (18)WTO在“电子商务”层面,对于通过互联网提供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有所讨论。See Sacha Wensch-Vncent,"WTO,Ecommerce,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From The Uruguay Round Through the Doha Development Agenda",http://yinjiang.iie.com/publications/papers/wunsch1104.pdf,last visited on 9 May 2013. (19)EC-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complaint by Ecuador,Guatemala,Honduras,Mexico and United States),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WT/DS27/AB/R,25 September 1997,para.221. (20)See Tim Wu,"The World Trade Law of Censorship and Internet Filtering",7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68(2006). (21)Ibid.,p.268. (22)See Japan-Trade in Semi-Conductors,Report of the Panel,L/6309-35S/116,4 May 1988,para.104. (23)See Turkey-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Products,Report of the Panel,WT/DS34/R,19 November 1999,para.9.63. (24)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Report of the Panel,WT/DS285/R,10 December 2004,paras.6.250-6.255.关于该案的评述可参见黄志雄:《WTO自由贸易与公共道德第一案——安提瓜诉美国网络赌博服务争端评析》,《法学评论》2006年第2期,第122-128页。 (25)See supra note(19),para.180. (26)See e.g.China-Measures Affecting Trading Rights and Distribution Services for Certain Publications and Audiovisual Entertainment Products,Report of the Panel,WT/DS363/R,12 August 2009,para.7.1442. (27)2011年“问题清单”中提到,当某一外国网站使用与中国认为有害的网站相同的IP地址,该网站可能受到“无辜”的屏蔽。参见“问题清单”中第三部分的问题。 (28)参见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状况》,2010年6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6/08/c_12195221.htm,2013年11月15日访问。 (29)例如,我国相关立法关于严禁传播含有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煽动民族仇恨、破坏民族团结、宣扬邪教以及淫秽色情、暴力、恐怖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内容的信息等规定。 (30)在WTO法上尚未出现“授权行使权力”的相关判例,可供参考的是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二读通过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5条之规定:“虽非第4条所指的国家机关,但经该国法律授权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人或实体,其行为依国际法应视为该国的行为,但以该人或实体在有关事件中系以政府资格行事者为限。”虽然该条款草案尚未生效,但被广泛认为反映了习惯国际法的内容。相关讨论参见贺其治:《国家责任法及案例浅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1-92页。 (31)Canada-Certain Measures Affecting the Automobile Industry,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WT/DS 139 & 142/AB/R,31 May 2000,para.155. (32)See ibid.,para.156. (33)See Mitsuo Matsushita,Thomas J.Schoenbaum & Petros C.Mavroidis,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Law,Practice,and Policy,2[nd]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630. (34)也有学者对这一归类提出不同见解。See Henry-Gao,"Google's China Problem:A Case Study on Trade,Technology and Human Rights Under the GATS",6 Asian Journal of WTO and International Law & Policy 359-365(2011).应当看到,WTO设立和GATS生效时,互联网的发展尚处于刚起步的阶段,很多基于互联网的服务都是近年来才得到迅速发展。因此,如何合理地将这些互联网服务纳入GATS所涵盖的服务贸易部门(子部门),的确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35)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世界贸易组织司译:《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中英文对照),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16-717页。 (36)由于中国香港是WTO的一个单独成员,2010年3月23日后谷歌公司通过其在香港的服务器向中国大陆用户提供“未经审查过滤的搜索引擎服务”,显然是超出了中国政府在GATS下承诺的义务范围。 (37)具体措辞为:“外国律师事务所只能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口、大连、青岛、宁波、烟台、天津、苏州、厦门、珠海、杭州、福州、武汉、成都、沈阳和昆明以代表处的形式提供法律服务。”参见前引(35),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世界贸易组织司书,第716-717页。 (38)See supra note(19),para.220. (39)See supra note(31),paras.148-167. (40)See supra note(24),paras.6.250-6.255. (41)See Mitsuo Matsushita,Thomas J.Schoenbaum & Petros C.Mavroidis,supra note(33),p.630. (42)See supra note(24),para.6.432. (43)See Argentina-Measures Affecting the Export of Bovine Hides and the Import of Finished Leather,Report of the Panel,WT/DS155/R,19 December 2000,para.11.77. (44)See United States-Sunset Reviews of Anti -Dumping Measures on Oil Country Tubular Goods from Argentina,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WT/DS268/AB/R,29 November 2004,para.217. (45)一些研究者还提出:中国政府对“脸谱”、“推特”等境外社交媒体网站加以禁止而允许本国的人人网等提供类似服务,这也构成对GATS国民待遇条款的违反。See Cynthia Liu,supra note②,p.1228.对此,笔者认为,需要对“脸谱”等网站所涉及的服务加以定性后考察《中国承诺表》中是否对开放相应服务做出了承诺;只有在存在相应承诺时才会存在可能违反国民待遇原则的问题。 (46)中国政府并未就对“问题清单”的答复公开提供任何信息,但据笔者向相关政府官员咨询的情况,可能性较大的是中国政府对该“问题清单”进行了答复,但在较为敏感的问题上,只提供了原则性的信息。 (47)一些研究者主张:对于中国所具有的互联网监管技术水平而言,针对特定违法信息进行选择性的过滤可以视为能够达到与全部屏蔽特定网站保护水平相当而又贸易扭曲效果较小的替代措施,在此情况下,将很难主张全部屏蔽某一网站是一种“必需”的措施。See Brian Hindley,"Protectionism Online:Internet Censorship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Law",ECIPE Working Paper No.12/2009,http://www.ecipe.org/publications/ecipe-working-papers/protectionism-online-internet-censorship-and-international-trade-law/PDF,last visited on 9 July 2014.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原则上是可以成立的。 (48)See United States-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 and Conventional Gasoline(complaint by Venezuela and Brazil),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WT/DS2/AB/R,29 April 1996,p.22. (49)当然,如果西方国家最终将我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而我国最终败诉,根据《WTO争端解决程序谅解》(DSU)和GATS等协议的规定,我国除了废除被认定与多边贸易规则不符的互联网监管措施外,还有接受他国贸易报复、赔偿以及寻求撤销《中国承诺表》中相关承诺等选择。限于篇幅,本文不对此加以详细探讨。See Brian Hindley,supra note(47). (50)Services Sectoral Classification List,Note by the Secretariat,MTN.GNS/W/120,10 July 1991. (51)See e.g.Patricia Stirling,"The Use of Trade Sanctions as an Enforcement Mechanism for Basic Human Rights:A Proposal for Addit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11 Americ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Policy 1-46(1996).See also Mitsuo Matsushita,Thomas J.Schoenbaum & Petros C.Mavroidis,supra note(33),pp.923-924. (52)参见李春林:《国际法上的贸易与人权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53)Anupam Chander,"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et Freedom",102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37(2008). (54)“谷歌事件”出现后,一些西方学者直言这将是利用商业政策(WTO规则)来约束互联网监管政策的突破口。See Fredrik Erixon & Hosuk Lee-Makiyama,supra note③,p.4. (55)根据2013年6月“斯诺登事件”披露的机密文件,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不仅以“反恐”为名,长期通过黑客攻击入侵中国、俄罗斯乃至其欧洲盟友的电脑和通信系统,还利用“棱镜”(Prism)等秘密计划获得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九大网络巨头的合作,通过这些网络公司大量监控电子邮件、收集敏感数据。《参与机密计划大量收集数据九大网络巨头被爆“听命”美情报机构》,《参考消息》2013年6月8日,第6版。 (56)2007年美国就进口电影、音像产品、录音制品及出版物等文化产品的贸易权和分销服务措施投诉中国的贸易争端(WT/DS363)中,这种基于社会制度差异而产生的贸易摩擦就已经初露端倪。关于该案的相关评述可参见彭岳:《贸易与道德:中美文化产品争端的法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136-148页。 (5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0/28/c_1113015330.htm,2014年10月31日访问。 (58)中国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也强调:应加强网络立法、网络执法、全网守法,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建设。鲁炜:《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4-10/25/c_133741732.htm,2014年10月25日访问。 (59)事实上,国际法作为国际关系的规范维度,已经成为一国软实力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参见何志鹏:《走向国际法的强国》,《当代法学》2015年第1期,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