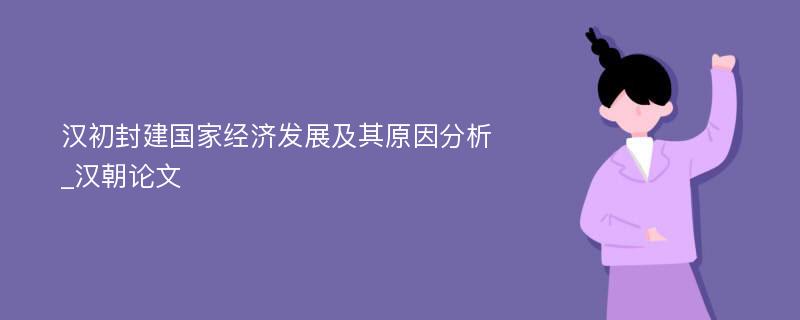
汉初封国经济发展及其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原因论文,汉初封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2)01-0001-10
西汉初年,统治者在地方上推行了郡县与封国并行的双轨行政体制,局部实行分封不仅在政治上起到了辅弼中央的重大作用,而且对当时经济的发展亦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由于资料的不足和零散,给探讨汉初封国经济带来了诸多困难,今笔者不揣鄙陋,运用文献和考古资料,列举汉初封国经济发展的表现,并试图分析促成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
近年来,秦汉考古为我们审慎研究历史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开辟了研究领域的新篇章,借助西汉前期地下出土资料,我们可一管窥汉初封国经济发展的诸多表现。
(一)农业
1.铁农具的发展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后在全国设置铁官49处。[1](《地理志》)汉初属王国的就有30处,铁矿资源王国占了大半,说明王国冶铁业发达。在战国秦汉时代,冶铁作坊制造的铁器以农具居多,王国冶铁手工业的普遍存在,说明王国人民铁农具的使用当更为普遍。以位于“火耕水耨”之区的吴国为例,吴国素来被认为农业生产落后,但广西贵县罗泊湾出土的西汉初期墓中有一件自题为《东阳田器志》的木牍[2],记有铁锄、铁锨、铁钪、铁锸等农具,东阳(今江苏盱眙县)是吴国东阳郡(县),在南越之地发现东阳郡的铁器,无疑说明吴国生产的铁农具数量较大,除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外,还远销岭南,铁器在吴国的普遍应用自不待言。
根据考古资料统计,虞国时的铁农具主要有锄、斧、镬、镰、叉、犁(铧)、铲(锸)等,种类不超过十种。而且在战国时期先进的农业区——黄河中下游地区,非铁制的农具仍占相当部分。时至汉初,封国所拥有的铁农具无论在品种、还是在质量上都比战国时期有很大增加和提高。从山东莱芜县(即齐国泰山郡的嬴县)出土的汉初农具铁范来看[3],当时已有了整地工具耙,这是汉代出现的新农具。《释名》解释为“播也,除以播除物也,亦言拨也,拨使聚也。”即用于犁过的田地,以平土除草,劈碎土块,清除杂物,从而使土地平整的工具,后来农村使用的铁搭和手耙大抵是它的改进和演变。除新式工具外,与战国相同的工具,其具体的形制也有改进,莱芜所出铁范显示,起破土作用的犁,其犁头已由战国时的钝形变尖,犁铧的上口加宽,铧的头部角度减小,两刃内侧交接处向后延伸,这种铧头既比较坚固,耕种时又省力而深入;镢(即镬)的刃部较之战国加宽。另外,汉初的王国可能已创造出了装在铧上的翻土装置——犁壁,犁壁作为犁铧的复合设备,其效用在于翻土、作垄、灭草,这在属于齐国北海郡的安丘曾有发现。[4]铁农具品种的增多和改进不仅提高了耕作效率,同时也为提高耕作质量创造了条件。
2.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齐鲁梁楚等国自古就是种植业生产区,农业生产技术有一定基础,农业生产工具分工已较细,从耕种到收获,田间作业的每一过程都有相应的农具与之配合,耕作栽培日趋精细,《庄子·则阳》载:“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韩非子·解老》曰:“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表明战国时此地人们已认识到深耕和粪灌的必要性,好稼穑耕作的齐鲁梁楚等国的农民肯定会进一步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吕后时,齐王刘襄之弟章给高后说《耕田歌》:“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鉏而去之。”[5](《齐悼惠王世家》)这当是对齐国境内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西汉初期已懂得收集人畜粪尿来作肥料,《史记·吕太后本纪》所载以戚夫人为人彘“居厕中”之厕即为与猪圈相连的厕所,说明汉初人民确已注意养猪积肥,以粪肥田。解放后,在考古发掘的西汉中期墓中有许多陶屋和陶猪圈,陶屋是干栏式建筑,上面住人,下面关牲畜,上层还设有厕所与屋下猪圈相通,人粪可以从楼上直落猪圈,与圈中的猎粪及饲料残渣充分混合,沤成熟腐的肥料,表明人们已懂得生粪需要沤制腐熟才能加速肥力的转化,提高在农田的施用效果。这种结构在西汉中期墓中普遍存在,说明汉初已经出现,这是以前生产经验的总结。
江淮以南的封国种植水稻虽仍“火耕而水耨”,但当时已很注意选择肥沃而湿润的土壤来栽培水稻。如吴王濞时东阳县有沼泽地长洲泽,麋鹿“千千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麋畯”。这种麋畯既肥沃又湿润,当时有些农民就“随此畯种稻,不耕而获,其收百倍”[6](《郡国三·广陵郡》)。又《史记·河渠书》记载:“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索隐》释曰:“其田既薄,越人徙居者习水利,故与之,而稍少其税,入之于少府。”越人是会稽郡人民,汉初属吴国,汉武帝时,徙居河东,因为他们栽培水稻有专长,故把河东渠旁的薄地租给他们,河东地区在春秋时已开始种水稻,但对于在贫瘠的水田上如何有效地栽培水稻的技术显然不及吴国人民。说明江南人民栽种水稻的技术已十分精湛,远远超过了北方。
3.农作物品种丰富,产量提高,加工技术进步
汉代作为食物的农作物品种以粟、稻、小麦、大麦、黍、豆等谷类最为重要。现在我们一般认为北方宜粟、麦,南方植稻谷,但汉初王国由于农业耕作条件的优越,作物品种并没有严格的地域区分,楚国不仅种麦、粟,还种植稻谷,1972年徐州奎山一座西汉初的墓葬中即出土有稻粒[7]。由此可知黄淮流域的梁、楚等国在汉初已成为水稻和旱谷的间作区。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情况来看,南方王国的水稻种植不仅已很普遍,而且稻作物的品种极为丰富,籼、粳、粘、糯并存,长粒、中粒、短粒并存,有芒和无芒并存[8]。长沙国除植稻外,还种植小麦、大麦、黍、粟、大豆、赤豆、葵、大麻等农产品[8]。除上述谷物外,作为食物的农产品还有薏苡、芋、芥菜、甜瓜、葫芦、笋、藕、生姜等类,果品方面则有栗、枣、梨、桃、李、杏、梅、杨梅等[9],这都可从汉初王国墓葬中发现,兹不赘述。
汉兴,接秦之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1](《食货志》)。可谓粮食极端缺乏,到文帝时已是“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5](《律书》)。宣帝时则“谷至石五钱”[1](《食货志》),粮食价格的不断下跌,反映出粮食供应量的增加。当时关东广大地区绝大部分是诸侯王统治区,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十万石”,武帝时已“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10],仅漕粮一项就增至汉初的40倍,这一信息透露了西汉前期整个关东诸侯王国农业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事实证明,经过汉初短短四五十年的发展,王国人民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对全国粮食的增加做出了突出贡献。
不仅关东诸国如此,江南诸国粮食产量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以农业不算发达的吴国计,汉初刘濞为吴王,措施得当,农民生产积极性高,使得“国用富饶”[5](《吴王濞列传》),粮食不仅自给,而且有了大量剩余,吴国太仓所储粮食足以与中央媲美。七国之乱爆发前,吴国郎中枚乘指出文帝后期由关东漕运西向长安的粮食,还不如吴国太仓所储的粮食多[1](《枚乘传》),汉武帝初,东海闽越王企图反叛,淮南王刘安上疏曰:“越人欲为变,必先田馀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1](《严助传》)馀干即余汗县,隶属淮南国,说明在西汉中叶以前馀干县已成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区。“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怜之,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使者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焉。”[1](《食货志》)北方人民流徙到江淮间就食,证明该地区的粮食仍自给有余,因饥民过多,方才从巴蜀调粮食来接济。
谷物加工方面,虽然不能肯定汉代画像石《庖厨图》中所表现的石磨加工、妇人杵臼舂米[11]的成套作业的现象在汉初已经出现,但当时已普遍使用改良过的石磨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改良过的石磨仅徐州地区就出土不少。我国传统的石圆磨虽在战国就已出现,但其磨齿成凹坑形,形状有枣核形、圆形、菱齿形不等,不规则地分布于磨盘上,很容易使粮食堵塞在磨齿中,难以磨碎,而且又难以送出磨体。汉初封国人民对此进行了改良,从徐州九里山出土的明器磨[12]和河南淇县发现的石磨[13]来看,上下两层磨均呈弧形,底内凹,磨齿呈斜线辐射型,这样既能充分磨碎谷物,又有利于送出谷物,大大提高了粉碎加工能力,而且有的磨已安装了磨架,更有利于操作。此次改良后的磨一直成为我国民间一种主要的粮食加工工具。
4.农业人口的增长
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人口的增长,农业劳动力的增加也就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口与生产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影响着汉代社会的进步。
汉初长沙国户口据文帝时贾谊“上疏陈政事”中可知:长沙国乃二万五千户耳[1](《贾谊传》)。据《汉书·诸侯王表》知吴氏长沙国南北疆界线是“波汉之阳,亘九疑,为长沙”。西部至《汉志》所载武陵郡界,东部包括豫章郡三县[14]。其疆域相当于今一个半湖南省的面积,达到30多万平方公里,可谓幅员广大,但户口却极少,若每户以五口计,长沙国只有12.5万人,平均二至三公里才有一人。贾谊陈政事疏离汉初建国仅二十多年,他所提供的户口若有所据的话,很可能是汉初吴芮始封长沙国时的数字,而非文帝时的户口数,因战乱影响,民人逃亡流徙,户口可得而数者才什二三,故人口显得尤为稀少。
绘制于吕后末年的《长沙国南部驻军图》[15]对五岭山区二千平方公里的五十多处居民点的户口作了详细的标注,总户数为八百多户,每户以五口计,则有四千多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二人,但考虑到五岭山区的人口密度素来比江汉平原及湘、资、沅、澧等水下游平原低得多。故可估计,到高后末年,长沙国的人口密度至少已达每平方公里二人以上。全国总户数当不低于十二万户,口数当不低于六十万人。人口比汉初翻了二番多,说明除原来因战乱逃亡的人回归故里外,人口自然增长的数目也很高。1960年长沙杨家山发掘了一座文景之际的汉墓,出土有“洮阳长印”和“逃阳令印”,洮、桃、逃三字相通。《汉书·百官公卿表》曰:“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由此二枚印章知,在墓主人任职期间,洮阳已由一般不到万户的小县(洮阳长)升为万户以上的大县(洮阳令),这当是文景之际长沙国户口迅速增长的一个缩影。
另从吴国户口看,借鉴葛剑雄先生的推算,景帝三年吴国全部人口已达一百二十万[16]。时刘濞王三郡五十一城,则对于地广人稀的吴国来说,平均每县已达到了四五千户,二万多人,人口已不算少。吴楚之乱时下邳人周丘为报答刘濞,要求得节征兵,“周丘得节,夜驰入下邳,”一夜得三万人[1](《荆弟燕吴传》),下邳此三万人当多是壮年男子,且匆忙之中征集肯定不彻底,故以三分之一计,则时下邳人口已达9万余人,一万八千户,已属万户以上人口密集的大县。下邳在秦代尚不出名,张良博浪沙阻击秦始皇失败后,亡匿下邳,作为朝廷缉拿的要犯尚能在下邳从容闲游,为任侠,可见下邳在秦不过为一偏僻的不为人注意的小县而已,说明汉初楚国人口的增长也是相当快的。另齐国的临淄已发展成十万户五十万人的大市,可谓“人众殷富,巨于长安”[1](《齐悼惠王世家》)。
另外,政区的沿革变化首先是人口盈缩的结果,汉初至武帝时陆续在封国所属的东部沿海一带增设了盐渎(今盐城)、淮浦(今涟水)、射阳(今宝应县射阳湖镇)、海陵(今泰州)、高邮、江都等县,新县的辟置当是人口繁衍生息的结果,表明人们开始从人口集中的中原地带向东部地区迁移定居[17]。以上信息均反映出汉初封国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
5.养殖业的新发展
养殖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汉初封国疆域而言,黄河中下游的梁、楚、淮南及赵国的大部分,长江中下游及江淮之间的长沙、淮南、吴等国气候温润,土地肥沃,适于农作物的生长,这里的封国人民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一般农家极少饲养马、牛等大牲畜,但作为一种家庭副业,则多普遍饲养少量的鸡、猪、狗等牲畜,对种植业的收入略作补充,“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18](《散不足》)。同时也为有效积肥壮田提供了条件。在徐州奎山一座早期汉墓中出土有小狗、鸡、鱼等的骨骼[7]。长沙国墓葬中则出土有鸡、鸭等家禽模型和猪、羊、狗、兔等家畜模型,《汉书》还记载了长沙国曾向南越国输出马、牛、羊、狗、兔等牲畜的情况,另在西汉鲁王墓中有鸡、猪、鱼等骨头[19],齐王刘襄随葬器物坑中则有大量狗骨[20],这都说明属于农业区的封国其家庭饲养业十分发达。《汉书·公孙弘传》记载淄川薛人(齐国人)公孙弘年轻时就牧豕海上。封国人民对于养猪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齐民要术》卷六引用了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编的《淮南万毕术》一书,该书讲到了:“麻盐肥豚豕”之法,其作法是“取麻子三升,捣千余杵,煮为羹,以盐一升著中,和以糠三斛,饲豕即肥也。”说明淮南国人民确已懂得在饲料中加麻子粉和食盐可以催肥的养猪技术。另江淮以南水乡之地的渔业养殖亦相当发达,利用陂池养鱼较为普遍,专门从事捕鱼的渔民较多,故吴王濞时代就有“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之说[1](《五行志(中之上)》)。
封国燕、代则属于半农半牧的经济区,其地势平坦,水利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和潜力,同时又拥有大片的草场牧地,未开发的荒地极多,成为畜牧养殖的良好地区,其利用天然的畜牧资源显然比农业区单纯依赖谷物饲料喂养有利得多。《史记·货殖列传》所记的“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的素封地主中,必有不少属于汉初的燕代人,其畜牧业的经营规模已颇为可观,“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样的经营规模并不完全是为自家食用,更多的则是把多余的畜产品作为商品去出卖,随着商品经济的扩大,封国庶民百姓对副食的享用也会较前代为多。
(二)手工业
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民得冶铸,汉初王国的工商业在国家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大大发展,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喜人景象。
1.冶铁业
如前所述,汉初王国铁矿资源丰富,其冶铁业有官营和私营之分。北京大学历史系所藏的封泥中就有“齐铁官印”、“齐铁官长”、“齐铁官丞”、“临淄铁丞”四枚[21]。又据《续封泥考略》有“临淄采铁”封泥和“铁官”半通印封泥。又《临淄封泥文字目录》有“采铁”封泥四枚皆同文。这当是汉初齐设有铁官、铁器官卖的实证。而且武帝官营盐铁后,王国的反抗斗争也反证汉初王国对冶铁有官营权,如“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1](《张汤传》),赵王多次上书反对冶铁由汉王朝专营。“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22]可见,汉初王国即设有铁官,此铁官管理权在王国,盐铁专卖后,各郡国铁官统由大司农设铁市长丞管理其事,武帝所设四十九处铁官,必由不少是原来王国所设。
除官营之外,王国私营铁业也很兴盛。“往昔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18](《复古》)《盐铁论·禁耕篇》中,大夫有言:“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此“朐邴”当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讲的鲁国的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5](《货殖列传》)而以山东莱芜出土的西汉初年的农具铁范铸有的“山”、“李”、“氾”氏铭文来看,当为不同的私营冶铁手工业作坊主的姓氏。另有所铸“口”字则可能是私营冶铁手工业作坊的标记[3]。
汉初王国的冶铁规模相当大,从考古发掘看,虽然如中期及以后的大型冶铁遗址未得发现,但仅从齐王刘襄墓器物坑所藏铁器之多就可想见[40]。而从西汉初期墓葬中均有铁器出土这一点则可推知当时冶铁经营业又是十分普遍的。
再从冶铁技术来看,汉初王国已能铸造出低硅灰口铁,1972年在莱芜出土的农具铁范为此提供了佐证。铁范的金相检查及化学分析表明:石墨呈片状,含硅量为0.16%,这种低硅灰口铁的生产被认为是铸造史上的一项奇迹[23]。徐州子房山一座西汉早期墓中曾出土1件锛[24],它是利用铸铁脱碳成钢技术制作而成的。这种工艺是在铸铁返火过程中,以碳的氧化为主,不析出石墨而形成的钢铁复合件。西汉中期以后,这种工艺才更为普遍地流行,说明汉初楚国冶铁技术已十分精湛。另从文献记载看,汉初的楚国极可能已掌握了生铁炒钢技术,《拾遗记·前汉上》记有这样一件事:秦亡汉兴之际,寓居在丰沛山中的一个冶工曾铸成一把铁钢之剑赠给刘邦之父,后藏于汉“宝库”中。一个穷冶工就能会炒铁成钢,足可想见楚国整体的冶铸水平之高。这种工艺在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出土物中才有更多的发现,说明汉初掌握这种工艺的冶工实在不多。
2.铸币业
汉初,听民自铸钱,为王国、私人铸币提供了合法权力。因此,汉初吴、齐、赵等国纷纷进行铸币活动。《盐铁论·错币篇》载:“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滑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齐国在临淄、安平、阻上、淳于、姑幕、高密、临朐等地均设有铸币作坊,出土有文帝四铢钱。在代郡的高柳出土有“高柳四铢”当是代国铸钱的佐证。另外,楚国的东海郡有“兰陵四铢”、“东安四铢”,沛郡有“下蔡四铢”,燕国涿郡有“高阴四铢”[25]。又据《齐鲁封泥集存》,齐鲁有“钟官火丞”封泥,“技巧钱丞”封泥。齐国还设有“齐钟官长”管理王国铸钱[26]。
从考古发掘看,从1976-1987年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内外先后四次出土汉代半两钱范,共14件[27]。钱文大小一致,文字较为工整。齐国莒县出土榆荚钱范四块,是西汉前期大量流通榆荚钱的明证[28]。江苏六合出土吴王刘濞一个铸钱遗址,面积约210平方米,出土有铸钱的铜块和大批四铢半两。吴国采铜之地,在六合的有铜城,在扬州的有大小两铜山,在江宁的有冶山等处[29]。吴钱数量很大,有“钱布天下”之说。楚国铸的铜钱一定也不少,仅铜山北洞山楚墓出土的铜钱就有七万余枚[30],更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长沙5号墓出土有铁半两钱33枚,铜半两钱2枚。1956年衡阳西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铁半两钱。可见长沙国还有了铸造铁钱的作坊,而当时西汉都城所在地陕西尚未发现有铁钱出土[31]。
由于王国所铸之钱并非普通商品,而是财富的象征,是随时可用的绝对财富形态,铸出了多少钱就获得多少财富。故铸钱“为利甚厚”,而且私钱的质量并不比官钱差,据《汉书·食货志》注引《西京杂记》云:“时吴王亦有铜山,铸钱微量,文字肉好,皆与汉钱不异。”故能畅通无阻,布流天下,王国财富与日俱增。
3.制盐业
在汉代工业中,制盐与冶铁、铸钱并称为三大工业,这是因为盐是五味之首,“食肴之将”,在古代社会食盐几乎成了与粮食同等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不可或缺。正如《管子》所说:“十口之家,十口食盐;百口之家,百口食盐。”
汉初王国多靠近海滨,海盐产量丰富。汉代盐产之富,莫盛于齐。虞夏之时已有青盐之贡,管仲相齐兴鱼盐之利,齐以富强。盐利富足是齐桓公得以称霸的一个重要原因。汉代的齐国依然保持这种优势,司马迁曾说:“齐带山海……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5](《货殖列传》)一齐之地,设盐官十二处之多。齐地出土封泥有“琅玡左盐”,“玡左盐印”(“玡”为琅玡省文)[26]。皆为齐悼惠王或齐襄王时之物。以煮盐起富的大家则有武帝时担任盐铁官的齐之大煮盐——东郭咸阳[1](《食货志》)。齐国刁间使人“逐鱼盐商贾之利”[5](《货殖列传》)。据《汉书·食货志》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置盐官37处,西北所设多于东南,会稽郡只一处,广陵且无之。证以现今盐产地,惟江淮福建。福建时为闽地,不设情有可原,两淮产盐区产量极大,何以无盐官?可见产盐之处必不限于所设盐官的37处。从文献记载看,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5](《吴王濞列传》)。广陵之“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5](《三王世家》)。另会稽郡之“海盐县”、临淮郡之“盐渎县”、代国沃阳县之“盐泽”等地名的出现当与盛产盐有关。此外楚国东海郡之朐县也盛产海盐,《盐铁论·通有篇》说有“朐卤之盐”。燕国滨临渤海,“有鱼盐枣栗之饶”[5](《货殖列传》),盐产也颇丰,燕地有“滑盐县”,在渔阳、辽东、辽西三郡均设盐官;赵、代亦有盐官。
据《汉书·地理志》,武帝所设37处盐官中,属于王国的有19处,已占半数稍强。汉王朝所辖的18处盐官有5处设于武帝开边后的新辟郡(越隽、犍为、益州、朔方、五原等五郡),显然这五处盐官在汉初并未设立;又查《西汉政区地理》,北地郡和上郡在武帝以前辖域都不及秦代,其在两郡下辖的弋居、独乐、龟兹三县设立的盐官在汉初是否属汉统辖是颇有疑问的,故能肯定汉王朝所辖的盐官只有10处,远远低于王国辖区的19处。可见从盐产地来讲,汉初的王国辖区肯定比汉朝辖区多,其盐产量自然较高,与汉朝贸易,取利必然丰厚,这又成为王国经济的一项新的经济增长点。
4.纺织业
在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纺织业实与农业并重,“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32]。
汉初王国纺织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又获发展。齐国素有“冠带衣履天下”的美称,齐地“宜桑,人民多文綵布帛鱼盐”,齐国都城临淄尤其久负盛名,故中央在此地设有三服官,“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齐地”。所谓三服是指“春献冠帻縰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1](《刘禹传》)。据“齐国归有三服之官”[1](《元帝纪》),可知临淄三服官在秦代以前的齐国就已设置。汉初封王拥有封国内的土地和人民,汉王朝的临淄三服官当由齐王国官营,专门生产和供应皇室享用的高级奢侈丝织品,其生产规模较之战国、秦朝已有很大发展,据逄振镐先生推断,战国秦时齐三服官一年输物不过百匹,百匹不过百万钱,作工不过20人,汉中期以后,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较之前代,工人大约增加了500倍左右,一年耗费约增加了数百倍,由此可见,齐国官营纺织业的规模比过去扩大了数百倍,其速度之快,达到了惊人的地步[33]。
除齐国临淄外,襄邑亦设有三服官。《论衡·程材篇》曰:“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襄邑在陈留郡,原属淮阳国,后属梁国[14],可见梁国的纺织业亦相当发达,故《盐铁论·本议篇》有“齐陶之缣”的说法。
汉代丝织品的主要产地是齐、蜀、襄邑,汉初王国辖区就有两个,应当说在丝织业方面,汉初王国颇盛于中央所属郡县。
从纺织品种类和技术上看,王国织物实代表了汉初纺织业的先进水平。汉代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丝织品,几乎包括了整个汉代丝织品的品种,有绢、罗纱、锦、绣、绮等,其中所出各种锦袍,色彩鲜艳,花纹精美,有一件素纱蝉衣质轻而薄,突出反映了汉初缫纺蚕丝技术之高超。此外长沙国的织锦技术,彩绘印花技术和麻纤维的纺织技术都十分高超[34]。
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锦、绮、菱、纹罗等提花织物看,提花束的装置——镊,在这一时期不但已广泛使用,而且机织提花技术已经具有了高度水平[35]。汉代提花机究竟始于何时,史界并无定论,范老认为是东汉明帝时方能制成织花机[36],郭老认为,西汉中期“已经使用提花机”了[37]。但从长沙马王堆机织提花技术水平如此之高看,难以排除汉初出现的可能性。对此,我们还可从文献资料找出一佐证,《西京杂记》卷一载:“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巨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谓光妻)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一般认为巨鹿陈宝光家所用的一百二十镊的织机实际已是一种提花机,所织的蒲桃锦、散花绫已能大批传到汉朝大将军霍光妻手中,并被召入传其法,显然技术十分高超。考陈宝光是西汉中期昭宣时人,据此似乎可以说提花机的始出时间为西汉中期,但任何一种新发明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经一个较长时期的改进和完善过程,再加上古代封建经济的闭塞性、孤立性和保守性,这一过程将更为漫长。故陈宝光家使用的一百二十镊的提花机一定有一个较长时期的不断改进和完善过程。因此可以说,西汉中期以前一定有了比这一百二十镊简单的提花机了。而巨鹿在汉初属赵国,陈宝光家可能是赵国的纺织世家。作为私营小业主已使用了提花机,那么主作天子之服的齐、梁二国的官营纺织业是没有理由晚于赵国之巨鹿私家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汉初王国的纺织业水平代表了西汉前期的先进水平,极有可能高于中央所辖郡县,至少不会落后于中央区。
除以上所介绍的四种手工业王国稍盛于中央郡县外,在漆器制造、陶器制作、造船、玉石雕刻等行业上,王国与中央郡县并驾齐驱,都获得了全面发展,实不分高下。篇幅所限,此不赘述。
(三)商业
汉初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商业获得很大发展,出现了许多富商大贾,仅《史记·货殖列传》中所举著名者就有赵人蜀卓氏,山东迁虏程郑、梁人宛孔氏、鲁人曹邴氏、齐人刁间、周人师史、宣曲任氏、桥姚无盐氏、关中诸田、粟氏、杜氏等十多人(家族)。中小商人之多更不待言,此中周流天下的王国籍商人必占相当部分。
汉初王国的贩运性商业比较发达,从作为商业贩运对象的各种农产品、手工业制品、天然矿产品、林牧副渔等采集猎获品来看,王国产品是颇占优势的,就司马迁所指来看:“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往往山出棋置。”[5](《货殖列传》)山西是汉人泛言的关中,意谓函谷关之中,称之为山西,是以太行山为界的一种笼统说法。傅筑夫先生认为,战国秦汉时关中经济区已向西北和西南扩展,“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皆宜属焉”[38]。大抵是汉初中央所辖区域,此地实为一个重要的农业区,可供贩运的产品总体上讲并不如王国辖区的山东、龙门碣石以北的大部和江南为多,故在贩运业上王国收入要颇丰于汉朝郡县。
汉初王国的商业性都会蓬勃兴起。细究《史记·货殖列传》,商业性的都会中央所辖有:长安、洛阳、杨、平阳、温、轵、宛、江陵、番禺;王国所辖有:陶、睢阳、邯郸、燕、临淄、陈、寿春、合肥、吴。中央所辖数量与王国所辖相等,但从其发达程度上讲,被司马迁列为亦一都会的九个之中,中央只有三个:宛、番禺、江陵(江陵是故郢都,说明自古就是都会)。王国辖区则多达六个:邯郸、燕、临淄、陶、睢阳、寿春,占67%。所谓都会是指郡国的政治中心,“亦一都会”意为“也是郡国的政治中心”,其深意是说它的主要社会作用,不在于政治地位,而在于它作为商业区的经济地位,即“亦一都会”的社会价值,经济是第一位的,政治是第二位的。王国六大都会中,都是战国时即已发展起来的天下名都。以齐国邯郸为例,邯郸早在战国时就已成为工商业集中的大都会,“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18](《通有》),商业贸易十分发达。到西汉时,其盛自然有增而无减。到汉武帝时已是“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5](《齐悼惠王世家》)。无疑作为“亦一都会”的城市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规模和作用要比其它新兴的一般商业城市大得多,故商业都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王国会稍大一些。
二
秦末农民战争的洗礼和楚汉拉锯式争战对代之而起的汉王朝经济的破坏十分严重,以致“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食货志》),可谓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正是在这种极为薄弱的经济基础之上,汉初封国仅用了短短50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如上所述的工农业生产的进步,不能不说是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而这种奇迹的出现则是内因与外因,主观和客观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
首先从外部条件看,汉初王国所处地理环境的优越为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奠定了经济开发的良好基础。
汉兴,高祖“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无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5](《齐悼惠王世家》)。高祖所封同姓九国,异姓长沙一国,“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渡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榖、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5](《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此后直至汉景帝大规模削藩之前,除内部调整和变迁外,封国的整体封域并无大的变化。[14]可见,西汉置王的主要地区在东部沿海一带,多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贸易旺盛之地。齐、鲁、梁、楚等国所处之黄淮冲积平原,是中国古代人民开发最早的农业区之一,其中,“齐带山河,膏壤千里,宜桑麻”[5](《货殖列传》);“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1](《高帝纪》);“邹、鲁滨洙泗……颇有桑麻之业”,“(梁、楚)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5](《货殖列传》)。又梁“为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5](《梁孝王世家》)。其田多属中等或上等[1](《地理志》)。南部地区的吴、长沙、淮南等国,虽“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溽”[5](《货殖列传》),农业生产水平自古就十分低下,但却具有极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草木繁茂,是适合发展农业的良好地区。而且物产又十分丰盈,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5](《货殖列传》),荆扬有“皮革骨象”[18](《本议》)等。这些都是时人的喜好之物,故都可成为商品的丰富的来源。燕、代、赵之北部地属半农半牧的经济区,农业还属粗放,较之中原落后,但畜牧业比较发达,盛产“马、牛、羊、旃裘、筋角”[5](《货殖列传》)等畜产品,由于接近开发较早的三河地带,故其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
封国所处之地又多是河网陂塘密布、灌溉较为便利的地区。被誉为四渎的河、济、淮、江水系均流经封国区。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黄河下游全面筑堤,河道改徙有所控制[39],汉初封国发展正值黄河安流的大好时光。时淮河水系相对稳定,干流独自入海,支流相当密集。修筑于战国中期梁惠王时的鸿沟系统上引黄河,下通淮水,从上游把河淮之间的济、泗、汴、睢、沂、沭、汝、颍诸水联系起来,“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5](《河渠书》)。大大改变了黄淮平原上的水系面貌,扩大了诸水流域面积,使这些河流不仅可以通航,“有余则用溉,百姓飨其利。至于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沟渠甚多,然莫足数也”[1](《沟洫志》)。汉初去战国未远,此等水系仍在发挥作用,足见齐鲁梁楚等国用于灌溉的水利条件十分优越。淮河下游南岸的中渎水,古称邗沟,系利用自然水系与湖沼穿凿而成的人工运道,沟通了江淮两大水系,有利于改造江淮下游地区的自然环境。江淮流域湖沼密布,如吴国之具区泽、长沙之云梦等薮泽对调节河流流量、灌溉农田起着良好作用。淮南国境内则拥有许多人工陂塘,最著名的当数春秋时楚相孙叔敖所造的芍陂,它合理利用了淮河南岸的有利地形,以北部天然湖沼为水源围堤蓄水,形成了一个大型的陂塘水利灌区,集蓄、灌、排于一体,“陂径百里,溉田万顷”[6](《王景传》)。又据《越绝书·吴地传》记载,秦始皇时会稽造起马塘陂,以蓄水溉田,又“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凿通河道与钱塘江相通,两岸可种树、溉田,促进生产发展。西汉初期虽未见修建大型水利工程,但以上河网陂塘仍在发挥作用。
交通是工业发展、商业腾飞的保证。封国所处之地交通便利,以燕代地区为例,秦始皇所修弛道中的一条即是沿太行山东麓北上,经邯郸、中山而至于蓟,由于紧靠太行山脉,又处于诸水上游,地势高,不易受到洪水威胁,成为商业发展的重要通道。而封国交通的优势地位更多的是表现在水利交通方面。如邯郸拥有漳水、滏水、沁水等舟楫之便,使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成为漳、河之间的一大都会。中原地区的鸿沟水系北通河、济,南临淮水,并通过巢肥运河、邗沟、堰渎、胥浦、古江南河和百尺渎,向南直达长江、太湖、东海及钱塘江;沿济水东下,经淄济运河可通齐都临淄;由济水北上通过濮水入卫,并可由济入河,由河入洛,“此渠皆可行舟……百姓飨其利”[1](《沟洫志》)。流经楚、吴、淮南等封国的淮河经鸿沟等运河和河道的开凿,交通更为发达。横贯齐梁境内的济水早在春秋时代就已成为沟通东西的重要河道,齐国又利用临淄城下的淄水与济水临近的有利条件,在淄济之间开了一条运河,这样齐国的船只就由淄人济,直接通往中原各地,使临淄成为东方的一大都会。由《越绝书·吴地传》所记秦始皇“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之事,可知吴县(苏州)以南至钱塘江的水道秦时已可由杭州入江,北起京口,南至余杭的江南运河已基本形成。
汉初王国之封域又多以历史、地理诸因素自然形成的地方疆域为界,每一王国可成为各具特点的经济区域,这又为王国政府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经济提供了方便。
其次从内部因素来看,王国政府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为其经济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提供了动力支持。
汉初封藩建国与西周的封国制度有根本性区别,西汉的封国必须如同郡县一样受中央统一的管辖,其自主权力要受种种限制,但这些限制主要是针对政治军事而言(如不能自置傅、相,无调兵权,不得窃用皇帝专用仪制,必须定期朝觐、上计,按规定纳献费和酬金等),其在经济上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在封国内自行征收赋税、征调徭役,并有权直接经营煮盐、冶铁和铸钱,推行发展王国经济的政策和措施。经济利益的推动,必然大大提高了诸侯王发展本国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鉴于天下初定,百姓贫困,经济凋敝极需休养生息,故王国“各务自拊循其民”[5](《吴王濞列传》),“从民所欲,而不扰乱”[1](《刑法志》),诸侯王们大都能做到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这与中央倡导的无为而治的精神是一致的。所谓“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聘,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5](《淮南衡山列传》),楚元王好读诗书,梁孝王喜欢文学,广交四方文士,河间王善藏诗书,实际都是在向世人示以无为而治的姿态。中央委派的王国相在辅助王国实行无为政策方面更具典型意义,如曹参为齐相,“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后又请来“善治黄老言”的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主张,被曹参引为治国方略,“相齐九年,齐国安集”[5](《曹相国世家》)。另外高帝时的赵相周昌、先相齐后相代的傅宽,文帝时的燕相栾布、先相齐后相吴的袁盎,景帝时的鲁相田叔、淮南相张释之等人,都朴质无华并敢于直言,这对于督促王国实行无为而治起到了关键作用。
诸侯王国能在与民休息的大环境下,切实关心民众疾苦,减轻人民赋役负担,吸引劳动人口,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政策较之中央直辖的郡县更为优厚。如吴王刘濞为人“重厚”,“惠仁而好德”[5](《孝文本纪》),“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它郡国吏俗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5](《吴王濞列传》)。淮南厉王长“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其财物爵禄田宅”,“赦免罪人”,“厚养亡命”[5](《淮南衡山列传》)。胶西王端“令吏毋得收租赋”[5](《五宗世家》)。概括而言,诸侯王采取的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三点:一是减轻封国人民的赋税负担。汉初诸侯王在封国内征收的赋税主要有两项,即山川园池市肆之入和田租口赋,前者作为诸侯王的“私奉养”,由王国“少府”管理,后者是按西汉政府统一的赋税标准征收,此项收入一部分上交中央,称为“献费”,另一部分王国“公用”,作为王国官吏俸禄及其它财政开支。诸侯王国为发展经济,常常从王室收入中抽出一部分交纳“献费”,以减免百姓赋税,如吴王“擅山海之利”,大力发展煮盐、铸钱业,百姓“以故无赋”,如淳注曰:“铸钱煮海,收其利以足国用,故无赋于民也。”[1](《荆燕吴传》)“在吴王濞时代的吴国,可能是各种赋都不收,他得自铸钱和煮盐的收入是很丰足的。”[40]胶西等国也取消了压在农民头上的沉重的赋税负担。而同一时期中央所辖郡县除偶有重大灾异或特赦外,都必须定期交纳赋税。两厢比较,王国区的人民,其赋税负担明显低于中央直辖郡县,为王国人民营造了一个发展经济的良好环境。二是招纳“亡命”,争夺劳动人手,赦免罪人,增加劳动生力军。“亡命”是指来自中央直辖郡县的脱籍逃亡或犯罪之人,他们多系贫民,诸侯王以优惠的政策让他们在封国安顿下来从事铸钱、煮盐或从事农业,且为其治家室,赐予田宅财物等生产生活资料,并对亡命之人予以保护,不准中央郡县前来抓捕。从生产力角度分析,由于封建时代劳动工具的变革十分缓慢,生产力的另一要素——人的作用对于发展生产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从事生产和自我生产的人口的总和即人口因素是封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不强调人口质量且存在大量荒地的西汉初年,劳动人口数量的增多必定会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三是减轻封国人民的徭役负担。汉制,徭役有更卒、正卒、戍卒三种。王国所辖吏民一般在封国内从事各项徭役和戍守,同远离京师的中央直辖郡县相比,徭役相对要轻一些。贾谊就曾明言:“今淮南地远者或致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1](《贾谊传》)徭役负担的沉重,使郡县人民纷纷逃往王国。而且诸侯王还很注意减轻国内人民的徭役,最为典型的要数吴王濞“卒践更,辄与平贾”,对此服虔注曰:“以当为更卒,出钱三百,谓之过更。自行为卒,谓之践更。吴王欲得民心,为卒者雇其庸,随时月与平贾也。”[1](《荆燕吴传》)谓由王国政府定期出钱雇人代其国民服役,吴王濞给受雇者费用时,按“平贾”付钱,以示公平。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在汉初各地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的情况下,诸侯王能根据王国国情因地制宜地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充分开发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宜农则农,宜商则商,或半农半牧,或以工商立国。以封王为首的王国统治集团与国民一起群策群力,为本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而突出的贡献。仅以吴国为例,吴王刘濞初封,面对封国东临滨海的特殊地域,因地制宜,“东煮海水以为盐”,带动国民搞起了煮盐工业,又鉴于国内铜矿资源丰富,又“内注消铜以为钱”[5](《淮南衡山列传》),领导人民采铜铸钱,并注意吸收劳动人口补充国内人力资源的不足。同时为有效地运输所煮海盐,还专门修筑了一条盐道,据《太平御览》记载:“吴王濞开莱萸沟,通运至海陵仓。”[41]《淮安府志》卷六又称:“汉吴王濞开邗沟,自扬州莱萸湾通海陵仓及如皋蟠溪。”说明这条运河又向东延至如皋,这样就可把全国范围内生产的海盐先蓄至海陵仓,经由邗沟沿淮水运销至全国,达到产运销一体化。吴王刘濞经过三四十年的苦心经营,搞活了地方经济,很快使吴国成为东方的经济强国,吴国的富强与关中汉皇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七国之乱爆发前,吴国郎中枚乘所说:“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于中国。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文帝后期郡国数),方输借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吴王府藏)。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吴国之仓)。修治上林,杂以离宫,积聚完好,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吴苑)。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吴以海水潮汐为池)。深壁高垒,副以关城,不如江淮之险。”[1](《枚乘传》)此话出自文人之口,难免浮夸之嫌,但恐怕也是以一定的事实为依据的,可见其经济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
西汉前期,王国所辖疆域占全国的1/3以上,人口占全国的1/2[42],这就决定了封国的发展对全国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汉初经济的残破凋敝现象十分严重,封国利用中央下放的政治、经济权力分担了艰难的重建任务,减轻了中央的压力,仅经过短短四五十年的发展,到文景时期就出现了带有普遍意义而非局部地区、局部现象的繁荣局面,为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为我国封建时代的空前强盛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包含正反两个方面,封国经济实力的强大也增强了其对中央的离心作用,“大抵强者先反”[1](《贾谊传》),景帝三年终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叛乱固然不应肯定,但却不能因此而否定吴楚等国前此几十年对推动本国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更不能把刘濞在吴国几十年的苦心经营统统说成是为叛乱作准备。应该看到,正是由于吴楚等国和其它各郡国的共同的经济发展才促成了西汉前期经济的全面繁荣。正是汉初封国经济的发展,使西汉中央政权具备了剿平一切叛乱的实力,貌似强大的吴楚七国之乱,仅用三月就被平定,足以证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安定了社会秩序,加强了中央集权,纵有叛乱分裂也不堪一击,远远不能构成威胁中央的强大势力。故我们不能因为封国的离心叛乱而否定其对汉初经济发展的贡献,更不能因这种分裂因素而否定封国体制在汉初存在的必要性,抹杀其捍卫中央皇室、发展地方经济的有效性。
收稿日期:2001-10-12
标签:汉朝论文; 吴国论文; 汉代建筑论文; 西汉论文; 货殖列传论文; 齐国论文; 食货志论文; 长沙国论文; 王国论文; 临淄论文; 长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