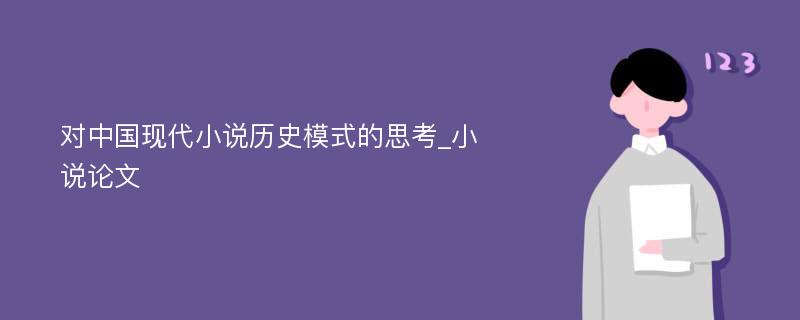
中国现代小说史格局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格局论文,现代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另一条系列
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有明显的两条系列,一条是人们所熟悉的新小说系列,一条是客观存在的不受重视的通俗小说系列。现代通俗小说是从晚清小说革命开始的。晚清“小说界革命”是凭借政治改革的旋风掀动起来的,改革者看中的是小说的宣传的功能和启蒙的作用。他们对现实社会特别关心,社会小说也就成了此时小说的创作主流。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全面兴起是在民国初年。1912年徐枕亚的《玉梨魂》和吴双热的《孽冤镜》在《民权报》上隔日连载,轰动一时,引起了天下有情人“同声一悲”。在它们的影响下,一百多部长篇言情小说一下子跃上了文坛,这就是民国初年的言情小说热。对这些言情小说新文学作家是不屑一顾的,他们用“一对鸳鸯,一双蝴蝶”一言而蔽之。写情理之争的文艺作品在我国明清以来就不乏佳作,为什么此时言情小说能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呢?这的确是和时代有很大关系。当时的言情小说家蒋著超在他的小说《白骨散》的引言中说:“比来言情之作,汗牛充栋……无非婚姻不自由而发挥文章而已。”确实这样,借着言情小说,民国初年的作家们痛感中国婚姻制度的不自由,寻找出路,并要求改革。这些小说的结尾都是悲剧结束,而且悲得很彻底,要么主人公全死(如《玉梨魂》);要么主人公一死一疯(如《孽冤镜》);要么主人公一死一出家(如《霣玉冤》)。夏志清曾专门撰文论述过徐枕亚的《玉梨魂》,他说:“这本书的结尾如日记之引用,叙述者之爱莫能助,苍凉景象之描写等等,都预告着鲁迅小说的来临”,虽然徐枕亚“对中国的旧文学和旧道德忠心耿耿,他却引发了读者对中国腐败面的极大恐惧感,其撼人程度,超越了日后其他作家抱定反封建宗旨而写的许多作品。”(注:夏志清:《〈玉梨魂〉新论》,载《明报月刊》1985年第9期。)这一评价是可以看作为对当时整个言情小说而发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青年中最能产生共鸣的莫过于喊出“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口号了,之所以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其社会心理的准备从民国初年就开始了。此时也是中国通俗小说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文坛上出现这么多的长篇小说是和文学期刊的创刊热分不开的,据阿英在《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统计,1902年到1909年晚清文学期刊共20种。据我不完全统计,1910年到1921年的十年间文学期刊共创刊42种(不包括《新青年》等综合性期刊)。文学期刊的创刊热说明了中国通俗小说由新闻型向文学型的价值回归,说明了文人脱去了“报人”的帽子。在他们的手中,中国传统小说的文本开始出现了重要的变化,第一人称的写作已相当普遍,第三人称和纯客观的叙事角度已经出现,人物的叙事视角正在取代传统的全知视角;情节中心虽然还占绝大多数,但写人物命运的性格中心和写社会问题的背景中心已占相当比例:场面描写和心理刻划是小说创作的必备手段;传统的连贯叙述已被打破,倒装叙述和交错叙述已成了时髦文体。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白话创作已成为了很多作家的自觉意识,1917年1 月在上海创刊的《小说画报》明确提出:“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成了我国第一份白话文学杂志(注:1917年1月创刊的《小说画报》。), 和“五四”新文学的优秀小说相比民初的小说有很大的差距,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为“五四”新文学作家对于引进新的人文精神和运用现代文学的创作技巧具有明确的意识,而民国初年的小说家的那一点现代意识和现代型的创作技巧来自于现有的外国小说的启发和摹仿。但有一点是相当明确的,中国小说已开始走向现代化之途。
新小说登上文坛之后,就对通俗小说展开了批判,通俗小说受到了挫折。然而不久通俗小说就再一次勃兴,再次勃兴的通俗小说在价值取向和表现手法上都不同于民初的通俗小说。那种单纯的言情小说几乎不见了,文学的社会批判性明显加强;情节中心依然不变,人物命运已逐步成为作品的主要线索;“记账式描写”固然还有,人物刻划已成了小说主要的表现手段。现代通俗小说作家正在有意无意地将新文学作家对他们批判中的有益成份融会于他们的作品中。30年代,现代通俗小说进入繁荣期,社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历史小说、滑稽小说等各类体材的小说层出不穷,它们吸引了大量的读者。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通俗小说作家创作了大量的“国难小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此之后,现代通俗文学的社会责任感明显加强。
40年代的中国通俗小说作家队伍有三个方面组成,一是以一些大学生为主体的创作群,如“复旦大学创作群”,“东吴大学创作群”等;二是前一段时间一直活跃于文坛的老作家,如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平襟亚、孙了红等人;三是新近出现的一些青年作家,如张爱玲、苏青、潘予且等人。这三组创作群体的作品的价值取向有着明显的差别,创作风格也明显不同。但真正成为40年代通俗文学的创作主体的是后两类作家群。包天笑、周瘦鹃的短篇小说、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平襟亚的故事新编、孙了红的侦探小说都意在激发民族的抗敌情绪,批判社会的腐败现象,劝戒民众的做人规范。张爱玲等人的作品政治性虽不强,但对人性的揭示和批判,特别是女性心理的刻划,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文化定位
中国小说出现两条系列的状况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新文学登上文坛之后,把既有的小说称之为旧小说或“鸳鸯蝴蝶派”小说,而称自己的小说为新小说,并对前者展开了严厉的批判。
“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很强的现代意义,它所依据的是欧美、日本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依据的人本精神,是那些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留学生们用新的思维方法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思。朱自清曾经说过:“在那个阶段上,我们接受了外国的标准,而向现代化进行着。”(注: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载《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集。)“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封建政体覆亡后民主精神的补课,是为了现行的国体更为合理和牢固而在思想文化层面上提出的要求。与此相适应,“五四”新文学作家提出“人的文学”也正是民主精神在文学上的表现。应该说,此时新文学作家对通俗小说的批判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对中国文学实质意义上的改革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问题是他们对通俗小说采取的一概否定的态度,缺乏对其合理性的认识,缺乏对其人文精神的科学的分析,而且这种态度贯穿于整个20、30年代,而不论通俗小说是否发生了变化。新文学的这种态度反而束缚了自我发展。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继续,它所表现的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是有不少封建糟粕,但更多的是已作为优良的道德标准融化于中国人的是非判断和行为规范之中了。1911年以后包天笑曾说过一句话很具代表性,他说:“所持宗旨,是提倡新政体,保守旧道德。”(注: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7月版。)新政体又怎么能和旧道德糅合在一起呢? 当时的通俗小说作家就是这样的认识。到了20、30年代通俗小说的时代性明显加强,但传统的人文精神还是评判是非的标准和表现的思想主题。他们总是从做人的角度批判那些官僚、军阀、政客、商人的行为举止,这些人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又怎么能管理好国家呢?他们表现的是除暴安良、因果报应、慈悲为怀、尊老爱幼、赤胆心肠……这些文化思想维系着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中国的现代化之途属于“冲击—反应”的形态,是在一次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和一次次民族屈辱之中被迫走向现代化的,物质力量的落后是公认的,这是客观事实所证明的,传统的人文精神虽然受到了一次次冲击,但始终就没有承认失败过,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的精神力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一个重要的潜意识,那就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自有比外来文化高明之处,这种潜意识贯穿整个20世纪。正因为如此,通俗小说所表现的文化观念虽然没有新小说那么具有“世界性”,却对中国老百姓有更大的影响力。
新文学作家对通俗小说的文化价值认识不够,而且轻易地将通俗小说所依赖的读者层也否定掉了。他们给通俗小说定位为:封建的小市民文艺。将通俗小说说成小市民文艺并不错,广大市民阶层是通俗小说的最主要的读者层,通俗小说主要表现的也是市民阶层的思想和愿望,问题是如何评价这些小市民。在中国人口中农民占有绝大多数,市民占有的比例并不大,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真正能识字读文者也只是市民阶层,他们的人数虽少,却是文学作品的主要读者群。城市的范围当然不能和广大农村相比,但它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代表着社会风气的迁徙和时代心理的变化,是整个社会的动脉。如此重要的一环却被新文学推出了创作的大门。相反,通俗小说作家却在这个领域之中如鱼得水,他们主要以都市社会为创作背景,写出了城市中的各个重大事件:“五四”运动、“五卅”事件、军阀混战,工厂罢工、金融危机、“一·二八”事变等;写出了城市中各种人物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有买办、政客、商人、金融家、军阀,也有工人、店员、学生,甚至白相人、混混儿、妓女等;同时他们全面地表现了城市的人文景观,有交易所、银行、跑马场、游艺场、大饭店,也有工厂、作坊、街道和弄堂。通俗文学作家本身就是小市民,他们把发生在身边的事诉诸于文字,市民读者感到十分亲切,容易产生共鸣,市民读者自然就成为了通俗小说的稳定的读者群,他们使得通俗小说批而不倒。通俗小说正是从市民特色上体现出它的题材价值来,不管它的水平高低,要了解中国都市的发展状况,要了解此时中国市民的心理状态,就不得不读通俗小说。把中国最主要的读者群都否定掉了,只能使新文学自己处于更为尴尬的地步。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新文学对通俗小说一直持批判的态度,而且有着明显的论人不论作品的态度,只要是通俗文学作家的作品,不论其价值如何一概予以否定。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通俗小说作家创作了不少“国难小说”,这些小说的思想意义和艺术表现均不俗,就因为它们来自通俗文学作家的笔下,新文学作家就将这些小说称作为“在国难的事件中打打趣而已”,是“封建余孽作家在小说方面活动的成果”(注:钱杏邨:《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载《现代中国文学论》,1933年6月出版。)。 新文学作家这种以人划线的态度,使得20、30年代的新文学杂志只载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通俗文学杂志只载通俗文学作家的作品,两大作家群泾渭分明。在逼迫之中的通俗小说作家加强了内部的凝聚力,他们聚集在一起向各个通俗文学杂志滚动,支撑着通俗小说的生存与发展。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繁荣与发展,一方面是它所表现的文化思想符合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思想状况;另一方面是新文学的自我束缚,却给了他们巨大的发展空间。新文学作家此时提出文学大众化的口号,并进行了多次讨论,但它们的作品始终没有“大众”起来,相反,通俗文学作家并没有给自己提出什么要求,反而对普通大众的启蒙作出了不少贡献。这些结果都是耐人寻味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格局的思考
新小说和通俗小说作为两条系列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坛上,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对现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小说史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此后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编写不断,但总体思路并没有离开既有的格局。 它们都是以新小说的价值取向和作家作品作为批评对象,略提或不提通俗小说系列,这样的小说史只能是中国新小说史。将通俗小说系列放置于编史的系列之中,现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格局将作出必要的调整。
20世纪以来,中国走向了现代化之途。新小说代表了时代的精神,它们是20世纪的小说主流,其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主流”从来就是和“非主流”相辅相成的。事实上,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对中国现代小说的流变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中国小说的现代化的起点是以清末民初的小说改革为标志的,它和“五四”小说改革构成了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阶段。这是小说现代化的启蒙和建立小说现代化标准的时期,是内部的变革的要求和外部的变革动力相结合的时期。小说的变革毕竟不同于历史的变迁,它不能以某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为转折点,更不是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革。小说的变革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更多的民众认可的社会基础。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发生期曾有这样一个过程,有这样的民众基础,但现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却没有能全面地反映出来,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很多文学现象也难以得到更深入的理解。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白话小说在清末民初时就大量存在,而决非等到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才宣告出现。当然鲁迅小说中的白话与清末民初小说中的“说话”有着重要的区别,但毕竟中国小说的创作语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小说语言的变化,其意义要远远超过语体的本身。语言作为一种文化前结构,可以制约使用者的思维逻辑,文言文和白话文实际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逻辑和思维方法。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作家用“说话”进行小说创作,说明了一种新的思维方法正在形成,白话为正宗在“五四”时期得到确立,并得到社会的基本认同,正说明了开放的形态和创造的思维已成为了时代的主流。再例如“五四”小说以短篇小说为主,几乎没有什么长篇小说,其根本原因不是什么环境的逼迫无暇顾及长篇巨制,而是“五四”小说家们所奉行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他们认为清末民初的作家写不出短篇小说,不符合“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注:钱杏邨:《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载《现代中国文学论》,1933年6月出版。),在当时会写短篇小说, 不仅仅是掌握了一个新体裁,而且是新小说家的一个标志。对“五四”新小说重要意义的认识,只有与清末民初的小说革命结合起来考虑才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小说史的编写需要对文学现象整理和淘洗,但决不是对一些作家作品全部地摒弃而不提;小说史的编写同样需要文学史观,但是将符合本土文化心理而为本民族读者所欢迎的文学现象列入批判对象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将通俗小说系列列入编史的视野之中,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小说如何地在新时期变型变化,看到中国新小说被读者接受的心理过程,看到中国小说形态的基本确立和发展走向。通俗小说入史也使得中国小说史具有了完整性和全面性,使得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有了立体感。中国现代小说不仅仅是农民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还有大量的社会言情、武侠侦探、历史宫闱、滑稽幽默等作品。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表现或个人感情胸臆的抒发,它还表现了广大民众的政治愿望、社会要求、生活企盼和道德标准。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仅仅是启蒙文学的记载,它还有消遣愉悦的成份。
在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进程中新小说是文化的先导,它表现更多的是对人生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中国的生活问题、文化思想以及变革的出路均带有强烈的启蒙意识和使命感,但对中国现实社会生活领域正悄悄发生的变化不感兴趣,对其中的积极意义很少考虑,而后者却正是与广大民众的利益直接发生关系而为广大民众所关心的问题,通俗小说也正是在这里表现出它的价值。这两条小说系列是有区别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条小说系列又互相渗透。在20世纪20、30年代通俗小说明显地向新小说学习,通俗小说作家在注意作品的情节生动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人生命运的起伏,注意到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这在张恨水等人的小说中表现得相当明显。新小说是否有变化呢?我认为也是有的,只不过显得更加隐蔽而已。特别是新小说作家开始热衷于长篇小说创作后,小说中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也就浓厚了起来,对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关心也就密切了起来,小说中自然也就出现了一些“通俗小说的要素”(注:根据既定的通俗小说的批评标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的家庭世俗的描写、老舍的《骆驼祥子》中的市民生活气氛以及茅盾《幻灭》中的革命加恋爱都是通俗小说最常见的表现素材。)。到了40年代这种相互渗透就更明显化了,从大环境上说民族战争要求文学为广大民众服务,要求作家关注大众的意识。40年代初的“民族文艺形式”的讨论是继30年代“大众化运动”后的又一次对文学大众化的思考,与此同时,通俗文学作家也开展了一次颇有声势的“通俗文学运动”,要求加强文学的理念化。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看,新小说和通俗小说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各自的优势已相当明了,互相吸取长处势在必然。纵观此时的小说,无论是新小说还是通俗小说都有重大的变化,它们都趋于大众型。巴金的小说更侧重于表现家庭内部的血缘关系和伦理关系;老舍的小说中的胡同和大鼓艺术表现出更强烈的世俗气氛;茅盾的社会分析小说并未停笔,却也用通俗小说作家常用的日记形式写个人的感情经历;张恨水此时跳出了家庭的“藩篱”,而把国难和家仇一起表现(如《弯弓集》),有时干脆就直接抨击时事政治(如《八十一梦》);包天笑和平襟亚借古讽今,创作技巧十分娴熟,令人忍俊不禁,却意味深长;孙了红的侦探形式不是单纯地追求情节的曲折性,犯罪心理的刻划把读者引向更为深刻的文化空间的思考……用以往的新小说和通俗小说的美学观念分析这些小说,是无法分类排队的。同样,张爱玲、苏青、潘予且等人的小说可以用新小说的角度分析,用通俗小说的角度分析也未尚不可,这不是说他们的小说复杂,而是他们创作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什么是新小说什么是通俗小说。这说明了20世纪初形成的新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各自不同的美学观不符合40年代的小说创作实践。中国40年代出现的新小说和通俗小说合流的现象对中国小说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小说在民族化、现代化之途中的又一次跃进。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分析新时期以来的众多作家(如贾平凹、陈忠实、苏童、池 莉等)以及金庸等人的作品,对这样的表述就会有深刻的理解。同样,我们还可以作出更深入的思考,那就是新小说和通俗小说的既有的划定标准在将来是否会成为历史概念呢?我想也许是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