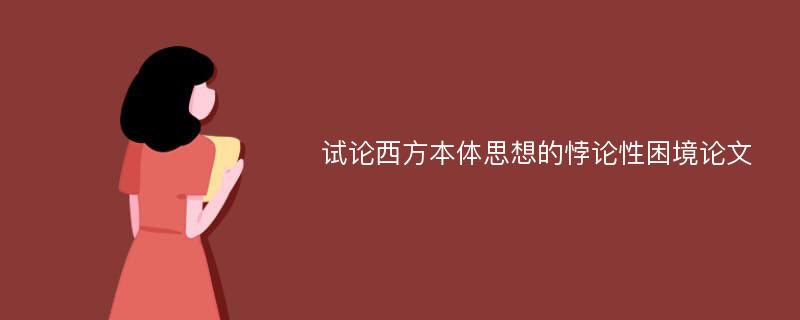
试论西方本体思想的悖论性困境
史忠义
通过分析柏拉图的本体思想及其美诺悖论、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命题主义及其悖论、海德格尔的本体观及其悖论和科学与形而上学的两难处境亦即悖论,可以得出只能通过抛弃作为解决范式的毋容置疑性的理想,超越无根据的所谓“科学”和认识基的垄断地位,抛弃必须把本体置于任何询问之前的西方本体论规范的结论。本体论只是对下述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的承认。这种形而上学仅拥有多重性却强行思考必然统一性,只能是一种天方夜谭。本体是命题主义失败的代名词,而非超越命题主义的钥匙。形而上学只有不再是本体论时才有意义,本体论让科学与形而上学处于一种不即不离的尴尬地位。
[关键词] 美诺悖论;命题主义;毋容置疑性;本体;形而上学
一、西方本体思想的起源与美诺悖论
西方的本体思想酝酿于诡辩派(又称智者派)和苏格拉底,开始于柏拉图。物质变成什么(le devenir)的偶然性,众说纷纭的多样性,充斥着不确定信息的感性世界,反馈着占据了希腊人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性。诡辩派的兴趣是利用思想的开放及其变得难以决断的交替项(les alternatives),以促进最有利的意见,继而毫不尴尬地捍卫相反的论点。而苏格拉底则调转问题性的方向攻击那些以为可以掩盖问题性以利于自己的人士,他们是掌权者、城邦的名人以及他们收买的诡辩派人士,掩盖问题性的目的是为了让思想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在让这些思想接受彻底叩问的考验时,苏格拉底不仅因此而创立了此后人们所谓的哲学举措,而且显示诡辩派和名人们所建议的回答都是肤浅的回答,在对话结束时并没有解决一开始提出的问题。
柏拉图认为,苏格拉底的方法表达了恰当的彻底性,这一点是宝贵的。但与苏格拉底相反,柏拉图拒绝一下子就使任何可能的回答信誉扫地,理由是,在“何谓X?”这个问题里,人们不知道到底要寻找什么。X到底更多的是这个抑或那个?人们无法作出决断,因为这正是大家询问的东西。如何达致肯定的状态呢?永远不可能达到,任何回答都会沾染上问题性,人们以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性,实际上只是把它转移了而已。柏拉图以为能够确定回答苏格拉底问题的条件,并由此建立理性思维的逻各斯。这样思考的东西可以作为苏格拉底问题的答案吗?笔者以为不能,因为苏格拉底问题揭示的东西是,相对于他的问题,人们走不出这个问题的圈子。例如,对逻各斯问题的回答是,唯有排除任何问题性,才能得到这样的逻各斯。柏拉图在回答逻各斯的建立问题时取消了需要建立逻各斯这个问题,似乎逻各斯必然是由自身支撑的,具体体现为肯定必然性①是内在的必然性。于是柏拉图完全进入了循环。
柏拉图的思维逻辑是,当人们像苏格拉底那样询问何谓X时,其实并不知道寻找什么,因而不可能确定是否找到了答案:如果肯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知道什么是X,那为什么还要询问呢?这里其实就是美诺悖论(《美诺篇》),柏拉图使用这个悖论以期说明,需要另一种逻各斯的理论,才能解决苏格拉底的问题,仅仅以问题性为支撑的概念是不行的。柏拉图抛弃的全部东西与苏格拉底的问题性相吻合:交替项的不确定性,多重意见造成的不可决断性,感性世界的混沌等。于是,柏拉图提出了自己的理念论或实质论。他的理念论或实质论是怎样产生的呢?很简单,假设人们询问何谓X时,人们假设X是某种东西,那么,X之所是(本体)就是回答的客体,因而也是问题的对象。这样假设的结果是,“何谓X?”的问题应该解读为“(这个)X是什么?”。询问X与询问X的本体不可同日而语,因而就出现了X、Y、Z与X、Y、Z之本体一分为二的现象。实质反馈到知性世界,而物体本身属于感性世界。这些理念(或实质)显示,柏拉图期待逻各斯的排他性的必然性,排他性的必然性就成为逻各斯的标准。柏拉图称之为证明的毋容置疑性(apodicticité,apodeixis)。为了避免意见的多重性和感性混沌的不确定性,这样就需要被回答的X确定是它的本体,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需要它的本体排他性地与它相一致,不出现可能的替代项(亦即可选择项)。这样的必然性就是逻各斯的必然性。X的理念就是使X成为X排除其他东西的理念:替代项在这里是以否定的名义和被排除对象的名义提及的。柏拉图其实实施了一次滑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当代哲学家兼修辞学家米歇尔·梅耶称之为本体论滑动[1](P88),这种滑动不是别的,仅仅是一种假设,但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后果,它真正构成了本体论的“出生证”。假设物质的问题乃是物质本体的问题,因为物质进入了本体状态,柏拉图想象询问行为先验性地关涉一种本质,因而本体就是这种本质,实际上,询问何谓X并不因此而意味着X之所是提出了一种本质。另外,柏拉图心中的答案应该先验地是单义的,因为回答的多重性被排斥。
柏拉图认为,辩证法从感性出发,上溯到理念,然后重新降临感性世界解释后者,最后才成为纯粹的理念游戏,如在数学领域那样。这种辩证法既是毋容置疑的,亦即科学的,也扎根于问题之中,即扎根于滋养着对话、表达参与者之主观愚昧状态的各种问题中。
米歇尔·梅耶驳斥了柏拉图的理念说和本质说。他说:“X可以是很多东西,但没有一个固有的本质性的本体。‘X是这个或那个’肯定不证明它拥有一个本体、这个本体像所有本体论思想所支持的那样与众不同和自我命名,更不证明这个本体等于把必然性引为逻各斯之规范的一种本质。但是对柏拉图而言,由于“X是”符合它的理念、它的本质这一事实,它是它的理念,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绝不是,亦即必然不是)。喻示或提出所有这一切只能投入种种先验中,柏拉图在没有真正问题的情况下投入了这些先验之中。”[2](P36)这正是我们所说的,物质的实体与概念是一体的、须臾不可分离的,没有实体哪来的概念呢?柏拉图把理念与实体相分离,让理念主导实体,显然是先验形而上学的。促使柏拉图引入这些先验的动机,乃是对排除苏格拉底疑难的关注。在该疑难中,不管苏格拉底如何施展解数,感性的矛盾性都重新引了进来。这样就出现了柏拉图的观念:回答具化为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让任何问题消失。自此,通过取消叩问的开创性作用,把叩问置于被深埋在记忆中的种种本质所遗忘的本体的揭示之下,感性所显现出的问题行将消失,有益于对理念的肯定。柏拉图的逻各斯正是从消除交替项而诞生的。但是,由于这个逻各斯不再反馈到任何问题,它就不能自视为回答。
海德格尔想通过打碎“一与多”的同一性而解决这个矛盾,即把所是命题化,把这种同一性作为源自形而上学固有的某种遮蔽之混淆而牺牲掉,他宣称要超越形而上学。统一性的本体将是本是(Sein),而多重性将被称作“现是”(“此在”,l’étant,das Seiende)。海德格尔同时提出了接触本体(本是)的问题(这个问题具体被亚里士多德通过“主语是谓语”的谓项方式所保证的命题性对等解决了)。由于这个做法,在海德格尔那里,本体超越了言语。人们不再可能通过“默听”而与本体关联起来。在第一阶段,海德格尔确实采纳了一种更合乎理性的方法,把可能与本体(本是,存在)关联的可能性置于“人类的实在”(Dasein,现是,此在)中。我们从那里重新找到了分析与综合、从我们心中某种先前性出发的认识秩序与拥有另一类型的先前性、即分析所导致的自身先前性出发的物质秩序的古老分离。感觉、感性,一言以蔽之,人文拥有的根基不同于物质秩序自身固有的根基,后者传统上以上帝为绝对根基。在海德格尔那里,这种双重结构像在整个命题主义那里一样。本体真正的第一被隐藏在似乎向我们显现的第一(此在)里。作为现是的本体隐藏起来了,同时又展示出来,但通过一种预先的感性关系,它永远被作为“现是”(此在)。柏拉图已经支持有关知性的这种论点。为什么命题主义不能躲开这种既必要又无法坚持的二元论呢?主语与谓语的差异也构成一种同一性,这可能显得有些矛盾。命题主义在把谓项作为我们心目中先前的场域时,暂时以感觉、老生常谈为优先,以期随后上溯到真正的根基主语本身,后者本质上永远先于界定它的各种性能。于是一种上升的辩证法与一种下降的辩证法结缘,后者恰恰从我们出发的感性中被解放出来,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说,从我们因物质的力量所迫从感性出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连接命题化与本体论同时让两者对立起来的无法克服的张力,这种张力将落脚到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冲突上,应该引起学术界的特别重视。
二、命题主义本体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诞生及其悖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美诺悖论是需要解决的二律背反现象,因为它是绝对根本性的矛盾,因为关涉知识的获得。他在《分析续论》中介绍了自己的科学观,坦言他的观念是要解决任何认识论都会面对的柏拉图提出的这种悖论。本体论以本体为必然,展示为本体的不可避免的解决途径。但亚里士多德认为,从永远假设并具有偶然属性的感性世界出发,建立科学、建立知识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能接受的,两者都不可能是科学知识,因为科学知识以毋容置疑的必然真理为宗旨。可是,柏拉图的辩证法扎根于从永远假设并具有偶然属性的感性世界出发这样一种起点:归根结底只能受制于这种起点。如果从问题出发,怎么可能希望源自问题的东西不是问题呢?从感性出发以期上溯到知性,这等于设置了一个不可超越的断裂带。知识如果并非诞生于毋容置疑的东西,就不可能是毋容置疑的。辩证法或者像对话者的问答一样是偶然的,或者像知识一样是必然的,那么,知识就不再是辩证的,而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是分析属性的。给予自己一个起点,乃是确立一种律则。那么,这种律则将是感性律则,知性本质上与之不同,不可能压缩为感性律则;倘若是确立知性律则时,怎样接触知性律则就应该得到解释,尤其是当我们接受人们首先从感觉和感性认识开始的事实。二律背反现象似乎无法解决,因为它反馈到不可接触的神秘性与人们并没有真正认识的感性世界之偶然性的交替中。柏拉图以为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把辩证法分裂为上升和下降两种运动,它们相当于帕普斯几何学中所谓的分析和综合。柏拉图的辩证法就是这种把分析和综合统一为一种完整的往返行程的双重运动。毋宁说,扎根于分析及其最初的假设结果的综合,同样具有问题性,并且在其结论中保持着循环性。把辩证法分解为分析和综合看似能够解决上述悖论,因为第一的东西既非第一同时又是第一,根据人们考察的是分析范畴抑或综合范畴。但由于分析范畴让我们从一种假设为第一的实在开始,(综合范畴意义上)自身第一的东西只能让我们认为是问题性的,而根基自身乃是逻各斯毋容置疑性的源泉。这里是双重的二律背反现象:分析范畴假设的第一与综合范畴自身第一的悖论,综合范畴自身第一的东西因为显示有问题而不符合逻各斯的毋容置疑性。每次也许都以更普遍的方式重新出现的二律背反现象,就是要弄清究竟本体是第一抑或认识是第一。肯定前一种论点预设了已经对本体的认识,而这种论点则取消此类预设。支持第二种论点不啻反馈到本体,因为认识的对象不是本体又是什么呢?这里也一样,第二种论点也自我摧毁了。
但是,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认识基只能是所有这一切,因为一种毋容置疑性的理想支撑着它,它大概实践了这种认识基,但不负责提供论证。为什么科学不思考。这等于说,知识建立在一种必然性的基础上,它毫不尴尬地证明其必然性,似乎最卓越的言语就是展示性、证明性、真实有效性、排除其对立面的言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样一种言语先验地被知识基投入实践:知识基从自身出发展开,把言语当作其自身科学实在性的一种构成性明证性。科学为了真正是科学,为了拥有某种意义,无法躲开使必然性成为逻各斯之本体的必要性。因此,它需要某种比它更形而上学的东西。形而上学应该负责科学而非本体,本体并非只是必然的。形而上学将被科学一方与本体论一方所分裂。
正是在这个阶段,人们看到了知识界的一场真正的革命:抛弃只知道必然性的理念论,促进一种以整合多元性、偶发性和可以是非A的A为核心的新视野,这种新视野没有使非本体因此而获得“公民权”。但是,本体的东西必然是自我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是他者呢?单一性本体至少先验性地从内在可能性方面是多重的,但并未停止其自身属性,即停止自己的必然性。它不可能在同一关系(不矛盾律)下既是一又是多。亚里士多德解释说,本体从主体身份言是一,从谓语身份言是多。谓语的多重性被归结为几大组,他称之为(本体的)类型。于是命题理论产生了,其基本形式被编制为:主语、谓语和连词,以便连接一个不矛盾的整体内部的差异性。
古庙之战打响后,团救护队的五个女兵,在汪队长的带领下,一直跟随着一连。李晓英,马国平不仅认识,在工作中还有过接触。她既是护士,也是颇有几分才气的宣传员,是“连部五花”中的“花王”。
亚里士多德走到了这一步,把自身第一的实体与我们眼中的第一即感觉相区分,感觉反映为来自感性的谓项。人们拥有从个别出发然后回溯到一般的特点,一般用以支撑感性品质。那么,这种主谓结构的命题主义的悖论性何在呢?在于偶然性(随意性)在其中占据的位置,而动感之情乃是偶然性的见证,且原初时,这种见证是对既吸纳在、同时又无法吸纳在主语的同一性里的品质的谓语性见证。事实上,主语的同一性似乎是形式上的一种必然性,但它与命题的性质本身休戚相关:苏格拉底是这个或那个,但他必然是苏格拉底。他可以是的所有身份,他的大部分表语只能是偶然性的,似乎都吸纳在主语的强制性的统一性中。
当我们回头分析本体概念本身时,问题就更集中了,因为疑难爆发了。作为主语的本体是必然的,但它融化为无限物体,这种情况是以完全意外的方式发生的。一种本体的科学,一种本体论,因此而成为不可能的,倘若存在着与本体问题相关的某种窘境,那就是这种情况。人是多重的,但他是一个,因为他是本体:一种刚刚宣示的实在就毁灭了,但这是本体论本身的“真相”。
被很好理解的命题主义会导向主要管理逻辑-实验验证这种程序的科学,而非导向本体论,而本体论仍然关注命题主义的建立,把本体陈述为任何根基、任何必然性的源泉。形而上学是这种建立的场域:那么它将内在于在命题中实现毋容置疑性的科学呢,抑或需要通过对本体的专门思考去探索毋容置疑性的科学呢?
三、海德格尔的本体观及其悖论
那么,叩问对柏拉图还意味着什么呢?叩问的作用并未因此而降为虚无,苏格拉底创立的典型性依然鲜活。但是,柏拉图当然赋予它另一种意义。他说,如果我们提一个问题,那是针对人们所询问X之本体显示我们的无知:人因为被感性世界所包围,忘却了知性和本体论(《美诺篇》)。
综上所述,基于LWT-LSSVM的数控机床热误差建模方法比单纯的LSSVM建模方法对数控机床的误差预测精度高8.51%,这表明改进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方法可用于数控机床热误差建模,并且模型精度比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高。
命题主义是在不矛盾律的支持下出现的:如果人们建构逻各斯作为对问题性的反击,P/非P的交替并非像人们可能担心的那样是一个问题的表达;一种偶然性的出现有可能使人们看到命题的语项次序的调换,但是永远肯定一种命题。P和非P最好时可以相继用于主语S的谓语,在这种主语情况下,每次只能有一个命题,或者只能有一个真正的命题和一个错误的被排除的命题。必然如此。逻各斯保留着作为规范性的毋容置疑性,因为主体的兼爱(pathos,情感)的多重性毁灭在主体(必然的)统一性中。
全部问题在于弄清楚这样一种二分法是否可以坚持。笛卡尔把这种双重范畴称作分析与综合。对于分析而言,人作为自身之意识,从我们自身的即时出发,尽管实际上上帝是第一要素(《回答续》/Secondes Réponses)。认知理性(la ratio cognoscendi)与本质理性(la ratio essendi)的根基不同。然而,倘若我们说认知理性反映的是真理(真相),那么,两者就应该吻合。尤其是,按照正确的方法,人的精神所遵循的秩序对于接触这种真理至关重要。分析的目的在于让精神接触(物自体的)真理,这蕴含着认知理性由于先于这种真理而跌出了后者之外。或者两种理性相吻合:但是,如果人们被认为与认知理性一起处于真理中时,为什么还要使用某种本质理性呢?理性的分化何以能够得到论证呢?聚精会神的读者显然能够从这种二元对立中辨认出问题的悖论性。通过等同于物质范畴物质实际状况之真相的认知理性,人们知道自己寻找什么,且已经进入真相的分析中;通过也应该与本质理性不同的认知理性,我们尚不知道本质理性所体现的真相。两者既同一又相互区别,在它们的悖论性耦合中,再现了人们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以期可能对它进行探索,且这种探索是有用的,因为人们不知道它。判断以其主谓的二元结构再现了这种悖论性的耦合,在排除它的同时远未解决它。本体既是现是,又不是现是。
海德格尔抛弃了一兼多的本体观,打碎了主谓语结构,将其分化为“本是”(本在)与“现是”(此在)。本体是可以接触的,不再通过逻各斯,而是通过“现是”(此在)这样的本体论结构。这样的本体论结构同时包含着对本体的遮蔽和揭示,本体既与现是同化,又与现是相异,因为“真正的”(Eigentlich)关系是可能的。
但在这里,另一种困难破土而出,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定位对于本体的困难。海德格尔的方法具化为,从导致命题主义诞生并与命题主义共延的因素出发,试图超越命题主义,因而只能遭受挫折。更哲学层面,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在海德格尔那儿关乎接触本体的条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和物体不是大写意义上的本体,因为他们不与现是的多元性对立,现是也是一种本体。这当然是一种不可能性、一种矛盾,亚里士多德宣称任何情况下都用他的逻各斯的、理性的谓项概念解决它。这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但是,亚里士多德在保存理性时,让一些未经思考和以这样的主题被讨论的区域性本体论得以诞生,并因而发动了西方理性思维的探索。海德格尔通过打碎命题的统一性,自以为解决了矛盾,但没有看到这种做法使本体问题无法解决。超越现是且不同于现是的本体于是像诗一样,需要另一种逻各斯,更佳状态下,似乎需要缄默和聆听。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还滋养着通过关于接触本体之条件的言语而理解如何接触本体的希望。把存在于斯和不存在于斯、在退隐中给出的本体移入人类的实在里,他把本体论的悖论置于人那里,这种悖论不是别的,而是被颁布已经解决的问题的悖论。
四、科学与形而上学的两难处境
辩证法何以能够同时是(客体的)必然的声音和人们(主体)不知状态(我知道这个,另一人不知道,因而询问)的表达呢?这样一种二律背反的现象直到亚里士多德才解决,亚氏把辩证法(论证的场域)与科学相分离,后者是由逻辑编织而成的。亚里士多德因而创立了一种论证和修辞理论,也创立了一种逻辑学。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必须编纂逻辑学,并且第一个把修辞学系统化,那是因为柏拉图的辩证法不可避免地分裂为旨在承载人的痕迹及其偶然性的逻各斯,与能够仅产生那些真正毋容置疑的判断命题的逻各斯,两者之间是悖论的。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2018-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7%,主要原因在于2018年欧元区、英国和拉丁美洲的经济数据弱于预期,以及存在全球贸易问题及新兴市场风险。IMF指出,贸易政策以及不确定性的影响,在全球宏观经济层面愈加突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就贸易摩擦阴影下的世界经济与发展环境谈了自己的观点。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与海德格尔的路径不再重合:海德格尔选择了本体论来抨击命题性和认识基(l’épistémè),而亚里士多德则进行了相反的选择,但我们发现,命题主义与本体论是分不开的。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海德格尔都无法躲开他们拒斥的交替现象。这样,亚里士多德确实应该建立逻各斯,而神学将保证一种最高本体的存在。但是,本体是多重的。另外,在中世纪,平衡的打破有利于神学,那时的本体论首先就是神学,由上帝的唯一性来保证的本体的唯一性,并不阻遏多重性(这是经院派无休无止难以决断的辩论内容)突出本体论所宣布并体现的统一性的人为性。笛卡尔的《论方法》问世的基础是以另样的方式而非从本体出发解决所是问题的意愿,哪怕这种本体是神性本体。海德格尔错误地把笛卡尔相对于经院主义的独特之处当作一种疏忽进行批判,经院主义被徒劳无益的本体论辩论搞得精疲力竭,那里上帝占据一切,根本无法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怎样理性地选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命题表述这是什么,即脱离任何具体命题,践行第一哲学理应奠定之本体的必然性,是很正常的。命题永远陈述交替中的一个项而把另一个项作为矛盾一方抛弃掉。真理与谬误相对立。倘若形而上学就是必然性的这种言语,那么,科学就是内在的形而上学。它显示出一种本体论属性的介入,这种介入就是唯一的必然性,在那里,一种本体论让物体的片段性、多元性显现出来,并由此显示出宣布本体统一性的虚幻性指令。
在授课过程中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进行情境创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能够成功地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必然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效果。
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播种,选择中熟油菜品种,用种量是0.3~0.4公斤/亩。基肥施复合肥(15-15-15含量)50公斤/亩,硼肥(10%含量)0.5~1公斤/亩;苗肥于4~5叶期施尿素5公斤/亩,腊肥每亩施尿素5公斤/亩,氯化钾2公斤/亩,于春节前施用;薹肥每亩施尿素、氯化钾各3公斤/亩,初花和盛花期结合一促四防喷施磷酸二氢钾和硼肥。
在笛卡尔看来,一如现代许多哲学家的观点一样,本体论作为思考本体的言语,阻止对这是什么的表述。人们更恰当地表述了这是什么而遗忘了本体,“对本体的这种遗忘”远未构成思想的一种缺陷,而是思考这是什么的唯一方式。真正的本体论是不可能的,这是命题主义为了实现它而应该接受的代价。这肯定是悖论性质的,但这不是别的,只能是一般命题主义的命运本身,而命题主义在这里与任何本体思想都是分不开的。
绘画是幼儿表达自己美好愿望的语言和符号,它反映着幼儿智力的发展情况。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幼儿在绘画上会表现出三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那就是涂鸦期、象征期和形象期。
科学确实也无法真正地自我论证,而一种限制为奠定科学的形而上学应该把科学的毋容置疑性扎根于一种本体论的理想里,后者必然引导这种形而上学作为纯粹的认识论而自我毁灭。揭示一种无法绝对论证自己的本体论,这种形而上学既“摧毁”绝对必然的科学理想,也摧毁作为根基的大写本体不可能的统一性。由此产生了一种科学的不可压缩的对立:以必然方式表述本体的科学,按照本体论的说法,这是形而上学承认的目的,与试图前往科学所预设的这种必然性的根源来论证这种目的的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科学与形而上学之所以对立,那是因为本体论无法拥有和谐。一旦形而上学自我表述时参照了本体论(后者以必然性的理想为核心,却无法证明自己是必然的),就宣称自己无能为力。很简单,因为这种理想脱离实际,而逻各斯应该能够表述问题,而非仅仅通过摧毁它的排除项来界定自己。无论如何,一种希望复制、表述科学之毋容置疑性的形而上学,立即背离了科学,而由于要找到本体的必然的统一性(而所是之物不可能不是自身,也不可能就是它本身),这种形而上学就变成了本体论,而人们要求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目的恰恰是为了避免成为本体论。于是,它被摧毁、被分离、被破碎。科学在自诩天然的形而上学时,当然想成为真正的本体论,但这样一来,就反馈到它所拒斥的自身的彼岸。把形而上学作为本体论而抛弃,同时比本体论更真正地实现它,这显然是互相矛盾的。科学的隐性的形而上学是以它作为科学所体现的理想的名义对形而上学的抛弃。一种反思性的本体论不可能是奠基性的,科学尽管是毋容置疑的,但如果未能在一种反本体论(反本体论唯有通过本体论才有意义)的形而上学里超越自己,就不可能更多地把自己论证为毋容置疑的。科学在实现本体论属性的介入时,展现为不能大白于天下的本体论的真相,亦即未能提出、无法提出就获得解决的不可能的本体问题。科学体现论证的范式,它之所以排斥形而上学,那是因为形而上学宣称在其同一性和必然性的层面思考本体,科学所实现的东西比它更好。在这方面,形而上学是幻想的,且它与科学的竞赛在预测中已经失败。形而上学在被一种理论思维的命运(它因而超越之)与不可能一定将它建立为一种本体论(后者也是自相矛盾的)的撕扯下,只能是一种被分裂的形而上学。
五、结论
人们只能通过抛弃作为唯一可能颁布的解决范式毋容置疑性的理想而超越无根据的“科学”的垄断地位。认识基内在地体现着这种理想,而当它显现这种理想时,即反馈到一种建立本体论的要求,人们把这种本体论称作形而上学,一种没有自我摧毁就无法被担当的形而上学。文化内部科学有时近乎令人恐怖的自律现象(海德格尔)就是建立上述形而上学的后果。应该抛弃把本体作为先于任何询问的必然性的本体论规范,它使人们无法从其自身出发来思考它。倘若形而上学被压缩为本体论,它就只能沉没于本体的离散中,而它以为能够某种程度上超越本体这样去思考后者。本体论只是对某种形而上学之不可能性的承认,仅拥有多重性而思考必然统一性的形而上学,毋宁说它是一种天方夜谭。本体是命题主义失败的名讳本身,而非超越它的钥匙。形而上学只有不再是本体论时才有意义,本体论让科学与形而上学处于一种不即不离的尴尬地位。
注释:
在该实验中,算法使用RBF核函数,其中C=120,gamma=0.02。用10组真实数据交叉验证得到经验误差为x=0.012, y=0.009;真实误差值为ΔE= 1.21。
①必然性是西方本体思想的主导概念,即探寻唯一的、单义的、确凿无疑的绝对一致的东西。毛泽东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这里的必然性与必然王国同义。
[参考文献]
[1]Michel Meyer.De la problématologie.Bruxelles,Mardaga,1986.
[2]Michel Meyer.Pour une histoire de l’ontologie.P.U.F.,1999.
On the Paradoxical Dilemma of Western Ontological Thought
Shi Zhongyi
The author introduces and analyzes Plato’s ontological thought,Ménon’s paradox,Aristotle’s propositionalism and its paradoxes,Heidegger’s concept of ontology and dilemma of science and metaphysics,and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undoubted ideal as a solution paradigm can only be abandoned,and the monopoly position of the so-called“science”and the cognitive base can be surpassed.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ontology must be placed in the Western ontological norms before any inquiry.Ontology merely acknowledges the following metaphysical impossibility.This kind of metaphysics,which only has multiplicity but enforces the unity of necessity of thinking,can only be a kind of fantasy.Ontology is the pronoun of the failure of propositionism,not the key to transcending it.Metaphysics is meaningful only when it is no longer ontology.Ontology puts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in an awkward ambiguous position.
[中图分类号] B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9)09-0094-07
史忠义,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化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浙江绍兴 312000)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
【责任编辑:张 丽】
标签:美诺悖论论文; 命题主义论文; 毋容置疑性论文; 本体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化研究院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学文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