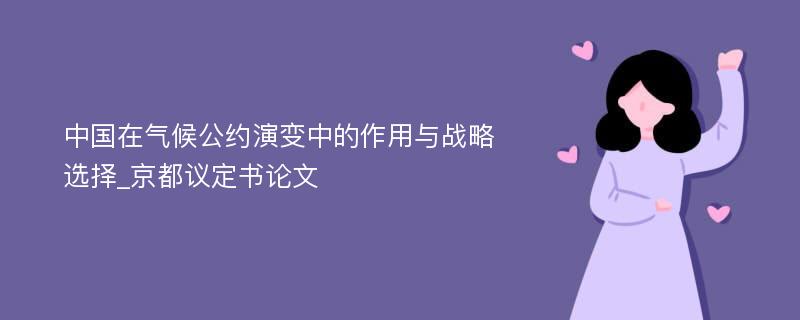
中国在气候公约演化进程中的作用与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约论文,中国论文,气候论文,进程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92年6月召开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153个国家和欧共体共同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CCC),到2001年11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第七次缔约方会议达成《马拉喀什协定》,在近十年中,国际社会围绕如何落实公约规定的目标、原则和缔约方义务等问题,经过艰苦的谈判和妥协,不断推动着公约发展演化的进程。这是一个国际制度从无到有、从粗到细、从松到紧,建立、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国际环境制度的一个缩影。
在这一演化进程中,中国一直是参与谈判及相关活动的重要成员,“加入”已不是问题。1992年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里约会议期间签署了公约,同年底全国人大审议并批准了该公约。1994年3月21日,该公约在50个国家批准后正式生效,中国是公约最早的10个缔约方之一。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COP3)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中国在1998年5月29日签署了议定书。随着2000年10月29日~11月9日在摩洛哥召开COP7达成了《马拉喀什协定》,国际社会促成议定书正式批准生效的努力终见成效。中国批准议定书也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然而,顺利的“加入”并不意味着顺利的“适应”。事实上,用“适应”来描述中国与气候公约的未来关系并不确切。因为从国际环境制度的角度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其他国际公约相比发展历史较短,仍很不完善。经历一波三折的艰苦谈判才达成的《京都议定书》不过是国际社会为减缓气候变化而作出努力的第一步,距离公约规定的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最终目标仍相差甚远。因此,未来气候公约的发展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充满矛盾和变数的演化过程。中国与气候公约的关系,必须在这一演化进程中加以考察。显然,中国绝不是简单地“融入”,也不是被动地“适应”某个现成的制度框架,而是作为这一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并力图使之向着有利于维护和增进中国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
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和在国际谈判中的作用
伴随气候公约的演化过程,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注重环境含义。气候公约起源于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在公约谈判的开始阶段,尽管欧共体将这一科学问题上升为国际政治议程,具有打击美国竞争力使欧洲与美国相抗衡的深层政治和经济用意,但限于当时的科学认识水平,且主要议题仅针对发达国家的减排问题,中国基本上将气候公约视为一个国际环境协定,在签署和批准公约问题上表现了非常积极的合作态度。
2.注重政治含义。1995年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一次缔约方会议(COP1)通过了“柏林授权”(Berlin Mandate),决定开始谈判发达国家具体的减排义务,并不得为发展中国家增加任何新的义务。而在此后的谈判中,一些发达国家不仅不提出减排承诺目标,还将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引向主要发展中国家,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对此,中国保持了高度的政治警惕。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三次缔约方会议(COP3)上,“77国集团加中国”代表发展中国家要求大会必须遵循公约和“柏林授权”的有关规定,并提出了关于为发达国家制定具体减排义务的议定书基本要素的全面主张。COP1之后,气候公约的政治含义成为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关注的重心,国际气候谈判基本上作为一场“政治仗”来打。
3.注重经济含义。1997年京都会议通过《京都议定书》后,随着谈判进入制定操作细则的阶段,公约的经济含义逐渐显现。议定书引入的三个灵活机制,尤其是鼓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项目级的合作的清洁发展机制(CDM),直接关系到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经济利益。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参与问题上,中国面临日益强大的国际压力。而国内对于中国限排的宏观和部门经济影响、政策措施的潜力和效果的经济评价等诸多问题的研究仍十分有限。在此背景下,中国在关注气候公约政治含义的基础上对公约经济含义的关注明显上升。
气候变化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环境、法律等多角度、多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全球问题。中国气候变化的战略决策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远不是单一部门所能胜任的。1998年,中国政府将原先设立在国家气象局的气候变化政策与协调办公室改到国家计委,以便更好地协调外交部、财政部、科技部、环保局、气象局等相关部委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工作。这是国际气候谈判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和对公约本质认识的提高和深化。
从公约演化的总体进程看,中国不仅在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参与程度在不断加强。
在气候谈判“南北对立”的基本政治格局下,尽管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但欧盟、以美国为首的伞型国家集团以及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加中国”基本上是决定公约演化进程的三支最主要的政治力量。虽然代表“77国集团加中国”发表立场声明的往往是“77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的代表,但中国以其大国的国际地位,通过艰苦的内部协调工作,实际上承担了发展中国家阵营领导者和协调员的角色。中国始终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既在诸如发展中国家参与等关键问题上,坚持原则立场,毫不退让,又在某些情况下为争取更广大的国际支持而采取灵活、妥协的策略。在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抗衡中,努力争取和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权益。在参与谈判的过程中,中国除发表原则性的声明表明国家的基本立场,也就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例如,针对发达国家为降低减排成本引入并极力推行基于市场的三个灵活机制,却一直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问题上设置障碍,中国在COP4上提出“技术转让机制”(TTM),并被写入COP4会议决议的正式文本,即“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为公约制度的完善做出了贡献。
此外,中国参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科学评估活动的情况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不断强化的参与程度。在1990年和1995年IPCC推出的第一、二期《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中国科学家没有参与或仅有极少数人以个人名义参加,几乎谈不上发挥什么影响力。到2001年推出的第三期评估报告,中国有一人担任了第一工作组的联合主席,共有20人次作为主要作者和评阅人参与了报告的编写,另有许多科学家参与了先后三轮的科学和政府审评工作,使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大大增强。
未来气候公约演进的趋势及影响谈判进程的主要因素
《马拉喀什协定》为《京都议定书》正式批准生效扫清了障碍。然而,议定书对于实现公约规定的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目标的真正价值何在?
单纯从环境目标看,它无疑是令人失望的。这是因为占全球总排放量约1/4的第一排放大国美国逃避了减排责任,剩余大多数发达国家利用重新计算碳吸收汇和“海外减排”的灵活机制大大缓解了自身的减排压力,而如俄罗斯等经济转轨国家不仅不用减排,更可以利用大量可供贸易的“热空气”(注:热空气(hot air)是指不采取减排措施下的基准排放情景BAU超出议定书规定减排或限排目标的部分。俄罗斯等经济转轨国家1990年后由于国家经济衰退使排放量大幅度下降,因而存在大量可供贸易的热空气,为这些国家带来巨大的潜在经济利益。)从中渔利。实施公约的减排目标对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效果实在是微乎其微,相比公约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的最终目标更相距甚远。环境目标的强化必须通过新一轮的谈判,制定新的、目标更高、约束力更强的议定书来逐步推进。
但从法律意义上看,议定书的批准实施推进了国际环境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它又是值得欢迎的。议定书奠定了国际减排行动的法律基础,开创了在气候变化方面采取全球共同行动的先例,是国际社会在环境领域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一个胜利。尤其是解放有关京都三机制的基本运行规则问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CDM项目合作创造了条件。正如荷兰环境部长、公约COP6及其续会主席普朗克指出,COP7为美国参与全球对付气候变化的进程提供了适合的法律框架。
同时还必须看到,随着《京都议定书》的前途趋于明朗,前一段被暂时搁置的“发展中国家参与”问题将再次成为谈判关注的焦点。正如在一些发达国家学者看来,《京都议定书》至少具有环境、法律和政治的三重目标,环境目标只是象征性的,实现法律目标之后,下一步的政治目标就是说服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减排行动。(注:Benito Müller,"Does US Ratification Really Matter?",Oxford Institute forEnergy Studies,May,2000.)公约COP8将于2002年10月23日~11月1日在印度召开。在COP7上,一些发达国家就提议从COP8开始具体讨论发展中国家参与问题谈判的议程。虽然该提议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下未写入协定的最后文本,但可以肯定,围绕发展中国家参与问题的谈判已变得越来越紧迫,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公约演化的趋势。谈判一旦正式开始,必将异常艰难。尽管目前仍无法预见谈判的最终结果,但就影响谈判进程的主要因素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发达国家的履约状况。公约原则上肯定了发展中国家采取行动的程度取决于发达国家履约的状况,尤其是发达国家履行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转移的义务承诺,当然也包括发达国家承诺率先采取减排行动的示范作用。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则强调以发展中国家“有意义的参与”作为自身行动的先决条件。无论如何,将发展中国家参与程度与发达国家履约状况挂钩将是未来谈判的必然趋势。因此,《京都议定书》能否尽早批准生效,议定书规定的附件Ⅰ国家在第一承诺期的减排义务能否得到切实履行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2002年不仅是一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年份,(注:2002年是里约会议十周年,气候公约签署十周年,《京都议定书》签署五周年。)可以扩大气候变化公约在国际上的影响,而且从减排政策和技术措施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角度考虑,恐怕也是议定书规定义务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最后机会了。
(2)美国的态度和行动。美国虽然于2000年3月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但美国作为公约的缔约方和占全球总排放量25%的第一排放大国,仍是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成员。从推行其全球战略出发,美国不可能长期游离于任何重要的国际制度之外。2002年2月14日,布什总统宣布了美国的替代方案,即在未来十年将美国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单位GDP的温室气体碳排放量)降低18%。(注: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the Press Secretary,"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ClimateChange and Clean Air",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Administration,Silver Spring,Maryland,Feb.14,2002.)无论美国的替代方案受到国际社会怎样褒贬不一的评论,美国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绝不会放松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关注。在布什的讲话中,他一方面肯定发展中国家有发展的权利,美国愿意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作为排放大国如果不承担减排义务是不负责任的。布什在2002年2月21~22日短暂的访华行程中专门就气候变化问题与中国最高层进行了磋商,并成立了专门的中美联合工作组。美国退出多边合作框架转而强化双边合作的真实意图尚不明朗。
(3)南北阵营的内部分化与协调。COP7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告一段落,南北阵营内部也将随之发生重要的分化和重组。根据《马拉喀什协定》,允许发展中国家实施单边CDM项目,并出售所获减排额度,这大大增加了能够参与CDM的发展中国家的数目,并使基于项目级的CDM合作向发达国家所期望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全球排放市场前进了一步。同时,协定允许实施碳吸收汇CDM项目,虽然有一定的数量限制,但也给在吸收汇项目上拥有很强竞争力的一些南美国家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加之握有大量“热空气”的俄罗斯等经济转轨国家对排放市场的影响,未来在利益的驱动下,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争取更多的资金、技术流入本国,有可能出现“恶性竞争”的局面。尤其是某些急需资金的最不发达国家,可能因此改变立场,这无疑增加了发展中国家阵营内部协调的难度,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而发达国家阵营内部在暂时解决了利益分配之后,矛盾分歧弱化,联合的趋势大大增强。利益集团的分化和重组有可能改变南北阵营的力量对比,甚至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对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十分不利。
(4)发展中国家排放量的实际增长。尽管公约承认发展中国家为了满足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会增长,但如果发展中国家排放量的实际增长速度过快,尤其是某些排放大国绝对排放量或人均排放量达到某个标志性的水平,如中国的绝对排放量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位,则会使发展中大国的处境更为不利。
(5)科学研究的新进展和IPCC的科学评估活动。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是气候公约产生和发展的科学基础,IPCC的科学评估活动一直是气候公约演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2001年刚刚推出的第三期《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在发展中国家的坚决要求下,删除了一些有关发展中国家参与等明显带有政治含义的论述。第四期评估报告的准备工作将于2002年启动,计划到2006年前后推出。届时正值《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第一承诺期即将到期,其对新一轮议定书谈判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中国面临的双重压力和两难困境
尽管目前发展中国家仍作为一个整体维持着“77国集团加中国”的基本模式,但从发达国家的分化策略看,要说服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减排,关键是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占世界第二位的排放大国,自然成为发达国家说服的首要对象。由此可见,中国面临着日益强大的国际压力和严峻的挑战。在发展中国家参与问题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立场的关键分歧何在?从发达国家的立场看,不外乎以下几点理由:
(1)环境原因。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全球的共同努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很快,如果仅由发达国家承担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不参与,就会出现所谓“碳泄漏”(carbonleakage)问题。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努力将被发展中国家排放的过快增长所部分抵消,甚至有可能反而导致全球总排放量上升。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并最终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和全球生态系统都将遭受气候变化的重要危害。因此,从维护全球利益和全人类利益出发,发展中大国应尽早参与全球减排行动。
(2)经济效率原因。温室气体一经排出很快在大气中完全混合,这一“均质”特性决定了在哪里减排、由谁来减排对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同等功效。发达国家减排的经济成本较高,而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廉价的减排机会。中国被认为是减排成本最低、减排潜力最大的国家。如果中国等发展中大国不参与,全球减排的总成本就会大大上升。从追求全球最优效率的角度出发,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减排机会应作为全球共同资源来加以开发利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较大的边际减排成本差异使得建立全球排放市场是一个对买卖双方都有利的“双赢”方案。发达国家通过“海外减排”降低了履约成本,而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在资金和技术转移等方面获得经济补偿。
(3)国际竞争力原因。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贸易上的竞争对手。如果只有发达国家为减排付出经济代价,而发展中国家不付出减排成本却享受了减缓气候变化的好处,即经济学上所谓“免费搭车”(free riding),则发达国家可能因生产成本的上升,而使能源密集型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发达国家的企业会因此蒙受巨大损失。
(4)政治原因。不可否认,某些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在国际社会的霸权地位,常常借环境问题之名,散布“环境威胁论”,向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影响,推行所谓“环境霸权主义”或“环境帝国主义”,目的在于控制、遏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源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利用,而能源提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在某种意义上讲,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就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空间,经济、能源、环境(所谓"3E")之间的密切关系,正好为其实现政治目的提供了绝好的借口。
发达国家的这些理由,既不是等量齐观的,其是非曲直也不能一概而论。虽然其中有维护“全球利益”的成分,但更多的是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例如,发达国家所说的环境原因和经济效率原因强调“全球利益”或“人类社会共同利益”,听起来颇为冠冕堂皇。但“全球主义者”未必是“全球利益”的维护者。发达国家在宣扬“全球利益”和全球最优经济效率的同时,只谈“共同”责任,不讲“有区别”的责任,默认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排放和现实排放存在巨大差异的合理性,回避发展中国家在较低发展水平条件下现实能力的不足,漠视发展中国家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不可能得出公正的结论。
国际竞争力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眼前的经济利益,它是国际市场竞争中多种要素的综合表现。企业的经济竞争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这个国家长期、稳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因此这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政府最看重、最忧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出于急取国际支持的需要,发达国家的官员和学者又往往淡化甚至否认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大国参与全球减排有维护本国竞争力的目的。(注:Robert Repetto and Crescencia Maurer,with Garren C.Bird(1997),"U.S.Competitiveness Is Not at Riskin the Climate Negotiation",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ClimateNote,Climate Protection Initiative,Oct.1997.)
发达国家以环境为借口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政治用意,是冷战后国际关系中思想文化冲突的一种延续和新的表现方式,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国际气候谈判中南北对立的基本政治格局的必然反映。这是中国必须坚决反对的。
除了中国面临的日益强大的国际压力,由于自身独特的人口、经济、能源、技术、环境等具体国情以及发展的紧迫需求,也使中国面临强大的内部压力。
首先,中国拥有庞大的13亿人口,其中中西部地区部分贫困人口尚未满足营养、健康、教育等基本生活需求,改善生存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十分迫切。
其次,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增长的起飞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7%~8%较快的GDP年平均增长速度,能源消费量由1978年的5.7亿吨标煤增长到1999年的12.2亿吨标煤。由于资源条件的限制,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中煤炭的比例虽然缓慢下降,但仍在70%左右。
在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三大驱动因子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呈现出总量大、增长较快、单位能耗排放密度高,但人均量很低的基本特点。1997年,中国CO[,2]排放量约为8亿吨碳,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3.6%,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排放大国。商品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密度约为0.6吨碳/吨标煤,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3%。而人均CO[,2]排放量约为0.7吨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6%。(注:刘江主编:《中日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页。)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必然呈现较快增长的趋势,从排放总量上有可能在二三十年后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但人均排放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根据“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项目”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结果,在不同排放情景下,到2030年,能源活动的CO[,2]排放量约在12~21亿吨碳范围,人均CO[,2]排放量约为0.7~1.3吨碳,与1990年世界平均水平相当,约为OECD国家1990年平均水平的1/4~1/2。(注: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小组:《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美国总统布什在提出《京都议定书》替代方案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只有经济增长才能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只有经济增长才能为环境保护和清洁技术开发投入更多的资金。“经济增长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不是问题本身”。“美国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将给美国带来4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失去4900万个就业机会”。(注:The White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Remarks by the Presidenton Climate Change and Clean Air",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Administration,Silver Spring,Maryland,Feb.14,2002.)如果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技术、已达到很高发展水平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美国尚且如此,中国面对大量尚未摆脱贫困的人口,面对尚未根本遏制的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民健康的严重威胁,在目前较低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下,如果承诺限排或减排义务,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像的。
在上述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在气候变化战略选择上面临一系列两难困境:
(1)一方面,国际环境制度的演化向着约束范围更广、约束力更强、约束规则更细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为了满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实现摆脱贫困和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目标,中国需要较大的排放空间。
(2)一方面,在相当一段时期中国尚难以找到经济、安全的方法根本改变长期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及由此造成的排放总量大、单位能源排放密度高的现状;另一方面,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使得能源利用效率很低,从项目级看,中国的确拥有许多低成本的减排机会。
(3)一方面,从长远看,中国脆弱的生态环境易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从现实看,中国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技术水平和有限的资源,又使中国难以承受与自身能力不相适应的国际义务。
(4)一方面,中国日益上升的大国政治地位使中国实际承担着发展中国家阵营领导者和协调员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国实行“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又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愿挑头,以避免成为众矢之的。
(5)一方面,中国要维护自身权益,必须对一些重要的核心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具体方案;另一方面,由于未来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科学研究基础相对薄弱,中国对许多具体问题的取向又难以做出清晰的判断。
总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长远利益与现实成本、政治意愿与现实能力、实际角色与外交策略以及未来发展和气候变化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等多重矛盾的交织,构成了中国气候变化战略决策的独特背景,这是一幅复杂的立体画面。面对利害攸关的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挑战,中国不得不慎重行事。
中国的责任与战略选择
如何看待中国的责任,以及在未来公约演化进程中应采取怎样的战略是气候变化领域的决策者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科学工作者正在积极研究的问题,对此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
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无论面临多大的国际压力,中国必须继续积极参与气候公约的演化进程,不断增强参与的程度,提高参与的能力,力争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同意一些学者所讲的“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作用既不是单一的挑战或伙伴、旁观或领导,而是几种角色都要选择,在不同问题、不同时期、不同领域起不同作用”。“中国应参加到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去,只有参与其中,才能参加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进程,才能在体系内部维护中国的利益,同时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注:叶自成:《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几点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期,第15~10页。)但具体到不同问题时,许多人往往将意识形态划为应“挑战”领域,而一提国际环境制度,就统统划入全球利益的范畴,主张适用“伙伴参与战略”,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危险的。在气候公约的演化进程中,最终目的是维护全球利益,但全球利益远不能代表问题的全部,关键在于现实减排义务和成本的分担。中国尽管可以采取灵活多变的外交谈判策略,但中国参与战略的立足点必须放在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必然形成对发达国家的“环境霸权”挑战。
中国对国际环境制度的参与和其他国际制度相比有其特殊性。在经济领域,国际经济体系的规则主要由西方制定,中国加入这一体系基本上只能适应,承认西方的主导权,中国在其中要改造、修改规则非常困难,也相当有限。而正在建立之中的国际环境制度仍很不成熟,尽管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科技实力具有一定的主导优势,但在其演化发展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发挥作用的空间,中国应该努力争取在某些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气候公约作为一个多边外交的国际舞台,对美国有较强的制约作用,这在国际制度中是少有的例外。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许多国际制度中具有主导地位,甚至一些国际制度成为美国战略和利益的工具或“软权力”。而由欧共体启动的气候变化公约谈判进程某种程度上是欧盟制约美国的制度工具。这是因为欧盟人口增长缓慢,经济发展步入成熟阶段,能源利用效率较高,温室气体排放已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而美国为满足经济扩张和推行全球战略的需要,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仍呈现上升的趋势。欧盟相比美国有较大的减排优势。欧盟一方面希望通过气候公约的制度工具来打击美国的竞争力,牵制美国的经济,但另一方面,为了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又往往联手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施压。中国既反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但作为排放大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也与美国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美国在对抗欧盟制约作用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制度工具来限制中国的崛起。由此可见,中国—欧盟—美国在气候公约的谈判中形成了复杂的相互制衡的关系。中国必须参与并巧妙利用多边协调的国际制度来维护自身利益。
在积极参与的前提下,中国应承担怎样的责任?对此,中国政府通过部长级发言阐述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在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前,不会承诺减排义务。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后,中国会认真考虑这一问题。”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在该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仍毫不动摇。然而,不承诺减排义务并不像某些西方国家指责的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一,不承诺减排不等于不承担义务。中国作为公约缔约方,较好地履行了公约和议定书为非附件Ⅰ国家规定的义务,如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准备国家信息通报,开展公众教育等。
第二,不承诺减排不等于对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没有贡献。事实上,中国从1981~1999年的18年间,单位GDP能耗下降60%,累计节能9.49亿吨,相当于减排约5.5亿吨碳。中国通过节能、调整产业结构、开发优质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植树造林、人口计划生育等多项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不承诺减排正是为了负起国际和国内双重责任。尽管国内外有许多研究结果,但由于模型、参数的不同设置,这些结果差别很大。减排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究竟如何仍很不清楚,此时轻率承诺与自身能力不相称的义务本身就是不负责任。中国不能为了承担国际责任而对国内13亿人民的未来生活不负责任。
第四,不承诺减排并不等于行动上的无限推延。中国完全可以也应该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框架和目标下,采取“无悔”(no-regret)的政策措施,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国际合作机遇,推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不可否认,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要在国际制度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我们绝不能轻信西方学者对中国减排经济影响的盲目乐观的估计。例如,1999年美国副总统戈尔转交给我国政府一份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列举西方学者应用不同模型工具的计算结果,试图论证中国承担适当的减排义务并参与全球排放贸易,不仅对全球环境有利,还将给中国带来至少四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二是增加经济收入,三是促进技术转移,四是减少局部空气污染。中国在2010年在BAU(注:BAU,即Business as usual,指按目前发展趋势,不采取专门针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情况下的一种未来排放情景,常作为分析其他情景的参照基准线(baseline)。)基础上减排14%~24%,2008~2012年中国通过出售排放配额每年可获得40~140亿美元(注:U.S.Council of Economics Advisers,"The Economics of GreenhouseGas Emission Abatement in China,A Preliminary Analysis",Sept.1999.)的额外收入。西方学者这些过于乐观的估计带有很大程度的虚幻性,除受“科学政治化”影响、有意夸大可能收益而回避有利影响的因素之外,其他可能原因还包括:
(1)数据来源问题:国外研究普遍难以取得中国准确的基础数据,或根据中国历史数据外推,或由于统计体系不一致不得不粗略估算,导致基础数据与中国现实情况有较大偏离。
(2)估算方法问题:为了弥补减排成本,国外引入了衍生效益的概念,估算温室气体减排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的间接效益。这部分效益的估算基本上依赖主观判断和假设,从理论到方法都很不成熟。例如,环境改善减少因环境破坏造成的死亡人数,但人的生命价值如何估算,按人均GDP上百倍的差别赋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人的生命价值是否符合伦理学原则等,都没有获得国际上的共识。
(3)模型工具的弱点。模型是社会经济影响分析的有效工具,但不同模型工具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各自不同的弱点。例如,模型计算减排成本时往往对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转换等的成本考虑不足,在减排的经济成本之外很少考虑社会成本,如煤炭行业的失业问题、能源系统的惯性和惰性、市场失灵和行政力量的不适当干预等。
(4)对全球排放市场假设。模型研究往往将全球排放市场假设为完全竞争、充分交易的理想状态,实际上,刚刚建立尚未进入实施阶段的全球排放市场与成熟市场相差甚远。各国对全球排放市场的参与方式、规模、程度和市场供需关系都是极不确定的。
总之,气候公约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演化进程才刚刚开始。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并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迎接即将到来的严峻挑战。
标签:京都议定书论文; 全球气候变化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