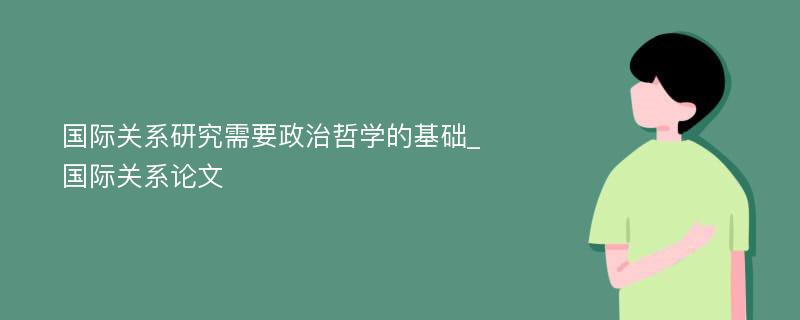
国际关系研究需要政治哲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关系研究是一个兼具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研究领域,但这门学科始终缺乏一个研究的基础。一项没有基础的研究好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论及其研究的目标、内容和方法时,本身都无法实现自我完成。在资讯化、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一项丧失了基础的研究也会丧失它的价值。在这一领域中,相关的研究林林总总,特别是近些年来,大批研究人员投身其中。但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可持续性,却一直存在着争论。研究的可持续性代表着学科的生命,一代一代的国际关系学人为之付出心血。时至今日现状如何?无论对研究人员抑或是学科本身,应该说,可持续性都是一个挑战。而国际关系研究的可持续性源自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基础。
确立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政治哲学
国际关系,顾名思义,是研究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学科;从另一个层面上理解,在国与国关系的层面上分布了诸多问题,它们都是在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架构之上存在的,因此也属于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从后一个角度来思考,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术界,包括国际规则、国际制度等问题在内的研究成果或范式都可以作为国际关系研究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上述业已形成并广为接受的理论假设,诸如国际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的有限理性,以及由生物本能演绎出的国家竞争模式等对经验的模拟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这些仍是远远不够的。今天,国际关系的研究是否应该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次?这便要深入到国际关系的政治哲学基础。
这种推进曾经并不显得十分急迫,因为既有的理论架构可以完成对现实问题的讨论。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尽管对于“全球化”的定义各具千秋,但有一点不容置疑,便是各国之间逐渐呈现了一种“切身共处”的局面。在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很多问题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出现,原有的范式与假设变得不再适用且亟须调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国际关系研究缺乏质的飞跃恰恰在于人们对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没能做好准备;究其原因,这种转换的完成缺乏另一个学术空间的支撑,这便是上文提到的政治哲学基础的缺失问题。
政治哲学如果要承担起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便要思考它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是本有的、内生的,还是具有可替换性?实际上,这一基础本身并非一成不变。打个比方,就像北京城市的发展变迁,今天我们所见的城市是从城市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拆解出来的,各种元素新旧杂处:一幢现代化的摩天大厦旁边可能坐落着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四合院,既有延续亦有替代。政治哲学作为基础也是如此,既有其内生性,也有外源的不断介入;而这种外源性,便是所谓的时代性。与老一辈学者孜孜以求的,利用文化、历史、哲学等“武装”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不同,我希望引发的,是从这一门学科的研究中寻找它的基础。从表面的意义看,国际关系中包含政治研究,与政治哲学具有关联性。对于政治哲学,尽管目前缺乏精确的语词加以概括,但可以理解为用“思辨和反思的哲学方式来分解和演绎政治问题”。反思,代表历史;思辨,代表形而上、代表逻辑,它们属于哲学的基本要素,其背后体现了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这样的哲学方式来研究处理政治问题,这便体现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政治哲学基础性。
用道德基础审视国家的行为与认知
举例来说明。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道德问题一直作为基础出现;它既是人类的行为基础,也是人们基本的认知基础。道德作为一种准则、一种境界、一种心绳,扶持和伴随人类生存、生命的历程,东西方皆是如此。尽管道德作为认知基础,在一些情况下也许会存有争议,例如一些学科会持有“道德中性”的假设;但这里所说的基础,指的是一种哲学范畴。道德可以想象为一个“精神之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背景之下,内容也是随之变化的。理解道德的内涵并非亘古不变非常重要,因为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能够演化出具体时期的准则,也用于演绎具体时期的合法性。例如商业资本登上历史舞台后,被当时的社会主流阶层,如国王、君主描述为贪婪、不择手段、心怀叵测、缺乏道义之徒;为避免这种“社会公敌”的形象,也是出于集体生活的逻辑与博弈,商业资本主义亟须寻找一种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边沁、霍布斯、亚当·斯密等适时出现,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大幕中,为新兴的社会阶层找到了全新的道德基础,即人性需要人类理性,进而也证明了其存在的合法性。道德演绎合法性,而政治离不开合法性;将道德与合法性关联起来加以透视和研究,便体现了政治哲学。这一脉络也应该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出发点。遗憾的是,将国际关系的研究局限于贸易数字,而忽视它背后隐含的政治哲学基础,恰恰是这一领域当前的研究现状。
再举一例。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乃至亚里士多德时代,不存在“天赋人权”的观念。彼时人们的权利地位与社会属性是通过“人与共同体(国家)形成的精神联盟”得到体现。人的权利身份由共同体决定,因而人需要把自己充分地融入到共同体之中,才有可能完成自我属性的实现。这也是柏拉图提出“分工正义”的依据:完成了在共同体之内的“分工”,便体现了“正义”、获得了“道德”,人也完成了自身“种”(species)的实现。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有识之士通过对古希腊的挖掘,创造性地发展了人权的道德观念,即“天赋人权”,实质上是扩展了古希腊人与共同体权利的内涵,强调了人权的先验性。这一全新的道德观念,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飞跃。这样的拓展,使商业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力量,能够对抗其他社会阶级、神权国家,随之催生了现代革命和民族国家。而同样地,民族国家也需要自身的道德基础,这便回归到了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政治哲学基础问题。只有用道德基础来审视民族国家的行为与认知,才能使我们的研究不至于遗漏掉很多国家关系中的精微、鲜活和隐蔽的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
从方法论回归研究的现实性
打开了政治哲学基础这扇视窗,便可以发现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存在着很多“议题群”,如何排列、设定问题以及如何开展研究,便涉及政治哲学与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问题。而初期,如何对此进行筛选?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正义性问题可以引申出很多议题。例如,美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事实上为世界其他实体或体制的存在(甚至包括恐怖主义的存在)提供了前提;很难想象没有美国,二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会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因而美国存在的背后是否有着某些隐蔽的、具有正义性的逻辑?这些可以视作中美关系中蕴涵的正义性问题,需要用合法性加以论证。可惜的是,这样的视角,在目前国际关系的研究中较少涉及。如果将类似的正义性研究,即国家之间隐而不宣的背后的线索作为准则来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使其包含官方关系、民间关系等全方位的因素,对于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来讲,无疑具有建设性和时代性。
从形而上的政治哲学基础到实现学科研究的现实意义,即“落地”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中美关系体现了时代性的碰撞,包括贸易摩擦、文化碰撞等各个方面。对于中国而言,建立在政治哲学基础之上的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实现将自身引向不断地修改、调整和建构,使之更加适应时代的正义与道德基础,也就是时代的准则。
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天一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