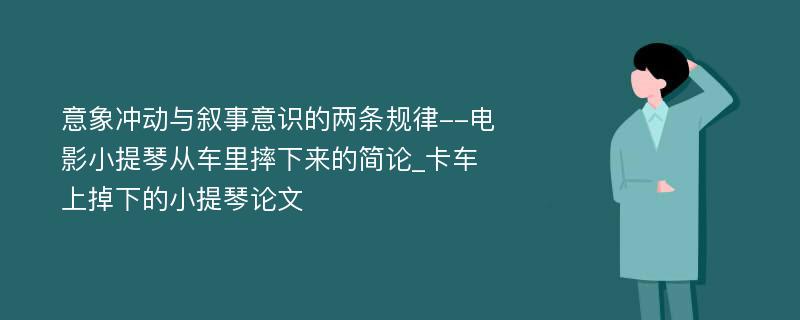
影像冲动和叙事意识的二律背反——略评影片《卡车上掉下的小提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掉下论文,卡车论文,小提琴论文,影像论文,冲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影片《卡车上掉下的小提琴》(江澄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得到媒体关注是从它 意外获得美国圣何塞电影节“最佳环球视觉效果奖”开始(注:新浪影音娱乐2003年7月 7日05:26转引北京娱乐信报消息。)。不过这种关注并没有顺理成章地转向对影片本身 的兴趣和宣传,而似乎只是停留在对国外电影节大奖的欣羡(并非了然)上——从报道文 章的数量和深度看都是如此,各媒体报道的时间前后相差竟达数月,有的甚至连获奖的 具体时间都没有提及。进而大众对这部影片几乎一无所知——各处音像商店遍寻这部影 片的光碟都难以获得,问店员也都一脸茫然。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卡》的冷暖命运倒是真切体现出许多国产电影创作生产方面 的一些症侯。一方面,导演对他的作品有很多想法,不能简单地说这些想法本身对错, 另一方面,完成的影片却未必将这些想法实现,我们总觉得影片定位暧昧难明。其中的 意味虽然不是《卡》一部影片能够尽显,却仍可以从中看出一条结构性的裂隙。
裂隙的一边是影像冲动。在《卡》片中,一系列上海下层民众的生存空间被摄录成影 像:昏暗狭窄的居室弄堂,江边空地上杂乱的个体摊位,拥挤混乱的玩具加工车间,人 群车辆川流不息的轻轨车站,等等。以这些空间为场景,导演又采用了相当纪实化的摄 影手法展现主人公——下岗工人胡佐衡的生活:批发报纸,出摊,做临时工,日常起居 。这些手法当中,既有长镜头对某一空间的连续展示,有自然光照对人物环境的造型作 用,也有变焦镜头对大景深空间的顺序透视,还有近年风行的肩扛摄影摇曳不定的跟拍 。显然,导演努力、自觉地追求着纪实风格的影像,在纪实影像得到传媒大量宣传和鼓 吹的今天,观影者很难无视这种努力。
然而影片的纪实风格并不纯粹。首先,影像空间不能给人完整的感觉,这主要因为影 片中的场景是刻意设置的(而非自然选择的空间),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剧情中比较重 要的一个镜头如:胡在自己的摊边第一次拉响琴弦,随即目光投向——镜头向右上拉起 、落幅至——远处高楼上少年宫琴房的窗口,年轻女子的背影清楚可见;我们稍后会被 影片告知这位女子是琴课老师吴冰。这里使用了变焦镜头,但且不说动作略快带来的粗 糙突兀,至少在场景转换、情节发展的逻辑上,缺少必要的铺垫过渡,显得牵强巧合。 又如,胡在轻轨车站张望着,随即吴从自动扶梯入口处出现,第二个镜头拍摄角度应该 是胡的主观视点,但实际空间关系的限制取消了这种可能,只能采用近距离较大角度的 俯拍,画面也无遮无挡,太过“干净”。
其次,运动摄影似是而非。无论是用肩抗,还是固定机位,都应当遵循必要的视知觉 规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轻轨车站站台上的运动摄影获得了晃动起伏的效果,高速运 行的车厢内的摄影却非常平稳!这就轻易取消了前面营造出的真实感觉。此外,人物交 流的许多场景使用摇镜头顺序摄录人物动作语言反应,这种手法在个人影像时代日趋流 行,但是《卡》片中过多、过快的摇镜头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物内心活动的节奏, 而这种节奏可能是这一场景的重心。
实际上,在一些重点渲染的场景导演仍然依赖非纪实化的手法。片中三次使用了高速 摄影,效果最好的当属胡母心力交瘁昏倒的一场:高影调,除了海鸟拉长的鸣叫,环境 声音全部隐去,老人站起、目眩、摇晃、倒下,黑场——这个延长的时值成功地强化了 悲剧色彩,比起用纪实化手法的场景更具感染力。
除去上述一场,《卡》片在音效方面实在乏善足陈。影片是后期录音,在听觉上无空 间层次的变化,楼下邻里的吵嚷和楼上老人敲窗一样清楚;关窗前和关窗后音质一般无 二,无真实感可言。更重要的是,一个学琴的故事和声音关系太过密切,这决定了琴声 在影片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按照剧情,主人公年近不惑,毫无音乐基础,初学小提琴的 效果可想而知。一名音乐专业的学生告诉我,初学弦乐一年之内不堪入耳。这情景在文 学中不成问题,甚或可以成就一片生动文字,而在视听综合的媒介中则适足以成就一场 噩梦!而且,主人公愈执著,他引发同情共鸣的可能性在实际上愈小。不妨说,这里撞 上了艺术介质的界限。
追求影像——应该还有声音——表现力并没有错,尤其是在中国电影创作队伍总体上 视听语言能力偏低的情势下。但是似乎应该了解这样一个前提,即:每一种可以在美学 上称为风格的影像都有其内在逻辑:它的生成,它的精神实质,它的所长和所短。在深 刻地把握这些以前,贸然采用其形式未必能够达成意愿。
影片没有营造出有机联系的影像空间,其中一个原因是镜语过多集中在主人公个人的 遭遇即情节上。设想,如果影片聚焦在一系列事件,则确实可以类比于新写实主义生活 流的风格;或者换另一个极端,聚焦在个体的内心意识,则可能呈现出现代主义的意蕴 。《卡》在精神气质上与此二者都相去甚远,尽管编剧导演已经努力淡化情节、松散结 构、开放结尾,但整个叙述对个人遭遇/情节的推重已经决定,《卡》仍然是一部以叙 事为核心理念完成的影片。
我们可以指认许多属于中国电影的叙事传统或者说元素。《卡》故事的核心是传奇, 这意味着它不具备普遍性。以胡的身份,捡到一把卡车上掉下的小提琴虽然是可能发生 的事件,几率无疑很低;至于他突然爆发的痴迷,在现实中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不过 因为是传奇,后面的情节才便于夸张下去:胡在乐团窗下听着吴冰的琴声热泪盈眶,以 及胡在歌厅门口冒雨等候吴冰至深夜,诸如此类。这些情节同我们日常的经验很难沟通 。胡在报摊旁练琴招致众人围观的那个段落就更加缺乏足够的理由,尽管导演不惜用高 速摄影和主观音效来渲染这一幕。
为弥补情节的不足,演员需要付出许多气力,这项工作无论如何不是业余演员可以胜 任的,必须启用职业演员。即便如此,因为故事本身难以自圆之处太多,演员只好借助 夸张的形体、表情和语言。在表现胡学琴的举动时,演员的表演明显过火,同样的过火 表演还出现在许多角色身上。不言而喻,一旦涉及到演技,也就和纪实电影美学又隔一 层。不过换个角度看,依赖演员表演长久以来是中国电影的重要叙事手段。
《卡》最高潮的两个段落运用的都是相当典型的“苦戏”手法,突出地体现了上述两 个元素。一处是胡母和众邻里周旋,沉重的悲剧气氛全凭演员对人物的表演,包括造型 和哭诉,抽离这些,胡母申辩的理由并无情与理的说服力。在另一处,编剧导演试图解 决一个最大的难题:怎样给胡的执著以肯定?编导一定意识到自己走上了钢丝:胡需要 一种成功,而胡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成功!否则就完全是好莱坞炮制大片奇迹的路数, 这对于前边努力经营的纪实风格简直是崩溃性的灾难,决不可行。编导的出路是:众人 怀疑胡精神失常,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检查,胡在医院里奋然演奏一曲,一群精神病患者 围拢过来倾听,然后为他鼓掌;闻讯赶来的吴冰见到这一幕,也为他鼓掌——就这么给 了胡一个说法,虽然可以自圆其说,却总觉接受起来为难。
只是不知编导是否想到,真正的执著根本不需要成功!没有得到说法的胡会升华为悲剧 人物——个体的挣扎和群体规范之间必然的悲剧,疯癫与文明的主题不是曾为福柯论述 过的吗?在胡高喊“我没病”的时候,编导和悲剧擦肩而过,重回苦戏的传统和大众的 趣味。
在导演把影像定位于纪实风格的前提下,指出悲剧和苦戏两个范畴的区别或许对我们 评价这部影片意义不大。还是换个角度看,这样的安排倒给出了另一种形式的大团圆结 局,始作俑者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叙事传统和接受心理!相比之下,胡最终失去小提琴的 情节带给人心理的冲击反倒不那么重要。
追求纪实风格的影像冲动,和潜层的传统叙事意识,这是《卡》片创作中的二律背反 ,前者代表着一种视听语言现代化的自觉,后者则显示出中国传统叙事仍然强大深刻的 惯性。由于后者,使得启用非职业演员不可能,同期录音难度过高也遭弃用,而人物、 线索、情节发展、高潮等经典叙事研究词语倒似乎更能自如地运用。与此同时,由于前 者,《卡》又放弃了主流故事片惯用的影像声音造型手法,放弃了对观影者心理的吸引 而要求其保持旁观冷静的态度。很明显,这两种导向背道而驰,以至于有的场景会不自 觉向某一端靠拢。胡为了学琴辞去了刚获得的工作,母子发生了争执,胡母离去,胡颓 然转过身来,背后高架桥上列车呼啸而过。这个镜头采用的表现手段回归主流故事片的 套路,反倒马上把信息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观影者。
之所以认为这种二律背反是结构性的,因为当下国产电影创作和生产甚至批评理论界 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像冲动和叙事意识两种力量拉扯的困扰。一方面,标榜影像成为传 媒舆论的时髦,另一方面,叙事能力低下导致国产电影无力挽回观众的局面仍然继续着 。一部影片的成败或许不足虑,作为整个产业,长时间面对困扰则相当危险。
即使把导演意图实现与否当作评判标准,我们至少要求这种意图明确:是艺术电影的 还是大众口味的?众所周知,二者不在一个层面上,艺术电影永远是少数精英分子的奢 侈品,大众口味的成功制作才能保证电影产业的运行。《卡》在标举艺术电影旗帜的圣 何塞电影节获奖其实意味着《卡》在西方评委眼里是纯粹的艺术电影,所以“美国非常 著名的影评人DENNIS HARVER在美国两大电影杂志之一的《VARIERY》上撰文对影片的评 论是,‘这是部好影片,可以在美国艺术电影院线放映。’”(注:来源:联和电影网 ,上海热线娱乐频道。)换句话说,《卡》不适合在主流电影院线放映。精心编剧,职 业演员阵容,加上骨子里十分传统的叙事意识,竟完成了一部纪实风格的艺术电影,个 中滋味实在难言。
很有趣的,这个二律背反并未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中。“在电影节的一个PARTY上,一 位德国制片人对中国同行说,他观看了影片后让他想起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偷自 行车的人》。”(注:来源:联和电影网,上海热线娱乐频道。)看来,中国现实题材影 片和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运动之间长久的、“美丽的”误会还将继续下去。不管多少 国人为此自豪骄傲,建立在东方主义误读基础上的西方学界的类比对于中国电影自身的 问题毫无补益。圣何塞的大奖不足为凭。
笔者丝毫无意揶揄艺术电影,也尊重艺术电影人的努力,只是想说,在弥合这一结构 性裂隙的问题上,中国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电影产业化的经济规律不会等待文化 融合完成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