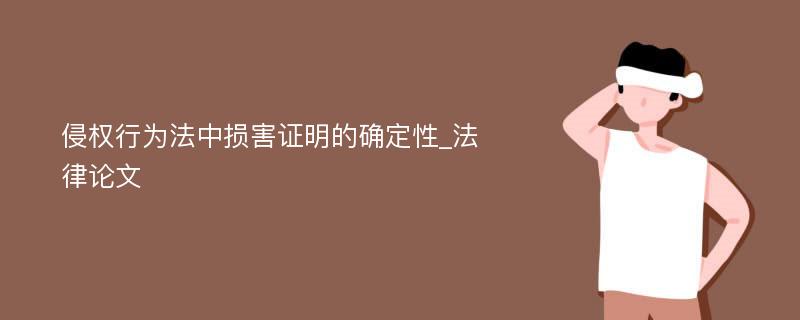
侵权法上损害证明的确定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不同的证明对象及其证明标准
在讨论侵权法上损害证明的确定性时,首先需要讨论的是,所要“证明的对象”是什么?根据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这里的证明对象有三种:损害的存在、损害的程度,以及赔偿的数额。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7条规定:“如果当事人对是否有损害、损害的数额以及应赔偿的利益额有争执,法院应考虑全部情况,经过自由心证,对此点做出判断。”其中,“是否有损害”即指“损害的存在”,“损害的数额”指“损害的程度”,而“应赔偿的利益额”是指“赔偿数额”。
(一)对损害存在的证明
在侵权法上,受害人能够从加害人处获得赔偿的前提之一是,他能够用具有确定性的证据证明损害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受害人因为不能以具有确定性的证据证实损害的存在而不能获赔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某商场发行空号奖券,致使所有的持券者都丧失了获得奖金的机会,但是,某一特定的持券者却难以证明,假如商场没有发行空号奖券,他本来可以中奖。又如,一个律师因过失而未在法定期间内代理其当事人起诉,致使当事人丧失了胜诉的机会,但是,当事人很难证明,如果该律师在法定期间起诉,他一定可以胜诉。
在英国,侵权诉讼中的原告必须基于盖然性权衡(balance of probability)③证明,他因被告的侵权行为而遭受了损失。因此,如果原告所受的损害既有可能由甲事件引起,因而归咎于被告,也有可能由乙事件引起,而法官认为只有30%的可能性是由甲事件造成了原告的伤害,那么,原告针对被告的主张就得不到支持。然而,如果法官认为原告的损害是由甲事件引起的可能性比由乙事件引起的可能性大,哪怕大一点点,该案就会被认定是由甲事件引起的,仿佛这就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实,而且,损害赔偿也不会因为原告的受伤有49%的可能性是乙事件单独造成的而有所减小。④
关于对损害存在的证明,美国的《第二次侵权法重述》⑤第912条下的评论a写道:“当某人试图就导致其人身伤害或有形财产损失的损害获得赔偿金时,他有责任证明,另一人侵犯了其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他蒙受了损害,并且,该另一人的行为是该损害的法律上的原因。因此,如果某人被另一人弄伤,后来在身体的某一部位出现了败血症,他试图就此疾病主张赔偿时,有义务证明这样的可能性大于不可能性:最初导致受伤的接触,是引起该疾病的实质性因素”。⑥
在美国伊利诺斯州上诉法院1932年审理的Chicago Coliseum Club v.Dempsey案⑦中,原告(甲)是一个组织拳击比赛的经纪人,乙是一个拳击手。根据双方签署的合同,原告将为乙和另一个拳击手安排一场拳击比赛。在原告尚未为组织此场比赛支出费用之前,由于被告(丙)的侵权行为导致了原告的违约。该法院判决说,原告只有证明了他本来可以安排这场比赛,且该比赛盈利的可能性大于不可能性,同时,能够为这一利润数额的估算提供一个合理的基础时,才可以要求该经纪人支付补偿性的损害赔偿金。
上述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了普遍的采纳。例如,在南非,一般的规则是,侵权诉讼中原告必须证明其损害的存在,且必须证明其成立的可能性高于50%。⑧
关于侵权法上损害存在的证明,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形成一致的倾向。总体来说,德国法院采用的标准是“充分地确定”(sufficiently certain)。也就是说,如果受害人不能以“近似确定的盖然性”(probability next to certainty)证明其损害,法院不会支持他的主张。⑨
而在比利时,损害存在的可能性,只需达到使法官不会认为情况是相反的程度;当这样的可能性已经得到证实时,尽管从理论上说,该“期待的损害”永远不会出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当事人的请求也可以得到支持。⑩
笔者认为,关于侵权法上损害存在的证明,英美法上的制度是更为可取的。首先,在大量的案件中,尽管被告的行为实际上导致了原告的损害,原告却无法用具有充分确定性的证据对损害的存在加以证明。其次,采用上述英美法的制度,并没有任意降低举证的标准,而只是在损害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可能性的情况下认定损害已经发生,兼顾了被告方的利益。再次,上述德国标准即使在大陆法系国家也没有得到普遍的仿效。上述比利时的制度与英美法上的制度实际上并无差异。
(二)对损害程度的证明
在许多情况下,侵权诉讼中对损害程度的证明,区别于对损害存在的证明。例如,在英国的H.West & Son Ltd.v.Shephard案(11)中,原告是一名已婚妇女,事故发生时她41岁。她在事故中遭受了严重的头部损伤,导致大脑萎缩、四肢瘫痪,而她的身体状况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医生预计她的存活期约剩5年的时间。有证据显示,她或许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状况,但她此时已经无法讲话。
在该案中,原告因被告的侵权行为而受到了伤害,作为“损害存在”的事实,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她还能存活多久?假定“便利生活的丧失”是可赔的,在已经不可能康复的情况下,她活得越久,蒙受的损害就会越严重。因此,损害的程度成为难以证明的问题。
在英国的早期,受害人要想获得“实质性损害赔偿金”(substantial damages),必须同时证明损害的事实及损害的程度。如果他不能证明其中的任何一点,他或者会败诉,或者,最多可获得名义性的赔偿金(nominal damages)。(12)在1825年的Dixon v.Deveridge案(13)和1853年的Twyman v.Knowles案(14)中,原告尽管证实了损害发生的事实,但未能提供有关损害的“量”的证据。结果,仅仅获得了名义性的赔偿金。
然而,英国法院后来意识到,如果不分情况地要求受害人以具有绝对确定性的证据去证明损失的确切量值,则会使受害人在大量案件中无法得到赔偿,特别是涉及未来损失的案件。(15)于是,1911年,在英国的审判史上,出现了关于此类问题的权威案例(16)Chaplin v.Hick案。(17)该案的判决改变了先前的理念,清楚地表明了一种新立场,并被沿用至今。在该案中,Vaughan Williams法官书写了如下著名判词:“损害赔偿金不能被确定性地估算的事实,并不能否定不当行为人支付赔偿金的必要性。”尽管该判决意见所谈的是赔偿额的证明问题,但也适用于损害程度的证明问题。
在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912条明确地写道:“由于他人的侵权行为而遭受损害的当事人,在且只有在,依侵权行为的性质和当时的情形所允许的确定性,证明了损害的程度以及能适当地弥补其损失的赔偿额后,才有权就该损失获得补偿性的损害赔偿金”。依此规定,涉及对损害程度的证明,原告须提起的证据的确定性是相对的,即,该确定性决定于“侵权行为的性质和当时的情形”。
如上所述,根据《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912条下的评论a,证明“损害的存在”所须的确定性,要达到“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可能性”的程度。(18)而关于证明“损害存在”的确定性与证明“损害程度的确定性之间的区别,《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912条下的评论a继续写道:“然而,法律并没有一般性地要求,受害人应当以相似的确定性证明,作为侵权行为的后果,他蒙受伤害的程度。人们期望,除非原告能够证明,伤害产生于受指控人的不当行为,而该证明应具有合理的确定性,否则,由此产生的责任不应被施加。人们还期望,有关损害的的证明,应在合理的限度内尽可能地确定。然而,人们更加期望的是,一个受到伤害的人,不能仅仅因为,他不能充分确定地证明其受到伤害的程度,就被剥夺获得实质性赔偿的权利”。(19)
《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912条的“范例16”(20)举了这样的例子:在一个根据报纸上的公众投票授予奖项的比赛中,甲是幸存的3个比赛选手之一。这3个比赛选手获得的票数大体上一致。为了玷污甲的名誉,另一个参赛选手的朋友乙使得甲被逮捕,从而使甲丧失了可能获得3 000美元奖金的机会。如果甲可获得该奖项不仅仅只是可能性(more than a mere possibility),(21)甲可从乙获得的赔偿金相当于他可能获得该奖项的机会的价值。在缺乏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这个机会的价值为1 000美元。(22)
在上述案件中,第一步要证明的是损害的事实。如果评审团认为,“甲可获得该奖项不仅仅只是可能性”,则这一事实得到了证明。第二步是对损害程度的证明。由于在该案中,侵害的是原告“未来的机会”,(23)该方的举证不可能达到充分确定的程度,故此种侵权的性质决定了对举证确定性的要求应适当放宽。最后,审理该案的法院依据原告获得该机会的概率,让原告得到了一定比例的赔偿。
关于法国的情况,法国学者Suzanne Galand-Carval指出:在法国,受害人必须同时证明其损失的存在和损失的程度。如果受害人不能证明其损失具有确定性,则无法获得救济。(24)但他指出:确定性明显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在主张未来损失时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如果要求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受害人根本不可能获得任何赔偿。在未来损失的证明方面,法国法甚至比英国法还要宽松。(25)
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7条规定,(26)法院在确定“损害的数额”时,应考虑全部情况,经自由心证,作出判断。德国学者U.Magnus就此评论说:当花费过高或过于困难时,法院可以对损失的存在及其数量进行估计。(27)
依照《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273条,如果原告证明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量确实存在不合理的困难,法官可以根据自己的心理确信决定损害赔偿额。流行的观点认为,适用第273条的条件是,原告能够证明损害的明显存在,但不能清楚地证明损害的具体程度。(28)
在荷兰,一般地说,法院需要获得损失发生或程度的证据以便计算损失的量值。但是,如果做出此种计算是不现实的,法院可予以估计。(29)
综上,关于对损害程度的证明,多数国家的法律所奉行的原则是一致的,即,受害人提供的证明,应具备案件的情况所允许的确定性。这里所指的案件情况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难以一一列举,但最重要的是,受害人蒙受损害的性质和由此决定的让受害人进行充分举证的现实可能性。例如,在英国法上,对诽谤造成的损害是可推定的,即,不加证明即可认定的。(30)这是因为,当诽谤的事实成立时,损害必然是存在的,另一方面,让受害人确切地证明其蒙受损害的程度是不可能做到的。又如,当损害的量值很低而举证的成本过高时,要求进行充分举证是脱离实际的。
(三)对赔偿额的证明
在侵权诉讼中,对赔偿额的证明,既不同于“对损害的在”的证明,又不同于“对损害的度”的证明。例如在上文提到的英国案例——H.West & Son Ltd.v.Shephard案31(31)中,原告在事故中遭受了严重的头部损伤,导致大脑萎缩、四肢瘫痪,医生预计她的存活期仅剩约5年的时间。从这一估计的存活时间,可以估算出损害的程度,例如“丧失生活便利”的时间,需要他人护理的时间,等等。而原告有权获得的赔偿额,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计算出。
美国的《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912条的“范例14”(32)包含了这样的情况:甲所从事制造业每年可获得的净利润大约为50 000美元。作为竞争者的乙采用了违法的不公平竞争手段,使得迄今为止一直在增长的对甲产品的需求量开始下降。造成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新的竞争者加入到了竞争行列之中。因此,对乙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额,在计算上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在这样的案件中,“损害的程度”表现为甲因乙的侵权行为而丧失的市场份额,而对损失额的证明成为该案争议的焦点。
如上文所述,在英国,根据1911年的Chaplin v.Hick案的判决,(33)“损害赔偿金不能被确定性地估算的事实,并不能否定不当行为人支付赔偿金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在受害人不能就其蒙受损失的具体金额提供具有确定性证据的情况下,法官可以依其裁量权对该数额进行确定或者调整。
根据《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912条,对于赔偿的数额,受害人的证明义务是,“依侵权行为的性质和当时的情形所允许的确定性”证明“能适当地弥补其损失的赔偿额”。(34)而美国法院在原则上要求,受害人应当“为这一利润数额的估算提供一个合理的基础”。(35)
《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912条“范例6”(36)的案例事实为:甲因其过失而伤害了内科医生乙,乙因此而不能照料他的病人。甲除了能证明他曾经在一个小城镇行医8年外,没有提交任何有关其收入的证明。针对乙的收入损失,他仅能获得名义性的赔偿金。
该《重述》“范例7”(37)的基本事实与前例相同,但乙能够提交证据,表明他在受到伤害之前的两年内的平均年收入是20 000美元,而且在他不能履行职务期间,他雇佣了一个替代者,每年花费10 000美元,因此而使得他诊所收入减少至每年7 500美元。乙有权根据这些证据获得该项收入损失的赔偿。
以上两个例子是以美国法院判决的真实案例为基础的。(38)这两个案例进一步表明,涉及赔偿金的举证,法院并不要求受害人提供精确的数字,但要“为这一利润数额的估算提供一个合理的基础”。
《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912条“范例13”的情节如下:甲与乙签订了一个由甲将乙生产的产品打入墨西哥市场的合同。合同规定中关于计算甲的佣金的方式是:在甲指定的当地代理商依该合同规定的价格将货物售出后,甲可获得代理商得到的佣金的10%。日后,由于丙的欺诈行为,甲未能在当地找到代理商,致使该合同未能得到履行,乙因此撤销了该合同。如果甲能够证明,在丙的侵权行为之前,甲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分销机构,这些分销机构在每个月里已经依合同价格售出了一定量的货物,墨西哥其他地区的情况与那些已经取得业绩的地区的情况实质上是一样的,因而可以合理地期望,其他的分销商也能实现相似的销售额,甲就有权以这些销售额为依据获得补偿性的赔偿金。(39)
在“范例13”中,甲是就预期的利润提出索赔的,其数额是无法精确地计算出来的。在此情况下,法院依据甲提供的证据(包括已经建立的销售网络、已经取得的销售业绩、与其他待开发区域情况的可比性,等等)对赔偿额进行了推测。这些证据所构成的证明效果的确定性是相对的,但从合理补偿受害人的目的出发,已经是充分的了。
在欧洲大陆法系各国,普遍的情况是,关于赔偿额的证明,法律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如上文所述,依照《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7条,法院对于“应赔偿的利益额”有权在考虑全部情况的基础上经过自由心证做出判断。
在比利时,当计算赔偿数额时,尽管法官必须明确地估算损失是否存在以及损失的数额,但总会存在一定灵活变动的余地,从而使法官可以将众多的因素考虑在内。(40)
在奥地利,涉及利润损失的计算,《奥地利民法典》第1293条并不要求原告提供其本来可获得利润的充分证据,他只须证明,按照事物通常的发展过程,他原本是可以获得利润的。(41)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奥地利民法典》第1324条的规定,赔偿水平的高低与被告的过错程度密切相关:如果加害人仅有轻微的过失,他只须就实际发生的损失(actual loss)做出赔偿,对利润损失和非实质性的损失(immaterial damage)无须做出赔偿。而如果加害人有重大过失或者故意,他就要对全部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包括非金钱损失。不过,即使某一损失仅仅是非实质性的,且无论加害人的过错程度如何,加害人都须就受害人蒙受的疼痛和痛苦负赔偿责任。(42)
需要指出的是,第1324条做出的这种区分被最高法院在1999年的一项判决削弱了。该法院说,当原告本来可以获得利润时,利润的损失是一种实际发生的损失。(43)
在希腊的法律学说和案例中,对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并不是根据其性质分为已发生的损失或期待利润的损失。相反,如果原告可以完成相关的举证,这两类损失均可被平等地视为可赔的损失,从而得到补偿。不过,相关的证明规则有所不同,在涉及第二种损失,即期待利润损失的案件中,对损失的证明具有“合理的可能性”就足够了。(44)
荷兰法院对赔偿金的给予拥有较宽的自由裁量范围。实体法上的许多条款为法院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比如涉及赔偿金的计算问题和非物质性损失的赔偿问题。进一步说,法院在确定赔偿金的类型和数量时不受一般证据法规则的约束。不过理所当然的是,涉及这些问题,法院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证明。然而,对损害的证明不需要是确定的。一般来说,只要法院认为损害的发生看起来可能,就能满足条件。(45)
从上文的介绍可以看出,在各国法律规定中,有关“损害程度的证明”与有关“赔偿额的证明”有时是不分的。这是因为,在有的情况下,损害程度问题与赔偿额问题是难以区分的。例如,在前述美国的Chicago Coliseum Club v.Demp的案中,(46)原告声称,原告因被告的侵权行为而丧失了一次组织拳击比赛的商机。此时,他须证明的本来可以获得的利润额,既表明了损害的程度,又表明了他有权请求的赔偿额。可是,在许多情况下,或者严格地从逻辑上讲,这两种证明是有区别的:在损害程度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对赔偿金的计算仍然是一种独立的需要另行解决的问题。
根据上文对各国法相关制度的介绍,涉及“赔偿额的证明”,许多国家的法律表现出了更加灵活、赋予法官更多裁量权的倾向。在美国,涉及赔偿金的举证,法院并不要求受害人提供精确的数字,但要“为这一利润数额的估算提供一个合理的基础”。后者是一种较严的要求。这两种解决方案各有利弊。从上文对美国几个案例的介绍可知,在后一种制度下,受害人的证明达不到该要求,法官就可能驳回起诉。因此在美国,诉讼通常是由律师代理的。而在前一种制度下,即使受害人的证明达不到一定的要求,法官仍有权作灵活的裁量。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采纳前一种制度恐怕是更为适当的。笔者认为,在这里,法官应考虑的情况特别包括:受害人容易举证而未举证的情况应有别于其不能或难以举证的情况;加害人故意侵权或有重大过失的情况,应有别于其仅有轻微过失的情况;损害程度严重的情况应有别于仅存在轻微损害的情况。
二、在证明上缺乏确定性但可以获赔的损害
在侵权诉讼中,如果原告有可能提出确切的证据证明其所受到的伤害,法院当然有理由期待证据的较高程度的确定性,比如,原告的索赔所针对的,是从侵权行为发生到审判时这一期间,已经发生的收入损失。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当做出这种证明的可能性不存在时,原告提出的索赔也应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分别阐述:
(一)推定的损害(presumed damage)
在英国的侵权法上,存在着一般损害(general damage)与特殊损害(special damage)的划分。“一般损害赔偿金是对一般损害的补偿……一般损害是指法律从被诉的过错行为中推定出的,因而无须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中明确提出的损害”。(47)而对特别损害,不适用关于一般损害的法律推定,原告只有在其诉讼请求中明确证明了这些损害,才能获得针对该特殊损害的损害补偿金。
一般损害的案件,常常涉及干扰原告与他人关系的情况。比如,原告因遭到被告的诽谤而被第三人拒绝进入其家中,或者,在对原告的诽谤发生之后,其他人停止了与原告的商业或社会关系。此时,对原告蒙受的损失是难以估算的。(48)在1824年的Tripp v.Thomas案(49)中,原告在受到诽谤之后无法证明其受到了实际损害,但仍得到了40英镑的赔偿金,因为陪审团认为,在此种情况下,仅仅授予原告名义性的赔偿金是说不过去的。
一般损害与英国法认可的另一种侵权行为——“自身可诉性”(actionable per se)侵权行为(又称“诉因侵权行为”)(50)所导致的损害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后一类案件中,侵害本身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损害形态,无需由原告进一步证明存在实际的或有形的损害,并且,只要存在侵害的事实就会导致赔偿后果。(51)在1936年的Nicholls v.Ely Beet Sugar Factory Ltd.案(52)中,地方法院判决说:“之所以能够支持一个无法证明实际损害的诉讼,乃是依赖于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原则,即,当你的权利受到干涉时,法律就推定你有损害”。
在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904条(53)(关于“一般损害赔偿金和特殊损害赔偿金”)写道:“(1)‘一般损害赔偿金’是针对某一损害的补偿性的损害赔偿金,该损害如此频繁地产生于该作为诉讼基础的侵权行为中,以至于该损害的存在通常会被预见,因而无需证明即可认定其存在。(2)‘特殊损害赔偿金’所针对的,是会判给一般损害赔偿金的损害之外的损害”。
《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569条(关于“不需证明特殊损害的责任—书面诽谤”)规定:“某人虚假地发布毁损另一人名誉的事项,而其方式使该发布成为诽谤的,须对该另一人承担责任,尽管该发布并未造成特殊的损害”。
第570条(关于“不需证明特殊损害的责任——口头诽谤”)规定:“某人发布毁损另一人名誉的事项,而其方式使该发布成为口头诽谤的,须对该另一人承担责任,尽管该发布并未造成特殊的损害,只要该发布对该他人造成了以下后果:(a)触犯刑律,如第571条所述;(b)令人厌憎的疾病,如第572条所述;(c)与其生意、行业、职业或职位不相称的事项,如第573条所述;或者(d)严重的不当性行为,如第574条所述”。
由上文可见,如果从一种侵权行为可以当然地推导出损害的存在,且受害人对损害的程度是难以证明的,那么,尽管受害人无法确定地证明损害的量值,也应当让加害人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
(二)非金钱损失(non-pecuniary loss)
关于非金钱损失,英国法官Halsbury勋爵在The Mediana案(54)中作了如下阐述:即使此种损害不是被推定的,而是实际地发生的,也很难用数学上的准确性进行估算。他又说:“人们怎么能用可计量的金钱数额来衡量疼痛与痛苦(pain and suffering)呢?当一个人因事故而蒙受疼痛与痛苦时,任何人都无法主张,你能通过数学计算证实,能反映此种损失的确切金额。但是法律承认,此种损失是可以提出的并可据此判给赔偿金”。
以对“丧失便利生活”的赔偿为例,尽管证明此类损失的数量没有丝毫的确定性可言,但大多数法院都不拒绝对它的赔偿。在Wise v.Kaye案(55)中,原告自事故发生之时起便不省人事,丧失了除生命之外的所有生理功能,变成了植物人。上诉法院的大部分法官同意给予受害人15 000英镑,作为对其丧失便利生活条件的损失赔偿。
在前述英国的H.West & Son Ltd v.Shephard案(56)中,原告受伤后四肢瘫痪,而证据显示,她或许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状况,但她此时已经无法讲话。英国上议院的多数法官判决,给予其17 500英镑作为对其丧失便利生活的赔偿。正如法官莫里Morris勋爵所言:“受害人不省人事的事实并不能消除其被剥夺了享受正常生活及其乐趣的这一现实,尽管这一现实不可避免地是由某些身体损伤所引起的”。
在美国,关于非金钱损失,《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912条的评注b(关于“对身体、情感、声誉的伤害”)首先指出了其证明上的不确定性:金钱和这类损害之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留下一处伤疤或丧失听力是不能用市场价计量的,因为在计量时不可能去想,有人愿意以受到伤害为代价以换取某一赔偿额。
该条的“评注b”继而认可了合理人的判断是应被采用的衡量标准:在为决定此种赔偿额而可行使的裁量权中,惟一的标准是合理人为了实现公平的赔偿而做出的估价。
那么,一个合理人应当如何判断呢?该条的“评注b”进一步指出:在这些案件中,事实的裁判者(57)会适当地就某些损害给予实质性的赔偿金,而该损害是指通常产生于此种侵权伤害的损害,甚至在没有可证明其存在的特定证据的情况下也会给予,比如殴打造成疼痛的情况,或者,由伤疤导致羞辱感的情况。
依照该评注,判决金额可能因案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差异。该评注说:证明蒙受的损害比通常会发生的损害多或少的证据,也是可接受的。考虑得最多的是这样一些因素:疼痛或羞辱的强烈程度,其实际延续的期间或可能延续的时间,以及其可以预期的后果。
在非金钱损失的估算方面,法国法中并没有特殊的规则。法国法学家Suzanne Galand-Carval指出:很明显的是,不论采用何种方式,此种估算通常都会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而且在实践中,一直以来都有一种看法,那就是,解决这种非理性的最好方法就是把问题留给法官,用“法官的智慧”来解决。然而,如今占主流的观点是,在非金钱损失的估算方面,还是应该让某些理性因素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人身伤害案件中。而作为此种努力的体现,法院已经制定出一套供内部使用的“司法价目表”。(58)
这方面的例子是,昏迷不醒的受害者的损失应该被客观地评估。这意味着,他必须和清醒时一样,获得相同的赔偿,并且,他有权就丧失便利生活条件的损失和生理疼痛的损害获得赔偿。(59)
德国的情况是,由于在将非金钱损失折算成金钱时法官必须运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明确表示了他们对非金钱损失进行金钱赔偿的不赞同。(60)于是,加入《德国民法典》第253条的规定是:当损害为非物质上的损害时,仅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形下,始得要求以金钱赔偿损害。所以,德国的成文法不倾向于对非物质损失规定金钱赔偿。但是,《德国民法典》第847条(61)就此规定了例外情况,由于人身伤害而引起的疼痛与痛苦可以获得损害赔偿。
然而,根据德国的法学理论,非金钱损失是一种不能用精确的、客观的、以市场条件为导向的金钱来进行计算的损失,对它的估算不存在确定而便捷的规则。对因人身伤害引起的疼痛和痛苦的赔偿,在估算时必须将与案件相关的所有情况考虑在内,主要的因素是疼痛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以及伤害的长期后果,也包括年龄、受害者的个人情况以及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甚至双方的经济状况或者保险状况都会起作用。(62)进一步说,即使受害人已失去了一切能力且不会再感觉到任何痛苦,债务人也应支付可观的有关疼痛和痛苦的损害赔偿金。(63)
比利时最高法院始终明确地将“精神损害”作为一种可获偿的损害。在父母因子女受到伤害而感到疼痛和痛苦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对此种“精神损害”请求作了如下描述:精神损害的索赔请求,旨在补偿疼痛、悲痛或者其他形式的精神苦难。因此,不仅直接受害者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其他任何因“间接地”遭到损失的人也可以提出此种请求,例如,他或她的亲戚。受害者个人的过失,将会影响其亲属以继承人的身份通过起诉行使其个人的权利,以及影响受害人对个人损失的诉求。(64)
根据《奥地利民法典》第1323条的规定,如果被告的行为具有重大过失或者故意,就必须对原告受到的非金钱损害进行赔偿。但该法典第1325条又规定,在人身伤害案件中,侵权行为人必须对受害人的疼痛和痛苦进行赔偿,即使该侵权行为人只存在轻微的过失。
做出上述规定的理由在于人身的不可侵犯性,并且,对于伤害的严重性,是可以用客观的标准进行判断的。另一方面,在财产权受到侵害的案件中(《奥地利民法典》第1331条),个人的情感价值只有在侵权行为人具有特别的主观故意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赔偿。这样规定的原因是,此类非物质性利益的重要性相对较低,以及缺乏客观的证据来证明伤害的程度。(65)因此,在奥地利,是否对非金钱损失进行金钱赔偿,取决于法律利益的位阶,以及表明损害程度的客观证据的存在与否。
奥地利最高法院近期创制的规则表明,受害人在昏迷不醒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非物质性损害赔偿。该规则的依据是,即使当事人感觉不到疼痛,他也有权以其人身权遭到严重损害为由要求损害赔偿。赔偿数额应与遭受同样身体伤害的清醒的受害人一致。最高法院就此判决的赔偿额已达到了140万和150万奥地利先令。(66)
综上所述,“非金钱损失”是一种难以用金钱加以计量的损失。然而各国法律普遍奉行的原则是,此种损失尽管难以确定地加以证明,也应当给予赔偿。不过,对于可赔的“非金钱损失”的种类,各国法律是有限定的。(67)
在赔偿额的计算上,有的国家将这一问题交给法官或“事实的裁判者”去裁量,有的则通过制定统一的“价目表”来解决这类问题。
这一领域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受害人在受伤之后丧失了意志,因而也就没有疼痛和痛苦可言,加害人还要不要做出赔偿。对此,一些国家的法律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三)未来的收入损失
在人身伤害案件中,关于未来收入损失的诉讼请求每时每刻都会发生。有英国学者指出,有两个重要因素降低了估算此类损失的确切性:第一,原告的能力丧失可持续的确切时间的不确定性;第二,如果没有被告的侵权行为所导致的伤害,原告在未来所能赚取的金钱数额的不确定性。(68)以U.Magnus教授主编《侵权法的统一:损害赔偿》一书中的第8个调查范例(69)为研究对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此种情况。
这个假定的供讨论的范例的情节是:乙的过失行为使得一位20岁的化学系学生甲大脑严重受伤。其结果是,甲在未来只能从事临时性的劣等工作。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1)计算甲蒙受的损害的依据是什么?(2)如果甲是一个低收入家庭的6岁小孩,且至今只展现出一般的天赋,那么计算损失的依据又是哪些?(3)如果乙的过失使甲成为植物人,甲能得到的损害赔偿又是什么?
根据该书编写者的设计,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没有将由社会保障系统负担的医疗费用考虑在内。
以下是各国学者依据其本国的法律或法学理论针对上述问题做出的评论:
英国学者W.V.Horton Rogers依据英国法对此案情作出的评论是:这类案件处于“收入损失”(loss of earnings)和“收入能力丧失”(loss of earning capacity)这两个领域之间。
关于第一个问题,该案中的受害人如果是一个学生,因为有此类毕业生一般收入水平的证据,损失的计算不会有什么困难。有些这样的案件就是依据受害人从事的事业前景解决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在英国上诉法院1992年审理的Cassel v.Rierside HA案(70)中,原告刚一出生就受到了伤害。考虑到其优越的家庭境况,该法院以国民的平均工资乘以2.5倍作为其未来收入损失的依据。因此在英国,对劣等工作的收入情况当然是在考虑范围之内的。
关于第三个问题,当原告成为植物人时,假定原告的寿命不会减少,对其收入损失的赔偿额也不会减少。然而,这样的原告还有权就“非金钱损失”(non-pecuniary)获得实质性赔偿金。目前,对大脑严重受损导致的瘫痪,已经形成了赔偿额大致相同的价目表。(71)
美国学者Gary Schwartz在分析“大脑受损案”时做出的评论是:在这类案件中,对甲蒙受损害的评估是由陪审团完成的。其任务是对甲未来的收入作最准确的估计(best estimate)。如果甲的年龄是20岁,他可能已经具有关于其教育背景和能力等方面的可供参考的记录。陪审团在评估其损害的程度时可予以考虑。然而,在评估甲的诉讼请求的合理性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院是选择“合理确定”原则(reasonable certainty)还是“可能大于不可能”原则(more-likely-than-not)作为相关的证据标准。(72)如果甲只有6岁,法院很可能会采用“合理确定”原则,因而基于普通美国人一生的平均收入来进行估算,而不可能采用“可能大于不可能”原则,即依据特定家庭的收入来估算。因为后一种作法可能会导致过分的阶级或种族歧视风险。(73)
《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912条评注d(关于“收入(earnings)或利润(profits)损失”)阐述道:对收入的丧失或赚钱能力的损害要求获得赔偿时,受害人必须提供证据,使事实的裁判者确信:其相当数额的收入已经丧失,或者,他的赚取收入的能力已经在极大的程度上被损害了。在进行举证时,他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在损害之前,他获得收入的数量,或者,他有能力赚钱的数量;至少,他提供的证据能够具有这样的导向性,在其主张的收入损失发生的期间,他本来是可以赚取一些收入的。
在法国,对于此种情况导致的收入损失,应根据受害者的年龄而有所不同。如果甲是一个20岁的化学系学生,他可以主张,他实质上被剥夺了拥有一份回报丰厚的工作的机会。如果他提供的证据令人信服,他可获得的赔偿为:他今后可能得到的薪水与未受伤时原本可获得的薪水之差额的一定百分比。
如果甲是一个6岁儿童,他就得不到任何赔偿。这种苛刻的解决方式的正当性,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受害者年龄幼小,无法估计其职业前景。(74)
在德国,对这类案件中的收入损失的计算是很困难的。法庭必须估计受害者获得收入的前景,因此必须考虑个案中所有的相关情况。
对于上述范例,法院必须评价甲能否成功完成学业并找到一份化学家从事的工作的前景,进而估算出甲可能获得的收入。甲作为化学家可能获得的收入和甲受伤后实际可能获得的收入之间的差额,就是甲有权主张的损失。因此,甲可以主张该差额的分期支付的损害赔偿金。但是,该损害赔偿金只能从甲可能完成学业之日起计算。
对年幼儿童的未来收入损失更加难以估算。德国法院在此类案件中假设,该儿童可能获得与其父母相同水平的收入,而以其父母(特别是父亲)的职业和收入作为参照。但是,法院只能对儿童可能的在学业结束之后的收入损失判决分期支付的损害赔偿金。(75)
在奥地利,对于这个案件,侵权行为人须赔偿甲的收入损失。该损失的计算建立在甲原本可能成为化学家而获得的收入的基础上。其中的原则是,应根据一般事件的发展过程进行估算。在此必须考虑的一种因素是,甲只能在他有可能获得收入之后再提起诉讼,例如,在其本来可以完成其学业之后。
上述赔偿只能建立在概率判断的基础上。在此过程中,最高法院将考虑其父母的职业和收入。(76)
从上文的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未来的收入损失是一种在证明上难以实现其确定性的损失。从各国学者对“大脑受损案”的分析可以看出:首先,各国法律普遍认为,对受害人未来的收入损失应当给予赔偿。其次,对此种预期的实际收入和预期的应得收入都应尽可能准确的估算,但容许存在推测的因素。再次,在原则上,赔偿的数额为其受伤后实际可能获得的收入与如果不受伤其本应获得的可能收入之间的差额。第四,当受害人是一个儿童时,各国法的分歧较大。法国法认为,在此情况下,对其未来损失的计算是缺乏依据的,故不应支持原告在此方面的请求。根据英国、德国和奥地利的法律,可以考虑受伤儿童的家庭背景情况。而美国法认为,为了避免过分的阶级或种族歧视,不应考虑受伤儿童的不同家庭状况。(77)
(四)未来的机会损失
假如某人可以证明,如果不是另一人的侵权行为,他本来可以通过一次交易获得利益,他应当有权就其遭受的损失获得全部的赔偿。然而,在很多案件中,受害人并不可能以具有确定性的证据去证明此种事实。这样的情形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律师因过失未在法定期间内代理当事人起诉,致使当事人丧失了胜诉的机会,但是,当事人很难证明,如果律师在法定期间起诉,他一定可以胜诉。然而,这种举证上的困难并不能当然地剥夺受害人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正如英国法官Vaughan Williams在前述英国Chaplin v.Hick案(78)中所说:我承认,关于受害人能否赢得奖牌,其所依赖的事实表现出了不确定性。这使损害赔偿金的计算不仅变得困难,而且不能以具有确定性的、准确的方式做出,但是,我惟一要强调的是,应该摒弃这样的观念:因为达不到精确性,陪审团就不能在损害赔偿金的估算上发挥作用。这一判例虽然是一个合同法上的案例,但它的规则同样适用于侵权法。(79)
对于机会损失,英国法上的原则是:法律可以限制性地对此类损失提供救济。在1913年的The Empress of Britain案(80)中,原告是一艘船的承租人,他与出租人签订了一份有效期为7年的租船合同,而出租人在任何一年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取消合同。在合同生效后的第二年,由于被告的侵权行为,这艘船沉没在海上。原告就其在剩余的租期内的利润损失要求被告给予赔偿。法院判决,在估算有关该利润损失的赔偿金时,合同的7年有效期和其中所有的偶然性都应被考虑在内。
关于决定机会损失是否具有确定性的标准,英国法院在关于Mallett v.McMonagle案(81)和其他案件的判决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Diplock法官在Mallett v.McMonagle案中说:在基于将来会发生什么或本来会发生什么的看法而估算损害赔偿金时,法院的作用与其在决定过去发生过什么的民事诉讼中的一般性作用是相反的。在决定过去发生过什么时,法院依据的是“盖然性权衡”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某事发生的可能性比其未发生的可能性大,它即被当作是确定的。但是,在基于将来会发生什么或本来会发生什么(如果某事件没有发生)的看法而估算损害赔偿金时,法院必须估计该特定事件将发生或本来会发生的机会,从而折射在损害赔偿金的数量上,不管它们是多于还是少于50%。
关于机会损失证明标准的适用范围。在Allied Maples v.Simmons & Simmons案(82)中,Stuart-Smith法官在其判决意见中将机会损失与须基于盖然性权衡证明的损失区分开来。他将案件情况分为三种类型:(1)被告的过失由积极的行为或不当行为构成,问题起因于某一历史事实。此时,基于盖然性权衡的举证标准应当被采用。(2)被告的过失由不作为构成,问题起因不是基于某一历史事实,而是基于对这样一种假定问题的回答:如果没有被告的过失,原告本来会如何做?此时,原告本来会如何反应,仍决定于在盖然性权衡基础上获得的证据。(3)原告的损失依赖于某一第三人的假设行为,不管该行为是附属于原告的行为的还是独立于它的。此时,原告只须证明,他本来有实质性的机会让该第三人以某种方式行事从而使原告受益。(83)Stuart-Smith法官的论述将机会损失的适用限定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原告是否受到损害取决于第三方可能采取的行为或做出的决定。
在1995年的Spring v.Guardian Assurance案(84)中,被告因为过失而在原告向第三方递交的工作申请书中写错了联系人。法院说,我们无法确定如果第三方获得了准确的联系人信息,他是否就会雇用原告。但是,“一旦一项责任成立并且被告的过失被证明了,原告只需证明由于该过失他丧失了一个被雇用的合理的可能性(这个机会必须经过评估)……他不必证明若非是联系人信息的错误,第三方一定会雇用他。”
根据澳大利亚法院的判决,在侵权导致商业机会丧失的案件中,允许受害人通过证明盈利的几率而获得相应比例的赔偿金。比如在1994年的Sellars v.Adelaide Petroleum案(85)中,原告(甲公司)本打算与第三人签订出售公司股份的合同,但由于被告的代理人提供了虚假的信息,表示愿意以更优越条件购买该股份,甲公司决定不再与第三人继续洽谈该事宜。在原告与被告的交易失败后,第三人撤回了先前的要约,仅愿意以较低的价格成交。原告以被告作了不真实表示致使其丧失了与他人以更优惠的条件缔约的商业机会为由向法院起诉。法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缔约并获得经济利益的可能性为40%,因而判决被告对该机会的丧失承担赔偿责任。
南非的情况是,由于未来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未来损失的臆测性,法律并不要求原告必须证明他在将来一定会蒙受损失。需要原告证明的是,他必须以超过50%的确定性证明某一特定量的损失将以某一特定几率的可能性发生(例如40%)。在符合这些要求的情况下,此种比例的赔偿金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86)
关于美国的情况,《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912条的注释e(87)涉及到“未来损害的赔偿金”(damages for future harm)。其中说:“当某一受害人试图就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害获得补偿时,他有权基于这样的理由获得赔偿:某一种或另一种损害很可能会发生,与此同时,该损害一旦发生很有可能是严重的”。举例来说,如果原告是一些人中的一员,假如没有被告的不当行为,其中的一个人本来可以获取利益,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哪个人将成为最终的获益者,那么,为了获得赔偿金,原告就有责任证明该利益将由其中的哪一个人获得。
假如原告能够证明,如果没有被告的不当行为,他本来具有实质性的和可计量的机会(substantial and measurable chance)来获得利润,而不会有损失利润的机会,损害的确定性要求便被满足了。损害赔偿金应当建立在受害人本来可能产生的利益的数量和可以获得该利益的机会的基础之上,这种情况区别于亏损与盈利都具有实质机会的情况。然而,当一种不可转让的权利被侵犯,且情况表明,即使原告行使了该权利,也不会产生利益时,原告便无权获得实质性损害赔偿金。(88)
由于机会损失具有的不确定的特征,对它的适用范围是颇具争议的。以商业机会损失为例,《第二次侵权法重述》912条评注e中的“范例8”包含了这样的例子:原告是一个拳击运动的经纪人。原告主张,由于被告的侵权行为,他失去了组织一场拳击比赛的机会。在此情况下,甲只有证明他本来可以安排这场比赛,且该比赛会盈利的可能性大于不可能性,同时,可以给这一利润数额的估算提供一个合理的基础,才可请求被告支付补偿性的损害赔偿金。这表明,在商业机会损失的案件中,美国法原则上并不承认受害人能通过证明盈利的几率而获得相应比例的赔偿金。(89)
根据《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的注释d,(90)在无形权利被侵犯的案件中,例如商业干扰的案例,受害人至少应该证明该权利是有价值的。因此,如果某人的侵权使得另一人不能开始或继续进行一种商业活动,或开始某一特定的交易,而此种商业活动或交易可能获得利益也可能亏损,此时,受害人若想获得补偿性的赔偿金,就应该证明该活动或交易是可以或可能赢利的,而他赢利的机会被破坏了。然而,尽管受害人有责任以具有公平程度确定性的证据证明,其商业活动或交易原来是盈利的,或本来是有利可图的,但是,他能否确切地证明他本来可以获得的利润的数量或被告引起的损害的数量,对于他获得实质性的赔偿金并不是至关重要的。惟一重要的是,他能够出具在当时情况下可能被合理期望的可用证据。(91)
在前述《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912条的“范例14”(92)中,甲所从事的制造业每年可获得的净利润约为50 000美元。由于乙的不公平竞争,对甲的产品的需求量开始下降。造成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是,新的竞争者加入到了竞争行列之中。因此,对乙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额,在计算上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尽管如此,美国法院依然判决,甲有权根据可合理利用的事实数据获得补偿性的赔偿金。(93)
对于一项新的商业活动,人们更容易怀疑它盈利的可能性。对于此种商业活动,美国法院一般并不愿意就其利润损失判决赔偿金。否认原告请求的传统理由是:新商业活动缺乏以往的可获盈利的证据,或者,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在因果关系上过于遥远,或者,原告主张的损失过于模糊和具有偶然性。但是,近来美国各州的判例情况表明,这种习惯性做法正在发生转变。
在德克萨斯州的Helena Chemical Co.v.Wilkins案(94)中,最高法院维持了初审法院就新商业活动的利润损失给予赔偿金的判决,并且指出:过去的利润记录加上其它的事实与条件,当然可以满足有关损害后果确定性的要求。但是,仅仅缺乏获取利润的历史这一事实,并不能排除一个新商业活动在将来获取利润的可能性。其它的客观性事实,比如,将来的订单,也可以被用来证明利润的丧失;事实上,对于受害人来说,重要的不是精确地计算预期利润,而是能够出具客观的数据,证明其损失后果。
在佛罗里达州的Air Caledonie Int.Inc.v.AAR Parts Trading Inc.案(95)中,法院认为,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不管原告是否有盈利的历史记录,企业只要能够证明以下事实,就可以获得丧失利润的损害赔偿金:A、被告的行为造成了原告的损害;B、有一些标准可以确定原告的损害量。
在法国,Suzanne Galand-Carval指出,在未来损失的证明方面,法国法比英国法还要宽松,比如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不会因“偶发事件发生之可能性”而相应地降低。(96)
德国学者U.Magnus说,涉及到未来损失,德国法律存在一个例外:《德国民法典》第252条(97)的规定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即,受害人如果证明了盖然性,即使未达到确定性,就满足了可能产生利润的举证责任。(98)这样的规则显然也适用于机会损失。
在比利时,若要使未来损失获得赔偿,受害人须证明,该损失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确定的)情形通常的后果,或者是该情形的发展,或者是该情形的结果,或者是该情形的完结或重现。
进一步说,在计算有关未来损失的赔偿额时,所遵循的是“衡平与善”(ex aequo et bono)(99)的原则,(100)即,法官在决定有关未来损失的赔偿额时,可以视案件的具体情况,为实现公平的结果而做出灵活的裁量。
此外,仅仅是对未来可能有损失存在担心尚不能构成赔偿的基础,这种忧虑还必须伴有实际的(可获赔的)不利情况,特别是,如果未来损失的威胁足够严重。(101)
在希腊,《民法典》第298条第2款规定,只要原告能够证明,在特定情况下,特别是考虑了已经采取的准备措施,根据事物的通常发展过程,其本可获得的利润减少了,就可以对此种利润损失要求给予支持。(102)
如上文所述,(103)在荷兰,一般的原则是,法院需要获得损失发生或程度的证据以便计算损失的量值。但是,如果做出此种计算是不现实的,法院可予以估计。对未来损失也适用这样的规则。
综上所述,对于侵权导致机会丧失的情况,各国法律普遍认为,当某种机会是一种很可能发生的机会时,或者说,根据事物的通常发展过程,一种机会是存在的时,对该机会的损失导致的损害应当给予赔偿。问题在于,如果受害人不能证明某种机会本来是很可能发生的,但能够证明该机会原本有一定的可能性发生,是否允许受害人通过证明获取该机会的几率而获得相应比例的赔偿金。对此,英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的法律倾向于肯定。
笔者认为,英国和澳大利亚制度值得仿效。首先,该制度适当地顾全了受害人的利益。其次,此种法律有利于防止加害人通过实施侵权行为而获得利益,因为对机会损失的证明越困难,因剥夺他人机会而承担责任的可能性越小。
进一步说,法官在决定某种未来的机会损失应否赔偿时,应有权运用公平和诚信原则作通盘的考量,其中应特别考虑加害人是否有恶意侵权的情节,比如,通过干扰受害人与他人的合同关系而谋取商业利益的情况。
三、在我国构建相关制度的建议
(一)概述
迄今为止,关于侵权损害证明的确定性,我国法律尚未形成相关的制度。同时,在这一领域制定相关规则的必要性却日益显现。
以侵权导致的人身伤害赔偿为例,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19条,(104)当公民的身体受到伤害时,赔偿的范围仅限于由此导致的财产损害。2004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制定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105)中规定:在人身伤害案件中,对公民的“非金钱损失”也应给予保护。《解释》的第1条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当人身伤害导致的“非金钱损失”成为侵权法的保护对象时,其证明如何做到具有确定性,成为我国起草侵权法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如上文所述,“非金钱损失”是难以用具有确定性的证据加以证明的。(106)
《解释》的发布也引发了对“未来损失”的计算问题。依照《解释》的第19条,对于医疗费的赔偿数额,原则上应截止到诉讼发生时,但对于未来的“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107)当这样的未来利益成为保护的对象时,如何对这种损失的量加以证明成为有待研究的问题。
进一步说,根据《解释》第25条,(108)对“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应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伤残程度和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依据,支付期限原则上按20年计算。如此一刀切地对受害人的年龄进行估算的做法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但应采用何种更为科学的方法,亦为我国的立法者面临的难题。
(二)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和规则
1.有关损害证明确定性的一般原则
关于证明的对象,(109)如上文所述,在侵权法上,涉及损害证明的确定性,证明的对象包括3种:损害的存在、损害的程度,以及赔偿的数额。
关于对损害存在的证明,(110)正如上文所论证的,一种更为可取的制度是:受害人的举证能使裁判者确信,损害很有可能是存在的。
关于对损害程度的证明,(111)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受害人进行的举证,应具备案件的情况所允许的确定性。其中,裁判者应当特别考虑,受害人蒙受损害的性质和由此决定的让受害人进行充分举证的现实可能性。
关于对赔偿数额的证明,(112)根据上文对各国法上相关制度的介绍,法官应有权依案件的情况进行裁量,此时应特别考虑:受害人举证的难易度,加害人有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以及损害的严重程度。
2.推定的损害(113)
如上文所述,如果从一种侵权行为可以当然地推导出损害的存在,且受害人对损害的程度难以证明,那么,尽管受害人无法确定地证明损害的量值,也应当让加害人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尽管上述制度可以为我国采纳,为了防止法院在运用时过分地行使裁量权,对于这些侵权行为的具体种类,应当由法律做出列举。
3.非金钱损失(114)
如上文所述,非金钱损失是一种难以用金钱加以计量的损失。笔者认为,在我国,关于此种损失的赔偿额,原则上不要让法官灵活地裁量,而应当制定出可供参照的客观标准,比如像有些国家那样,针对不同的非金钱损失制定出赔偿的“价目表”。对于某些非金钱损失,可以在制定“价目表”的基础上,依据其特点规定可变通的例外情况。
4.未来的收入损失(115)
根据上文的介绍,对受害人未来的收入损失,各国法律普遍规定应当给予赔偿。笔者认为,在我国,随着对公民人身权保护程度的提高,也应当确认侵权受害人的此种权利。
关于此类赔偿的计算,在原则上,赔偿的数额应当为其受伤后实际可能获得的收入与如果不受伤其本应获得的可能收入之间的差额。在对其本应获得的可能收人进行计算方面,应制定出可供参照的客观标准。
对于受害人是儿童的情况,更适合我国国情的,是前述美国法上的制度,即,“为了避免过分的阶级或种族歧视”,不应考虑受伤儿童的不同家庭状况,而应以特定地区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作为计算的依据。
5.未来的机会损失(116)
正如上文介绍和阐述的,对于侵权导致的机会丧失,当某种机会是一种很可能发生的机会时,换言之,当一种机会根据事物的通常发展过程是存在的时,对该机会损失导致的损害应当给予赔偿。
如果受害人不能证明某种机会本来是很可能发生的,但能够证明该机会原本有一定的可能发生,应当允许受害人通过证明获取该机会的几率而获得相应比例的赔偿金。
四、结束语
近年来,私法领域的比较研究在欧洲层面获得的发展令人耳目一新。这使我们仅仅借助英文即能了解到欧洲法在私法的许多领域发展的概况,(117)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将英美法与大陆法进行较深入的比较,并在此基础上使我们的研究得到深化。这在本文的研究中即可得到印证。
涉及侵权法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当我们把林林总总的各国法上的相关制度以及这些制度背后的政策、理念和文化放到一起的时候,它们在相互碰撞中迸出了火花。这无疑会让每一个把法律作为科学去研究的人感到振奋:首先,在许多情况下,当我们针对一个具体问题把各国法上的制度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们是如此地一致,以至于我们不用再怀疑,其中认可的东西也可以为我们认可。其次,在更多的情况下,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我们看到了各国法之间分歧的存在。这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问题,而经验常常告诉我们,问题一旦被发现,距离其解决已经不远了。
注释:
①在奥地利学者U.Magnus教授主编的《侵权法的统一:损害赔偿》(Ulrich Magnus(Editor):Unification of Tort Law:Damages,2001,Kluwer Law International)一书中,“损害的确定性”是供参加编写该书的来自10个国家的学者讨论的问题之一。
②请参照《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版,certain词条。
③目前,我国学者普遍将英文中的“probability”一词译为“盖然性”。Probability的含义是,“较大的可能性”或“很大的可能性”。
④W.V.Horton Rogers,Damages under English Law,from U.Magnus (ed.), supra note 1,p.67.
⑤在美国,《法律重述》共有9部,分别涉及私法的不同领域。它们是由美国法学会起草,推荐给各个州采纳的。从性质上说,它们是学理性质的,但自问世以来,已经对各州的司法实践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⑥Restatement of the Law,Torts,Second,§ 912,Comment a.
⑦265 Ⅲ.App.5429 (1932).
⑧Johann Neethling,Damages under South African Law,from U.Magnus (ed.),supra note 1,p.165.
⑨U.Magnus,Damagers under German Law,from U.Magnus (ed.) ,supra note 1,p.100.
⑩H.A.Cousy and Anja Vanderspikken,Danages under Belgian Law,from U.Magnus (ed.) ,supra note 1,p.38.
(11)[1964] A.C.326.
(12)名义性损害赔偿金是一种象征性的赔偿,其数额极低。给予此种赔偿的情况是,尽管原告的某种法定权利被侵犯了但是并没有遭到损失,或者,其蒙受的损失没有得到证明。
(13)(1825)2 C.& P.109.
(14)(1853)13 C.B.222.
(15)McGregor on damages,Sweet & Maxwell,2003,p.298.
(16)Ibid.,p.297.
(17)(1911)2K.B.786,CA.该案的基本案情为:在一次由报纸读者投票竞选女演员的比赛中,原告从6000名参赛选手中胜出,成为前50名有资格参与进一步比赛的选手。可是,被告在原告缺席的情况下,从其它49名选手中选出了12名奖牌获得者。
(18)见上文:一、(一)。
(19)Restatement of the Law,Torts,Second,§ 912,Comment a.
(20)Restatement of the Law,Torts,Second, § 912,comment a ,Illustration 16.支持该范例的法院判决包括:Wachtel v.National Alfalfa Journal Co.,190 Iowa 1293,176 N.W.801 (1920); Kansas City,M.& O.R.Co.v.Bell,197 S.W.322 (Tex.Civ.App.1917); Chaplin v.Hicks,[1911] 2 K.B.786.
(21)more than a mere possibility是指:“大于‘一般的可能’”,即“很可能”。
(22)Restatement of the Law,Torts,Second,§912,comment e,Illustration 16.
(23)关于侵害“未来的机会”的证明,见下文:二、(四)。
(24)Suzanne Galand-Carval,Damages under French Law,from U.Magnus (ed.),supra note 1,p.84.
(25)Ibid.
(26)关于该条的原文,见上文:一。
(27)U.Magnus,supra note 9,p.100.
(28)Helmut Koziol,Damages under Austria Law,from U.Magnus (ed.),supra notel,p.18-19.
(29)Mark H.Wissink and WiUem H.van Boom,Damages under Dutch Law,from U.Magnus (ed.),supra note 1,p.144.
(30)见下文:二、(一)。
(31)见上文:一、(二)。
(32)Restatement of the Law,Torts,Second,§912,comment a,Illustration 14.
(33)见上文:一、(二)。
(34)见上文:一、(二)。
(35)例如伊利诺斯州上诉法院在1932年审理的Chicago Coliseum Club v.Dempsey案中即采用了这样的原则。见上文:“注7”及其注释的正文。
(36)Restatement of the Law,Torts,Second,§ 912,comment a,Illustration 6.
(37)Ibid.,Illustration 7 .
(38)前一范例依据的是:Yost v.Studer,227 Ark.1000,302 S.W.2d 775 (1957);后一个范例是归纳了许多案例的结果,其中之一是:Stafford v.City of Oskaloosa,64 Iowa 251,20 N.W.174 (1884).
(39)Restatement of the Law,Torts,Second,§ 912,Comment d,Illustration 13.这一范例依据的案例至少有10个,其中包括:Eastman Kodak Co.v.Southern Photo Materials Co.,273 U.S.359 (1927).
(40)H.A.Cousy and Anja Vanderspikken,supra note 10,p.32.
(41)Helmut Koziol,supra note28,p.18.
(42)Ibid.,p.8.
(43)Ibid.
(44)Konstantinos D.Kerameus,Damages under Greek Law,from U.Magnus (ed.),supra note 1,p.110.
(45)Mark H.Wissink and Willem H.van Boom,Damages under Dutch Law,from U.Magnus (ed.),supra note 1,p.144.
(46)见上文:一、(一)。
(47)Salmond and Heuston on the law of torts,the 20th edition,Sweet & Maxwell ,p.517.
(48)McGregor,supra note15,p.299.
(49) (1824) 3B.& C.427.
(50)在英国,法院判决原告胜诉的前提之一是,原告须证明诉因的存在。诉因是使案件得以成立的事实,而缺乏诉因将导致诉讼被驳回或撤销。“诉因侵权行为”涉及到这样的情况:根据行为的存在即可认定诉因是存在的。权利侵害本身就构成“诉因侵权行为”的情况包括:各种类型的非法侵入、文字诽谤、口头诽谤的部分形态和私人妨害的部分形态。
(51)Clerk & Lindsell on Torts,the sixteenth edition,Sweet & Maxwell,p.1094-1100.
(52)(1936) 1 Ch,343 CA.
(53)Restatement of the Law,Torts,Second,§ 904.
(54)(1900)A.c.113 at 116.
(55)[1962]1 Q.B.638.
(56)见上文:一、(一)2。
(57)事实的裁判者一般指评审团,但在没有评审团参加的案件中,法官即是事实的裁判者。
(58)Suzanne Galand-Carval,supra note 24,p.81.
(59)Ibid.,p86.
(60)U.Magnus,supra note 9,p.94.
(61)《德国民法典》第847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第l款规定:在侵害身体或者健康,以及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受害人所受损害即使不是财产上的损失,亦可以因受损害而要求合理的金钱赔偿。
(62)U.Magnus,supra note 9,p.96.
(63)Ibid.,p.103.
(64)H.A.Cousy and Anja Vanderspikken,supra note 10,p.31.
(65)Helmut Koziol,supra note28,p.14.
(66)Ibid.,p.22.
(67)对于“非金钱损失”应作什么限定,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故不详述。
(68)McGregor,supra note 15,p.308.
(69)U.Magnus,supra notel,p.4.
(70)[1992]PIQR Q 168.
(71)W.V.Horton Rogers,supra note 4,p.71-72.
(72)在美国,对事实问题的认定有评审团完成,但对事实问题的判断离不开法律的指导。此种指导是由法官进行的。
(73)Gary Schwartz,Damages under US Law,from U.Magnus (ed.) ,supra note 1,p.8.
(74)Suzanne Galand-Carval,supra note 24,p.86.
(75)U.Magnus,supra note9,p.103.
(76)Helmut Koziol,supra note28,p.22.
(77)请参见德国学者U.Magnus关于该案分析的综述:U.Magnus,supra note l,p.209.
(78)见上文:一、(二)。
(79)McGregor,supra note15,p.297.
(80)(1913) 2 K.B.786,CA.
(81)(1970)A.C.166,本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机会损失案件。
(82)(1995)1 W.L.R.1602,CA.
(83)该论述虽然也有瑕疵,比如第一类与第二类案件将作为与不作为引起的过失责任作出区分,但第二类案件重要的不是过失责任的组成,而是原告的反应须以怎样的确定性证明的问题。参见:McGregor,supra note14,p.317.
(84)[1995] 2 AC 296 at 327,per Lord Lowry.
(85)(1994)179 CLR 332.
(86)Ibid.
(87)Restatement of the Law,Torts,Second,§ 912,Comment e.
(88)Restatement of the Law,Torts,Second,§ 912,Comment f.
(89)支撑该范例的真实案例包括:Chicago Coliseum Club v.Dempsey,265 Ill.App.542 (1932); Camera v.Schmeling,236 App.Div.460,260 N.Y.S.82 (1932).
(90)Restatement of the Law,Torts,Second,§ 912,Comment d.
(91)Restatement of the Law,Torts,Second,§912,Comment d.请进一步参见上文引述的该《重述》的范例16(见上文:一、(二))。
(92)Restatement of the Law,Torts,Second,§912,Comment d,Illustration 14.
(93)支持该范例的判决包括:American Can Co.v.Ladoga Canning Co.,44 F.2d 763 (7th Cir.1930); Wood v.Pender-Doxey Groc.Co.,151 Va.706,144 S.E.635 (1928).
(94)47 S.W.3d786 (Tex.2001).
(95)315 F.Supp 7448 (S.D.Florida 2004).
(96)Suzanne Galand-Carval,supra note 24,p.84.
(97)《德国民法典》第252条(关于“可得利益”)规定:应赔偿的损害也包括可得利益。可得利益是指依事物的通常进行,或者依特殊情形,特别是依已采取的措施或者准备,可预期取得的利益。
(98)U.Magnus,supra note 9,p.100.
(99)ex aequo et bono是拉丁文,意思是“依照衡平和善去行事”。这意味着,做出决定的人可以不受法律规则的约束,而是可以按照衡平法上的原则行事。请见:Black's Law Dictionary,the 8th edition,ex aequo et bono词条。
(100) H.A.Cousy and Anja Vanderspikken,supra note 10,p.38.
(101)Ibid.,p.39.
(102)Konstantinos D.Kerameus,supra note 44,p.111.
(103)见上文:一、(二)。
(104)该条的原文是:“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105)该司法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3年12月4日在第1299次会议上通过,实施日期为2004年5月1日。
(106)见上文:二、(二)。
(107)《解释》第19条第2款的原文是:“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108)《解释》第25条的原文是:“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109)见上文:一。
(110)见上文:一、(一)。
(111)见上文:一、(二)。
(112)见上文:一、(三)。
(113)见上文:二、(一)。
(114)见上文:二、(二)。
(115)见上文:二、(三)。
(116)见上文:二、(四)
(117)今天,欧洲人在进行比较法研究的过程中采用的主要是英语。而在过去,即使一个人懂得德语或者法语,也不可能方便地对欧洲各国的法律作比较研究,因为一方面,欧洲各国一直坚的持用本国的语言表述法律,另一方面,欧洲的语言实在太丰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