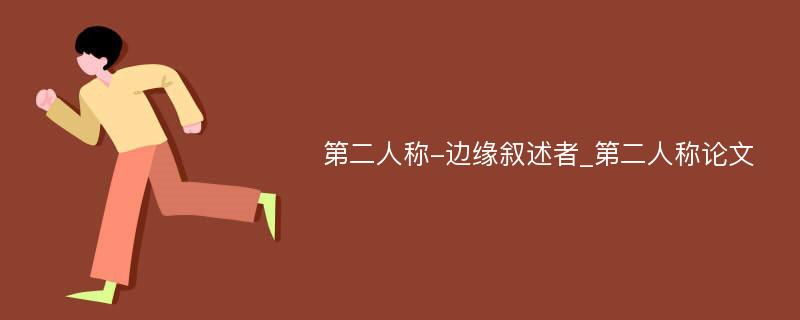
第二人称——边缘叙述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叙述者论文,人称论文,边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3)03-0169-03
在叙事文本中,人称不仅仅作为代词发挥主语和宾语的功能,“人称的转换其实是叙述者与故事之间关系的变化”[1],在叙事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传统叙事作品中,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拥有绝对权威的话语权,而第二人称在20世纪初才在现代主义创作浪潮中崭露头角,无论是在使用频率还是影响效果上,都无法同第一、第三人称抗衡,第二人称仍是“叙事虚构世界”中的边缘人。在当代叙事作品中,纯粹用第二人称叙述的作品并不多,更多的则是插足到“我”和“他”二人世界,充当“说与被说”的“他者”。也就是说,在叙述功能上,第二人称与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的区别并不十分明显,在许多作品中虽然是用“你”来指代,实际上这个“你”仍然扮演着“我”和“他”的角色,是“我”和“他”的替身和变体,在性质和作用上与“他”类似。但“你”毕竟是一个有别于“我”和“他”的新的叙述看,“你”的出现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叙述结构,在叙事作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一、在场的“他者”
在场,指“你”是故事情境中人,作为人物有丰满的性格,作为行动元推动情节的发展。根据“你”在文本中与其他人物关系,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纯粹的第二人称,叙述人不在作品中出现,叙述内容完全通过“你”的声音表现出来,“你”相当于全知全能的“他”。如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通篇用“你”来叙述。“你”是一个农村青年叫齐文栋,在第五次高考失意之后,“离开了苍老疲惫的家门”,坐在自杀的年轻姑娘鱼翠翠的坟头前浮想连翩,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死亡的“欢乐”。齐文栋饮了农药后有这样一段感受:“紧接着咽喉的痛楚,一团熊熊的烈火在你的胃里翻滚起来,你听到自己的头发梢子像燃烧的豆秸一样噼噼叭叭地响着,腐烂苹果的香气像浪潮一样涌来涌去……但痛苦很快就消逝了,你大汗淋漓,四肢柔软,瞳孔紧密收缩,终于缩得比针尖还小,黑暗如锅底一般罩下来。……你恍惚觉得有一只手牵着你走,那只手很大很柔软,那人身上有一股熟皮子的味道……爹!我又见到你啦,爹!……”叙述人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既能洞悉到你因绝望痛苦归于平静的复杂心境,也知道你的身世和现实处境。在这篇作品中把“你”换成“他”不会引起丝毫的混乱。
另一类是叙还看以第一或第三人称叙述,“你”是叙述者在作品中经常面对的一个人物,是叙述者的一个谈话对象,或是故事中的叙述接受者。由于叙述者“我”或“他”的存在,“你”的叙述视角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格非的小说《褐色鸟群》:“别装蒜了,格非。你离开都市到这个锯木厂旁边的臭水沟才几年,你的神志竟垮成这样啦,我三个月前曾到你这里来过,你答应给我看你的小说,还答应过我其他一些事。”这篇小说事实内容非常简单,即“我”向一个叫棋的女人叙述和一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之间若即若离、如梦如幻的关系,作品中“格非”、“你”、“我”、“棋”构成一个模糊的对话关系,“你”不过是“我”面对的一个人物、一个相当于“他”的叙述对象。
二、缺席的“他者”
缺席,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不在场,即“你”不是虚构的情节中的人物;一种是在场的旁观者,“你”虽然存在于作品人物的圈子中,但不过是道具、局外人。
不在场的“他者”,最明显的是作者用第二人称“你”把目光投向读者,直接与读者对话,强行把读者拉入文本中。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看官,你道花也憐侬究竟醒了不曾?请各位猜一猜这哑谜儿如何。”显然,“你”不会去猜什么谜语,因为你只是文本之外的“看官”。再如刘鹗的《老残游记》:“你想,可有余资给他儿子应用呢?”叙述者在这里直接面向受述者,以一种十分友好的态度将老残名字的由来与他的经历娓娓道来,力图以诚实态度来打动与说服读者。
在场的旁观者,指“你”虽然是文本中的人物,但并没有鲜明的形象,也不能左右矛盾冲突的进程,实质上是一个相当于读者的旁听者。如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你别打瞌睡。跑长途,我最怕旁边有人睡觉,瞌睡是会传染的。你抽根烟吧,不会?拿笔杆子的怎么不会抽烟……过去就像汽车上的反光镜,你开车的时候偶尔看一眼你会把车开得更安全更稳,但你如果一直看着反光镜开车的话,你的车非翻不可。”再如洪峰的《翰海》:“我想,只要你去过沙漠然后再到我的故乡来,你就会觉得我的故乡跟天堂差不多。”从这两段叙述可以看出,前者的“你”是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位听众,后者是叙述人面对的虚拟的谈话对象,并不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作品中的真实人物。对“你”进行叙述,字里行间充满了商量的语气。
三、本我的“他者”
本我,是指真实的自我,或我的另一半。在很多以第二人称叙述的作品中,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是从叙述者自身分离出来的一个或是灵或是肉的“他者”。这类作品中最富代表性的是法国作家布托尔的长篇小说《变化》。它描绘一个以第二人称“你”的形式出现的主人公台尔蒙,乘火车前往罗马会见情人的情景。叙述者自始至终都是用“你”来描述故事中的人物台尔蒙。开头是“你把左脚踩在门槛的铜凹槽上……”,结尾仍是“你在里昂车站买的那本小说至今还没打开”。随着车窗外场景的转换,他的意识也发生着变化。他不断地问自己:“你为什么神经这么紧张?”“你到底是哪一个?”“你正往哪儿去呢?”主人公把自己一分为二,自我同自我对话,其中一个自我扮演当事者,另一个自我扮演审判者。在两个自我的矛盾斗争进程中,展示了台尔蒙先生意识的觉醒和内心的成熟。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一篇叙事作品中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交互运用,叙述者频频变换叙事视点,“你”和“我”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不是一个人,这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叙述的主体。这类作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的长篇小说《灵山》。在作品中第二人称和第一人称并用,忽而“你”忽而“我”,从“你”又衍生出“她”来,建构了一个实体和心灵对话的虚幻世界,把一个“寻根”者的心理活动从不同的角度展现给读者。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在现实生活中感受人事时是“我”,冥想时自言自语变成“你”,进行思考时则易为“他”。所以这部作品读后使人感到:“我”的叙述亲切真实,“他”的平白具有纪实性,“你”则飘忽不定。
第二人称标新立异,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格局,在叙事作品中发出了新的声音。虽然由于其视角过于狭窄,单独运用还有一些致命的弊端,使其一直还处于第一、第三人称叙述视角的补充地位,但是,第二人称“你”的加入还是在多方面弥补了第一、第三人称叙述的某些不足,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可大致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实现了叙述功能的自我完善。
叙述的完善过程是作者权力的自我限制过程。第三人称全知全能视角,由于叙述人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有权力知道并说出故事中任何秘密,这种居高临下的优越地位,使其逐渐失去传达的亲合力。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叙述者知道的和人物知道的一样多,人物不知道的事,“我”无权说,“我”的活动受到种种局限,为了叙述的需要“我”不得不经常越界。第二人称的介入使视角转换变得更加灵活,由“你”来分享第三人称的权力,“你”便成了“他”的代言人,起到约束行动和限制权力的作用;由“你”来完成“我”所不能涉足的领域,拓展了第一人称的活动空间。
其次,调整了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传统的叙事作品,无论是讲“你”的故事,还是讲“他”的故事,读者都置身于文本之外,第二人称叙述使读者与文本中的叙述接受者“你”建立起心灵上的默契和情感的认同,从而拉近了作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作者同人物面对面地演绎情节,而读者会不知不觉地把看别人的故事当成自己的故事,最终参与到文本之中。这样就从叙述学的角度实现了接受美学所极力倡导的“文学作品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一创作原则和审美理想。
再次,增强了叙述的艺术感染力。
现代叙事学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谁来说”和“如何说”,比“说谁”、“说什么”,更重要。如果我们把文字作品比作是一个虚构的独立的世界,那么采用第三人称叙述有如把读者挡在这个世界的门外,读者只能“坐在高高的土堆旁边听人讲那过去的事情”。第一人称有如把读者关在城内,读者却不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第二人称“你”则打开一条了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相通的情感之路,给叙述活动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第二人称所建立的对话色彩和读者的“卷入”气氛,使作者、读者、人物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更容易沟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叙述的游戏功能。
〔收稿日期〕2003-0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