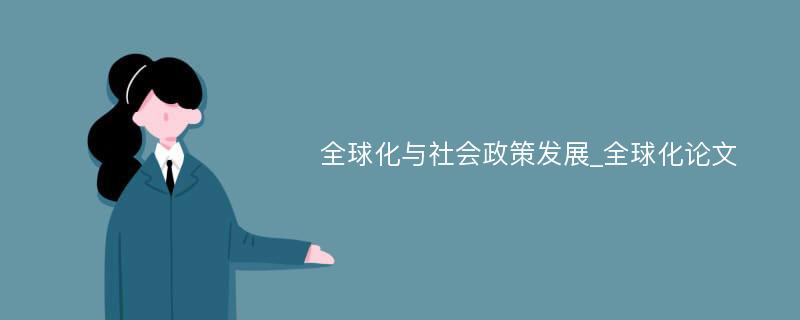
全球化与社会政策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政策论文,社会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09)05-0024-13
一、导言
全球化对于社会政策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全球化对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的发展而言是一种威胁吗?抑或全球化更倾向于使社会政策得到扩张和巩固呢?在国家乃至于国际或者全球的层面上,政治是至关紧要的吗,或者说政治如何发挥其影响力?
在过去的10到12年间,“全球化”一词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术语,在此容许笔者首先就此概念的含义作一个简要的说明。现在回想起来,不可思议的是,大约17年前,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一般公众使用网络和电子邮件开辟了机会,一场规模庞大的全球通讯革命就这样开始,如今已成为其他类型的全球化的根基所在。新技术的潜能,只要一个例子就可以表露无遗:2009年1月31日,在“Google”的搜索引擎中快速查询“全球化”一词的定义,以美式拼法“globalization”有1910万余个随机结果,而以英式拼法“globalisation”则有2560万余个随机结果。世界上通行的对该词的不同解释和定义浩如烟海,而今要作一个概述是如此之简单:敲几下键盘就可以了。
对笔者而言,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意指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一种正以某种方式变得更为全球性的事物。该概念指的其实是一个过程。这种“状态或事物”可以是很多不同的东西。广义上说,它指的是民族国家对于各种超国家或跨国家的影响力持越来越开放的态度这样一个过程(Mishra,2004:29)。更宽泛地说,它指的可以是所有行动者,无论它们是民族政府、非政府组织、公司还是公民,一方面对于各种国际影响力持越来越开放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与这些影响力发生关联、做出反馈并对它产生作用。全球化为跨越国界的交流、贸易、经济交易以及政治动员和行动带来了新的机遇。
全球化有众多不同的维度,对于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家或地区而言,不同的维度其重要性并不相同。得益于在该课题上的文献所选的例子,笔者应该指出全球化这一概念的三个主要维度分别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并列出及讨论各维度的重要指标。
本文的题目还进一步指向全球化与社会政策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有关讨论。就全球化的某些意义而言,它对社会政策发展已有什么影响?并且在将来哪些影响是可以预期的?这些都是有趣的问题。谈到社会政策,笔者假定我们有这样一个总的概念,即这是在劳工、雇员或公民失去(或缺少)收入(来源)之时一些以不同方式维持其收入的政策,一些提供医疗和保健服务的政策以及其他使所有公民都能适度过上体面生活的政策。当然,对于不少人甚至所有人而言,何谓“适度”,什么又算“体面”是一个永远有争议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中不同的行动者都会有不同的见解。瑞典、美国、博茨瓦纳和中国面临着不同的福利问题和挑战。在那些处于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国家之中,其公民、政权和其他行动者对这些问题和挑战的理解也迥然不同。无论是在这三个维度(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中的任何一个之上,全球化都(或者说可以)被认为影响着社会政策的发展。
二、全球化的维度和对社会政策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
就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的发展而言,研究兴趣往往聚集于经济全球化这一题目之上。例如,那些促进超越国界的经济关系和金融交易并因而削弱了国家自主权的因素,(大概)置福利和社会保护的政策于压力之下。一般而言,当谈及全球化时我们想到的是经济全球化。但这一概念可以延伸到诸多层面,就维持或者扩张社会政策的可能性而言,在这些层面中彼此之间并非都有着同等的重要性。根据帕利尔和塞克斯(Palier & Sykes,2001:2-3)的观点,经济全球化指的是:
经济交换和生产的国际化;
贸易国际化;外国直接投资;
国际商业网络;
通过撤销对资金流动和贸易的监管从而增强资本及其所有权、货物、服务和劳工的流动性;
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竞争的不同体系;
全球市场;经济活动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紊乱移位和重新分布;
不同国家间越来越激烈的税务竞争。
在国家的层级上,这些经济全球化的指标与社会政策发展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各国为社会保障和福利建立了不同的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其制度遗留也各不相同。在经济全球化的众多方面加速发展之时,从1980年代末起,各国创造出了规模和类型各不相同的福利制度,因此不应该认为不同的国家会以相同的方式去应对新的经济挑战。不同国家的社会政策对于这些问题和挑战的回应如此悬殊有诸多原因。政治和文化均至关紧要。例如大量的经验研究证实,在过去20年间,西欧各国政府以相当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些经济问题和挑战。价值观念、兴趣意愿以及政治偏好都不同。例如谈及:政府在社会问题上的角色应该如何完善;应该确保社会保障在什么水平上;什么程度的平等是合乎众人意愿的。民意不但由于某种价值观念和兴趣意愿的不同而在应该推出什么政策上相左,还经常在不同的政策可能带来什么影响之上存在分歧。两个以类似方式融入世界经济中并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可能出于政治和文化的原因走上不同的社会政策发展之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府就选择了与英美两国截然不同的道路。泰国选择了与香港不同的路径,而两者的选择均迥异于韩国。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典型的经济开放体,其特点是公共部门庞大、税率高,并且就所满足的需要和覆盖的人口而言,这些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健全的社会政策。经济上的开放性或许并不是一个直接的重要因素,却能解释为何选民、政治代表和政府均偏好更大规模的国家社会政策。对于那些突如其来的外部的国际经济冲击所造成的破坏性,社会政策能使其影响减轻。例如,芬兰和瑞典便能相对快地从1990年代初的危机中恢复过来,并且不需付出太大的社会代价,而这全赖经济危机来袭时两个国家已建有一套健全和具有普世性的社会政策。美国、英国和香港拥有不同的税务制度,其经济体的开放程度以及社会政策的受限规模也有所不同。较之于香港和泰国,韩国政府选择在社会政策方面扮演一个更为主动的角色。相比较而言,韩国以更为主动的社会政策回应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并且显然也因为做出了这一政治决定而获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Mishra et al.,2004)。
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少最发达的福利国家,亦即那些社会和福利项目开支占GDP百分比最高的国家,往往也是那些历史上更为开放(或者说更为全球化)的经济体,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Esping-Andersen,1996; Katzenstein,1985)。健全的社会政策一直被视为一种保护国内劳工市场的方式,亦是一种为受到起伏不定的国际经济直接冲击的公民而提供的防卫力量。社会政策还被视作一种提升“人力资本”的方式,借此增强生产力,并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稳定,从而有利于吸引外国投资和刺激经济增长,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便是一个好的例子(Kuhnle & Hort,2004)。其他近期的研究也证实了高福利开支并不必然不容于一个开放和具竞争性的经济体中(Hay,2005)。
(二)政治全球化
我们说的政治全球化是指在政府层级上以及非政府组织间跨国政治互动的增强;全球性的议题、理念和机构可谓俯拾皆是,例如民主和人权、环境保护。同时也有对世界上大多数人而言带有明显负面特点和影响的一些政治议题和现象,例如国际犯罪,武器和恐怖主义的非法传播。就福利政治而言,可以争论说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或者说“福利国家”)已逐渐变得全球化,因为越来越多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提供性质内容千差万别的社会保险和医疗计划。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均已为所有公民或一部分人群设立了某种形式的养老政策,而全球范围内失业保险的发展则最为缓慢。
政治全球化往往被认为是民族国家的弱化(例如Gray,1998),这是因为它们在社会的和政治的合法性上的缺失,但同时也蕴涵着重建或创立(崭新的)国际政治机构的意图(Palier & Sykes,2001:3)。在全球的福利政治中,诸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简称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OECD)、欧盟(EU)、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及其他国际组织,均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其中一些组织例如世行、IMF和OECD一直以来都鼓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视角,而另一些例如欧盟和ILO则捍卫和提倡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应该在社会议题上发挥更积极作用。过去12年间的一些事件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动摇了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这不仅特指在2008年9月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还包括此前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传染病。所有这些事件似乎都佐证了强调政府角色的观点,也强化了各国政府在福利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对于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而设定了的各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将带来什么影响,诸如专家,以及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等政治行动者,可能出于种种原因而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政策是不同价值观念、利益以及预期结果博弈的产物。无论是经济决定论还是政治决定论都不足信。
公共福利项目及社会支出往往被认为会拖累国民经济竞争力(例如OECD和世行多年来的众多出版物),然而同样清晰的是,这些项目和支出也被认为是社会投资、社会公正、社会保障和平等之类的大项目中的一个部分,并且有助于经济更为高效且富有生产力,减少社会动荡。以竞争视角来看待社会政策的角色和重要性渐趋明朗,对于政府而言或许已毋庸絮言,因为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国际组织之间这种视角已经在全球社会政策的话语之中得到体现。
(三)文化全球化
最后,全球化与不同“生活方式”方面的信息和知识的自由、即时传播密切相关。正是信息技术、电子通讯以及其他形式的通讯技术使这种传播成为可能。有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一种“西化”甚或“美国化”(Scholte,1996),理由是美国和“西方”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信息、知识、理念、制度和产品等方面拥有技术上和政治上的优势。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全球化起码意味着世界文化的同质化。然而,从实证角度看,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多种不同的转变过程:人们在发觉越来越多麦当劳和必胜客出现的同时,也会注意到中餐馆在世界各地同样越开越多。当“寿司比萨”出现在日本时,我们有了一个关于全球理念和产品如何本土化,并使新产品涌现的案例。
在某些时候,全球化被理解为一种对传统、地方和民族文化的威胁,其程度深浅取决于我们如何去看此类存在(Palier & Sykes,2001:3);或者是某种理念、信仰、看法、生活习惯、产品和消费模式变得全球化。全球化不仅可以被理解为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普世化(universalization),也被认为是使公民史无前例地直接面对着众多日益不同的理念、制度、产品和生活方式的某种过程。文化全球化的重点是,世界上所有人都同时面对着同样种类繁多的理念和产品,世界各地的差异性因而缩小,但每个人能经历到的事物却比以前要多得多。文化(和政治)解读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从历史观的角度看,欧洲国家能建立起比美国更为强大的福利国家,为何会出现“社会欧洲”的概念却不是“社会美国”。究竟不久前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能否改变美国的这种反差,我们仍将拭目以待。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例如Rieger & Leibfried,2003)东亚地区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根基,使建立起全面的、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政策的可能性不大,但另一方面,我们观察到全民医疗体系和全民养老计划出现在了韩国和中国台湾(Wong,2004)。人们还观察到,形式不同的社会保险项目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出现,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比社会保险在西欧出现时西欧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还要低(Hort & Kuhnle,2000)。众多思想理念在今天更容易传遍全球,并不表示它们必然能得到世界各地的接受。理念总能触发反理念(counter-ideas)。最有可能的是,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有助于全球性话语(global discourse)在社会政策所面临的挑战及其解决方案方面的发展。对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论述,其结果将通过地区的、国家的和本土的政治及文化“过滤器”予以调解。
(四)通盘认识全球化和社会政策发展
全球化和社会政策发展可以在上述提及的任何一种全球化维度的框架中进行探讨,然而由于民族国家多半处于一个较之以往更具竞争性的全球环境中,经济全球化往往得到了最多的关注,但迄今为止的经验显示,对于类似的国内和/或国际挑战,不同国家的回应并不相同,这昭示了政治和文化背景所拥有的反弹力。因此,要理解社会政策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及改革,必须把政治和文化全球化也考虑在内。
自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福利国家危机就成为OECD地区的西方各国争论不休的题目。1981年,OECD就出版了一本题为《危机中的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 in Crisis)的书,议题是严厉警告福利国家(或者用我们现时的术语,“社会政策”)必须“回撤”(roll back),而人们应各自为福利问题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可以视为对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及其对国民公共经济(实际的或预期的)影响的某种反应,但是这本书出版于一个经济全球化还没有出现且通讯技术尚未飞速发展的年代。从1980年代初开始,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上台执政为标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横扫全球。这场对英美福利国家或者说社会政策制度的袭击,便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先兆。当时很多学者预言福利国家的终结,但结果是福利国家的反弹程度远甚于预期(例如Van Kersbergen,2000; Sykes et al.,2001; Yeates,2001; Rieger & Leibfried,2003; Kuhnle,2000)。这样一个悖论出现了,对政府承担起的社会政策角色上的拓展的猛烈攻击,往往不是来自那些建立了完善的福利国家制度的斯堪的纳维亚或者欧陆国家,而是来自那些最不完善的现代西方福利国家。这本身就已经很好地说明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自由主义成为一种强大的横扫全球的意识形态—政治力量,但正如社会政策在世界各国发展的众多例子所显示的,新自由主义并不是现世仅存的唯一意识形态。在全球化这一概念的任何一个维度中,由于国内原因促使社会政策发生的转变,也许(事实上已经)不但不少于甚至还要多于由全球化而导致的变化。例如,有学者在一篇综述近年来全球化和地区化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中,强而有力地挑战了全球化是OECD国家出现福利消解现象的近因的观点(Hay,2005)。
不同的视角存在于社会政策之中,亦同样存在于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尽管经济的条件、表现和预期对关于社会政策的意见和偏好有所影响,但社会政策说到底还是取决于价值观念、利益关系和政治选择。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那些处于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富积累水平、拥有近似的开放程度的国家中,社会政策的覆盖范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证明了社会政策其实是政治偏好和选择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对社会政策发展的独立影响(independent effect),或者说这种独立经济影响的程度,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关研究和视角的综述参见:Palier & Sykes,2001; Yeates,2001; Hay,2005)。影响总是难以测量的,何况迹象并不明显。而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更为重要,我们见到一些社会政策的视角在全球性话语中取得了统治地位,亦即一些全球性的社会政策理念越来越为众多国家的政府所接纳并转化为具体的政策。较之于经济全球化过程,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不遑多让,甚至更为显著。因此,要增进我们对社会政策发展的理解,研究全球化和社会政策的全球政治话语相当重要。原因是这种话语产生并构建于若干具主导地位的国际和全球性机构和组织中。此外,同样重要的是研究如何传播并推荐这些理念给全世界国家层级的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并最终得以接纳。社会政策在不同国家的发展经验以及各国应对全球化的假定影响的举措,不应仅仅增加我们关于社会政策变迁的实证认识,还应该提升我们的理论认识,这包括何以推出这些政策而不是那些,以及在多样的全球化情境下社会政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影响渐增,监管方面的合作更国际化、政府化,从而确保一些公认的社会标准并避免所谓的“探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① (即为了提高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而牺牲社会政策)。作为跨国的、甚至超国家的地区组织的一个例子,欧盟便在监管税收和社会政策上表现出了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取向。过去20年间,欧洲的发展,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发展,显示了在社会政策中存在着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其他理念。因此,要进一步理解社会政策在各国未来的发展趋势,重点是要研究哪一种社会政策视角在全球性的机构和组织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研究中,关键是要对各国的历史传承对当前福利政治的影响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例如,在收入维持和福利服务提供方面的政府责任、对社会权利的信奉、人民对政府在社会政策领域内应有何作为的期望(Ferrera,1993; Flora,1993)等一系列问题上,美国和欧洲(整体而言)有着显著的政治文化差异。这意味着政治辩论和福利政治在欧美两地以不同的方式构建。这种对比有相当高的全球政治重要性: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在那些经济飞速发展、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快步成为现代和富裕的经济体。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和组织融合在不断扩大,而理念和经验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国境传播。某些国家和地区比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控制了更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上的权力以及影响力,因此某些福利哲学也更易于散布和传播开来。这个世界已经全球化且仍在进行,对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部分挑战在于如何在关于政府和福利的全球思考中拥有一席之地。谁拥有构建福利政治论辩的权力,而怎样的社会政策视角又将拥有主导地位?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那些新兴经济和政治强势力量又将为社会政策的全球辩论带来些什么视角?诸如OECD、欧盟、世行、IMF、ILO等国际组织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其中一些组织一直是推行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它们通过发展“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推动一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视角并对各国政府施加影响(Deacon,1999),而“全球理念”似乎在合理化各种福利改革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三、结论
对全球化和社会政策发展的众多研究得出相当不同的结论:因为察觉或观察到市场经济越来越重要的主导地位,有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对于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一些观点却认为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影响并不大,而“中间立场”则认为全球化对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发展有影响,但(国家)制度结构以及政策回应调和了这些影响(有关综述参见Palier & Sykes,2001)。最后这种观点最接近笔者的看法:经济全球化当然有影响,但全球的和/或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因素才具有决定性(Kuhnle,2005)。
本文的结束语很简单,看起来,要理解国家层级的社会政策发展,要探讨在一个更全球化的世界中社会政策的理念和政府的角色如何形成、传播并取得支配地位,研究政治和文化全球化至少与研究经济全球化同样重要。自然地,同样重要的是,要更好地理解在多大程度上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和政治以及文化全球化互为影响,或者互不影响。
注释:
① 在经济层面上,该词指的是处于竞争关系的各方经济主体(地区、国家或者厂商)争相压低劳动者的薪金水平和福利待遇以降低产品成本,从而提高竞争力的做法。该词有多种不同的译法,另一种常见的译法为“竞次”。(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