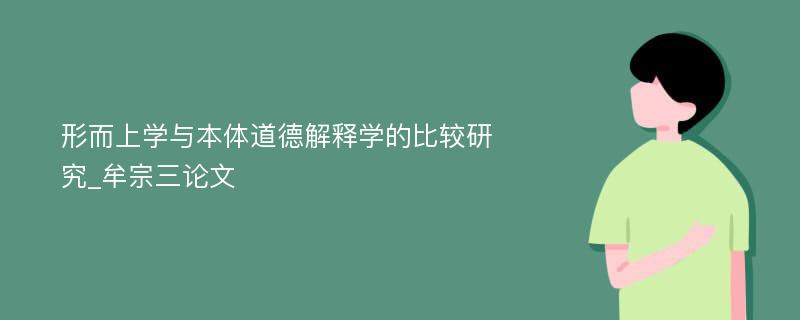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三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如何才能实现德性与理性的具体联结,真正贯通“内圣”与“外王”呢?现代新儒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见仁见智的理论建构,形成了不少颇具特色的理论学说。从总体上而言,可以将现代新儒家围绕这一问题的理论努力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不同的路向。
众所周知,从原始儒学起,儒家思想内部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义理入路,这就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强调道德的先验性、以纵贯和内省为特征的路向与以荀子为代表的注重道德之后天人为、以横贯和外观为特征的路向。经过宋明理学的发展,最终形成了注重明心见性、以尊德性为特征的陆王心学与强调格物穷理、注重道问学的程朱理学。现代新儒学发展中的两个不同的路向正是新儒家在处理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之关系的问题上顺承前贤而作出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其理论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以解决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但是由于义理入路的不同,他们之间又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尊德性”一系的基本特点在于:由于他们较为严格地持守了“德性优先”的理论立场,因而虽然也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中作了定位,但却依然将之置于“第二义”的地位。与此不同,“道问学”一系则在程朱理学比陆王心学更具理智性特色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力图由此而真正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中确立根本的地位。
在现代新儒学迄今为止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系均是代有传人。前一系以熊十力开其宗,中经第二代的牟宗三、唐君毅等到第三代仍有刘述先、杜维明等绍述前贤、宏扬师说。后一系在第一代中以冯友兰、贺麟为代表,中经第二代的方东美,到第三代中的成中英与余英时而达到成熟形态。其中,牟宗三与成中英分别成为两系中的重要代表。在一定的意义上,“尊德性”一系发展至牟宗三而完成了其理论的建构;“道问学”一系至成中英则因为以一种颇具系统的理论形态确立了理智理性与德性在儒学本体中的齐一地位而实现了现代儒学发展中的“歧出转向之新”。因此,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和成中英“本体诠释学”作为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现代儒家哲学理论,其比较研究对于厘清现代新儒学两大路向的理论特色并进而把握现代新儒学的整体特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为了展开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的比较,我们首先来对这两个学说的具体内容作一展示。
借助于康德哲学对本体界与理象界的二分,按照陆王心学“纵贯”的义理入路,牟宗三力图实现“道德的形上学”的现代重建。所谓“道德的形上学”,是“依道德的进路对万物的形上说明”①,而非就道德问题所作的形上说明。它涵盖了“本体界的存有论”或曰“无执的存有论”与“现象界的存有论”或曰“执的存有论”。何谓“纵贯”呢?牟宗三解释说:“纵贯者,照字面意思解,是‘竖起来而竖直地直贯下来’的意思。什么东西能竖直地直贯下来?直贯下来贯至什么?落实说,这是预设一道德的无限智心,此无限智心通过其创生性的意志之作用或通过感通遍润性的仁之作用,而能肇始一切物,而使之有存在者也肇始一切物而使之有存在即所谓‘创生’或‘始生’。无限智心能如此创生一切物即所谓竖直地直贯至于万物--贯至之而使之有存在。”②这也就是显发了那“道德的同时亦是形上学的绝对实体”③。
不难看,这里“道德的形上学”实即儒家传统的“内圣心性之学”,而作为“绝对实体”的“自由无限心”或“无限智心”、“知体明觉”亦即“良知”或“仁”。如果牟宗三仅仅停留在如上结论上,那么他的“道德的形上学”充其量也就只能是以现代语言赋予了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以现代形式,但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特色在于:他要从“道德良知”这一本体出发,下开现象世界,以成立“现象界的存有论”或“执的存有论”,在保守传统心学道德中心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在儒学中为知识理性留一地盘。为此,他借助黑格尔“精神之内在有机发展”观的哲学理论,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牟宗三指出“我们将依那道德的同时亦是形上学的绝对实体的自我坎陷而开出识心之执(感性与知性)”④。这里所谓“坎陷”约略相当于黑格尔哲学中的“异化”。正是“本于黑格尔历史哲学而立言”⑤,以黑格尔关于绝对理念自我异化,不断变现为自然、人类社会及人类思维的“精神之内在有机发展”观作为理据,牟宗三力图证明儒学之良知本体亦可自我变现出知性之体或现象世界。“良知自我坎陷”说的中心意旨就在于:为了充分地实现道德精神,作为儒学之本的良知,可以自觉自愿地自我吩主体。
从德性主体开出知性主体。
牟宗三这样描绘良知自我坎陷出现象界的过程:“此步开显是辩证的(黑格尔意义的辩证,非康德意义的辩证)。此步辩证地开显可如此说明:(1)外部地说,人既是人而圣,圣而人,……则科学知识原则是必要的,而且亦是可能的,否则人义有缺。(2)内部地说,要成就那外部地说的必然,知体明觉不能永停在明觉的感应中,它必须自觉地自我否定(亦即自我坎陷),转而为‘知性’;此知性与物为对,殆能使物成为‘对象’,从而究知其曲折之相。它必须经由这一步自我坎陷,它始能充分地实现其自己,此即所谓辩证地开显。它经由自我坎陷转为知性,它始能解决那属于人的一切特殊的问题,而其道德的心愿亦始能畅达无阻”。⑥“知体明觉的自我坎陷即其自觉地从无执转为有执。自我坎陷就是执。坎陷者下落而陷于执也”。“这一执就是那知体明觉之停住而自持其自己。所谓‘停住’就是从神感神应中而显停滞相。其神感神应原是无任何相的,故知无知相,意无意相,物无物相。但一停住则显停滞相,故是执也。”这一“执”也就开出了知性主体,同时也就是开出了现象界:“知性即对立,则感应中之物即被推出而为‘对象’,而对象即现象”。⑦现象界或识心之执即已开出,“执的存有论”遂可告成立。这样,涵括价值世界与知性世界、道德主体与知性主体之“两层存有论”的道德形上学即告成立。
(三)
尽管德性与理智理性的联结在成中英本体诠释学中也是一个中心问题,但是,成中英并没有象牟宗三那样,以“德性优先”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理论立场。一如其他的新儒家,成中英也将哲学视为“生命的学问”。然而,在他看来,这一生命的学问却不能仅仅只专注于人之德性修为的一面(价值)而自绝于理性宇宙(知识)之外。成中英指出:“哲学乃是缘知以求志、缘志以求知的过程。”⑧具体言之,“哲学应该是自生命的肯定,产生生命的价值与知识,再进而对知识的反省来探讨价值,从价值的反省来寻绎知识,并从两者的交互反省中来彼此充实与重建”⑨。
成中英认为,儒家哲学正是这样一种“生命的学问”。在他看来,先秦原始儒家的道德哲学就已经为包含知识与价值的整体理性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模型,真正的道德都是仁智互用的志行,但仁智如何互用而成为道德志行的问题,则有待于心的综合智慧与整体慧识。他说:“这一慧识,孟子谓之‘本心”、‘良知’,吾人则定名为本体理性。”⑩由于价值是仁的发用,知识是智的发用,因而本体理性兼括了知识与价值,“任何先秦儒家都重视此仁智互用的融合,而不偏执于一端”,因此,“先秦儒家充分显示了此一本体理性的功能及其内涵,因之为本体理性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模型。”(11)
显然,不同于牟宗三坚持认为“德性优先”是儒家正统的真精神,成中英则从先秦儒家的“仁智双彰”中得出了儒家历来都是知识与价值并重或曰德性与理性并举的结论。正是基于此,成中英明确强调,儒家哲学从孔子之“知”到朱子之“理”的发展,表现了“儒家发展的线索以及其包括的重大的人生智慧--亦即人的心性之学是以知识与理性为基础的,而知识与理性又是以心性之学为起点的”。因此,“只有在道德与知识相互支持及彼此推动下,知识才能成为更深沉的知识,而道德也才能成为更落实的道德,生命的广大面及高明面,精微面及中庸面,才因而得以发挥。……这也是儒家最高、最后的理想。”(12)
有如牟宗三哲学,成中英也没有简单停留在儒学传统既有结论的宣说上,而是力图顺此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推展。为此,成中英鲜明地揭示了价值与知识的内在关联。哲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而人的生命存在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面是理性,一面是意志。理性以知为目标,因而产生知识化的宇宙以及科学的知识架构;意志以行为目标,促使人实现理想与价值,意志又可以分为情感与欲望两个方面。情感与欲望都注重行,是行所以可能的动力,但两者之间仍有差别存在:情感注重精神、心灵的感受,欲望则偏向身体的需要及其满足。成中英据此勾勒了一幅生命存在的图像:“生命包含了理性的动向与意志的动向,意志的动向分化为情感的活动和欲望的活动,分别实现为知识、价值和行为。”(13)。
基于生命之动,意志遂生;基于对生命运动的反省,理性遂生。由此可见,“理性与意志是不可分的。两者在生命发展的过程中具有自然的辩证关系。”(14)从人的生命整体而言,理性与意志缺一不可,意志是生命的动源,没有意志就没有行为的主导,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理想也就陷于空寂。理性是对生命运动的反省,因而代表了人生意义、价值理想实现的途径与方法,缺少理性的人生就只能是盲动的人生。就两者的交互促进而言,意志可以规约理性的投向及其强度,理论则能帮助意志实现其理想及决策目标。同时理性还能帮助意志对所趋向的目标予以更清晰、更具体的掌握,以提供更好的价值,并逐渐促使意志创造更好的意志。因此,尽管理性与意志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便更有其内在的、整体的相关性:理性与意志在生命的本质上不是相反相抗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同为生命存在的两个层面,也是完成生命的两大动力,生命缺一不可”。理性与意志及其相关性构成了生命本质的整体内涵(15)。
成中英将“知识与价值”问题归结为哲学的基本内容显然与他对生命本质之整体内涵的认定有着紧密的关联。由于理性与意志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分别发用为知识与价值,而理性与意志共同构成了生命之整体,因此,知识与价值具有共同的生命本体。这也就使得知识与价值之间具有了“原始的统一性”与“内在的统一性”,从而构成了哲学思考中背向同体而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16)。它们相互需要、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不能分离而单独作用。就价值对知识的重要性而言,人的行为以价值为主导,人生意义以价值为来源,价值因而构成了个人与社会的生活目标。如果把价值完全知识化,知识就会因缺少了价值的滋润与指导而难以真正造福于个人生命与人类社会。换言之,如果把意志完全变成理性设计的机械行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会陷于空寂。就知识的重要性而言,价值问题需要知识来解决,价值行为也需要知识来引导与润饰。如是,价值本身才具有改善环境、开拓境界的能力。宇宙的生命是变动不居的,新的生命与新的环境不断形成,而价值则必须紧扣生命的真实来讲求。因此,只有通过知识的把握才能为实现价值奠定基础,也才能发挥价值充实生命的效能。因此,知识是价值实现的条件和基础、手段与方法,并具有改变价值的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成中英明确宣称:“知识对价值的重要性正如对价值对知识的重要性,乃两相依持,不分轩轾(17)。
正是基于对知识与价值的整合,成中英对宋明以来的儒学发展走向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宋明儒学把重点只放在形上学的精神构造上,强调的是圣贤之道以及如何成为圣贤,而此一圣贤乃是形上学意义上的,而非社会实践意义上的,这就使得儒学只能上达而不能下贯,从而表现出了“封闭及软弱的一面:对社会缺乏批判力,对立化缺乏创造力。因之,宋明的理学与心学只是儒家形上学的纵深发展,而非儒学社会实践面的横贯展开。(18)”由于儒学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其封闭与僵化是难免的。
如何才能重建儒家心性之学,使之与现代社会保持紧密的相关性呢?这就要求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建立要和现实生活相衔接,以把儒家的价值理想贯注于现实,也把现实的问题和要求投射在理想世界之中,从而显示儒家思想与现实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的探索自然就应再现为一个新儒学系统的建立。由于理性主义与知识主义的世界化成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因而“宋明心性之学应发展为一套涵盖科学知识的形上学或本体学,而不可划地自限独立于理性思考的科学宇宙之外。换言之,吾人必须发展心性形上学为一整合的知识形上学与理性形上学,使其兼具主体和客体两个面向或层次,而且又能融合为一体。(19)。显然,这也就是在更高的基点上对原始儒家整合了知识与价值的本体理性之完整模型的复归,以重显原始儒家完整的形上智慧,尽广大尽精微,并最终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儒家最高、最后的理想”。而这也正是本体诠释学之理论鹄的。
(四)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了,无论是牟宗三还是成中英,他们都以一种颇具规模的理论形态达成了儒家传统的德性精神与现代社会所突显的理智理性的联结,从而以各自的思想理路实现了完成儒学第三期发展之时代使命的理论尝试。这也就奠定了他们在各自的思想理路中的重要地位。
在“尊德性”一系中,尽管熊十力具有创制之功并奠定了基本的精神方向,但是在牟宗三之前,由于第一代新儒家大多持守了科玄论战以来价值世界与事实世界两分的理论立场,因而很难完成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相联结的理论任务。从儒学的内在立场来看,牟宗三正是秉承了陆王心学“心外无物”的传统,既摄物归心又推心及物,既摄知归德又扩德成知,在保守“德性优位性”的前提下,打通了两个世界,实现了德性与理性的具体联结,证立了儒家“圆教”。再加之牟氏以卓异的思辩能力与训练有素的知解理性能力,赋予了儒家心性哲学以现代的逻辑理性形式,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儒家心学到牟宗三这里堪称表现出了较为成熟的形态,以心学理路实现了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也正因为此,“尊德性”一系的后学至今仍没有取得在整体上超牟越氏的理论成就。
在“道问学”一系中,虽然冯友兰与贺麟早在30年代就分别在儒家哲学的形式和内容中凸显理智理性的重要性,但他们都没有在理论的高度实现德性与理智理性的联结。作为成中英的老师的方东美虽然提揭了一个“情理双彰”的哲学理想,且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知识与价值”并重的理论框架与之也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但方东美哲学实际上是以“生命情调”见长,并没有明确地强调理智理性的本体地位。成中英则在继承前辈有关思想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理推展,以一种颇具系统性的理论形态,不仅实现了德性与理性的联结,而且真正赋予了理性与德性完全齐一的本体地位。由于本体诠释学相承“道问学”一系对理智理性的注重,并最终突破了儒家传统的“德性优位性”,堪称是现代儒学发展中的“歧出转向之新”。
由于现代新儒学中的“尊德性”与“道问学”是相承传统儒学的不同理路在现代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它们不仅分别与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而且也由此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论特色,这在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中有着明显的表现。
众所周知,陆王心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心外无物”。陆九渊的名言即是“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也明确指出:“天地无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起于良知之外?”(20)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正是通过既摄物归心又推心及物,充分强调了“良知”本体对于包括现代科学、民主等理性主义生活实体在内之“万物”的主宰乃至“创始”作用。牟氏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极为严格地保守了陆王心学的基本精神。与充发凸显本心的主宰作用相关联,陆王心学的另一重要特色在于明显的反智识主义倾向。王阳明充分强调了良知在人的道德活动中的作用,他指出:“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盖日用之间,见面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的发用流行”,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21)。由此他明确反对对知识的追求:“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22)
作为陆王心学的现代发展,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倒是不仅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反智识主义倾向,而且还力图为知识理性在儒家心学中予以定位,这可以理解为生活在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中的牟宗三站在儒家心学的内在立场上对其价值系统的调适。但是即使如此,道德的形上学在为知识理性定位的问题上依然与传统心学的反智识主义立场保持了某种本质联系。在牟宗三看来,认知对象并不是本然的事实世界,而是来源于价值世界:“现象底全部由识心之执所挑起,它们可间接地统摄于无限心而为其权用。心外无物。识心之外无现象。”(23)认识主体也不例外:“外而现象,内而逻辑性,皆是识心之执之痉挛或抽搐。(24)可见,无论是外在的认识对象还是内在的认识主体,它们都源自识心之执,而识心之执又仅仅只是知体明觉的一个“权用”,就其实质而言它们都是统摄于知体明觉的。这样,在道德的形上学中,整个知性活动不仅不原于价值世界,而且只是价值世界的一个“权用”,因而科学理性也就只能是自身没有形上根据的“虚执”。牟宗三固然借助于康德哲学的理论框架全幅地贯注了儒家心学的传统精神,但是这种贯通不仅没有象康德那样为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认识论的基础,反而把外在的认识对象和内在的认识主体都变成了“无而能有,有而能无”(25),在根本上不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东西。显然,就在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活动中没有认知活动的根本地位而言,道德的形上学与传统心学依然保持了本质的一致。而这必然要从根本上限制儒家思想与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相衔接。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本体诠释学“整合性形上学”的确立,正是面对“尊德性”理路难以真为中国哲学确立理性之独立地位的困局而提出的另一条可能的道路。在本体诠释学看来,理性与意志作为生命存在的两大基本要素,它们之间虽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更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因而“理性与意志在生命的本质上不应相反相抵,而应相辅相成。”(26)顺此而进,它不是象道德的形上学那样,在肯定德性之优位性的前提下,力图从德性中下开理智理性,而是从生命的本质出发,肯定了理性与意志、知识与价值在哲学本体中完全齐一的地位,并在中国哲学中确立了统一心性与理智、知识与价值的“整合性形上学”。这就避免了道德形上学的理论难局,以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形态,既在中国哲学中为知识理性确立了完全的独立地位,又保留了心性之学注重价值安顿之优长。由于它为知识理性确立了本体地位,因而突破了儒家传统的“德性优先性”。与此同时,它又保留了德性的根本地位,同时也以追求“生生而和谐”为理论目标。因而尽管它对儒家传统的价值传统作了调适,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不失为一种儒家学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它认之为现代儒学发展中的“歧出转向之新”。
不同于牟宗三高扬陆王心学而力斥程朱理学为“别子”、旁枝,成中英则明确宣称以整合程朱、陆王为己任。但是,从思想渊源来看,本体诠释学与程朱理学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与心学逆觉体证的纵贯系统不同,理学更强调格物致和的横列系统。本体诠释学与程朱理学之间的联系首先在于:其哲学一体之二元即生命理性之下的理性与意志,首先是横列置放的。就其哲学的主要内容而言,也是处理知识与价值之间的“横列”关系,而不是象心学那样,表现为心性一本之下的直贯。可以认为,不同于牟宗三的纵贯理路,横列则是本体诠释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点。第二,程朱对“格物”与“居敬”的并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本体诠释学整合知识与价值、建立整合性形上学的思想资源。不同于陆王心学中较为明显的反智识主义倾向,程朱虽然也把“闻见之知”局限在道德实践的领域,但他们对“格物致和”的注重的确表现出了更多的理智性特色。如果将这一特色加以抽象和推广,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认为,程朱理学在坚持道德第一性的前提下,表现出了在儒学中接纳知识内容的理论意向,这就为成中英在儒家哲学中谋求知识理性的本体地位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思想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或中英正是沿用了程朱格物致知并最终落脚于心性修养的思维理路,既认肯知识与心性之间的互基性,又在程朱依然保守道德第一义的结论上更进一步,赋予了知识理性以不能为德性所笼罩的独立地位。
(五)
以横列为理论出发点的本体诠释学,与以纵贯为基本思维理路的道德的形上学,正好提供了两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现代形态的儒家哲学理论。这不仅在于它们分别代表了理学与心学这两大儒家流派的现代发展,而且更在于它们都自觉地站在儒家哲学的立场上回答了当代哲学中重大的理论问题。如所周知,人们通常把现代哲学中的种种流派在总体上区分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阵营,前者重科学理性,后者重人文精神。由于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在思维方式上都表现出了中国哲学注重整体、强调分中求合的根本特色,力图会通众家而归宗于儒,因而它们实质上都体现出了从儒家哲学的立场出发,力图贯通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统一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理论努力。当然,正如本文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道德的形上学所实现的统一实质上是将理性笼罩在德性之下,因而其理论努力是不成功的。本体诠释学则在生命本质的层面颇有理论深度地揭示了德性与理智理性的统一性,因而它得以东方哲学智慧为其理论背景而又展示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特质,以人文主义为体认基础而又涵括了科学主义的合理成份。它在对儒家价值系统作了基本调适之后,也为儒学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也就由此与儒家的未来走向密切相关。由于道德的形上学十分强调儒家心性之学的本身生命功能,也由于它没有赋予认知理性以独立地位而与现代社会之间的隔膜,它完全有可能推动儒学向超越现实人生与社会、发挥宗教性功能的方向发展。第三代新儒家中“尊德性”一系的代表刘述先强调儒家“超越理想与政治现实的对反性”(27)。杜维明进一步明确地将儒学称之“宗教哲学”,认为“它是通过严格的反思以探寻人类的洞识达到精神的自我超越为主要目标”(28)就代表了这一趋向。本体诠释学则代表了儒学在与人生、社会的不断互动之中,更加切近现实的理论努力。由于突显儒学的超越精神与使之更具现实性代表了儒学在未来发展的两个基本走向,可以断言,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对于今后一段时间的儒学走向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同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哲学理论,本体诠释学与道德的形上学也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理性制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它们都力图恢复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的主导地位,这与这个时代发展的主流是背道而驰的。第二,“中体西用”的深层文化心态使得它们过份强调了中华文化的优长,而对西方文化内在之体则体认不够。第三,后顾性的文化价值取向使得它们不是以时代精神为标的,而是或者以儒家“万古长青”的仁心仁性来框衡、裁剪现代社会,或者明确强调向中国哲学的“原点”复归。第四,它们都对儒家传统的修己体认、躬行践履精神传承发扬得不够,就是说,身处一个“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时代,许多现代新儒家虽然能够以儒家义理为自己学问的宗主,以儒家的价值理想为自己终极关怀的归趋,但却并没有以儒家的基本价值系统作为自我人生实践的行为准则,有的甚至采取了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成中英、牟宗三也不例外。所以,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的上述理论缺失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现代新儒家整体的理论限制。如何克服上述理论难题,就不仅关涉到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而且也关系到整个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开展。
* 限于篇幅,这里对此只能略述轮廓,具体论述尚需另撰文
注释:
①③④⑥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38-39、39、122页。
②牟宗三:《圆善论》,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328页。
⑤牟宗三:《历史哲学·自序》,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⑦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第122-123页。
⑧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
⑨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页。
⑩成中英:《文化·伦理与管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98-99页。
(11)(12)成中英:《文化·伦理与管理》,第98-99、102页。
(13)(14)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第222、234页。
(15)(17)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第233-235、232-233页。
(16)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第366页。
(18)(19)成中英:《现代新儒学建立的基础:“仁学”与“人学”的合一之道》,《当代儒学论文集·内圣篇》。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31页。
(20)王阳明:《传习录》下。
(21)(22)王阳明:《传目录》中、下。
(23)(24)(25)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第40、210、177-178页。
(26)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第233页。
(27)景海峰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28)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