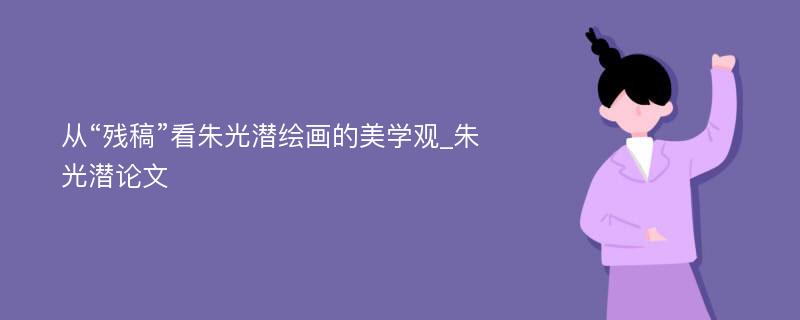
从新发现朱光潜画论“残稿”看其绘画美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残稿论文,画论论文,美学论文,看其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1)05-0046-08
一、朱光潜绘画美学“残稿”的发现
研究朱光潜美学时常会为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朱光潜有没有相对系统的绘画美学思想?尤其就中国绘画而言。若说没有,为什么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诗论》等著作里经常引用中西绘画来佐证他的美学原理且驾轻就熟?如果说有,我们在已出版的《朱光潜全集》20卷里只能见到为数不多的几处,譬如他给好友画集所作的序或观后感之类的杂文,但很少见到论述中国绘画的文字。最近,笔者为了编校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的《朱光潜全集》(30卷本)而翻检朱光潜的遗稿时,欣喜地发现他居然还有专门讨论中国绘画美学的文稿,尽管文稿已残(或根本未写就),但也足以见出他研究中国艺术(绘画和诗歌)的心得。他的方法往往是中西绘画、中西诗歌相互印证、相互阐释的方法(互为体用)。现照录全文如下,然后在此基础上略作剖析:
中国造型艺术达到最高成就而为世人所熟知的是绘画。像俑一样,最早的绘画大半是放在墓穴里为死人服务或纪念死人的。这种画可以采取各种形式,最常见的是壁画,其次是墓志碑上的“造象”浮雕,也有用笔涂水彩画在帛上的死者生平事迹,铺在棺材上,例如近来发掘出来的长沙马王堆林侯墓的帛画就是这样。墓穴之外,一些著名的宫殿和庙宇也常用壁画作为雕饰,纪念神佛或表扬功勋。此外像上文已提到的敦煌莫高窟以及麦积山、榆林、辽阳之类的石窟是专门凿制出来,为宣传佛教用的。
综合这些壁画和造像来看,中国早期绘画都侧重仙佛人物和他们的事迹,往往采取连环画的形式。这种画艺到隋唐时代在顾恺之、陆探微、阎立本、吴道子、周昉一系列大画师手里已达到高度成熟。隋唐以后一直到明清,中国画就由侧重人物事迹转到侧重山水风景,也就是由专业画师的画转到“文人画”。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自东晋陶渊明、谢康乐以后一般文士多以隐逸和怡情山水相标榜,为的是逃避尘世纷争或自慰穷途失意(应记住当时是个兵(慌)[荒]马乱、社会矛盾日趋剧烈的时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王羲之的《兰亭诗序》和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都透露出此中消息。这多少也受到佛教的影响。这些文士大半与僧徒有来往,中国向来是“天下名山僧占多”,他们“入山惟恐不深”,于是也的确尝到“世外桃源”的乐趣。陶谢以后中国诗转到侧重歌咏自然,中国画也转到侧重山水风景,道理是一样的。这个大转折有两个明显的结果:其一是诗与画开始密切联系起来,其次论画的理论著作也日渐多起来,绘画领域的美学从此诞生了。这方面的资料有人民出版社的《画论丛刊》和《宣和画谱》等书可以参考。
关于诗画结合一点,唐王维(摩诘)最足以说明问题。他是山水画的开山鼻祖,也是伟大的自然诗人。宋苏轼(东坡)称赞他的作品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宋画论家赵孟潆也说过“诗为有声之画,画为无声之诗”,和希腊诗人Simonides的著名的格言几乎一字不差。罗马诗人Horace也说过,“画如此,诗亦然”。从此可见诗与画有共同点,这是古今公论。但是这个看法和德国诗人莱辛(Lessing)在LaoKoon里所论证的诗画异质,诗写动态而画写静态之说却是显然对立的。不过莱辛并不否认诗可以用“化静为动”和“化美为媚”的办法去描述特宜于画的静态。他举荷马史诗描写特洛伊元老们在危城上接见海伦后为例。我们为便于说明,可以举中国《诗经》中一段描写美人的名句: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颌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段诗头五句用油脂、蚕蛹、瓜子和灯蛾之类杂凑在一起,费了许多笔墨,终写不出美人的美;到了最后两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美人便一跃而出,活灵活现,这便是“化静为动”,“化美为媚”。读王维的《辋川诗集》歌咏自然的短诗,就经常碰见类似的事例。
关于画论,晋唐以来这方面的论著是美不胜收的,这里只能举意义深长影响深远的三种为例。
(一)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说
形(体躯)与神(精神)是画艺中两个重要概念。中国画家历来强调“神似”,文人画往往轻视单纯的“形似”。顾恺之是东晋擅长人物画的大画师,他的“仕女箴图”仍存大英博物馆。他的主张是通过“形似”进一步去求“神似”。《宣和画谱》举过他的一些实践事例来说明他的主张,现在姑选其中四个事例:
“……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美丑),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此,即睛)中。’尝图裴楷像,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又为谢鲲像在石岩里,云:‘此子宜置在丘壑中。’欲图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辞。恺之曰:‘明府(仲堪)正为眼耳,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使如轻云之蔽月,岂不美乎?’……”
这里几个具体事例说明了画艺中几个重要原理。第一点点睛例说明了画艺首先于眼睛,西方美学家黑格尔也曾提过类似的论点(见《美学》①),从上引“美目盼兮”这句也可以见出这个道理。第二个“颊上加三毛”例说明了为着达到“神似”,画艺可以借助于虚构夸张,颊上本无三毛,加上三毛,观者就觉得“神明殊胜”,也就是说,牺牲浮面的“形似”有时可以加强“神似”。第三个置谢鲲像于丘壑中,说明了“典型环境下有典型性格”的道理。谢鲲是一位好“老”“易”,善歌唱和弹琴的高人雅士,尝自谓“一丘一壑”胜于当时宰相度亮。第四个画殷仲堪像用“轻云蔽月”的例说明了画家可以凭艺术手腕把“形似”方面的短转化为“神似”方面的长,也就是说艺术转化“第一自然”为“第二自然”。
(二)荆浩《笔法记》中的六要
荆浩是五代梁朝的一位著名的山水画家,他的《笔法记》讨论山水画的要素和表现方法,是用对话体写的。对话者为洪谷子和一位老叟(实际上是荆浩一人自问自答)。老叟问洪谷子是否懂得画法,洪谷子谢不知;“叟曰:……夫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
下文叟又对六要进行如下的说明:
“叟曰……图画之要,与子备言;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不俗;思者,删拔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深浅,文采自然,似非因笔。”
这段文字艰晦,参考后来画家的论述,略作如下的解释:
气:气随笔运,即意到笔随,摄形(客观景象)必同时立意(主观情思),才胸有成竹,意到笔随,画出正确的形象(取象不惑)。
韵:隐迹立形,删削浮面细节,突出要表现的形象;备仪不俗,仪即宜,具备必要的法则而不落俗套。
气韵二要即谢赫的“六法”中的“气韵生动”。
思:相当于“六法”中“经营位置”,包括构图方面的构思。删拨大要,即去粗取精,概括集中;凝想形物,即聚精会神地构造艺术形像。
景:景即情景。“制度时因,搜妙创真”,即衡量具体情境而作适合时宜的处理,使作品既妙而又真实,“搜”与“创”才见出苦心经营,“笔夺造化之功”,是创造而不是单纯摹仿。
笔:即画笔的运用,依法而不拘于法,运转自如,“不质不形”指不粘滞于外形和质朴粗糙的末节,这样才可见游龙流水之妙。
墨:相当于着色渲染烘托,浓淡深浅都符合对象的自然本色,像是自然生出来而不是画出来的。
笔墨两要是中国画的特色,作者在文中还提到“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明画家董其昌在《画旨》里解释说:“但有轮廓无皴法,即谓之无笔;有皴法而不分轻重,向背,明晦,即谓之无墨。”
《笔法记》除标出六要外,还谈到“华”与“实”和“真”与“似”的分别和关系。洪谷子听到老叟提到六要之后,就提出疑问:
曰:“画者华也(画是一种有文采的花),但贵似得真,岂此挠矣!(只要画得像,见出真相就行了,何必讲这些诀窍?)”叟曰:“不然。画者画(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衡量事物形象,取出它的真实本质)。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以为实(是华就取华,是实就取实,不可以华为实)若不知术(法),苟似(貌似)可也,图真(掌握精神实质,即‘神似’)不可及也。”
曰:“何以为似,何以为真?”
叟曰:“似者得其形,遗其气(即‘神’或精神实质);真者气质(神形)俱盛。凡气(神)传于华(花的文采),遗于象(如果象没有神),象之死也(象就没有生气)。”
这里寥寥数语,说透了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荆浩是现实主义文艺的一个很早的而且自觉的拥护者,所以可贵。
(三)谢赫(缺)
此外,朱光潜还有这篇文稿的一个提纲,从提纲看,他是原打算写到明清的。现也照录如下:
人物 汉魏六朝成熟 山水 唐宋——明清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张舜民
顾恺之“以形写神”
为人画像,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他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此,即睛)中”。
六要
荆浩 《笔法记》
“画有六要:一气,二韵,三思,四景,五笔,六墨”。
六法 谢赫:《古画品录》
“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采,五经营位置,六转移模写”。
唐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章
南北宗 董其昌将唐以来山水画划分为南北两大宗,“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马(远)夏(珪)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而北宗微矣”。②
展子虔 隋 青绿山水 小幅咫尺千里之势
《游春图》韩幹牧马图。
一般说来,绘画、雕塑在艺术分类上属于造型艺术,或者称空间艺术;而诗、音乐则属时间艺术。朱光潜对中国传统诗的研究,以近代学科方法重新整理、阐释,试图使其从“诗话”提升到“诗学”的高度,形成的大著《诗论》已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想见,朱光潜此时以绘画为研究对象,并且常常结合诗歌作比较式的贯通研究,一方面可能是受到德国莱辛《拉奥孔——诗与画的界限》的启发;另一方面,中国画与诗的融合在世界文化史上也确实是不多见的,通过对中国绘画史的进一步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艺术精神的了解。朱光潜的比较式的研究显然立于此。此外,中国绘画的形式化因素也契合了朱光潜一贯的美学立场。这种立场虽然只是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的美学观的某个方面,但是这种形式因素在他的早期美学思想中还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因此,揭示中国传统绘画对朱光潜美学(尤其是早期)的影响也是很有意义的。
二、“残稿”中几个重要的绘画美学观点
(一)以情趣和意象的契合来研究诗与画融合的轨迹
朱光潜研究中国传统绘画理论是和他研究诗学联系在一起的。残稿称:“隋唐以后一直到明清,中国画就由侧重人物事迹转到侧重山水风景,也就是由专业画师的画转到‘文人画’。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又说:“陶谢以后中国诗转到侧重歌咏自然,中国画也转到侧重山水风景,道理是一样的。这个大转折有两个明显的结果:其一是诗与画开始密切联系起来,其次论画的理论著作也日渐多起来,绘画领域的美学从此诞生了。”
朱光潜明确指出中国的绘画美学诞生于六朝,这当然和诗歌与绘画的逐渐融合有关。朱光潜早在写《诗论》时就已经发现中国绘画美学的兴起固然和魏晋文人恣情于山水以及佛教的影响有关,但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情趣和意象的契合更加精巧。他以诗歌的嬗变轨迹为例进行了说明。
众所周知,“情趣”偏于主观,“意象”偏于客观。诗歌偏于“情”(趣),绘画偏于“形”(意象)。但艺术是整一性的,艺术分类终究是个大略的。就整个美的境界来说,朱光潜认为美的境界实质上是情趣和意象的契合,也可以说是情趣的意象化和意象的情趣化(主客观的统一)。就个体说,情趣和意象之于创作者和欣赏者的比量是不尽相同的,“有人接收诗偏重视觉器官,一切要能用眼睛看得见,所以要求诗须‘显’,须如造型艺术。也有人接受诗偏重听觉与筋肉感觉,最易受音乐节奏的感动,所以要诗须‘隐’,须如音乐,才富于暗示性。所谓意象,原不必全由视觉产生,各种感觉器官都可以产生意象。不过多数人形成意象,以来自视觉者为最丰富,在欣赏诗或创造诗时,视觉意象也最为重要”③。这就是说,情趣与意象之于个人创作与欣赏也有心理和生理上的差异。倘就诗歌的历史看,“如果从情趣与意象的融合看,中国古诗的演进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情趣逐渐征服意象,中间是征服的完成,后来是意象蔚起,几成一种独立自足的境界,自引起一种情趣。第一步是因情生景或因情生文;第二步是情景吻合,情文并茂;第三步是即景生情或因文生情。这种演进阶段自然也不可概以时代分。就大略说,汉魏以前是第一步,在自然界所取之意象仅如人物故事画以山水为背景,只是一种陪衬;汉魏时代是第二步,《古诗十九首》,苏李赠答及曹氏父子兄弟的作品中意象与情趣达到混化无迹之妙,到陶渊明手里,情景的吻合可算登峰造极;六朝是第三步,从大小谢滋情山水起,自然景物的描绘从陪衬地位抬到主要地位,如山水画在图画中自成一大宗派一样,后来便渐趋于艳丽一途了。”④
由此可知,朱光潜残稿里讲的诗画道理是一样的,是以其美学理论为基础的。从大的方面讲,就是美是主客观统一,或者说是情趣(主)和意象(客)的统一(可以是情趣的意象化或意象的情趣化)。从具体方面讲,朱光潜分析诗歌或绘画是从主与客、情趣与意象的二元对立的彼此消长、冲突与融合的矛盾中揭示艺术的规律性。这和时下某些学者以为讲中国艺术精神,只能讲“天人合一”、讲主客同一(不是统一)是相去何等之远!这些学者讲的是无差别的同一,而朱光潜讲的是有差别的同一(统一)。前者好似黑格尔批评谢林的“绝对”如“夜间观牛一切皆黑”。后者则是把历史和逻辑有差别的同一放在历史的辩证发展中揭示艺术规律的一致性。毫无疑问,朱光潜是受到黑格尔的美学思想影响的。他从情趣和意象的分量来说明诗画的历史演进,仿佛与黑格尔以物质和精神的分量来说明象征、古典、浪漫三阶段的方法是同出一辙的。但是,这并不是完全西方化的,它透显着浓重的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情与象),应该说是中西合璧式的文化解释学。就朱光潜个人来说,他偏袒于陶渊明,也是因为他认为到了陶渊明那里,情与景(情趣与意象)达到了理想的契合状态(犹如黑格尔赞扬古典是内容与形式、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一样)。不过,朱光潜并不诋毁六朝的“艳丽”,这种“为意象而意象”也自成一格,而且恰恰是中国绘画美学所追求的“画境”的诞生之日。所以我们也不难想见朱光潜为什么在写过《诗论》后,在上世纪70年代着手研究中国的绘画美学,这是因为诗与画走向融会之路已经打通。从绘画而不是从诗歌的一面来阐释情趣与意象的契合关系就成了朱光潜新的研究课题。
(二)从中西美学的比较中阐释中国传统绘画的“理”
美学是美的科学。科学是讲普遍性的,否则就不能称为科学。同理,美学如果只讲特殊性,只讲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特殊审美特性,不去探究作为共同人性(不论中土还是西方,人性是共通的)意义上的美的相同价值,那么,美学就不能称为美学。朱光潜是个“世界主义”者,他讲美学并不囿于某一民族、某一文化的范围,他的视野很宽,是在中西美学的相互比较、相互印证、相互阐释的基础上寻求一种互为体用(既不是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的“新范式”。残稿对中国绘画的阐释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略举数端说明如下:
首先,朱光潜认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所谓诗画同质的理论是古今中外的“公论”。这可以看作朱光潜乐观地认为美学的普遍共同性的基础是存在的。当然,在诗画同质说之外,还有莱辛的诗画异质说。“莱辛的功绩在于指出诗和画的特点。即向来比较被忽视的一面”⑤。毕竟,从残稿看,朱光潜更看重莱辛《拉奥孔》中强调诗与画的界限也是可以打破的观点,他说:“但是这个看法(指诗画同质说——引者)和德国诗人莱辛(Lessing)在LaoKoon里所说的诗画异质,诗写动态而画写静态之说却是显然对立的。不过莱辛并不否认诗可以‘化静为动’和‘化美为媚’的办法去描述特宜于画的静态。”这里的“化静为动”和“化美为媚”则是从“诗中有画”的视角来作分析的。朱光潜看重的不是各种艺术的媒介不同所带来的特殊性,虽然我们讲离了这种特殊性,诗歌就不是诗歌,绘画就不是绘画,音乐就不是音乐。不过,“艺术受媒体的限制,固无可讳言。但是艺术最大的成功往往在征服媒介的困难。”⑥ 所以,当朱光潜认为拿中国诗画理论印证莱辛的诗画异质说不免有些扞格不通,他说:“一种学说是否精确,要看它能否到处得到事实的印证,能否用来解释一切有关事实而无罅漏。如果我们应用莱辛的学说来分析中国的诗与画,就不免有些困难。中国画从唐宋以后就侧重描写物景,似可证实画只宜于描写物体说。但是莱辛对于山水花卉翎毛素来就瞧不起,以为它们不能达到理想的美,而中国画正在这些题材上做功夫。他以为画是模仿自然,画的美来自自然美,而中国人则谓‘古画画意不画物’,‘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莱辛以为画表现时间上的一顷刻,势必静止,所以希腊造型艺术的最高理想是恬静安息(calm and repose),而中国画家六法首重‘气韵生动’。中国向来的传统都尊重‘文人画’而看轻‘院体画’。‘文人画’的特色就是在精神上与诗相近,所写的并非实物而是意境。不是被动地接收外来的印象,而是熔铸印象于情趣。一幅中国画尽管是写物体,而我们看它,却不能用莱辛的标准,求原来在实物空间横陈并列的形象在画的空间中仍同样地横陈并列,换句话说,我们所着重的并不是一幅真山水,真人物,而是一种心境和一幅‘气韵生动’的图案。这番话对于中国画只是粗浅的常识,而莱辛的学说却不免与这种粗浅的常识相冲突。”⑦
从此可知,朱光潜对莱辛步古希腊“艺术即模仿”的老观念并不赞同,尤其是莱辛把美仅限于物体,而诗则根本不能描写物体,因而诗中就不能有美的观点。这种观点把诗和艺术对立起来,“美”和“表现”也分离为两事。朱光潜一方面肯定克罗齐的“美即是表现”就是要纠正这一偏差,另一方面就是拿着中国传统的诗画融合说的利器来对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发难。
其次,朱光潜用西方的美学范畴和中国传统的美学范畴作相互比较、相互印证,以达到相互阐释中生发出一种“新质”。如朱光潜拿顾恺之的点睛例的“传神”和黑格尔相关论述作比较;拿置谢鲲像于丘壑中以说明顾恺之已揭示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拿画殷仲堪像用“轻云蔽月”例以说明艺术家有把“形似”转化为“神似”的权力,这就是西方所谓艺术转化“第一自然”为“第二自然”。还譬如拿荆浩关于“华”与“实”范畴的阐述以证明荆浩“说透了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荆浩是现实主义文艺的一个很早的而且自觉的拥护者,所以可贵”。
应该指出,朱光潜的这种比较,不是比附,不是皮相之论。如前所述,他是试图在共同人性基础上探寻中西美学的融合之道。有的学者认为朱光潜以西方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讲美学问题,那实际上原来是文艺理论问题⑧。我以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没有理由说文艺理论所讨论的内容不能和美学相交叉,这个边界并不如某些学者所以为的那样清晰。更何况,朱光潜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艺流派的运动和它们作为文艺创作方法的精神实质是区分开来的。因为后者实际涉及美的本质和艺术的典型问题,当然属于美学问题。所以朱光潜说:“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文艺流派运动,应该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在精神实质上有区别的两种文艺创作方法区别开来。前者是文艺史的问题,后者才是美学的问题。”⑨ 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光潜并不是在文艺史意义上运用“现实主义”的,而主要指一种美学上的意蕴。如他指出席勒较早运用“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并且席勒敏锐地指出现实主义也可能蜕化为“自然主义”的经验。“自然主义”是以“实在的自然”或“庸俗的自然”为审美对象,而现实主义则以“真实的自然”为审美对象。由此可知,朱光潜说荆浩对“华”与“实”的辨别是“说透了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显然是指荆浩说的“真者气质(神形)俱盛”已是以“真实的自然”为审美对象,而非“形似”的“实在的自然”。
有学者精确指出:顾恺之的“神”的观念,并不同于黑格尔的“理念”,倒是近于重视个体感性的康德哲学。因为顾恺之不是从个体感性存在中去找寻或“显现”某种“理念”,而是要通过个体感性存在的直观去捕捉或表现人生的某种哲理性的东西⑩。的确,顾恺之的“神”不是像黑格尔“理念”以牺牲感性直观(虽然在感性中可以显现“理念”的真,但最终哲学要代替艺术哲学,因为哲学直接陈述理念)为代价。顾恺之的“神”是通过“直观”(悟)达到的。
其实,朱光潜只是想说明顾恺之的“以形传神”的“神”已不是普通的认知,而是包含生活(道德、伦理)于其中,是以有限的“形”达到无限的超越精神(不可言)。所以他把顾恺之和黑格尔作比较。如果我们把黑格尔在《美学》里的那段话仔细咀嚼,即会发现朱光潜无非是肯定这种超越有限而达到的无限的自由和精神价值。黑格尔说:
艺术也可以说是要把每一个形象的看得见的外表上的每一点都化成眼睛或灵魂的住所,使它把心灵显现出来。……不但是身体的形状、面容、姿态和姿势,就是行动和事迹,语言和声音以及它们在不同生活情况中的千变万化,全都要由艺术化成眼睛,人们从这眼睛里就可以认识到内在的无限的自由的心灵。(11)
因此,朱光潜只是从一个侧面来说明顾恺之的“神”和黑格尔“心灵”有相通之处。至于美是直观,并不需要通过它的“主人”理念来干预,一样可以达到,这是克罗齐的观点,也是朱光潜所接受的。恰恰是因为这样,朱光潜心目中的克罗齐并不是一般新黑格尔派的,他宁愿把克氏看作是康德哲学的继承者(这从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和《西方美学史》中可以见出。因为这个论题与本题较远,此不赘述)。如此说来,朱光潜的论点和前此学者的观点并不矛盾,只是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而已。
三、从“残稿”申论朱光潜绘画美学思想
“残稿”所用的稿纸是1977年的,由此可以断定朱光潜是在文革结束后“重操旧业”,来重新审视他早年一直关注的诗与画的美学相关问题。这个视角是直面中国绘画史来谈的。虽然朱光潜并没有像他在《诗论》里系统说明了“诗中有画”(情趣的意象化)的观点那样从绘画的视角说明“画中有诗”(意象的情趣化),但是已经大体可以见出绘画美学在朱光潜美学思想系统中的地位。大致说来,有几点值得强调:
其一,自然主义文艺创作(朱光潜早期美学称“写实主义”)是“见物不见人”的美学方法。艺术离不开人,“第二自然”高于“第一自然”,就是说明审美有艺术家的理想在里面,是要来源于“自然”(第一自然),但又要高于自然(第二自然)。用朱光潜早期美学的观点看,这种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就是“距离”太近,而不是审美心理距离的“不即不离”。从现实主义的观点看,都是要透过现象的表层把握某种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中国绘画的“传神写照”、“度物象而取其真”都是对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美学的反驳。所以,朱光潜说:“中国从前画家本有‘远山无皱,远水无波,远树无枝,远人无目’的说法,但是画家精义并不在此。看到吴道子的人物或是关同的山水而嫌他们不用远近阴影,这种人对于艺术只是‘腓力斯人’(Philistines)而已。”(12)
其二,朱光潜看重顾恺之的“传神”的“神”,用黑格尔的话讲是体现了“心灵的理想和自由”。这“心灵的理想和自由”在黑格尔那里是比自然要在价值上高一层。只有人才有理想,人的自然美(人体)自然比自然美更高一层。朱光潜在“残稿”里虽没有申论,但我们从他早期美学论著中可以找到这样的说明:“不过我们不能不明白这些皈依自然在已往叫做‘山林隐逸’的艺术家有一种心理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或者说,自然与人的冲突——而他们只直走到这冲突两端中的一端,没有能达到黑格尔的较高的调和。为什么不能在现实人物中发现庄严幽美的意象世界呢?我们很难放下这一个问题。放下但丁、莎士比亚和曹雪芹一班人所创造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不说,单提武梁祠和巴惕楞(Parthenon)的浮雕,或是普拉克什特里斯(Praxiteles)的雕像和吴道子的白描,它们所达到的境界是否真比不上关马董王诸人所给我们的呢?我们在山林隐逸的气氛中胎息生长已很久了,对于自然和文人画已养成一种先天的在心里伸着根的爱好,这爱好本是自然而且正常的,但是放开眼睛一看,这些幽美的林泉花鸟究竟只是大世界中的一角度,此外可欣喜的对象还多着咧。我们自己——人——的言动笑貌也并不是例外。身分比较高的艺术家,不尝肯拿他们的笔墨在这一方面点染,不能不算是一种缺陷。”(13) 可见,人物画逐渐为“人文画”所替代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轻视人物,就是抛弃了自然(人也是自然)中最美、最该表现的对象。顾恺之还是人物画时代,朱光潜有意拿顾恺之和黑格尔强调人的美学思想来比较,其用意是深刻的。
其三,朱光潜认为美是情趣和意象的契合。这情趣和意象的契合因受媒介的限制而有偏于主观和偏于客观之别。粗略地说,诗偏于主观,它主情(志);画则偏于客观,它主形(象)。朱光潜在《诗论》里很好地、系统地说明了诗中的情趣与意象契合的分量,是侧重“诗中有画”的视角。至于从绘画美学的角度,也就是从“画中有诗”的观察入径,似乎朱光潜有系统地从中国绘画美学理论来说明这点的愿望,“残稿”大概就是这项工作的开始。倘若能完成这项伟业,必定更能深化“美是情趣与意象的契合”这一美学命题。这绝不是我们的臆断,我们从朱光潜为什么非常青睐好友丰子恺或许可以得到些证明。朱光潜《缅怀丰子恺老友》里称赞他的画品和人品,也都是从“画中有诗”这个角度说的,他说:“他(指丰氏——引者)的漫画可分两类,一类是拈取前人诗词名句为题,例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指冷玉笙寒》、《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之类,另一类是现实中有风趣的人物的剪影,例如《花生米不满足》、《病车》、《苏州人》之类。前一类不但有诗意而且有现实感,人是现代人,服装是现代的服装,情调也还是现代的情调;后一类不但直接来自现实生活,而且也有诗意和谐趣。两类画都是从纷纭世态中挑出人所熟知而却不注意的一鳞一爪,经过他一点染,便显出微妙隽永,令人一见不忘。他的这种画风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妥帖结合。”(14)
总而言之,“残稿”虽然还不能说是系统地表达了朱光潜绘画美学思想,但透出了进一步从绘画的视角阐明他关于美是情趣与意象契合的美学命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遗憾的是,朱光潜未来得及完成他的《诗论》的“姐妹篇”——《画论》,只留下一个提纲,而且还是残缺的提纲。不过我们无须求全责备,毕竟,我们看到了顺着“画中有诗”的理路,通过情趣与意象契合的分量来揭示中国绘画如何从六朝走向现代的光明大道已经敞开了。
注释:
① 朱光潜没有注明黑格尔观点的具体出处,估计应是《美学》第1卷里这段话:“把每一个形象的看得见的外表上的每一点都化成眼睛或灵魂的住所,使它把心灵显现出来。”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98页。
② 此处所引,与董其昌原文有所不同——编者注。
③ 朱光潜:《诗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54~55页。
④ 朱光潜:《诗论》,第68页。
⑤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4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329页。
⑥ 朱光潜:《诗论》,第152页。
⑦ 朱光潜:《诗论》,第152~153页。
⑧ 章启群说:“朱光潜先生所特别强调的这四个‘关键性问题’(指朱氏《西方美学史》最后总结的四个论题),只有‘美的本质’和‘形象思维’才属于真正的美学问题,而‘典型人物’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则属于文艺理论问题。”章启群:《新编西方美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页。
⑨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4卷,第761页。
⑩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52页。
(11) 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98页。
(12)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6页。
(13) 商金林编:《朱光潜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16页、117页。
(14) 商金林编:《朱光潜批评文集》,第247页。
标签:朱光潜论文; 顾恺之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诗论论文; 美术论文; 国画论文; 笔法记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