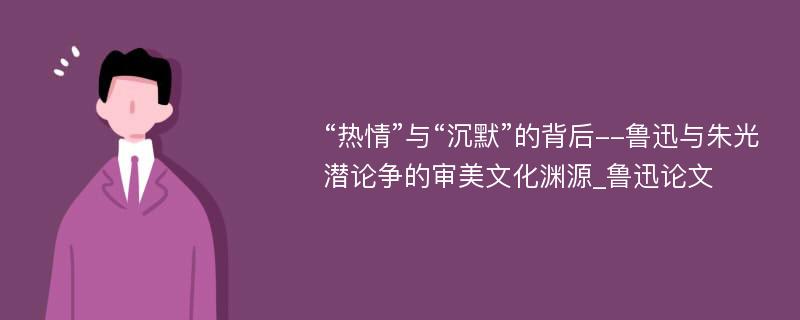
“热烈”与“静穆”的背后——鲁迅与朱光潜论争的美学、文化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静穆论文,美学论文,根源论文,热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5年,朱光潜在《中学生》杂志发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一文,高度称赞钱起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认为它在“静穆”里抵达了永恒,就如同华兹华斯的《独刈女》一样,又如同陶渊明的诗歌一样。古希腊人把“静穆”看作是诗歌的极境。“静穆”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陶渊明浑身都是静穆,所以他是伟大的诗人。为此,鲁迅这年年底写了《“题未定”草(七)》,以其一贯的犀利质疑、反驳朱光潜的“静穆”说,认为朱光潜的“静穆”是以偏概全,没有顾及到诗歌全篇,也没有考虑到陶渊明全部诗歌和为人。“静穆”不过是“抚慰劳人的圣药”。陶渊明没有那么“静穆”,“静穆”既不是古希腊诗歌的最高境界,也不是艺术的极境。朱光潜当时并没有做出回应,鲁迅也没有就这个问题继续发表文章。在你来我往,冲突激烈而频繁的1930年代文坛,这种摩擦实在不算什么,但是,从这小小的波澜中,我们可以透视双方在美学、人生态度上的巨大差异,从一个角度深化对鲁迅、朱光潜这两位极具代表性人物的理解,同时,也是对1930年代文坛多样化美学风景的一种欣赏。 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论的批评,根源于他们两者之间的美学观念和人生态度的巨大差异。 首先,我们看看美学观念上冲突。在现代文学中,朱光潜大体上属于那种稳健、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是“京派”的理论家,无论是他的散文创作还是理论主张,都带有浓厚的“京派”美学趣味。他虽有八年的留学英法的经历,受叔本华、尼采、黑格尔、克罗齐等人的影响,但他的精神深处却更倾心于中国传统的温柔敦厚的美学,深深地痴迷中国传统文学的“无言之美”。在他的美感天平上,“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所谓怒目,便是流露;所谓低眉,便是含蓄。凡看低头闭目的神像,所生印象往往特别深刻。”①“与其尽量流露,不如稍有含蓄;与其吐肚子把一切都说出来,不如留一大部分让欣赏者自己去领会。”②在中西诗歌的对比中,朱光潜认为,中国诗歌以“委婉、微妙、简隽胜”,西方诗歌则“以直率、深刻、铺陈胜”。他显然更倾向于前者。在这种“无言之美”中,艺术家应该保持与现实的适当距离,从容内敛,不应该完全与现实对象混合在一起。就新文学创作而言,他最崇拜的作家是周作人,特别喜欢周作人那种闲适冲淡的小品文,还有废名《桥》那样充满禅趣诗意的小说。朱光潜也创作小品文,却是以说理取胜,知识广博,柔和、流畅而又清晰,像阳光下平原上的河流,缓缓流动,没有汹涌的浪涛和狰狞的岩岸。 面对西方的时候,古典主义者温克尔曼对古希腊艺术的美学概括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希腊杰作有一种普遍和主要的特点,这便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正如海水表面波涛汹涌,但深处总是静止一样,希腊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在一切剧烈情感中都表现出一种伟大和平衡的心灵。”③他认同英国湖畔诗派诗人华兹华斯的那句话:“诗起于经过在沉静中回味来的情绪。”④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湖畔诗人的诗歌创作具有浓厚的田园风味,是一种宁静而秀丽的自然之美。华兹华斯曾有过长期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经历,天性恬静而柔和。人生和自然经由他的“沉静中回味”,变得柔和而圆润。勃兰兑斯说,“在他无论是生活或是诗篇里,也确实难以发现激情。在某些杰出作家的生活中,常能看到某种异常的处境,一起或几起波折,这样那样导致忧郁、砥砺性格或促成多产的明显原因;而在华兹华斯的生活中却找不出任何这一类的机缘。既不曾有先天的不幸造成他的缺陷,也不曾有凶猛的故意憎恶使他惨遭痛苦的煎熬或是在心灵上留下创伤。”⑤因而,华兹华斯的诗风很容易和朱光潜的“无言之美”产生共鸣。因而,他喜欢钱起的诗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把陶潜看成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我在别的文章里曾经说过这一段话:‘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明白古希腊人何以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把诗神阿波罗摆在蔚蓝的山巅,俯瞰众生扰攘,而眉宇间却常如作甜蜜梦,不礴一丝被扰动的神色?’这里所谓‘静穆’(serenity)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型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⑥ 鲁迅的美学追求恰恰与朱光潜相冲突。鲁迅钟情于热烈的激情、力量和反叛的美感。这里面包含着左翼文学的因素,同时,也活跃着拜伦、雪莱等激进浪漫主义诗人的血液。在留学日本时期,拜伦等恶魔诗人深深地吸引了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这样概括拜伦的一生,“则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⑦鲁迅陶醉在拜伦、雪莱等那种如狂风暴雨、闪电雷鸣般的诗风之中。而且,鲁迅还有意识地将恶魔诗风与中国诗风、文化进行对比,对中国“静”的文化及其源头老子却极为不满,认为老子无为而治,“不撄人心”,缺乏激发、振奋人心的激情、力量,令人精神萎靡:“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⑧。即使是屈原的《离骚》也缺乏强劲的反叛力量,“……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⑨到五四以后,摩罗诗人的精神弥漫在鲁迅的创作之中。这表现在两种力量的交织、混合,相互激荡,复杂而充满张力。一方面揭露病苦以便于治疗的社会良知和责任,另一方面则是“个人的自大”、“自己给自己裁判”的勇猛而孤独的反抗。前者在1930年代使鲁迅成为左翼阵营的“同路人”,即使成为左翼的“同路人”,鲁迅也未曾抛弃拜伦、雪莱的精神。鲁迅文学趣味不是线性的延伸,后边完全替代了前面的,而是一种多元因素构成的立体结构,左翼文学因素与摩罗诗人的激情有差异也有交融、共鸣。纵观鲁迅的文学世界,这里有“狂人”、“疯子”的凄厉而勇猛的叛逆嚎叫,有黑色人宴之敖者的以命对命的复仇精神,有悲惨的死亡,有麻木而冷酷的心,有孤独、焦虑和挣扎,有匕首、投枪的寒光。鲁迅呼唤那种“撄人心”的恶魔的声音,“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⑩鲁迅喜欢猫头鹰,用猫头鹰确定自己的文学身份。甚至有人给他起个“猫头鹰”的绰号:“在大庭广众中,有时会凝然冷坐,不言不笑,衣冠又一向不甚修饰,毛发蓬蓬然,有人替他起了个绰号,叫猫头鹰。”(11)他主张冲进现实,向现实挑战,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释放情感,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鲁迅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12)“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体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13) 因此,鲁迅对“静穆”不以为然,却将“热烈”作为一种最高境界。“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14)对于陶潜鲁迅则注意到了他的矛盾性,鲁迅感兴趣的是那个金刚怒目的一面,那个吟诵“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陶潜,那个大胆、赤裸地书写《闲情赋》的陶潜,和关注政治、现实的陶潜,而不喜欢悠然闲适的那个陶潜。其实,鲁迅自己也并非完全没有宁静、闲适的心态,比如写《朝花夕拾》就是从纷乱里寻求一点闲适来,但是,鲁迅在内心深处,却不嗜好这种宁静而微微甜蜜的东西,甚至觉得这种宁静会消磨人的斗志,总是警惕着它。古希腊艺术也并非全是“静穆”,“古希腊人,也许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的罢,这一点我毫无知识。但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我想,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也许和立蛋形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终不见于人一样。”(15)这里既显示出鲁迅的广博学识,也表明了他强烈的嗜好和坚定的文学立场。鲁迅似乎没有过多地关注过古希腊文学艺术,周作人却深通古希腊。鲁迅的修养和见识或许早已经知道古希腊艺术的另一面:热烈。实际上,温克尔曼对古希腊艺术的概括,只是古典主义的一种理解。在他之前和之后,德国的哈曼、赫尔德、诺瓦利斯、荷尔德林直到尼采,都注重古希腊酒神精神的阐释,将酒神的激情、迷狂看成是古希腊诗歌、艺术的重要根基。 艺术趣味往往和人生观、世界观具有密切关系,鲁迅与朱光潜的冲突根植于他们之间人生观、世界观的碰撞。 朱光潜大体上属于那种温和、稳健、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而且,带有浓厚的书斋气质,其间融合着中国佛教、道家思想和西方保守的浪漫主义的底蕴。他的自由是道家文化中那种静逸的自由,是类似湖畔诗派华兹华斯的那种有规矩、有分寸的带有绅士风度的自由,这恰好与陶渊明式的自由产生了极大的共鸣。他并不是没有认识到社会普遍存在着的丑恶,也不是没有意识到现实中人性的肮脏、堕落和人生的艰难、悲苦,他甚至对叔本华的人生即苦的观点也表示理解,但是,他主张以一种超然的心理、冷静的心态对待人生的纷扰、困难和丑恶。他的理想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是陶渊明式的魏晋人格理想。超然心理获得的关键是“摆脱得开”,就如同释迦牟尼遁入深山、静坐在菩提树下的悟道,像苏格拉底、屈原等人那样在生命攸关的时候从容就死,或者如同斯宾诺莎那样拒绝世俗社会的诱惑,默默地坚守自我。人生的许多悲剧就是摆脱不开,就像黑格尔的悲剧一样,黑格尔认为悲剧的本质是不同性格的冲突,每一种性格都按照自己的意志不断追求,最后形成无可挽回的悲剧。为此,朱光潜将“静”作为人生的重要修养,就像周作人那样从纷乱的世事中抽身出来,在忙乱中安下心来,专注自我内心,让心灵平静下来,静观人生。他对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这两部作品不以为然,不喜欢“十字街头”的喧嚣、纷乱,因为这种喧闹、纷乱会淹没自我,淹没人的创造性、独立性。学术、艺术一旦进入十字街头,就要被世俗化、庸俗化,就会被社会习俗即“时尚”和“民众肤浅顽劣”所吞噬。朱光潜在《谈人生与我》中说,有两种人生态度,一种是站在“前台”,一种是站在“后台”。站在“前台”的时候,“我把我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不但和旁人一样,并且和鸟兽虫鱼诸物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16)显然,这是庄子的“齐物”心态,“我把自己看作草木虫鱼的侪辈,草木虫鱼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活著,在炎暑寒冬中也还是那样活着。象庄子所说,它们‘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它们时而戾天跃渊,欣欣向荣,时而含葩敛翅,晏然蛰处,都顺著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它们决不计较生活应该是如何,决不追究生活是为著什么,也决不埋怨上天待它们特薄,把它们供人类宰割凌虐。在它们说,生活自身就是方法,生活自身也就是目的。”(17)站在后台的时候,则是一种审美的心态,超越善恶判断,“我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律看待,我看西施、嫫母、秦桧、岳飞也和我看八哥、鹦鹉、甘草、黄连一样,我看匠人盖屋也和我看鸟鹊营巢、蚂蚁打洞一样,我看战争也和我看斗鸡一样,我看恋爱也和我看雄蜻蜓追雌蜻蜓一样。因此,是非善恶对我都无意义,我只觉得对着这些纷纭扰攘的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件件都很有趣味。”(18)朱光潜又把人生分成两种风格、两种理想:“看戏与演戏”:“世间人有生来是演戏的,也有生来是看戏的。这演与看的分别主要地在如何安顿自我上面见出。演戏要置身局中,时时把‘我’抬出来,使我成为推动机器的枢纽,在这世界中产生变化,就在这产生变化上实现自我,看戏要置身局外,时时把‘我’搁在旁边,始终维持一个观照者的地位,吸纳这世界中的一切变化,使它们在眼中成为可欣赏的图画,就在这变化图画的欣赏上面实现自我。因为有这个分别,演戏要热要动,看戏要冷要静。打起算盘来,双方各有盈亏:演戏人为着饱尝生命的跳动而失去流连玩味,看戏人为着玩味生命的形象而失去‘身历其境’的热闹。能入与能出,‘得其圜中’与‘超以象外’,是势难兼顾的。”(19)尽管他试图以客观的态度对待这两种人生风格,侃侃而谈,旁征博引,中西贯通,但是,他最心仪的却是“看戏”的人生态度。 用朱光潜的眼光看,鲁迅恰好是“演戏”的人生,是热烈而躁动的人生。他属于激进、激情的浪漫主义者或硬朗的存在主义者,1930年代又融合了“左翼”的反抗精神。在他接受摩罗诗人的影响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克尔凯郭尔、尼采等存在主义哲学,如果说朱光潜更具有古典主义的意味,而鲁迅则更倾向于浪漫的现代的人生观。“左翼”文化之所以对鲁迅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它那种强烈的反抗精神。但是,左翼文化并没有取代他的浪漫的激进的生命文化,而是矛盾地统一在他的身上,那种浪漫的激进的生命体验,借助于左翼文化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他仍然赞扬拜伦,认同尼采。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看,鲁迅也喜欢魏晋人格,但是,他喜欢的是嵇康、阮籍等那种富于激情、反抗的刚烈性格。鲁迅骨子里流淌着道家文化的狂放血液,而不是“静逸”的气韵。他认为世界总是处在一种冲突、矛盾和运动的状态,不存在一个平和世界,社会里充满着黑暗与光明、丑恶与美好以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复杂斗争,渗透在人的生活之中和个体生命之中。根本不存在一个完全和谐的黄金世界,即使是黄金世界也会把叛徒处死。因此,他以一种“精神界之战士”的激情和力量投入现实之中,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就如同他笔下的“过客”那样,将人生看做是永无休止的奔走过程,同时,他的内心也充满着矛盾、焦虑、纷争。像尼采那样,他推崇野性的自然,喜欢“狼”、“野猪”、“野牛”的狂野不羁,他觉得中国人的人性当中缺乏的恰恰是野性,人们跪伏统治者脚下,如驯服的家畜。他感叹中国青年的温顺,低眉弯腰,唯唯诺诺,呼唤青年勇敢地直起身来。他一生介入文坛各种各样的冲突之中,却无怨无悔,依然倔强、顽强地坚守着他那热烈、峻急的自我。鲁迅晚年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中说,中国社会往往要把孩子塑造得“静”一些,而日本却偏向于“动”,在照相的时候,“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20)“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21)鲁迅晚年在那组著名的“文人相轻”的文章里,尖锐批评文人圆滑、懦弱,主张文人“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无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轻’不可的!”(22)“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佬。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23)“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24) 有意思的是,鲁迅与朱光潜都深受尼采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们所接收的精神却各有不同。 朱光潜接受了尼采酒神与日神的二元论,却更注重日神精神,用日神精神综合、融汇酒神,甚至让酒神臣服在日神的脚下。晚年的朱光潜把自己看成了尼采的信徒,说尼采的悲剧观念在美学、人生观方面均对他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读者都认为我是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信徒,现在我自己才认识到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的信徒。在我心灵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25)在《悲剧心理学》中,朱光潜对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是尼采最好的著作,并有对叔本华、尼采的专章论述,但是,他却强调日神的重要性,“靠了日神的奇迹,酒神的苦难被转变成一种幸福。”(26)他的《文艺心理学》,在谈到“刚性美”和“柔性美”的时候,也用酒神与日神的区别,酒神是刚性美,日神则是柔性美,但是,朱光潜在文艺实践上更倾向于委婉、隽永、微妙的日神境界。朱光潜经常用尼采的酒神与日神解释艺术和人生,他喜欢按照这种二分法来区别不同艺术风格和人生风格。在《心理上个别的差异与诗的欣赏》中认为,诗歌有两种,一种是明白清楚的,一种是迷离隐约的,这两种诗歌来自于两种不同的“心理原型”即尼采的酒神与日神、法国心理学家里波的“造形的想象”和“泛流的想象”。朱光潜对这两种心理原型有着非常透彻的认识,他说,“尼采在《悲剧的起源》里拿两个希腊神象征艺术上两种相反相成的精神。一个是日神阿波罗。他以光辉普照世界,一切事物有他才呈现色相。他的心灵永远还是恬静肃穆,忧喜不动于怀地观照人生世相的‘真如’。极悲惨和极丑陋的情态经过他的观照都变成灿烂庄严的意象。这种精神所产生的艺术是史诗,图画和雕刻。一个是酒神狄俄倪索斯。他常在沉醉的状态中,受狂热的情感鼓动,随着生命的狂飙巨浪旋转,不肯停止一顷刻来静观事物的情态,只一味地没在生命的中心,领略它的变化。他知道人生是苦痛的,所以要在激烈动荡中忘去苦痛。这种精神所产生的艺术是抒情诗,跳舞和音乐。这两种精神和艺术的分别是静和动,客观和主观,想象和情感,冷和热的分别,也是我们在本篇所说的‘明白清楚’与‘迷离隐约’的分别。”(27)朱光潜应该是属于前者。朱光潜认为尼采是用日神阿波罗化酒神狄俄倪索斯的精神,“尼采专就希腊艺术着眼,以为它的长处在以阿波罗精神化狄俄尼索斯精神。希腊艺术的作风在后来被称为‘古典的’,和‘浪漫的’相对立。”(28)朱光潜将这两种精神扩展到人的性格上,在《谈冷静》中,朱光潜开篇就谈尼采的酒神与日神,“说冷静的、纯正的、情理调和的人是‘古典的’;热烈的、好奇的、偏重情感与幻想的人是‘浪漫的’。”“这两种性格各有特长,在理论上我们似难作左右袒。不过我们可以说,无论在艺术或在为人方面,浪漫的都多少带着些稚气,而‘古典的’则是成熟的境界。”(29)这和他那种以“看戏”的态度对待人生也是一致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朱光潜把艺术看成是一种对人生苦难的心理超越,这种超越就是将人生看成艺术,就像尼采那样将人生审美化。人生充满了苦难,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但是,日神的表象世界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精神避难所。 这或许是朱光潜对尼采的有意误读。在尼采那里酒神精神显然更为重要。尼采性格激情、峻急而热烈,他在自传中不无骄傲地宣称,“我是哲学家狄俄倪索斯的弟子”(30)。他喜欢那种更有刺激性的烈性酒,“少量的冲淡了的烧酒竟会引起心烦意乱。但如果是烈酒,我竟会像水手般地开怀畅饮。甚至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表现出这种勇敢精神。”(31)尼采说《悲剧的诞生》,“这本书有两项带根本性的革新,一、对希腊人的狄俄倪索斯现象的首次心理分析,这本书把这一现象看成整个希腊艺术的根据之一。二、对苏格拉底主义的认识:首次认识到苏格拉底是希腊消亡的工具,是典型的颓废派。”(32)前文已经提及,尼采并非是古希腊的酒神精神的发明人,但是,他却是把酒神精神提升到哲学高度并予以充分肯定的第一人。尼采的确和叔本华一样,把人生看成是苦难,但是,他并不主张超脱,他的将人生的艺术化是将酒神精神艺术化,是对不断的动的过程的艺术化,这里的逻辑是:尽管人生是充满苦难和不幸的,但是,这恰好是人的勇敢无畏、大胆创造的广阔天地。 鲁迅受尼采影响也非常大,但是,鲁迅所注重的却是尼采那种以意志、力量、激情为核心的酒神精神,即峻急、激烈的个性主义、存在主义式的个人选择,以及对社会文明、历史文化传统的怀疑、反抗、批判精神。 在鲁迅早期的《文化偏至论》中,“若夫尼佉,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33)鲁迅赞成尼采的“天才”——“超人”论及其对庸众的批判。在鲁迅笔下,以尼采、叔本华、克尔凯戈尔、斯蒂娜、易卜生等“新神思宗”,都是“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34)“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35),这和鲁迅对“摩罗”诗人的热情赞扬相互呼应。在五四时期,鲁迅呼唤“个人的自大”,反抗“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将尼采看成了旧事物的扫荡者和反叛者。鲁迅的“狂人”既可以看做是“摩罗诗人”的变型,也可以看做是尼采酒神精神的象征。《狂人日记》明显具有尼采的酒神与日神的二元论色彩。“狂人”混乱而梦魇般的内心世界是酒神力量的显现,而那种一潭死水般的——文言小序所呈现出来的现实则属于日神。本体的主观意志的酒神一旦进入世界的表象,凝固为可感的现实就被压抑、淹没。鲁迅那种决绝、激烈的反传统文化,锐利而深刻的文化批评,和尼采文风、精神气质极为相似。鲁迅的《野草》可以看做是《狂人日记》的变型。《野草》的世界是“动”的世界,充满着焦虑、躁动、挣扎、痛苦、冲突和无法化解的矛盾,这是《野草》抒情主人公内心状态的投射,也是鲁迅精神世界的反映。《野草》构建了一个二元对抗的世界:酒神与日神的世界。庸众、世俗伦理构成了社会、文化的总体秩序,是日神世界,而诸如“这样的战士”、“叛逆的猛士”、“过客”等则构成一个酒神精神,带有尼采式超人气息。《铸剑》中黑色人的复仇明显带有尼采、拜伦式英雄的印记,以恶为善,带着虚无的色彩,是凶悍而孤独的英雄,而统治者和大众则构成了一个凝滞的现实。鲁迅喜欢“战士”这样的称号,他“好斗”,这也带有尼采的烙印,尼采就愿意把自己称为文化战士。 在与陈西滢的冲突之中,鲁迅质疑“公理”,嘲讽“公理维持会”,这显示出他对稳重、平衡和平静的厌恶。“我早有点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听说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开过了。我没有见,我就不以为有杏花和碧桃。”(36)“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37)鲁迅说,“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38)这种对“公理”的质疑,显然和尼采的视角主义认识论具有密切关系。尼采认为,人面对世界的时候,不可能是全知视角,因而也不可能有普遍真理,真理是基于个人所处的位置、个人的好恶和价值而产生的。人尽管很渺小,却不得不把自己当成一个品评的尺度。人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衡量万事万物。古希腊哲人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到了尼采这里变成了更尖锐的个人主义的认知原则:人只能以个人的角度去衡量万物。鲁迅之所以拒绝当导师,也有这种视角主义的影响:只能自己给自己裁判,只能按照自己的本性,按照自己的身体、心理的全部感觉进行评判,释放自己的激情,将自己的火热的意志喷发出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四平八稳。 ①②朱光潜:《无言之美》,《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下同),第65、66页。 ③[普鲁士]温克尔曼:《希腊人的艺术》,邵大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④朱光潜:《诗论》,《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63页。 ⑤[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四分册,徐式谷、江枫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61页。 ⑥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页。 ⑦⑧⑨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81-82、67、69页。 ⑩鲁迅:《“音乐”?》,《鲁迅全集》第7卷,第54页。 (11)沈尹默:《鲁迅生活中的一节》,《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 (12)鲁迅:《忽然想到(五)》,《鲁迅全集》第3卷,第43页。 (13)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4页。 (14)(15)鲁迅:《“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6卷,第430、427页。 (16)(17)(18)朱光潜:《谈人生与我》,《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57、58、59页。 (19)朱光潜:《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20)(21)鲁迅:《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全集》第6卷,第81、81-82页。 (22)鲁迅:《“文人相轻”》,《鲁迅全集》第6卷,第299页。 (23)鲁迅:《再论“文人相轻”》,《鲁迅全集》第6卷,第336页。 (24)鲁迅:《七论“文人相轻”——两伤》,《鲁迅全集》第6卷,第405页。 (2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译本自序》,《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210页。 (26)朱光潜:《悲剧心理学》,《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362页。 (27)朱光潜:《心理上个别的差异与诗的欣赏》,《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466页。 (28)(29)朱光潜:《谈冷静》,《朱光潜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30)(31)(32)[德]尼采:《看哪这人》,张念东、凌索心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4、68页。 (33)(34)(35)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2、52、54页。 (36)(37)鲁迅:《新的蔷薇》,《鲁迅全集》第3卷,第291、292页。 (38)鲁迅:《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全集》第3卷,第244页。标签:鲁迅论文; 朱光潜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化论文; 尼采哲学论文; 美学论文; 酒神精神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文学论文; 朱光潜全集论文; 悲剧的诞生论文; 读书论文; 古希腊论文; 野草论文; 哲学家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