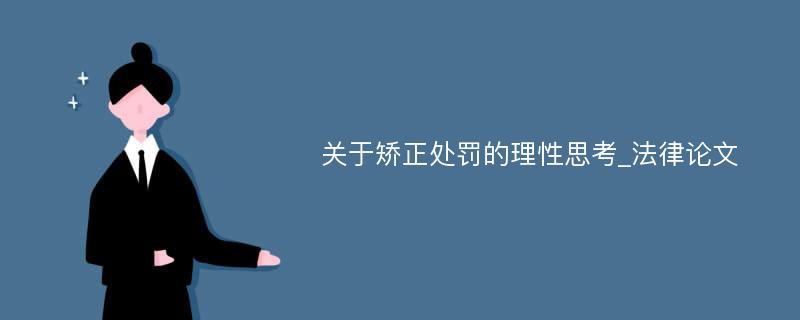
矫正刑的理性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历史的车轮由近代拐入现代,刑罚由等价时代步入矫正时代,刑罚的重心由对犯罪的等价报应与等价威慑转向对犯罪人的隔离、教育、感化与改造。等价刑体制自此崩溃,以个别预防作为刑罚的基本理性与唯一的目的的矫正刑体制应运而生。本文立足于刑罚的基本理性,(注:本文所称的刑罚的基本理性或刑理,系指笔者所提出的报应——功利统一化刑罚理性。详见邱兴隆著:《刑罚理性导论——刑罚的正当性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对矫正刑这一兴起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衰落于本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曾作为“科学”的刑罚模式为世界各国刑法所广为采纳的刑罚体制予以反思,力图在展现其表征的基础上,揭示其理论基础与认识论上的成因,全面评价其利弊得失。
矫正刑的表征
以预防犯罪人再犯罪为基点的矫正刑,使刑罚的视角由行为转向了行为人,由一般人转向了个别人,因而在制刑、动刑、配刑与行刑诸方面显示出其不同于以行为与一般人为视角的威慑刑。
一、制刑的表征
矫正刑在制刑上的总的特点是削弱刑罚的惩罚性,增强其教育性,具体表现如下:
1.废除死刑。在矫正时代,在被认为与杀人罪极具等价性且具有无与伦比的一般威慑功能而幸存于等价时代的刑罚体制之中的死刑,因不符合矫正理念而首当其冲地受到抨击,进而成为此间制刑者力图废除、以使刑罚体系由等价化转向矫正化的首选目标。
矫正刑从理论到实践,缘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此同时,在此间,出现了第一次世界性的废除死刑的高潮。如:意大利于1889年从立法上正式废除死刑;美国在1853年前只有密西根、罗得岛与威斯康星三州废除死刑,但自1853年到1915年缅因等五州相继废除,(注: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7页。)自1877年至1928年,南美的哥斯达尼加、尼瓜多尔、乌拉圭、哥伦比亚与北欧的冰岛也相继废除死刑。(注: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所列“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一览表”。)
虽然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死刑在此非常时期的价值受到非常重视死刑,其废除因而在此间被搁置于一边,但随着大战的结束,废除死刑又被许多国家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因而出现了又一次废除死刑的高潮。如:自1949年至1969年,原西德、洪都拉斯、摩纳哥、委内瑞拉、多米尼加、奥地利、梵蒂冈等国均从立法的角度彻底废除了死刑。(注: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所列“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一览表”。)
2.简化自由刑。矫正刑着眼于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因而注重自由刑的积极作用,相应地,等价刑时代基于惩罚与威慑的需要而设置的多种不同的自由刑之间的严厉性等级之别,对于教育、改造犯罪人已显不适应,因此,自由刑的统一化成为矫正时代制刑的又一特点。如:英国1948年的《刑事审判法》将自由刑简化为监禁一种。
3.改造自由刑。与注重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相适应,削减自由刑的严厉性,并赋予其教育、感化、职业训练与心理矫正等有助于对犯罪人的矫正的新内容,也是矫正刑在制刑上的重要特点。虽然此间在刑法典中明文规定自由刑应以教育、感化与心理矫正等为内容者并不多见,但在许多国家的监狱法规中,却有相应的规定,甚至为联合国有关文件所规定。如:联合国第一届防止犯罪与罪犯处遇大会通过的《在监人犯最低标准规则》规定,“对于一切受行刑人,可因教育而受益者,应继续施教……”,“受行刑人之教育,在可能范围内,应与国家之教育相统一”,“劳动应……使受刑人能维持并增进其开释后之谋生能力”,“受行刑人劳动,应以……职业训练为主要目的。”显然,在这里,教育与职业训练被作为矫正手段所确认。
4.改良资格刑。由于资格刑本身不但不具有改造性,而且毁损犯罪人的名誉,使其自尊心受到挫伤,并易于给其留下耻辱的标记,不利于犯罪人的改过自新,有碍其再社会化,不符合矫正理念,因此,在矫正时代,不少国家要么是废除资格刑,要么是使资格刑非刑化。如:丹麦在1951年废止市民权利剥夺制度。而日本刑法典则在刑法中不再将资格刑作为一个刑种,而只在诸如《众议院选举法》之类的某些法律中规定禁止罪犯行使选举权之类特定权利,从而实现了资格刑非刑化。
5.增设保安处分体系。矫正刑的基本理念是教育、改造犯罪人,但并不排除对不堪教育、改造者或尚未构成犯罪的人采取与社会相隔离的手段而使之不为害的可能性。这便是所谓“矫正可以矫正者,使不可矫正者不为害”。正是如此,矫正时代的制刑者在改造传统刑罚体系,使之符合矫正的需要的同时,又在传统刑罚体系之内增设或在其外单设了使具有人身危险性者与社会相隔离的保安处分体系。如:前苏联1922年、1926年刑法,古巴1926年刑法以及瑞典1959年保护法草案等,都在传统刑罚体系中加设了保安处分措施,使之与传统刑罚方法组合成新的刑罚体系,而南斯拉夫1929年刑法、丹麦1930年刑法、意大利1930年刑法、波兰1932年刑法等则在传统刑罚体系之外增设了与之相并列的保安处分体系。(注:这便是通常所谓的刑罚与保安处分一元化与二元化。详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次修订版,第467-474页。)
二、动刑的表征
矫正刑基于对犯罪是犯罪人自由意志的结果的否定而理所当然地否定了法律责任是动刑的前提,而代之以社会责任,即社会有义务教育与矫治有犯罪的人身危险性的人。因此,人身危险性的有无构成社会承担所谓教育与矫治义务与发动刑罚(或称予以“处遇”)的前提,作为等价刑之发动前提的定罪被作为正刑之发动前提的人身危险性的测定所取代。相应地,矫正刑的发动具有如下特点:
1.对不具有责任能力者,只要其具有人身危险性,便可予以保安处分。出于社会防卫的需要,精神病人与未达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虽因对刑罚具有不适应性而不应以刑罚作为教育矫治的手段,但在其具有危害社会的人身危险性的情况下,有必要将其与社会相隔离,以消除其危害社会的可能性。相应地,对有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人适用强制医疗、对有人身危险的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者适用保护管束等保安处分便成为必然的选择。如:1921年由菲利拟定的意大利刑法草案规定,对精神病犯应予以交监管所、送犯罪狂病院或特别劳作所,对少年犯应予以监视、交职业感化院,交少年劳作所或农业所或者交监置所。前苏俄1961年刑法典规定,对精神病犯应安置在普通的精神病院或专门的精神病院。1930年意大利刑法典规定,未满14岁的人犯法定罪行,且有危险者,可交司法感化院或付保护管束。这表明,矫正刑体制下的保安处分并不将不具有刑事义务能力者排除在发动对象之外,从而突破了威慑刑与等价刑体制下刑不及无能的限制。
2.对于不构成犯罪者,其具有人身危险性,可以予以保安处分。是否构成犯罪与有否人身危险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虽不构成犯罪但具有某种危险倾向者,同样可以构成人身危险的载体,从防止其未然的危害着眼,可以将其作为适用保安处分的对象。如:1930年意大利刑法典规定,不能犯未遂与教竣未遂虽不视为犯罪,但应予以保安处分。这表明,矫正刑体制下的保安处分也不以违反刑事法律义务为发动的前提,从而突破了等价刑体制下动刑以违法行为主体为对象的限制。
3.虽然构成犯罪但不具有人身危险性者可以不予动刑。正如未实施犯罪者未必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一样,已实施犯罪者也未必具有人身危险性。因此,对虽然构成犯罪但不具有人身危险性者,从其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角度着眼,可以不对之定罪动刑或虽予定罪但免予动刑。如:英国与美国在矫正时代创立并广用缓起诉与缓判刑制度。缓起诉制度为对已犯罪者暂不予以有罪指控,缓判刑制度为对犯罪者虽作有罪认定,但暂不予判刑。1953年韩国刑法典也确立了刑之暂缓宣告制度,规定构成犯罪者在作有罪宣告的同时暂不予判刑。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典确立了免刑制度,规定对应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的人可以免除其刑。因此,矫正刑的发动也突破了等价刑的有责必罚的限制,实现了刑事责任主体与动刑客体基于不存在人身危险性的相对分离。
三、配刑的表征
与以人身危险性的有无作为动刑的根据相适应,矫正刑的分配以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亦即个别预防的需要为根据。刑罚的性质、严厉性程度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相适应成为矫正时代配刑的基本准则。具体表现为如下特点:
1.重惩累犯、惯犯。累犯与惯犯是人身危险最大的两类罪犯,对其所分配的刑罚自然严厉。因此,在矫正时代的各国刑法中,累犯与惯犯首当其冲地构成重惩的对象。如:在法国,1885年颁布法律对职业犯与常习犯新设了终身流放到殖民地的刑罚,1891年又颁布法律加重了对累犯的刑罚。在美国,自1927年至1929年,颁布了若干关于累犯的法律,规定对于再犯应处不低于最低法定刑和不高于最高法定刑二倍的剥夺自由,对于被四次定罪的累犯,应处没有提前释放之可能的终身监禁。在意大利,1930年以来的不少法律规定,对于习惯犯、职业犯或“倾向犯”,应加重判处2年以上3年以下或者4年以上之移民区监禁并终身剥夺其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在德国,1933年颁布了“关于危险习惯犯与保安、改造处分”的法律。该法规定,对于危险习惯犯,只要认为有必要,便可延长其刑期。在丹麦,1933年生效的刑法典规定,对两次实施不同犯罪的人,应加倍惩罚。
2.少年犯处理专门化。由于少年犯的思想尚未定型、可塑性大,因而在通常情况下不应对之处以传统的刑罚,而应采取专门的处理措施。因此,在矫正时代,绝大部分国家纷纷修改刑法,用特殊的处理措施取代对少年犯的传统制裁。1899年,美国的芝加哥率先制定了少年法,确立了少年法院审判制度。自此以后,各国相继仿效,专设了少年法院。按照少年法的规定,对于少年犯,即使认定其有罪,一般也不处以刑罚,而分别采取如下措施:①交付特定的保护观察人员,予以教育;②委托给环境良好的家长教养,或送入特设的教育机构;③责成家长教养;④对于恶性较深者,或有生理疾病者,交付特定的感化机关,加以矫正教育,或进行治疗。所有这些措施,至少在理念上都不带有惩罚的成份,即属于非刑化措施,其之适用于少年犯,体现了对人身危险性小的少年犯的处理的非刑化。即使在非处刑不可的情况下,对少年犯的配刑也明显地有别于对成年犯的配刑,具体表现为对少年犯通常不适用死刑或无期徒刑,以及从轻或减轻处罚。
3.采用不定期刑。为刺激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的改造,使刑罚的轻重直接与犯罪人的悔改表现相适应,矫正时代实行了自由刑的不定期分配制。根据这一制度,判决所确定的刑期是相对不确定的,即只确定上、下限,而不能确定具体的期限。这一制度最先于1869年在美国的纽约州开始施行,适用对象是16岁至30岁的青少年犯。经1910年与1925年举行的第八、九次国际监狱会议的肯定与倡导,美国各州和英国、芬兰、瑞典、挪威、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刑事立法相继采用了不定期刑,主要适用于少年犯、累犯等特殊犯罪人。
4.短期自由刑非刑化。由于短期自由刑存在既不足以使犯罪人得到有效的改造又易使犯罪人互相感染的弊端以及与对犯罪人的教育、矫正不相适应的缺陷,在矫正时代,各国刑法普通采取非刑化措施取代短期自由刑,即对本应判处短期自由刑的犯罪人改为适用其他措施。如:英国创立了缓起诉与缓判刑制度,授予检察官与法官对可能适用短期自由刑的犯罪人暂时不予起诉或判刑的权力。还有的国家刑法规定对应处短期自由刑者可易科罚金刑。(注:拙著:《刑罚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5.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如前所述,死刑是一种不具有教育性因而与矫正理念相冲突的刑罚。因此,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死刑的分配受到严格限制,许多国家将死刑的分配限于几种或一种犯罪。如1929年,墨西哥对普通犯罪废除了死刑,瑞士、意大利与以色列也分别于1942年、1947年与1954年对普通犯罪废除了死刑,从而使死刑在立法上的分配只限于某些政治或军事犯罪,从而大大缩小了死刑的分配范围。(注: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而另有相当多的国家,则从司法的角度控制死刑的适用,以致其名存实亡。如:日本在1918年仅判处40人死刑,自1919年至1942年,每年判处死刑的人数最多为60人,最低则只有12人;自1950年至1967年,每年判处死刑的人数最多为62人,最低则只有7人。(注: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120页。)同样,在素有“犯罪王国”之称的美国,自1931年至1969年,适用死刑最多的一年的人数只有199人,而适用死刑最少的年份只有1人。(注: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四、行刑的表征
在矫正时代,理所当然地,刑罚的执行以教育、矫正犯罪人为鲜明特色。相应地,行刑表现出如下特点:
1.赦免死刑。根据矫正刑的基本理念,凡可矫正者,均应予以矫正,只有不堪矫正者才应以死刑彻底剥夺其再犯罪的能力。据此,在相当多的国家,对于既已判处死刑的人,也不一定予以实际执行,而是通过赦免的途径尽量减少死刑的实际执行,以给犯罪人留有改造的余地与自新的机会。如:在日本,在1875年至1881年间,凡判处死刑者,无一例外地均被实际执行。但自1882年始,每年所实际执行的死刑少于所判处的死刑,如:1897年实判死刑80人,但只有21人被实际执行,死刑的实际执行率仅为25%左右。(注: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0页“表二”与“表一”对比以及第129页“附表一”与122-123页“附表二”对比。)同样,自1918年至1966年,所判处的死刑也只有一部分实际执行。(注: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70页“表二”与“表一”对比以及第129页“附表一”与122-123页“附表二”对比。)
另据联合国1967年的死刑调查报告表明,在1961-1965年间,美国宣告了492起死刑,但实际执行的只有132起,加拿大宣告55起,只执行4起。在调查所及的国家,此间共宣告2066起,但实际执行者仅为1033起。(注:拙著:《刑罚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页。)
2.创设并大量适用缓刑与假释。缓刑与假释,作为节俭用刑、刺激犯罪人改过自新的两项重要制度,是矫正时代的产物,并成为行刑矫正化的鲜明标志。1870年,在美国的波斯顿,缓刑制度应运而生。此后不久,美国的其他州以及其他国家都把缓刑当成鼓励人身危险性较小的偶犯与初犯等改造的措施之一予以采用。如:英国在1887年、德国在1895年、比利时在1888年都通过对刑法的修改而增设了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世界各国的缓刑适用率相当高,而且呈现出日益上升的趋势。如:在日本,1955年至1976年有大约60%的被判自由刑的罪犯被宣告缓刑。在法国,1960年有39.3%的被判拘禁刑者被宣告缓刑。到1973年,这一比率已上升到58%。在缓刑创制前数10年,假释制度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已具雏形。但是,这一制度之被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纳则几乎是与缓刑制度的兴起同步,尤其是其之被广为采用,则是19世纪末以后的事,因而同样是矫正刑之兴起的表征。英国于1853年正式采用假释制度,美国直至1910年才有2/3的州增设了这一制度。与缓刑之适用一样,假释之在实践中的适用率也相当高。如:在美国,1970年共有18个州的假释率高达75%。在日本,因假释而出狱者的比率也远远大于刑满出狱者,1954年的假释率高达79.5%。(注:拙著:《刑罚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3.行刑社会化。为避免自由刑的执行导致犯罪人与社会的不适应,矫正时代实施了有利于对犯罪人的改造的行刑社会化措施。具体表现为改良行刑机构之结构,创设狱外工作制度、采用归假制以及实行周末监禁或半周末监禁制等。就改良行刑机构之结构而言,主要表现为监狱由封闭式走向开放式。自1891年始,瑞士监狱工作者凯勒黑尔斯(M.keuu-erha)便开始尝试将传统的封闭式监狱结构改造成开放式。他在伯尔尼创设了无狱墙、栅栏等戒备设施的新型监狱并使狱内的生活条件尽量与外界保持同步。由于这种新型监狱寓有狱于无狱之中,狱中的生活与外界无异,因而颇受受刑人欢迎,狱内秩序井然,成效卓著,从而为许多国家相继仿效,欧美多数国家因而都建立了类似的开放式监狱。就狱外工作制度而言,其要旨是责令受刑人在行刑机构外与普通人在同样条件下工作,但下班后,其回到特设机构受押。在1880年左右,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女监,首开受刑人在监外从事社会性工作的先例。至1913年,美国的威斯康星州通过立法,将这一制度予以正式认可,规定对于犯轻罪的轻刑犯,可由法院作出判决后,在监外从事社会性工作。这一制度相继为英、美、法、德、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荷兰等国采用。就归假制而言,其指的是对正在执行自由刑的犯罪人,给予一定期限的假日,允许其返家与亲人团聚。作为沟通犯罪人与社会之联系的桥梁,这一制度也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而被许多国家所采用。瑞典、美国的某些州、英国、西德等国都在其行刑法或监狱法中规定了归假制。就周末监禁或半监禁制而言,其主要为比利时等国所采用。周末监禁是对因特定犯罪而被判处1个月以下自由刑者,以星期六上午2时至星期一上午6时之假日监禁代替,监禁1日折抵刑期2日。半监禁则是对被判处3个月以下短期自由刑者,白天允许其在社会上照常工作或就学,但夜间及周末须在监狱中拘留。
4.行刑人道化。矫正时代,由于注重对犯罪人的矫正,因而重视对其的感化。相应地,以尊重犯罪人的权利、提高其待遇等为内容的人道化措施受到应有的重视。如:1957年,联合国通过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具体规定了犯人在各方面的最低限度待遇标准。瑞典、英国、德国等国的监狱法都规定犯罪人在行刑期间可以与家属及亲友定期通信或接见,而且还为受刑人提供了必要的医疗卫生设施等。
5.行刑教育化。注重对受刑人的教育与感化是矫正时代行刑的基本特征之一。由此,刑罚尤其是自由刑的执行由消极的隔离、惩罚转向积极的教育、感化与矫正,对受刑人的品德教育、职业训练、心理矫治等成为了行刑的重要内容。
6.行刑个别化。在行刑方式上,矫正刑的执行,以受刑人的不同特点为根据,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执行,以适应矫正犯罪人的需要,即实现行刑个别化。如:将成年犯与未成年犯、累犯、惯犯与初犯、偶犯分别行刑,以免其互相感染,对少年犯予以高于成年犯的待遇,并予以特殊的教育、感化等等。
7.行刑规范化。由于行刑已作为一个积极教育、矫正受刑人的过程,其远比单纯的隔离与惩罚要复杂得多,因此,在矫正时代,行刑的规范化不可避免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其最明显的标志便是各国在此间均制定了诸如行刑法、监狱法之类的法律,用以确定行刑者与受刑人的权利与义务,以规范行刑活动,确立行刑的标准。如:日本随1908年新刑法的施行而颁布了监狱法及其实施规则,首次将监狱制度以立法方式予以确定。在中国,清末也制定了历史上的第一部独立的监狱法规即《大清监狱律草案》。(注:但未实施。)此后,北洋政府时期与国民政府时期也分别颁布了《中华民国监狱规则》与《监狱行刑法》。
矫正刑的理论基础
矫正刑在19世纪末的兴起与在20世纪前半期的盛行,是新的哲学与刑事学理论崛起的结果。构成矫正刑之哲学基础的是实证主义哲学,构成其刑罚学基础的是以剥夺犯罪能力论、社会防卫论与矫正——隔离论为核心的个别预防主义。
由法国哲学家孔德创始于19世纪前半期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是主张哲学不应研究事物的本质与本源,即不应追问世界“为什么”(why),而只应研究世界“是什么”(is),然后去研究“怎么做”(how)。根据这种理论,哲学的价值在于立足现实,解决问题,而不在于揭示现实背后的客观规律性。换言之,科学只是对经验事实或经验现象的描写与记录,既不反映任何客观规律,也不反映事物的本质。这种以立足现实、解决问题为方法论的哲学理论,构成对以康德、黑格尔等为代表的以解释事物与世界之本质与本源为出发点、以逻辑演绎为方法论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全盘否定,同时也就彻底否定了理性主义哲学所主张的人是理性动物、具有自由意志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而代之以人是主观感觉的奴隶,其行动完全受制于经验事实与经验现象,人的意志在主观感觉面前无能为力的哲学命题。(注:关于实证主义哲学的基本主张及其对实证主义刑事学的影响,陈兴良博士在《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第1版)中已作详尽评述,在此不作赘述。)这种从哲学上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否定,毫无疑问地摧毁了等价刑赖以存在的理论根基。这是因为,法律报应论与威慑论均是奠基于犯罪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因而具有可责性与可控性这一命题之上,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必然否定人对犯罪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与人可因对刑罚的畏惧而不敢犯罪。因此,可以说,实证主义哲学在摧毁理性主义哲学的同时,也就为等价刑举行了葬礼。
然而,实证主义哲学只是为矫正刑的崛起廓清了地基,而不构成矫正刑的直接母体。作为矫正刑之直接理论渊源的是作为实证主义哲学在刑事学上之应声虫的实证主义刑事学。
受实证主义哲学观念与方法论的影响,在19世纪下半期,在刑事学领域崛起了刑事实证学派。与实证主义哲学同理性主义哲学针锋相对相适应,实证主义刑事学派也与刑事古典学派分庭抗礼。以龙勃罗梭(Ce-sare Lonboroso,1835-1909)、菲利(Enricl Ferri,1856-1929)、加罗法洛(Baron Raffaele Garofalo 1852-1934)与李斯特(Franz von Liszt 1851-1919)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刑事学派撇开刑事古典学派所推崇的理性思辩与逻辑演绎的方法,而以实证的方法着手,从犯罪人的生理特点、心理素质或社会环境、生活条件等诸种综合因素中来考察犯罪的原因,并从经验考察、实证研究与定量分析中得出犯罪是遗传基因或社会因素的产物的结论。根据这一结论,实证主义刑事学派认为,人的意志完全受生理或外在的社会因素的制约,不具有自由性。即是说,人的生理特征或社会环境决定了人必然犯罪,其在是否犯罪之间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社会没有权力让犯罪人就犯罪承担责任,也不可能借助刑罚的惩罚使人们产生畏惧而不敢犯罪。相反,社会应该对犯罪人承担治疗或矫正的义务,也只有通过治疗或矫正犯罪人,才可使社会免受犯罪之害。这便是所谓社会责任论。
与社会责任论的提出相对应,在刑罚理论上,实证主义刑事学派提出了以社会隔离论、社会防卫论与矫正——隔离论为内核的个别预防中心论。(注:关于个别预防主义及其分野,将在《刑罚理性辩论——刑罚的正当论批判》中详细评说。)
对犯罪是自由意志的产物的否定必然地构成对作为等价刑之根基的法律报应论与一般预防论的同时否定,社会责任论对个人责任论的取代必然地使刑罚的视角转向了防止犯罪人再犯罪。正是在对报应论与一般预防论的这种否定中,龙勃罗梭提出了剥夺犯罪能力论、菲利提出了社会防卫论、李斯特提出了隔离——矫正论。
龙勃罗梭在犯罪原因论上的初始主张是遗传论即基因决定论,认为犯罪的唯一原因是遗传,与此相适应,他提出,防止天生犯罪人犯罪的唯一途径是剥夺其犯罪能力,具体的说,便是:对尚未犯罪但有犯罪倾向的人实施保安处分,即预先使之与社会隔离;对于具有犯罪生理特征者予以生理矫治,即通过消除犯罪人的生理特征而消除犯罪之源;将危险性很大的人流放荒岛、终身监禁乃至处死。(注:拙著:《刑罚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42-43页。)
菲利在犯罪原因论上主张生物、地理与社会三因论,认为犯罪是生理因素、地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综合结果。相应地,他主张以社会防卫手段取代刑罚,即取消具有惩罚性的刑罚手段,而代之以立足于防止犯罪人再犯罪的社会防卫方法。这种社会防卫方法,便是保安处分。
李斯特在犯罪原因论上主张行为者人格特点与社会环境二因论,即认为犯罪是行为者个人因素与周围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应地,其主张,“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使不可矫正的罪犯不为害。”即认为刑罚对于可以教育矫正的罪犯应是教育、矫正的手段,而对于不可教育、矫正的罪犯则应是使之与社会相隔离、阻止其犯罪的手段,从而提出了矫正——隔离二元刑罚目的论。
剥夺犯罪能力论、社会防卫论与矫正——隔离二元论,虽然立论有别,但总的说来,都是主张刑罚的目的在于防止特定的个人再犯罪,即个别预防。而且,其立论的前提都是否定犯罪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从而否定报应与一般预防作为刑罚的根据的合理性,因而在本质上并无不同。正是这种立足于社会防卫的需要、主张对犯罪人予以消极地剥夺犯罪的能力、积极地予以教育改造的个别预防刑罚论,构成矫正刑的理论基石。龙勃罗梭的剥夺犯罪能力论之被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刑法,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刑法采作种族灭绝、去势等的“科学根据”而产生的直接影响自不待言;菲利的社会防卫论对前苏联早期刑法的影响亦是定论,至于由其以社会防卫论为指导思想而提出的刑罚与保安处分一元化的“社会防卫手段”体系之于矫正时代制刑的影响、其基于同一理论而提出的不定期刑对此间的配刑与行刑体制的影响等更是巨大而深远;而李斯特的矫正——隔离论则甚至直接规定了矫正刑模式,从理念上构成以消极剥夺犯罪能力、积极教育与矫正犯罪人为内容的矫正刑体制的直接渊源。
矫正刑的认识论分析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矫正刑处于一种既合理又不合理的悖论之中。
矫正刑建立在对犯罪人的可矫正性的认识之上,即肯定人的不良思想意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外界的正面影响得以矫治与改造。这是对人的趋善避恶的自由意志的肯定。而另一方面,矫正刑又奠基于犯罪原因的绝对决定论之上,即以犯罪是生理与社会因素的影响的必然结果,不利客观因素注定犯罪人只有趋恶的必然性、不具有避恶的可能性为前提,这又是对人的趋善避恶的自由意志的一种绝对的否定。因此,在肯定犯罪人的可矫正性的同时肯定犯罪人具有避恶趋善的自由意志与肯定外在的不良因素注定人必然犯罪的同时否定犯罪人具有避恶趋善的自由意志之间,构成一种悖论,使矫正刑的刑罚目的论与犯罪原因论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
不仅如此,矫正刑还以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具有可预测与判断性为赖以存在的前提,这是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之于作为客观存在的犯罪的规律性的可认识性以及对犯罪的可控制性的一种揭示,构成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肯定。而另一方面,矫正刑又奠基于犯罪人是客观存在的生理与社会因素的奴隶,即其对不利的客观因素只有被动地受制的可能而无主动地回避的可能这一命题之上。而这又构成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否定。因此,在肯定犯罪的可认识性与可制性的同时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在肯定犯罪人对客观外界的不良影响无能为力的同时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又构成一种悖论,从而使矫正刑又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
矫正刑在认识论上的悖论还表现在其所主张的社会责任与社会防卫论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社会责任而言,其强调的是犯罪是社会不良因素的必然产物,否定个人应对犯罪承担责任,主张社会不具有惩罚犯罪人的权力,只有治疗与矫正犯罪人的义务。从表面上看,这是将个人作为社会绝对的目的,否定社会将个人作为手段的合理性。而就社会防卫论而言,其强调的是对犯罪人的矫正是社会为使自身免受犯罪侵害所使然,主张矫正犯罪人是出于社会防卫的需要。因此,在实质上,这又是将矫正犯罪人作为社会的一种权利,将犯罪人作为实现社会目的的绝对手段。正是如此,矫正刑才被归于功利刑即行为功利主义的范畴。显而易见地,在以社会责任否定个人责任、否定社会拥有惩罚犯罪人的权力与主张社会基于防卫的需要而具有矫正犯罪人的权力、犯罪人具有接受矫正的义务之间,矫正刑构成对个人是社会的目的的既肯定又否定与对社会是个人的目的的既否定又肯定,因而难以自圆其说。
应该肯定,从社会不良因素中寻找犯罪的原因,主张人具有可矫正性、犯罪具有可控性以及强调社会应对犯罪人承担矫正义务,均是矫正刑在认识论上的合理因素之所在。这些合理因素的存在,使刑罚由消极惩罚与有限威慑转向了积极改造,从而克服了等价刑对刑罚的个别预防理性的忽视,因而构成刑罚理性认识论上的一种突破与飞跃。然而,主张绝对的客观决定论,否定人具有相对的自由意志、强调社会防卫需要是社会的唯一目的,又是矫正刑在认识论上的致命弱点之所在。这些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又导致了犯罪人的权益不是因其犯罪而是因社会认为其可能犯罪而被以社会防卫需要的名义的任意剥夺,以致刑罚因不具有与已然的犯罪的等价性而不具有公正性,从而使矫正刑因与威慑刑一样陷于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误区而构成刑罚理性认识论上的一种倒退,即虽然与威慑刑在所追求的功利的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因都是将犯罪人当成实现社会目的的纯粹手段,即使得之功利也失之公正而在本质上构成对威慑刑的一种复归。相应地,刑罚这匹本已由等价刑以等价这根公正的有形的缰绳牢牢地牵制在理性的轨道上的劣马,因被换之以矫正的需要这根无形的主观的缰绳,不再受公正的牵制,而再次成为用刑者任意驱赶的野马,狂驰于理性的轨道之外,在尊重人权的名义下践踏人权,在教育、治疗与矫正犯罪人的名义下无理地惩罚着犯罪人。
矫正刑的刑理评价
矫正刑不但在认识论上构成一种合理与不合理的悖论,而且,从刑罚的基本理性的角度来看,其从理性基础到具体运用上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同样明显。
一、矫正刑的合理性
就理性基础而言,矫正刑的合理性首先表现在对报应性的修正规定体现得较为完整。社会责任论的确立,从观念上带来了对犯罪人的评价的变革,犯罪人因而不再被视为罪犯,而被视为病人,刑罚也不再被称之为刑罚,而被称之为处遇(treatment)措施。以矫正犯罪人为中心而建立的处遇模式往往与医疗模式相类比。社会对犯罪人的惩罚权力因而被对其的教育、矫正义务所取代。相应地,刑罚的人道性、宽容性与奖赏性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死刑之废除或在分配与执行上之受到严格根制,行刑过程中受刑人的待遇的提高,少年犯的处理专门化,是人道性被矫正刑视为刑罚的重要理性的明证;缓刑、假释制度的创立与运用以及非刑化措施的采用,是宽容性与奖赏性受到重视的明显标志。因此,作为报应性之修正规定的人道性、宽容性与奖赏性之被完整地体现,是矫正刑的合理性的重要表现。
矫正刑在理性基础上的合理性其次表现在其充分体现了作为刑罚之重要功利根据的个别预防理性。“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使不可矫正者不为害”,奠基于对刑罚的积极的改造与消极剥夺再犯能力功能的认识之上,而为实现矫正目的所为的教育、人道待遇、宽容与奖赏又注重的是刑罚的个别鉴别与感化功能。尤其是强调司法人员不应对犯罪人满怀敌意而应对其象医生对待病人一样满怀慈善心肠,更是对刑罚的感化功能的重视的明证。因此,矫正刑既是对等价刑消极地剥夺犯罪人的再犯能力功能的继承,又使刑罚升华成了一种感化、教育与改造犯罪人的积极手段,从而使刑罚的个别预防理性得到了充分重视。
矫正刑在理性基础上的合理性还表现在极大程度上体现了报应性的修正规定与个别预防的同一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报应与功利的统一理性。在矫正刑体制下,刑罚的人道性、宽容性与奖赏性虽然未被视为报应性的内容,但其被视为感化犯罪人的有效手段即被作为发挥刑罚的感化功能的前提而受到重视,在客观上意味着对报应性的修正规定与作为个别预防之重要功能的感化功能的同一性的承认。尽管这种承认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但其毕竟在刑罚体制中得到了体现。因此,正如在肯定公正的刑罚有助于一般预防功能的发挥的同时便不自觉地肯定了报应与一般预防的同一性一样,在肯定人道、宽容与奖赏有助于感化功能发挥的同时,矫正刑也就自发地体现了报应的修正规定与个别预防的同一性。
在刑罚的具体运用上,矫正刑的创制、发动、分配与执行均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刑罚的理性规定,具有其明显的合理性。
1.制刑的合理性。
在刑罚的创制上,矫正刑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刑罚的人道性与节俭性的同一性。
死刑之被为数不少的国家所废除,标志着矫正刑在等价刑的基础上向刑罚的人道化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如果说死刑因剥夺的是人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而构成一种不人道的刑罚,那么,死刑的废除便意味着对人的生命之不可剥夺的绝对性的肯定与承认,毫无疑问地构成以人道性对死刑所具有的等价性的抑制,符合以人道性修正严厉的惩罚性的规定。而另一方面,死刑虽因具有剥夺犯罪能力的彻底性而可收最大的个别预防之效,但这只能表明死刑对于个别预防的有效性,而不能表明其对于个别预防具有必要性。这是因为,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可以通过积极的教育、矫正得以消除,从而使之不再犯罪,即使是不堪教育、矫正者,也可以通过长期监禁或终身监禁而使之难于再犯罪。即是说,防止犯罪人再犯罪未必非用死刑不可。这就决定了死刑对于个别预防来说是一种因过份严厉的刑罚而构成一种浪费之刑。相应地,死刑的废除意味着以代价小的刑罚收代价大的刑罚可收之个别预防之效,符合刑罚的节俭性的规定。因此,废除死刑体现了作为报应性之修正规定的人道性与基于刑罚的功利根据之重要内容的个别预防而生的节俭性的同一规定,因而构成矫正刑在制刑上的合理性的重要标志。
矫正刑在制刑上对人道性与节俭性的同一性的体现其次也表现在对自由刑的改造上。在等价刑体制下,自由刑只不过是消极地惩罚犯罪人与剥夺其再犯能力的手段,其内容只是简单地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且剥夺的程度较大,以致犯罪人的人身自由以外的其他许多权益都受到连带剥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合人道性的规定。而在矫正刑体制下,实现了自由刑的简单化,自由刑的轻重等级之别被消除,自由刑的严厉性大为削减,其对人身自由的剥夺被严格限制在最低程度上,这较之等价时代的自由刑无疑更具人道性。而另一方面,教育、感化与矫正性措施之引入自由刑之中,以积极的改造取代消极的剥夺,不但不以加重刑罚的惩罚性为前提,而且为缩短犯罪人所应实际承受的人身自由的剥夺提供了前提,构成节俭用刑的重要途径。因此,矫正时代对自由刑的改造是刑罚的人道性与基于个别预防而生的节俭性的共同体现,符合报应性的修正规定与个别预防的同一理性。
矫正刑在制刑上对人道性与节俭性的同一性的体现最后还表现在保安处分之创制与替代某些刑罚手段上。保安处分,无论其是与刑罚手段合而为一共存于刑罚体系之中,还是与刑罚体系相并列而自成一体,其之被引入刑法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传统刑罚方法的惩罚的严厉性。这是因为,在对人的权益的剥夺上,保安处分总是轻于传统刑罚措施,其之替代传统刑罚,直接轻化了刑罚的惩罚性,而其在刑法中的存在又使相当一部分应受传统刑罚惩罚的行为或行为人只受保安处分而不受刑罚,从而从总体上缓和了刑事制裁的严厉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保安处分构成刑罚人道化的重要杠杆。而另一方面,保安处分作为严厉性轻于传统刑罚方法的手段,其所可收个别预防之效往往不但不低于而且还大于传统刑罚手段,因而构成代价小于而效果不亚于传统刑罚手段的手段,具有节俭性。因此,保安处分的创制与替代某些传统刑罚,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刑罚的人道性与节俭性的同一性,符合报应性的修正规定与基于个别预防而生的节俭性的统一规定。
2.动刑的合理性。
矫正刑在动刑上的合理性在于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报应性的修正规定与个别遏制的必要性的同一性规定。
矫正刑以人身危险性的有无作为定罪动刑与否的前提。据此,即使行为依法构成犯罪,但如果犯罪人不具有再犯罪的可能性,也可以不对之定罪或动刑。前文所揭的英美国家的缓起诉或缓判刑制度即是附条件地不定罪或不动刑的例证。一方面,这体现了对犯罪人已然的犯罪的宽恕,符合刑罚的宽容性的规定,另一方面其又符合不必动刑者不动刑的个别遏制的必要性规定,使刑罚具有节俭性。因此,其体现了动刑的宽恕性与个别预防的必要性的同一性规定,符合刑罚的统一理性。
不仅如此,对既已构成犯罪者不予定罪动刑,以示刑罚的宽容,还有助于作为刑罚之重要个别预防功能的感化功能的发挥,可以促使犯罪人产生悔罪心理,自觉地接受改造与矫正。因此,矫正刑之对不具有人身危险性者不定罪、动刑,又符合动刑的宽恕性与感化功能的同一性规定,从而符合刑罚的统一理性。
3.配刑的合理性。
矫正刑在刑罚的分配上的合理性在于体现了配刑的人道性与个别预防的同一性以及配刑的宽恕性与个别预防的同一性。
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从立法上严格限制死刑的分配范围、在司法上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这实际上是以刑罚的分配来极大限度地避免死刑的不人道性,即以配刑来补救制刑的不人道性,因而是配刑的人道性的明显体现。而从个别预防的角度来看,严格限制死刑这一最严厉的刑罚的适用,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对本可矫正的犯罪人不予积极矫正而以极刑来消极剥夺其再犯能力的可能性,从而符合刑罚的节俭性的规定,因此,严格限制死刑的分配,是作为配制之修正规定的配刑的人道性与作为配刑的适度性之重要内容的刑罚以个别预防的需要为限度的共同体现,因而符合配刑的人道性与适度性相统一的理性规定。
与动刑以人身危险性的有无相对应,矫正刑以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作为配刑的根据。据此,即使所犯罪严重,如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小,对其所分配的刑罚也必然较轻。而一方面,这符合作为配刑之等价性的修正规定的配制的宽恕性规定,另一方面,这既有助于刑罚的感化功能的发挥,又符合刑罚以个别预防的需要为限度的配刑的适度性规定,因而符合配刑的宽恕性与配刑与个别预防相适应的共同规定。在这一意义上说,以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作为配刑的根据,也符合配刑的理性规定。
4.行刑的合理性。
以个别预防为中心的矫正刑的最合理之处在于刑罚的执行,具体表现在如下诸方面:
其一,体现了行刑的人道性与行刑之于个别预防的相应性。在行刑上,矫正刑大量赦免死刑的执行,直接构成对不具有人道性的刑罚的限制,明显地体现了行刑的人道性规定,其所贯彻的行刑社会化,极大限度地保障了受刑人不受剥夺的婚姻、家庭生活权等的行使,其人道性同样明显;其强调尊重受刑人的权益、提高受刑人的待遇,更是行刑的人道性的直接表现。因此,矫正刑的执行较明显地体现了行刑的人道性规定。而另一方面,诸如此类人道性措施的贯彻,又为刑罚的感化功能的发挥创造了充分的条件,构成教育与矫正受刑人的有力保障,因而符合行刑与个别预防的相应性的规定。正是如此,符合行刑的人道性与相应性的共同规定,构成矫正刑的执行的合理性的重要表现。
其二,体现了行刑的宽恕性与行刑的必要性的同一性。对判定刑为死刑者不予执行而予以赦免、对判定刑为短期自由刑者不予执行而予以缓刑,毫无疑问地是行刑的宽恕性的表现。而赦免不必处死亦足以遏制其再犯罪者的死刑,对不必执行短期自由刑者不予实际执行,又是立足于个别预防的需要而生的动刑的必要性的体现。因此,矫正刑之执行体现了行刑的宽恕性与行刑的必要性的共同规定。
其三,体现了行刑的奖赏性与适度性的同一性。假释制度的适用以受刑人有良好的悔改表现为前提。因此,以假释的方式缩短有悔改表现的受刑人的判定刑、变轻其行刑方式,构成对受刑人的善行的一种奖赏,符合行刑的奖赏性规定。而根据受刑人有良好的悔改表现适用缓刑,实际上是根据受刑人的人身危险性减小而相应地缩短其判定刑与变轻其行刑方式,因而又是行刑的适度性的体现。因此,矫正刑之引入与大量适用缓刑制度,体现了行刑的奖赏性与适度性的同一性。
其四,体现了行刑的平等性与个别化的同一性。矫正刑的执行以消除受刑人的人身危险性为核心,以教育、感化与矫正作为行刑的统一方式,因而使受刑人在受刑过程中所享有的待遇与所接受的惩罚与矫正具有平等性,符合行刑的平等性的规定。而在此前提下,矫正刑又对人身危险性不同的受刑人以不同的方式予以教育、感化与矫正,从而实现了行刑方式的个别化。因此,矫正性在行刑方式上实现了平等性与个别化的统一。
其五,贯彻了依法行刑原则。矫正刑时代实现了行刑规范化,将行刑活动纳入了法制的轨道,从而贯彻了依法行刑的原则,使行刑的理性规定以行刑立法为中介而得以在行刑实践中实现,因而具有其合理性。
二、矫正刑的无理性
矫正刑虽然在多方面具有其合理性,但其从理性基础到刑罚的具体运用又都具有明显的无理性。
1.对刑罚的报应性的一般规定的否定的无理性。
就理性基础而言,矫正刑的无理性首先表现为其奠基于对刑罚的报应性的一般规定的完全否定之上。
矫正刑以对犯罪是犯罪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的否定为赖以存在的前提。而这一否定本身是极为荒谬的。原因在于,虽然一定的心理特质与社会因素是促成犯罪人犯罪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因素只有通过犯罪人的主观意识与意志的作用才能对犯罪产生遏制影响。换言之,心理特性与社会因素对犯罪的决定作用只是相对的,其并未将人置于非犯罪不可的绝对状态。相反,即使是具有特定心理因素与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其也可以在犯罪与不犯罪之间作出自身的选择,否则便不能解释具有同样心理特质与处于同样社会环境中的人,有的犯罪而有的却不犯罪。而这种在犯罪与不犯罪之间的可选择性,正是人的自由意志之所在。否定人具有自由意志,否定犯罪是犯罪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无异于是对人的理性即人不同于动物的本质属性的否定,即否定人自身。
对自由意志是犯罪之恶源的否定,必然地导致对犯罪人的道义责任与对犯罪的道德评价的否定,从而必然否定刑罚之道义报应根据。不仅如此,矫正刑还完全否定了对犯罪的社会报复心理的正当性。因为其主张犯罪不是一种害恶,而是一种社会病态,犯罪人不是恶人,而是社会疾病的感染者,因而认为对犯罪人不应有憎恶心理,而只能有同情、怜悯与宽容心理,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对犯罪与犯罪人的社会报复观念的合理性,进而不可避免地否定刑罚的社会报复基础。
对道德责任与社会报复观念的否定顺乎自然地导致对犯罪的否定的法律评价、犯罪人的法律责任以及刑罚的法律报应根据的全盘否定。由此,矫正刑在制刑、动刑、配刑与行刑上都必然违背刑罚的报应性的一般规定而表现出不公正性。
基于对刑罚权的否定,刑罚被以“社会防卫手段”或“处遇措施”所取代,制刑在理念上已不再以惩罚性为其基本特征。然而,在事实上,包括保安处分在内的所有“社会防卫手段”或“处遇措施”,又无一不以剥夺犯罪人的权益为内容。因此,在制刑上,矫正刑之否定惩罚性的理念与所创制的不称为刑罚但实为刑罚的手段所具有的惩罚性的客观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悖论。因此,作为矫正刑之制刑结果的刑罚体系与保安处分体系难以完整地从制刑的一般理性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动刑上,矫正刑的发挥虽然以社会责任为理论基础,即以社会无权惩罚只有责任教育与矫治犯罪人作为动刑的理念,但发动刑罚或保安处分的前提条件是有人身危险性存在,即以个人有可能危害社会、社会为防卫自身不受危害而有动用“防卫措施”之必要作为动刑的决定因素。因此,矫正刑的动刑以教育、矫正犯罪人的社会责任为理念,又以社会防卫自身的权力为实际前提,从而使动刑难以完整地得到动刑的一般理性的圆满解释。其结果是,在无权惩罚但有责任教育、矫正犯罪人的公正的名义下扩大个人的刑事责任与国家的刑罚权,导致动刑的不公正。保安处分之被适用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者、虽未犯罪但有犯罪倾向者等等,(注:陈兴良博士在《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次修订版,第475-480页)中对各国刑法中的保安处分的适用对象与条件作了较详细的分析、比较。在此不作赘述。)便是不以责任能力或已然的犯罪为前提的追究刑事责任,不符合动刑的报应性规定,使动刑不具有公正性的表现。虽然在严格意义上,保安处分有别于刑罚,但其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人的权益的强制剥夺,构成刑事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因此,仅仅从概念上将保安处分与刑罚区分开来,是无法说明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者与未犯罪但有危险倾向者发动保安处分的公正性的。在这一意义上说,矫正刑的发动在否定个人责任、强调社会责任之于个人的公正性的背后,掩盖着强调社会防卫需要、将个人当成实现社会目的的纯粹手段的不公正。
在刑罚的分配上,矫正刑虽因有其人道、宽容与节俭的一面而具有其合理性,但同时又因完全抛弃配刑的等价性规定而有其失之公正的一面。这是因为,矫正刑以人身危险性大小为配刑的唯一根据,其在对犯罪严重但人身危险性小的犯罪人处以轻刑而显示出人道、宽容与节俭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因对犯罪轻微但人身危险性大的犯罪人超出其犯罪的严重性的限度处以重刑,以致犯罪人不是因已然的犯罪严重而是因再犯罪的可能性大而承受重刑,形成轻罪重罚的不等价局面,使配刑失之公正。前文所列的法国1885年增设的对职业犯与常习犯处以终身流放刑,美国1927年至1929年所颁布法律规定的对被四次定罪的累犯处以终身监禁等等,均是将人身危险性凌驾于犯罪的害恶性之上,超出按罪配刑的限制而单纯地按需配刑的表现,其不公正性自不待言;而不定期刑的采用,更是对罪刑法定、依法量刑的直接否定,使犯罪人不是因法律对其已然的犯罪的评价的严厉而受重刑,而是因其在犯罪后、行刑过程中可能有的不良表现而受重刑,从而为行刑的不等价留下了隐患;在刑罚之外,并处保安处分,(注:如:英国1907年的保护观察法和1908年的少年法规定,对少年常习犯,保安处分可与刑罚并科适用。)使受刑人在以受刑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得承受保安处分,导致一罪二罚,变相加大刑事责任的份量,其不公正性同样显而易见。如此等等,足以表明,矫正刑的分配同样有以社会防卫的需要为名将犯罪人作为实现社会目的的纯粹手段的不公正的一面,其不合理性不言而喻。
在刑罚的执行上,矫正刑之悖离行刑的报应性规定,以致行刑不公正,同样明显。其最集中的表现便是悖离行刑的等价性规定。不定期刑的执行,使受刑人的刑期处于悬而未决状态,不可避免地使受刑人可能因不是构成新的犯罪而是因表明其人身危险性有增无减的因素而最终受到重于其所犯罪应受的刑罚的惩罚,使实行刑重于应判刑;对于危险习惯犯,只要认为有必要,便可无限制地延长其刑期,更是行刑不等价的明证;至于对已执行完毕刑罚但仍有人身危险性者加之以保安处分,实际上是变相加重行刑的份量,以致刑外行刑。如此等等,足以表明,矫正刑在执行上追求行刑的适度性,无视行刑的等价性,因而有失对受刑人的公正,同样因系其将受刑人作为实现社会目的的纯粹手段而表现出无理性。
2.对刑罚的报应性的修正规定与刑罚的节俭性的差异性的忽视的不合理性。
按照刑罚的报应性的一般理性规定,除人道性对报应性的一般规定具有绝对制约作用,在人道性与报应性的一般规定相冲突的情况下,刑罚应绝对服从人道性的规定、舍弃报应性的一般规定之外,作为报应性之修正规定的奖赏性与宽容性对报应性的一般规定的修正均是相对的、有限的,即基于对犯罪人的善行所为的奖赏与基于社会宽容观念而对犯罪人的宽恕均只能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能奖赏无边与宽容无度,以致得之对犯罪者本人的宽容而失之对社会的公正,即不能满足社会对犯罪的报复欲望与道德谴责要求,并导致超出善有善报与宽容观念所允许的限度的有罪不罚或重罪轻罚而显失法律的公正。
然而,由于矫正刑不是立足于善有善报与宽容观念主张刑罚的奖赏性与宽容性,而是单纯立足动刑的必要性、配刑的适度性、行刑的必要性与适度性的角度主张刑罚的节俭性,将宽容与奖赏作为发挥刑罚的教育与感化功能的单纯前提,即只是在追求个别预防效果的同时不自觉地体现了作为报应性之修正规定的奖赏性与宽容性,未反映二者作为报应性之修正规定与作为功利性之规定的节俭性的差异性,(注:应该指出,矫正刑时代的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刑法关于不具有人身危险性者只有所犯为轻罪才可免刑或缓刑的规定考虑了宽容、奖赏的有限性及其与节俭性的差异性。)即奖赏性与宽容性具有有限性,而节俭性具有无限性,前二者只允许刑罚在一定程度上减免,而后者则完全以足以制罪为限度。正是如此,矫正刑完全不顾奖赏性与宽容性的限度而片面追求刑罚的节俭性,以致刑罚虽因避免了不必要与剩余而得之节俭但同时又因奖赏无边、宽容无度而失之公正。矫正刑在配刑上对犯有严重罪行者,只要其人身危险性不大便可处轻刑,在行刑上,即使所犯罪严重,只要人身危险性消除便可无限制地假释等等,便是因悖离刑罚的宽容性与奖赏性规定与刑罚的节俭性规定的差异性规定而导致配刑与行刑失之对社会的公正的明证。
3.对刑罚的一般预防根据的否定的无理性。
基于对犯罪是犯罪人的自由意志的产物的否定,矫正刑在绝对否定刑罚的报应根据的同时,也绝对否定了刑罚的威慑功能赖以存在的前提,从而否定了一般预防作为刑罚的功利根据的正当性。这一否定的结果不但使矫正刑处于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地,而且直接悖离功利性的最大效益性的规定。
矫正刑因否定一般预防的有效性而导致的难以自圆其说表现在对犯罪的可控性与刑罚的威慑功能的既否定又肯定之中。一方面,矫正刑否定犯罪是自由意志的结果,因而主张刑罚不可能通过对潜在犯罪人的意志决断的影响而对犯罪产生遏制影响,即认为犯罪不可能因刑罚的威慑而得以遏制,刑罚也不可能因使人产生畏惧而遏制犯罪,另一方面,其又主张犯罪人可受感化、教育与矫正而消除人身危险性,从而不犯罪,刑罚可以通过感化、教育与矫正犯罪人而使之不再犯罪,即认为犯罪人可受刑罚的影响而形成避恶趋善的选择,刑罚可以给犯罪人创造这种选择的条件,从而又肯定了犯罪人具有自由意志,刑罚具有遏制犯罪的作用。这无异乎是说一般人不具有自由意志、犯罪人具有自由意志,刑罚不能遏制一般人基于自由意志的犯罪但可遏制犯罪人基于自由意志的犯罪。这种既否定又肯定刑罚的遏制功能的悖论,最明显地体现在对刑罚的一般威慑功能的否定与对刑罚的个别威慑功能的肯定上。矫正刑否定人的自由意志,进而否定刑罚可使人产生畏惧而不犯罪,即否定刑罚的一般威慑功能,已如上述。另一方面,矫正刑体制所创设并运用的缓刑、假释制度,以保留行刑的可能性为条件,即以恢复行刑的可能性威慑受刑人,使之因恐惧行刑而不敢再犯罪;不定期刑以执行重刑的可能性相威慑,以促使犯罪人弃旧图新,因而均奠基于刑罚的个别威慑功能之上。而一般威慑与个别威慑只存在对刑罚产生畏惧的原因的不同,在使人畏惧刑罚而不敢犯罪这一基本原理上并无二致。因此,否定刑罚可以使一般人产生畏惧从而否定刑罚的一般威慑功能,却又肯定刑罚可以使犯罪人产生畏惧进而肯定并利用刑罚的个别威慑功能,极为明显地体现了矫正刑在理性基础上的自相矛盾性。
对一般预防作为刑罚正当根据的否定,不可避免地导致矫正刑在刑罚的运用上的无理性。
就制刑而言,作为制约刑罚之创制的理念的是刑罚只能是感化、教育与矫治手段,而不是惩罚的手段。这使制刑因不具有给人以损害与痛苦的属性而在理念上只体现刑罚的个别遏制性,而未能体现刑罚的一般遏制性,从而不可能符合最大效益性的规定。换言之,作为感化、教育与矫治手段的刑罚因不具有惩罚性而充其量只可收个别预防之效,而不可能收一般预防之效,自然不可能收最大限度地预防犯罪之效。
就动刑而言,矫正刑以人身危险性的有无为发动刑罚的唯一前提,只考虑动刑个别遏制的必效性,而全然不顾一般遏制的必效性,其结果必然是导致所发动的刑罚得之个别预防之效而失之一般预防之效,因而不具有最大效益性。矫正刑之对大量已犯罪但不具有人身危险性者不动刑,便充其量只是得之个别预防而失之一般预防。
就配刑而言,由于所分配的刑罚不以犯罪所侵害的社会权益所需的保护力度为根据,而以犯罪人再犯罪的可能性的大小为根据,只体现了个别遏制对刑罚的需要,忽视了一般遏制的需要,要么是因配刑超出一般遏制的需要而失之过重,造成浪费之刑,不具有节俭性,要么是因配刑不能满足一般遏制的需要而失之过轻,造成无效之刑,不具有有效性,因而不符合最大效益性的规定。矫正刑对犯有严重罪行但人身危险性小者一律只处以轻刑,同样只符合个别预防的需要而不符合一般预防的需要。
就行刑而言,矫正刑的执行只以消除受刑人的人身危险性为唯一目的,因此,判定刑是否实际执行、判定刑是否调整、行刑方式是否变通与如何变通均只取决于受刑人人身危险性之有无与增减,而不考虑一般预防的需要对行刑的制约性,从而使行刑得之个别预防而失之一般预防,不符合最大效益性的规定。对犯罪严重但不具有人身危险性者予以缓刑、对判处重刑但悔改表现明显者不受实际执行的刑期的限制便予以假释、对判处短期自由刑者易科罚金等等,均是矫正刑只求个别预防的需要不顾一般预防的需要的明显标志。
4.夸大人身危险性的可预测性的无理性。
矫正刑在动刑、配刑与行刑上均以人身危险性为中心,即动刑与否以人身危险性的有无为前提、配刑的方式与轻重以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为根据、判定刑的实际执行与否、在行刑期间调整与否以及如何调整均以受刑人有无人身危险性及其增减情况为转移。撇开这种以人身危险性为中心的刑罚体制的前列无理性不谈,仅就其对人身危险性的可预测性的片面夸大而言,其无理性也极为明显。
毫无疑问地,犯罪有一定规律可循,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也必然以某些外在的特征得以表现。因此,通过对犯罪的规律性的认识与体现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特征的综合分析,可以就人身危险性的有无与大小作出某种程度的测量与判断。
然而,正如人的主观能动性永远只是相对的而不具有绝对性一样,受人的认识能力的制约,对基于已知的犯罪规律与犯罪人的客观情况而测定其再犯罪的可能性的有无与大小,所得出的结论只可能是相对准确的、大致而模糊的,而不可能绝对准确无误与具体而明确。这是因为,犯罪人的个性特点千差万别、诱发犯罪的原因纷繁复杂、犯罪的随机性极大,对犯罪的规律性的认识因而往往只限于对不同犯罪人的共性与一般性的揭示,而不可能精确到对每一具体的犯罪人的个性与具体性均予以揭示的程度。相应地,对具体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预测能力是有限的,所得出的结论也只可能是大致准确的。
而矫正刑既片面夸大对人身危险性的预测能力,又使对人身危险性的预测结论绝对化,动刑、配刑与行刑均以基于对人身危险性的这种有限的预测能力所得出的大致准确的结论为唯一根据,以对人身危险性的有无与大小的预测的大致结论作为动刑、配刑与行刑的唯一前提,其结果必然是使本具有人身危险性的人因被误认为不具有人身危险性而不动刑、本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人因被误认为具有人身危险性而反被动刑;本来人身危险性大的人因被误认为人身危险性小而处轻刑,本来人身危险性小的人因被误认为人身危险性大而被处重刑;本来人身危险性大或有增无减的人被缓刑、假释,本来人身危险性小或减小的人未能减刑、假释。正是如此,矫正刑自身的所谓科学性的背后,潜在着极大的反科学性,即使其理念是合理的,也因其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只不过是一种不现实的幻想。正是如此,矫正刑因以无法准确测定的、主观臆断性极大的个别预防的需要作为用刑的根据而与以无法准确测定的、主观臆断性极大的一般预防的需要作为用刑的根据的威慑形形异而质同,不可避免地导致罪刑擅断。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矫正刑在本质上是对威慑刑的一种复归,同样构成一种预防需要决定一切的纯粹的功利刑。而且,在某些方面,矫正刑的纯功利色彩比威慑刑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威慑刑还以主观责任作为动刑的基础,从而将不具有意志自由能力的精神病人与未成年人排除在刑事义务主体、刑事责任主体与动刑的客体之外,而矫正刑却以对不具有意志自由能力的精神病人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者适用强制医疗与监护措施等保安处分的方式变相地追究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矫正刑在追求对犯罪人的教育、矫正,赋予刑罚以积极性而扬弃等价刑的消极被动性,从而具有其合理性的同时,又因将个别预防绝对化、断然否定刑罚的报应性与一般预防根据而失之公正与效益,从而又具有其无理性,其合理性决定了其相对等价刑是一种进步的刑罚体制,其无理性则决定其在本质上是威慑刑的复归,相对于等价刑是一种倒退的刑罚体制。因此,合理与不合理因素并存、进步与倒退兼具,是从刑罚理性进化的角度考察矫正刑所必然得出的结论。由此可以定论,矫正刑是刑罚进化史上的畸型儿。这便决定了矫正刑在取等价刑而代之的同时,也就注定了其被新的合理的刑罚体制所取代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