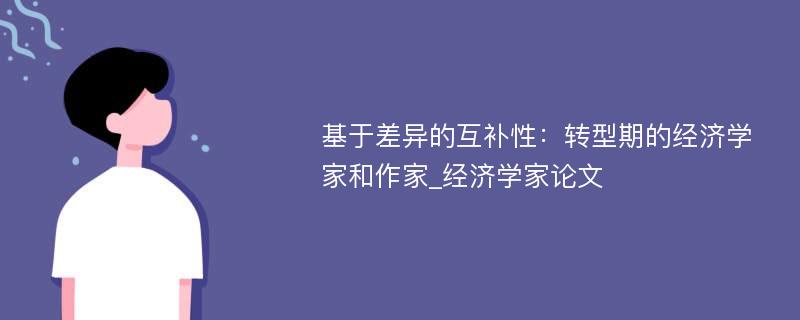
基于差异的互补——转型时期的经济学家与文学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家论文,经济学家论文,差异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学家与文学家的差异
陶:都说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型的时代,都说中国的文学家应当关心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都说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应当反映现实,等等等等。这些当然都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如何关心以及怎样关心。比如,文学家与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对于中国今天的社会转型所持的态度,尤其是他们“审时度势”的角度、标准、出发点、着眼点等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就是很有意思但仍然未经深入探讨的问题。1997年底,北京市作协与《管理世界》杂志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学术会,叫“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与青年文学家研讨会”,召集在京的部分青年经济学家与文学家一起探讨:1.青年经济学家与青年文学家对企业改革现状的思考;2.转型期经济学家与文学家的价值判断、文化立场与社会视角选择。结果发现,经济家与文学家在看待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的确存在很大的分歧。其中具体观点的分歧不是最主要的,也不是我们这里所感兴趣的。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思维路径、价值取向、判断角度的分歧。我认为这是更为根本的分歧。
金:这个创意应当说非常好,说明当前人们已关注到文化与经济的区别及相互间的联系。历史上传统的欧洲学术分类是采用两分法,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分,它更看重社会科学作为整体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而后起的北美学术则采取三分法,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分,这种划分强调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我国沿续了传统的欧洲式的分类,而近年来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分属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科与分属人文学科的文化艺术,一方面显示出越来越大的独异性,另一方面二者之间又呈现出日益紧密的相互联系。以往文学界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意识形态都有过不少深入的研究,唯独对文学与经济研究最少。这也许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既定观念作怪:文学艺术是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意识形态,而经济则是整个社会大厦的基础,一个是高高在上,一个是扎地三分,二者相去甚远。故而研究甚少,也在情理之中。但在今天这个转型的时代,文学(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也日益提上了社会发展的议事日程。仔细研究文化(文学)与经济的关系,不论对文化研究还是对经济研究都具有现实意义。
陶:显而易见,经济学家——按照你的划分,其实还可以包括社会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等,因为他们都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与文学家在个性、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举其要者言之,经济学家务实而文学家务虚;经济学家重理性而文学家重感性;经济学家更多考虑可行性(在现实中是否行得通),而文学家更加执着于“合理性”(此指是否合乎自己的理想,与韦伯意义上的“合理性”不同);经济学家更多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而文学家更喜欢“我向思维”(或“自我中心”);经济学家对社会机制的运行与操作更感兴趣,而文学家则念念不忘个体人格修炼;等等。由此决定了,在对待社会转型时,经济学家更注重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尤其是物质生产与制度建构层面),而文学家则更关心社会转型在个体心灵上产生的看不见的影响(个体心理体验层面)。以上的种种差异当然会导致两者在具体分析与评价社会转型时的分歧乃至对立。比如,对于市场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商业伦理、契约伦理,经济学家主要持肯定的立场,因为契约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新的联系纽带取代了原先的以人情与习惯为轴心的人际关系,这是社会的一个进步,也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文学家看来,市场经济中的商业伦理与契约关系充满了“铜臭味”,太缺乏诗意与浪漫。人间真情岂是能用契约这种斤斤计较的玩意儿所能表达的!
再比如,对于官僚科层化与工具理性化的看法。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表明,现代化必然导致科层官僚化,这里的“官僚化”与我们熟悉的贬义词“官僚主义”有所不同。科层官僚制是一种现代的机构管理方式,它用客观化且较稳定的规章制度来取代更具个人主观色彩的惯例人情,通过一个人的技术知识与管理能力而不是关系资历来作为选择升迁的标准。在社会学家看来,这当然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工具理性化以及相关的世俗化也是如此。在一个宗教本位或伦理本位传统深厚的社会中,想要实现现代化似乎必须经过世俗化与工具理性化的阶段(尽管会在另一方面带来严重的后果),把原先的神圣价值加以悬置、限制或划定其范围,使社会活动的领域,尤其是经济、器物、物质方面的活动脱离价值理性的限制。但是文学家可能会出来唱反调:科层官僚化导致了等级制,世俗化扼杀了价值的神圣性与终极性,工具理性化则把人当机器看待与使用,使个体丧失自由,使人成为非人。对于这两者的批判,一直是并仍然是当今中西方人文学者的主导立场。
金:经济学家务实、文学家务虚,可谓一言中的。这与他们各自的社会定位和人们对他们的期许密切相关。经济学家要解决当前经济的运作,他们的目标是设计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当代经济生活的最合理的模式,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速度,其自我定位是经济发展的“工程师”或“设计师”,人们对他们的期许也是尽可能地解决现实实践中的问题。文学家、艺术家则不同。文学艺术要解决人类的精神需求问题,人类当然必然首先活着,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还有文化的、精神的、文学艺术方面的需求;如马克思所说,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人的感官不断解放的历史,是自然的人化也即自然文化化的历程。因此这些需求也是人类的不可或缺的基本需求。由此,文学家的自我定位就不同于经济学家,他们有的取精神牧师的定位,有的取社会批判者的定位,有的取历史代言人的定位。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不同还在于文学家与经济学家各自的知识谱系不同。由于训练,由于教育,由于约定俗成的社会习俗,他们观察世界的思维范式不同,前理解视界不同,因而他们对同一社会现实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判断。换句话说,他们可能关注的是同一社会现实中的不同层次或不同侧面。
对于工具理性的态度最能见出经济学家与文学艺术家的不同。在经济学家看来,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当然应是一个高度理性化客观化制度化的社会。在中国当代的经济学家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人治的伦理传统社会中,最缺乏的就是工具理性。我国的现实是,经济活动中的契约、效率意识、科学理性大大不足,市场成份大大不足,因此,必须大力倡导现代经济意识与经济模式,为此而付出相当的代价,甚至经历某种“商品崇拜”的阶段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在文学艺术家、人文理论家看来,人类在这个科技理性霸权的时代已被大大的异化从而失去了人的自由的本性。他们更关注终极价值、关注对存在的追问,关注生活的深度、情感的深度、思维的深度,他们执着地寻找人类生存的“诗意”,他们对物欲横流的世界,面对市场经济的现实大声疾呼:道德沦丧了,人何以堪?
此外,经济学家往往从个体而不是从团体、社会、国家等作为整体的行动单元出发,他们观察、研究艺术不会像艺术家主要考虑自己和喜好、趣味,而是去考虑个体可以支付多少资金、时间和工作量,他们可能更多地关注文化艺术中的外在制约因素如物质与货币的变化。经济学家总是关注那些可计算可实证的内容,更关注影响人们生存环境的经济物质条件和组织规约以及相关制度,关注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综合资源,以及生产者的体质、时间与潜能发掘等。而文学家艺术家则耻谈金钱,他们注目于人类情感传达的深度模式,后现代条件下艺术作品的“气韵”的消失,复制品与真品的天壤之别,等等。就拿对复制品与真品之间关系的看法来说,经济学家和艺术家在关注重心、切入角度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从一般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对于原作与复制品之间的区分并不像艺术家那样认真,对于以复制品代替艺术品,或批量复制艺术品,他们大多十分宽容。经济学家在此问题上往往会倾向于普通人的意见。但艺术家与艺术批评家则对此至为敏感。他们坚持复制品已不再是真正的艺术,真品是唯一的。因为艺术的复制品如本雅明所言,缺少艺术真品所特有的“气韵”(艺术法方面的律师也强调这种差异,因为他们要考虑原作的创作权是否受到影响)。而经济学家看待艺术则无须参与复制品是否艺术的论争。他们更关注的是从经济角度看完美的复制品及批量复制将怎样改变艺术品的供求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复制品与真品(原件)之间没有什么差异,原作的价值就会下降。这样,一些原作的复制品就可列入博物馆,以弥补真品的匮乏。但这样的结果也会派生另一个两难:博物馆有能力展出人们喜欢的艺术作品了,其保管、储存费用也将大大降低。但如果这样的话,艺术爱好者还会参观博物馆吗?人们不远千里万里慕名而来不就是为了一睹真品的风采吗?复制品的泛滥会不会导致艺术品对新一代青年吸引力的消失呢?
二、经济学家与文学家的互补
陶:我们应当把这种分歧看成是正常的现象。 文学家对于社会时代的评价本来就不应当与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相同。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器物、体制、心理多种层面;而知识的分工与知识分子的分化所必然造成的结果是: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都很难全方位地准确把握与正确评价转型带来的种种结果;就是说,他们都存在思维的盲点。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社会科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应当是一种基于差异的互补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文学家都有各自的洞见与盲点。文学家不应当放弃自己的视角与立场,我们也不应当要求他们是社会发展(尤其是物质与器物层面的发展)的设计师;小说不能写成社会发展报告或现象记录,否则文学与文学家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理由。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在常态的情况下,文学家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微弱的、“边缘”(姑且用这个不太准确的词)性的,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的观点,当然更重要的是物质生产自身的“铁律”以及政治家的施政方针(值得指出的是,现代社会中政治家与科技专家的联盟远远超过其与人文学者的联盟)。西方社会不乏对于现代文明持激进批判态度的文学家,但是没有一个西方社会因为文学家的批判而回到古代去。没有一个政治家会依照文学家的作品来施政。但是这不是说文学家的“边缘”位置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在于提示社会转型在人(主要是个体)的心理产生的看不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常常被社会科学家忽视(这也不是他们研究的强项),因为这种影响常常只能用心去体验,而不能用图表去统计,或用调查问卷去把握。
再说,审美规律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作家不能像社会科学家那样去审视社会、反映社会、表现社会。常言道: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一个精通社会分析的作家未必、甚至经常就是不能写出有审美意味的文学精品。一部把社会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的作品只能说有社会学的意义(意义多大很可怀疑),而很难说有美学的意蕴。在一般情况下(中国解放后到80年代中期前后这一段时间或许是例外),读者不是要到小说中去寻找社会问题的答案。也许正因为这样,中外古今那些真正有艺术韵味的文学作品常常是“挽歌式”的;也就是说,常常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有些错位乃至相悖。《长恨歌》是如此,《红楼梦》是如此,托尔斯泰是如此,福克纳也是如此(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还有如此艺术力量)。可以说,西方现代派文学,除了未来主义对于现代文明诗歌颂态度,其余差不多全是反现代文明的(如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机械化等),西方的现代派作家也基本上都是对于现代化持否定的立场。文学与社会应当是有距离的。这与关注社会与时代并不矛盾。这是一种特殊的关心,是有距离的关注。因为知识分子绝不应当无视社会转型在人的心灵上产生的影响与震荡。
话说回来,文学家固然可以对于社会转型持不同于社会科学家的立场与视角,但是切不可丧失界线意识与距离意识。我所谓的“界线意识”与“距离意识”,是指文学家不应当天真幼稚地认为社会应当按照自己的人性理想与审美乌托邦来建构,更要警惕自己的乌托邦冲动与政治权力结合或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家利用,用来在现实社会中建立“道德理想国”或“人间天堂”。我非常欣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也喜欢桃花源中“鸡犬之声相闻”的境界。但是桃花源美就美在它是幻象而非现实;如果桃花源不再是幻象而是现实,或者有人为了建立桃花源而把人类的文明成果统统毁灭(为了人性的“纯洁”这个“崇高”的目的),结果恐怕只能出现人间地狱,出现令人发指的专制统治——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一致同意以毁灭文明为代价去建构所谓“桃花源”,结果只能是强迫同意(事实上,每个人心目中的人间天堂都是不一样的,也不可能是一样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自己去建构自己的人间天堂)。这是一种走火入魔的道德理想主义。这种道德理想主义不但有害于社会发展,侵犯了人的自由,而且从审美的角度看也是不美的。作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与人性乌托邦如果想要获得美感,就不应当丧失审美的距离,不应当成为声嘶力竭的道德控诉。即使他留恋过去的天堂,对于即将消逝的美好(至少在他心目中是美好的)事物、美好人性倾注了全部的同情,他也不应当失态地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让自己的声音失去应有的从容与委婉。因为暴跳如雷的道德控诉或许表明了一个人的正义感与道德义愤,但是我相信它必然是缺乏美感的。美学家苏珊·朗格在她精彩的《艺术问题》中反复强调:艺术是人类情感的表现性形式,而不是人类原始发泄或自然征兆(如同一个孩子的大哭大叫)。大家都知道,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法国上流社会的一曲挽歌,他的所有同情都在那个注定要灭亡的阶级(即贵族)身上,但是巴尔扎克并不用自己的道德态度取代社会历史理性,所以他写出了贵族必然灭亡的命运,虽然他同情贵族。同时,他的同情是有距离的,因此也是美的,他没有让自己的同情直接成为对于历史发展的声嘶力竭的诅咒、控诉或叫嚷,也没有对于资产阶级进行破口大骂。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千古名句,但是它的美恰好来自一种挽歌式的情调:美的夕阳的消逝引发的是李商隐无可奈何的喟叹与惋惜,深情而不狂躁,从容而不冷漠。狂躁的激情因为失去了距离因而也将失去美感,而冷漠的从容是一种“没良心”的历史理性,它从来与文学无缘。
金:尽管一个政治家不可能依照文学家的小说来施政,但我们确实经历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那样的时代,经历过一出戏剧便构成“对党的猖狂进攻”的时代。所以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有文化的制衡因素。没有社会民主文化的监督、批判、否定、制约,就会出现“文化大革命”那种灭绝民主文化的政治唯一化的不正常社会秩序;没有合理的文化、伦理、宗教的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完全市场法则的经济的发展也就可能变成一个“无耻者富”、“弱肉强食”的社会。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与新教伦理相互伴行的。当然人文学科对社会的批判、否定、制约,不是那种“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的方式,不是阶级斗争那种你死我活的方式,而是现代民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互独立又相互制衡、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的关系。由这一角度来看,西方的现代派文学的反现代恰恰具有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实际上,文学艺术家与经济学家也不总是截然对立的。在当今社会,整个世界经济越来越文化化。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那些具有高文化、高科技附加值的产业日益兴盛起来。而时尚等社会心理因素则成为文化产业兴盛的重要契机或基本条件。像美国的好莱坞电影成为全美仅次于航空航天、电子科技等的重要大创汇产业,就是证明。从总体上看文学艺术家越来越经济化了,比如张艺谋从艺术电影走向商业化,高雅艺术如交响乐的商业炒作,都是如此,更不用说雅尼艺术的商业运作方式了。现在的大多数文学家已越来越具有商业头脑了。其实当年的伏尔泰、巴尔扎克、大仲马等,无一不是商业运作的奇才。伏尔泰放弃桂冠诗人的殊荣,离开宫廷走向市场,大仲马的小说生产流水线更是开近代小说商业制作之先河。而经济学家则主要是在从专业角度观察世界时采取关注当下的更为务实的态度,而略去了更为长远虚在的精神问题。实际上,每个现代的经济学家自身也必将有诸多精神的、道德的、文化的问题。当他们作为个人进入文学艺术领域时,则不一定一律是“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崇拜者。
三、纠正两个偏向
陶:联系到中国,我以为当今中国作家对于转型时代的把握,存在两个比较典型的偏向。一是偏激狂躁、缺乏节制的道德理想主义。它的主要误区是:1.许多持有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文学者缺乏应有的界线意识与距离意识。他们谈论的是社会问题,但是采用的是文人的视角。比如在分析社会道德状况(不是个人道德修养)时,缺少社会分析的视角与眼光,有些人甚至错误地把旧制度造成的问题当成是尚未确立的新制度(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恶果”,或把社会性的道德现象归结为个体的人格问题,而忽视了道德的制度环境。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相信社会学家(如韦伯)的观点,对于大多数的公民来说,他们之所以遵守法律或他们之所以使自己的行为合乎道德,是因为特定的社会制度使得合乎道德的行为比之于不合乎道德的行为对于自己更加有利。也就是说,道德问题与利益问题无法分离。2.以声嘶力竭的控诉乃至诅咒抵抗当今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方向。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张炜笔下的“葡萄园”(见张炜的长篇小说《柏慧》)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显然,“葡萄园”作为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理想乌托邦,与桃花源有类似之处,但是作者在捍卫“葡萄园”(它象征一种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纯洁人性与理想人际关系)的时候,却发出了狂躁的道德宣言与失态的道德诅咒,从而使得这种捍卫失去了应有的距离与美感(且不说这种捍卫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是否真的合理)。
另一种偏向是没有距离的所谓“新现实主义”,以所谓“三架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其实三人在创作上还是有区别的,这里姑妄沿用)为代表。此类作品常常直接地记录当前社会转型的种种现象,尤其是基层单位的改革现状,被戏称为“记者”文学。应当说,这些小说中的大多数对于社会问题停留在浅层描写,即使涉及对于社会问题的剖析,一般也是比较肤浅的,写得最好也不过是社会问题小说。我还是想以巴尔扎克为例,简单谈谈我对于所谓“现实主义”的看法。我以为现实主义在于精神而不在于题材;在于怎么写而不在于写什么。谈到现实主义时,人们总热中于它的“认识价值”,但即使是所谓“认识价值”,也不同于调查问卷或社会统计学的认识价值。恩格斯曾经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这句话一直被用来证明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但我体会这恰恰是因为巴尔扎克不是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也没有像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那样去写小说。巴尔扎克也是处于当时的社会转型期,但他始终抓住了人性的主题,写出了社会转型在人性层面造成的震撼。正因为这样,它的认识意义是独特的,是历史学、经济学与统计学所不可替代的。
中国目前的社会转型既为社会科学家,也为文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反映与揭示这个转型时期是他们共同的使命。但是他们的视角应当是不同的与互补的,而互补的前提是不同,相同就无所谓互补了。就文学家而言,更值得描写的是转型时期人的心态,是人性的变化,是社会转型在人的心理层面造成的隐秘而又深刻的震荡(这种震荡的剧烈与深刻决不亚于器物或制度的层面),比如感性与理性、道德与历史、传统与现实等的深刻悖反。这样的文学既不是救世良方也不是施政方针,但它将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与情感力量,同时也是具有艺术震撼力的文学杰作(如果写得好的话)。
金:当代经济学家对待文化也有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根本上无视精神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对经济活动完全采取操作主义的态度。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人类理性地追求利功最大化”的基本模式之上。他们对经济活动之外的人类的哲学、精神、道德、伦理、美学等问题很少予以关注;而这恰恰是西方20世纪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文化思潮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基本原因之一。它们直冲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的霸权而来,直冲着后工业社会的商品拜物教等种种社会弊端而来。在今日中国,经济学已成为当代“显学”,它已“帝国主义式”地侵入一切领域。经济学的术语正大踏步地占据媒体以及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领地。而一些经济学家则将自身学科中的假设、命题、主题、概念推及其它,将之视为一切领域的普遍性公理。实际上经济学家也应了解人文科学学者们的思考,听听文学艺术家、伦理学学者们的意见,他们也需要关注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
经济学家中的另一种偏向是对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缺乏足够的批判否定意识。他们认定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已完善如金科玉律,具有不可置疑的真理性。经济学也需要一种经济批评或经济批判。经济学家竭力追求理性与功利最大化,推崇现实、实惠的自利行为,他们相信社会整体的最大好处就在于通过个人在市场中的自利行为获得,这种最大的好处便是效率。实际上,人类所有的经济行为都不是孤立的,都必然受到文化与政治的制衡(当然制度经济学并不乏对制度文化的关注)。我们经历过政治决定论的时代,今天又经历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决定论。然而,如果没有政治和文化(包括伦理与艺术)的制约,我们的经济也可能成为脱缰的野马。
同时,现代阐释学告诉我们,每一种经济模式的设计,也只具有部分的真理性,它是此时此地经济学家依据某一前理解阐释现实的结果。当代世界经济的多元性和经济学范式的多元性,导致经济学阐释方式的多样性。从根本上说,每一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是独特的、唯一的,因而,每一位经济学家在研究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时,多一份批判意识和否定意识,多一份“中国国情”或“中国特色”的意识,就是十分必要的。
有一种说法,说未来世纪的经济学“将让位于心理学”。日本松下公人提出新文化产业的观点,认为未来的文化产业应该是:①创造某种文化;②销售这种文化;③生成文化符号。由此他还提出第四产业和第五产业的观念。第四产业为高技术高知识信息产业;第五产业为心理知识文化产业。未来世纪,人类心理上的需求将日益突现出来,内在情绪的满足、人的心理表现将越来越成为经济关注的重要课题。文化符号将越来越成为能产生高额利润的产业。有鉴于此,经济与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的结盟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所以未来不是经济学让位于心理学,而是让位于文化(包括心理)的经济学或经济的文化学。
标签:经济学家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文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