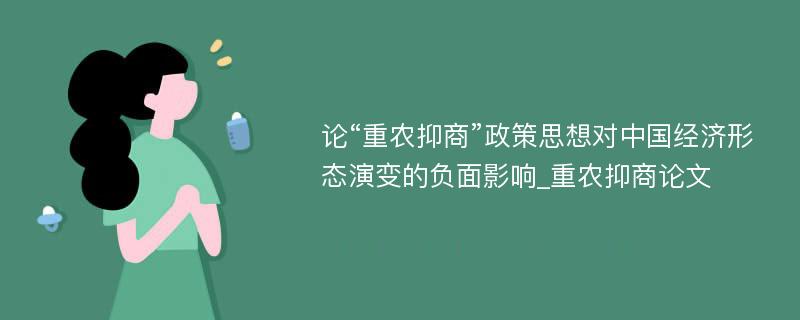
论“重农抑商”政策思想对中国经济形态演进的负面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负面影响论文,形态论文,思想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奉行数千年而不替,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为什么华夏民族能够接受这种政策主张?这一主张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有什么关系?这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被忽视的问题之一。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与“重农抑商”的关系,从表现上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当我们深入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本质关系之中,就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与中国古代以来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是有着某种联系的,这个联系就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数千年来,在本质上始终是农业社会经济形态的阶段性转换,而“重农抑商”政策正是稳定这种农业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经济政策”要素。
一、商品经济受到周期性破坏,促使农业社会经济结构长期稳定。
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农业收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命脉。中国文明大门刚刚开启的时候,就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政体。统治阶层作为社会产品与商品的大宗消费者,是以直接消费农业产品为主的集团,并用农副产品的收入,来换取其他生活奢侈品,因而,从奴隶社会以来,社会就没有刺激工商业生产的社会消费市场,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这种情况没有改变。对于统治阶层来说,社会商品流通的数量不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消费水平。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生活与生产关系是封建经济关系赖以生存的前提,其本质是排斥商品经济的,因此,必然在一定阶段内排斥商品经济,使农业经济保持在自然经济关系为主的状态下,进而使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关系长期稳定。农业社会的生产形式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为主要形式,这种生产与生存形式,最重要特点是分散,分散的生产形式虽然对来自政治上的动乱及天灾人祸没有很好抵御能力,但是,对国家税收来说,个体数量的绝对值越高,税收就会越多。封建经济关系内周期性土地兼并,使社会与国家对个体的土地经营形式更加依赖,而工商业的发展及其对土地经营的回归,对封建经济关系内的土地兼并是雪上加霜,从而又使土地兼并更加激烈,封建土地关系周期性兼并必然使自耕农数量减少,地主阶级个人富有与封建经济形态周期性凋蔽形成对应性、规律性发展,而在这周期性经济灾祸面前,本来长期受压抑的工商业,在每一次经济凋蔽都要受到严重打击,因而导致自然经济关系得到某种深化,自然经济关系深化的必然结果就是封建农业经济关系的结构稳定系数增强。
二、“重农抑商”是封建专制政体“强化剂”。
高度集权的封建国家政体,需要以自然经济生产形式为主的社会基础,需要一个广大而分散的社会生产基础,这个分散的社会基础在超经济关系的强制下,可以发挥整体优势,发挥国家政体优势。封建专制国家“有大部分人口可供支配”〔1〕,可以指挥千千万万人的手臂〔2〕,去为集权国家修建与集权政治关系相匹配的社会物质实体。这一点在东方社会表现十分强烈,如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等,都是社会集约力量的产物,没有强大的集权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强大的集权制度来自于社会下层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薄弱,换一个角度说,对阶级对立的社会来说,社会底层的社会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越松散,权力的作用功能体现越大,即权力作用的对象力量越小,权力所显示的功能就越大。对自然经济能够起瓦解作用的是商品经济,而对权力经济起到瓦解作用的也是商品经济,马克思说:“商人对于以前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3〕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的“重农抑商”思想与政策是与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和基础经济——农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也是其集权政治的必然结果。因为工商业发展会促进商品经济关系的深化,商品经济的深化过程,也是社会民主关系发展的过程,商品经济越是深化,人与人的“契约关系”也愈加深化,从而使社会产品不具有权力属性。因为“交换,确立了主体间的平等”〔4〕,在商品经济深化社会关系内, 权力者再不是富有者的代名词,有钱的人可以与贵族平起平坐,可以在商品面前,以平等的身份出现。因此,“重农抑商”与其说是经济关系的产物,不如说是社会政治结构的产物。
三、“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造成社结会构中的人口职业构成失调,使社会分工单一化,并呈畸型发展结构,从而成为社会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历史上多次社会经济波动和朝代更迭,其原因大体一样:如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虫灾等)、朝廷内讧、农民战争、统治阶级挥霍无度等,历数中国几千年来朝代更迭无一例外,只是上述几个原因的排列顺序不同而已。而这些原因深藏着社会对工商业者排斥的因素,进而造成社会经济关系结构不合理,除了统治者就是广大的农业生产者。不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不可能有稳定的发展过程的。
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服务性行业和总体的职业构成种类少于西方,这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从理论上讲,社会分工不发达,职业构成必然简单。社会分工不发达,特别是城市社会分工不发达,城市人口数量应该小,但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城市人口数量从古典时代起就大大超过了西方。但是,有大量统治集团存在的中国城市,不但以简单的社会人口构成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且,还能使这个城市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保持一定水平,其原因就是城市依赖农村而生存,专制国家可以通过强迫手段集聚农业生产领域的财富和产品,使农业人口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上挣扎,而养活大批超量存在的城市人口。因此,可以认为“重农抑商”之政策,从深层次上制约着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构与发展走向。
“重农抑商”是以“重农”为前提的,封建统治者“重农”的最重要也是唯一举措就是让农民不离开土地。商鞅认为农业人口的比例,应该占总人口的90%,他说:“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5〕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是农业人口达到90%以上, 虽然有些时期城市经济有一定发展,城市数量也比较多,可是城市里有大批人是农民,还有一批人是土地占有者。“重农抑商”的政策使社会分工中的职业分工呈不合理状态,这个不合理状态还表现在,社会全员消费集中在农业生产领域,消费产品的农业产品化,使除统治阶级而外的社会中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是低水平的,而农业生产领域的产品,长期处在“匮乏经济”范畴,因而在理论上和行为方式上,统治阶级要求广大被统治阶级“安贫乐道”、“守穷守困”,而统治集团却以畸型消费方式,来挥霍社会不充分的产品,这种畸型消费也是构成封建经济形态周期性凋蔽的一个原因。
四、“重农抑商”使社会生产要素构成失调。
在“抑商”政策下,私人工商业者对再生产的积极性不高,所谓通过工商业来发财,用土地来“守财”,这是中国“重农抑商”的历史的一个结果。因为社会生产中创造财富的生产形式在封建经济关系内,除了农业就是手工业,而当时的手工业又是农业家庭的副业,再生产能力弱,“重农抑商”政策限制了这种再生产形式的发展。大宗农业产品不能进入流通领域,“重农抑商”政策使流通渠道时通时闭,手工业产品也不能经过流通领域在竞争中得以发展。所以,几千年来,中国的封建经济结构在农业经济结构内自我循环,整个社会的基础是农业和农业家庭手工业副业相结合的结构,因此,社会长期缓慢发展,直到近代社会仍被排斥在世界经济发展主流之外。
五、“重农抑商”政策使社会经济生产中的技术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形态的进化,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来看,必须有社会生产质的飞跃,而要达到这一项目的前提是,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有质的进化改变,而这一改变的前提是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及在这一繁荣下的社会需求的刺激,要达到生产发展、商品经济繁荣就必须保证包括工商业生产者在内的生产者和技术发明创造者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地位的非奴隶化,即最低要保证“凡人”的地位,即从事某项科学技术的发明与科学技术产品的生产应该得到社会认可,并应该得到较高的社会荣誉。中国历史上的情形恰恰相反。
在中国农业经济关系内的发展中,在“重农抑商”政策和思想观念下,把许多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视为“奇器”、“淫巧”之作,从事这些手工业和其他技术类生产和发明的人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工匠,从西周以来,工匠就是处在与奴隶为伍的地位。从中国文明诞生以来,建造许许多多的宫殿,很少有人知道其建造者姓名,也很少知道设计者名字;也出现过无数人世罕见的工艺大师,被人知晓的屈指可数;也流传下来无数的工艺珍宝,这些珍宝的创造者,在统治阶级眼里也只是愚蠢的“劳力者”而已;也有许多有价值的科学的发明,可是这些对人类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人,在中国文化中世人称颂的“正史”上,却没有他们真正的一席之地。
六、“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阻滞了封建经济下国内市场的形成。
从商品发展的则律来讲,商品生产能否发达,首先要有市场,而在封建经济关系内,是要看有没有相对的消费群体,只有消费群体扩大,从而出现市场扩大,才能使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其相关的社会要素是,有相对城市市民人口,即有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在商品经济面前,商品没有政治属性。可是相反,在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发展中,中央集权制条件下,许多产品还没有走出生产场地,就已经有所有属性,即产品还没有走进市场就已经有了主人。如中国人熟知的“贡品”,就是国内市场不发达的表征。更有甚者是:“(农民)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日用。”〔6〕而且,早在西周时期, 许多商品就开始与市场无缘,当时许多产品已经有了政治地位属性和权力属性,如周礼规定:“有圭璧金璋,不鬻于市。命服命车,不鬻于市。宗庙之器,不鬻于市。牺牲,不鬻于市。戎器,不鬻于市,”禁止上市商品达数十种〔7〕, 在禁止上市的产品中,有些是专门表示身份地位和等级的,作为一般市民是没有权力消费的。在封建经济形态内农民是大多数,而这大多数又不是商品经济的享受者和消费者,商品经济就失去了其发展的社会基础,市场的扩大就成为不可能。
市场的扩大是需要多重的社会关系深化才能体现的。社会生产分工,是市场扩大的集中体现,可是如前述所论,“重农抑商”政策使社会分工结构向单一化发展,除了自耕农就是政治阶层,而没有中间的手工业和商业中的各种社会阶层,这就使得人们的谋生手段过于单一化。从中国封建经济关系发展的总体层面来分析,虽然也有一些游离于自耕农与统治阶层中的阶层,如一些城市中手工业者和“行商坐贾”,但是,因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过小,其中的大部分人,也是以经营城市外的土地为生。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封建形态内,作为商品经济关系的城市内的市场也不发达,就不可能谈到国内大市场,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缓慢也是自然的事了。
七、“重农抑商”推行的过程,也是抑制城市经济发展过程。
工商业的发展其必然结果形式,就是商品经济的载体—城市经济的发展。乡村是自然经济的产物,城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城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可是“重农抑商”政策使城市经济发展始终处在政治的从属地位上,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条件下,城市成为封建国家政治结构的一种武器,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说明封建经济关系内的城市是为统治者建造的。墨子说得更为清楚:“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8〕在一些思想家眼里城市完全可以和粮食、 兵器并列,足以说明城市这一商品经济载体形式,在中央集权制下的形态内的政治工具功能。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居民构成不是商品经济的必然结果,而是自然经济关系的必然结果。城市起不到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社会发展的推力就不足,只能在农业经济关系内循环。
八、“重农抑商”的过程也就是“以农立国”抑制货币作用的过程,从而为自然经济关系的稳定创造了社会前提。
以农立国,就必须创造一些依靠农业的“政策”,这些政策反过来又加深了对工商业发展的抑制作用,如农业经济中实物地租,劳役地租和实物赋税,这些措施从表面上看对农民有利,减少了通过货币渠道转换的交纳租税的形式。可是实物租税,说到底对维护超经济强制关系是有作用的,这种经济关系,从深层次上强化了自然经济结构。统治阶级还以限制货币的发行为手段,以达到“抑商”的目的。在中央集权制下的封建经济关系内,货币只是改变政治关系的一个“物品”,并不是作为经济关系的一个必然环节。中国历史上货币从产生的那天起,就成为统治阶级手中一个维持政治稳定的砝码,当封建王朝发生政治危机,出现经济凋蔽的情况时,就下令废止货币,如东汉时曾规定:“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9〕到了公元221年,“魏文帝又罢五铢,使百姓以谷帛为市。”〔10〕以谷帛为币,出现许多弊端,就是在魏文帝罢五铢钱后,“谷用既久,人间侈伪渐多,竟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不能禁也。”在中国封建经济关系内,实物货币一直与其他形式的货币长期共存,从春秋时代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到汉唐间的“以布帛为市”,再到明清时一些地区“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这些都说明中国历史上的“重农抑商”政策对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构构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抑商”的过程中实物货币长期存在,这既有封建统治者“抑商”政策的原因,也有中央集权制下的封建经济关系对自然经济有依赖关系的原因。
九、“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超常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重农抑商”所起的实际作用来看,对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国家是产生效果的,这个效果就是:对巩固封建地主政体是有效的;对延长封建制度是有效的;使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附着在土地上是有效的;在保证封建等级的制度下畸型消费生活是有效的,商品经济不发达,可是统治阶级却不缺乏“商品生活”,虽然他们的生活奢侈品可以不用货币购买,但是权力结构,却可以使他们得到天下珍奇;在保证封建等级制度上是有效的,商品经济是排斥权力的经济关系,“抑商”就是统治阶级不愿意与商人为伍,不愿意让商人与统治者享受同样的生活方式等等。有人认为“重农抑商”有积极意义,这也许就是积极意义,这个积极意义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封建社会运祚长久,在近代社会被世界排除在发展主流之外。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0—37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1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7页。
〔5〕《商君书·农战》。
〔6〕陶煦:《租檄·推原》。
〔7〕《周礼·王制》。
〔8〕《墨子·七患》。
〔9〕《后汉书·朱珲传》。
〔10〕《晋书·食货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