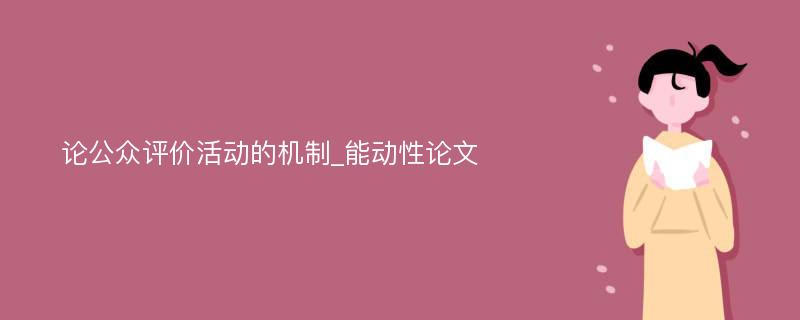
论民众评价活动的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众论文,机制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群体、群体主体和民众评价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个人无论怎样表现自己的存在,都要与他人发生联系。个人的存在只有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才能得到实现。现实的个人都避免孤立状态,而聚合为群体。群体是个人存在的普遍形式。当然,这并不排斥人类在发展中不断地变换着群体存在的具体形式。人们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永恒的现象。
群体的形成需要三个要素:其一,共同活动。共同活动的前提是个人的独立活动,个人总是以某一方面的独立活动能力,成为群体的成员。众多个人共同活动的对象是外界的人或事,共同活动使一群人与另外的人群区别开来。其二,相互作用。这里的相互作用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沟通。沟通的工具是符号。在众多个人的沟通中,会形成一定的沟通网络和沟通渠道。网络越牢固、渠道越畅通,则沟通越有效。二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操作,即一个人的活动引起其他个人的相应活动。其中以相互肯定的活动(如响应与酬答)为主,以相互否定的活动(如骂架与打架)为次。其三,时间的持续。一群人要成为群体,必须存在反复的共同活动和相互作用,通过时间的持续,表现为相对的稳定性,群体也就形成并表现出来。
群体可以作多种划分,根据本文题意的需要,我们把群体分为有形群体和无形群体。在有形群体内,基于某种共同需要从而形成共同利益和情感的众多个体,通过一定的形式组织起来并发生协调的行动。在无形群体内,基于某种共同需要从而形成共同利益和情感的众多个体,未通过一定的形式组织起来。
评价活动是主体对于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价值关系的认识活动。我们把以群体为主体的评价活动称为社会评价活动。群体何以成为评价主体?
黑格尔认为,主体的特质“便是我们称作‘理念’的东西”,(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第73页。)绝对理念是能动的主体,它把自己外化为客体,又通过“理性本能的两种不同运动”——一是“理念的认识活动”,二是“理念的实践活动”,使主体与客体达到统一。黑格尔还直截了当地指出,“主体在本质上就是具有能动性的实体”。(注:转引自《哲学大辞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页。)强调主体的能动性, 这是黑格尔对主体分析的重要贡献。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主体能动性的思想,并把这种能动性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主体是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8页。)而“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同时,更重要的是, 人“通过实践创造了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因而“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为主体的最重要的特征。人作为主体不是单独孤立的个体,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从个体扩大到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4页。)因此,“人作为主体的活动,既有个人形式”,然而更重要的“又有超个人的、集体的形式”。集体(即群体)之能作为主体,就在于具有能动性。
群体具有能动性,这是与群体具有需要、利益、意志联系在一起的。众多个人通过共同活动、相互作用和时间持续等要素,形成特定的需要。这种特定需要把众多个人联结起来形成群体,它自身也就转化为群体的需要。对于群体需要,可以作两点分析:其一,这是人的需要,因而具有人的需要的一切本质特征。群体当然不等于群体内的一个个的个人,但离开了人的需要就不能理解群体的需要。其二,它不是所属的众多个人需要的总和。群体需要实际上包括两部分:1.有的群体需要只是单个人需要中的一部分,即是群体内众多单个人的共同需要;2.有的群体需要只是单个人需要的一部分之基础。它不是单个人需要的一部分,但单个人部分需要的满足,离不开这种群体需要的满足。
众多个人的共同活动、相互作用并在时间上的持续,必然会反映在观念形态上,这就形成群体意识,群体需要总要反映在群体意识之中。利益是“人对自己在正常的生命活动、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中因缺乏必需的物品和条件而产生的一种意识”,(注:斯皮尔金:《意识和自我意识》,莫斯科版,第119页。)利益就是群体需要在意识中的反映。 一般说来,群体需要总会通过各种方式以利益的形式反映在群体的意识之中。意志是“人自觉而有目的地对自己的活动进行调节的心理”,“人的意志表现了人在活动中所特有的自觉目的性与选择性,表现了人的价值定向选择”。(注:《哲学大辞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944页。 )利益是目的形成和价值选择的根据,因而利益也就成为意志形成的根据,群体利益必然转化为群体意志。意志是主体能动性的内在规定。恩格斯说:“一切动物的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58页。 )人通过实践活动在自然界上打下人的意志的印记,意志作为主体能动性的内在规定也就在实践活动中转化为主体能动性的外在尺度。
具有能动性是主体的本质特征。群体具有意志,就具有主体能动性的内在规定,并且能推动群体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从而转化为主体能动性的外在尺度。为此,马克思明确地把群体称之为“实在主体”。群体作为实实在在的主体,因而成为“直观和表象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4页。)群体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是社会认识活动的主体,因而也必然是社会评价活动的主体。
群体作为主体,其能动性在评价活动中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群体主体发挥主体能动性,直接地推动社会评价活动。群体需要表现了群体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定的匮乏状态。为了克服这种匮乏状态,群体主体首先感兴趣的是客体对于满足群体需要所具有的意义。其二,群体主体的能动性贯彻于评价活动的全过程。这可以从三点来理解:首先,群体主体的能动性表现在选择评价标准上。在社会评价活动中,群体需要的多样性转化为群体利益的多样性,而群体主体的能动性表现在意志选择一种或几种主体利益作为现实的评价标准上。其次,群体主体的能动性表现在整合价值信息、形成价值判断上。群体主体选择评价标准的实质,是把一定的群体需要与客体属性之间的价值关系作为反映对象。把价值信息正确地反映到群体主体意识中来,需要发挥群体主体的能动性;对反映上来的价值信息进行整理,并用一定的规范予以整合,仍需要发挥群体主体的能动性。最后,群体主体的能动性集中反映在作为社会评价活动外化的实践活动上。只有在实践活动中,群体主体的能动性才得以最充分的体现。
群体在评价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以两种形式现实地体现出来。一种是权威机构评价活动。有形群体具有一定的组织和结构。处在群体组织和结构最高位置上的机构即权威机构,一般总能集中地代表群体的需要和利益。于是,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就成为群体主体进行评价活动的现实形式。另一种就是本文讨论的民众评价活动。无形群体不具有一定的组织和机构,评价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就不能通过群体的权威机构现实地表现出来。有形群体在评价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固然能通过权威机构现实地体现出来,也可以不通过权威机构现实地体现出来,在权威机构不能有效地代表群体的需要、利益时,尤其是如此。从辞源上分析,“民”与“官”相对应,意谓不处在权威机构中的平民;“众”与“寡”相对应,意谓多,即大众。为此,我们把不通过权威机构现实地体现出群体主体作用的评价活动称为民众评价活动。
黑格尔把一个群体内的成员“没有经过某种程序的组织”而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方式,称为“无机方式”。(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1页。 )黑格尔接着对无机方式所表现的两重性作了分析:在一个群体内,“个人所享有的形式的主观自由在于,对普遍事务具有他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因而表面上是混乱的;然而,内在的东西却是“绝对的、普遍的、实体性的和真实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2页。)一个群体内的众多个体总是从各自的需要、 利益出发对众多个体共同感兴趣的“普遍事务”发表意见,由于在一个群体内,因而总与群体主体的需要、利益发生一定程度的联系,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着群体主体的意见。从表面上看,各种意见林林总总,有很大的杂乱性;但群体主体的意见作为“绝对的普遍性、实体性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也就实现了。正是在这种众多个体评价活动所形成的“无机”形式中,群体主体的意志和主体作用现实地体现了出来。
二、民众评价活动的几种主要形式
(一)舆论
舆论是指一定群体内相当数量的成员对社会事物所发表的倾向较为一致的议论。我们可以从精神内核和现象外观两方面对舆论进行分析。
舆论的精神内核是群体意识,其本质是“社会公众对社会某些事件、现象或人们行为的评价和态度”。(注:《哲学大辞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 )舆论者从来不打算把自己置身于利害关系之外作纯客观的解说,而是在解说某一社会事物时表示肯定或否定、赞成或反对、颂扬或谴责的态度。舆论带有公众的主体性,反映出一定群体的特殊利益、立场和情感。古往今来,舆论都是利益的奴隶、利益的浪花、利益的飓风。舆论就是一定群体关于某一现象的整体性评价意见或评价态度。
议论形态是舆论的现象外观。舆论总是表现为纷纷扬扬的诸多公众的意见过程,没有议论纷纷,就没有舆论。议论纷纷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人要公开自己的意见,这就需要人们对某一社会事物有兴趣,而兴趣总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切身的利益使人们感到“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非讲不可。这样就形成了一定群体内众多个体之间的信息传播和意见交换,产生了议论纷纷,而这也正是舆论扩大声势和影响的过程。第二,社会能允许一定群体的人们合法地利用某些表达方式和传播手段,公开地表达和交流意见。如果不能做到社会公开,群众的议论纷纷就不能实现,或者不能合法地公开地实现,那么舆论就不能形成,或者不能正常地形成。
人们常常说:“是非曲直,自有公论”,称舆论为“公论”。这说明,舆论作为一定群体中群众的评价意见,较之个人的评价意见一般来得公正。现实生活中,舆论的形成与一定的群体利益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群体范围内具有“公论”的性质,但相对于其他群体或乃至更大的群体来说,就不一定公正,有时甚至是偏狭、自私和反动的。第二,舆论领袖的作用和权威机构的作用有可能使舆论发生偏差,使之不能真正代表群体的公意。我们在后面要予以研究。
(二)谣言
舆论具有公开性,如果不能做到社会公开,而人们“一吐为快”的欲望又非常强烈,人们之间的意见传递和交流就会利用非法的、地下的渠道,这时就会出现小道谣言纷起的现象。谣言是社会挤压下的舆论非体制化的产物。它不是一般的舆论,而是否定性的舆论形式。因而,谣言在本质上仍然是群众的社会评价活动。
人们往往对谣言的起源很感兴趣,到处去追查谣言的始作俑者。这实际上是将谣言现象简化为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问题,而否认了谣言的本质是一定群体的社会评价活动。谣言的生命在于流传。在社会压制下,为什么谣言能“不胫而走”而且“疾走如飞”?这里除了谣言内容本身具有某种可信因素(如“某要人身染沉疴”,而一个人患绝症总是可能的)以及谣言的传播渠道具有某种可信因素(如“我的朋友告诉我的,而朋友的丈夫正是某要人的医疗组成员”)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谣言所传递的消息正是某些人们所希望的、而能引起思想上“共鸣”的消息。“共鸣”是与人们的利益与愿望联系在一起的,谣言表达了人们心中暗自思忖或不敢希冀的评价结果,与人们的内心想法协调一致,从而引起思想上的“共鸣”。有时“共鸣”如此强烈,以至动摇了人们平时对可信规定的标准,甚至排斥对于谣言的任何核实。“共鸣”使谣言成为人们愿意相信甚至竞相传播的消息,这样,谣言也就流传开来,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变化。
(三)民谣
在中国语言中,“谣”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谣言,二是指歌谣。歌谣是人们在生活中的即兴歌。歌谣作为民众集体的作品,又称为民谣。
官样文章中颂词谀词连篇累牍,一到老百姓口中,立刻清浊分明。“诗言志,歌咏言”,民谣是老百姓唱的口头诗,它抒情言志,最能道出民心民意,而且迅速、形象、真诚,因而是群众的舆论。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民谣的评价本质。
首先,从民谣的形成看,民谣没有具体的作者,也没有确切的创作日期。街谈巷议,人们关心的同一个话题谈得多了,于是有些人就把它编成顺口溜。顺口溜本身就具有节奏,在“溜”的时候再赋予某种喜闻乐见的音调。这些表达同一主题的顺口溜在流传中又相互融合,逐渐形成更能体现人们情感、表达人们态度的顺口溜,或者再赋上某一地区的特有音调,民谣就产生了。例如,近年来流传较广的关于“十等人”一类的新民谣,开始时听到好几种讲法,后来听到的就比较的统一了。这说明同一主题的顺口溜在流传中融合,民谣在流传中产生。“十等人”民谣的产生,形象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清廉政治的呼唤,对腐败邪佞的鞭达。民谣是众人的共同创造,体现着群众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评价态度。其次,从民谣的流传来看,民谣的生命如舆论和谣言一样,在于流传。民谣的形成过程已经内在地包含着流传过程,同时在流传中,又被有意或无意地改变着。民谣能广而久地流传,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民谣所涉及的社会现象和所体现的情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一首出自陕北农民之口的《东方红》就是如此,它唱遍了整个中国,唱了半个世纪而不衰。民谣的流传体现了群众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评价态度。
民谣是艺术形态的评价,民谣的艺术性来源于两方面:第一,来源于群众的日常的朴素语言,民谣是“那些牧童、灶妪、村妇、野叟以天籁的方言方语表达他们真挚浓厚的情意”(注:钟敬文编:《歌谣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的产物。如一首明朝末年的民谣这样唱:“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够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乐过一场”,真是天籁的语言,来自生活,平易近人,朗朗上口。第二,来源于口耳相传,融合了千万人的智慧,因而言简意赅。如“五十年代人帮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人防人,八十年代各人顾各人,九十年代认钱不认人”;“五十年代爱英雄,六十年代爱贫农,七十年代爱文凭,八十年代爱经营,九十年代爱真诚”;“五十年代,跟着革命走,拉着同志的手;六十年代,跟着斗争走,挥舞钢铁般的手;七十年代,跟着运动走,摸着没准儿的手;八十年代,跟着感觉走,抓住梦的手;九十年代,跟着市场走,握着钱的手”,都是从50年代说到90年代,寥寥几句,今昔对比鲜明,分明能看到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变化,社会风气和群众心态的变化,但又引而不发,需经过琢磨,方能悟出深层的道理。这些民谣言简意赅,寓意深刻,确非一人之力,正是在共同的深切感受中经过千万人口耳相传、千锤百炼而提炼出来的。
在这三种民众评价形式中,舆论是最基本的形式,谣言是舆论的否定形式,民谣是舆论的艺术形式。
三、民众评价活动的社会作用
群体主体通过民众评价活动表达自己的评价意见、体现自己的意志,从而发挥自己的作用。马克思称民众评价活动的作用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强制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37页。)民众评价活动通过舆论、谣言、民谣等形式体现出来,民众评价活动的“强制力量”也就通过舆论、谣言、民谣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作用体现出来。兹先对舆论、谣言、民谣所具有的特殊社会作用分别作些分析:
舆论的社会作用是一种精神的强制,与暴力、经济手段为后盾的法律、行政的强制相区别。舆论的社会作用有两个方向:其一是指向群体的权威机构或群体外的某一主体。舆论不是坐而论道,不是清谈,它具有明显的实践意向和积极的参与意识。人们通过舆论活动,深明大义,陈述利害,坦露请求,目的是向群体的权威机构或群体外的某一主体施加压力,以影响他们的决策,制约他们的行为,最后达到与舆论倾向和要求相一致的实践结果。为了加强舆论的实践意向,舆论活动往往会伴随一定的伸展性或示威性行为,如散发传单、静坐示威等。但舆论的实践意向仅仅是意向,它推动而不是直接代替社会实践去解决社会问题。其二,是指向群体内的个体。对于群体内的个体而言,违背舆论除非意志坚强不为所动,或者干脆逃之夭夭,否则是不可能排除在遭白眼、嘲讽、冷落之后的内心压抑、苦闷、孤独、紧张等等不良感觉的。而对舆论的归顺,则意味着不良感觉的解除,甚至会产生荣耀、幸福等等情感。
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社会控制》一书中就舆论对个体的强制作用作了三方面的分析:首先是“意见制裁”。他认为粗俗而生命力强的人可能不在乎社会污名,有教养的人则可能尽量设法避免邻居在评价中对自己的轻蔑。其次是“交往制裁”。邻居轻微的不满表现为冷淡和回避,作为舆论对象的冒犯者便失去了外界的朋友和习惯了的社会关怀。在更严重的情况下,冒犯者必须面对这样的社会共同感情的表露,诸如大街上的怪叫、辱骂等等。当这种愤怒渗入冒犯者家庭时,制裁便达到了顶峰。“这样,个人同社会土壤联系的根茎一个又一个地被铲除了,束缚被一点点拉紧,直到交往被完全切断,坏死的社会成员从社会机体中跌落下来”,(注:(美)E.A罗斯:《社会控制》,华夏出版社, 1989年版,第69—70页。)最后,“暴力制裁”,即“实际存在的肉体制裁”。当然,“这种惩罚在文明社会已经移交司法机关实施”。(注:(美)E.A罗斯:《社会控制》,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9—70页。)
谣言是一种舆论,因而它具有舆论所具有的社会作用。谣言作为否定性的舆论形式,还具有与一般舆论相区别的特殊作用,它是无人邀请的自发的匿名评价,这就决定了以谣言形式出现的社会评价活动所具有的反权威性。谣言作为一种“反权力”,对于社会的现存秩序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这种破坏性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可能起积极作用,也可能起消极作用。先进的群体可以利用谣言,反动的群体也可以利用谣言。但是,谣言作为一种“反权力”,决定了社会当局不会利用谣言,相反却要利用舆论宣传和其他行政手段来反对谣言。
民谣的艺术性使民谣在社会评价方面具有一种特别的尖锐性和感染力量。民谣在街谈巷议中产生,能迅速地反映时弊,它短小精悍,往往是寸铁刺人,一针见血。在林彪、江青一伙倒行逆施的时候,民怨沸腾,民谣如星星闪烁,如匕首投枪。最近又听到这么一首民谣:“想暴富,三条路:假药、贩毒、卖文物。”乍一听,不禁有点心惊肉跳。假药、贩毒、盗卖文物,尽人皆知都是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然而由此暴富的却也不在少数。这首民谣深刻揭露了市场经济大潮中的这种怪现象,同时也在实际上抨击和警告那些纵容者和包庇者。这首民谣共十三个字,愤懑和忧患之情溢于言表,听了使人拍案而起。这就是民谣的魅力所在,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民众评价的强制力量不是赤裸裸地发生作用的,而是在“普遍的、隐蔽的”形式下发生作用的。
民众评价是普遍的强制力量。当一种民众评价流行时,报纸上有它,电视上有它,在单位、在家里议论它,甚至走在大街上也会听到它。人们处处感受到它的存在,摆脱不了它的刺激,因而它就能形成一种声势。这种声势的作用是非常有力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舆论的普遍性的作用,曾有过一段很生动的描述:“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很多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舆论的普遍性就是民众评价强制力的普遍性。之所以能有“千夫所指,无疾而亡”,就是因为民众评价指向的对象时时处处都感到被“所指”,这种无孔不入的氛围使对象无可逃逸,产生极大的精神压力,甚至崩溃。
民众评价是隐蔽的强制力量。民众评价是一个不可触摸的实体。它并不常常表明自己的身份,存在于议论纷纷的街谈巷议之中。人们可能已经受到它的制约和左右,但到底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受到它的制约和左右,就可能讲不清楚了。民众评价的这种隐蔽性使它作为强制力量,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民众评价在街谈巷议中体现出来,常常是在潜移默化中为人们所接受的。这就是说,作为民众评价的强制力量,常常通过非强制力量作用于人们。这对于群体内的个体来说是如此,对于群体的权威机构或群体外的某一主体来说,也是如此。由此决定了第二,民众评价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对于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作出的决定,人们可以抵制它、批判它,但处在民众评价的氛围中,人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民众评价所表达的评价意见。
四、民众评价活动中的悖论
一般说来,群体主体以无机的方式进行着的社会评价活动,较能真正地代表群体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由此就有“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以及“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睹;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的民本主义思想。同时也产生了“公议必公”的说法和“众情必允”的提法。但仍然应该对民众评价活动能否真正地代表群体主体的需要和利益作具体的分析。下述情况中的民众评价活动往往不能有效地代表群体主体的需要和利益。
其一,舆论领袖的作用所引发的民众评价活动的悖论。由于种种原因,众多个体所作出的评价意见在民众评价活动的初期总是分散的,不容易集中和趋向一致。这时候,在众多个体中有威望的和有影响的个体所作的评价意见,对于众多分散的评价意见的集中具有重大作用。在民众评价活动中,常常会出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情况。人们之所以会服从某些人的评价意见,是因为这些人的评价意见往往能比较系统地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使评价意见具有理论的色彩,从而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是因为这些人往往具有一定的演说才能,辩才无碍,巧发奇中,使评价意见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渗透力。这些人就成为黑格尔所称谓的“公共舆论”中的伟大人物,(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4页。)即一定群体中的舆论领袖。 舆论领袖在民众评价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在整体上不能改变民众评价的“无机”状态。这是因为:舆论领袖在民众评价活动中的作用不是通过组织机构来实现的;舆论领袖的评价意见,只是许多评价意见中的一个,它的作用只能通过众多个体在对各种意见比较中的自我认同来实现。
值得指出的是,舆论领袖的评价意见由于常常能较全面和较深刻地反映一定群体的需要和利益,因而常常被一定群体的公众认为是正确的,由此这些评价意见便往往会成为群体所形成的民众评价的意见核,从而也使舆论领袖在群体的公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但是,舆论领袖的评价意见并不必然全面、深刻地反映群体的需要和利益,而舆论领袖在公众中的威望又常常使公众认为舆论领袖的评价意见是正确的,这就使民众评价活动存在着盲从权威、走向歧途的危险。在不少情况下,舆论领袖的错误评价意见能使民众评价活动发生偏向,从而对该群体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放大了的危害。舆论领袖的评价意见若不能代表群体的需要和利益,不应该具有权威却仍然具有权威,并使民众评价活动发生偏差,那么该群体的全体成员则必须为这种不体现他们意志的评价活动负责。这就是舆论领袖的作用所引发的民众评价活动的悖论。
其二,权威机构的作用所引发的民众评价活动的悖论。民众评价活动常常与该群体的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联系在一起。由于民众评价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强制力量”,因此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往往要通过调动各种宣传工具,造成宣传声势,把一定的评价结论灌输于公众的意见互动的过程之中,使众多个体形成倾向较为一致的意见。在这种宣传氛围中,群体内的个体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权威机构的评价结论,与权威机构保持一致的行动。
值得指出的是,民众评价活动受到了权威机构评价活动的影响,既可以使民众评价活动减少盲目性(在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确实体现着群体的需要和利益时),也可以使民众评价活动增加盲目性(在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不能体现群体的需要和利益时)。关于后一种情况,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说过,“新闻、宣传能制造出舆论世界”,“舆论是可以操纵的”。(注:转引自徐向红:《现代舆论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受到操纵的民众评价活动,虽然仍然是民众评价活动,但已经不能真正代表群体主体的需要和利益,但该群体的全体成员必须为这种不能体现他们意志的评价活动负责。这就是权威机构评价活动的作用所引发的民众评价活动的悖论。
还值得一提的是,民众评价活动形成错误评价意见与民众评价活动由于舆论领袖的作用或权威机构的作用而引发的悖论是不同的。前者是指民众评价活动确实代表一定群体主体的需要和利益,但一定群体主体的需要和利益不一定是正确的,由此形成错误评价意见;后者是指由于舆论领袖的作用或权威机构的作用,使民众评价活动发生偏差,群体主体的全体成员必须为不能代表他们的需要和利益、不能体现他们意志的评价活动负责。应该把两者区分开来,应该研究民众评价活动中引发悖论的这两种情况。
收稿日期:1999—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