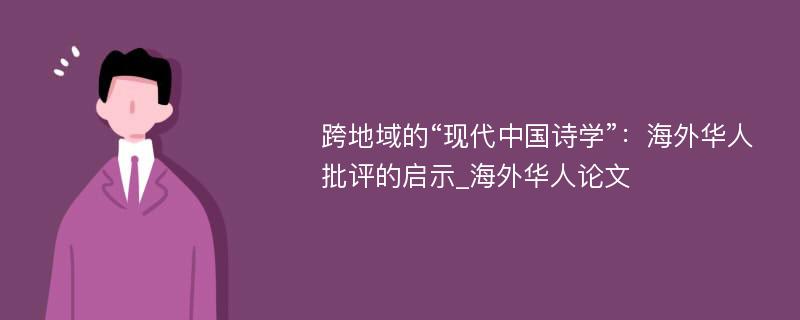
走向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海外华人批评家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批评家论文,海外华人论文,中国论文,地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以来,有关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考察日渐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一涉及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海外汉学、华侨华人研究诸领域的崭新论题,随着海内外学术交流的频密,其学理意义与实践价值得到不同科际学者的关注和思考。在“批评理论”研究不断受到重视的语境下,海外华人批评家的跨国批评实践,提供了一个考察当代西方批评理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崭新而特别的视角,其对中国当代批评建设的借鉴意义格外突出。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如全球化时代的“学术流散”倾向、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力”关系、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的复杂面貌等等,正日益重要地凸显在文学理论及比较诗学研究的视阈中。一种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正向我们走来。
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他者”
海外华人批评家进入中国内地学者视野,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国门再开后的中外学术交流。1983年,应钱钟书先生的联络,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夏志清教授回内地访问,掀开了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交流新的一页。接着,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领军人物的论文陆续见诸国内学术刊物。较早进入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视野的是李欧梵①。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3期发表了李欧梵、邓卓的《论中国现代小说(摘要)》,李的另一篇论文《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②,发表后在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界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并被广为征引。颇有意味的是,1986年,李欧梵两次在内地发表介绍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情况的文字:一次是与李陀、高行健、阿城三人在天津《文学自由谈》编辑部的座谈,另一次则是回到家乡河南大学的讲演③。这两篇文章无疑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随着国门的打开,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交流、互动及影响正在不可避免地加强。
事实也正如此。80年代末以来,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交流呈现出一种“加速”趋势,海内外学术研究的“整合”也出现了一些成果。如果说1987年开始推出的“海外学人丛书”尚是海外人文社科学术成果的全面展示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海外华人批评家群体的关注则显得更为集中:1997年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批评空间的开创》就收录了多篇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文章,显示出将海外批评家群体融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努力;1999年上海三联书店推出“海外学术系列”,包括刘禾、郑树森、张错、杨小滨等人的论著;2001年许子东、许纪霖主编的“边缘批评文丛”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赵毅衡、黄子平、唐小兵等人的著作;2002—200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讲”书系收录了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和王德威的《现代中国小说十讲》;200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的“海上风系列”收录了刘绍铭、李欧梵、王德威、张旭东等人的学术随笔集,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外华人学者论丛”收录了张英进、刘康、王斑等人的近著;季进、王尧主编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2008年起由上海三联书店陆续出版。近年来,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出版渐成中国内地学术出版的一个热门选题。
伴随着海外学术成果的译介,对海外华人批评家的研究也渐成热潮。2004年的《当代作家评论》“批评家论坛”连续刊出李欧梵、王德威、许子东等海外批评家的研究专辑,有关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的专题论、个案论陆续成为国内硕士甚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显示出国内学界对此一研究领域的不断重视。译介与研究伴随着争议。海外华人学者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像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刘禾等,其著作和观点都曾受到内地学界不同程度的讨论甚至批评,而由此形成的“批评—反批评”现象也成为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之一。
毋庸置疑,海外华人批评家之进入中国内地学界,最早是以一种带有异质性的“他者”身份。无论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沈从文、张爱玲、张天翼等人的褒掖,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对鲁迅思想的重新思考,《上海摩登》对上海“孤岛”时期文化性质的判定,还是王德威那一声“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断语,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颠覆成规与权威的论述策略,抑或史书美“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论述对“现代中文文学”的挑战,都在刺激着内地学术界早已麻木的思维和神经。这种挑战性的声音,并不限于上述从台港走进西方的华人学者。即便是20世纪80年代国门再开后负笈欧美的内地年轻学人,也不时传回迥异于国内主流的思想和观点,像刘禾对“国民性神话”的批判、唐小兵对“十七年文学”的再解读、王斑对“创伤记忆”的思考、张旭东对“后社会主义”走向的判断、刘剑梅对“革命”与“情爱”关系的叙述、许子东对“文革小说”叙事模式的整理、陈建华对“革命”概念的溯源及“通俗文学”的追问,以及张英进、鲁晓鹏、张真等人对“华语电影”概念不同角度的切入,等等,都曾在内地学界激起一阵阵的波澜。
从港台或内地“流散”至“他方”的华人学者,因其对产生于文化母体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先后扮演起“学术反哺者”的角色。不仅仅由于学术规训的差异,更因为言说位置的区别,海外华人学者的言论从总体上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另一种声音”。这样说,并非暗指海外华人学界铁板一面、意识统一;恰恰相反,海外华人学术圈的内部争议十分明显,甚至时而激烈,而这些争议往往关联着发言者的身份、学科、年龄甚至场合。但不可讳言的是,作为“整体”的“海外华人批评家”,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中切实起到了“他者”的作用。这一批评理论刺激了内地学界陈陈相因的学术话语,呈现了别样的观念与方法,彼此构成了较为热烈的互动(不管是以赞同还是争论的方式)。打破统一性之后的内地现代文学研究界,再也无法忽视大洋彼岸这真实的“另一元”了。
二、多元比较的“中国现代诗学”
作为“彼岸性”存在的海外华人批评家,不只相对于内地现代文学研究界、批评界充满了“比较”意识,而且就其自身的形成和现状来讲,也呈现出斑驳鲜明的“比较性”特质。这种特质,使得海外华人批评家内部呈现出缤纷多元的研究走向,同时也给内地的现代文学研究不断带来新的气息。海外华人批评家的这一比较气质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不仅是因为地理空间上与中国内地的延异,更指向一种学术话语空间上的差别。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比较意识首先植根于它的学科属性和批评家的身份背景。海外华人批评家,不论是来自内地、台湾,均以外语出身的居多,出国后多攻读比较文学学位,或从事东亚区域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他们取得学位后,又多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职业,其切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入口,大体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这一点,在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镇的北美表现得特别明显。事实上,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比较文学在美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偏重理论的“精英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成了西方各种文学理论的操练场。在这一学术语境中从事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海外华人学者,无疑也濡染了这样的批评气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旅美分会的成员,大多是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学者,似乎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比较意识的由来。
其次,海外华人学者的比较意识,还植根于一种问题意识。“什么是理论?就是‘问题意识’。”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的这句话,把海外比较文学研究者偏爱理论的本质说得再明白不过。在她看来,所谓“理论”,就是“提出别人没有提过的问题,它不是炫耀名词概念,更不是攀附知识权贵”④。经受比较文学理论训练的海外华人学者,也将这一“问题意识”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刘禾本人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学术个案——她对“国民性神话”的质疑,研讨路径是对语词译介及流变过程中增值或耗损意义的分析,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刘禾写作中无处不在的现代思想史旨趣。王斑的《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一著的方法和立论似乎也可佐证海外学人的“问题意识”。该书历史跨度大,从晚清改革到共和国时代的建立,再到新中国政权和“文革”始末。作者选择20世纪中国美学和文化活动中一系列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透视其间潜存的历史意义,以“崇高”为关键词,讨论美学思潮、政治运动和文化传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一探讨反映出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即给历史另外一种系统阐释的可能性。用王斑自己的话说,就是“观念姿态比较强”,而观念“主要是从当代历史中产生的,像世界主义、民族主义等问题,并不是因为观念本身重要,而是因为它们在当下这种环境下很重要。所以我往往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对观念非常感兴趣,然后回到历史中去”⑤。带着“问题”先入为主,虽有“主题先行”的嫌疑,却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拓了一爿风景独好的天地。
最后,海外华人批评家的比较意识,还受到其所在学术语境的影响。以较典型的美国学界为例,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奠定过程,作为美国庞大学科体系中的“小众”,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化目前还不能说彻底完成——既没有一部真正成体系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也没有一套完整的英文版《鲁迅全集》,有的只是零星的研究、选择性的译介。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这种“边缘性”,必然要求从事这一研究的华人学者进行研究策略上的选择和调整——他们要么继续以英文写作,用欧美的文学尺度丈量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度,或以欧美作家作品为比较对象,以获得主流学术界的阅读兴趣和学术认可(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多以欧美作家作品为比较对象);要么换以中文写作,在汉语世界求取更广泛的知音之声(赞许甚或是质疑)。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这一处境,还导致了另一种学术倾向,即在研究方法上,流散、后殖民、身份意识等成为一种基调,这既契合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身的处境,也暗含了海外华人批评家一种巧妙的学术策略——以边缘谋取中心,这也正是当前美国人文知识界的学术游戏规则之一。海外关于“华语语系文学”的探讨,正是这一规则践行的一个例证。
在分析了海外华人批评家比较意识的成因之后,我们不妨更进一步,探讨一下其比较实践的具体形态和特质。应该说,海外华人学者从事文学比较的学术空间十分开阔,其中,既有中国现代文学的西学阐释(周蕾)、中国经验世界意义的揭示(张旭东),又有跨国(境)文学批评的实践(张错)、跨语际交流的考察(刘禾)、跨国文学概念的尝试(如“跨国华语电影”、“华语语系文学”),还包含了对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的个案分析(赵毅衡)等。跨科际、跨媒介、跨语言的比较与整合,日益成为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重要特征。
伴随着科际整合和媒介跨越,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大大扩容。如果说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较多地坚守着文学这一阵地,那么90年代以来,在文化研究等潮流的裹挟下,海外华人批评家不断将研究的触角旁及文学之外的其他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视觉文化首先进入海外学人的研究视野,华语电影研究的盛行,适应了海外华人学者从事中国文学教学及顺应文化研究潮流的双重需要。除此之外,早期美术、海报、月历、刊物、中国当代艺术、电视等一批视觉文本成为海外学者观照的对象,媒介研究成为跨文本分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海外有关Sinophone的研究,就是这种科际和多媒介整合的产物。在此情形下,坚守文学文本分析的学者,往往会秉持某种特别的认识或定性,如王德威就认为,海外华人批评家的跨界研究。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美国历史较短、尚未定型有关,虽然视觉文化研究是大势所趋,但每一行仍应有其特别的风格⑥。除了视觉研究,历史、思想、城市、社会、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进入海外华人批评家的比较视野,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呈现出更加斑驳的面貌,大有从比较文学转到比较文化研究之势。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这一转向,仍应溯源至相关的学科设置。在美国大学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隶属于开展区域研究东亚系的“中国研究”项目。一般来说,“中国研究”涵盖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如哲学、宗教、历史、政治、文化、文学、艺术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仅是其中极小的一个分支,教师往往不仅要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更需讲授先秦以来的整个中国文学史,有时还需兼任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其他课程。作为“小众”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考虑为自身的存在寻求更广阔的学术空间,于是,向视觉文化、思想史、城市研究、性别研究等方向兼顾或转移,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一种学术抉择。美国唯一的《中国现代文学》杂志更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可以看做这一研究领域在美国学科设置中所处情境的一个缩影。
三、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
至此,我们似乎能够讨论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整体观”了。
这里所讲的“整体观”,主要还不是针对作为对象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打通,而是指向作为主体的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强调的是通过海内外学人的互动,更新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观”,尝试以跨国意识、比较视野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气局。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上海学者分别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陈思和)以来,打通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已渐成学术界的一种共识,由此还形成了几次“重写文学史”的浪潮。毋庸讳言的是,内地学界“重写文学史”的呼吁,本身也是海内外学界互动的结果。正是有了近30年的“请进来”、“走出去”,大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元化意识才得以逐步消解,一系列基于“现代”意识的广义“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才得以真正诞生。
在海外华人学者那里,这种“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似乎走得更远。在学科意识明确的王德威笔下,这种整体观体现得尤为显著。王德威的“中文小说”研究大体上呈现出这样三个特征:一是空间上跨越现有的政治地理疆界,涉及内地、台湾、香港、海外;二是时间上打破内地学界关于现当代的分立,甚至将视野引入“晚清”这一重要领域;三是在写作思维上超越文学、历史、政治、思想、想象的交叉领域,体现明显的跨科际特点。当被笔者问及是否有意识地追求这种中文小说研究的“整体观”时,王德威这样回答:
对于打破时间和地理疆界这么一个做法,我的确是有意而为的,而且一开始就觉得我应该利用在海外的优势。这种优势在台湾也做不到……我不敢说我做了多少,但是我确实是有意识地在做,我也期望我在海外的其他同事,能够利用我们的优势——就是在海外比较远离国内政治语境的优势——来做一些真正交流和沟通的工作⑦。
经“整体观照”后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确实呈现出一种阔大的学术气象。仍以前阶段海外讨论热烈的“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为例,虽然海外学人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依然存在较大差异(如史书美倾向于以此指称“中国内地以外的华语文学”),但较主流的看法,仍是包含全球的华文写作。这种“打破中文小说研究的划地自限”(王德威语)的做法,展示出研究思维上的拓进与务实。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广义的“华语语系文学”,其研究旨归、价值立场和理论方法,同中国内地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仍有较大的分野,但二者的对话空间显然已被强烈放大。
海外华人学者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对于启发我们打通海内外研究界的努力不无裨益。虽然因种种原因,无论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内部还是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中,仍然存在着“学术政治的凸显”和“理论方法的碰撞”,海外的“去意识形态化”学术写作也不免还有“另一种偏见”,但彼此的交流仍有极大意义:唯有交流,才能祛除误解,减少偏见;唯有交流,才能在“双重彼岸与多元思考”中构建起一种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意识,实现海内外的互动与双赢。
交流并非要谋求所谓的“一体化”,也并不排除差异的继续存在。实际上,正是有了观念、立场、视角和方法上的差异,才可能造就对话和互动的学术空间。一切有价值的交流,都直是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发生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不应再像过去三十年间那样,以内地学界对境外的“单向接受”为主。事实上,随着海外学术资源的不断开放,海内外的学术落差正日益缩小,海外华人批评家们业已感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过去拥有的学术资料和理论方法的丽重优势,已不复存在,甚至发生了逆转;海外的宽松学术环境,也因华人学者需通过不断重回“中国现代义学”的发生地获得“现场感”而弱化。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海外学人正日渐感受到因传统学术优势丧失而带来的心理落差,频频回国兼职或短期工作,成了满足其多方面学术和心理需求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除少数台湾背景的学者外,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多数学者均以不同的方式回到内地开展学术交流,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为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学术话题。比如,可否尝试邀集不同国别的华人学者,运用新的体例或思路,以不同语言编印全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再如,在学术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能否对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模式进行归结,从中寻求合作交流的新路径?又如,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能否借助于会议、项目、出版、互访等方面的学术合作,逐步推进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的形成?
上述构想似乎并非不可能。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海外学人将跨文化、跨学科、跨媒介、跨语际的研究观念投射到国内,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过去中国文学研究的封闭单一视角,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今天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各自成就,严格意义上讲都曾得益于“彼岸”的存在。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我们并不奢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同世界”的到来,却有理由相信,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正以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弥散于不同语言和国家的华人学者之中。
注释:
① 1983年及其后几年大陆译刊的夏志清论文,主要是在中国古典小说领域,如夏志清:《论〈水浒〉》,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4期;《论〈儒林外史〉》,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3期。二文由郭兆康、单坤琴译自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英文版第三、五章;该书第一章译载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李欧梵:《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载《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
③ 李欧梵:《文学:海外与中国》,载《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6期;《美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现状与方法》,载《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5期。
④ 刘禾、李凤亮:《穿越:语言·时空·学科——刘禾教授访谈录》,载《天涯》2009年第3期。
⑤ 李凤亮:《美学·记忆·现代性:质疑与思考——王斑教授访谈录》,未刊稿。
⑥ 李凤亮:《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王德威教授访谈录》,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
⑦ 李凤亮:《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及其批评实践——王德威教授访谈录》,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2期。
标签:海外华人论文; 比较文学论文; 李欧梵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王德威论文; 现代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