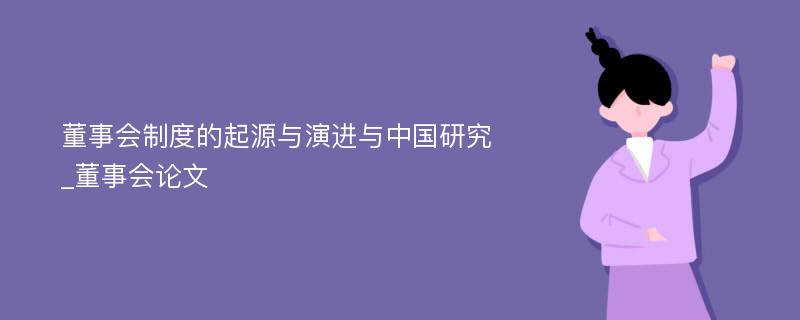
董事会制度的起源、演进与中国的学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董事会论文,中国论文,起源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今中外,有公司必有董事会。这一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一致性,要远远超过大多数法律中的问题。和纷纭芜杂的公司理论及其延伸命题——公司特性究竟包括哪些因素——的持久争论相比,① 董事会在规范意义上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行使者,集体决策、合议和共管的行为模式,几乎没有例外。但中国的公司和公司法理论研究,常常忽略了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模式必然存在的特征。
董事会的存在及其运作模式,受制于公司理论,这在过去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在19—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对公司的理解受制于拟制论和实在论的争论;20世纪30年代之后,各种各样的合同理论和政治理论沉溺于解释股东如何形成群体或实体及其权威或利益分配,更多关注公司管理者作为代理人对股东利益的偏离。近年来,董事会制度的原则、合理性、角色定位等规范命题的研究开始涌现。本文试图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一个中国文本。
一、董事会制度的原则性规范
纵横观察各国成文法和判例,公司董事会制度中有三个隐性的统领原则,界定了公司董事会运作的边界,即(1)董事会是公司权力的最高行使者(director primacy);(2)董事会采用一人一票平等的并且集体合议方式行事;(3)董事会对公司制度的有效和正当运作负有最后责任。这三个原则相互联系并交错在一起,这种集体决策权力行使方式,传统上称为共管(Collegial)。②
董事会作为公司权力的最高行使者是传统原则,也是目前除中国之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明确在成文法中的表述。这一原则首先确立了股东和董事会之间的两权分离,除非股东一致同意(美国特拉华州是唯一的例外,允许所有有投票权的股东在无需法定的会议通知程序下以书面形式进行多数决③),股东不能越过董事会直接作出决策,股东的投票参与的权利是由法律和章程限定的,它区别于完整、统一、至上的物的所有权。董事会的权力是完整和最高的,而股东权利则是依情形约定的,章程只是对权力作出限制而已。其次,决定了许多衍生法律规则,最典型的是法定诚信义务,以及业务判断规则。④ 最后,这一原则伴随着股东选举董事成员中的比例代表制,通常是简单多数,但也会存在诸如累积或累退投票制之类的变化,以用于反对控制股东的霸权。⑤
董事会采取集体和以投票方式决策的共管模式,英美法对这一原则的恪守要比大陆法严格。具体而言:(1)除非例外情形,比如在势均力敌的情形下,可能有些国家允许董事长或资方代表有第二票,董事会议应当采用合议方式决策,一人一票,有些法律直接规定人数必须为奇数。(2)董事通常应当亲自出席。这有许多细致的操作规定,比如委托投票,只能就某次会议作出授权,长期授权会被视为出卖职位;比如传统上不得采用书面一致同意的方式作出董事会决议,必须有实际的会议过程。⑥ 尽管如今有所放松,允许采用一致的书面意见或电话等方式开会,此类案例仍然会受到严格审查;⑦ 这其中的默认假定实际上是“政治人”,即董事决策时应有研究、辩论、说服和被说服的过程。修订标准公司法(RMBCA)的起草人对此有明确表述,“相互咨询和观点交换是董事会发挥功能的应有组成部分”。⑧(3)多数规则,以投票方式作出决策,董事会决议是“书面的、可执行的合同”。对合议存在不同意见,应当记录在案。(4)必须有正式记录(minutes)。
集体决策有个别例外。英美法、法国法、德国法⑨ 都有明确规则限制董事个人行使公司权力,他们只能以合议方式作出决策。比如RMBCA规定,董事“无权单独代表公司行为,而应当作为董事会的一个成员来行为”,甚至规定,除非得到明示授权,董事只能在会议上行动。但日本、韩国等则允许董事个人代表公司行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中国的公司法并不存在类似于后者的规定。在上市公司中,证监会在规则制定上受英美法的影响,通过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塞进了近似的规定。
董事责任方面,和合同法、行政法等趋向于程序或形式审查方式不同,公司法施加了实体倾向的诚信义务(fiduciary duty),这甚至被视为公司法的核心规范。⑩ 具体而言:首先,公司错误、非法、犯罪行为后果的第一责任人是董事,即权力行使者,而不是“财产所有权人”。其次,控制股东只有在行使了公司权力、替代了董事会或管理者的职责、直接作出决策或指挥的情形下才需要为公司行为负责。最后,董事会派生其他公司机关,通常是选举执行或管理机关。其他机关的设立理由,要么属于基于规制产生的强制性要求,要么是基于其他利益攸关者的考量,但诚信义务则是待定、模糊的,其责任要么来源于法律,要么来源于其专业或职业角色。在比较法层面上,各国法在前两项上规定比较清晰,但在最后一点上有些模糊。同时,受到法律调整方式的影响,大陆法系中的诚信义务更多带有事前强行禁止的特色。
尽管董事会制度存在着比较法上的诸多差异,但上述三个原则如同惯性,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在不同法律制度中以不同表述和形式呈现出来。公司实践的变化以及理论内在的统一性要求,会对这些原则形成一些冲击。理论上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公司理论对董事会制度的忽视或者强调。法律实践对董事会的冲击,主要体现在近几十年来美国和德国法律中董事会模式的变化。受到一体化和规模经济的影响,公司规模扩大,现实中的大公司决策和管理上的集权不断增强,尤其是公司结构不断从U型向M型发展,导致权力趋向于管理层,比如CEO的出现。(11) 在股东、董事和经理的关系上,美国公司逐渐趋向于总经理和董事会平行,从而将纵向关系转变成了实际上的三角关系。Eisenberg教授提出,基于结构变化,一方面应对股东和董事的两权分离程度进行调整,加大董事会的权威;(12) 另一方面战略管理职能日益成为总裁或总经理的职责,董事会应当以监督、督导管理层,以系统设计和维护作为主要职责和角色定位。(13) 董事会不再需要亲自管理公司,可以通过组建下级委员会或向管理层授权的方式将其战略管理职能转让出去,但第三个原则仍然不能动摇,因此,不得将监督职责授权出去。
1980年代以来,学者和立法者已经普遍将管理者角色作为传统模式,而将监督者角色作为现代模式。这表现在修订标准公司法的表述从“公司的业务和事务应当由董事会管理”,转变成“公司事务应当在董事会裁量下管理”。(14) 另外一个变化和两权分离有关,有些原本属于股东的权力,法律开始允许通过章程授予董事会,比如修改公司章程,甚至废除绝对多数票制度。
在另一种主流模式中,德国的董事会制度则趋向于员工参与,采用社会民主方式以确立公司存在的正当性。1937年纳粹时期,德国采用董事会—监事会制度(欧洲大陆模式)对抗方式,作为压制工会集体谈判方式的一种替代。二战之后,在英占鲁尔区的钢铁和煤炭企业中,英国军政府要求这些企业组成11个成员的董事会,其中股东代表和员工代表各5人,第11人则由前10个人选举,其依据是资方和劳方的“均势”原则。战后,军政府向联邦德国政府移交企业,于1951年通过法律确立下来,即共同决策法(也称为Mortan Act),但是董事会中的均势变成了董事会中监督委员会中的均势。(15) 社会民主党上台之后,一直致力于扩展这一制度。德国的董事会分成监督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两者存在着严格的划分,即监督委员会负责公司的总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选举、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董事,而管理委员会则负责日常的管理,并且两者之间不得兼任、相互授权。管理委员会有义务经常或应要求向监督委员会汇报。其中明确存在着监督和战略管理的分离。
Dallas教授将董事会归结为三种类型,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职能定位和角色:传统上和美国式的制约管理霸权式(contra-managerial hegemony)、德国的权力联合式(power coalition),以及她所倡导的关系理论(relational theory);(16) 与此相对应,董事会也有着“管理”、“监督”、“关系”以及英国传统式的“战略管理”等职能的定位。(17) 从战略管理到监督的职能演变中,董事会的职责集中于更重要的选任、监督和撤换最高管理者,维持公司作为一个制度系统,共管、合议的决策方式,采用平等协商、辩论和投票机制。在审慎决策、消除分歧、平衡不同目标上,集体决策模式与这种职责更为契合。
二、效率理论
占主导地位的产权—不完全合同理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发展中,强调市场和股东的财产权利之于公司的重要性,对董事会的制度、原则及其理性并没有过多关注。因此,合同理论对诚信义务的解释也就不够充分。(18) 关系型契约理论则强调董事会对公司资产的保护。在比较了股权和债权融资之后,Williamson指出,董事会内生地出现,充当了一个可置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通过限制重新配置资源,降低了用于融资项目的资本成本。董事会对来自股东和债权人的财产充当中立保护。和一般合同相比,它可以提供更好的保护。(19) 关系型契约为两权分立和董事会权威提供了一个功能解释,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法律对合议、共管等董事会行动方式也采取了强行性规定的方式。
试图采用经济理论或效率方法提供解释的是Bainbridge教授,他注意到主流公司理论在解释上对两权分离的漠视,根源在于两种合同理论本身的分歧。合同理论中坚持不完全合同理论,或者团队生产理论,会倾向于股权;而如果采取关系性契约理论,则会倾向于权威集中。与实证法相结合,Bainbridge教授将公司理论建构为两个不同的维度:目的和方式。前者意味着公司规范的目的或者价值取向,后者意味着决策权的集中与否。Bainbridge引用了Arrow的两种决策模式:共识模式(consensus)和权威模式(authority)。在共识模式下,组织中的每个成员拥有同样的信息和利益,所有成员可以自行选择合适行动;而在权威模式下,成员具有不同的利益和信息量,产生集中决策的需要。董事会作为最天然的合适机关,代表公司充当中心签约人的职能。现代公司是这种决策结构的天然结果。股东本位,既不是事实上的,也不是规范上的,仅仅是对公司目的的要求,而不能当成是一种实现方式。股东未必愿意参与到公司的管理之中,其角色也摇摆不定。(20)
为什么董事会需要集体决策?Bainbridge指出,董事会是一个生产团队,其职责在于管理和制定政策、监督管理者,同时作为合同连接体中的中心签约人,可以为公司提供资源(监督和关系角色)。(21) 依据组织行为理论,尤其是实证研究,集体决策的正确性要高于个体决策。集体决策的效率在于:(1)有限理性。决策有四个要求,第一,观察或者获得信息;第二,记忆或者储存信息;第三,计算或者掌控信息;第四,交流或者转化信息。而个人理性是有限的,可能会在有些情形下个体决策优于集体决策,但集体决策并不会妨碍好的个体决策获得集体认可。(2)集体决策可以消除偏见。第一,可以汇集不同意见(herding);第二,可以消除过分自信;反之,其成本则是集体偏见。(3)代理成本。组织总是存在着纵向监督和横向监督,而集体决策有助于监督的强化,克服代理成本;同时,集体的董事会有助于解决“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22) 在Bainbridge看来,法律之所以明确规定共管模式的行事方式,是出于集体决策理性的坚持而要求采取的特定方式。(23)
但Bainbridge的解释仍然不能令人满意:首先,集体和个体决策各自有优缺点,而且前者在追究错误决策责任上比较困难,其在量上的优势并不意味着绝对排斥个体决策,而这显然和公司法中对董事会模式的严格恪守之间存在差距。为什么公司法不能允许当事人在这两者之间自行选择?其次,如果集体决策仅仅起信息交流的作用,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出席或进行辩论和讨论?采用书面形式轮流批注,或者群发邮件交流是否可以视为开会?实证法中并不允许这种方式,一定要遵循相应的程序。再次,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一定要采用特定的集体决策方式,即一人一票的机制。纵观各国,为什么都明确界定了这一原则?最后,其解释是针对现在的公司运作方式,并不能解释过去。群体决策如果是基于效率产生的,人类在公司历史上似乎应当尝试过很多其他类型,最终发现这是一个有效率的模式。但是这恰恰错了,公司从一开始产生的时候,这三个基本原则就没有重大的改变。基于经济理论和效率,只能解释结果,而不能解释过程的唯一性。
三、历史和政治理论
Bainbridge的关系型契约分析忽视了早期公司观念受制于“政治理论”的历史。董事会的“共管”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是经济理性的构建?公司是历史发展而来的法律制度,董事会的三个原则,是否有过不同的替代方案?
Gevurtz教授基于历史和政治理论进行了分析。美国当今董事会模式的三个原则是:股东选举董事会,即两权分离;集体决策和一人一票;董事会负有选举和监督管理人员的最后职责。其功能理性在于:集中管理的需要;群体决策;代表不同利益攸关者(constituents,选民)和协调不同的分配要求;监督管理者的需要。对这一制度的渊源探索,他采用“追溯式”、“考古挖掘式”(archeological dig)的方法来表述。(24)
“私”的采取准则设立,允许私人自由组织并承担有限责任的,和现代公司法最相近的,最早可以追溯到1811年的纽约公司法。当时对董事描述的术语是“信托人”(trustee),其法律规定,除了董事会还负责战略管理之外,和现在并无不同。此前,美国更早期的以特许方式设立的公司,更多集中于公共领域。比如汉密尔顿作为发起人的1791年的美国银行,每年由股东选举25个董事,其中四分之一不得连任,董事会任命总裁。(25) 美国大陆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董事会制度,这源自英国。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是其样板。该公司最早使用了Director来指代董事,其章程规定,股东选举产生24名董事,其中三分之一不得连任。英格兰银行模式被Gevurtz称为最早的两权分离。
再向前追溯,1606年詹姆斯一世对北美颁发了两家公司的特许。第一家最早称为伦敦公司,后来更名为弗吉尼亚公司,在北纬34°—41°之间殖民。另外一家普利茅斯公司,在北纬38°—45°之间殖民。每家公司都在当地和英国组建双层理事会,而英国的13人的“弗吉尼亚理事会”,负责“最高管理和指导”。詹姆斯一世在1609年颁发了一个新章程,将公司行政管理权力转到司库(Treasurer)和副司库手中,组建了新的理事会,由公司成员选举产生而不是经过国王任命。当地理事会被取消,直接由理事会任命的总管(Governor)来负责具体管理。这被Gevurtz认为具有了董事会中心的治理方式。(26)
同时期的英国,存在的公司形式是以殖民公司(Trading Company)为主业的合股公司(Joint Stock Company),包括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俄罗斯公司、地中海公司、哈德逊湾公司等,有证据表明,它们均持续采用了董事会制度。比如1600年,伊丽莎白一世颁发章程,允许216名骑士、市府参事(alderman)、商人组成“政治体和公司”,即东印度公司,授权范围包括管理航线,以及与公司相关的其他事务。其中,总管和24个人组成“委员会”(committees),即今天的董事会。章程任命Thomas Smith为首任总管,但委员会成员由公司成员每年选举产生。这些合股的殖民公司被视为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公司来源。(27)
早于合股公司的是规制公司(Regulated Company,也译为公共公司),相当于今天的行会,可以继续向下授权组建合股公司。规制公司实际上并不从事经营,而是商人之间的协调组织。最早的两家规制公司是斯台伯商人公司(The Company of the Merchants of the Staple)和商人冒险家公司(The Company of Merchant Adventures)。前者大约在1313—1363年间采取了董事会治理方式,后者在1505年亨利八世时成立,也设立了董事会。它们从国王获得授权,垄断各自领域的对外贸易。商人(即成员)选举产生总管,而董事会的主要职责是解决内部纠纷,对外支持商人的贸易行为。英国公司的起点到此为止,但欧洲大陆同时期的其他公司,包括荷兰东印度公司、汉萨同盟(Hanse),都有类似董事会的治理方式。(28) 这些公司中的董事会,负责制定规则、立法(管理成员)和纠纷解决(处理成员间的纠纷),履行立法和司法功能。合股公司是规制公司向下的授权和复制,故而董事会治理方式也随之延伸。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这可能是今天的公司制度从“公”发展到“私”,继承了某些政治组织特点的原因之一。
Gevurtz的考察揭示出,董事会的存在、选举和代议、按人投票、集会行事等制度原则,几乎从有公司出现伊始,就“顽强”地存在着,其间可能有所损益,但并无根本变化。尽管董事会的职能,在治理结构中的位置,随着所在组织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也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但基本原则始终沉淀其中。今天的董事会治理方式及其制度原则的顽强存在显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组织概念的自我复制。(29)
不过,公司作为一个创造物而非自然产生的制度,其对代议制民主的引入和使用,在思想上有其他来源。“代议式的董事会,和一个首席行政官一起工作(早期公司章程中采用的典型术语是‘主管’),是中世纪晚期西欧政治实践和理念的反映”。(30) 规制公司出现之前,在英国地方政治中广泛采用的“集会”(assemblies)或“议会”(parliaments),城镇理事会,行业理事会以及教会中,已经存在着类似的机制。Gevurtz对此也进行了“考古挖掘”,集体决策的委员会制度,政治上来源于“顾问团”。比如中世纪的大多数国王,都拥有一个顾问团,采用委员会机制。地方贵族(barons)和国王之间的斗争,要求统治者获得更大范围的正当性,推动了更广泛的教士和地方贵族的代表、集会机制的产生,这促使委员会机制和选举结合。例如1295年,爱德华一世颁布了“模范议会”谕令,要求地方长官推动选举组成议会,每个县(county)两名骑士,每个城市(city)两名市民,每个市镇(borough)两名村民作为代表,组成议院(chamber),和贵族分开议事,此后逐渐成为下院(the House of Commons),区别于贵族组成的上院(the House of Lords)。这是议会的来源。西班牙国王也差不多同时设立了议会,德国和法国也在地方和中央政治层面逐渐出现了代议制。(31) 地方的城镇或乡村理事会是董事会的另外一个来源,有证据表明,在12世纪之后,英国有些自治城镇组成理事会,由12或24名成员组成是一个普遍做法。而公司的监督者(auditor)则被认为是来源于行会。(32)
除了政治层面的来源之外,中世纪的这些制度,文化上受制于基督教是毋庸置疑的。合议、代表和投票选举制度并不是自然产生的,是和特定的制度、文化、对人的假定等联系在一起的。在1200年之前,可以考据的、由代表以平等协商和投票的方式进行决策,尤其是选举最高领导的制度,是11世纪中期的红衣主教团(the College of Cardinals)。尽管代议制可以追溯到325年的尼西亚(Nicaea)会议。1059年,教皇尼古拉二世颁发谕令,授权教会内部的红衣主教团选举教皇,以改变在此之前国王指定教皇的规则,导致随着政治斗争同时出现过三个教皇的局面。因此,合议与共管制度,内部人选举最高领导,是为了保证组织的独立性。公司(corporation)本身来自于拉丁文中的“体”(corpus),遵循“影响全体之事必经由全体同意”(quod omnes tangit ab omnibus approbetur)的原则。(33)
董事会治理方式作为一种代议制(representative)民主方式,选举代表、合议、负责产生最高管理者,和希腊的直接民主以及罗马的元老院治理方式不同。总结一下Gevurtz的观点,在前公司时代,有两个源头非常关键:第一,在一个独立的非国家组织中,按照章程,采用这种治理的方式,很显然是受到基督教传统的直接影响,其目的在于保证组织的自治和独立;第二,公司负有殖民、商业垄断管理等政治或社会职能,并受到中世纪的议会、合议、代议等政治传统的影响,采取了政治组织的原则。这种进化源头符合公司作为私的政治实体的特点,从规制公司,到合股公司,再到现代私人公司,董事会的治理方式,尤其是三个原则,在底层顽强地生存。
Gevurtz“考古挖掘”的启示是:(1)公司董事会的权威和特定行使职权方式,更多是促进组织独立,制约管理霸权,为了体现全体成员意志。(2)理解公司应当和对历史的考察相结合,许多原则的边界是和政治理论甚至宗教、文化联系在一起的。(3)董事会的原则和角色、职能是不同的,在历史上董事会承担的职责更多是保持对法律的遵守,而不是追求效率;更多是为了制定规则(立法)、进行内部仲裁(司法)或提出建议而不是决策和执行。
四、对照与检验:日本和中国的近代化
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最初在欧洲形成,伴随着殖民扩张成为世界性的公司治理方式。(34) 这种特定组织形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和宗教观念。这可以从伊斯兰世界和东亚国家——主要是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中国对公司制度的学习与借鉴中得到验证。
公司及其制度并不会简单地随着商业贸易和人际交往而通过市场方式繁衍,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典型例子。12—13世纪之间地中海南北岸就存在着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持续交易,但双方采用的交易制度却因为受到各自文化观念的影响发生了制度分化。(35) 1851年奥斯曼帝国才建立了伊斯兰世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合股公司。在欧洲和中东交往的一千多年之后,借鉴法国以变法模式采用了公司形式。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伊斯兰教义和公司制度间的不兼容。(36)
不只是伊斯兰世界,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也有类似现象。公司及其治理方式,对非基督教文明和政治体而言,是纯粹的舶来品。面对陌生领域,人们总是用传统中的固有观念去填充未知领域。缺乏基本的政治和宗教观念支持,采用主动变法模式,照搬照抄法律规则,而不是进行充分理论准备之后,或者经过完整的理论研究以确定制度合理性,在变法之后就会遇到许多“橘逾淮为枳”的情形。这种舶来品产生的移植局限,在许多制度细节中可以发现。日本和中国作为主动转轨的国家,是最典型的基督教文明之外的例子。
Gevurtz教授分析了日本的例子。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不存在西方式的多数投票决策、代表、共管等制度。当时诸侯式封建模式统治着日本,商业领域的组织采用家族企业形式,家长作为领导,与其他成员共同拥有企业财产,儿子可以以家族企业的名义建立分支。在17—18世纪,这些企业中有雇佣管理人员的存在,如同中国的山西商号一样。很多家族企业之间存在着协调,是一种协商机制(discussion system),首领是轮换制的。(37) 这些特点,本质上是封建模式在公司治理中的延伸,是企业间的合作模式受制于政治文化的另一个例子。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引入了公司制度。1872年,日本颁布了国家银行法令,逐渐产生了近150家合股银行。这些合股公司和银行采用与传统行会相同的机制,董事会有3个董事,但是轮流代表公司对外行为。每个董事有30个干事(steward),其中6个一组按月轮换监督管理具体商业事务。在日本正式采用德国模式强行规定董事会治理模式之前,这些银行的治理规则,作为一个转轨中的系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政治结构。一直到1893年的公司法,日本通过照搬照抄的方式,才正式确立了董事会为公司管理中心的制度。尽管如此,今天仍然可以在日本公司法,乃至于日本法输出的韩国,和东亚其他受到日本影响的地区中,找到缺乏政治文化和宗教观念的董事会制度:(1)董事可以独立对外代表公司,履行分工职能进行管理,而不是以监督为中心,必须采取合议、共管、投票的方式;(2)董事间的相互授权时间缺乏限制,不存在对卖官鬻爵的限制。
日本在短短20年间采用全盘西化、囫囵吞枣的方式完成了公司制度的引入。中国与之不同,作为一个文明原生国,对公司制度的吸收情形要复杂、长期和多样化得多。中国的公司制度始自清末立法。晚清时期,公司的概念进入中国,并伴随着贸易、殖民、洋务运动和变法分层次、分阶段地引入。中国对公司的最早了解始于19世纪早期。西方传教士所办的《东西洋每月统计簿》(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中文杂志在道光戊戌年(1838)9月期对“公班衙”(Company)进行了介绍,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最早中文文献,“公班衙者,为群商捐资贮本钱,共同作生意也……自从五印度国属英公班衙之手,四海平静,治百姓,以宽和处之……故曰,公班衙之治天下,可运之掌上。”(38) 这篇短文将公司的合资、独立地位及其商业和政治功能阐述得非常清楚,但并没有涉及公司内部治理的具体原则和方式。这是从功能上进行知识介绍。避免核心价值的冲突,并希冀阅读者接受。这种视角对外来文明的传播者而言,是非常合理的选择。当然也可能是作者对公司的认识受制于当时流行的观念,即拟制理论的影响。上述短文基本上被魏源的《海国图志》全盘接受。这之后,直到薛福成的《论公司不举之病》,陈炽的《纠集公司说》等著名论述,均将公司等同于筹资,设公司等于工商救国。(39)
这些早期有些狭隘的公司观念,对制度学习者来说,在实践中受到观念、知识、时局、政治等因素的制约,一旦超出简单观念的边界,就容易走样,而其固有的传统知识就会作为填补。比如1867年容闳所起草的《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被视为中国官方确认的第一个公司章程,共计16个条款,其中具备了许多公司的基本特点,比如股本、股东、股东权利和义务、公司账号和名义,甚至某种程度的诚信义务,但在内部治理上并未规定董事会,而是采用类似于晋商商号的经营方式。(40)
这个章程因试图雇佣外国人而引起非议,谨慎的曾国藩并没有实施。第一家官方许可的公司是1873年李鸿章设立的轮船招商(公)局,其章程被称为《招商局条规》,共28条,是典型的官督商办模式,其中仅在第4条提及董事,“有能代本局招商至三百股者,准充局董”。(41) 该公司实行总办负责制,由官方任命,不过是行政模式的翻版加上商人出资而已。这里所谓的董事(局董),并没有明确其角色和职能,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股托”而已,是领薪水的特权股东。由于招商不足,半年之后就进行了改组,新版的《轮船招商章程》明确了董事的选举,“选举董事,每百股举一商董,于众董仲推一总董”,但“将股份较大之人公举入局,作为商董,协同办理”,(42) 这种董事会不过是类似于股东会的常设机构而已,在实践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1885年,盛宣怀拟定了《用人章程十条》,改回到官方直接任命督办,再用两名“查账董事”作为监督机制。这个改革,目的在于防止当时流行的腐败现象:官员及其亲属利用董事的身份领薪,变相收受贿赂、冗员充斥而公司亏损。但这显然并没有理解董事会之于公司的必要性。当时,包括张謇在内的诸多实业家,其实践都表现出人们对公司的理解局限于合资、融资(《招商局条规》中还有备受诟病的官利规定)、实业、商业贸易等层面。(43) 那时候大多数中国人理念中的公司,更多是具备了股份融资功能的工厂、商行而已,受制于将公司等同于商号融资的认识。
对公司尤其是董事会的认识在1880年代之后有很大的进步,这有赖于郑观应、钟天纬,以及哲美森等在《申报》等刊物上的批评和对西方公司治理的介绍。(44) 人们开始陆续认识到董事会具有制衡监督的功能,“层层钳制,事事秉公”。(45) 此外,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更强调了官督商办的不合理,强调“按西例,由官设立办国事者谓之局,由绅商设立,为商贾事者谓之公司”,明确了公司的公私划分上的属性,也认识到了公司内的分权层次,如“公司总办由股董公举,各司事由总办所定”,(46) 开始意识到公司作为组织要求自治的特性。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严复对公司的认识可能是同时代人中最深刻的。在其翻译的《国富论》中,通过按语清晰地阐明了公司在法律上的特点,(47) 而在《法意》中,更通过按语揭示了公司受制于政治特性的特点,“欧美商业公司,其制度之美备,殆无异一民主,此自以生于立宪民主国,取则不远之故。专制君主之民,本无平等观念,故公司之制,中国亘古无之”,(48) 但是这种卓越的认识,却被时代所淹没。
对公司认识的进步,也来自于官方的推动。也许是经历了漫长的学习与摸索,也许是因为日本学者照搬照抄,清末《公司律》大致恪守了董事会制度的三个原则。首先,明确了两权分离,第45—61条明文界定了股东权利,选举董事,尽管没有明确董事会和股东会的权限划分,很难判断是否明确了董事会中心,除非对第67条进行扩大解释。其次,确立了董事会共管模式,第64条规定了董事会三人到场即构成会议,并且遵守会议条例;第89条规定一人一票,第91条规定僵局时董事长有第二票;第92条规定必须有书面记录。最后,明确了董事会作为产生其他机构的中心,第67条规定“各公司以董事局为纲领,董事不必常川住公司内,然无论大小应办应商各事宜,总办或总司理人悉宜秉承于董事局”;第77条规定“公司总办或总司理人司事人等均由董事局选派,如有不胜任及舞弊者,亦由董事局开除”。(49)
和日本类似,1908年颁布的《公司律》是以照搬照抄的方式来实现的比较系统西化的法律版本,明确了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对公司及其特定治理方式的认识,从接触、尝试到施行,经历了近100年。这可以看成是原生文明的转轨或学习成本。
五、现有制度的检讨
中国对公司的学习路径,是从功能视角上、而不是从本质上来理解的,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方富国强兵的特定需要而引入的,在学习过程中也缺乏系统的理论辨析,加上特定历史时期的理论影响,大清《公司律》对董事会制度原则的吸收,并没有沉淀为中国法律体系的一般知识。之后法律模式几经变化,当我们在1978年之后重新认识公司时,这些知识被遗忘了。
中国目前的董事会法律规则,采用了法条比较的研究方法作为基础,或者说“博采众长”,或者说“东拼西凑”。在一些形式规则上,和其他立法例之间颇为近似,比如股东会按资投票,董事会按人投票,多数决,甚至还有累积投票可供选择,新修订的法律中大幅完善了诚信义务,甚至试图将两大法系的不同做法熔为一炉。但仔细检验一下,对董事会的前述三个原则,现行法并没有明确的坚持。
第一,没有明确董事会作为公司管理的最高权威,第47、109条款中采用了列举方式界定了董事会职权,明确表述“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关”,允许章程自行规定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职权。许多行政规章会较为任意地改动股东和董事之间的分权界限,比如证监会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将许多战略管理的权力给了股东会。在司法实践中,将公司看成是股东财产延伸的观念广泛存在。这和现实中广泛存在的董事会不过是控股股东对公司控制权延伸、董事席位是股东按资瓜分而不是选举的等诸多情形是吻合的。总体来说,当下主流公司治理理论是倾向于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在股东会和董事会纵向权力上的收缩,导致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过度控制了董事会的成员,特别是,由于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作为公司中的主要构成,使得董事会的独立地位不能保证,董事会成员受控于其所提名或选举的股东,其向全体股东负责的诚信义务不能得到法律裁判的支持。这影响到了董事成员之间的平等,合议也常常流于形式。
第二,对董事会的共管模式,缺乏明确的原则,边界并不清晰。虽然规定了诸如一人一票、记录、合议、多数决(所有董事人数为基准)等,同时存在着法定代表人制度,并不存在董事独立对外代表公司的情形。但下列情形反映出现行法没有理解共管原则。(1)董事间相互授权并无实体限制,《公司法》第113条允许董事在不能亲自出席的时候委托其他董事行事,对授权次数和期限无限制;(2)董事产生方式是选举产生的,但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反对席位瓜分等方式,而现实生活中采用董事派出制是典型的“潜规则”;(3)没有明确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必须将实质辩论、说服与被说服等包含在内。
第三,责任原则是非常特别的,中国现行法中存在着不同层面。首先,无论是法条表述上、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董事对公司行为负有最后责任是明确的。在认定犯罪等行为的时候,一旦公司行为被认定为非法,作出决策的相关董事都应当承担责任。其次,董事会派生其他机关、尤其是总经理是明确的,但监事会、法定代表人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和协调是不明确的。最后,权力和义务并不对称,没有事前的最高权力,常常受到控制股东的直接指挥,但却要承担最后的决策责任,既没有业务判断规则保护,也缺乏权责一致的激励。
结论
考虑到中国现行法不能坚持三个原则而有别于其他“普遍性”立法例,如果站在将公司等同于股东的延伸,纯粹从功能及经济效率来考虑的话,我们可以提出一些非常好的问题:董事会有什么意义?尤其是那些一年只开一两次会议,并不存在着实质交流、辩论的董事会。集体决策就一定好于个体决策?这种高成本维持的法律制度,究竟能获得多少制度收益?假如自然总是选择最短的道路,单纯从功能上认识,在中国人曾经探索的模式中,除了容闳模式的公司仍然是晋商式的,或者是可能被利用来为高级官员洗钱、获得干股等方式来从事不当行为之外,盛宣怀模式的独裁的总经理+查账董事(事实上是监事)可能更加符合经济效率或者股东利益。为什么不能像盛宣怀所尝试过的那样,略略改造一下,股东会选举总经理,然后由董事履行查账功能?为什么还要啰啰嗦嗦地先选举一个董事会,然后由董事会(实际上也是代理人)选举一个管理一把手?
对董事会存在正当性的辩护,Eisenberg的观点是其中的一种。在新的社会条件和理论背景下,董事会的战略管理职能已经被放弃,CEO或总裁随着公司规模扩大越来越趋向于集权,他们拥有直接的顾问和智囊团,而董事会的角色则趋向于监督。监督需要选举和解职的能力,踩刹车式的决策和维护系统的职责,这需要斟酌和考虑更多的因素,通过辩论、讨论的方式来加强信息的沟通,消除偏见,更适合合议和共管方式。这仍然是从功能上论证的,并不能排除其他的选择项。
回答董事会制度的理性,应当回到公司的本质理论。确保组织的独立和持久存续,保证董事会向全体股东负责而不是只向某一部分股东负责,向公司的长期利益而不是单纯体现为股东意志的股东利益负责,才是董事会制度存在的理性所在。仅仅从功能、效率上去认识公司,而不是从公司的政治理论、独立地位和社会属性、董事会合议方式作为小型民主制度上入手;(50) 不是从强调公司的宪法特性、责任权威、审慎决策和可争论性入手,从组织的独立性入手考虑公司董事会的存在、功能和角色,是无法解释和判断董事会在其他法域中的行事方式与原则的。(51) 尽管公司的本质理论存在着二元对立甚至“精神分裂”,(52) 但公司董事会制度及其规则的政治和民主属性并不能因为“执其一端”而被忽略。
当下中国的公司法理论中,一些假定或基础知识被忽略了:公司是两权分离的实体,不仅仅是一个融资或扩大生产的工具。组织自治,才会产生董事会作为立法者和裁判者的角色的需要(商人冒险家公司),或者是内在的、自我选择选举最高领导者的举措(红衣主教团),或者是基于董事作为政治人的假定(说服、辩论和讨论的过程)的。换一个角度来说,公司法发展的历史逻辑是:公司在前,股东在后,才会产生已有的垄断性企业如何去扩大融资吸收新股东,进而发展出资本市场,发展出股票等工具。而效率理论也好,功能视角也好,则是从逻辑上颠倒过来,要解决的命题变成了股东如何利用公司去实现扩大再生产。
当下中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和对董事会制度意识的淡薄,毫无疑问受制于儒家法律传统中缺乏合议、共管、投票决策的知识,受制于现行体制下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构成主体的现实,受制于资本市场受到规制并被分割的规制模式,受制于在法学知识上倾向于股东会中心主义的思维习惯。但随着公司组织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的进化,重新认识董事会制度及其背后的深层逻辑,“认真对待”公司的政治属性,在董事会权威中心、合议和共管制度上继续不断学习,也许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注释:
① 参见John P.Davis,Corporations:A Study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Great Business Combinations and of Their Relation to the Authority of State,vol.1,New York:G.P.Putnam's Sons,1905,PP.13-34.
② Douglas M.Branson,Corporate Governance,Charlottesville,VA:Michie Company,1993,pp.153-157.
③ 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228条。参见Edward P.Welch and Andrew J.Turezyn,Folk on the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Fundamental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3,pp.510-515.
④ 参见Melvin Aron Eisenberg,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Organizations,8[th] edition,New York:Foundation Press,2000,pp.180-181.
⑤ 参见Stephen M.Bainbridge,Corporation Law and Economics,New York:Foundation Press,2002,pp.450-452.
⑥ Rufus J.Baldwin and another v.Thomas H.Canfield,26 Minn.43,1 N.W.261; 1879 Minn.
⑦ May v.Bigmar,Inc.,838 A.2d.285,288 n.8 (Del.Ch.2003).
⑧ Stephen M.Bainbridge,The New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82.
⑨ 参见Mads Andenas and Frank Wooldridge,European Comparative Company La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288,291,308.德国明确允许公司章程作出例外规定,但个体决策不能对抗多数决策。
⑩ 参见Lawrence E.Mitchell,“FaIrness and Trust in Corporate Law,”Duke Law Journal,vol.43,no.3(Dec.1993),pp.425-491.这里所说的合同法和行政法,只是一般规范意义上的,在理论上也存在着争议,包括合同法中的对价理论和行政法中的公平要求。参见Larry A.DiMatteo,Contract Theory:The Evolution of Contractual Intent,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8;也可参见H.W.R.Wade and C.F.Forsyth,Administrative Law,7[th]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44.
(11) 参见Oliver Williamson,“Corporate Governance,”Yale Law Journal,vol.93,no.7(Jun.1984),pp.1197-1230.
(12) 参见Melvin A.Eisenberg,“The Legal Role of Shareholders and Management in Modern Corporate Decision-making,”California Law Review,vol.57,no.1(Jan.1969),pp.10-14.
(13) 参见Melvin Aron Eisenberg,“Legal Models of Management Structure in the Modern Corporation:Officers,Directors,and Accountants,”California Law Review,vol.63,no.2(Mar.1975),pp.375-439.
(14) 参见James D.Cox and Thomas Lee Hazen,Cox & Hazen on Corporations:Including Unincorporated Forms of Doing Business,2[nd] Edition,vol.1,New York:Aspen Publishers,2003,p.409.
(15) 参见Benjamin A.Streeter,III,“Co-Determination in West Germany-Through the Best (and Worst) of Times,”Chicago-Kent Law Review,vol.58,no.3,1982,pp.982-983.
(16) 参见Lynne L.Dallas,“The Relational Board:Three Theories of Corporate Boards of Directors,”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vol.22,no.1 (Fall 1996),pp.1-25.
(17) 参见Lynne L.Dallas,“The Multiple Roles of Corporate Boards of Directors,”San Diego Law Review,vol.40,no.3 (Fall 2003),pp.781-820.
(18) 参见Oliver Hart,“An Economist's View of Fiduciary Duty,”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vol.43,no.3 (Summer 1993),pp.299-313,305-309.
(19) 参见Oliver E.Williamson,“Corporate Boards of Directors:In Principle and in Practice,”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vol.24,no.2 (Oct.2008),pp.247-272.
(20) 参见Stephen M.Bainbridge,“Director Primacy and Shareholder Disempowerment,”Harvard Law Review,vol.119,no.6 (Apr.2006),pp.1735-1758.
(21) 参见Stephen M.Bainbridge,“Why a Board? Group Decisionmaking in Corporate Governance,”Vanderbilt Law Review,vol.55 (Nov.2002),pp.1-55.
(22) 参见Stephen M.Bainbridge,The New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pp.89-100.
(23) 参见Stephen M.Bainbridge,The New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pp.80-82.
(24) 参见Franklin A.Gevurtz,“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Corporate Board of Directors,”Hofstra Law Review,vol.33,no.1(Fall 2004),p.108.对Gevurtz的公司历史起源的文章,国内学者有过介绍。参见吴伟央:《董事会职能流变考》,《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25) 参见Franklin A.Gevurtz,“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Corporate Board of Directors,”p.109.
(26) 参见Franklin A.Gevurtz,“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Corporate Board of Directors,”pp.110-111.
(27) 参见Franklin A.Gevurtz,“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Corporate Board of Directors,”p.116.
(28) 参见Franklin A.Gevurtz,“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Corporate Board of Directors,”p.129.
(29) 组织发展是按照已有的知识结构自我复制扩张的,这是组织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理论中新发展出来的一种解释。参见Barbara Levitt and James G.March,“Organizational Learning,”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14,1988,pp.319-340.也可参见Geoffrey M.Hodgson and Thoibjorn Knudsen,“The Firm as an Interactor:Firms as Vehicles for Habits and Routines,”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vol.14,2004,pp.281-307.
(30) 参见Franklin A.Gevurtz,“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Corporate Board of Directors,”p.129.
(31) Franklin A.Gevurtz,“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Corporate Board of Directors,”p.131.
(32) Franklin A.Gevurtz,“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Corporate Board of Directors,”p.162.
(33) Franklin A.Gevurtz,“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Corporate Board of Directors,”p.134.
(34) 参见Franklin A.Gevurtz,“The European Origins and Spread of the Corporate Board of Directors,”Stetson Law Review,vol.33,no.3 (Spring 2004),pp.925-954.
(35) 参见Avner Greif,“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2,no.5 (Oct.1994),pp.912-950; 也可参见Avner Grieif,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Lesson from Medieval Trad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36) 参见Timur Kuran,“The Absence of the Corporation in Islamic Law:Origins and Persistence,”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vol.53,no.4 (Fall 2005),pp.785-834.
(37) 参见Franklin A.Gevurtz,“The European Origins and Spread of the Corporate Board of Directors,”pp.931-934.
(38) 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计簿》,黄时鉴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18—420页。爱汉者是德国籍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Gutzlaff)的笔名,杂志由中国益智会举办。参见黄时鉴导言。
(39) 许多经济史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且将其与中国面临的亟需富国强兵的观念、官办企业的方式等联系在一起。参见豆建民:《中国公司制思想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杨在军:《晚清公司与公司治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40) 《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下册(共三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第873—875页。
(41) 《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下册,第921页。
(42) 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下册,第846—847页。
(43) 参见朱荫贵:《从大生纱厂看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同时参见李玉:《中国近代股票的债券性——再论“官利”制度》,《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44) 这方面的研究众多,例如杨勇:《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演变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45) 钟天纬:《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策》,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26,户政三,理财下。
(46) 《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12页。
(47) 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5—116页,“严复案语”。
(48) 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40页,“严复案语”。
(49) 此处所引《公司律》,均源于《大清新法律汇编》,杭州:麟章书局,1910年再版,第551—580页。
(50) 参见Mark M.Hager,“Bodies Politic:The Progressive History of Organizational‘Real Entity’Theor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vol.50,1989,pp.575-654.
(51) 参见Stephen Bottomley,The Constitutional Corporation:Rethi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7.
(52) 参见William T.Allen,“Our Schizophrenic Conception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Cardozo Law Review,vol.14 (Nov.1992),pp.261-280.
标签:董事会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公司法论文; 组织职能论文; 监督学习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