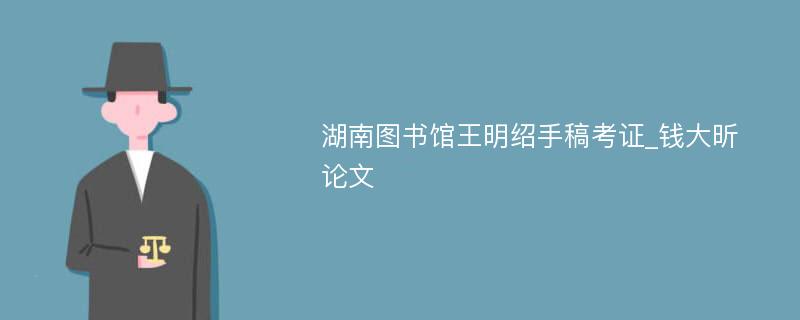
湖南省图书馆藏王鸣韶稿本《鹤谿文稿》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稿本论文,湖南省论文,文稿论文,图书论文,王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文人别集数量繁夥,“清人别集丛刊”也陆续得以刊印①。但由于清代文献繁复,仍有不少清人别集深藏于各地图书馆,学界了解甚少。清代著名藏书家、同时也是清代书画史上“后四王”②之一的王鸣韶所撰稿本《鹤谿文稿》就是较为稀见的清代别集之一。作为有清著名史学家、经学家和考据学家王鸣盛的胞弟,王鸣韶虽然在藏书史和书画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但其文学创作情况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却鲜为人知悉。《鹤谿文稿》一书收录有王鸣韶不同时期24类各体文章192篇,充分反映了王鸣韶在文学创作层面的成就;且稿本正文前后留存有清代以来著名学者钱大昕、朱春生、汪照以及民国时期藏书家叶德辉、叶启勋的亲笔题识、序跋多则,则凸显出稿本传承的渊源有自;而清代“吴中七子”之一的文学家王昶(兰泉)针对稿本文章作了批校,其有关诗学观念的评点颇具文学批评特质。所有这些,对于深入了解王鸣韶生平交游、文学创作以及诗学观念等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笔者拟对《鹤谿文稿》的相关情况略作考辨,并努力发掘其中包孕的文献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以就正于方家。 一、王鸣韶及其《鹤谿文稿》概述与清以来学者的批校题识 王鸣韶(1732-1788),字鄂起,原名廷鄂、字夔律,自号鹤谿子,嘉定人,是清代较为著名的藏书家、书画家和文学家。诗宗眉山、剑甫,为“江左十二子”之一,著有《逸野堂文集》、《竹窗琐碎》等。钱大昕所撰《鹤谿子墓志铭》详细记载其生平事迹,可知他“性落拓,澹于荣利”,“好为诗古文,兼工书画”,富于藏书,“生平喜钞书,所收多善本”,并且留心搜访乡邑文献③。 湖南省图书馆藏《鹤谿文稿》稿本四册,不分卷,王鸣韶撰,王昶批校,钱大昕、朱春生、汪照、叶德辉、叶启勋题识。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偶有二十二或二十三字者)。墨笔楷书,所用稿纸或为印有黑色版框的稿纸(左右双边,单鱼尾),或为纯白宣纸,其中亦杂有已刊入他人文集或其他书籍中的王鸣韶撰写的序跋文章。这些序跋为刻本形态,当为《鹤谿文稿》编撰时直接从他人文集或书籍中移入。从所用稿纸的情况,可以判断文稿来源的原始状态,也进一步证实王鸣韶《鹤谿文稿》的原创性。稿本收录王鸣韶撰写的各类文章192篇,按目编次,共分24类,包括:“序”47篇、“记”28篇、“书”19篇、“论”9篇、“议”1篇、“说”2篇、“考”4篇、“跋”20篇、“书后”9篇、“传”7篇、“问”1篇、“赋”2篇、“疏”2篇、“论”2篇、“书事”2篇、“碑”1篇、“墓志铭”15篇、“墓表”2篇、“塔铭”1篇、“行述”4篇、“事略”1篇、“像赞”3篇、“哀辞”2篇、“祭文”6篇,另有附录2篇。从稿本中文章的文体看,《鹤谿文稿》大多为应用性文章,其中以“序”、“记”、“书”、“跋”、“墓志铭”为夥,共有129篇,占了文章总数的67%。 《鹤谿文稿》编纂成集以后,颇受历代文人学者和藏书家的重视。许多学者或对正文内容进行品评批校,或为其撰写序跋、题识,既丰富和完善了稿本的内容,又为深入了解《鹤谿文稿》的编纂传承、正确理解正文内容提供了线索,指明了方向。 《鹤谿文稿》的批校题识数量较夥,形式多样。既有学者、藏书家出于介绍稿本渊源、阐述稿本特质等撰写的题识序跋,也有基于文本本身进行文学品评鉴赏,富于批评特性的各类评点;既有着眼于文字校勘的批校,也有表属各种增删改补的圈点。仅就评点形式而言,就有眉批、尾批和补记等多种方式。经粗略统计,《鹤谿文稿》共有各类批校题跋100多则,其中题识序跋6则,正文处眉批21则,尾批补记9则,旁批数十则。 稿本的题识序跋因大多署有姓名,序跋作者清晰明了,包括钱大昕、朱春生、汪照、叶德辉、叶启勋等著名学者,但《鹤谿文稿》中的批语则很多未能明示,尚须略加考查。这些批语的作者除有明确署名外,如《昭庆寺修建记》文末的尾批补记明确题有“乾隆壬寅二十一日述菴昶书于鸳湖舟次”字样,知此条尾批补记出自清代文学家王昶之手;其他的应当主要出自汪照之手,其中《华萼堂记》明确注明“汪照拜读”,而大多数批语则没有注明。关于这一问题,汪照在作于戊申二月三日的题跋中已明确提及自己评点《鹤谿文稿》之事: 新岁酬应纷如,读一篇未竟,辄有冗事扰之。今连两竟日门稀剥啄,始得焚香卒业,间出己意,时附评语于后,特余之于古文,如扪烛扣槃,毫未有当,为可愧耳。 汪照在题跋中交待了自己在“新岁酬应纷如”之空隙,花费“两竟日”阅读《鹤谿文稿》的状况,并加以品评,“间出己意,时附评语于后”。由此可知,汪照当为《鹤谿文稿》评语的主要作者。另外,叶启勋在1919年(己未)的题跋中又明确断言:“篇末评语则为汪手批,眉上评语验其字殆亦兰泉、少山手笔。”这说明篇末的评语主要出自汪照之手,而眉批则又出自王昶等人之手。 《鹤谿文稿》的批校概括言之,有如下几类: 1.富于文学批评特征的评语。《鹤谿文稿》中富于批评色彩的评点主要体现在眉批和尾批补注上,数量虽不算特别多,但从内容看,大多为切中肯綮之评,且多有见识,富于理论色彩。或借题发挥,直抒己见,如《谢洯源诗序》眉批: 诗有汉魏六朝,又有唐之盛、中、晚,宋之南、北,如味之为五,音之为七,盖运会风气使然,不可以偏废,使必出一家,是犹强好甘者而食辛、强酸者而食苦,其可乎?使必出于一家,是犹用官而废徵、用徵而废商,又可乎?好汉魏即学汉魏也可,好唐宋即学盛唐也可,其他皆类是。盖嗜好所在,即情性所在。言诗者绌人之性情以就我之性情,天下无真性情,又安有真诗乎?明中叶以后,举世耳食何、李,不惜舍性情以从之,是以无当于风雅之正,彼颛之焉。墨守宋元,以绌彼伸此,其于方隅之见一而已矣。 此处以谢洯源的诗歌特征为出发点,然后以“味之为五”、“音之为七”来分析诗之有汉魏六朝、盛唐、中唐、晚唐、北宋、南宋之区别,强调学诗不可偏废,要博采广收,兼容并蓄,阐发性情,“嗜好所在,即性情所在”,“天下无性情”,即无真诗,并对明中叶文学复古派“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举世耳食”,“不惜舍性情以从之”的现象予以批评,认为其“无当于风雅之正”,极具理论色彩。又如《书韩文公答刘秀才论史官书后》尾批:“尽信书不如无书。记注、实录之编,其忌讳迁就,盖不少矣。古来国史已未可凭,何况野史乎?‘据事直书’一语,正非易易,安得促膝对谈,缕陈其故乎?”亦是从“记注、实录之编”,“忌讳迁就”之语不少的现实出发,强调“国史已未可凭”,野史更不足信,从而得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点,用此来反证《韩文公答刘秀才论史官书》能“据事直书”,颇为不易,推论严密,观点鲜明,可自成一说。或阐述文章作法,品评优劣得失。如《宋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记》眉批:“宋史有传者,其传略叙,无传者,须详书其人。”以《宋史》传记为参照,肯定《宋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记》一文在文章作法方面的详略处理策略;《书柳柳州〈论语辩〉下篇后》一文“盖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夫子阐之以垂教万世,一气相承,一心相印也”处眉批“忽作一束,作文章法,简劲得自南丰”,指出该文行文简洁,文章作法得自北宋散文家曾巩;《子妇诸氏行述》中“母有淑德而后家有良子,苟礼仪不修,起居不慎,安冀有贤子姓哉”一段眉批“神韵似熙甫”,指出王鸣韶为儿媳所撰行述一文与明代归有光的散文作品神似,高度肯定了作品情真意切的成就。又如赞扬《答诸雪堂书》一文“议论透辟”、“淡古”、“抑扬顿宕,笔如游龙”;批评《元至正十年山东乡试题名记》一文“乡试殿试一段不必”,指出《程容与先生传》一篇重出“当删此而存彼”。诸如此类,均属批评性评语。 2.补充与正文内容相关的资料或阐释正文内容的批语。与正文内容相关的资料性批语乃批点者根据自己耳闻目见的故事所作的补充,这类批语主要见于尾批之中。如《昭庆寺修建记》文末有“乾隆壬寅腊月二十一日”王昶的尾批补记: 学公精持秽迹《金刚经》,往往有神验示灭。时大暑,阅三日,入龛,肤革润泽如生,蝇蚋不敢集其体。先是乾隆庚申秋,城中大疫,去寺数十步,有鬻菽乳者,疾甚。所居临街肆,以秋热夜启窗不闭,窗下有席,席上置油灯。夜半,灯垂烬,群鬼皆集,与病者嬲之不置,方窘苦无如何,忽有金色臂从窗中入剔其灯,鬼见之骇散,其人因以获安。久之渐愈,能行入寺中,见学公方坐廊下,谓之曰:“若大病,今全愈否?”其人曰:“和尚何以知之?”公曰:“汝不记某夜烦苦时,我为若剔灯烬耶?”其人大惊,曰:“和尚真活菩萨也。”搏顇致谢而去。以上二事,通侯先生尝为余道之,迄今盖三十馀年矣。附书于此,以补记所未及云。 《昭庆寺修建记》主要记述了昭庆寺的修建情况,但于昭庆寺有关的传闻未能有详细记载,王昶根据自己三十馀年前的闻见予以“补记”,大大丰富了正文的内容,亦可作志怪传奇读之。又如《华萼堂记》一文,乃汪照请王鸣韶为其华萼堂所撰之文,汪照在文末亦以尾批形式补充相关背景资料: 余既辟华萼之堂,欲作箴以自警,而并以训我子孙,牵于冗俗,未暇为也。先生能善道人意中事,文笔尔雅,亦可法可传,余华萼之堂将藉是文以不朽矣。 汪照的批语对于理解文章的创作背景具有重要价值,也高度赞扬了王鸣韶之文的艺术成就。同样,《与诸雪堂》一文关于“治心”问题的讨论,联系《朱子语类》关于天理、人欲之观念进行,在尾批中引用其兄王鸣盛(别字西庄)之语来补充文章内容:“西庄曰:动静交养,知行并进,诚明互执,敬义夹持,正与朱子之意合。”亦属此类批语。 当然,也有些批语主要针对正文内容进行阐释,如《萧何论》一文关于“何不于釁端未启之先,教信以樽节退让,可释疑忌”一语,眉批称: 高祖猜忌疑信久矣,吕后窥见其意,故锻炼此狱以成之。高祖未至而先诛,要知非高祖不欲居诛戮功臣之名,而假手于吕后耶?鄼侯颂系之馀,亦惴惴恐不得免,开陈其功,械系以竢,似非知当日情事者也。 《萧何论》中认为萧何未能在争端兴起之前,让韩信约束退让以释疑忌,而批语则联系“高祖猜忌疑信久矣”的历史事实,针对正文观点进行反驳,认为其“似非知当日情事者”,批驳有力。同样,《陈东论》一文认为“古来大奸慝能善其终者,李林甫、秦桧而外,殆无几人也”,但其眉批却引吕惠卿之事,称“吕惠卿再入拜军,至八十馀卒”,反驳了正文观点。针对《陈东论》中“陈恒弑君,有请讨之告”一句,眉批亦解释称“陈恒弑君时,孔子在鲁,故有请讨之举”云云,都属于阐释性批语。 3.品评文章优劣、鉴赏艺术高下的批语。有些批评者虽未直接写出评语,却在每篇文章后分别标注“上”、“次上”、“次”带有明显品评意蕴的字样,以表达自己对文章优劣的看法。《鹤谿文稿》中这种方式的品评出自清代学者朱春生之手。朱春生在丙午春三月三日的题跋中有所说明: 每篇尾注“上”字、“次上”字,皆必存之作,但注一“次”字者,在可存不可存之间,浅陋之见,知不足当万一也,付之一笑而已。 朱春生将王鸣韶的文章分为“上”、“次上”、“次”、“次次”四类。笔者统计,《鹤谿文稿》中被评为“上”的文章19篇,“次上”的文章60篇,“次”的文章62篇,“次次”的文章1篇,还有52篇文章则未予品评。被评为“上”等的文章包括《玉山名胜集序》、《送秦复山赴任绍兴太守序》、《元至正十年山东乡试题名记》、《重建陆清献公祠堂记》、《药州图记》、《太仓州钟楼铜钟记》、《与诸雪堂》、《与钱竹汀简》、《答曹檀济师》、《萧何论》、《侍命一篇赠钱可庐》、《范文正公学术事业考》、《咸林郑地考》、《郡县考》、《书龟巢集后》、《张南华先生传》、《程容与先生传》、《候补员外郎福建崇安县知县幔亭陆公墓志铭》、《滕县知县玉亭程公墓表》等文章,而被其认定为“次次”的文章是《记石先生语》一文。朱春生之品评,在评定等级后,都钤有“春生”朱文方印,以标示评定者。但就其品评的整体情况看,朱春生对王鸣韶的文章多以“次上”、“次”视之,可见其评价并不算高。这种评价是否准确?诚如他本人所言,“浅陋之见,知不足当万一也”,这或许确非谦辞,其中除少数文章品评得当外,大部分文章还是有失偏颇的。 4.以校勘为主的批语。《鹤谿文稿》的批校中,批抹、删改、校补之处甚多。相对于那些以理论批评见长的批语,这些批语侧重于“校”,包括对稿本文字的增、删、改、补等多种形式,基本保持了稿本的原始状态。或增补文字,使句意更为明确。如《篆书孝经序》中“唐之李谌、李阳冰、徐锴,宋之徐铉、郑文宝”一句,在“徐锴”二字前添“南唐”二字,补充确切的时代,以与前后文字对应;《息关先生释疑录序》中“亦先用功于佛,久之而无所得”一句,在“而”字后增补“谓其”二字,以补充遗漏,虽此句增补前亦能读通,但增补后句意更明晰。而在有些文章中,文本存在明显的文字缺漏,如不加增补,则意思不连贯,只有通过批校文字的增补才能得以有效理解。如《赠族孙漪文序》中“因推本于先世之德以赠之使而皆念其先也研存之家风其不坠矣”,此句语意不通,显有阙漏。批校则增补为:“因推本于先世之德,书以赠之,使予宗人而皆念其先也,研存公之家风其不坠矣”,得此增补,句意明确许多。或删除繁冗,精炼文句。如《陈东论》中的一段:“今日读之,犹想见其节概,然而君子之于天下也,当为有用之用,勿为可名之名。吾以有用之身,必当权于实用,无务乎空言,而屡试于危地。”此段文字繁复冗长,语意有重复之处。批校将“为有用之用,勿为可名之名,吾”以及“必当”数字删去,变得更为精炼:“今日读之,犹想见其节概,然而君子之于天下也,当以有用之身权于实用,无务乎空言,而屡试于危地。”经此删改,该段文字行文更加简练,语气更为顺畅,而语意也未有损伤。或校改错讹,疏通文句。有些批校是校改明显错讹的,如《郁无文加编录后序》中“雍年三年”校改为“雍正三年”。有些则是根据表达语气的需要进行校改,如《郁无文加编录后序》中“非亲民之父母,谁责哉”一句将“哉”校改为“乎”,《玉山名胜集序》中“可为深慨哉”一句将“哉”校改为“矣”,《长生指要序》中“人生寿不过百年,何为以有限之精神,易尽之岁月施于功名富贵”一句将“何为”校改为“乃”等,均属此类。而有些批校则通过调整文字前后顺序,使语句更为顺畅。如《唐抡三青藜馀照集序》中“宜其卷帙之多而益博,而益精善矣”一句,批校中将“精”字提到第二个“而”字之前,变成“宜其卷帙之多而益博,精而益善矣”,改易一字,而语句顺畅许多。 《鹤谿文稿》中附带的这些批校文字,虽形式零散,随文而批,但通过考察其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些批校文字对于《鹤谿文稿》的文本定型和文集编纂具有重要的校勘学价值;其中藏书家关于稿本传承的题识序跋对于了解《鹤谿文稿》的传承演进更是具有明显的史料价值(详下文);至于那些富有理论色彩或补充阐释性的批语,不但有助正文内容的理解,还具有重要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二、《鹤谿文稿》的发现、编辑和流传 为《鹤谿文稿》撰写题识序跋的有著名学者钱大昕、朱春生、汪照,藏书家叶德辉、叶启勋等。其中钱大昕、朱春生、汪照、叶启勋各1则,叶德辉2则,这些题识序跋充分反映了稿本的发现、编辑和流传过程,是了解稿本形成和传播的重要史料。 《鹤谿文稿》的发现,叶德辉在壬戌(1922年)展重九日的题跋中进行了明确介绍: 右王鸣韶《鹤谿文稿》,计文百九十二篇。从子启勋两次从书估手中购出,始成全璧,因命依其兄西庄先生文稿,按目编次,分二十四类,余为手书其目,以俟异日梓行云。 从叶德辉所撰题跋可知,王鸣韶《鹤谿文稿》乃是叶启勋分两次从书估处购得,后在壬戌闰端午日所题书末题跋中再次肯定“从子启勋两次获此稿本”,由此可见,《鹤谿文稿》的发现与叶启勋有着密切的关系。叶启勋(1900-1972),字定侯,号更生、南阳毂人,湖南长沙人。为叶德辉三弟叶德炯之子。通晓目录学,以藏书知名,家有藏书楼名“拾经楼”,藏书达10多万卷,也是小有名气的藏书家。对于《鹤谿文稿》的发现,叶启勋本人为该书所撰题跋有更加具体的描述: 此稿余于丙辰夏仅得其半,有钱、汪二君跋,又有朱春生一跋,钱跋后有“钱侗过眼”四字朱文方印……旧藏县人袁漱六太守芳瑛家,固不知其全与否。已未冬,闻估人又得袁氏书,急往物色之,又得二册。细阅稿中《谢洯源诗序》文后有“王鸣韶印”四字白文方印、“鹤谿”二字朱文方印、“逸野堂主人”五字白文方印,《蝇蚊喻》后钤“钱侗过眼”四字朱文方印。书估知余必欲得此以成完璧,始颇居奇,迁延月馀,以残册无人过问,卒为余有。 由此可知,叶启勋分别于丙辰(1916)、己未(1919)两次从书估中购得《鹤谿文稿》,始成全璧。而稿本旧藏于袁芳瑛家。袁芳瑛(1814-1859),谱名袁世矿,字挹群,号伯刍,一号漱六。室名卧雪楼,清代藏书家,与朱学勤、丁日昌并称为咸丰时期的三大藏书家。 《鹤谿文稿》的原始编辑过程,因文献资料阙如,其过程已难以知晓。目前所见之稿本实际上是经过叶启勋整理后的本子。对于这一问题,上引叶德辉的题跋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可知叶启勋在《鹤谿文稿》的编纂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稿本中的大部分文章出自手写抄录,但也有几篇文章如《流爱集序》、《金如山墓志铭》、《其绵金翁墓志铭》等来自刻本,并非手写而成。为何在稿本中会存在刻印的文章?是否该稿本已经刻印过?为了弄清这一问题,笔者仔细查看了刻印的几篇文章的版刻中缝,其中明确标记出文章出处来源:《金如山墓志铭》、《其绵金翁墓志铭》两篇文章乃出自《金氏族谱》,题王鸣韶撰。《流爱集序》来源于《流爱集》,标明“王序”,可知此文乃为《流爱集》所撰序言(此文末题“王鸣盛”撰,下文对此有分析考辨)。据此推断,《鹤谿文稿》某些刻印的文章为王鸣韶所撰并已经为别的刻本收录,为了省却抄写之烦,编者直接在编辑过程中将其原封不动地编入稿本,因此,也造成了稿本中夹杂刻印文章的现象。 另外,稿本中有些文章署名并非王鸣韶,而别有他人,其中尤以其胞兄王鸣盛居多,如《流爱集序》文末题“乾隆四十三年岁次戊戌九月既望赐进士及第光禄寺卿治第王鸣盛拜撰”,《夏氏谱序》文末署“王鸣盛书”,《后归公集序》文末题“王鸣盛撰”,《徐世嫂裘老夫人六十寿序》文末署“王鸣盛”,《益亭何君传》文末则题“钱大昕撰”等。《鹤谿文稿》既然为王鸣韶的文集,为何其中还会掺杂他人文章?这一现象又是如何出现的呢?实际的情况是,这些文章本身就出自王鸣韶之手,是王鸣韶应王鸣盛、钱大昕等人之请撰写的应景之作。王鸣盛、钱大昕等人影响甚巨,盛名之下,请他们作序、作传、撰写贺词、墓志铭者当不在少数,于是,在他们文债纷繁不堪重负时,偶尔交由王鸣韶捉刀亦属于正常。而且从行文的风格与内容比较,这些文章与其他文章亦大致相同。在《答邵西樵》一文中,鹤谿子即明确提及“四、五月内,西庄先生属撰应酬文字”。朱春生在批点这些文章时,亦毫不隐讳称这些文章为“代”笔,这亦可作为这些文章著作权归属的证据。 从稿本传承看,《鹤谿文稿》的传承渊源有自,脉络清晰。其题跋、钤印已大略勾勒出其传播演进轨迹。庚戌正月(1790),即王鸣韶去世三个月后,稿本即归藏钱大昕(1728-1804)处。王鸣韶为钱大昕妻弟,钱并为王鸣韶的著作《祖德述闻》撰写过序言;王鸣韶去世后,钱大昕为其撰写了墓志铭,成为了解王鸣韶生平的重要史料。王鸣韶去世三月后,钱大昕为该稿题跋称: 鹤谿之文,其妙处有三,曰不俗,曰不腐,曰有物,较之吾乡四先生,殆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当世无谢象三其人者,遂使撰述不得流播海内,然丰城剑气,自有不可掩抑者,显晦有时,必不终没己也。庚戌正月钱大昕题,时鹤谿下世已三阅月,抚卷泫然。 题跋中除了肯定王鸣韶文章“不俗”、“不腐”、“有物”三大妙处外,更明确地提示了该稿本在王鸣韶之后,即归藏钱大昕处。 钱大昕之后,归朱春生、汪照。朱春生丙午春所撰题跋中称: (《鹤谿文稿》)久置案头,恐为人取去,急读一过,仍归箧衍……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使镌板时,先生当细细手定之可耳。丙午春三月三日愚弟朱春生拜读。 从“久置案头”、“仍归箧衍”之语,可以断定朱春生曾珍藏此文稿。汪照同样在题跋中称“新岁酬应纷如,读一篇未竟,辄有冗事扰之”,亦可知文稿曾经汪照之手。至于到袁芳瑛、叶德辉、叶启勋等藏书家之手,已辗转多手矣,上文叶德辉、叶启勋题跋可为证据。 此外,根据稿本钤印,亦可证其传承过程。《鹤谿文稿》在不同地方钤有“王印鸣韶”白文方印、“鹤谿”朱文方印、“逸野堂主人”白文方印、“钱侗过眼”朱文方印、“汪照观”朱文方印、“□□□勿污损”朱文长方印、“春生”朱文方印、“郋园”朱文方印、“启勋珍赏”白文方印、“叶启发藏”白文方印、“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珍藏”朱文方印、“湖南省立图书馆”朱文方印等。“鹤谿”、“逸野堂主人”为文稿撰著者王鸣韶字号。“钱侗过眼”为钱侗(1778-1815)藏书印,钱侗系钱大昕侄子,清代文献学家、藏书家、文字音韵学家。“郋园”为叶德辉藏书印。由此,可以略微梳理《鹤谿文稿》之流传过程大体如下(实线为有明确记载之传承;虚线为经其手,是否直接传承则不明。): 王鸣韶--→钱大昕--→钱侗……→朱春生……→汪照……→袁芳瑛--→叶德辉(叶启勋)--→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南省图书馆 三、《鹤谿文稿》的文学与学术价值 《鹤骆文稿》迄今尚未刊印面世,未能引起学界的关注重视,但是其价值却不容忽视。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鹤谿子具有极其特殊的身份。他不仅是当时大学问家王鸣盛的胞弟,在学问研究方面耳濡目染,深得其壶奥。而且因为其兄的缘故,与当时学术圈中的鸿儒巨擘们如卢文弨、汪照、王昶、戴震、钱大昕等高尚博雅之士多有往还,文稿中收录的一些与他们相关的文章,对于研究乾嘉时期的学术具有重要价值。其二,正如钱大昕《鹤谿子墓志铭》所言,鹤谿子勤勉向学、濡染家学,具有很高文学艺术天赋,稿中许多文章具有较高的文学和学术价值,在清中叶卓然堪称一家,值得后学研读学习。 对于《鹤谿文稿》文学价值,我们可以引述题跋中两位学人的评价,以见其价值之所在。一是钱大昕,我们在前面曾提及,他在题跋中称:“鹤谿之文,其妙处有三,曰不俗,曰不腐,曰有物,较之吾乡四先生,殆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另一位是朱春生,他在题跋中说: 先生之文,长于考据,熟于援引,胎息经史,而出于欧阳氏门户。本朝三家中,神似玉遮山人。其一种纯古澹泊之味,实寝食于震川先生得来,若以吾乡四先生论,边幅较阔大矣。 这两位学人不仅对《鹤谿文稿》的文学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还对文章的特点及其根柢加以概括和追溯。如钱大昕称扬其“不俗”、“不腐”、“有物”,朱春生提及其文“长于考据,熟于援引”皆是对其特点的概括,而朱春生所谓“出于欧阳氏门户”、“实寝食于震川先生得来”则是对文章根柢的溯源。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钱大昕还是朱春生都曾提及“吾乡四先生”。四先生何许人,为何两位学人都不约而同地将鹤谿子与他们加以对比呢?所谓“吾乡四先生”指的是明代嘉定四位著名的文化名流唐时升(1551-1636)、程嘉燧(1565-1643)、娄坚(1567-1631)、李流芳(1575-1629)。这四人均是享誉嘉定甚至在明代亦有一定影响的文人才士。其中唐时升专意古学,工诗文,善画墨梅;程嘉燧侨居嘉定,通晓音律,工诗善画;娄坚善诗古文辞,书法妙绝天下;李流芳擅长诗画,风格自然清新。四人才艺过人,不同流俗,影响之巨,当地一时无人能够与之比肩。而鹤谿子能够在数十年后,得到诸如钱大昕等如此高的评价,其成就与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钱大昕论鹤谿子之文,曰其“不俗”,乃称扬其文风格不落俗套,卓然独立;所谓“不腐”,乃称扬其文识见高远,不拾人牙慧;曰其“有物”,乃称扬其言之有物,不无病呻吟。以此衡量鹤谿子之文,的非虚言。我们可从三方面加以分析,以见其大概。 一是文备众体,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卓然独立。如前所述,《鹤谿文稿》有文192篇,体裁涉及序、记、书、论、议、说、考、跋、后书、传、问、赋、疏、论、书事、碑、墓志铭、墓表、塔铭、行述、事略、像赞、哀辞、祭文等24类,其中墓志铭、墓表、哀辞、祭文等类文章追思先人,哀抑沉痛,庄重肃穆;序、纪、书、考、跋、后书等类文章怀人记事、考辨源流,醇正古淡;论、议、说等类文章谈天说地,随意挥麈,则多有风趣幽默之作。《谕鼠》一文采用寓言及赋体问答形式讽喻世事,自我解嘲,嬉笑怒骂,随意点染,形象生动,幽默风趣。与此相类,《憎蝇怒蚊喻》采用寓言及赋体问答形式论事议理。该文先状苍蝇之种种可厌,以触及作者心中烦恼不平,并由此引发人生之感慨:“吾之困抑,既无通途,动而得毁,顾影区区。”在其愁绪满怀、“方欲詈之”时,一客出现,称其“糊涂”,居然为此区区之事而烦恼。接着他以蚊之作恶为例,委屈譬喻,说明蚊子之为恶甚于苍蝇,并由此阐明“物理相生,枉直互更”,世间“害人者众,岂在翃翃,何物不有,宇宙之精,恶彼微类”的道理,并劝喻作者“寒暑代嬗,痴冻薨薨,盍不少忍,毋以过清”。这篇文章以寓言赋体文的体式阐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世间之大,害人扰民者众,对付他们的法宝在于自身的定力,当害人扰民者出现时,如果一味地自怨自艾、烦恼忧愁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充分认识到“物理相生,枉直互更”的辩证关系,心静如水,假以时日,等到一定的时候,终究会云开雾散,那些害人者自然会不攻自退。这一思想虽存在着消极退避的一面,但是亦有其深刻的内蕴。 二是鹤谿子之文无论评论事情,抑或品评人物,均高屋建瓴,不同凡响。如其在《范文正公学术事业考》一文中高度称赞范仲淹之学术功业,认为其无论处边塞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均能诚心敬上,鞠躬尽瘁,屡建奇功。其学术则能跳出训诂词章的狭小天地,经营天下经世致用之学,慨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乃大儒之学。在这一方面,鹤谿子认为可与三国时的诸葛亮相提并论,但又有所不同,“诸葛武侯,崎岖于危弱之邦,而公效用于太平之日,其功业各有所表见。然武侯之功不成者,天为之;公之不得竞用者,人为之也”。所论境界阔大,立意高远。 三是鹤谿之文虽篇幅不长,三五百字短文居多,但内容丰富,言之有物,绝不作无病呻吟之态。在行文中,无论是谈文论艺,还是品评人物,皆能紧扣实际,有感而发。如《张复画山水跋》,文章首先介绍张复籍贯、时代、师从,并着重点明其山水画“清迥有别致”。然而,画作虽在,却“无人举其姓氏矣”。行文至此,鹤谿子轻轻宕开一笔,引发对于功名富贵的思考:“由此观之,功名富贵,第如画中之丘壑,只可充耳目之玩,而非可认以为真者乎?比于声销响寂,万事总归无有,则转不如一幅画,犹得流传于艺苑,供人之评赏也。”这一段议论,紧扣乾嘉时期广大儒生在八股取士制度的诱惑下汲汲于功名富贵的现实,有感而发,切中时弊,发人深省。在行文上则由画及人,巧妙勾连,水波无痕。鹤谿子之笔力于此可见一斑。 就学术价值而言,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鹤谿文稿》记载了鹤谿子与许多乾嘉学者交流切磋乃至交游的线索,由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寻绎出一些学者的学术源流、治学过程与学术成就,可以弥补学术史文献的不足,对于拓展乾嘉时期的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戴震是乾嘉时期重要的经学家,《江慎修先生墓志铭》一文中,鹤谿子不仅记载了自己与戴震间的深厚情缘,而且对戴震的老师,清代著名的经学家、音韵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江永(字慎修)(1681-1762)的学术生涯及成就进行了全面公允的评价。如文章所论,江永学识渊博,精于“三礼”,朝廷开馆命儒臣纂修《三礼义疏》及《通礼》,桐城方苞以“士冠礼”、“士婚礼”数事向其请教,江“即条析其疑义”,“望溪大折服”。而后,江所撰之“《礼经纲目》实补朱子《仪礼经传通辞》之阙”。江永不仅学问深湛,而且赋性恬淡,“乾隆十六年,天子命大臣举经学之士,授以国子监司业,时议者咸推先生,先生亟止之,谓颓然一老,无复可用,因不果荐”。江永是戴震、程瑶田、金榜的老师,其渊博的学问及低调的为人品质对于学生的影响当不言而喻。对于戴震的学术,鹤谿子在《鹤谿文稿》亦有研讨考辨。《校定〈水经注〉跋》虽为跋文,但对《水经注》的版本源流进行了系统完整的梳理,对戴震的整理进行了深入的考辨,并比较了戴氏当时所存的两种《水经注》本子:“戴氏之本有二,一为武英殿所刻之聚珍板;一为曲阜孔氏所刻,在《戴氏遗书》之内。聚珍板依向所流传本细为校正,而原缺之十四水则仍其旧,为三十五卷。《戴氏遗书》本则无卷次,各以其水为次。后附郦道元先生自叙一篇。盖谓河自塞外来,而入中国;其次叙出入于河之水;次则自济水以至入济之水;次则自淮以至入于淮之水;次则大江以至入江之水,而渐至南,而二十水。群川就绪,厥维懋哉!且聚珍板所刻,有明所以订正之故,据某本改易甚详且悉。”《水经》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群川源流走向的著作,为汉代桑钦所撰,郦道元为之作注。宋元以来,“经注混淆,文字错乱,几不可读”,明代一些版本如嘉靖甲寅吴郡黄省曾刻本,其间“伪误与诸家等”,经戴震之手厘定,“庶可见其原委”。鹤谿子从学术史的角度肯定戴震厘定之功且辨析之,对研究戴震学术无疑是有助益的。 鹤貉子为钱大昕妻弟,交往甚密。《鹤谿文稿》中收录了《与钱竹汀学士书》、《与钱竹汀简》两篇书信,其中不仅记载了二者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而且还记载了他们在学术方面的切磋交流。在《与钱竹汀简》中,他开门见山曰“二年来,得亲教诲,兼师友之益,别后倏逾三月”,随后即描述别后与其相见之梦境,由此可见其悬念之切,情谊之深。在表达过思念之情后,又一一罗列了近期所见书籍特别是一些珍稀古籍,分析优劣,提出疑义,并将一些有价值的书籍推荐给钱大昕。 二是鹤谿子受其家学及胞兄的影响,勤勉于学,在学术研究方面也颇有造诣,特别是在史学、文学、艺术领域多有不俗的见解,值得关注。下面着重分析一下鹤谿子文学方面的主张与见解。乾嘉时期,文人学者惕于文字之祸,多致力于文字、声韵、训诂学术研究。而于文学,或过于强调文字声律等形式方面的内容,或蹈袭古人,追踪唐宋,袭其貌而失其神者大有人在。对于这两类现象,鹤谿子均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提出一系列关于诗歌创作的新见解。在《秋树读书楼诗序》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当时文坛存在的弊端,所谓“登临感慨,吊古悲今,揣摩格调,此今日诗家所谓不刊之法宪也。风云月露、即景言情、刻画尽致、赋物精工者,不讥其纤巧则嫌其浅近矣”,然后直接表露自己的立场观点:“吾则谓诗以写情,亦以言志,随其意之所寓而发之于诗。如先定其体例,有方格之状,曰初盛唐、为南北宋,秦皇汉武,叹陈迹之易逝,代古人以兴悲,其或香奁狎亵,翦巧绮褴,是皆假面吊丧,而我之真面目不存在焉。”在批评的基础上,他提出诗歌创作务必要“真”,并且对“真”的内在涵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然则诗之真安在?曰有我之真,性灵真境界也。随所感触,自然成韵。一花一木,可以移情;一水一山,可以托兴”。对于借鉴古人,他认为诗歌创作虽本于前辈,但一定要有所创新,要建立自己的“风骨”,他说:“夫言者心声,而诗以言志,尤声之入微者也。或揣摩格调,而性真不存,或翦巧绮艳,而骨气不立,此末流之弊,非所以为诗也。”在《寓圃诗草序》中,鹤谿子对作者独特的诗风大加赞赏,称:“纵横排戛,顿挫沉郁,出入杜韩苏陆,不屑屑于一家,其于摩拟矩仿之习,弗为也,何其艺之精欤!”在宗唐宗宋的问题上,他并未刻意地偏向某一方,而是认为唐宋诗歌各有所长,不能简单地确定其孰优孰劣,他还以宋诗如何借鉴汉魏唐诗而形成一朝独特诗风为例,来说明借鉴而不是因袭前人的重要性。他在《宋诗略序》中说:“宋承唐后,其诗始沿五季之馀习。至太平兴国以后,风格日超,气势日廓,迨苏黄辈出而极盛焉。乃其所以胜者,师法李杜而不袭李杜之面貌,宗仰汉魏而不取汉魏之形憮,此其卓然成一朝之诗而不悖于正风者也。”鹤谿子的诗论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对此,我们将撰专文论述。但从以上简单论析可见,在当时的社会,他的思想与见解的确不同凡响,甚至比我们目前文学史上所提及的许多文学思想家要高出许多,对鹤谿子文学思想的总结研究将会大大丰富和促进清代乾嘉时期的诗歌理论的研究。 概言之,王鸣韶《鹤谿文稿》稿本作为稀见的清人别集之一,是全面展现清代藏书家、书画家王鸣韶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的重要史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自清代以来,著名学者和藏书家对稿本的批校题识,不仅补充、完善了稿本内容,其富于理论性的批评文字,更是文学批评史上难得的批评资料。王鸣韶《鹤谿文稿》等稀见清人别集由不为学界熟知到被发掘整理,充分反映了清人别集整理与研究的复杂性、繁重性,而这还有待于我们继续不断努力。 ①如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图书馆编《清人别集丛刊》、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江晓敏主编《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等。 ②“后四王”指的是继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和“四小王”(王昱、王愫、王玖、王宸)之后的四位画家,即王廷元、王廷周、王鸣韶和王三锡。 ③钱大昕撰、吕友仁标校:《潜研堂文集》卷四八《墓志铭七·鹤谿子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