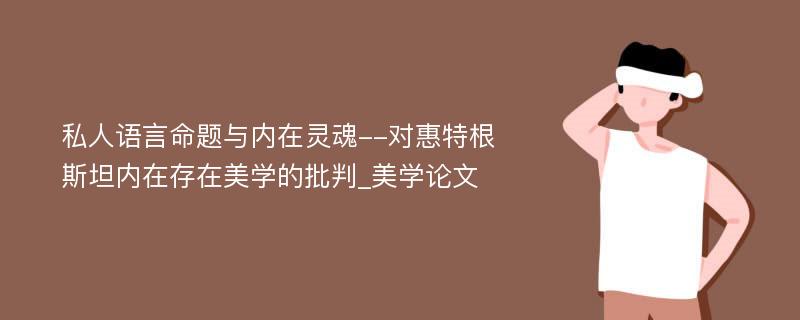
私有语言命题与内在心灵——维特根斯坦对内在论美学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根斯坦论文,美学论文,命题论文,心灵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内在心灵世界的形而上假设
一般的文学观念总认为文学是内在心灵的倾吐,我们在心灵中体验到一种特别的审美情感,这种情感或激昂,或悲痛,或温婉,或沉郁。它潜藏、转折、压抑、冲撞,寻找喷发的突破口,最终,这个契机找到了,伴随着语词,它喷涌而出,百转千折,形成诸般文学的样态。这就是文学产生的过程,其中蕴含着文学的本性。
在这一形而上学观念的阐发中,文学成为以语言为载体的内在情感的表述。内在情感在心灵中被塑造出来,它完满充实,具有无法替代的完整性,一旦通过语言被表达出来,这一完整性就会丧失,变得残缺不全。因此,语言既是内在情感抒发的桥梁,又是一种阻碍,语言与内在情感之间就形成了既依存又排斥的矛盾关系,但内在情感的完整性却是无可置疑的,它在内心中成形,毋须语言,寂然存在。
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讲述了一段颇为神奇的遭遇,可以从文学的角度为上述观点提供佐证。一个奥地利人,忠诚的皇室保卫者,被关进纳粹的监狱。纳粹怀疑他掌握着奥地利皇室巨大财富的秘密,想通过特殊的审讯手段逼迫他吐露实情。这种方式是骇人听闻的:他被关在单独的牢房里,没有任何人跟他说话,时间一长,这种无言的压迫比任何酷刑都要有效,他迫切地希望与别人交流,说任何话都行。在他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由于偶然的机缘,他获得了一本棋谱,通过与心灵中的对手下象棋,他获得了清晰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甚至赢得了纳粹军官的尊敬。但是好景不长,象棋书中记载的棋局是有限的,他必须自己发明新的棋局来保持理智的清明,因而,他铤而走险,把自己当做对手,将自己的头脑分成两个独立的部分,这种自我的格斗最终导致了理智的崩溃,他在癫狂中依然高喊着棋谱进行自我对弈。
这部小说似乎在主张我们能够在内心中进行自我对话,一个“我”可以对另一个“我”说话,甚至可以把它当做对手进行对抗。这种自我对话真的可能存在吗①?从小说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一旦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自我对话者在现实的对话活动中就会成为最顶级的高手。那个奥地利人通过一年多的自我对话,从一个平庸的业余棋手急剧蜕变,竟然能够击败世界象棋冠军,真是一个奇迹。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它与现实情况可能完全不同。
本文并不想从现实的角度反驳自我对话的存在,而是关心故事的潜在预设:我们先在内心中想清楚,然后用语言表述出来,语言是运送内心思想的载体。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文学观念,也是一个传统的经典假设。如今,这一观念已经渗透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无所不在。我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认为先有内在自我的思考,然后才会有言辞的表述。
这一观念不仅表现在小说创作中,还表现在可名之为“内在论美学”的观念中。所谓“内在论美学”,在中国语境中可称之为“艺术心理学”,即强调内在审美心灵是艺术的本源。之所以不使用“艺术心理学”这一名称,是因为它更强调艺术与心理学的亲缘关系,而本文只是着力批判“艺术心理学”的哲学美学基础,即内在心灵(或内在情感)本质观的错谬。“内在论美学”这一名称显得更集中,更有的放矢。
在弗洛伊德的艺术观念中,可以看到最明确的内在论美学质素,他的观念也是维特根斯坦所着力批判的。弗洛伊德说:
我注意到,在许多以“心理小说”闻名的作品中,只有一个人物——仍然是主角——是从内部来描写的。作者仿佛是坐在主人公的大脑里,而对其余人物都是从外部来观察的。总的说来,心理小说的特殊性质无疑由现代作家的一种倾向所造成:作家用自我观察的方法将他的“自我”分裂成许多“部分的自我”,结果就使他自己精神生活中冲突的思想在几个主角身上得到体现。②
这一观念从实际生活中也可以发现很多佐证。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困难的时候跟自己说,一定要坚持住,不能气馁,为了让自己听见,甚至念念有词,乃至大喊。电影里英雄人物拯救人类的最关键时刻,也总是不断地在嘟囔些让观众紧张的话。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仿佛听到自己谴责自己,也仿佛听到别人在自己的背后指指点点。见某个关键人物之前,为了不要说错话,先在心里默默练习要说的话。
这些都是我们的经验,凭借这些经验,我们认为一个人总是在内心中想清楚了,然后才告诉别人。如果我们没有想清楚,怎么能够把内心的想法告诉别人呢?这个疑问显得如此自然,在某种意义(即日常使用的意义)上,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当某个人表达含糊不清的时候,我们总是批评他没有想清楚,只有想清楚才能说清楚。这是对的。那么“想清楚”指的是什么呢?是自言自语,不出声音吗?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是这样的。
但我们是怎样“想”,凭什么来“想清楚”的呢?人们倾向于认为,我们在心里凭借语言把问题和想法理清楚,然后再将它说出来,告诉别人。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将内心的想法完整地说出来是很困难的,唯患辞之不达,所以,我们愿意说心灵是丰富的,语言与心灵相比总是苍白无力的,语言无法表达心灵。中国古代早就有言象意的争论,言不尽象、象不尽意的观点更有支配力。但这一观点必须受到语言学的批判和检验。
二、内在心灵与私有语言命题
“人的精神世界作为主体,是一个独立的,无比丰富的神秘世界,它是另一个自然,另一个宇宙。我们可称之为内自然,内宇宙,或者称为第二自然,第二宇宙。因此,可以说,历史就是两个宇宙互相结合、互相作用、互相补充的交叉运动过程。精神主体的内宇宙运动,与外宇宙一样,也有自己的导向,自己的形式,自己的矢量(不仅是标量),自己的历史。”③上世纪80年代的刘再复如是说。这样的观点,代表了80年代文艺理论界的新探索,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反驳机械的唯物质主义文艺观,高扬主体的地位,提高主体的主宰力,强调内在的精神世界的独特性和自由性。但它同样带来了难以解决的问题——语言的桥梁作用是自明的,内在世界向外在世界的转换成为意识的任务,而意识如何完成这一转换也成为巨大的难题。这一难题在中国80、90年代还未动摇其理论根基,因为语言转向还没有获得普遍共识。9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的语言转向观念在中国渐渐获得支持者之后,语言再也不是不言自明、默会于心的了。语言作为沟通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桥梁地位渐渐变得可疑起来——这里不是质疑其可能性,而是质疑其机制。
如果我们内心真的有一个独特的世界的话,如何将这一世界与别人分享?这个问题乍一听有些奇怪,因为在一般想法里,我们天然就知道自己的内在世界,为什么还要谈论其确定性的问题呢?这个问题从一个颠倒过来的角度来提问也许会更合理些——我们怎样确定内在世界就是如此的,我们说出这个内在的世界吗?没有外在世界的语言,我们怎样言说这个内在的世界?
这是一个难题,但也有应对之举,早就有人提出内在世界同样有它的语言,这种语言是独特的,只为持有这一语言的个体所理解,别人无法理解,要想让别人理解,必须将其翻译为公共语言。奥古斯丁式的语言略作推衍就可以得出如此结论④。现代语言学家平克(Pinker)也持这种观点。他提出,存在一种内在语言(mentalese)⑤,我们先用“mentalese”思考,然后再把它表述出来,表述就是一种翻译⑥。
这样一来,我们就得思考相应的问题:这种内在语言能理解吗?从内在语言到外在的公共语言的转换是一种翻译吗?如果它是一种翻译的话,有什么标准来衡量它的准确性?
维特根斯坦强烈批判这种观念。他提出“私有语言”⑦这一命题来破解其中的重重迷雾。在此之前,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一种内在的私有语言的存在,但维特根斯坦指出,如果我们认定语言是内在之意的表达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假定一种内在的私有语言,它与我们心中的思想和谐一致,充分地把握了内心之思的所有内涵,这一语言只为我们自己所享有,别人无法完全理解和把握⑧。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内在的私有语言指的不是我们在说出一些话的时候总是先在心里想一下。我们在遇到比较复杂的问题,一时说不清楚的时候,总是先在心中权衡一番,理出个头绪后再说出来。这并不是私有语言。私有语言指的是我们拥有一种独特的意识语言,这种意识语言是专门为了表达内心的想法而设计的,它与内心想法直接一致,它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说的话。但这种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日常语言是一个外部的平台,私有语言却只是为自己而存在,只有自己能理解。要想让别人理解自己内心之所想,必须把这种内在语言翻译为外在的公共语言,但这种翻译无论如何都是不完全的,会出现各种遗失,这就造成了意在言先、言不尽意的情况。
从日常语言使用的角度,我们的确先在内心中思考一番然后再说出来,这种经验每个人都有;但假如由此推论语言与思考的关系就是如此这般的话,却是将个体的经验上升为形而上学的假定了。这种上升的过程是这样的:个体经验(心中默想,然后表达)→设想他人经验(一个类比:心中默想,然后表达)→形而上学假定(先有思想,再有表述,语言是载体)。这一上升过程乍看是合情合理的:从时间顺序上看,默想在表达之前,思想就应该在语言表述之前,这是一一对应的。然而这种看似合理的一一对应关系却是虚设。前一观念是经验观察,而后一观念关涉到整体的哲学观念,在单个经验中,我们可以只观察一个过程,而把其他制约因素忽略掉,但整体的哲学观念却不能如此,它必须全面地考虑到各种制约因素。单个经验中忽略掉的东西必须得到充分思考,这样,就不能简单地把单个经验的观察过程与形而上观念进行简单的一一对应。
三、私有语言(内在心灵)的翻译误区
如果私有语言为个体心灵所独享,那么这一私有语言向外在的公共语言的转换就需要进行翻译。但我们也知道,这种翻译是很特殊的一种翻译。它假定,翻译者掌握私有语言,也掌握公共语言,就像一个中英文翻译者需要同时懂得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一样;而内心的私有语言只为个人所掌握,所以必须将内在语言翻译为外在语言。这样的推论乍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仔细想想却疑惑丛生。此处的“翻译”指的是从内向外翻译,而不是从外向内译,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先在内心里想明白,然后再说出来的。我们假定已经先用私有语言想清楚了,剩下的问题就是把这个语言转换为外在的公共语言。
平时我们说起翻译的时候,基本上指的不是上面的翻译,而是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比如从英文转换为汉语,或从汉语转换为英语。这才是翻译的原型。两种语言都是实际存在的,不同族群使用着它们。私有语言的翻译不过是翻译的比附。一旦使用了这个比附,就不可避免地承接了翻译原型的所有内涵,这让我们不自觉地假定私有语言与公共语言的区别就像英语和汉语的区别一样实在,毋须置疑。
如果内在语言与外在的公共语言之间存在着翻译,那么这种翻译就是一种最奇怪的翻译。我们所说的翻译是一种转述行为,翻译的桥梁是掌握两种不同语言的个体。但是内在语言和外在的公共语言之间的“翻译”却不同:它是一个个体内部的交流⑨,是个体把内在的语言用公共语言展现出来。这一翻译过程在个体内部完成。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异的过程,为了使这个过程不至于太过怪异,我们只好假设这是翻译过程的一半儿,实际的翻译过程是由两个不同的个体共同完成的。两个个体各有各的内在语言,公共语言是两种内在语言的桥梁。某人A具有内在语言A',某人B具有内在语言B',A'与B'要想沟通必须通过公共语言C,A将A'翻译为公共语言C,B接受了公共语言C的表达(间接地接收了A'的意思),再把C翻译为B',最后B理解了A的意思。通过这一过程的设计,我们就建立起了不同个体间交流的模型,但我们看到,这里就存在两重障碍:A'向C的转述,C向B'的转述,每一次转述都会产生遗失,那么B理解了A吗?我们不知道。更麻烦的不是意思到底遗失了多少,而是,这种遗失依然是一种假定,因为我们无法判断每一次转述到底是正确的还是有遗失的,因为没有标准。当A'转述为C的时候,假如我们问:这次转述正确吗?怎样判断?无法回答。我们不能知道A′到底是什么样的,只有A本人知道,同样只有B知道B',所以我们(作为旁人)无法判断C是否完好地翻译了A'和B'⑩。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无法理解他人,他人之心不可知(11)。这是一个多么悲伤的断言啊!在文学作品中,这一断言也许能够引发某种伤感情绪,但在哲学中,这个判断却毫无意义,只会引发混乱。
四、内在感觉的不确定性
我们时常以为,人的情绪是复杂多变的,语言总是跟不上情绪变化的节奏。意识流小说努力复现这一复杂多变的样态。在福克纳的笔下,白痴儿的情绪变化既快速又无逻辑,我们认为这几乎复现了白痴儿的思维特征。如果我们处于对小说世界的天真信任中,无疑会认为这么想是对的,但是不幸,我们,特别是现代的读者,不再天真,已具有大量的阅读经验,不会轻易被拉进小说的世界,因而形成了天真阅读与审视阅读之间的张力。利用读者的天真是一种令真正的小说家羞耻的行为。现代小说的作家们也有意识地提醒读者与小说世界保持距离,它并非就是日常生活世界,不是生活的折射,而是一种“幻想的诗学”。
我们能够在小说中塑造一个新世界,也能够在这个新世界中体会到以前也许不曾体会过的喜怒哀乐,同样,这个世界中发生的故事也帮助我们判断现实世界中的事件。这并不是新鲜的见解。但维特根斯坦的想法并不止于此,他提醒我们,无论内在感觉为何,如果没有外在的语词的参与,这个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根本不知道。
如果我们相信私有语言是对内在感觉的描述,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描述呢?外在语言描述的是客观对象及其关联,那么内在语言描述的就是内在感觉吗?乍看这个比附,仿佛架起了内在感觉与外在描述之间的桥梁,描述是两者之间的关联。沿着这样的路径,我们就会问到底是怎样进行描述的以及在描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仿佛在描述的时候有某种事实发生了。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只是语言带给我们的假象:不是事实引发我们的语言,而是语言误用带着我们假定了错误的事实。此处的语言误用就是把“描述”一词用在了内在感觉上。我们说语言描述对象,描述内心,仿佛是说这样一个顺序:首先确立对象,或内心的某种情绪,把它固定下来,然后找到合适的词儿盖在它上面。这是描述。如果描述具有如此本体论的意义,那么它恰恰是维特根斯坦所反对的,他把这种定义称为“指称论”。指称论的最大问题是忽略语言在确定对象过程中的本体地位。没有语言的参与根本无法确定对象,所以维特根斯坦主张语言游戏观,对象不再具有基石的作用,而是转变为语言游戏中的样本(sample),语言也不再是在“对象”(object)这个基石上产生的,而是在与样本的游戏中固定下来的。这样,带着样本的语言游戏就构成了语言的本性(12)。外在对象尚且如此,内在感觉更不必说。如果我们认为不依靠语言就能确定内心的某个感觉,那么到底怎样确定它呢?是有一双内心之眼紧紧地盯着它吗?然而用什么方式让这个感觉保持不变,以便迅速地找到一个词为它命名?如果一个感觉还没有一个名称,我们是否能为它发明一个名称?别人怎样识别这个名称对应的是哪种感觉?
如果我们认为先有一个感觉,然后再有一个名称把它描述出来,上面的问题就不可回避,而且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这个名称能够适当地描述这个感觉吗?
我们来看如何确定一个内在感觉。在《哲学研究》第258条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如何确定一个内在感觉的问题:假设我们将符号E与一个内心里反复出现的感觉联系起来,应该用什么办法联系?是将E指派给这个反复出现的感觉吗?怎样指派这个符号?一般我们会习惯性地回答,我们可以将注意力内在地集中于这个感觉上面,这就仿佛将这个感觉固定下来了,然后将E与这个感觉联系起来。但这一做法却是可疑的:
(一)如果真有相同的感觉出现,那么它必须反复出现,并且能够被我们当做同一个感觉来看。我们真地能够识别这个反复出现的感觉吗?或者把这个问题变化一下会更清楚:我们怎么能够把不断出现的感觉认做同一个感觉?这将引出下面的问题。
(二)如果这个感觉反复出现,我们还得把这些感觉系列记住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这些感觉实际上是同一个。那么如何正确地记住它又成了问题,而判定是否正确的标准在此基本是失效的,因为此时这种感觉尚未被定义为“E”。如果正确与否只有感觉者个体才清楚,那就与正确无关了,因为每个感觉者都会认为自己“正确地”记住了这个感觉。“正确”这个词不是无所不包,就是完全无用。我们对感觉的反复出现的确定也变得极端随意,毫无必要。
(三)上面的思路中,假定了单一感觉的真实性,假定了我们先有一个个的单一感觉,然后再有感觉的复合和综合,那么如何确定一个单一感觉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从单一到复合,从简单到复杂,这是一个预设的基础主义思路。如果单一感觉是确定的,那么我们就会问,如何确定这个单一的感觉呢?是像盯着一个苹果一样盯着它吗?为了进行确定,我们往往会预设内在的注意力,要想正确地确认这个感觉,我们必须得集中注意力在这个感觉上面,以便我们能够记住它。但多强烈的注意力才是必须的?有什么标准没有?在《意义诠释与未来时间维度》一书中,我曾经相信,必须有内在注意力的存在才能保障感觉的真实,但无可避免的是:这一真实最后必须诉诸相信,即相信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其上的感觉是存在的,除此别无它法。除了相信它(注意力足够集中)以外,我们找不到最终确信的基点(13)。然而,所有的内在确信都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你如何确信你的确信?这样的思考路线几乎是一个死胡同儿。维特根斯坦从一个奇妙的角度告诉我们:“我们在这时有什么根据把E称做某种感觉(feeling)的名称?根据也许是在这个语言游戏中使用这个符号的方式方法。——为什么说它是一种‘特定的感觉’,即每次都一样的感觉呢?是啊,我们已经假设好了我们每次写的都是E啊。”(14)
这段话颇有破坏力,一下子把我们从确信和信仰的泥淖中拉出来。维特根斯坦提醒我们一个滑稽的事实:你怎么知道你的感觉一定是这个感觉,而不是别的?如果没有一个符号E,我怎么知道有一个感觉E?比如我们学习一种嶙峋的感觉,你是心中先有一种嶙峋感,接着产生了一个要把它表述出来的欲望,并用一个词“嶙峋”为它命名吗?当然不是!如果没有“嶙峋”这个词,并且不断把它放在各种语境中使用,我们不会把内心的某种感觉跟这个词对应上。
五、区分内在心灵与外在世界的谬误
我们是怎样把感觉拿出来的?就像拿出一块石头?
一旦我们认为感觉是内在的,只有个体自己独享,这个问题必然会冒出来。我们一般会设想内在感觉就像外在的石头、树木一样,是能够确定下来的东西。我们能够认识内心,就像我们能够认识外物一样。在极端的内在论者那里,内在感觉甚至比石头、树木等外物还要确定,因为它离我们的内心更近。而外物要经过感官的接触,受到种种现实因素的影响,很可能是变形的、不准确的。心中之物没有这段感觉上的距离,它就更纯粹、更准确。
这一观念有两种主要表现方式。一种是强调直观的纯粹性,这是康德的思路。他认为若无纯粹直观,就没有真正知识的产生。推而广之,我们总是能够对自己内在的感觉状态进行直观的,这种直观是纯粹的、独立的,正是在意识中,对单一感觉状态的直观才得以可能。
还有一种是现象学的思路,即意识对一种感觉的观照过后,反省活动会将这一意识观照固定下来。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提到,布伦塔诺强调“感觉的直接感受”(immediate feltness of a feeling)和由其后的反省活动而产生的对它的知觉之间的区别。詹姆斯非常同意这种区别,他认为心理学家必须具备这两种能力(15)。但是我们看看什么是“感觉的直接感受”:好像这里已经是一个直接的感觉行动(feel action),其实不然,这个句式本身已经是一种反思之后产生的分裂—复合。你如何去感觉(feel)你自己的感觉(feeling)?好像感觉(feel)之后,这个感觉(feeling)就停滞了,然后有一个,另一个自我(self)看着这个感觉,又运用这个自我的感觉(feeling)来感觉(feel)前一个停滞下来的感觉(feltness),然后再对这一固定下来的感觉进行反思。这是语言在自己打转转!詹姆斯是美国重要的心理学家,他是维特根斯坦最喜欢批判的思想家之一。
上述两种思路最重要的缺陷是混淆了私有感觉(private feeling)和个人感觉(personal feeling)的区别。我们平常会认为,感觉就是个人的、私有的;“个人的感觉”与“私有的感觉”是划等号的,两者可以相互推导。这种观点似是而非。“感觉是个人的”不等于“感觉是私有的”。维特根斯坦同意“个人的感觉”,反对“私有的感觉”,其中的关键在于“个人感觉”可以个人独享,也可以说出来被他人分享;而“私有的感觉”却只能自己独享,他人根本无从理解。前一个概念在实践的心理学层面上有意义,而后一个却是形而上学的误用,是需要被诊治的东西。两者之间不是同一关系。
为了加强这个区别,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248条中特别指出,“感觉是私有的”这个命题可以和“单人纸牌是一个人玩的”相比较。将两者相比较不是说两者是一样的,恰恰相反,这两个命题的表面相似性让我们混淆了它们在实质上的差别。“感觉是私有的”这个命题强调内在的确定是最真实的确定。而单人纸牌游戏则是一个公共的游戏私下里玩。如果将两者混淆,就会将我们心中的一闪念快于语言表述这一现象当做内在思想先于语言表述这一形而上学判定,这是一个错误的转换,也是维特根斯坦极力反对的东西。
“感觉是私有的”就像在说,我们可以为自己一次性地建立一个规则,别人都不懂这个规则,只有自己懂得。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不能一个人一次性地遵守一条规则。所谓规则,就是公共的、为很多人订立的东西。它必须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群体性,二是重复性,三是约束性。三个特点同时具备才能构成规则。如果没有其他人参与,只是一个人在重复一个行动,这不叫遵守规则。如果没有重复的行为,也不能算做规则。当然约束性就是规则这个概念本身内蕴的,规则本身就具有约束的力量,如果一些人只是偶然地重复行为,也不可能形成规则。当然,一个人可以在私下里遵守一条规则,但这不等于遵守一条私人规则。私人规则好像是一个人为自己制定的,而私下里遵守一条规则却是在公共领域中形成的。两者有天壤之别。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规则不是像交通法规一样的东西,而是深藏在人的行为中,我们在遵守规则的时候从不需要明确意识到它,“我遵从规则时并不选择。我盲目地遵从规则”(16)。所以“感觉是私有的”这个违反规则的命题完全是错误的。
当我们把感觉当做完全私有之物的时候,我们就在强调一种内在的感觉确定过程(我们会在后面的分析中看到这种内在的感觉确定过程是多么可疑)。我们依靠一种内在的力量确定一个感觉,然后寻找到一个词为这个内在的感觉命名。但如何确定这个感觉不变化?它如何能够像一块石头一样立在那里等待命名?我们的感觉石化了,但我们的感觉还继续着——这是一种多么滑稽的情形啊。这完全是“对象与名称”相符合的模型,即指称论的概念观。维特根斯坦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明这一概念观的悖论性质:“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我们称之为‘甲虫’的东西。谁都不许看别人的盒子;每个人都说,他只是通过看他的甲虫知道什么是甲虫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每个人的盒子里装着不一样的东西。甚至可以设想这样一个东西在不断变化。——但这些人的‘甲虫’一词这里还有用途吗?……如果我们根据‘对象和名称’的模型来构造感觉表达式的语法,那么对象就因为不相干而不在考虑之列。”(17)
我们通常认为审美情感是一种内在的感觉,我们在内心中体会到这种情感,并把它抒发出来。从经验的层面上说,这是对的。然而,这种观念却主要不是在经验层面上表述的,它往往上升为一种本体论层面的描述,将审美情感当做最原初、最基础的东西来对待,而语言与审美经验的关系就是描述与被描述的关系。这样一来,语言成了审美经验的表述工具。这就是“对象和名称相符合”这一模型的移用。如果我们真地如此认为,就需要好好想想维特根斯坦的“甲虫”了。这个“甲虫”当然只是一个比喻,它不是一个像石头、树木一样的物质性的东西,而是在内心中成形的东西,比如审美情感、内在之意等等。我们怎么知道别人盒子里的甲虫(审美经验)是什么样的?也许只能依靠猜测,而猜测还是有所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看看自己盒子里的甲虫(审美经验),然而别人盒子里的甲虫(审美经验)到底是什么还不得而知,因为它很可能是不断变化的,而且也可能根本就与我们自己的甲虫(审美经验)完全不同。那么我们怎样比较自己与别人的甲虫(审美经验)呢?无法比较,如果按照对象和名称这一模型的话。除了共用“甲虫(审美经验)”这一符号之外,我们无法确定自己与别人甲虫(审美经验)的一致或相近之处,如此,“对象就因为不相干而不在考虑之列”。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悖论啊!我们假设了名称描述对象,但最后对象却毫不相干,只要操练名称就可以了。但这样一来名称也失去了约束力,没有了着力点,真的成了“能指的游戏”了。我们习惯于说,“我”的情绪变化得很快,像一条永不停息的大河,是一种情绪“流”;“我”的思考总是不断在进行,没有停息,像一个“过程”。这好像是在肯定内在的情绪和思考,但倒过来想一下,所谓的“流”和“过程”不都是从现实的水流和操作过程中借用来的吗?我们只有把内心的情感比附为现实的东西才能真正理解它们。由此显露的已经不是使用方法的问题,而是语言使用的本性。就像维特根斯坦问的那样:“一个人可以充满情感或毫无情感地唱歌,那么为什么不把歌儿省略掉?——你还能有感情吗?”(18)对这么一个浅显的问题,我们都会回答:没有。所以对于情感和语言的关系,恰当的说法是,情感不是语词的基础,语言也不是情感的基础,情感只在语言的使用中得以展现。
从反面来讲,如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意,而他表达得又不完整,别人同样表达得不完整,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别人的心中所想?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公渡性在哪里?我们难道只能模模糊糊地理解吗?还是说我们根本就不能理解他人?如果根本就不理解,我们怎么又能在生活中实际地理解对方?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都是无理解的交流的话,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提到的理解不过就是一个个骗局,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理解别人,只是假装在理解,根本不存在任何理解。但是,当我们说“没有任何理解发生,一切都是骗局”的时候,“骗局”这个词就丧失了它的含义。
六、一个诊治:去除神秘主义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本人存在一个美学倾向的话,那么这个美学倾向既不是肯定性的,也不是否定性的(19),而应该称做“诊治性”的:“你的哲学目标是什么?——给苍蝇指出飞出捕蝇瓶的出路。”(20)
维特根斯坦说,我们的日常用法是正确的,但哲学家是错误的,因为日常语言使用者只是在语言使用的层面上理解语言,但哲学家却认为这样是对语言的片面理解,而力图把所有语言现象贯通起来,贯通的办法就是为语言使用设定一个语言本体,用来解释各种语言使用。维特根斯坦说这是错误产生的根源,哲学家假设了一个本来不存在的东西,还要为它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当然就要陷入困惑之中了。语言分析就是清除各种哲学的错误。“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本体就是这样的尘埃,扫净之后才能让语言自如地运转。
私有语言命题的辨析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是对本体论尘埃的清除。这一尘埃让我们误以为存在一种内在的神秘感觉,我们首先把握到这一神秘感觉,然后语言才能跟上,语言无法完全表达出这一神秘感觉,所以这一感觉永远保持着神秘。这似乎是一种内容上的或称实质性的神秘,正因为神秘,我们的语言无法达到它、触及它,它永远躲避我们的理解。艺术心理学特别集中地假定了内在的审美之意,这种审美之意往往披上神秘的外衣,“言不尽意”观恰当地说明了内在之意的神秘性。审美之意、意象、审美体验、审美情感基本都可归为内在的私有语言层面上的东西。
然而,这种内容上的神秘只是一种假象,它让我们觉得真的存在一种神秘的内在审美情感,毋须语言的存在也能在内心中成形,这种神秘的存在赋予文学以力量,文学从中汲取最本真的意义,并将它传达出来,形成具体而特殊的诸种意义形态。破除这一假象的方法就是揭示出文学神秘性不是内容上的神秘,而是一种推论上的神秘——是我们的推论方式出了错,这个错误让我们寻找一个仿佛存在的内在本性,可无论怎样都无法找到,所以我们就假定它永远躲避我们的理解。我们从来没有回过头来看看推论是否出了错,是否因为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从而让我们错失了揭示真相的机会。维特根斯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提醒我们从何处起踏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将我们误入歧路的思考拉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当然未来的路依然还需要不断地试探和纠错,这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如果谁以为纠正了一时错误从此就可以迈上康庄大道了,就又中了理性的狡计。这种情况只有在超越现实的电影和小说里才会出现,而理性从来都是面对着未来小心翼翼前行的。在这时我们一定要听从康德的告诫:“纯粹理性有一种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辩证论,它不是某个生手由于缺乏知识而陷入进去的,或者是某个诡辩论者为了迷惑有理性的人而故意编造出来的,而是不可阻挡地依附于人类理性身上的,甚至在我们揭穿了它的假象之后,它仍然不断地迷乱人类理性,使之不停地碰上随时需要消除掉的一时糊涂。”(21)因此,不断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对错误道路的诊治是理性的职责和命运。
“哲学家诊治一个问题;就像诊治一种疾病。”(22)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注释:
①详可参见拙文《自我对话的悖论——茨威格〈象棋的故事〉的一种解读》,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②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包华富等编译《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142页。
③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红旗》杂志编辑部文艺组编《文学主体性论争集》,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④(14)(16)(17)(20)(22)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第145页,第130页,第153页,第158页,第139页。
⑤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私有语言。简单地说,私有语言命题就是假定存在一种内在的意识语言,它有自己的语言形式,不能完整地翻译为外部的公共语言,只能被持有者自己理解。这一假定的主要推论是,他人不能理解我,我也不能理解他人,即他人之心不可知。
⑥Steven Pinker,The Language Instinct,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5,pp.44-74.
⑦一般认为维特根斯坦对私有语言命题的论述集中在《哲学研究》第一部分第243-315节,但其前后的一些部分也与此命题有关。
⑧Cf.P.M.S.Hacker,Wittgenstein:Meaning and Mind,Part I:Essay,Oxford & Cambridge:Blackwell,1993,pp.1-2.
⑨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方法,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句式本身就很奇怪。个体内部的交流?交流本来是不同个体间的事情,现在怎么把它移用到个体内部来了?维特根斯坦会说,看,这就是语言的误用。
⑩当然维特根斯坦在此处指出的是“知道”这个词用错了,我们不能把“知道”用在内心意思上,“知道”指的就是在公共平台上交换相互的想法,在公共平台上知道他人的想法。当我们说我们知道自己怎样想的时候,这句话不是有格外的深意,而是没有意义,因为“知道”这个词在此处用错了。
(11)《齐物论》中有一段话说明了庄子对此“标准”的思考,与上面的思考形成奇妙的呼应:“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闇,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庄子·齐物论》)
(12)详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4、8条。同时参见Gordon P.Baker & P.M.S.Hacker,Wittgenstein: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Essays on the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83,pp.97-102。
(13)王峰:《意义诠释与未来时间维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5)参见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田平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页。
(18)Ludwig Wittgenstein,Lectures and Conversations on Aesthetics,Psychology and Religious Belief,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p.29.
(19)关于维特根斯坦对美学的批判,详可参见拙文《美学是否是一个错误的学科?——维特根斯坦对传统美学的批判及对新美学的启示》,载《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
(2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