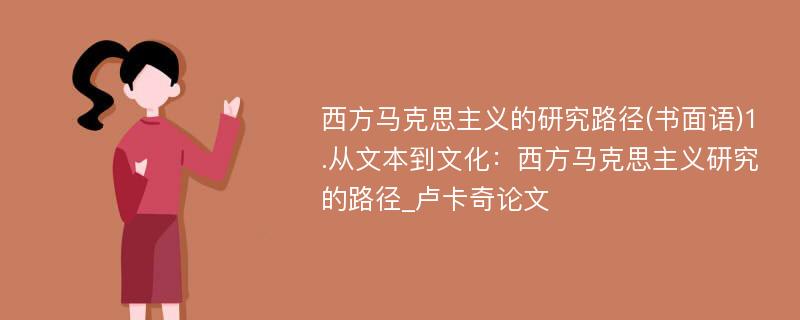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笔谈)——1.从文本到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路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路径论文,笔谈论文,文本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独有的理论话题和思想锋芒,自被译介到中国以来就一直受到国内学术界的特别青睐。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介研究,在新时期明显地起到了一种理论反思的助推器作用。从“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建构到“主体性问题”的理论突进,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学术争鸣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反思,无不投射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影。“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历经二十余年渐进式的发展过程,积累了十分丰硕的思想理论成果,同时也凸现了不少制约深化研究的路径问题。我们以往的研究多是囫囵吞枣式地转述和评说,还无法真正做到细嚼慢咽式地分析和解读,因此研究的方法以及内容往往是大而化之和立足表面的,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显然还缺少进一步深究。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不足和缺失,本文试图就深化理论研究的路径问题提出一些探讨性的观点。
一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史差不多就是一个不断变化和不断丰富的概念解释的历史。“回到马克思”,这似乎已经是一个常说常新的理论惯例。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这不仅仅是一个时代催生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理论建构的问题。应该看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遵循的不是线性的思想逻辑而是类似交响乐作品一样的理论“织体”,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单一的学科理论,而是跨越了学科界限的综合性的和实践性的社会历史学说。如果我们用一种狭隘的甚至是封闭的专业学科眼光去解读马克思的理论文本,就很难找到这一学说的“问题框架”。
卢卡奇等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另类解读,为我们开出了一条离经叛道式的理论发展路径。他们挑战的是那种定于一尊的领袖人物式的或执政党式的文本解读模式。相比他们的经典文本解读,我们已有的解读如果不是完全错误的,至少也是表浅的和狭窄的。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的层次角度上的不同,当我们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观点相遇的时候,如何判断这些理论观点的是是非非,就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往往他们说的是“西”而我们想的是“东”。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不可谓不重视不下力气,但是真正有创见的成果并不多。究其原因,首先是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彻底突破《联共(布)党史》所圈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完全用教科书式的理论思维去解读经典文本,只是对已有的定论进行论证,或者是作些细枝末节的考证。再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于白纸黑字式的阅读逻辑,总以为书面的文字就可以说明思想家的全部问题。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缺乏穿透文字句法的眼光,缺乏捕捉“总问题”的功夫。
反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别有一番理论的洞天。卢卡奇之前,几乎没有人探讨过“总体性”这一涉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范畴,当然更没有人把这个范畴当作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并成功地把它变成一门崭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实质”[1](P27)。由于马克思生前没有明确论述过“总体性”范畴,再加上第二国际时期盛行的经济唯物主义及其历史决定论的影响,这个范畴对于绝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和怪异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问世,即刻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一片哗然。卢卡奇关于“总体性”辩证法的全新论述,不仅打破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固有划分,更重要的是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问题。卢卡奇通过一种别样的文本解读,试图用总体性范畴来唤起历史主动性的方法论,最终确立一种人本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模型。
思想家往往都有一个不断调整自己思想的心路历程。马克思也不例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之间,显然有一个思想变化的轨迹。那么是不是存在着“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不同思想阶段呢?两个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关系又该如何解释呢?阿尔都塞采纳“症候阅读法”,从字里行间去探寻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得出了马克思有过“认识论上的断裂”这一基本的理论判断[ 2](P11)。翻开《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等论著,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精耕细作式的文本解读,而且有一种理论的想象力作用。事实上,理论的研究只有逐字逐句的研读功夫是不够的,恐怕还需要我们具备相应的理论想象力,因为作者本人不会把他的理论思路直接告白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去发挥想象力,将他的问题思路串联起来。
如果我们还是习惯于教科书式的理论解读的话,我们就无法进入卢卡奇和阿尔都塞等人的理论逻辑之中。我们之所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观点深入不够,原因就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认识、挖掘还不够深入。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确实需要我们站在一个应有的理论高度,至少是站在一个应有的理论平台上。这个高度和平台就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就是我们抛开原有的教科书体系之后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眼光,就是我们愈加开放的思想认知境界。
二
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大多是面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评析,少有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的直接论述,这样就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思想阐释空间。正如阿尔都塞强调的那样,思想家一般不会去思考他的“理论框架”本身,而往往是在他的“理论框架”范围内去思考具体的问题,“一般而言,问题结构并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而是躲藏在思想的深处,在思想的深处发挥作用。只有不顾思想的否认和抵抗,才能够从思想深处将问题结构挖掘出来”[2](P34)。在我们已有的原理教科书逻辑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及其理论性质似乎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正是这种观念妨碍了我们去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理论问题,封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发展的空间。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有如此多的新发现和新观点呢?为了重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品格,几乎每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十分注重探讨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副标题,其实这个副标题也可以用“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来代替。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最令人信服之处是在《精神现象学》中——同时是哲学又是历史哲学,就这个基本观点而言,它绝没有被马克思扔掉。黑格尔使思维和存在辩证地统一起来,把它们的统一理解为过程的统一和总体,这点也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的本质”[1](P35)。
自卢卡奇以来,黑格尔哲学就逐渐摆脱了被当作一条“死狗”的命运,翻身成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活水源头。与卢卡奇同时代的柯尔施写下《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旨在扭转“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极度轻视哲学辩证法的纯科学倾向,最终复兴马克思的“革命哲学”。在他眼里,“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前进时,废除哲学对他们说来决不意味着简单地拒绝哲学。甚至当我们考虑他们后来的立场时,也必须时刻把下述这一情况作为出发点,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先是辩证法家,然后才是唯物主义者。”[3](P208) 后来名气很大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马尔库塞写出了《理性和革命》一书,并用一个副标题“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指明了他的理论意图。他要一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以一种肯定的态度来重新阐述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按他的理解,马克思在去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外壳之后,完全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尤其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同黑格尔一样,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关注于这样的事实:内在的否定是一种‘运动和创造的原则’,因此辩证法就是‘否定的辩证法’。”[4](P267)
我们也承认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关联,但只是停留在一般性的和比喻性的是非评说上面。我们习惯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吸收了黑格尔的“合理内核”,把被颠倒的辩证法思想再重新颠倒过来。“颠倒”其实只是一个比喻性的用词,难道从黑格尔哲学转化成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这么简单吗?对此,阿尔都塞有一个相当中肯的评论:“关于把辩证法颠倒过来这个不确切的比喻,它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要用相同的方法去研究不同对象的性质(黑格尔的对象是理念世界,马克思的对象是现实世界),而是从辩证法本身去研究辩证法的性质,即辩证法的特殊结构,不是对辩证法含义的颠倒,而是对辩证法结构的改造。”[2](P72) 我们也应该去深究这个改造过程,应该深入到哲学的内在逻辑里面,不然就只是生吞下一堆概念而无法吸收到应有的理论营养。
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始终缺少一些哲学味道,这样的理论情形跟我们一直缺乏对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近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深入挖掘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对黑格尔哲学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那么我们如何去判断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关系呢?我们又怎么有资格去评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呢?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研究,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其实都将关系到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把握,关系到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基本判断。
三
当代西方哲学之所以让人感觉有些眼花缭乱,原因在于哲学方法上的推陈出新。生命哲学运动、现象学运动、分析哲学运动、精神分析运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运动等等,不仅给当代西方哲学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而且也给西方马克思主义贴上了时代的标签。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力图“回到马克思”以及“回到黑格尔”的过程中,也在积极吸收并发挥各种当代哲学理论的新方法,由此才出现了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诸如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
马克思是强调过经济基础和历史规律的决定作用,但是从来没有说让我们去消极等待和冷眼旁观历史过程的自行结束,就如布洛赫讽刺的那样:人们只需乘坐共产党开行的火车就可以抵达共产主义目的地。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满怀憧憬地“皈依”了马克思主义,尽管欧洲革命失败而使他们身处困境,但是心中的理想使得他们要继续寻找重新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及其实现条件。他们把欧洲革命失败归结为主体意识的缺失,于是将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动性方法论作为理论思考的方向。确立人的主体性这样的理论目标就直接书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上面。当时很出风头的新黑格尔主义以及生命哲学思潮,正好为他们的理论重建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可是,我们对于新黑格尔主义以及生命哲学的研究是非常表面和欠缺的,这样就影响到我们对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行的哲学分析。
萨特试图将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捏合在一起来建立他的历史人学。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待解决的“中介问题”:马克思主张人创造历史,同时也肯定历史创造人。如果说人创造历史和历史创造人都成立的话,那么在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中介问题”呢?萨特是想建立一种具体的人学辩证法,一方面要抵制和消除唯经济主义的决定论后果,另一方面要脱离那些抽象的唯心主义思想。在构建其人学中介方法的过程中,精神分析因为抓住了家庭中介问题也被萨特所看重,“今天,只有精神分析方法能够使我们深入研究一个小孩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是如何模仿着扮演大人强加给他的社会角色的……他是否对社会感到恐惧,他是否想摆脱社会给他的角色。只有精神分析方法能够使我们在成年人身上重新找到完整的人,不是只看到他现在的规定性,而且还要找出他的历史承负。如果我们认为精神分析学与辩证唯物主义根本对立,那就完全错了。”[5](P58)
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其实肯定了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情欲方面,但还没有具体深入地去探究它们的活动特征,这样就为社会主义革命留下了生物学的“空白”。根据这样一个理论判断,马尔库塞为他的“社会主义”生物学改造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对于一贯崇尚感性的马尔库塞来说,精神分析学理论将人的本质规定充分地生物学化了,“弗洛伊德提出了一种‘人’的理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这一理论使弗洛伊德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我们的目的不是去纠正或者完善弗洛伊德的理论概念,而是要发挥出这些概念的哲学和社会学的意义。”[6](P15) 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被法西斯主义和发达工业社会的问题所困扰,或许在他们看来,“社会批判理论”需要走一条“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道路。
为了证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历史科学”,阿尔都塞用“结构因果观”取代“线性因果观”,用“多元决定论”取代“经济一元论”,对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了结构主义的理论解读,“马克思用他的概念来描述经济的时候(我们这里暂时用空间的比喻来解释他的思想),他不是在同一个平面空间的无限性中,而是在局部结构所制约的,而且是作为整体结构的组成部分的特定领域中来说明经济现象的。他是把经济现象当作一个复杂深沉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又是另一个更为复杂深沉的空间的组成部分。”[7](P212)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不断创新就不会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理论作为。因此,如要弄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建”的种种得失,还需要我们更多地去了解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诸多变化。
四
文化批判为什么会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我们大体可以找出三个原因:一是需要解决马克思留下的一个问题:人创造历史和历史创造人之间的“中介问题”。对于这个理论上的难题,我们过去缺少深入的探讨。二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现实表明了文化的强力作用,尤其是消费文化的腐蚀作用。三是当代文化批判思潮的盛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马克思留下的一个有待完善的理论问题可能就是文化问题了。限于当时的历史发展条件,马克思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上面。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资本论》这一理论巨著,但没有能够留下“文化论”这样的思考作品。20世纪2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的失败,推动卢卡奇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文化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他们之所以提出了“回到黑格尔”的理论口号,是因为他们完全肯定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人的思想不仅仅是观念性的,而且也是生产性的。思想和行动,只是历史辩证法这个金币的正反两面而已。卢卡奇大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1](P318),还明确提出了“文化共产主义”的远景目标;柯尔施极力突出哲学批判的实践功能;葛兰西提出“历史集团”和“文化领导权”等概念,将文化斗争视为欧洲社会革命的特殊模式,并且强调了知识分子在社会革命中担负的使命;布洛赫用他的“希望哲学”来进一步充实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乌托邦”。在他看来,“具体的乌托邦作为最遥远也是最实际的乌托邦,它们所表示的东西,对个人的主体来说就是幸福和他的希望内容,对作为主观因素的社会方面来说就是团结合作,就是我们作为人应该走的可能的道路。”[8](P16) 于是,为了重新唤起欧洲革命的热情,“阶级意识”、“理论实践”、“知识分子”、“希望”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词。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上台执政,以及法西斯主义引发的战争灾难,促使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研究转向了社会心理机制方面。无论是他们的集体合作研究成果还是他们的个人研究著作,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希特勒的纳粹党能够上台?为什么在20世纪的文明时代会发生屠杀犹太人的残暴行径?在法西斯国家,事实上存在着相应的社会心理作为法西斯主义得以兴起的社会基础,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即使作为一般的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也需要探究这种社会心理。战后欧洲社会的迅速复兴,尤其是消费文化的兴起,使得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锋芒一转,几乎成了一种“文化工业”理论,其矛头直接指向当代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当务之急,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心转向“文化控制”和“交往行为”。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学生造反运动完全不是为了增加工资和减少工时,而是因为从心理上“厌恶”这个社会。这些都表明了今天西方社会变革的问题,不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变成了文化问题。为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他的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的“交往行为理论”[9],马尔库塞则要求用“爱欲解放论”来重新论证人类最后解放的共产主义目标应该是“非压抑性的文明社会”[6]。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我们应该看到的,一方面是它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变革的独特分析,另一方面是它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补充”和“完善”。由于我们不能身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环境之中,使得我们对于“文化批判理论”研究有些隔阂。事实上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文化批判已经变成了一种微观政治学,一种价值伦理学,一种解放美学。文化问题既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时代逻辑,同时也是寻求社会变革新途径的立足点。
标签:卢卡奇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