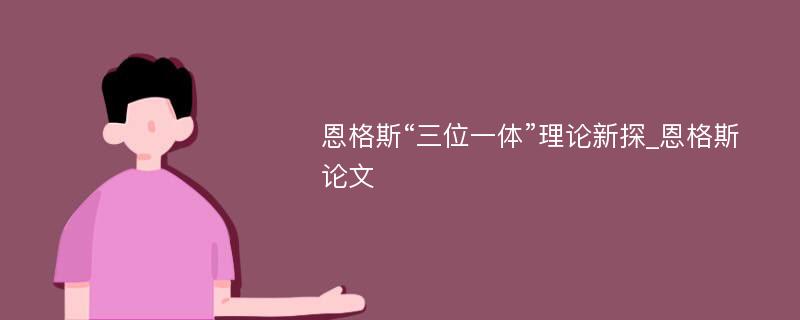
恩格斯“三融合”论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论新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三融合”究竟是由谁提出来的
您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1〕
这是恩格斯1859年5月18 日致历史剧《弗兰茨·冯·济全根》的作者斐迪南·拉萨尔的复信中的一段话。刘庆福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称它为“关于‘三融合’的著名言论”。“三融合”确实是马列文论中的一个著名观点,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对它的涵义的理解不尽一致,并且这里还存在着一个疑团,即“三融合”的要求究竟是谁提出来的?这项“知识产权”是属于恩格斯还是拉萨尔?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存在已经影响了对它的认识与研究,比如陆梅林先生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词典》虽然在有的条目中也提及过这个观点,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有关名言释义》这一编中却未收这个条目。这使笔者大惑不解,如此重要的一段名言为什么竟没有进入这部收录甚为详备的大词典的编者的视野呢(何况所收的有些条目还不及这段话的知名度高)?或许编者以为这只是恩格斯转述的拉萨尔的意见而非恩格斯提出的观点?的确,从这段文字看,“三融合”似乎是由拉萨尔在某种著述中提出的,恩格斯只是表示赞同罢了。倘如此,则又造成了“济金根论战”中的一些矛盾无从解释:我们从《济金根》序言中知道拉萨尔是推崇席勒而贬低莎莎士比亚的,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也批评他“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怎么可以设想,一个贬低莎士比亚、几近“忘掉”莎士比亚的人能够提出“三融合”这样的要求呢?如果拉萨尔还能如此看重莎士比亚,那么恩格斯又何必在同一自然段中提请他“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呢?
原来,这里的疑团和矛盾是由于译文不准确所致。读一下朱光潜《西方美学史》“据原文稍作校改”的这段话,疑团即可冰释,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朱光潜校改后的译文是这样的:
你不无理由地拿来记在德国戏剧功劳簿上的那种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须同莎士比亚戏剧情节的那种生动性和丰满性达到圆满的融合。这种融合只有到将来才会实现,大概不会由德国人来实现。〔2〕
这段话表明,拉萨尔至多不过是(为什么说“至多”,下文还有说明)谈到过德国戏剧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戏剧情节的那种生动性和丰满性达到圆满的融合”一语前的那个“须”字,无可置疑地说明“融合”是恩格斯提出的要求。如果说恩格斯在这里对拉萨尔尚有某种程度的赞同的话,那只是他承认拉萨尔所谓德国戏剧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之类的说法还属于“不无理由”罢了。但是,如果朱译“拿来记在德国戏剧功劳簿上的”这个短语是准确的,则揶揄色彩溢于言表,其中的赞同成分就更加有限了。
二、“三融合”提出的针对性
恩格斯提倡“三融合”,这体现了他对艺术规律的理解与尊重;而在致拉萨尔评论其《济金根》的信中提出这个论断,则又有其鲜明的针对性。大体说来,前两项是针对剧本序言中的一些议论而发的,后一项是针对序言中的创作设想和剧本存在的严重缺陷提出来的。
拉萨尔在剧本序言中说:“我认为德国戏剧通过席勒和歌德取得了超越莎士比亚的进步,就在于他们两个,尤其是席勒,首先创造了狭义的历史剧。至于其他的一切,特别是席勒戏剧中的更伟大的思想深度,那只不过是与这种狭义的历史剧有着密切关系的结果而已。”〔3 〕显而易见,恩格斯正是根据这段话说拉萨尔把“较大的思想深度”“拿来记在德国戏剧功劳簿上”的,只是恩格斯把“更伟大的思想深度”改为“较大的思想深度”了。这种改动既较为符合席勒和德国戏剧的实际,也为一般戏剧创作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要求。说席勒戏剧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的确是“不无理由”或“不无根据”的,恩格斯对席勒青年时代狂飚突进运动中的作品就曾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如认为“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4〕,又说“席勒写了《强盗》一书, 他在这本书中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5〕。但就思想倾向而言, 无论是席勒还是歌德,恩格斯说“他们年纪一大,便丧失了一切希望。歌德只写些极其辛辣的讽刺作品,而席勒假如没有在科学中,特别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伟大历史中找到慰藉,那他一定会陷入悲观失望的深渊”〔6〕。 又说,“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席勒以“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7〕这足以说明, 席勒和德国戏剧具有“更伟大的思想深度”的说法是夸大其词的,而恩格斯在信中又不可能过多地辨析这个问题,所以采取了姑妄听之又加以订正的办法,目的在于借此机由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
如果说,“较大的思想深度”这一项属于恩格斯对拉萨尔夸大其词的说法的订正,那么“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这一项则是恩格斯对拉萨尔关于戏剧题材内容的议论的升华和提纯。拉萨尔在序言中一方面推崇席勒戏剧的“更伟大的思想深度”,另一方面又对构成这类戏剧情节灵魂的“则还是纯粹个人的利害和命运、露骨的虚荣心、家族和皇室所欲达到的目的等等”不以为然。相反,在他自己的剧本中,“问题不再是关于个人”,“问题却在于那个最重大、最有影响的民族命运”。他提出,“一切悲剧的最主要的任务,是使时代和人民,首先是本国人民的伟大的文化历史进程成为悲剧的真正主题,成为可以在戏剧上加以刻划的悲剧人物,把这样的转折时代的伟大文化思潮及其激烈斗争作为戏剧化的真正对象”。这些议论既表现出他对席勒戏剧的看法的自相矛盾,又流露出相当明显的自负情绪,但他声称要把“民族命运”、“人民的伟大的文化历史进程”、转折时代的“激烈斗争”作为戏剧的表现对象,也还不无可取之处。恩格斯也就从这种议论中提炼出“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戏剧创作的必备条件。还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拉萨尔对席勒和德国戏剧题材内容的上述不以为然的态度,决定他“拿来记在德国戏剧功劳簿上的”东西只能限于“较大的思想深度”而不包括“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这从另一侧面证明“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不是拉萨尔提出的概念。
拉萨尔关于戏剧创作的议论中还存在着许多唯心主义的和违反艺术规律的观点。比如,他把社会矛盾理解为某种“普遍精神的最深刻的矛盾”,现实中活动着的人又只不过是“普遍精神”的矛盾的“代表和化身罢了”。这种撇开现实物质生产和阶级矛盾侈谈什么“普遍精神”的矛盾及其化身的观点,显然是抽象的唯心主义观点。他还说他的剧本要使这种“具有最内在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思想……得到展现和塑造”。这里,我们且不说他的“思想”是否正确的问题,单就“塑造”思想而言,也是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这岂不等于说要图解观念?他自己也承认“这样就更有可能陷入一种抽象的、学究式创作的危险”。恩格斯在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您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而又不够现实的”,并且目睹“抽象的、学究式创作的危险”没有象作者自信的样“完全可以避开”而是变成了事实,“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马克思对该剧本的批评),“道白很长,根本不能上演”,等等,所以向他提出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的历史内容,须同莎士比亚戏剧情节的那种生动性和丰满性达到圆满的融合”这种要求。“融合”的要求,实际上是对拉萨尔“抽象的而又够不现实的”戏剧观点和“抽象的、学究式创作”实践的双重批评。
三、“三融合”的涵义
目前对“较大的思想深度”的理解没有分歧,因为它的涵义很明确,指的是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偏重于主题而言,鲁迅所说的“开掘要深”正是这种意思。对“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涵义尚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说:“所谓‘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指的是在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下,深刻地反映时代历史的本质规律,换句话说,也就是达到艺术对时代历史的本质的认识。”〔8〕笔者认为, 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它未必符合恩格斯的原意。倘作如是解,那么它与“较大的思想深度”的涵义还有什么区别呢?“较大的思想深度”难道还不意味着“深刻地”认识并反映时代生活的某些本质和规律吗?照这种解释,二者岂不是同义反复吗?持这种看法的同志实际上也把这二者当作一项来看待了,他们在行文中把恩格斯这段话称作“关于二者完美‘融合’的思想”。〔9〕当然,称“三融合”或“二融合”这不关紧要, 重要的是尽可能准确地把握这段话的涵义。
那么,“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关于“历史内容”,恩格斯在信的下一个自然段就有论述:“至于谈到历史内容,那未您以鲜明的笔调和对以后的发展的正确提示描述了您最关心的当时的运动的两个方面:济金根所代表的贵族的国民运动和人道主义理论运动及其在神学和教会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即宗教改革。在这里我最喜欢济金根和皇席之间,教皇使节和特利尔大主教之间的几场戏……在济金根和查理的那场戏中对性格的描绘也是很动人的。”之后,恩格斯认为剧本“把农民运动放到了次要地位”,“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运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没有给“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没有“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同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这清楚地表明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内容”就是作品所“描述”、“描绘”、“描写”、“提供”的社会生活内容——生活现象、事件、背景、人物关系、人物性格等等,总之,是指题材内容面言的。他把社会生活内容称之为“历史内容”,是由于他通常是把“历史”和“社会”视为同义词的。如他说:“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10〕,“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11〕。同理,“历史内容”亦即社会内容、社会生活内容。鉴于评论对象取材于历史,这里用“历史内容”就更为恰切。
“意识到”即“认识到”,这个词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多次出现,如“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12〕中的两个“意识到”都可以用“认识到”加以置换。他把题材内容称之为“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意在强调这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13〕社会生活,是被作家正确认识正确描写的社会生活,是既“显出本来的面目”又蕴含着“较大的思想深度”的社会生活。
“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系指题材内容,这似乎并不难理解,一些同志之所以未做这种理解,大概又和如何理解“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涵义相关。或许他们以为“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这才是指题材内容,如果把“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解释为题材内容,则“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无以为训。当然,故事、情节属于作品的题材范畴,但恩格斯这里说的并非构成题材要素之一的情节本身,而是“情节的生动性性和丰富性”。它虽然与情节内容有密切联系,但主要是指处理题材安排情节的方式和技巧,是偏重于结构形式、剪裁布局而言的。这种解释有什么根据呢?首先,综观这一自然段的用意就是谈情节的安排和形式方面的问题的,前面说“如果首先谈形式的话”,最后又以“我在您的剧本的形式方面也用过一些心思”作结。“三融合”作为“首先谈形式”这个自然段的点睛之笔,如果不涉及形式方面的问题,那将是不可思议的。其次,已如上述,恩格斯认为《济金根》在情节安排结构布局方面存在着严惩缺陷,“就眼前这个剧本看来,它肯定是不能上演的”。他转述卡尔·济贝耳的看法以说明不能上演的原因:“由于道白很长,根本不能上演,在做这些长道白时,只有一个演员做戏,其余的人为了不致作为不讲话的配角尽站在那里,只好三番两次地尽量做各种表情。”他希望作者“在为这个剧本上演加工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点。当然,思想内容必然因此受损失,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三融合”恰恰是紧接着这句话提出来的,其中“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要求显然是直接针对剧本呆板、冗长、单调、“根本不能上演”的结构安排“这一点”的。他要求拉萨尔“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而一般所谓艺术“发展史上意义”,通常也是指这门艺术在形式技巧、表现方法的纯熟程度和艺术成就而言的。对于从未写过剧本的拉萨尔来说,莎士比亚剧作那种情节曲折、跌宕起伏、千变万化、巧于安排的炉火纯青的高超技艺,尤其需要“多注意”了。
概而言之,“三融合”的前两项是对作品的思想意蕴和题材内容提出的要求,后一项是对作品的情节安排和结构布局(实际上也包括语言、台词的运用)提出的要求。前两项解决的是“写什么”的问题,后一项解决的是“怎么写”的问题。“怎么写”虽然属于形式问题,但对于思想内容的表现又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而恩格斯认为为了艺术形式的完美那怕不可避免地会使思想内容受损失也是值得的。这种内容和形式必须完美融合的要求,正与他信中表达的“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态度互为表里。这足以证明,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只重视内容而忽视艺术形式的观点,甚至把这种批评视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
四、“三融合”为什么“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
恩格斯提倡“三融合”,却又认为它“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这是为什么呢?有一种意见认为,“旧时代的作家,包括莎士比亚那样的作家”,不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难以“达到艺术对时代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因而恩格斯说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14〕世界观固然对创作有指导作用,但有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却未必就能达到完美的“三融合”,这是早已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所证明了的。这里的关键是一个是否按艺术规律办事的问题,恩格斯不相信德国人能在短时期内达到这种完美的融合,主要是因为当时德国文坛普遍存在着违反艺术规律的创作倾向,并且这种根深蒂固的倾向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克服。
我们知道,德国是一个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特别发达的国家。受哲学的影响,不少作家都沉溺于理性中,在创作中常常出现抽象思维干扰、代替形象思维的现象。歌德就说“席勒对哲学的倾向损害了他的诗”〔15〕,“席勒式”创作便是这种“损害”的突出表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泛滥一时的“青年德意志派”、“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也都是借助于文学来宣扬某种哲学观点和政治倾向的文学派别。恩格斯就说所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缺乏一种讲故事的人所必需的才能”,“他们不是满足于按哲学结构组织一番,就是枯燥无味地记录个别的不幸事件和社会现象。”〔16〕问题还在于许多德国人对这种“损害”诗的、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倾向缺乏清醒的认识。如前所述,拉萨尔认为席勒戏剧超越了莎士比亚。几乎与此同时,1858年卢格为纪念席勒百年诞辰而写的文章中也说莎士比亚不是戏剧诗人,因为他没有任何哲学体系,而席勒由于是康德的信徒,所以是真正的戏剧诗人。这种扬席贬莎的喧嚣持续多年,1873年,戏剧评论家贝奈狄克斯又写了一本名为《莎士比亚狂热病》的书,他认为莎士比亚不仅不能与德国伟大诗人,甚至也不能与德国现代伟大诗人相提并论。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称这本书是“臭气薰天”的书,并以莎士比亚剧作与德国文学相对比:“单是《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和他的狗克莱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在一起更具有价值。”〔17〕在恩格斯看来,德国文学和戏剧根本无法望莎剧项背,加之那么多德国人缺乏起码的自知之明,他们要发扬其“国粹”、光大“席勒式”,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莎士比亚化”,达到“三融合”,谈何容易!所以,他把实现“三融合”的希望寄托于未来人,甚至是德国以外的未来人。
注释:
〔1〕〔4〕〔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454、501页。以下所引恩格斯这封信中的话,不再加注。
〔2〕《西方美学史》下卷(1979年版),第717页。
〔3〕《弗兰茨·冯·济金根》第10页。以下所引该剧本序言中的话,不再加注。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4页。
〔7〕〔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6、237页。
〔8〕〔9〕〔14〕《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247、246页。
〔11〕〔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21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15〕《歌德谈话录》第1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