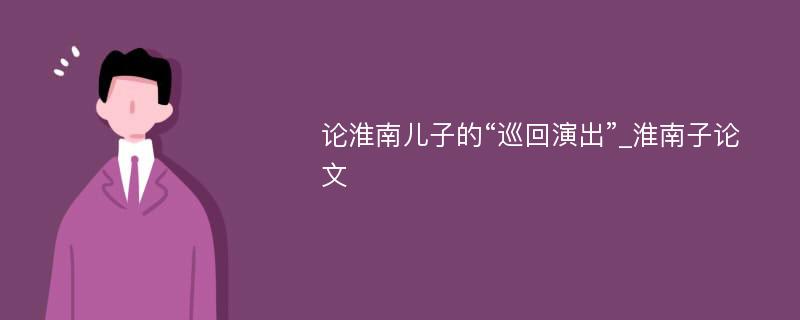
论《淮南子》之“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淮南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2)04-0080-06
《淮南子》是西汉时期一部重要的思想著作,体大思精,蕴涵丰富。因其体现出多元化的思想因素,而道家思想在其中又“究居优势”[1]118,所以历来被学者们用“道家”或“杂家”的学派概念来界定。不论如何认识《淮南子》一书的学派属性,从生命哲学的视角看,《淮南子》体现出极为浓厚的道家气息,特别对《庄子》情有独钟,“源引庄子思想资料特多”[2]26,而且内容也“尤与庄子为近”[3]366。但是,《淮南子》生命哲学并非只是继承,而是有所扬弃,对《庄子》之“游”的思想汲取与改造尤为如此。
“游”在《庄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地位,被有的学者看作是““庄子哲学思想的灵魂”,能够充分体现出《庄子》思想的“生命志趣”与“精神传统”[4]69。《庄子》是以“游”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命状态来追求的,“以游无穷”[5]17、“游乎四海之外”[5]28(《庄子·逍遥游》),寄托着其对生命主体所能达到精神自由境界的憧憬。“游”在《淮南子》中有着充分的继承,成为其生命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淮南王刘安等人对《庄子》之“游”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同,因为处于西汉王朝的政治转型之中,所以他们在政治上面临着各种“内外矛盾的总爆发”[6]102,尤其深切地感受到来自中央政权的政治压力,所以刘安等人渴望在汲取《庄子》思想资源的过程中实现自己“在压迫和危机感下对精神自由的祈向”[1]121。由此,“游”在《淮南子》中具有了独特的思想地位,成为恢复“人之本然”的自由状态[7]6的必然途径,被刘安等人极力地推崇,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淮南子》生命哲学的思想标志。
一、对《庄子》之“游”的思想扬弃
“游”作为《淮南子》生命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淮南子》一书中有着比较频繁的使用。只要涉及有关生命存在的思考与关怀,就会出现“游”的身影。《淮南子》对“游”的认识和理解承袭于《庄子》。在《庄子》中,《逍遥游》居于首篇,而且经常被学者认为是能够真正理解《庄子》思想真谛的关键所在。而在《淮南子》中,《庄子》的“逍遥游”思想的影响明显而深刻,成为其生命哲学着力汲取和融合的思想资源。因此,“游”的思想实际上成为沟通《淮南子》与《庄子》的生命哲学的桥梁,体现出二者在思想上极不寻常的内在联系,而且《淮南子》之“游”从精神上也“继承了庄子豪放的气魄,包容六合,雄视万物,显示了道家的博大襟怀”[8]287。
“游”在《庄子》生命哲学中有着特定的思想内涵,而且常与神仙化的“真人”(有时为“至人”)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一种超越性的生命意识和追求。《淮南子》承袭了《庄子》对“游”与“真人”的思想认识,也习惯于从生命哲学的视角出发将“真人”塑造为能够体现出“神仙出世的理论”[9]539的生命主体。“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藩”[10]227,“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毁而不能惊也,大风晦日而不能伤也”[10]228(《淮南子·精神训》)。这种对“真人”的艺术化描写,与《庄子》中“游乎四海之外”,“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5]30(《庄子·逍遥游》)的“真人”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5]96的“至人”(《庄子·齐物论》)具有思想的一致性,甚至《淮南子》所用的文字都是从后者那里直接化用而来。《淮南子》对“真人”的推崇和赞扬,实际上是对《庄子》生命哲学中所体现的“精神解放而获得精神自由”[1]120的生命状态的肯定和向往,这也正是《淮南子》生命哲学的思想实质所在。
在《庄子》那里,“游”不仅是对生命理想状态的追求和向往,也是对现实世界的离弃和疏远,而“真人”作为理想的生命主体就应该始终能够用超越的精神对待世俗的一切事物,体现出“物莫之能伤”[5]30。(《庄子·逍遥游》)的内在品质。因此,《庄子》认为凡是理想的生命存在,都需要实现“游乎尘垢之外”的“妙道”[5]97(《庄子·齐物论》)。这种对现实世界的生命态度,也得到了《淮南子》的继承。实际上,淮南王刘安等人对此而言,有着更加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感受。因为站在诸侯王国的政治立场上,不论刘安本人,抑或是淮南宾客群体,都深感到来自中央政权的巨大压力,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所以他们对一种自由而解放的生命存在状态有着内在的迫切渴望,甚至有些时候会萌生出“离世倾向”和“出世成仙的冀求”[11]287。由此可知,《淮南子》生命哲学对《庄子》之“游”的接受与认同,在思想上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因为这种既渴望超越,却又深感束缚的复杂态度实际上真切地反映出刘安等人对自身现实政治处境的切身感受。他们从《庄子》中不仅得到了思想与精神上的慰藉,也获得了构建《淮南子》生命哲学的思想资源。
但是,《淮南子》生命哲学对《庄子》之“游”的汲取并非全盘接受,毫无变化,而是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改造,“带上了汉代的特点”[12]282,以适应于淮南王刘安等人的思想旨趣。在《庄子》中,作为“游”之生命主体的“真人”更多地体现出士人——知识精英的人格形象,虽然这种理想的生命主体有时会倾向于出世化、神仙化,但其身上较少体现出浓厚的“政治性”的气息。而且,这些“真人”所面对的生命困境主要来自于“物”、“我”之间,经常处于“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5]172(《庄子·人间世》)的纠结之中,而对于现实中剧烈的政治危机和压力却绝少敏感而深刻的生命体验。
与《庄子》不同,《淮南子》对“游”的思想阐发中流露出内在的政治意味,其所言“真人”、“至人”也时常表现出世俗君主的政治形象。“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烛十日而使风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天地之间何足以留其志!”[10]61“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适情而行,余天下而不贪,委万物而不利,处大廓之宇,游无极之野,登太皇,冯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中”[10]241-242(《淮南子·精神训》)。这里的“真人”、“至人”就与《庄子》迥然有异,虽然都是向往着无比自由的生命状态,但前者却透露出一定的政治倾向,在思想、精神上表现出强烈的控制欲望。只是,《淮南子》中的“真人”并不是现实君主的简单再现,而是寄寓着刘安等人特定的思想旨趣。在其眼中,“真人”、“至人”实际上成为理想统治者的人格形象。这样的理想君主一方面符合《庄子》超越的生命态度,能让自己的精神自由地“游”于“虚无之轸”、“无穷之野”,另一方面却又对世俗政治怀有一定的欲望,非但不采取脱离、逃避的态度,“还企图解决其中的问题”[13]132。因此,《淮南子》之“游”从生命哲学上无法与《庄子》简单地等同,虽然二者之间在生命主体的精神自由上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但就二者“游”的主体的实质而言,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客观地说,在这一点上,《淮南子》体现出《庄子》所没有的强烈的统治国家的政治欲望和理念,这是二者生命哲学在精神实质上的重要区别。
由于这种生命主体精神的内在差异,《淮南子》中所言“真人”就无法反映现实世界中一般士人的精神追求,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贵族性。在《淮南子》中,“真人”经常可以被替换为“圣主”、“明王”等表示统治者的概念,以显示出君主在政治上“闲居而乐、无为而治”[10]468(《淮南子·诠言训》)的治国理念。这种精神旨趣实际上和刘安等人的政治理想和生命追求相一致。刘安等人在现实生活中,就存在着兼顾政治与生命的两面性:一方面对“神仙黄白之术”充满兴趣,渴望“去尘埃之间”[10]676(《淮南子·泰族训》)的仙人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对权力政治充满着热情与期待,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成为“圣王”、“明主”,“玩天地于掌握之中”。这种两面性在《淮南子》中促成一种思想的张力,使得政治性、贵族化的精神气质在“真人”之“游”的生命状态中明显地流露出来,成为和《庄子》既相近、又相异的生命哲学。
总之,《淮南子》之“游”源于《庄子》,在生命哲学上彰显出一种自由超脱、“逍遥一世之间”[10]708(《淮南子·要略》)的精神追求。二者虽然对生命理想状态的追求有着一定的相近性,但由于生命主体发生内在精神的变化,使得二者最终在生命哲学上有所差异。这就是《淮南子》之“游”比《庄子》更显示出把生命理想政治化的思想倾向,也更具有贵族性。
二、寻求生命与政治一体化之“游”
对生命与政治的思考,是《淮南子》的思想核心所在。“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国之本也”[10]686(《淮南子·泰族训》),在《淮南子》生命哲学中,“心”、“身”与“国”原本就不需要截然分开,而生命和政治能够在理想的生命状态中实现应有的融合。《淮南子》所设想的生命主体是现实中的专制君主,在其看来,君主的生命存在完全可以获得一种精神的超越,能够“道以优游”[10]686(《淮南子·泰族训》)。在现实政治中,君主的生命追求也可以同其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相互协调、融合,二者并非相互矛盾而无法共存。实际上,《淮南子》从精神修养着眼,特别对君主在“治国”的同时如何实现“治身”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10]466(《淮南子·诠言训》),试图从生命哲学上实现生命与政治的一体化,将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融入到理想生命状态之“游”中。
追求人类生命存在的超越与自由,这是《淮南子》之“游”的内在精神。但是,《淮南子》生命哲学并没有如《庄子》一样将生命主体的现实政治性较多地去除掉,相反,却采取了在生命追求中积极融入自己的政治向往和理念的做法。历史地看,《淮南子》的这种思想认识合乎刘安等人的政治现实。刘安本人作为西汉的诸侯王,“好读书鼓琴,不喜猎狗马驰骋”,且“辩博善为文辞”[14]2145,具有相当的知识修养与才干,这在与他同时的诸侯王中并不多见。刘安对政治十分热衷,“欲以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14]2145,希望能够在现实中有所为。《淮南子》一书的出现就和他试图对西汉王朝的政治发展有所影响的意图密切相关,所以在他眼中《淮南子》是“刘氏之书”,是既“言道”,又“言事”,能够“纪纲道德,经纬人事”[10]700(《淮南子·要略》)的著作。因此,在《淮南子》中,对生命存在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没有单纯地停留在“治身”上,而是力求将政治性的内涵渗透进理想的生命追求中,达到“治身”与“治国”合一之“游”。“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10]2(《淮南子·原道训》),这最能体现出《淮南子》生命哲学将生命追求政治化的思想内涵。
《淮南子》之“游”对待生命与政治的思想态度是复杂的,具有两面性。将生命追求政治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将政治向往生命化则是其思想内涵的另一个方面。在《淮南子》看来,“身得则万物备矣”,“吾所谓有天下者,非谓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则天下亦得我矣”,“吾与天下相得,则常相有”[10]36(《淮南子·原道训》),因此《淮南子》所追求实现的“得道以御”,“虚己以游世”[10]468(《淮南子·诠言训》)的生命境界与君主自身的内在修养密不可分,“使舜趋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犹弗能保,何尺地之有”[10]496(《淮南子·诠言训》)。换言之,作为生命主体,君主应该在“治国”中融入“治身”的内容,而“治身”则要能够“与道为一”[10]36(《淮南子·原道训》),从心理、精神上不断地修养自己,实现政治向往的生命化。
那么,君主能够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实现政治向往生命化的目的,从而达到“道以优游”的理想状态呢?《淮南子》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具体认识:一是君主应该具有清净的心神。“凡将举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意清平,物乃可止”[10]353(《淮南子·齐俗训》),而且君主作为“得道之士”应该做到所谓的“外化内不化”,因为“外化,所以人人也;内不化,所以全其身也”,唯有如此,方能“与物推移,万举而不陷”[10]622(《淮南子·人间训》)。因此,《淮南子》从政治实践的角度,对君主的心理状态有所要求,试图将生命修养内在化于君主的政治心态之中。二是君主应该“虚己”和去“机械之心”。“机械诈伪莫藏于心”[10]245(《淮南子·本经训》),“圣人无思虑,无设储,来者弗迎,去者弗将”[10]469(《淮南子·诠言训》),只有“内修道术,而外不饰仁义,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10]60(《淮南子·俶真训》),才能实现“虚己以游世”的“圣人之游”。三是君主应该在政治上以“无为”的手段驾驭臣下。“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任人之才,难以至治”[10]278(《淮南子·主术训》),“明主之耳目不劳,精神不竭,物至而观其象,事来而应其化”[10]298(《淮南子·主术训》),“人主逾劳,人臣逾逸”[100]300(《淮南子·主术训》),“圣主在上,廓然无形,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10]668(《淮南子·泰族训》),因此只有君主懂得“虚无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10]61(《淮南子·俶真训》)的道理,以“无为”的手段统治群臣,才能在政治上驭下有术,立于不败之地。总之,在《淮南子》看来,君主作为生命主体,其政治行为应该与生命追求相互结合,通过内在的心理状态的不断修养,达到“身得”而后“天下得”的根本目的。
综上,《淮南子》之“游”突破了生命与政治之间的隔阂与障碍,历史地扬弃了《庄子》之“游”的思想内涵,将生命追求与政治实践融合起来,实现了将生命与政治一体化的思想旨趣。因此,“游”的思想内涵在《淮南子》中变得更为丰富,成为刘安等人眼中政治主体能够通过自身修养与实践而达到的一种理想的生命状态。这种融合生命追求与政治实践的生命哲学,对秦汉时期的道家思想而言,也是一种历史的贡献,深化与丰富了其对生命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如果说《庄子》之“游”具有平民性、知识性的精神气质,那么《淮南子》之“游”则有所不同,始终流露出贵族性、政治性的精神气质。
三、走向信仰化的神仙之“游”
“游”在《淮南子》中不仅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化倾向,而且对“真人”、“至人”或“圣人”等生命主体实现这种理想的生命状态有着神仙化塑造的思想意识。虽然在《庄子》中已有这种情形,《淮南子》也是对前者在某种程度上的继承,但是,《淮南子》之“游”在进一步神仙化“真人”等生命主体的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生命信仰的意识却是比《庄子》那里更强的。换言之,对《淮南子》之“游”而言,对生命存在的关怀,已经不只是一种哲学性的思考和体验了,而是更多地具有了生命信仰的内涵。因此,《淮南子》之“游”与《庄子》之间除了政治化的差异外,同时还存在着生命关怀的信仰化的重要区别。
在《淮南子》之“游”中,“真人”超越世俗,游身世外,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命主体,他们都具有极强的非世俗性和人格上神仙化的特征。“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淮南子·诠言训》)“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徜徉于尘垢之外,而逍遥于无事之业”[10]227(《淮南子·精神训》),“以死生为一化,以万物为一方,同精于太清之本,而游于忽区之旁……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无间,役使鬼神”[10]229-230(《淮南子·精神训》)。“古之真人,立于天地之本,中至优游,抱德炀和”[10]50(《淮南子·俶真训》)。《淮南子》这里所说的“真人”,已不再是世俗之中的普通士人,而是能够脱离现实桎梏的具有超越性的生命主体。而且,“真人”对于现实世界的事物持有否定和抛弃的态度,将自身的“性命”是否能够获得“中至优游,抱德炀和”的理想状态放到生命实践的首要地位来对待。“圣人”在《淮南子》中有时与“真人”一样是以非世俗的形象出现的,而且身上也显示出人格的神仙化。“圣人内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寻九天,横廓六合,揲贯万物,此圣人之游也”[10]60(《淮南子·俶真训》)。这里的“圣人”与“真人”在思想内涵上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就是《淮南子》特别强调了“圣人”对“仁义”的排斥和对“道术”的推崇。但有时“圣人”在《淮南子》中又会表现出一定的现实世界眷恋,缺少“真人”那种完全超脱的精神。“圣人虽有其志,不遇其世,尽足以容身,何功名之致也!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则有以任于世矣”[10]60(《淮南子·人间训》)。但不论是“真人”,还是“圣人”,都极力脱离世间事物的束缚,追求超越性的生命状态,实现精神之和。因此,“真人”、“圣人”在《淮南子》而言,都已被视为非世俗的、超越性的生命存在,被赋予了神仙化的理想人格,所以只有他们才能在身体和精神上达到“忘肝胆,遗耳目,独浮游无方之外”[10]51(《淮南子·俶真训》)的生命境界。
《淮南子》之“游”中的“真人”等对宇宙、万物都有着深刻的生命体验,其对“游”的理想生命状态的追求与实践都建立在这种对现实世界的哲学反思之上。“古之真人,立于天地之本,中至优游,抱德炀和,而万物杂累焉,孰肯解构人间之事,以物烦其性命乎?”(《淮南子·俶真训》)“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为欢不忻忻,其为悲不惙”,“遗物而与道同出”[10]34(《淮南子·原道训》),对于“真人”等而言,天地是其存在的理想环境,而世俗世界的一切欲望都是生命的负累,只有“穷而不慑,达而不荣,处高而不机,持盈而不倾,新而不朗,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才能在精神上“随天地之所为”[10]39(《淮南子·原道训》),而“与道沉浮俯仰”[10]42(《淮南子·原道训》)。“真人”需要在意的并不是什么功名利禄,也不需要讲求什么世俗的仁义、智慧。“有真人然后有真知”[10]58(《淮南子·俶真训》),因为世俗之人“所立身者不宁”,“所持者不明”,所以他们无法像“真人”一样获得对生命与世界的真实的洞察和认识。“真人”由于具有明了“真知”的超凡能力,所以也就能体验不同于普通人的生命状态,“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圄”(《淮南子·俶真训》)。对“真人”而言,其精神是处于虚无之中的,是游于天地之间的,是徜徉尘垢之外的,真正需要关心的事情只是如何使自身的精神合乎“道”的规律,“唯体道能不败”[10]53(《淮南子·俶真训》),以此在治身、养性的过程中实现永久的长生,如同王乔、赤松子那样的仙人进入到“乘云游雾”的生命状态。
“真人”在实现《淮南子》之“游”的生命境界时,对生命存在实际上具有了一种自我反观、寻求超脱的信仰意识。生命对“真人”而言,不仅是一种具体的存在方式,而且具有超越现实世界的局限性。虽然《淮南子》中的“真人”十分讲究养生之道,探究不死之术,“闭四关,止五遁”,“闭四关则身无患,百节莫苑,莫死莫生,莫虚莫盈”[10]260-261(《淮南子·本经训》),表面看起来似乎仍留有一些世俗的烟火气息,但实际上真人在精神上是彻底超脱的。他们对于身体的关注根本地源于对生命本质的追寻,他们的治身、养性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其目的都在于陶冶自身的心性,“遗物而与道同出”(《淮南子·原道训》)。正是“达于道者,返于清净”[10]53(《淮南子·原道训》)的生命状态中,“真人”才能实现“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的理想追求。因此,当“真人”进入到精神之“游”的状态时,其生命意识实际上已转化为一种内在的生命信仰。对“真人”而言,这是实现生命超脱,进入“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10]250(《淮南子·本经训》)的自由状态的必然途径。
《淮南子》之“游”与《庄子》相较而言,在生命意识上是十分相近的,但是在形成初步的生命信仰上却有着很大的区别。虽然《庄子》之“逍遥游”也体现出一种自由、超脱的人生境界,也是将“真人”、“至人”或“圣人”等视为实现理想的生命状态的主体存在,但总的看,《庄子》之“游”更多地是反映作为知识精英的“士人”所具有的生命意识,是对现实世界中生命主体所感受到的种种“痛苦的体验”[12]50的一种内在而生的“精神反抗”。虽然《庄子》“热爱生命”,“高情远趣,创造一个辽阔的心灵世界”,然而“他的高超秀脱,内心却有其沉痛处”[16]130。因此,《庄子》对现实世界的局限性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以此来彰显出“游”的生命状态对士人精神所具有的解脱的意义。但《庄子》之“游”缺少《淮南子》那样从生命意识走向生命信仰的历史冲动,“真人”等理想的生命主体在人格上的神仙化意味也没有后者强烈。而《淮南子》对“游”的生命思考则比较充分地显示出“真人”等生命主体的自我解脱的意识,不仅在精神上强调对生命存在之“道”的反思,而且在养生上受到神仙方术的影响而讲求不死之术,这都促使《淮南子》之“游”不再是简单地承袭于《庄子》,而是向着“不愿做人而要做神仙”[9]542的信仰方向有所变化和发展了。
总之,“游”在《淮南子》中具有生命意识信仰化的思想倾向,这对“真人”等生命主体的存在而言,是根本的自我解脱之路。《淮南子》对“游”不同于《庄子》的诠释,折射出秦汉时期随着黄老道家的历史发展而逐渐萌生的生命信仰意识的增强。虽然《淮南子》中生命信仰的产生与发展还是初步的,并不成熟,但其中已经开始表现出生命的自我解脱的思想倾向,在“世俗的贵族思想体系中注入了生命关怀和生命自救思想”[17]88。应该说,这是《淮南子》之“游”与《庄子》之间历史性的差异,也是前者对后者进行思想扬弃的结果。
“游”是《淮南子》生命哲学中既充满想象力,又极具思想内涵的核心概念之一。从《庄子》以来,这一概念就获得了思想和精神上创造性的阐发,但作为“秦汉道家最成熟的著作”[12]282,《淮南子》并没有停留在《庄子》已有的诠释上,而是进一步给予改造和发展。《淮南子》之“游”所内含的政治化、信仰化的思想倾向,不仅意味着“游”作为道家的生命理想在西汉时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且也折射出那个时期“一种知识化和贵族化的宗教信仰”[17]89在逐渐的萌生过程中,而这正是后世道教等宗教出现的历史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