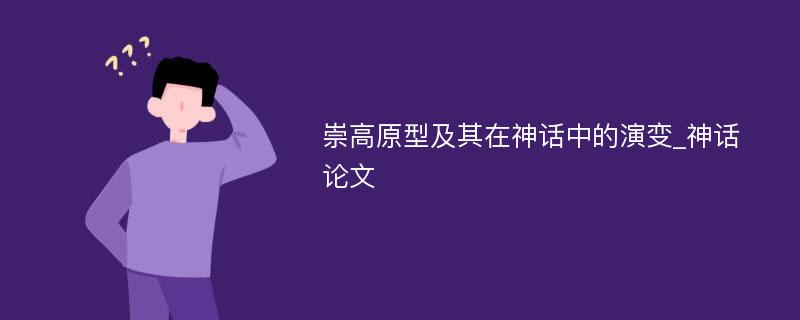
神话中的崇高原型及其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型论文,崇高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03)06-0008-05
如果说在神话时代的初期,人类由于缺乏自我意识而与自然融合一体,形成了二者之间的原始和谐格局,那么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确立,人作为主体已初步意识到同客体自然的分离和对立。自我意识的确立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是人类区别于其它物种,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且因而异于一般自然,那由于人知道他自己是‘我’,这就无异于说,自然事物没有达到自由的‘自为存在’,而只是局限于‘定在’[的阶段],永远只是为别物而存在。”[1]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本质,人只有具备了自我意识,才表明人是一种自为的存在物,而不只是一种自在存在物。
人的自我意识的确立使人具有了对象意识,自然作为人的对象是不同于人的异己存在。在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的格局中,原始先民的实践力量相对于自然力量而言显得十分薄弱,后者处于强势地位。此时,二者原有的和谐格局被打破,人对自然的亲和转为人对自然的敬畏。在神话时代的人类社会中,人类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于社会,而是来自于自然。神作为未知的自然力的象征,对人类具有极大的威慑作用。这种威慑力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始和谐格局中,人由于缺乏自我意识而未认识到这一点。而到了人意识到自然的异己性,认识到后者对自己的威胁,二者力量对比的悬殊使人感到自己的渺小,于是求助于神以超越自己的渺小,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这就形成了原始崇高。而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正是形成崇高原型的一个前提条件,它使人产生对崇高客体自然的敬畏,从而树立起人作为崇高主体的地位。
人类社会初期,人的实践力量十分有限。自然作为人的对象存在,在原始先民那里主要表现为一种非实践形式的对象,由于二者之间力量对比的悬殊,人还不可能真正地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自然身上,在强大对象的异己力量面前人感到更多的是恐惧,“当恐惧占上风,而这种尚未明确到足以使人采取适当的防御措施,从而发挥人类自我保扩本能时——无法预测的威胁,如飓风、地震以及漫漫长夜、无底深渊,毒蛇闪亮的目光,老虎的无敌威力——在这种场合,人类的想象意识便堕入了对于陌生事物的原始恐惧之中,他们将其视之为‘全然异己’。”[2]自然的强大与人的渺小之间的强烈对比,人类对“全然异己”的自然的恐惧,形成了原始崇高的一个首要条件——恐惧意识。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构成崇高,因为崇高最终象征的还是人超越于自然的一种精神状态。因此,人必须求助于一个更强有力者以同自然相抗衡,超越自身的渺小而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人类由于自身力量的孱弱,是不可能充任这一更强有力者的。原始先民的神话思维方式既不能正确地认识异己的自然,也不能正确地了解自身,因而通过幻想的形式虚构出无所不能的神祇,将自己的力量投射到神身上。凭借神人合一的力量去与自然力量相对峙,从而获取战胜自然的信心,这样就形成了神话中的原始崇高。在神话的崇高原型当中,既蕴含了人的力量,但更多的却是异己的自然力量,因此人的崇高感首先是一种恐惧感,不过由于神祇作为人与自然二者力量的中介,人对自然力量的恐惧便转化为对神的威力的恐惧,因而能够由恐惧而敬畏,进而上升到对神的崇敬,并在这种崇敬感中获取人自身的崇高自豪感,在原始崇高中,“人的个体正是从这种对万物虚无的承认以及对神的崇敬的赞扬里,去寻找自己的光荣、安慰和满足。”[3]人对神的崇敬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凭借神这个中介来观照自身,在神身上发现自己相对于崇高的客体——自然所具有的崇高主体精神上的自由。
表面看来,人对自然的这种“精神胜利法”还不如人同自然之间的原始和谐关系。但原始和谐并不是一种自由平等的和谐,人只是由于自我意识尚未确立而于无意识中与自然处于浑然不分的和谐之中,人在本质上是不自由的,是依附于自然的。在这个和谐格局中,人与其它的物种在同自然的关系中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人具有自我意识的潜在可能性,而其它物种则不具备。但正是由于人类具有自我意识的可能性,才能在物竞天择的生命进化过程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长”这样的佼佼者。人类从原始和谐的迷幻中觉醒过来,发现自然的异己性,这对于人类的发展而言不啻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虽然它不可避免地给人类带来了最初的创痛——人对强大自然力量的恐惧与敬畏,而这是人类最终将自然的异己性对象化为属人性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必经阶段,历史从来都是螺旋上升而非直线前进的。因此,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原始崇高在原始先民的社会中是一个更高于原始和谐的阶段。
神话中崇高原型的实质就是人类“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4]因此,原始崇高并不是实践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体现,而只是想象状态中崇高主体对崇高客体精神上的超越。原始先民在想象中借助神的力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所以原始崇高所表现的乃是虚幻的神的力量之崇高。
在古希腊神话中,神的力量之崇高表现得十分突出。根据赫西俄德《神谱》的说法,天神乌兰诺斯与地神该亚相结合生下了泰坦诸神、库克罗普斯(独目巨人族)以及复仇三女神。这些奇形怪状的神祇实际上象征着大自然的原始暴力。原始先民的微弱力量根本不可能同这些强大的自然力量相抗衡,前者在后者面前感到恐惧与颤栗。只是到了宙斯战胜了泰坦诸神,确立了奥林匹斯神族的统治地位之后,神才脱离了自然性而获得了人性。奥林匹斯神族对泰坦神族的取代,表面上看来只不过是诸神之间的权力倾轧,然而在深层上却寄寓了人类借助人格神的力量以征服大自然原始暴力的崇高精神。因此,“崇高不存在于自然的事物里,而只能在我们的观念里寻找。”[5]也就是说,崇高不在客体对象身上,而存在于主体人的精神状态之中。
希腊神话中表现人借助神以征服自然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普罗米修斯的盗火神话与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英雄业绩神话。
古希腊神话中的崇高是通过人格神的力量之崇高表现出来的。由于人格神与人同形同构,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神灵,他们同样具有人的七情六欲。所不同的是他们比人更有力量,是相对于人类而言更为强大的“超人”。因此,希腊神祇身上所体现的崇高具有浓厚的现世精神。这种崇高与其说是虚幻的神之力量的崇高,不如说是有待实现的人的崇高力量的萌芽,它的胚胎在神话的沃土中潜生暗长,终有一天它会破土而出,将崇高从“超人”的神身上移置到平凡而真实的人身上,人将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战胜自然,从而确立人的崇高主体地位。希腊神话中的崇高原型开创了西方文明外倾型进取精神的此岸世俗崇高传统的一极。
希伯莱人的《圣经》既是基督教的宗教经典,同时也是反映犹太先民生存状况的神话集大成之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圣经》首先是作为神话而存在的,只是后来由于被宗教所利用才成为宗教经典的。表现和颂扬神的崇高是《圣经》神话最突出的主题。如果说在古希腊神话中表现神的崇高力量神祇为数众多,那么在《圣经》神话中象征崇高力量的则只有唯一的一位神——上帝。在《圣经》神话中,上帝是创造世界万物向无所不能的神祇,任何事物与之相比都显得那么渺小无力。“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6]相形之下,上帝仅以言说的方式获取光明比普罗米修斯历经艰辛盗取天火更显崇高伟大。无怪乎朗吉弩斯在其《论崇高》中将这句话作为崇高的最突出的例子加以引用。上帝不仅首先创造了光,而且随后创造了空气、陆地、海洋以及动植物,这些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人类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为自己创造这些生存条件的,便想象是全能的神的恩赐,“神是宇宙的创造者,这就是崇高本身的最纯粹的表现。[3]上帝作为造物主,世界的一切都来源于他,除他之外,全体被创造者都是有限的,受局限的,都不是自为存在的,而只是为显示上帝的伟大而存在的。万物的有限与上帝的无限之间的强烈对比,更加衬托了上帝的无比崇高。虽然世界万物与上帝的崇高比较起来都显得无限渺小,但人类作为上帝的选民,相对其它物种而言又显得位高一等,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像而创造出来的。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帝是这样规定的,“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的一切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莱蔬一样。[7]人凭借神的谕示而凌驾于万物之上,成为自然的主宰。然而,人只有在依靠神的力量而非自身的力量而获得的这种崇高地位,说明了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有限而不可能真正支配自然,因而通过对神的尊崇,因神之力而在心理上获取一种支配与超越自然的崇高精神,“所以涉及人方面的崇高是和人自身有限以及神高不可攀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的。”[3]
黑格尔认为《圣经》是神话,尤其是其中的《诗篇》是真正崇高的典范。贯串《诗篇》始终的核心思想是对上帝正义和公道的崇高精神的赞颂。人在生活中颠沛流离,困窘蹇塞,面对未知的力量倍感恐惧。人自身的力量未能将自己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唯有从神的力量中寻求庇护。在原始先民眼里,上帝是公正的崇高力量的化身,每当人类面临危险,只要虔诚地向上帝祷告,便能化险为夷。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人对神的崇拜归结为盲目的信仰,须知在远古时代,人类落后的生产力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对自然进行对象化的,但人类的自我意识使人在面对异己力量的威胁时又不可能无动于衷,在这种情况下,寻求一个第三者作为平衡的中介对于人类而言是十分有必要的。只有这样,人才能在心理上获取战胜异己力量的信心,“他们尽情地向神,向一切值得赞赏的对象,抛舍自己,但是在这种自我抛舍中却仍然保持住自己的自由实体性,去对付周围的世界。”[3]人们虽然对神充满崇敬之情,但并未因此而变成神的奴仆,丧失人之为人的“自由实体性”,人向神“抛舍”自己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实现超越未知的自然力量的目的。因此,人颂扬上帝的崇高最终还是为了表现人类自身的崇高。
《圣经》中希伯莱神话所表现的崇高完全就是上帝的化身。同奥林匹斯的至上神宙斯相比,上帝更显得“神气”十足。宙斯是一位充满人情味的神,而上帝则显得似乎不近“人情”,人神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导致了人神殊途,二者之间的间距形成了上帝的崇高与人的卑微。上帝就是正义与公理的化身,他通过奖善惩恶而使人类产生敬畏感和原罪意识,人们只有在“静观”的崇仰之中才能认识到上帝的崇高与伟大。人类只有经受住上帝的考验,通过趋向神,跨越尘世的界限,在彼岸的天国中分享上帝的崇高。正是这种彼岸崇高的特征为将希伯莱神话改造成宗教经典提供了依据。《圣经》神话中的崇高原型开创了西方文明内省型信仰精神的彼岸宗教崇高传统的另一极。
中国古代神话中华夏先民“借想象以征服自然”的崇高神话也不少。在后羿生活的年代,天上曾经有十个太阳,过于充足的阳光造成了普遍而持久的干旱,为了将人类从死亡的边缘拯救过来,后羿临危受命,射下了其中的九个太阳,从此,唯一幸存的太阳对人类就温和多了。另一个同太阳有关的“夸父逐日”神话,记录了敢与太阳试比“速”的夸父,最终因道渴而死的英勇壮烈的崇高事绩。这两则同太阳作斗争的神话虽结果殊异一胜一负,但都表现了华夏先民在同强大自然相对抗过程中的崇高精神。不畏火热太阳的人们也同样不怕水深的大海,“精卫填海”的神话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人定胜天”的自信。娇小力弱的精卫在浩淼无垠的东海面前就如同沧海之一粟,但就是这似乎可不屑一顾的小精灵却矢志不移地衔着木石,要将东海填平。二者外形上的悬殊对比更加反衬出了精卫精神上的崇高。以上这些神话共同表现了华夏先民在远古时代借神话想象征服自然的崇高气慨。
无论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崇高,《圣经》神话中的崇高,还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崇高,它们之间的一个共同本质在于这种原始崇高的实质乃是一种精神力量的崇高而非物质力量的崇高。因为神身上所体现的物质力量的崇高是非现实性的,仅是人类美好愿望的想象性表现,人类借虚幻的神的物质力量的崇高以表征自己精神力量的崇高。虽然精神力量的崇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能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它有赖于人的强大物质力量即人的生产力水平的相对发达,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的一点是,对于原始先民而言,他们的物质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征服自然的,唯有“借想象力以征服自然”,这样就形成了神话中的崇高。原始崇高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使人类在面临困难与危险时能够战胜自己的恐惧,对自己的潜在力量充满信心,“即使它不能达到意欲的实际目的,即使它不能实现人的希求,它也教会了人相信他自己的力量——把他自己看成是这样一个存在物:他不必只是服从于自然的力量,而是能够凭着精神的能力去调节和控制自然力。”[8]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神的崇敬与信仰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中的自我信赖的最早最鲜明的表现,在此人不再感到自己是听凭自然力量的摆布了,在神的崇高中人超越了自然力量而在精神上达到了崇高境界。
虽然“崇高”这一范畴最先由谁提出尚难盖棺定论,但朗吉弩斯在其《论崇高》中对“崇高”的论述却是最早引人注目的。尤其是他将《圣经》希伯莱创世神话中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作为崇高的最突出的例子广为后人引用。朗吉弩斯援引希伯莱创世神话作为崇高的范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深受神话中原始崇高影响的必然结果。在朗吉弩斯看来,崇高的本质是心灵的崇高,“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恰到好处的真情流露那样导致崇高;这种真情通过一种‘雅致的疯狂’和神圣的灵感而涌出,听来犹如神的声音。”[9]由于人的心灵同神有相似之处,所以人的心灵因分有神的崇高而变得崇高起来。由此看来,朗吉弩斯所谓人的心灵的崇高与神话中人通过对神的尊崇而获取的崇高感仿佛如出一辙。但与此同时,朗吉弩斯所说的崇高已不完全是一种虚幻的崇高,而是一定程度上基于自信的崇高。人一方面承认客体自然的崇高,但相形之下,人作为崇高的主体比崇高的客体更加崇高,“大自然把人带到宇宙这个生命大会场里,让他不仅来观赏这全部宇宙的壮观,而且还热烈地参加其中的竞赛,它就不是把人当作一种卑微的动物;……一个人如果四面八方地把生命谛视一番,看出在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伟大的和优美的都巍然高耸着,他就会马上体会到我们人是为什么生存世间的。”[10]崇高伟大的自然己不再是令人恐惧的对象,而是激发人类与之竞争的存在物,人类通过同自然的竞争而确证自己的更为崇高伟大。朗吉弩斯的崇高理论并不完备,它一方面还受到神话中原始崇高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又是近代崇高的萌芽,处于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朗吉弩斯《论崇高》的意义在于“关于祟高的理论所以在近代思辨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大概也应因归于这部著作。”[11]
近代崇高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最初是由英国美学家博克提出来的,这看来不是偶然的,固然一方面,他可能受到朗吉弩斯崇高概念的影响,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提出这一概念时的深刻历史背景。英国是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近代工业社会的开始。博克作为这次划时代革命的见证人,亲眼目睹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恢宏壮阔的历史场景,他不仅感受到大自然的宏伟壮观,更认识到人类自身的伟大崇高。博克首先肯定了作为崇高客体的大自然的重要性,“凡是能以某种方式适宜于引起苦痛或危险观念的事物,即凡是能以某种方式令人恐怖的,涉及可恐怖的对象的,或是类似恐怖那样发挥作用的事物,就是崇高的一个来源。”[12]博克从心理上说明了崇高的缘由,它必须使人感到恐惧,但如果人不能最终超越恐惧则不能形成崇高,人类只有“在面临恐怖的对象而没有真正危险时,这种自豪感就可以被人最清楚地看到,而且发挥最强烈的作用,因为人心经常要求他所观照的对象的尊严和价值或多或少地移到自己身上来。”[12]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崇高主体人方面的崇高,这才是真正的崇高。博克认为崇高的形成是由于人将对象身上的崇高移置到了自己身上,但他并没有说明这种崇高转换机制的深层原因。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博克十分强调感性经验的重要性,当然不会从先验的观念出发,认为人是通过对神的崇敬而将自然的崇高转换到人身上。由于经验主义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博克虽没有明确地提出人的崇高源于人的实践力量的崇高,但他于潜意识中无疑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人类并不是由于恐怖对象对自己不构成威胁就能产生崇高感,在这种情况下,人只会产生一种苟且偷生的侥幸感。崇高之所以会从自然身上转换到人身上,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的实践力量已足以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自然身上,将自然的异己性转化为属人性。自然力量的崇高是不可否认的,但相形之下人的力量显得更为崇高,人的崇高超越了自然的崇高,因此,真正的崇高最终还是归属于人。
博克关于崇高的看法对康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康德也认为崇高源于自然,他将自然的崇高分为数学的崇高与力学的崇高两种。关于数学的崇高,康德认为,‘但是假使我们对某物不仅称为大,而全部地,绝对地,在任何角度(超越一切比较)称为大,这就是崇高”,“崇高是一切和它较量的东西都是比它小的东西。”[5]自然在数量上的巨大超出了人的感知能力,人由于无法把握它而感到震惊和惶恐,这样就形成了自然在数学上的崇高。不过在康德看来,数学的崇高只是暂时的表象,真正的崇高还是体现在人身上,“于是那自然对象的‘大’,——想象力在把它全部总括机能尽用在它上面而无结果——必须把自然概念引导到一个越感性的根基(作为自然和我们思维机能的基础)。这根基是超越一切感性尺度的大,因此它不仅使我们把这个对象,更多的是把那估计它时候的内心情调评判为崇高”,“真正的崇高只能在评判者的心情里寻找,不是在自然对象里。”[5]作为崇高客体的自然在数学上的崇高激发起崇高主体人的想象力,人对自然的观照使人产生同自然相协调的崇高感,崇高因而从自然身上移置到了人身上。关于自然力学上的崇高,康德是这样界定的,“自然,在审美的评赏里看作力,而对我们不具有威力,这就是力学上的崇高。”[5]自然作为崇高的客体必须具备力量,但这种力量必须在一定的度内,即它既要使人产生恐惧,又不能对人形成真正的威胁。符合这个度的自然对象之所以是崇高的,是因为“它们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力量越过平常的尺度,而让我们在内心里发现另一种类的抵抗的能力,这赋予我们勇气来和自然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5]在康德看来,自然界威力的崇高只是一种假象,因而人的精神力量足以与之相抗衡,因此自然力学上的崇高只是作为人的精神力量崇高的附庸而存在的,真正的崇高只能是人类精神的崇高。康德作为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研究的对象是人的主观意识而非客观存在的事物。因此,他对崇高的研究虽然是从客观自然对象出发,但自然对他而言只是达到研究目的工具和手段,他真正要研究的是人对自然对象的认识。所以在他看来,自然的崇高只是形成人的精神崇高的前提条件,后者才是真正的崇高。作为一个理性唯心主义者,康德突出了人的心灵与精神方面的主体性,这与神话中人非理性的虚幻精神主体性是完全不同的。毋庸置疑,崇高的实质确实是一种超越精神的表现,但这种超越精神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根源于人类实践力量的崇高,只有人类的实践力量克服了自然力量的威胁,人在精神上才能产生崇高的气慨。康德时代的人类社会已有足够的能力在自然面前表现出自己的崇高。因此,康德虽然是从心理角度提出自己的崇高概念,但他无疑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之下孕育了近代崇高的内涵。
以博克和康德为代表所提出的近代崇高概念,深深地留下了时代的烙印。无论是博克,还是康德的崇高概念,都将人类的崇高仅仅归结为心灵与精神方面的崇高。因而表面看来,近代崇高同神话时代人的精神崇高并无什么区别,然而实际上,二者表面的相似性背后隐匿着实质性的根本差异。近代人类精神的崇高有着鲜明的历史背景,其是以工业革命当中人类强大的物质实践力量为前提的。相反,原始崇高却正是在缺乏这种力量的情况下产生的。前者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因而是真实的;后者建立在想象的幻境中,因而是虚幻的。以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为标志而拉开了人类近代社会的帷幕,在农业社会所形成的人同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也随之消解。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也同时极大地增强了人的力量,人与自然之间力量的消长变化导致了二者关系的戏剧性变化,人类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摆脱了对自然的依附而成为了后者的主宰。人在征服自然的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无限力量赋予了人以自信以及人类超越于自然的崇高感。神话时代人类“借想象以征服自然”的历史已一去不返,人类在自然身上确证了自己本质力量的崇高,这种崇高不仅是精神力量方面的,而且也是物质力量方面的,并且精神力量的崇高不再是通过对神的信仰而是通过对自身实践力量的自信而获得的。近代社会是以人类的崇高作为显著标志的。
收稿日期:2003-0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