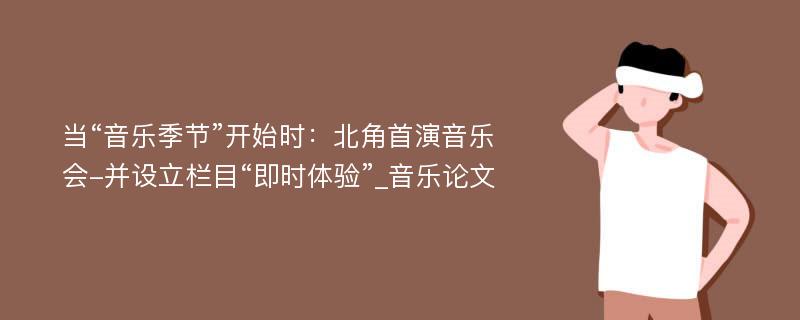
当“音乐季”启动之际:北交首演音乐会——并以此设栏“临响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乐会论文,经验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专栏前言
应《音乐爱好者》之约,在此开设专栏,并以“临响经验”命名。
所谓“临响经验”,说白了,就是指亲临音乐会现场进行批评,并由此成就一种经验。显然,这种临场批评,一方面,是对作品的诠释,对演奏的品味,以及对技术文本与风格样式的读解;另一方面,也是对主体经验的再度体验,无论是已有经验的预设,还是新生经验的形成。因此,我又把它看作为是一次文化的还原。毫无疑问,音乐会并非是某个部位的单一动作或者行为,而是一种规模作业,因为它必须由不同元件来共同组构,并且,需要不同功能的互相协同。由此前提,对处于音响发生现场的经验而言,不仅有自身的内在积累,而且,还有外向的投射;即以自身的现实设入,参与作品的真实存在。因此,“临响经验”的再一个策略,就是“重返音乐厅”——尽可能祛除笼罩与弥漫在音响之外的“精神遮蔽”,从而,真正亲近实际发生的音响。
需要说明的是,此“临响”术语,系笔者依据医学术语“临床”所杜撰,并摹其叙事模式。“临床”作为现代医学得以进步的重要途径与必要手段,已然无疑。此用“临响”,其用意与“临床”相应,一方面,直接针对人的聆听行为(以“耳闻”作为第一且根本路径,并由此涉及听赏、欣赏、鉴赏各个层面);另一方面,是将其作为音乐人文叙事得以推展的重要途径与必要手段,来予以“锁定”,进而,依此建构起非人文经验所不可替代之技理常规与学理范式。
作为“重返音乐厅”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以感性审美的姿态定位,并用“大音乐”(Musics)的观念重新审度具体实在的音乐。所谓“感性审美姿态”,就是以音乐的方式存在,以音乐的语言作为居住之家。所谓“大音乐”(冠以大写字头,并加缀复数形式),不仅显示音乐的多样化与相互接近的意义,而且,也是表示对人文化极限的再度扩张与延伸。于是,之所以设“临响”为根本前提,其理由在于,无论就人的特定感官(听觉系统),还是就人进行创造所凭借的约定语境(历史文化条件),或者就人的创造物(音乐)所依存的限定媒体(音响),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真实感抑或虚拟性,都必须将“临响”视为绝对条件。因此,作为“临响经验”,将包括所有于音乐之中者——立美性质的创意,审美性质的诠释,泛美性质的接受,以及由“立美—审美”复合一起,并经由“主体意向”而最终成型的“客体作品”。
遂,以“临响经验”冠之,并为“音乐厅还原”辩护。是以北京交响乐团'98音乐季首演音乐会为鉴。
基本情况预设:
●名称:北京交响乐团'98音乐季首演音乐会
●时间:1998年3月18日晚19时30分
●地点:北京音乐厅
●上演作品:[意]威尔第:歌剧《西西里晚祷》序曲/[俄]柴科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Op.35/[德]布拉姆斯:《E小调第四交响曲》Op.98
●加演作品:[德]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六号》/[中]方可杰:管弦乐曲《大起板》/[德]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五号》
●指挥:谭利华
●独奏:吕思清
●演奏:北京交响乐团
●座位:楼下5排32座
“临响经验”实录,并相关批评
毫无疑问,以上基本情况预设,除了对读者作一个交待外,对一个临场与现实音响融为一体者,不可不谓之一种定位的必须。尤其,末项“座位”之设,更具有现场存在之意义。就以此为开启,我的座位在整个音乐厅当中,不仅靠前,而且靠边。说实在,是一个不很理想的位置,无疑,受响面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尤其担心听赏像布拉姆斯这样的作品,会打比较大的折扣。
不过,我的担心不久就被乐队的实际音响判为多余。果然,刚刚接受过考核与改革重组洗礼后的北京交响乐团,尤其,当晚的演出是该乐团推行“音乐季”制度的首演,真是不同以往,尽管威尔第歌剧序曲《西西里晚祷》的第一组群音响,由于乐队面对几乎满座的音乐厅(其中,除了捧场官员外,更有大批音乐行家)有些许紧张,而显得有一点拘束(我觉得,更像是一种期待时的内心颤动),但不同器乐声部能比较有控制地奏出的,类似“命运敲击”式的短小动机音型(不仅独具威尔第音乐的风格特色,而且,可视为威尔第配器技法的一张底牌,在此,无疑具有音响结构的逻辑意义),使乐队逐步进入有序状态。其实,但凡老练的听众,都会因此而有这样一种期待的颤动,况且,作为“音乐季”首演,周围的一切都好像进入了一种“仪式”开始前的凝固,甚至,连空气都仿佛被一种神秘所笼罩,所弥漫。于是,这第一个音,不仅对台上整个乐队,对谭利华,而且,对听众席中的李德伦、吴祖强,以及所有的爱乐者,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一刹那,骤然显得是如此的重要和珍贵,以至于难以承受“尘埃”之轻。谢谢台上的音乐家,当第二组群音响开始主题呈示,并接着进入乐队全奏(这往往是乐队调整自己的最好时机)之时,台上台下的人们,似乎都进入了最佳状态。于是,在期待的颤动过去之后,便自然随着乐曲的持续而生发出真正的艺术激动(根本有别于前者,因整体心理紧张而造成局部生理障碍)。一般来说,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交响乐团,必须具备足以驾驭音响运动的“弹性”能力,也就是说,要有足够幅度的伸缩起伏。威尔第的这首序曲,应该说从作品本身看,无论在速度、力度,还是音域的极度扩张,或者高潮的推进,等等方面都有比较充分的展示。由此,作为一首音乐会序曲,可以说已成为一首世界乐坛所共同保留之“序曲”。就此而言,这场演出算是合格的,尤其管乐声部,不论是独奏部分还是整体的感觉,基本上已接近意大利风韵;打击乐声部,在烘托气氛方面,也是很有分寸,特别是有的地方,既能轻得下来,又能让人听到(一般这种要求较高,往往不容易兼顾);唯一感到不足的是,弦乐声部(尤其是低音部分)相比较而言,无论力度、音色,都显得稍弱,我的猜测在谭利华那里得到了部分证实:乐器太差。另外,整个乐队的编制尚未齐全完备(他的目标是四管编制),因此,不得不在整体平衡上有所欠缺。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弦乐声部在某些技术性方面相当出色,比如乐曲在临近尾声时的小提琴急速走句,在我的临响经验中,还比较少听到过如此整齐,而又不影响整体速度的,为此,我感到潜力很大。余下者,在风格方面,当然每个人可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以威尔第风格而言,其戏剧性色彩的体现算是可以了,但更进一步说,则略有世俗性过之而宗教性不足之感。
作为压轴,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无疑是整场音乐会的重头戏。不仅乐队与谭利华,而且在座的所有懂行的听众,几乎都把自己的“保”或者说“赌注”压在这个节目上面了。外话先说,乐章之间仍然有少量听众的鼓掌现象,不得不使整体进程有所中断,是个遗憾(看来,东西方人的听赏习惯,以至成为一种文化风范,永远也难以在根本上消除,就像中国京剧演出过程中的喝彩,或者西洋歌剧咏叹调后面的谢幕,都几乎是带有了程式化的意味,参与着整个过程的结构)。在西方音乐的发展史中,布拉姆斯的交响乐作品,曾有“哲学论著”之美誉,尤其,《第四交响曲》作为一首经典作品,不仅被世界上大多数交响乐团所保留,而且,还是一把“标尺”,就像谭利华一再说的,有关媒体也有报导的,这部作品足以衡量一个交响乐团的专业水准。总的说来,这场演出是基本到位的。确实,布拉姆斯的结构方式真是太严密了,况且,又饱含明显的德国贵族气质,甚至,还携带着某种难以掩饰的“日尔曼血统”。因此,面对如此的庞杂,确实对任何乐队,尤其是与之差异甚大的中国乐队来说,必须有非常的把握,反之,稍有不慎就会错位,以至失败。比其他作家作品更难的是,对此,不仅要把情绪搞对了(这是写诗的天赋),更重要的是要把句子说清楚(这才是哲学著作的功底),有如论证一般。恰恰在这方面,又遭遇布拉姆斯独特的“混合音色”管弦乐结构方式,于是,乐队的大小和编制是否齐全完备,在这里都变得无关紧要,或者被退降为次要,而真正要做到的是,如何使得乐曲各个层次的清晰分明,但又不失为一个整体。以往的印象,谭利华是一个抒情指挥家,似乎更擅长驾驭情绪型的作品,但这次对这部哲理思维性的作品,他和他的乐团有如此的把握,应该说是成功的。用相对学术的话语说,就是基本上做到了:将整体合一之“象”向单一平面之“象”的分离,同时,又使得多重复合之“象”还原成全息立体之“象”。其中,第二乐章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整个音响不仅融为一体,而且,是“竖着”“站立”起来的(这一点,在中国的交响乐队结构音响上是个大问题,至今,似乎尚未在根本上解决容易“塌陷”“趴下”的问题)。其中,木管声部的各自到位与相互协调,尤其具有支柱之功。第四乐章是一个变奏体式的结构,无疑,三十一个变奏,不仅要展示不同的风貌,而且,又必须将主题(无论是显在者还是潜在者)有所突现,对此,这场演出也是到位的。唯一不足者,三十一个变奏的总体结构布局稍欠,如果在各个段落层次和大的板块阶梯上,再有一点强调与悉心安排,则将会取得更加完满的效果。另外,作为布拉姆斯所有交响乐创作中最为感伤的一部作品,因时代的隔阂与族类的差别,再加上文化传统的不同,当下中国人似乎已很难有相当的体验,那么,经典版本的借鉴,也许就可以成为一种合适的途径。我不知道这次演出是否有所借鉴,但从音乐会现场的感受来说,谭利华的处理是比较适中的,既不有意扩张,也不任意改写,算是忠实诠释。在这方面,看来对一个乐团来说,也需要经验的积累与贮存,而这种“保留”的价值,比起单纯的曲目保留来说,则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
与前两者相比,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似有可商榷之处。毫无疑问,担当独奏的小提琴家吕思清,无论在技巧,还是在与乐队的协作方面,都是无可挑剔的。但不知是乐器问题,还是临场感觉问题,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最佳状态,甚至几乎持续了整整一个乐章。显然,音色问题不仅事关与乐队的融洽度,而且,事关作品的风格。就前者而言,我的感觉是发“干”,缺少必要的润滑度,有人感觉有点“涩”,或者说是不够顺畅,到了第二乐章情况有所好转,我感觉除了演奏以外的原因,主要还在于作品本身。平心而论,这部作品在音响结构方面,尤其在纵向关系上,比较松散,因此,在演奏上稍有偏差,则问题丛生无疑。另外,在这首乐曲的风格把握上,吕思清显然是纤细有余,粗犷不足,至于适度的野性,更是缺了些许。当然单纯从艺术演释方面讲,他的这种处理也不失为一种独特,是为后话。
由此引申,可告诫者,依我的主观估价,中国人的文化惯性,似乎对同一样东西不宜于过分“保留”,也就是说,不断地重复同一个作品,在达到一定的程度尤其顶峰之后,往往会出现滑坡现象,精益求精难以实现,倒是出现了“走油”现象,甚至,还会有“干糙活”之嫌。这一点,倒是民间音乐与之相反,作为一个很有趣的文化话题,可另外谈论。
与这场音乐会密切相关,显然,这次演出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吸引京城音乐界众多人士与覆盖面甚广的媒体,并且,还惊动了上层人士的关注,与北京交响乐团的新作为有关。一个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以此为开端,启动了“音乐季”的进程。据介绍,这是国内继中国交响乐团自1996年开始“音乐季”之后的第二家。其实,这一作为并非仅仅是一种有国际惯例在先的制度推行,而应该看作是一个乐团在职业化、规范化进程中的必然所为。这里,需要诸多条件的具备,诸如财力支撑、人力配合、市场响应,等等。但是,最最重要者,还是乐团的实力。我在音乐会之后,和该团音乐总监、首席指挥谭利华进行了一次电话长谈,我注意到,这一作为并不仅仅是出自于他个人的胆略,他的真正底气在于,乐团经过多年的实践,已在曲目、人员、经验等方面有不少的积累,除了骨干人员的支撑以外,再加上此次在全国范围的招聘考核,又吸收了三分之一的新人员。虽然,新的组合尚处于磨合阶段,但精神面目已然不同于过去,从这场首演音乐会看,一种成就感和荣誉感,很明显地在全团上下涌动,甚至,当演出进入高潮时,简直有所洋溢。
“音乐季”制度的推展,无疑,与文化市场相关。但是,与经济市场不同者,我的感觉是,但凡参与文化市场运作者,其目的应该是不断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而不是毫无节制地促进人们的特质消费(这一点,其实也不可能)。与经济发展相应,这同样是一个需要宏观调控的问题。在与该团总经理胡伟先生的电话交谈中,他向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该团在新制度的推行进程中,将始终以艺术生产为中心,不断提高艺术质量,以满足文化市场的需求(姑且也把它套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与此同时,为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实行音乐总监与总经理双轨负责制。显然,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此,人们有理由藉此期待,首都音乐文化市场的某个局部,当又有一种新的机制被注入之后,可望出现良性循环,并可持续发展。
作为本次音乐会批评的撰稿人,我自然关注一些媒体的报导和评论,然而,“大众评说”的泛滥与“雷同话语”的复制,引起了我的“警惕”。相比较而言,音乐会批评的力度之微弱,面目之苍白,难以与实际音乐生活相称,诸如“激昂饱满的情绪”,“抒情流畅的语调”,“庄重威严的气势”,“细腻委婉的风格”,等等。不仅没能触及作品,则更难以针对演奏,于是,说了也几乎等于没说。回过来看,既然新制度的推行已然启动,理应同时建立相应的批评机制,复辅之以助动,并最终与之形成互动。
话到末了,我似乎生成一种北方人的玩家心态,在有所品味之后,突然又想把这些“临响经验”收藏起来,至于能否成为财富,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但有一点十分明确,即它的所有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对音乐本身也是会产生“变值”作用的,无非,或者是增值,或者是减值。于是,批评本身也成了音乐结构的一个重要元件与因素,这显然是接受美学的见解和当下贡献。
1998年3月22日写在燕东新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