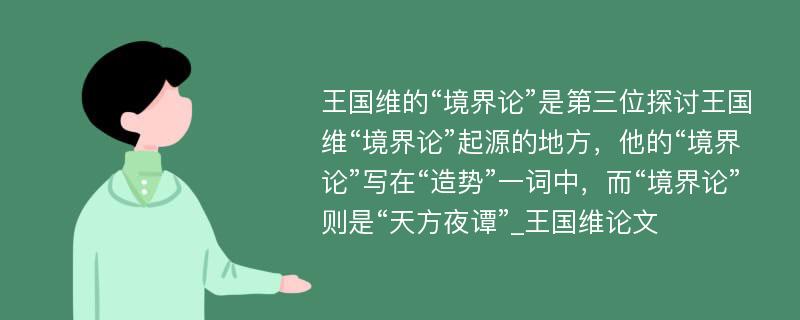
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王国维“境界说”探源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界论文,之三论文,王国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0257-5876(2006)03-0060-09
王国维《人间词话》手定稿第七则云: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①
这两句词是王国维举出的“有境界”的范例。但王国维仅仅是点到即止,并未说明个中原因。如果我们能够确切知道王国维为什么认为“著一‘闹’字”、“著一‘弄’字”便会“境界全出”,无疑对我们理解王国维“境界说”的内涵会有很大帮助。因此,近百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解释,比较有影响者,大约有以下四种。
一、通感说。钱钟书用“通感”来解释“闹”字。他认为,宋祁等“是想把事物的无声的姿态描绘成好像有声音,表示他们在视觉里仿佛获得了听觉的感受”②。在钱钟书的影响下,不少学者认为王国维也是依据现代心理学“通感”的理论作出上述判断的,但这种说法很难成立。首先,在《人间词话》评论的宋词中,不乏通感的例子,如姜夔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所谓“清苦”是味觉向视觉的“挪借”,但王国维却认为这两句词“隔”。其次,“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弄”并不涉及通感,通感说不能说明“弄”字所产生的美感。
二、移情说。所谓移情作用,是指审美主体在观察对象时,把自己的情感、生命移入到无生命的对象中去,把原本没有情感和生命的东西看作有生命的东西。如吴调公在评论《人间词话》这一则时便针对“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句写道,这句话的佳处就在于“不仅促使诗人把他对穿云之月和照影之花的关切倾注到眼前景物之上,也更成为诗人化身为月和花的情趣”③。但如果以此来解释王国维对这两句词击节赞赏的原因,则又会遭遇到类似上面的困难。如姜夔的“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都体现了诗歌的移情作用,但王国维评价甚低。
三、欲望表现说。有学者认为:“王国维之所以看重‘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和‘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弄’这两个动词,就是因为它们极富表现力地把大自然的欲望和意志活生生地写了出来,这就揭示了各自的本质。”④ 此说基本上是根据叔本华的理论来解释这两句词,但在叔本华的体系中意志和欲望的内涵基本上是负面的,更重要的是,王国维并不认为这种欲望是艺术表现的对象,他曾说:“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则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情感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异。”⑤ 艺术所表现的应是“微妙之情感”,而不是“生活之欲”。
四、意境说。持此说者是冯友兰,冯氏说:“所谓意境,正是如那两个字提示的那样,有意又有境。境是客观的情况,意是对客观情况的理解和情感——如果只写‘红杏枝头’、‘月下花影’,那就是有境而无意,‘闹’字和‘弄’字把意点出来了,这才出来了意境,这就成为这件艺术作品和它的作者的意境。”⑥ 对意与境作如此机械的划分,显然不符合王国维的观念。王国维主张的是“意与境浑”,像他在词话中称赞的“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均无法作这种机械的分拆,但王氏却认为“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
那么,王国维究竟是根据什么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呢?
也许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中国古代词论中寻求一些线索。
宋代词人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与同时代张先的“云破月来花弄影”在当时即是脍炙人口的名句。据词话记载,宋祁约见张先,戏称之为“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而张亦反戏之曰“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耶”。可见二人亦对此两句颇为自许。
在后来的词话著作中,关于这两句词,尤其是对前一句词的讨论和争辩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点是“雅俗”。《古今词话》称:“红杏枝头春意闹,一‘闹’字卓绝千古,字极俗,用之得当,则极雅。”⑦ 李渔在《窥词管见》中却表达不同的意见。李渔赞赏后一句,但对“春意闹”一句颇有微词:“云破月来句,词极尖新,而实为理之所有,若红杏之在枝头,忽然加一闹字,此语殊难着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争春,予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予谓‘闹’字极粗极俗,且听不入耳。”⑧
另一引起争议的是“自然”和“不自然”。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说:“词虽以险丽为宗,实不及本色语之妙……觉红杏枝头,费许大气力,安排得一闹字。”⑨ 另一位清代词学家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亦回应道:“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固炼,然太吃力,不可学。”⑩ 对于这种批评,刘熙载在《词概》中表达了不同观点。他认为“闹”字仍很自然,他表达这层意思的是“触著”。这种“触著”是极自然的,但又不是完全不经锤炼,而是所谓“极炼如不炼”。“词中句与字似能触著者,所谓极炼如不炼,晏元献‘无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触著之句也。宋景文‘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触著之字也”(11)。
但王国维却不是在上述理论脉络中作出自己的判断的,中国古代词学家关注的是用字本身,无论是雅还是俗,是不满其刻意雕琢还是赞赏其“极炼如不炼”,他们的关注点都在“闹”这一个字上。但王国维着眼的是这一个动词与“境界”的关系,尽管王国维没有对境界作出某种确切的解释,或者说他暗示了关于境界的多种解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境界不仅仅局限于用字,甚至不仅仅局限于词的语言。所以不妨说,王国维关注的是“闹”这个字与牵涉到作为整体的某种特殊的艺术质素的关系。
因此,我们还必须到另外的地方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如果要探询究竟,我们要从王国维对席勒“游戏说”的关注开始。席勒是王国维始终服膺的美学家,他的学生甚至称其为“吾国之席勒”。王国维最早接触到席勒,应该是通过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文氏的《哲学史》是王国维最初读到的两部西方哲学著作之一。当时王国维在编辑《教育世界》杂志,在诸多西方美学家中他较早关注席勒,尤其是席勒的审美教育理论,是很自然的事。
文德尔班在《哲学史》中指出,席勒对于康德的唯心主义知识科学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即是把艺术和美的问题放置在人的理性生活和它的历史发展中来考察。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这是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第一篇美学论文)中翻译的席勒下面一段话,就是从文德尔班的《哲学史》中转引过来的:“故美术者,科学与道德之生产地也,又谓审美之境界不关利害之境界,故气质之欲灭,而道德之欲得由之以生,故审美之境界乃物质之境界与道德之境界之津梁也,于物质境界中人受制于天然之势力,于审美境界中则远离之,于道德之境界则统御之(希氏《论人类美育之书简》)。”(12)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王国维第一次在美学意义上使用“境界”这一概念,尽管还有其他“境界”,如物质境界、道德境界。该词在文德尔班书中所用的英文是" state" ,文氏并指出,在席勒德文著作中是" staat" ,直译应为状态、情态、形态。后来朱光潜曾根据席勒德文译出,也译为“状态”。如同一段话朱氏译为:“人在他的物质(身体)状态中,只服从自然的力量。在他的审美状态里,他摆脱掉自然的力量,在他的道德状态里,他控制着他的自然力量。”(13)
王国维用“境界”来译" state" 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王氏在美学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首先是发生在翻译的过程中,即他希望用这个概念来传达和表示某一西方美学术语的内涵。因此不妨说,从一开始,王国维就基本上切断了中国古代境界说的美学内涵。王国维所谓之审美境界,即席勒之审美状态。尽管境界说此后有很丰富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的基本取向和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第二,王国维用“境界”来取代“状态”的同时也强调了原文中隐而不彰或未能凸显的某些方面。如境界与状态相比,便进一步强调了审美与物质、道德等的区分。在中国,“境界”一词最早的原意是边疆、边界,它指示的是某一确切的范围,而状态一词则较富于流动和变化。此外,境界一词后来由于佛教的影响,又衍生出高低不同位阶的含义,那么,在王氏看来,物质、审美、道德也便代表着不同的阶段。如果用状态来翻译,这层意思便不可能凸显出来。以上两点对于我们理解王国维后来提出的境界说都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这种审美境界,或者说审美状态与席勒所说的游戏有什么关系呢?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王国维接着便介绍席勒的审美教育学说:“希氏后日更进而说美之无上价值曰,如人必以道德之欲克制气质之欲,则人性之两部犹未能调和也。于物质之境界及道德境界中,人性之一部,必克制之以扩充其他部,然人之所以为人,在息此内界之争斗,而使卑劣之感跻于高尚之感觉,如汗德之严肃论中气质与义务对立,犹非道德上最高之理想也,最高之理想存乎美丽之心(beautiful soul),其为性质也,高尚纯洁,不知有内界之争斗,而唯乐于守道德之法则,此性质唯可由美育得之(芬特尔朋《哲学史》第六百页),此希氏最后之言。”(14)
王国维从《哲学史》中转引的这段话,对于席勒美学来说正是它的核心所在。席勒提倡美育,是鉴于在现代社会,无论是社会、个人还是个人内部都是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从人的内心来说,就是感性与理性的分裂。在这段文字中,即所谓“道德冲动”(moral impulse)和“感性冲动”(sensuous impulse)(王此处译为道德之欲与气质之欲)的彼此分裂和冲突,但是王国维在此处漏译了一个关键的概念,译文中“人之所以为人,在息此内界之争斗”如果完整地翻译过来,应当是“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只有当他平息了内心的争斗的时候,他才成为真正的人”。王国维在这里漏译的恰好是“游戏”这个关键的概念。
所谓“感性冲动”和“道德冲动”(或称形式冲动)都是人的自然要求和冲动,如何能使这对立的冲动和谐相处?席勒认为,能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是所谓的游戏冲动。游戏冲动的概念来自于康德“自由游戏”的概念和费希特的“冲动说”,感性冲动使人感到自然要求的强迫,而道德冲动又使人感到理性要求的强迫。游戏冲动“消除一切强迫,使人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恢复自由”。所谓美就是游戏的对象。在审美观照中,心灵是处于感性需求和道德法则之间,人充分实现了自己的本质,感情和道德不再分裂。只有在这时,人才能达到感性和理性的真正统一,物质和精神的真正统一,才能达到所谓“人格的完美”和“心灵的优美”(即王国维所谓“美丽心灵”)。所以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的第15封信中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15)
那么,一向严谨的王国维为什么会遗漏掉这一重要的概念呢?很可能是由于王氏当时对于“游戏”所包含的理论内涵还未能充分理解,或感到某些困惑,所以有意识地把它省略了。从王氏对席勒学说的使用和掌握情况来看,当时他基本上依靠的是文德尔班的介绍,很可能并未直接阅读席勒的原著,包括他后来引用的席勒关于诗歌的定义,“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都出自于文德尔班的《哲学史》,而文氏在该书中并未对“游戏”说的意义加以说明。
席勒还从生理学的角度对游戏的根源加以解释,提出了著名的“剩余精力说”。“狮子到了不为饥饿所迫,无需和其他野兽搏斗时,它的闲着不用的精力就替自己开辟了一个对象,它使雄壮的吼声响彻沙漠,它的旺盛的精力就在这无目的的显示中得到了享受……动物如果以缺乏(需要)为它的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它就是在工作(劳动),如果以精力的充沛为它的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如果是绰有余裕的生命力在刺激它活动,它就是在游戏。”(16)
席勒的游戏说给后来者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分化和发展的方向,一是通过自由的游戏实现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从而抵制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碎片化,其后继者是黑格尔、马克思;另一个方向是上承康德审美无功利学说,强调游戏活动的无直接目的性,剩余精力说开启的便是这样一种生理学、心理学方向,其后继者是斯宾塞、谷鲁斯。王国维后来呼应的主要是第二个方向。
尽管王国维很早就接触到席勒,但对“游戏说”并未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王国维的哲学时期,他醉心的主要是叔本华、康德、尼采的美学。“游戏说”对他的理论发生重要的影响,是在1906年前后,即他的文学时期。在《文学小言》中,王国维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17)
这种转变与王国维思想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王国维曾自述他的学术兴趣从哲学转向文学的原因:“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之快乐论与美学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18)
此处伟大之形而上学、纯粹之美学即指他在哲学时期一度醉心的叔本华和康德美学,当王国维觉察其“可爱而不可信”,对其产生怀疑时,他并不可能完全转向他认为“可信而不可爱”的以洛克、休谟等为代表的经验论美学,这时游戏说便进入了他的视野。席勒的“游戏说”,本身就具有两方面的背景,就其强调游戏和艺术都是超越直接功利目的、都应获得最大的精神自由等而言,它与王国维早期服膺的康德、叔本华美学是一脉相承的。但另一方面,继承席勒学说的斯宾塞、谷鲁斯等人,是在生理学、心理学方向发展了这一学说,把这一学说从思辨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转移到经验科学的形而下传统,这就给陷入思想矛盾和苦闷中的王国维提供了一条与康德、叔本华形而上学美学传统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新的形而下的理论路径。
在这一阶段对王国维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美学家谷鲁斯的“游戏”理论。王国维曾翻译过《哥罗宰氏之游戏论》(1906)。在王国维发表于这一时期的一系列论文,如《文学小言》(1906)、《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尤其是1907年发表的《人间嗜好之研究》中,谷鲁斯的影响清晰可辨。
谷鲁斯,也是“游戏”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两部代表作《动物的游戏》、《人类的游戏》分别出版于1898年和1901年,王国维在《哥罗宰氏之游戏论》中翻译了席勒、斯宾塞的游戏说的一些基本观点:
吾人亦欲从斯宾塞之说,以审美的感情为来自游戏之动向者……斯宾塞《心理学原理》第二卷……曰:“吾人所谓为游戏之活动实与审美的活动有共同点。何则?两者于人生之实际进行上俱无裨益也。”
希尔列尔(席勒)谓对吾人之性质及需要,可以一瞬而直达者,为吾人所不悦,而迂远者,反渴望之。是故剩余之势力无益于生命之保持者也。由此剩余之势力而生游戏之动向,由此游戏之动向而生美,而吾人乃以之为乐。
若夫有生者既得一定之势力矣,而其使用势力也,不用以满足其要求,又不为个体与(种)属,而用以保存其内外之关系之均衡,此外更无他法以泄之,则惟有用之于适意者及快乐者耳。是故游戏者,为欲表现快乐而消耗其所积蓄之势力者也。要之,游戏即潜势力之变形者,即由潜势力变为活势力,而以种种状态表出之者也。凡以快乐为目的而表之为游戏者,必与前所积蓄之势力之量,其值相等。今借嘉玛克斯之言以明之,则可曰:“游戏者,所剩势力之表出者云尔。”
游戏之成立,必以一定程度之知能、意识、感情、运动,为必不可少之要素。此事固易说明之。试观人类以下之生物则可恍然矣。动物之阶级愈下,其心的活动愈少,则其游戏的现象亦愈少。(19)
在以上几则中,第一则强调游戏与审美活动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超越直接功利目的的,第二、三则指出游戏的根源在于剩余精力,第四则指出,愈是高等动物,其游戏活动也就愈普遍。
这些观点都吸收、改造并反映在王国维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在《文学小言》中,王国维写道:“文学者游戏之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娈之儿,由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惟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感情及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20)
王国维在这里声明的仍然是他一贯坚持的文学的非功利性,但他的理论出发点已从康德、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美学转向了席勒、斯宾塞的游戏理论。这两种不同理论的交织使他这一阶段的思想呈现出一种比较复杂的状况。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王国维就把席勒的剩余精力说和叔本华的欲望说结合起来,用以解释嗜好的心理基础:“然人心之活动亦夥矣,食色之欲所以保存个人及其种姓之生活者,实存于人心之根底。”为了满足这种欲望,人们拼命工作,“工作之为一种积极的苦痛,吾人之所经验也”(21)。但另一方面:“且人顾不能终日从事于工作,岁有闲月,月有闲日,日有闲时,殊如生活之道不苦者,其工作愈简而闲暇愈多,此时虽乏积极的苦痛,然以空虚之消极的苦痛代之,故苟供其心之活动者,虽无益于生活之事业,亦骛而趋之如此者,吾人谓之嗜好。”(21) 在这里所谓“闲暇”以及因闲暇而生出的嗜好事实上是“剩余精力”的另一种说法,而所谓“积极的苦痛”、“消极的苦痛”则类似于叔本华所谓的“苦痛”与“无聊”的区分。
但王国维对“消极苦痛”的根源的解释,却与叔本华完全不同了:“活动之不能须臾息者,其惟人心乎。夫人心本以活动为生活者也,心得其活动之地,则感一种之快乐,反是则感一种之苦痛,此种苦痛非积极的苦痛而消极的苦痛也,易言以明之,即空虚的苦痛也。空虚的苦痛比积极的苦痛尤为人所难堪。何则?积极的苦痛,犹为心之活动之一种,故亦含快乐之原质,而空虚的苦痛则并此原质而无之故也。人与其无生也不如恶生,与其不活动也不如恶活动,此生理学及心理学上之二大原理不可诬也。”(23)
这种认为痛苦源于“不活动”的解释与叔本华是不同的。叔本华给痛苦下的定义是这样的:“我们把意志因横亘于它与它当前目标之间的一个障碍而遭到的阻挫称之为痛苦。”(24) 意志是不能遏止的盲目冲动,就是欲求。一切欲求都是基于匮乏,基于对现状的不满。欲求一日得不到满足,就产生痛苦,而又没有一次满足是可以持久的。每一满足都是新的欲求的起点。所以欲求是无止境的,痛苦也是无穷无尽的。就此而言,生命意志的本质就是痛苦,而王国维所谓消极的苦痛即空虚无聊就产生于新旧欲求的间隙之中。因此,对叔本华来说,要解除或减轻痛苦,不是依赖于活动,而恰恰是活动的对立面,即寂灭。
王国维承认,这种将精神的快乐与痛苦归之于活动与不活动的观点来自于“生理学及心理学”。其直接来源就是游戏说。在《人类的游戏》中,谷鲁斯把这种精神活动看作是游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发现所有感官都表现出无数要求活动的冲动。”“毫不奇怪,游戏中精力的活动以及相伴随的身体感觉是与愉悦的情感相联系的。”(25)
但是,谷鲁斯认为所谓席勒、斯宾塞的学说并不充分,每一种高等动物的游戏都有独特的形式,我们必须能够解释这些不同形式产生的原因。如果把它们都看作剩余精力的发泄,显然无法说明其间的差异。谷鲁斯因而提出“再创造理论”,作为对剩余精力说的一个补充:“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作为游戏的生理学有两个基本的原则,剩余精力的发泄和消耗掉的精力的再创造,它们可以同时发生作用。”(26) 与剩余精力说不同的是,这种再创造理论认为,愉悦并不仅仅来自于人心的积极的活动,“它是一种成功的喜悦,胜利的喜悦”。这种喜悦来自于在生存竞争中取胜带来的拥有力量的感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谷鲁斯认为,只有在低级阶段,游戏才是单纯的本能冲动的满足,而较高级的游戏“归根结底是我们惯常感到的对力量的快乐,觉得有能力扩张施展才能范围的那种欣喜”,以及自我炫耀的快乐(27)。
从这种观点出发,谷鲁斯不赞成那种认为艺术没有外在目的的说法:“就连艺术家也不是只为创造的乐趣而创造,他也感到这个动机(指上文所说的‘对力量的快感’),不过他也有一种较高的外在目的,希望通过他的创作来影响旁人。就是这种较高的外在目的,通过暗示力,使他显示出超过他的同类人的精神优势。”(28) 这与王国维过去接受的艺术是没有外在目的的观念,如康德的审美超越直接功利说、席勒的游戏说等是冲突的,但王国维要么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冲突(这种可能性较大),要么是有意回避了这种冲突。
王国维的《人间嗜好之研究》即是用这种“争胜”说来分析嗜好。王国维先把欲望分为“生活之欲”与“势力”之欲,“势力”即王国维对“精力”的翻译。所谓“生活之欲”大抵对应于谷鲁斯所谓“本能冲动”,所以与之相应的是“宫室车马衣食之嗜好”,而其他对驰骋田猎跳舞之嗜好,对书画古玩之嗜好,“一言以蔽之,欲其势力之胜于他人而已矣”(29)。此即谷鲁斯所谓“精神优势”。
在游戏中,“博弈”是最集中地体现出上述特征的。谷鲁斯把游戏分为四种,其中第一种叫作“战斗的游戏”,这种游戏又分为身体和精神两类,在精神一类中又分为两种,一种他称为“直接的智力竞赛”,这种游戏的代表是弈棋。下棋是一种理性的竞争,所以谷鲁斯说,“这种游戏快感的性质涉及到的是理性能力的使用”(30)。另一种称为“精神对抗”,这种“精神对抗”的特征是一种“机会游戏”,谷鲁斯把赌博看作是这种“机会游戏”的代表。“在机会游戏中,竞争者之间并不直接地相互攻击,而通过对某一困难的更好的解决而成为胜利者”(31),赌博是某种必然与偶然的结合:“完全的确定会摧毁赌博的价值,而完全的不确定使它成为纯粹偶然的游戏。就像最好的纸牌游戏一样,它应该依赖于一种理性与偶然的结合。”(32)
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也把“博弈”看作是满足人的争胜欲望的一种游戏方式:“今先论博弈,夫人生者竞争之生活也,苟吾人竞争之势力无所施于实际或实际上既竞争而胜矣,则其剩余之势力仍不能不求发泄之地,博弈之事正于抽象上表出竞争之世界而使吾人于此满足其势力之欲者也。”(33) 在讨论“弈”与“博”的性质时,王国维也沿用了谷鲁斯的区分:“且博与弈之性质亦自有辨,此二者虽皆世界竞争之小影,而博又运命之小影。人以执著于生活故,故其知力常明于无望之福,而暗于无望之祸。而于赌博之中,此无望之祸时时有可能性,在以博之胜负,人力与运命二者决之,而弈之胜负,则全由人力之决定之故也。又但就人力言,博者悟性上之竞争,而弈者理性上之竞争也……人亦各随其性之所迫,而欲于竞争之中发见其优胜之快乐耳。”(34)
这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不仅用来说明游戏的快感,也用来说明艺术产生的快感。谷鲁斯认为喜剧的快感“是由优越感构成的,它也属于战斗游戏的范畴”,“作为一种生存竞争的结果,每一种低能的表现都会在旁观者心中唤起一种优胜的感觉。无论是被观察者在身体或精神上的不适应,还是运气不佳,缺乏自信”(35)。谷鲁斯认为喜剧带来的“广泛的满足感”大都根源于此。在谷鲁斯看来,悲剧也同样属于战斗游戏,“悲剧也是如此,不仅情感风暴带来的欢悦,而且在竞争中获得的愉悦,都是克服悲剧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痛苦的一种手段”。在悲剧中,我们目睹主人公遭遇到灾难,但这种灾难仍能够给予我们快感,因为英雄外在的毁灭能够唤醒我们一种胜利的情感。其原因在于“一个战士的最高的胜利就是战胜他自己的恐惧和失败”(36)。在这种情况下,灾难成为了内在胜利的基础。
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是这样解释喜剧与悲剧的快感的:“常人对戏剧之嗜好亦由势力之欲出,先以喜剧(即滑稽剧)言之,夫能笑人者必其势力强于被笑者也,故笑者实吾人一种势力之发表……此即对喜剧之快乐之所存也。”(37)“悲剧亦然……自吾人思之,则人生之运命固无以异于悲剧,然人当演此悲剧时亦俯首杜口或故示整暇汶汶而过耳。欲如悲剧中之主人公,且演且歌,以诉其胸中之苦痛者,又谁听之而谁怜之乎,夫悲剧中之人物之无势力可言固不待论,然敢鸣其苦痛者与不敢鸣其苦痛者之间,其势力之大小必有辨矣。夫人生中固无独语之事,而戏曲则以许独语故,故人生中久压抑之势力独于其中筐倾而箧倒之,故虽不解美术之趣味者亦于此中得一种势力之快乐。”(38)
在分析喜剧快感时,王国维基本上重复了谷鲁斯的喜剧快感产生于“优越感”之说,所以他强调“能笑人者必其势力强于被笑者”的观念。在分析悲剧时,谷鲁斯认为,悲剧所表现出的胜利就是战胜自己的恐惧和痛苦。王国维认为悲剧主人公尽管无势力,但敢鸣其苦痛,所以优于不敢鸣的普通人。他尤其强调戏剧人物的内心独白,指出通过这种独白,悲剧人物可以充分表现“人生中久压抑的势力”,使读者“亦从中获得一种势力之快乐”(39)。对于谷鲁斯来说,悲剧人物所展现的力量,它所带来的胜利的感觉是由于其战胜自己所遭遇的苦痛的命运。而在王国维看来,则是他敢于以戏剧的方式将之告白于世人,“敢鸣其苦痛”。但把一种优胜的力量作为悲剧快感的来源则是二者共同的。
在谷鲁斯的影响下,王国维对悲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叔本华的美学里,悲剧是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在叔本华看来,真正的悲剧应当“叙述人生可怕的一面”,从而使人产生对生命本身的怀疑和放弃。用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的话说,它的目的“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40)。谷鲁斯与叔本华的悲剧观分属于不同的美学体系和传统,前者属于形而下的心理学的美学体系和传统,后者属于形而上的哲学的美学体系和传统。席勒的游戏说构成了二者的交汇点,王国维正是通过席勒的中介,从叔本华走向了谷鲁斯。
1908年,王国维在《国粹学报》上连续发表《人间词话》。在《人间词话》中,我们既可以发现叔本华美学的影响,又能看到谷鲁斯游戏说的影响。如未刊稿第五十则:
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性质,亦不可缺一也。
与之相关的还有手定稿六十一则: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令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这两则词话实际上表述的是谷鲁斯游戏说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佯信”说(make believe)。“佯信”又可称作“自蹈幻觉”或“有意识的自我欺骗”,是人类游戏中常常发生的一种心理现象。在《动物的游戏》中,谷鲁斯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谷鲁斯认为,各种游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佯信”,但它在艺术游戏中表现得最突出。他指出,这种“佯信”或“有意识的自我欺骗”的出现是与游戏相伴随的最为高级的心理现象。在这里,游戏已经站在艺术生产的门槛边上了。就其通过佯信获得快感,游戏与艺术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艺术生产的目的是影响他人,而游戏则没有这种目的。正是这种“佯信”使游戏、艺术与人类的现实活动区分了开来。
“佯信”具有两重性,即王国维所说“诙谐与严重性质,亦不可缺一也”。谷鲁斯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一个小孩戴上他爸爸的帽子,然后说:“瞧,我现在是爸爸。”从一方面看,这是一个游戏,一种滑稽模仿,即王国维所说的诙谐的性质,但另一方面,小孩所作的又不仅仅是一种模仿,因为他是以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来从事他的扮演的,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以热心为之”的严重的性质(41)。
谷鲁斯指出,这种两重性的态度是由一种“分裂的意识”构成的。游戏中的儿童一方面会产生一种有意的遗忘或习惯性的盲目,这使他能够全身心地沉浸在游戏里面,甚至对接近的危险也视而不见。“但在另一方面,与真实生活的联系并未中断,就像在消极或积极的催眠状态中产生的幻觉一样”(42)。那么,在游戏中,游戏的自我与真实的自我的联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谷鲁斯指出:“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是真实的自我不停地提醒游戏的自我,这是不真实的。二者关系的基础是我们确信自身是所佯信的对象和情感的创造者,是我们自由地创造了它们,正是这种创造的感觉使我们获得了满足。”(43) 谷鲁斯说,正是那种整个幻象的世界都依赖于我们自身,我们从自身的材料中创造了它们的观念,从真实的自我悄然地不被意识觉察地潜入游戏过程,使我们可能把“佯信”与现实充分地区分开来。
王国维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关于这段话有许多解释,大抵可以吴奔星下面一段话为代表:“这就是说,诗人必须站在现实的高峰,居高临下,争取反映现实的主动权,同时,又要密切关注现实,不脱离生活,争取和客观事物打成一片。”(44) 这实际上是用“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曲解了王国维的意思。
王国维在这里所说的,其实是谷鲁斯上述“佯信”内部的二重性。真实的自我既意识到自身是诗歌中一切的创造者,故能轻视,能“以奴仆命风月”。同时,游戏的自我在“佯信”的状态中又沉浸到对象之中,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谷鲁斯举例说:“我非常清楚我正在观看的飞溅的瀑布并未曾感到看起来显示的‘愤怒’,但我仍着迷于这个念头,我是通过幻觉(illusion)在观看,并使自己沉浸于其中。”(45)
诸如“沉浸在对象之中”一类说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移情”说,但谷鲁斯把自己的观点与移情说作了区分。他认为,移情说未能解决一般的欣赏与审美知觉的区别,他在《人类的游戏》中指出,移情是一个自身过去的经验,如恐惧、愉悦等与当前感觉印象融合而成的一个和谐的整体:“没有这样一种融合就不可能完成一种欣赏行为,问题在于作为一种特殊的满足,审美知觉不同于一般的欣赏。”(46) 他举例说,当小孩和野蛮人听到隆隆的雷声,会产生一种宏壮的声音在震怒中咆哮的印象,因而感到恐惧。但这种恐惧仅只是移情,却不是审美愉悦,只有当人能以游戏的态度从雷的吼声本身感到一种“独特的、自我中心的快感”时,他才对它产生一种审美的欣赏。
在谷鲁斯的游戏理论中,这种审美的欣赏就是“内模仿”。“内模仿”是谷鲁斯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谷鲁斯认为,艺术是与模仿的游戏联系在一起的。他指出,知觉都是以模仿为基础的,如看见一个圆形的物体,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用眼睛模仿它作一个圆形的运动。审美的知觉模仿和一般的知觉模仿不同,一般的知觉模仿会通过外部的筋肉动作表现出来,而审美的模仿只是一种“内模仿”:“假如一个人看跑马,这时真正的模仿当然不能实现,他不愿放弃座位,而且还有很多理由不能去跟着马跑,所以他只心领神会地模仿马的跑动,享受这种模仿的快感,这就是一种最简单、最基本也最纯粹的审美欣赏了。”(47)
在谷鲁斯看来,“内模仿”的快感就是审美快感的基本内容。他说:“内模仿是否应当看作一种单纯的脑里的过程,其中只有过去动作、姿态等等的记忆才和感觉知觉融合在一起呢?绝不是这样,其中还有活动,而活动按照普通的意义是要涉及运动过程的,它要表现于各种动作,这些动作的模仿性对于旁人也许是不能觉察到的,依我看来,就是对实际发生的各种动作的瞬间知觉才形成了一个中心事实,它一方面和对过去经验的模仿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和感觉知觉融合在一起。”(48)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当前形象的知觉和过去经验(如恐惧、愉悦)等的记忆的联想形成了移情作用,谷鲁斯不同意这种移情构成审美经验的核心,他强调的是活动,是一种运动感觉,这种运动感觉包含“动作和姿态的感觉(特别是平衡的感觉)、轻微的筋肉兴奋及视觉器官和呼吸器官的运动”(49)。
“内模仿说”与移情说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这种运动感觉以及其带来的力量、生命的经验。谷鲁斯说:“内模仿的行为本身就是愉悦的,对我来说不言自明的是,获得满足的程度是与对象成正比的,这也为最高的审美直觉、生命和精神完整的印象清楚地证实,为内模仿所显示的,回应运动、力量、生命、生机的愉悦的行动所清楚地证实。”(50) 这种运动、力量和生命的感觉构成审美经验的主要内容。
正是在谷鲁斯的“内模仿说”的烛照下,我们可以理解王国维为什么认为著一“闹”字、著一“弄”字,便可达到“境界全出”的效果。著一“闹”字和“弄”字之后,作品所呈现的便不仅仅是一幅静态的图画,而是充满了一种生机洋溢的动感形象。《人间词话》手定稿第二十三则云:
人知和靖《点绛唇》、圣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阕为咏春草绝调。不知先有正中“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者也。
又《人间词话》手定稿第三十六则云:
美成《青玉案》(当作《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
我们注意到,王国维赞赏的冯延巳的“细雨湿流光”的“流光”,周邦彦“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的“举”字,都是两句词中的点睛之笔。王国维赞扬这两句词“能摄春草之魂”、“能得荷之神理”,并不是如佛雏等所说,因为其揭示了叔本华所谓物之固定不变的理念,而是因为它通过一种动感,展现了对象的蓬勃的力量和生机。朱光潜指出,移情说与内模仿说的一个区别在于,移情说侧重表现的是由我及物的一方面,而内模仿说侧重表现的是由物及我的一方面。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举的上述例子,基本上都符合这一特征。
最后要补充的一点是,谷鲁斯在书中曾引用立普斯在《空间美学》中对希腊道芮式石柱的分析,立普斯指出,尽管石柱本身只是无生命的物质,只是一块大理石,我们在观照它时,它却显得有生气,有力量,仿佛从地面上耸立上腾。这种耸立上腾成为石柱所“特有的活动”。它之所以显出这种力量和活动,是因为它抵抗和克服了重量压力,使其才显得昂然挺立:“在我的眼前,石柱仿佛自己在凝成整体和耸立上腾,就像我自己在镇定自持,昂然挺立,或是抗拒自己身体重量压力而继续持这种挺立姿态时所做的一样。”谷鲁斯在书中引用了这个例子,是因为它十分适合说明自己的“内模仿说”,熟悉谷鲁斯著作的王国维应该读过这一段,我认为,这很可能就是他欣赏“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的背景吧。
注释:
①陈鸿祥编著《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以下所引《人间词话》均据此书。
②钱钟书:《通感》,载《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
③吴调公:《关于古代文论中的意境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
④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5页。
⑤王国维:《哲学辨惑》,载《教育世界》第55号(1903年)。
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页。
⑦《古今词话》,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⑧清李渔:《窥词管见》,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⑨清贺裳:《皱水轩词荃》,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⑩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11)清刘熙载:《词概》,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12)(14)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教育世界》第69号(1904年)。
(1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2页。
(15)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15封信,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6)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27封信,译文采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44—445页。
(17)(18)(20)(21)(22)(23)(29)(33)(34)(37)(38)(39)(40)《王国维遗书·静安文集续编》第三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624-625页,第611页,第624—625页,第580—581页,第580—581页,第580—581页,第583页,第582—583页,第582—583页,第584页,第584—585页,第584—585页,第430页。
(19)王国维:《哥罗宰氏之游戏论》,佛雏校辑《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268页。
(24)Arthur Schopenhauer,Manuscript Remains in Four Volumes,VOL.L,trans.E.F.J.Payne:Palgrave Macmillan,1988,p.425.
(25)(30)(35)(46)Karl Groos,The Play of Man,New York:Appleton,1901,p.389,p.196,p.234,p.325.
(26)(41)(45)(50)(27)(31)(32)(36)(42)(43)Karl Groos,The Play of Animals.New York,D.Appleton and Co.,1898,p.368,p.302,p.303,p.389,p.289,p.204,p.204,p.251,p.317,p.317.
(28)(47)(48)(49)译文采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第615页,第616页,第618页,第619页。
(44)吴奔星:《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境界论》,载《江海学刊》196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