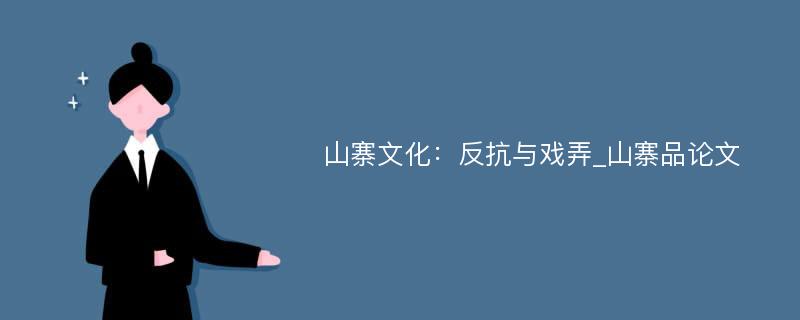
山寨文化:抵抗与揶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寨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9)01-0107-04
2008年,“山寨”一词频频出现于我们的视野,从山寨歌星到山寨春晚,从山寨手机到山寨影视作品……人们已经将他们对基于模仿而成的一切器物以及文化表现形式通称为“山寨文化”。西方学者诸如“威廉斯认为,‘文化’这一术语主要在三个相对独特的意义上被使用:艺术及艺术活动、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发展的过程”[1](P2)。那么很显然,山寨文化的“文化”一词是个极其具有包容性的词汇,它并不在上述三层意义上加以严格的区分。
“山寨”一词源于广东话,在广东话里山寨是山村营寨的意思,是指一个独立的封闭的与世隔绝的寨子。其流行是从广东某些地方和地方企业开始的,特别是东莞和深圳的城乡结合部地区,一些电子类、加工类小型企业,其中很多属于技术作坊类。这些企业有一定的自卫性和地下性,处于和外界联系的边缘位置、边缘状态。山寨产品活跃区域,往往是民间集资和乡镇企业的生存能力都比较强而管理又相对松懈的地方。产品输送终端往往是消费水平不高的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制管理难以严格的地区。这种发端于由民间IT力量掀起的产业现象,现在已经弥漫到文化产业,形成了一种汹涌之势,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面对山寨文化,如何评判其文化的特质是时下规导山寨文化的关键。
一、山寨文化特质一:抵抗
研究文化,脱离不了文化与权力关系的研究视角,“无论是哪种解释,它们的共同点都认为权力与文化是无法避免地联结在一起的,文化分析不能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中被分离出去”[1](P21)。山寨文化在多元文化生态中与其他文化共生,它与文化霸权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1.在器物文化层面,山寨文化以现实的产品形式抵抗着已经获得品牌优势的产品,冲击着名牌产品的市场,与名牌产品争夺市场份额。作为一种亚文化,山寨文化的产生与通常意义上的亚文化不同,它一开始并不是以文化的典型意义出现,而是从器物文化层面开始的。它以仿制名牌产品的路径,以现实的产品渗透于市场,给普通大众直接的印象就是产品本身,普通大众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文化内涵,甚至于有的消费者就将其视作名牌产品。反观名牌产品,仅仅看它的文化意义,其成长的历程可谓非常艰辛,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产品成为名牌产品,美誉度的培育有一个相当长的周期,名牌产品的文化诉求要达至深入人心,其实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尽管广告铺天盖地,仍有80%~90%的新产品以失败告终……”[2](P31)。因此,名牌产品高端的价格,除了它本身很好的品质以外,它的品牌维护需要花费极高的文化成本。在工业社会,产品的文化大众性内在地存在着不可名状的矛盾,“一方面,它是文化工业,必然受资本追逐利润的铁律所决定,也必然隐藏着中心化的、规则性的、霸权式的、一体化的、商品化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为大众所有,必须服从大众的需要,他们有权使某些文化商品变成‘昂贵的失败’”[3](P104)。而这些矛盾,山寨文化产品可以忽略,短平快的生产、流通、消费,低廉的价格,鱼目混珠的产品,灵活的营销方式迎合了社会化的大众,满足了收入水平不高而渴望拥有名牌的消费者欲求,表面上高端产品的平民化决定了它与我们老百姓知识产权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漠的国情相契合。
2.在文化理念层面,山寨文化夹杂在文化多元的时空下,向业已建立起来的霸权叫板,同时借机建立自己的认同。首先,山寨文化表现了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有意识抵抗。从我国社会所处的发展环境来看,社会转型以来随着多样化的社会思潮纷至沓来,裹挟着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社会思潮对普通大众的冲击力是巨大的。长期的中心化、主流化社会结构模式为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边缘化、多中心、消解化、解构化,为民间催生山寨文化提供了外部环境,精英主义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显然不复存在,普通大众完全可以参与文化的创造,正是如此,山寨文化以解脱的轻松感平添了寄生性、投机性、自发性、自立性、流动性和地方性。其次,山寨文化以抵抗性的姿态向业已建立的文化霸权叫板。从山寨文化剥离出的文化理念便能够看到,当名牌产品一旦确立中心地位,显示出华贵典雅、卓尔不群的时候,当影视明星一旦蹿红、风靡一时的时候,其独一无二的地位即是获得了某种文化霸权,这种文化霸权潜在的利益是巨大的,名牌产品的价格让人望其项背而咋舌,当红歌星、明星的出场费更是天文数字,山寨文化的理念主观上是获取利益,但客观上抵抗着名牌产品与众不同的身份认同,向业已确立的文化霸权进行挑衅。但是,“‘文化霸权’绝不只是由统治者自上而下地强加给被统治者的权力,而是占支配地位的集团与居从属地位的集团之间‘谈判’的结果,‘文化霸权’确立的过程是一个以‘抵抗’和‘融合’为标志的斗争过程”[3](P75)。即是说,文化霸权的取得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一种动态的关系,“霸权不仅仅是阶级制度,也需要共识。对一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言,它必须要被赢得,为之努力,再生产,被保持,动态的平衡”[4](P39)。在“谈判”的过程中文化消费主体受利益的驱使,开始寻找可能的替代品和仿制品,作为向正规品叫板的筹码,山寨文化以平民化的低调开始与正式化的文化模板讨价还价,实际上它不自觉地扮演了抵抗正式化文化模板的作用。再次,山寨文化大行其道的原因是以一种新的路径解决问题,目的是为了构建自己的社会认同。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非常明显,真实的不平等与社会意识形态意欲构筑的平等之间还有较大的距离,社会意识形态并不足以消解现实中的不平衡性,即便业已确立起来的霸权在现实领域的认同度也值得考虑。在霸权没有取得共识的情况下,对普通大众而言,于现实的窘境采取的策略就是以抵抗的方式构建一种与主流文化不同的亚文化,对社会—阶级的结构性问题提供想象性的解决方案,提供不同于学校和工作相反的有意义的休闲行动,构筑适合普通大众的集体认同。这一点无论从仿造性的产品还是所谓的“山寨歌星”、“山寨春晚”、“山寨排行榜”方面都能够得到彻底的体现。
3.文化产业层面,山寨文化以不拘一格的传播形式,以模仿、拼贴、改编、恶搞等手段取悦于社会大众,向主流文化产业公然抵抗。在文化产业层面,首先,山寨文化的主体是特定大众成员,特别是社会底层低端消费的大众,其核心或骨干是社会小资本势力和文化传媒策划活跃分子,但是它的受众接受面却没有边界,只要能够取悦于大众,其背后就会带来丰厚的回报。它的生成和发展也需要经济基础作支撑,因此,采取取悦于大众的另类方式才可能吸引人们的眼球,才可能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山寨文化与传播媒介的关系而论,它易于与商业媒介结合,以实现最大限度接近受众的目标。“商业媒介本身就其内在机制而言,原本就已经包含了一种促使其自身和流行文化的品位和结构产生某种程度契合的内驱力。传媒因其控制权造成文化同质化的同时,它的具体运作也为各种消费文化建构起巨大的市场,换句话说,通过传媒所放送的各种产品(电视节目、广播及网络信息等)直接目的是吸引观众和广告商,以获得商业利润,因而公共领域丧失了真正的公共性,而服从于某种权力的立场和利益。”[3](P155)从这个意义上说,山寨文化不拘一格的传播方式,见缝插针与主流文化产业的传播进行着抵抗,只要有传播的空间都是值得山寨文化钻营的。尤其是它不能为自己正名,而只能游走于正式化文化产业的盲区和边缘。其次,山寨文化的手段无非就是模仿、拼贴、改编、恶搞等手段,这些手段是以正式化文化产品的原本作参照的,有的本身就是正式化文化产业达至一定的规模和受众影响面,山寨文化便于利用现有文化产品的影响基础,根据受众良好的接受阈限制作而成;有的故意篡改正式文本,为了吸引受众的眼球而为之。比如,简单拼贴的电影《十全九美》成为奥运期间的票房黑马,也成为最典型的“山寨电影”。片中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大量运用当下流行元素,谈不上对现实有什么讽喻意义。所以它是大众文化中极有争议性的、充满狂欢乐趣和低俗趣味而又有消极影响力的特定的一部分,它和现代产业的低端部分和地方大众媒体紧密联系,互为表里,互为动力,相辅相成。总之,当“山寨”以IT业为切口渗透至人们的经济生活时,就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其他领域,除一些盗版商品加入山寨大军之外,山寨的概念也被扩大到日常生活诸多与“另类翻版”有关的人、事、物中,山寨影视剧、山寨音乐、山寨艺人、山寨门事件等令受众产生“各处皆有山寨”的错觉,山寨文化就这样形成了,继而慢慢地由幕后走向前台,抵抗正式化文化产品而形成自己的文化产业,获得与正式化文化产品同样的利益是山寨文化产业的目的。
二、山寨文化的特质二:揶揄
山寨文化除了具有亚文化的一般特质抵抗性以外,它还具有揶揄的特质,所谓揶揄即耍笑、嘲弄、戏弄、侮辱之意。谁在揶揄?揶揄谁?怎样揶揄?为什么揶揄?这是考察山寨文化特质的关键问题。
1.山寨文化始作俑者并不是社会大众,而是传媒策划者和社会小资本所有者的社会小众对正式化文化产品和文化理念的揶揄。表面上看,山寨文化拥有社会大众,似乎草根阶层尽可以参与文化创造中,实际上草根阶层仅仅参与了文化消费以及由此激发的社会互动,山寨文化的始作俑者绝对不是社会化大众。虽然可能每个人可以消费其中的某些文化产品,但草创山寨文化任何形式的活动并不是每个人能够担当的。所以,山寨文化开始之时,就是社会小资本所有者为了追逐利益的行为,后来逐步演化为文化草创活动,在此环节中传媒是关键。主流媒体往往不允许山寨文化传播,决定了它只能选择互联网等开放媒体和一些地方性媒体。由于山寨文化的另类性,它的出现颇能够吸引人的眼球,因此也可以赢得众多的受众,与主流媒体争夺传播空间,时不时会以特定的话语揶揄主流话语,以替代品揶揄正式化文化产品,以特殊的文化理念公然揶揄主流文化理念。以黄晓明首张专辑《It's Ming》为例,从Rain到Ming,听起来就很押韵,但是押的可不仅仅是一个尾音。黄晓明瞅准了Rain在亚洲市场的超人气,凭的就是坏坏的笑容、健硕的胸肌和一身好武功。唱片首发会上,掀开幕布,就看到黄晓明半裸上身,背对观众,左肩上还有刺青,粉丝当然惊呼性感,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黄晓明学着Rain也开始“卖肉”博话题了,封套、舞蹈、曲风、笑容、MV大玩韩版煽情……所有的一切,都让黄晓明的首张专辑最终成为功能强大的山寨专辑。
2.山寨文化诉求快感满足和平民化,借助于破坏既有符码和表达新符码的方法,以特定的文化符号进行表达,创造特别意义,揶揄主流文化的惰性和刻板。山寨文化迎合普通民众快感的欲求而在现实上进行抵抗。在明显迥异于主流的文化空间中,山寨文化充当着亲低端民众的角色,以各种各样方式表达底层民众的诉求,无论物质还是精神层面。“费斯克将大众的快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躲避式的快感,它们围绕着身体,经由身体被体验或被表达,而且在社会的意义上,倾向于引发冒犯与中伤;另一种是生产者的快感,即生产诸种对抗式意义时所带来的快感,这种快感集中在心灵,它们围绕的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关系,并通过对霸权力量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而且也是社会的意义上运作。”[5](P68)第二种快感即是上述的抵抗特质以构筑认同,但就从第一种快感而论,山寨文化的策划者往往以狂欢轻松的形式模仿主流群体的快乐,以娱乐至死的精神感染社会大众,尽管它与主流文化的厚重与深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却给底层民众情感诉求以极大的满足,达到以另类的经验抵抗主流文化表达方式的目的:你能够获得的,我同样可以获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山寨文化表达了最平民化的时尚,最全民的娱乐,进而在大众互动的过程中,山寨文化也越来越从一种表层的形式转向文化内涵,直插本质:从草根化、平民化中创造自我成就之路,自娱自乐、天下共赏。“大众文化制造了从属性的意义,那是从属者的意义,其中涵盖的快乐就是抵制、规避或冒犯支配力量所提出的意义的快乐。”[6](P144)
从物质层面到文化层面,山寨文化游走于主流文化的边缘,作为文化生态之中的亚文化,它与主流文化的共时性,决定着它必然采取别样的风格意义才能得到生存。赫伯迪格说过:“亚文化风格的确称得上是艺术,不过它是位于(或脱离)特定语境的艺术,它不是作为永恒的物体由传统美学不变的标准来判定,而是作为‘挪用’、‘窃取’、‘颠覆性’的转换和作为‘运动’来进行判定的艺术,它的美学力量在于‘破坏既有符码’和‘表达新的符码’,从而获得艺术表达和审美愉悦。”[7](P129)山寨文化在破坏既有主流文化秩序的同时,表达了自己的艺术情趣,其间,对主流文化的揶揄既彰显了它的态度,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质。山寨文化以自己特别的符码表达了对主流文化的揶揄。山寨文化的策划活跃分子更加注重无厘头精神的追求,它的语言形式不拘一格,既模仿正式化的表达,又运用了特别的符码,编码过程中巧妙地在社会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捕捉着人们的猎奇、从众等心态,形成一股备受关注的态势,具有让人津津乐道的意味。虽然说山寨文化传播者的编码与受众的解码可能各自使用着一套不同的符码和成规,但是随着社会互动的不断加强,那些被悬置的意义在互动中会被激活并且逐步趋于一致。山寨文化惯常使用一些主流文化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加以篡改、拼贴,既达到易于传播的效果,又易于为受众运用,与刻板深度的主流文化相较,它以自己独特的符码甚至于非常简单化的手段,达到主流文化不及的效果。
3.山寨文化以揶揄的特质宣告着草根阶层的生存方式,同时,由于利益动力,加快山寨文化成型化,使之及时地表达了草根阶层对社会现实的文化诉求。首先,山寨文化以揶揄的特质宣告着草根阶层的生存方式。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定发展阶段体现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阶层一定程度的不和谐,社会消费方式存在的不合理性,文化发展上缺少低端关怀的方式,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巨大消解力,高端技术创新的巨大软肋,社会发展积累的红利向社会低端注入的必要性,在农村大规模地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产生的心理需求及其满足,这些都是必须引起足够注意并需要加以改变的。现实生活中的利益诉求通过揶揄的口吻,表达了社会大众尤其是底层大众的生存的愿望、生存的要求和他们的生存的方式,但这种方式是有争议的,是不容积极评价的。然而,底层大众毕竟揶揄了主流文化的诉求,并且这种揶揄往往能够一针见血,直抒胸臆,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其次,从文化表达的时空机制看,主流文化往往是文化积淀与文化选择的结果,体现一个国家文化传统和统治阶级的价值判断,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与总结。但是,社会发展现实的文化表达与主流文化反映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一个内在的张力,这个张力就是主流文化不断丰富自己文化内蕴的时间区隔与空间展延。由于山寨文化并不是按照文化的生成规律呈现的,所以它的及时性、现场感恰恰填补了主流文化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时空,即使这种填补并不一定合乎科学,但是文化的解释性同样在山寨文化的意义上得以展现。一旦山寨文化至少一时间表达了草根阶层对社会现实的文化诉求,那么山寨文化的自鸣得意即是对主流文化的揶揄。
三、余论:山寨文化何去何从
山寨文化在我们的文化视野中呈现出别样的风景,它的命运最终如何是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作为亚文化的山寨文化,具备亚文化共同的风格特点:抵抗,而揶揄则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普通民众的文化诉求特点,以想象性解决问题的方式与社会主流文化进行比对,以特殊的符码表达自己的情绪,以另类的文化诉求张扬自己鲜明的个性,风格特征非常明显。然而,山寨文化和一般亚文化的结果一样:必将回归主流文化。
山寨文化从器物层面出现,便是钻了法律空子的投机行为,是以利益驱使而促动的,随着法制的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知识产权所有者法律意识的增强,以模仿起家的山寨文化必然遁形。就很少一部分非赢利性的、充满解构性和颠覆性的山寨文化而言,则是对主流文化的叛逆和颠覆,对于普遍价值的怀疑和解构,相信它会受到主流文化的制约和遏制,并最终回归主流文化。
同时,应该看到,山寨文化在吸纳社会流行文化元素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创新思维是主流文化应以借鉴的,它及时表达社会层面的文化诉求也是应予肯定的,新的文化符码创造和文化传播载体选择的灵活性是主流文化应以学习的,山寨文化这些优势必将为主流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所吸收。
收稿日期:2008-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