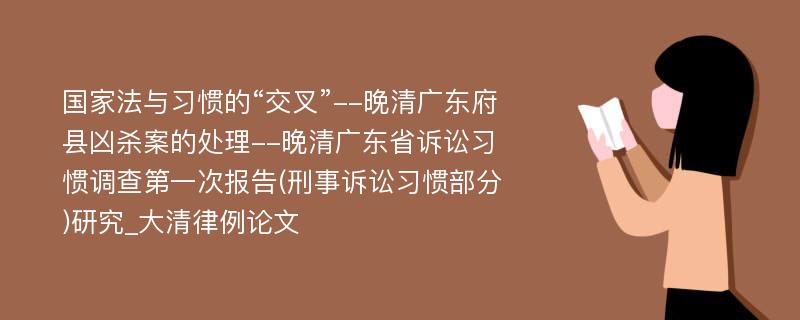
国法与习惯的“交错”:晚清广东州县地方对命案的处理——源于清末《广东省调查诉讼事习惯第一次报告书》(刑事诉讼习惯部分)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习惯论文,讼事论文,报告书论文,晚清论文,刑事诉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对中国法律史,尤其对制度史的研究,我们习惯于将注意力集中于律典本身,而不关注对成文法以外领域的考察。仅注重律典的研究,并籍此作为诠释传统法的基本依据的惯常做法,可能恰好使我们忽略了某些在传统社会法律秩序中发生重要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或许正是我们意欲构建近代以先中国社会和法律时所不应该忽略的。本文将以广东省于清末所进行的诉讼习惯调查后形成的《广东省调查诉讼事习惯第一次报告书》为例,考察晚清广东州县对命案处理的基本诉讼程序,试图探究其中以律令为代表的国法与当地诉讼习惯的相互关系。
正如清廷所强调:“州、县所司,不外刑名、钱谷。而刑名之重者,莫若人命。”(注:参见《钦颁州县事宜》:“圣谕条列州县事宜”一项,江苏书局影印本,同治戊辰首夏,页32。)《广东省调查诉讼事习惯第一次报告书》(注:以下简称《报告书》。)正是以人命案件为调查的开始,调查包括命案的投告、勘验及有无私和、图诈等情形。
一、命案的“告”与“验”
《大清律例》对命盗案件的投告人及投告期限并无规定,因此,从《报告书》的情况来看,广东各地方情形不尽相同。对“第一款”中所问命盗案件的投告人为地保、局绅、差役、邻右还是命案事主,在四十三个州县中,有二十八个州县明确表示:命案主要由“苦主尸亲”投告,地保、局绅、差役、邻右则“呈诉者甚少”甚至“绝不过问”。投告期限则依距城远近不同,有短至一、二日的,也有长至五、六日至十日的。若命案已经逾限,但“一经举诉,皆需准理,不能以逾限驳斥也”,(注:以上引用各处参见《广东省调查诉讼事习惯第一次报告书》:“刑事诉讼之习惯”、“第一款”的报告,原件为抄本。)这一事实,与《大清律例》有关律文的规定不无关系。(注:《大清律例·刑律》中“诉讼”律的“告状不受理”一条规定:“告杀人及强盗不受理者,杖八十。”)
命案既经受理,则州县接下来必亲往勘验。《报告书》的调查并未问及州县勘验的具体情形,但通过于光绪初年曾先后任广东阳山县、电白县知县的褚瑛的记载,(注:褚瑛撰有《州县初任小补》,其中记载了他为广东阳山、电白两县知县时的情形,从序及正文的内容推断,时间为光绪初年,距清末诉讼习惯调查的时间二十年左右。所记内容虽为初任州县者的告诫,但正如作者在“凡例”中所言:“集中所述各节,皆在广东闻见所及”,因而他所记载的有关州县受理词讼的情形,也反映了晚清广东地方的诉讼实况。)我们不难窥见其大概。
命案一经呈告,“惟是人命大事、抢劫重情,所关匪细。其事之大小、难易均难预定,务必亲诣勘验,”并且,“下乡相验勘案务必轻骑简从,以速为妙。”(注:褚瑛撰:《州县初任小补》(上):“亲验命案”、“相验轻骑简从”。)这些告诫,显然主要基于《大清律例》的有关律文:“凡(官司初)检验尸伤,若(承委)牒到,托故(迁延)不即检验,致令尸变;及(虽及检验),不亲临(尸所)监视,转委吏卒,”“正官杖六十,(同检)首领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注:参见《大清律例·刑律》(断狱上):“检验尸伤不以实”。)
验看生伤、尸伤需要专门的技术性学问,这尤其是初上任的州县所不熟悉的。因此《洗冤录》就成为州县从事此类公务的必读书。但同时,经验的积累对担当这一工作也尤其重要。褚瑛以其丰富的经历,不厌其详地描述了因殴、刀伤及各类因毒致死而呈现的较为常见的伤毒命案的不同状况,并讲述了各类尸伤检验的详细步骤。(注:参详褚瑛撰:《州县初任小补》(上):“验看生伤”、“验尸莫避臭”、“银钗探毒”、“断肠草毒”、“伤毒命案”各节。)
在勘验过程中是否存在朝廷所警示的种种陋习,(注: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朝廷所列举的诸种陋习正是许多清代州县的惯常做法。参见瞿同祖著《瞿同祖法学论著集》:《清代地方司法》一文,页449-45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诸如:未及开验,“先命衙役催搭尸棚,”“及至临场相验,官又躲避臭秽,一任仵作混报”(注:参见《钦颁州县事宜》:“验伤”一节。)等现象,据本文现有资料尚难定断。但褚瑛在其《州县初任小补》中多处强调州县官亲验尸伤,而不假手手下的重要性:“伤痕之轻重、事情之真伪了然于胸,心中稍有把握,抑且免后来许多事端,追悔无及,”以至“两造籍口生事”,而“差役人等亦不致任意索诈、滋扰无忌”,(注:见褚瑛撰:《州县初任小补》:“亲验命案”一节。)因而,身为州县,要想将“所关匪细”的人命大事审断详明而不出差错,必须亲力亲为。为了获得准确的结果,他谆谆告诫:“倘尸已发变,切不可避臭、不肯上前,必得眼(跟?)随尸亲将所告之伤验明”,包括“用手按捺”以查明尸身的伤势。(注:见褚瑛撰:《州县初任小补》:“验尸莫避臭”一节。)然而,勘验尸身究属沾染“晦气”,因此,褚瑛提醒:命案验毕并完结相关手续后,“当时不可回头,即到城隍庙浣沐、更衣、行礼,解晦回署。坐大堂、击鼓、排衙,多放鞭炮,”(注:见褚瑛撰:《州县初任小补》:“回署排衙”一节。)以驱逐晦气。
此外,州县所发生的命盗重案相对于“户婚、田土细事”的细故案件而言,终只占极少数,州县官们没有理由不经心办理。况且,这类案件“所关匪轻”,稍有不慎则可能获咎。因此,正如另一位具有丰富州县阅历的晚清官员所言:“而一州一县之中,重案少,细故多,必待命盗重案而始经心,一年能有几起耶?”(注:见方大湜撰《平平言》“勿忽细故”一条。此处转见自黄宗智著:《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195。)这位官员的目的,意在提示“勿忽细故”,但从他的这段议论中,我们正可以看出,清代州县对一年中发生数量很少的命盗重案应当是甚为“经心”的。如此,州县对命案的勘验亦应是在相当慎重的状态下进行的。
对《报告书》第二款的问题:“命案有无既经呈报而旋请免验者?”有州县回答“未曾经见”(或表示没有以及“极少”和罕见的有十一个州县);其余州县均不同程度地表示存在命案既经呈报而旋请免验的情况。至于免验的原因,其中八个州县指出,命案既经呈报而旋请免验者大都为“私自和息”命案,或为“籍尸图诈”所致(有关“私自和息”、“籍尸图诈”,见详下文)。
至于《报告书》第十八款“勘验命案有无当场拦验及滋闹者?”除“尸亲在场哭闹,向官求棺木恤赏者”、“妇人抢地呼天亦事之常有”,以及“因顾全(死者)体面亦有当场具结拦请免验”外,大都表示:当场拦验滋闹者甚少,甚至根本没有。其中,琼州府澄迈县知县的回答颇能说明问题。他说:“勘验命案,一经具报,即轻舆简从,带领刑仵弛赴尸场,对众如法相验、填格、取结。尸,饬该亲属领埋。尚无当场拦验及恃众滋闹者。”显然,只要州县官严格依照规则“对众如法相验”,尸亲、苦主及围观众人自无可挑剔,也就无由启衅拦验滋闹。相反,假如州县官不能严守勘验规则,或迟延、或避臭、或不亲自相验而委之仵作,则如褚瑛所言的“两造籍口生事”就有了可资凭籍的事端,拦验、滋闹势所难免。更何况,“倘遇土豪、恶衿、刁生、劣监便乘风生波,恃系事主言语,倨傲逞刁泼横,任意捏报,希翼挟制官长”,而“(命案)禀详稍有延迟、错误,轻则申饬记过,重则处分撤参。”(注:参见褚瑛撰:《州县初任小补》(上):“命盗案件不可匿报”一节。)显然,任何不愿因此获咎的州县都会谨慎从事,避免启人口舌。
二、命案私和
“命案有无以钱财贿嘱苦主私行和息者?”是调查涉及的第三项问题。从调查的情况来看,私自和息命案在广东各州县地方相当普遍。现摘取其中报告较为详细的几处:
海阳县报告:“潮属命案大都以钱财贿嘱苦主、私行和息。其贿嘱约分数种:由嬉戏致毙者,其贿无多,即可和息。由私愤格毙者,其贿稍多,即可和息。由乡界、族界斗毙者,其贿必多,方能和息。然命案之起初呈诉于官,而真凶先已远飏,其差拘及勒族绅捆送者,非无赖之徒,则贫弱之辈,极少正凶。故苦主每愿以钱财了事,甚有牵连殷富多人、图充欲壑者。”
普宁县:“普民命案报验后,官即就控开等名,指拘被告者。无论真凶、波累,概逃匿不前,旋乃有人居间代恳苦主,或赔贴丧葬,或赔赡养香火。又代为恳于官,准予苦主自悔息事,谓之:外结。其陋习如此。”
临高县:“县属命案,如或因伤致命、或斗殴、或威迫等案,未经呈控,而凶手悔过求和,补回埋葬费若干者,事亦有之,然均听苦主允从与否,不能强使和息。”
罗定州:“命案以钱财贿嘱苦主私行和息,乡曲无知细民,受劣绅、讼棍所哄吓,得以从中渔利,事所常有。”
广宁县:“本境陋习,命案一起,往往株累多人,以为讹诈地步,正凶不获,则株累者无已时,故间有以钱财贿嘱苦主私行和息者。”
饶平县:“命案之牵连隐忍,原因最为复杂。有视为奇货可居而希索重贿者,故凡凶手亲属,苟为家挟厚赀,则不指之为主,令即控之为凶手,反置真凶于不问,以为图诈地步;有自安良弱,因迫挟而隐忍者;有被告阳张声势,以恫吓阴局公人以请和。苦主既惧其势,且为薄利所餂,故依此两端之结果。命案之因钱财贿嘱苦主私行和息者,几于数见不鲜。”
兴宁县:“邑属命案,无论伤痕多少,控凶必列某某主使、某某正凶、某某帮凶、某人庇纵、某人坐视不救,甚有死者仅至一伤,而控凶多至七、八人以至十余人者。其中挟恨牵控者十之一,择肥图噬十常四、五。被告虑及拖累,以钱财贿嘱私和者最多。然多被诬者出钱,而真正凶手反逍遥事外,尸亲亦不过问也。”(注:以上各处皆引自《广东省调查诉讼事习惯第一次报告书》,《报告书》“第三款”的调查。)
由《报告书》的调查可以发现,部分州县特别指出,私自和息命案大都发生于投告官府之前,即,“一经到官,则不能准其私和”,或者,“以财贿嘱苦主,求私行和息者,必在未报官以前。既经官讯验,多难准行。”(注:参见《广东省调查诉讼事习惯第一次报告书》,《报告书》“第三款”肇庆府博罗县、封川县的报告。)但在其他地方显然也存在着例外。(注:比如,根据前引潮州府普宁县的报告,所谓“外结”,显然发生于命案投告到官以后。)无论属上述何种情形,很显然,对命案的介入,官府并不主动。其主要原因是,命案呈报到官后,官府的介入方才开始。而在此之前,已有为数不少的命案通过“私和”的方式解决。而对于明知是“有干例禁”的私和命案的发生,广东州县的普遍态度是:顺其自然。甚至,在官府已介入后,实际上仍有允许两造私和的情况。比如,上述潮州府普宁县的所谓“外结”,即发生于投告官府之后。
其次,可以看出命案的和息基于不同的情形:一是命案真凶主动与事主尸亲达成协议,只要苦主接受凶手的悔过和金钱赔偿(看来主要是金钱的赔偿),一桩命案即可以就此了结;二是“劣绅”、“讼棍”唆使、“哄吓”事主接受和息,以便从中渔利;三是借命案而施株连、讹诈,以求“择肥图嗜”。这种现象很普遍,是导致私和的重要因素。在此情况下,结果往往是家赀殷实者因被牵连而出钱,事主尸亲往往并不十分关心谁为真凶。
朝阳县较为清楚地描述了这一现象并加以评论:“潮属命案数百年来未有不私行和息者,特分迟早而已,此不独近世为然。书也、差也、绅与衿也、闾阎之细民也,均习为固然矣,官其如彼何?人命至重也,而相习若斯,责成难逭顾,有难尽责者。则苦主所控之正凶,非正凶,而有财者也。既被控为正凶,不敢家居,走南洋,案悬矣。即久而获之,按诸情实,案亦难定,所谓真正凶者,反逍遥法外焉。此所以末由办抵,而以钱财贿和之相沿为例也。”(注:引自《广东省调查诉讼事习惯第一次报告书》,《报告书》“第三款”潮州府朝阳县的报告。)
三、借命案诬告、讹索
《报告书》第四款问及有无“自尽图诈”或“移尸陷人”的恶习,三十八个州县不同程度地承认有此现象的存在。
乐昌县报告:“县属地居边隅,界邻湘楚,土著少而客民众。寄居斯土者,……凡有自尽图诈、移尸陷人及捏报人命之案,大率以楚人为最。迨经提讯取结、定期相验,旋即呈求免验。地方官虑及拖累,往往从宽,不予深究,积习相沿。”
龙川县报告:“邑内命案最多虚伪,或自尽图诈,或移尸陷人,种种恶习,皆不能免。即有真正命案,尝有牵涉多人,而指控首列之名,多属正凶之族人,或其邻右之有家赀者,而正凶仅列于二、三名或四、五名。甚有故免其名而不指控者。”
连州报告:“自尽图诈或移尸陷人之案亦间有之,并偶有因急症病故而控指他人致毙者。”
阳春县报告:“或妇女轻生,外家籍以讹诈。或病毙尸首,仇家籍端陷人,此种恶习亦或有之。”(注:以上参见《广东省调查诉讼事习惯第一次报告书》,《报告书》“第四款”各州县的报告。)
褚瑛对上述现象的描述更为详尽:
“不法之徒名曰鱼贩,专以籍尸讹诈为务。不论远近,凡有路毙无名乞丐,或江海浮尸,或年老无依、孤贫无人埋葬者,甚至有穷苦不堪之人病将垂死者,卖与鲨鱼贩做假伤讹诈,百奇千怪,实堪发指。一有死尸,即串通本地烂衿奸匪,买嘱无赖男子、无耻妇女,或为死者之父母伯叔兄弟,或作儿子媳妇子侄亲属。本属乞丐孤独,忽而儿孙媳妇俱全,男尸则哭父号爷,女尸则呼妈唤母。一见官到,即假号喊叫、诉说冤苦。问其情由,无不含糊支离、茫然莫对。且距死尸甚远,站立遥望,不敢近前伏视。掩面假号,毫无悲伤。种种虚诬,难以言喻。尝见路旁死尸数日无过问者,迨至地保报验,忽有哭儿者、哭夫者、伯父者,男男女女号叫不已。亦为遥望,不敢近前。既验明,乃无名乞丐病故者,皆烂棍串通买嘱,希图讹诈也。诸如此类,当未经报案之前,奸匪烂衿人等,开列各乡富户弱族姓名,某某为正凶,择肥而噬、任意讹诈。”(注:参见褚瑛撰:《州县初任小补》(上卷):“假命讹索”一节。)
此外,褚瑛还讲到其任广东电白县知县时遇到的一桩借死尸诬指仇人的案件。该案死者患“疯疾”多年,被族人以为已无药可治,于是族人与死者商量:“尔早晚是死,又不能入宗祠,倘能自己服毒而死,具控(与外族)争水被殴致命,若官司得赢,准入祠堂”,于是死者服毒身死,由于“疯毒发变”,致使尸身“块块青黑”类似殴伤,故死者族人以此诬陷正与他们争水源的外族人。但最终,知县褚瑛运用他丰富的尸检知识和经验,迫使事主不得不供认了案情的原委,诬陷没能得逞,死者大概也因此终不能被准入宗祠。紧接着,又举另一案为例。该案死者因偷牛而被失主所殴并被呈告县衙,盗案尚未及批示,被控偷牛者的妻子即控称其丈夫被殴致死。通过仔细检验尸伤及采用“银钗探毒”的尸检方法,褚瑛再次查明原委:原来死者起初偷猪,被失主发现。失主欲呈控,被劝阻。但死者不思改过,复又偷牛被获。因惧怕到案以后皮肉受苦,于是服烟土身死,意图以被“殴伤身死”来讹诈、拖累呈告人。(注:此案详见褚瑛撰:《州县初任小补》(上卷):“伤毒命案”一节。)
与此相关,我们发现捏控诬告不仅仅发生在命盗重案中,在其它刑事案件中也频频发生。
《报告书》第十六款:“刑事被告人而无确实证据者,如何处理之?”各州县主要处置方法包括:
1、谕绅查覆,访诸舆论,分别处理之;2、常以押候查明处理之;3、通禀请示办理;4、由公正绅商取具保领;5、不准理;6、反坐原告;7、从宽处理,将被告之名摘除。其中,“谕令绅耄查访”、“取保候质”及“绅商取保”的做法正如饶平县所说,是体现了“罪疑惟轻”的古意,因而看来是被采用最多的办法。(注:《广东省调查诉讼事习惯第一次报告书》,《报告书》“第十六款”的调查。)
其次,通过对上述办法的总结我们还可以发现,有为数不多的州县提到了:一旦发现所告之罪无确实证据,则反坐原告(有五个州县提到)。但事实上,对原告的反坐可能也仅停留在威慑或轻微责罚的程度上。
为增加官府受理案件的可能性,原告往往凭空捏造情节,以刑事罪名诬控被告。兴宁县报告说:“惟邑属诉讼向来不分民事、刑事,往往因民事争执而捏从刑事情节。如本系钱债口角,而捏称拦抢纠劫;本系田土争执,而捏称挟恨伏杀,多系讼师唆摆,希图动听。一经讯出实情,多就案断结,不予深究,以免讼嫌。”(注:《广东省调查诉讼事习惯第一次报告书》,《报告书》“第十六款”的调查。)
此外,在《报告书》的“民事诉讼习惯”部分,朝阳县报告说:“惟县属讼词支饰捏造特甚,即纤微之事亦无不捏架大题,往往口角争执,互控抄抢,及至当堂盘诘,均属子虚,件件类然。诬亦不可甚办,安能取愚黔首而尽绳之?县属坟山之案几居其半,毁坟之事,几于数见不鲜,而互控劫棺与骸者,时时而有,伪者居其半。”
在这里,无论诬控“拦抢纠劫”、“抄抢”还是“劫棺与骸”,均应构成诬告。由此,普遍存在的“非重情案件”中的上述现象同时也从另一侧面揭示了诬告同样出现于命案这类“重情案件”中的原因,即:诬告实为当地由来已久的“恶习”。
四、捕限
《报告书》第十七款问及:“刑事案犯,有无终年拘不到案以至案悬莫结者?”对此,四十三个州县均确认普遍存在此种现象,试举几县为例。
封川县:“刑事案件终年拘不到案者,以致案悬莫结亦常有之,缘县属水陆交通、轮帆络绎,逋逃甚易、查缉难周也。”
朝阳县:“县属距汕埠近,出洋甚易。大凡关于刑事案件,旬日不获犯,则难获矣。……事初起犯,暂避他乡,事急则逃香港或南洋,故旬日不获终年拘不到案者往往有之。”
普宁县:“普民遇有身犯刑案,类多逃匿外洋、贻害亲族,就中以命盗案为独多。故官差拘不到案,案悬终年,仍未能结者不一而足。”
文昌县:“刑事案犯终年查拘无获、案悬莫结事所恒有,盖县属出洋雇工之人最多,一经犯案,潜逃出洋,迄难弋获。”(注:参见《广东省调查诉讼事习惯第一次报告书》,《报告书》“第十七款”的调查。)
因此据各州县报告的情况来看,案犯拘不到案以至案悬莫结的主要原因是:粤省濒临海洋而紧邻外洋,案犯往往于事发之后潜逃出洋,因而致使终年拘不到案。其中往往以命案居多。
各州县对缉捕案犯的态度通常应是主动积极的。由褚瑛的感受而言,对案犯,尤其是案情重大的贼盗及命案嫌犯的缉捕,显然是一件极需慎重的事情,他甚至不惜重金。他说:“银钱之贵重,孰不知撙节为妙。然地方官有不能节省者,……有著名贼盗、紧要犯人、竖旗拜会等事,奉行严拿吃紧,饬令重出赏格花红,构线缉拿,动辄数百两,更不能节省也。尤宜不论何款何项,甚或出利揭借、典质衣物,随时给发,方期于事有济。”(注:参见褚瑛撰:《州县初任小补》(上卷):“勿惜赏费”一节。)
尽管如此,因案犯不能拘捕到案而悬而不结的现实仍难改观。其中,捕差的疲弱不力显然也是致使刑案悬而不结的原因之一。潮州府普宁县就抱怨说:“普属差役,奉缉案匪,历来百不获一。其疲玩无能几成一丘之貉。”类似的反映还可见于其他州县的报告。(注:参见《广东省调查诉讼事习惯第一次报告书》,《报告书》“第十二款”的调查。)
五、国法与习惯的“交错”
命盗案件在传统上被称之为“重情”案件,历来被认为是地方州县的大事,正所谓“人命关天”。但由上述研究我们发现:成文法律规范,包括象《大清律例》这样的清代基本法律,在命案的处理中并非都被严格执行。在上述各个诉讼环节上,粤省州县地方官对案件处理的依据事实上大量来自于成文法体系之外。
首先,如上所述的普遍存在于广东州县地方的私和人命的做法,正是《大清律例》所禁止的。《大清律例·刑律·人命》的“尊长为人杀私和”一条的律文规定:
“凡祖父母、父母、及夫若家长溪人所杀,而子孙、妻妾、奴婢、雇工人私和者,杖一百、徒三年。期亲尊长被杀,而卑幼私和者,杖八十、徒二年。大功以下,各递减一等。其卑幼被杀,而尊长私和者,各(依服制),减卑幼一等。若妻妾、子孙,及子孙之妇、奴婢、雇工人被杀,而祖父母、父母、夫、家长私和者,杖八十。受财者,计脏,准窃盗论,从重科断。(私和,就各该抵命者言,脏追入官。)
常人(为他人)私和人命者,杖六十。(受财,准枉法论。)”
由这条律文的规定视之,上述私和人命的做法即是犯罪行为。但看来这种行为不仅没有被依法查究,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被广东州县地方官民所普遍接受的、处理人命案件及其它刑事案件的一种习惯。(注:在《报告书》(民事诉讼习惯)“第六款”的调查中,兴宁县报告:“(民事案件)命令息讼,即批投局或谕局处息者也。亦有已经差传旁观处息,取两造遵结呈请和息者,惟多不叙明是非曲直,只浑言置酒和好而已。刑事如斗殴受伤等,亦有置酒和好者,为民省事,亦多批准。”)
其次,依照《大清律例·刑律》“诬告”一条的规定:“凡诬告人笞罪者,加所诬罪二等。……至死罪,所诬之人,已决者,(依本绞斩)。反坐(诬告人)以死。(虽死罪,仍令备偿取赎,断付养赡。)未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就于配所)加徒役三年。”
此外,《钦定光绪会典事例》也载明:“控告人命如有诬告情弊,即照诬告人死罪未决律治罪,不得听其自行拦息。”(注:参见《钦定光绪会典事例·刑部·刑事诉讼》卷八百一十八所载事例。)但是,并未见州县官们按照《大清律例》及事例的相关规定来处置,否则就不会“不予深究,以免讼嫌”,并继而发出“诬亦不可甚办,安能取愚黔首而尽绳之?”的慨叹。于是,对所诬控事项“统由绅衿调处,两造认可了事,地方官不能深究也。盖由法律上视为重大之件,而社会上成为习惯之事。”(注:《报告书》(民事诉讼之习惯):“第一款”的调查。)在习惯与法律相冲突时,终遵循“社会上成为习惯之事”。
再次,对于贼盗及命案嫌犯的缉捕期限,《大清律例·刑律·捕亡》的“盗贼捕限”一条规定:
“凡捕强、窃盗贼,以(事发于官)之日为始。(限一月内捕获)。当该捕役、汛兵一月不获强盗者,笞二十;两月,笞三十;三月,笞四十。捕盗官罚俸两个月。捕役、汛兵一月不获窃盗者,笞一十;两月,笞二十;三月,笞三十。捕盗官罚俸两个月。限内获贼及半者,免罪。
若(被盗之人)隔二十日以上告官者,(去事发已远),不拘捕限,(缉获)。捕杀人贼,与捕强盗限同。(凡官罚俸,必三月不获,然后行罚)。”
《钦定大清光绪会典事例》载明:“凡命盗一切重案,正犯脱逃,即行差役密拿,并开明年貌、事由,详请通饬本省州县一体协缉。偿未弋获,致犯远飏,逾限未获,仍将本案承缉官按限查参,照例分别议处。”(注:参见《钦定光绪会典事例·刑部·刑事捕亡》卷八百三十七所载事例。)然而,由粤省地方案犯一遇案发即“远飏”,以致终年拘不到案、案悬莫结几成风气的事实可知,上述有关捕限的规定,以及可能施之于负责缉捕的差官的处罚,对于晚清广东州县地方而言,显然都并未发生作用。
由上述材料视之,以律令为代表的国法虽然是地方对案件处理的依据(如本文中对命案的检验,我们得出的显著印象是,州县官处处以律令的规定行事),但就晚清的粤省州县地方而言,在命案这类重大刑事案件的处理中,国法并非事实上的唯一依据。粤省之诉讼习惯在对案件的处理上事实上起到了超越国法的作用。因而,至少就本文所掌握的广东一省的情况而言,在命案之处理上,国法与习惯显已构成共同之依据,并且,由于习惯与国法内容的冲突而使得两者间呈现出时而“交错”的状态。而作为负责处理案件的地方州县官,对于此种习惯与国法并存且相互“交错”的局面却是安之若素,表示颇能接受。正如潮州府朝阳县令所说:
“法律一定者也,而习惯无定者也。习惯之例,原因复杂,非一朝一夕之故。是以,国家法律之力,恒不及社会习惯之力,所谓积重难返也。”(注:引自《广东省调查诉讼事习惯第一次报告书》“第三款”潮州府朝阳县的报告。)
在这里,习惯被置于与国法并论的位置。并且,“一定”的法律相对于“非一朝一夕之故”的习惯而言,国法的效力显然不及积复杂原因、经日积月累、已成“积重难返”之势的社会习惯(按时常也被时人称之为“恶习”或“陋习”)的效力。实际上,要想成为称职的清代地方州县官,除了必要的对律例的了解以外,谙悉一方风俗习惯更是不可忽视。因此,对于襄理州县刑名的幕宾而言,研习律例的同时亦需深通风俗人情。曾为著名幕友的汪辉祖就说:“为幕之学,尚读律。其应用之妙,尤善体人情之所在。盖各处风俗往往不同。必须虚心体问,就其俗尚所宜,随时调剂,然后傅以律令,则上下相协,官声得著,慕望自隆。若一味我行我法,或怨集且谤生矣。”(注:参见汪辉祖著《佐治药言》:“须体俗情”一节,此处转见自滋贺秀三、寺田浩明、岸本美绪、夫马进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页64。)
故而,若一味以“律”为准而“我行我法”,必致案件难获理想的解决而使“怨集且谤生”;但若能于人情风俗“虚心体问”,并以之“随时调剂”,则算是懂得了律的“应用之妙”。而其中以风俗(或习惯)“随时调剂,然后傅以律令”一语,又分明透露出风俗(或习惯)与国法何者为急的意思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更多地理解以下的这段话:“中国法的基本法源是习惯。只有习惯才与民众的感觉一致,根据习惯能够按照万物自然的秩序确定各人的权利与义务。中国的习惯依国内各自独立存在的共同体之数而呈现出多样的形态,实际上是不可胜数的”(注:此为儒勒·达维德(Rene
David)在《比较法概论》一书初版中提到的,此处转见前揭《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一书,页76。但引用该段文字的作者滋贺秀三并不赞同儒勒·达维德的观点,认为:“在中国,习惯并不意味着与‘情理’不同的另一种实体”。由于作者并没有十分清楚地指出所谓“情理”的确切内容,而对“情理”的讨论又远远逸出本文的范围,为本文所不能胜任。因此,本文仍使用当时人自己也采用的“习惯”一词。)
虽然,是否能够定论“中国法的基本法源是习惯”还要等待相当广泛的对案卷材料的研究作出之后,但将它运用在晚清粤省州县地方对命案的处理中时,我们至少可以同意:习惯确实与国法“交错”存在,决定了案件的处理方式,带来了与国法的规定并不一致的后果。这种现象大概便是有学者所说的:“(中国古代法)它实际上是由多种渊源构成的复合体,其间充满了离散、断裂和冲突。”(注: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一文,收在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一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415。)尽管习惯与国法间存在着冲突,但由于它“很久以来便持续不间断地存在,从而便获得了法律效力”,(注:参见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Thompson)著:《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页97。)这恐怕就是上述那位县令选择让国法适从习惯的真正原因。因此,当我们试图对近代以往中国的法律状况进行了解和研究时,我们的视角绝不能仅局限于成文法的体系范围,(注:对中国古代成文法的研究本身也还存在很多迄今仍被忽略的问题。以清代为例,除《大清律例》的研究获得相对较多的注意之外,对“条例”、“事例”、“则例”及《清会典》中相关内容的研究还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否则,我们对那时中国法律及社会的理解将是极不完整的,因而,我们的研究也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远离历史事实的自说自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