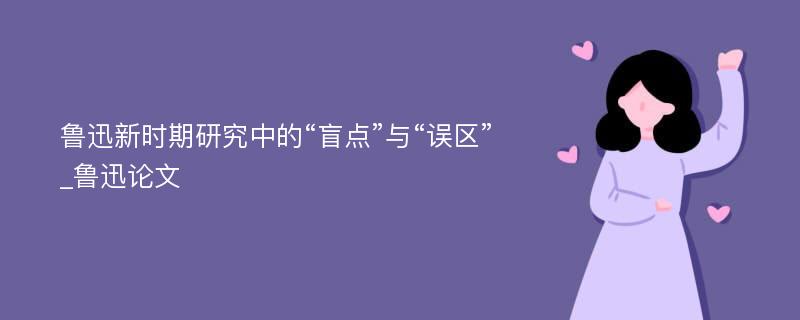
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盲点”与“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盲点论文,新时期论文,误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研究早已成为一门独立而富有特色的学科,但与其他传统“国学”比,与世界上一些历史悠久的学科比,它又显得年青、稚嫩。就以新时期的国内鲁迅研究而言,虽然可用“拓展、深化、突破”来概括其大好态势,其成就确实卓著斐然。但又不能否认,由于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造成我们的鲁迅研究仍存在严重的“盲点”与“误区”。
一
先说“盲点”。
这是指,我们的鲁迅研究至今还存在许多空白点与模糊点。举其要者,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世纪之交鲁迅的历史定位
从19世纪走向20世纪,鲁迅正是血气方刚、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处于人生旺盛的黄金时代。再延伸到从22岁起东渡日本留学7年,鲁迅先后创作《别诸弟三首》、《莲蓬人》、《祭书神文》、《惜花四律》、《自题小像》,并有功底雄厚、影响深远的多篇论文:《中国地质略论》、《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还编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给中国文坛引进一股清新的空气。特别是,此期间,他“弃医从文”,办《新生》,参加“光复会”等等。都是鲁迅在其所处的世纪之交,为自己谱写的光辉一页。尽管属于鲁迅的早期,但给青年鲁迅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定位?他是爱国主义者、进化论者、人道主义者、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个性主义者、启蒙主义者,抑或是虚无主义者、唯心主义者?众说纷纭。至今仍然缺乏权威的科学论断。争论是有必要的,说明这个问题的研究尚有潜力,尚有余地,大有文章可作。但从另方面去看,面对一个公认的历史伟人,史料又那么齐全,明摆在那里,研究来研究去,尚且得不出比较公正的评判,甚至个别问题似乎越争越复杂化,就有点不正常了。譬如关于鲁迅与人道主义。有人连什么叫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好是坏,都搞不清,又如何去界定鲁迅早期前期乃至后期的思想?说人道主义坏者,不敢往鲁迅身上抹;说人道主义好者,硬要一古脑儿往鲁迅身上堆。这就是离开鲁迅的个人实际或曰偏离鲁迅文本来瞎说了。只要鲁迅主观上真的属此而非彼,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我们就要大胆的承认。既不能误解曲解,也不必为尊者讳。对鲁迅早期的历史定位本来是不难的,希望能尽快得到圆满的解决。
(二)世纪之交的鲁迅研究的突破
我们的鲁迅研究快有100年的历史了,其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从1913年开始历经发轫期、迂回期、发展期、非常期、开拓期、丰收期、罹难期、过渡期,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当今,面临新世纪的挑战,鲁迅研究的“明日之星”在哪里?老一辈鲁研学者的肩膀能爬上去吗?能超越吗?或者对某些论断能提出质疑和异议吗?包括某些“定论”能持否定态度吗?我们的鲁研事业能否再创辉煌关键在突破,而突破谈何容易?从何入手啊?不过,只要面向未来,并有强烈的使命感,中国鲁研界会以崭新姿态表明:一个真的人的鲁迅即将回归。鲁迅世界被科学地开发,鲁迅研究将进入学术的“自由王国”与“独立王国”,不受政治干预,其“华盖运”也会随之摆脱。在民主、平等、自由、独立的争鸣氛围中深入研究鲁迅的方方面面,甚至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心目中的鲁迅。这样,鲁迅这个历史人物就不会越走越远。他将继续影响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所以,在文化转型期学习鲁迅,用现代意识重铸民族魂,便是新世纪鲁迅研究的新课题。当然,也可谓新突破。至于找突破口,说难也不难。关键在两点:一是承认鲁迅的“民族魂”价值;二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这不仅仅“回到鲁迅那里去”,还要从鲁迅那里跳出来,更高层次探视鲁迅世界的里里外外。由鲁迅看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又在大文化中看到鲁迅的位置与作用。
(三)鲁迅的时代局限性
鲁迅无疑是时代的骄子。而时代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稍有一点唯物主义知识,就不会以当代人的眼光去苛求一个历史人物。鲁迅绝不是什么完人。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足乃至失误(譬如极“左”思潮的影响,有过偏激情绪与某些历史误会,等等)。但如何运用历史的标尺去量度鲁迅的时代局限性,才不至于步某些人的后尘去肆意曲解鲁迅?才是科学而全面地认识鲁迅?例如,鲁迅是反帝反封建反一切恶势力的勇士,但为了孝道,他也无奈地接受母亲送给自己的“礼物”——包办婚姻,既伤害了自己,又牺牲了别人。对这个问题,有人为鲁迅辩护,以为鲁迅敢于弃朱安而爱许广平,是智者的选择,勇者的举措。有人则一味责怪鲁迅,说他屈服于封建礼教,甚至是“违反婚姻法”。除了后者纯属笑话之外,我认为,都不难理解。《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不是反抗旧礼教最激烈,最终还是要去当“候补”吗?鲁迅毕竟是人,而且又正好是个特定时代无奈的孤独者,真可谓“苦闷的象征”,他是应该得到体谅的。再如,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多事之秋,国难当头,鲁迅却被冷枪暗箭包围着,他不得不“横站”而迎战出击,不少论争难免有过激之词,受到某些极“左”思潮的影响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离开当时的背景,不分青红皂白,横加鲁迅是“骂人”“整人”专家的罪名,则太冤枉了他。“事后孔明”谁都可以当,但用以研究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历史现象,则未免过于轻浮、草率。不过,鲁迅研究既属学术范畴,又离不开政治,难度之大,深度之大,不可否认。唯其如此,一个有良知的研究者,绝不会对鲁迅的某些时代局限性与个人缺点夸大其词,或故意挖苦中伤乃至人身攻击。我们必须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保护学术空气的清新纯洁。
(四)“鲁迅学”的创立与研究
鲁迅是公认的“万有文库”。作为全方位研究鲁迅的一门重要学科,“鲁迅学”的创立已被国内外鲁研学者所认同,并以多方面的研究去充实它,发展它。但严格说来,本世纪内的“鲁迅学”还处于立项阶段,宏伟而艰巨的学术工程尚未真正运作,抑或刚刚上马。值此世纪之交,虽然已有一些论著,也有不少专家撰文探讨关于“鲁迅学”的问题,但一般都是在表层与小范围内做些文章,远远没有深入实质性与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尤其关于“鲁迅学”的内涵、个性与走向是什么?有哪些特殊意义?将发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都有待我们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过去,曾有人把“鲁迅学”当作社会学的分支来看待,夸大其功利性,结果,鲁迅一再被“利用”,一再被扭曲。这样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否则,“鲁迅学”将滑入歧途。某些传统“国学”曾被强权政治奸污,或遭受种种人为干扰,已有点面目可憎,成为前车之鉴。我们的“鲁迅学”还年青,尤其要百般警惕,再也不能充当什么“工具”了。
(五)鲁迅“未来学”的探索
鲁迅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他同别的历史伟人一样,其“未来学”也是有的,但实质怎么样?如何去探索?每个鲁迅研究工作者都要关注这个问题。而且,谁能把握住鲁迅的未来,谁就占有鲁迅研究的主动权,并有机会有可能攀登“鲁迅学”的时代高峰,成为鲁迅研究事业的“明日之星”。至于本世纪末、下世纪之初,我国鲁研界已进入第几代?各有各的说法。我却认为没有划分的必要。而且谁是一代之主或曰代表人物,都难以得到大家的认可。排座次是多余的,毫无意义的。若以事业为重,我的忧患意识则日见浓重。因为,只要我们冷静地观察、分析一下自己的队伍,老专家日见减员,中年一代面临各种干扰与挑战,专注鲁迅的也逐渐少了。青年学者中能称为专职鲁迅研究专家的屈指可数,鲁迅作品与鲁迅精神的宣传普及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更为惨淡,一些专心搞此项工作的人反而被讥为“珍稀动物”,不被人理解。长此以往,鲁迅的“未来”不是极可悲观的吗?不过,不管怎么样,希望总是有的。只要火种不灭,只要“民族魂”还在,国人是不会忘掉鲁迅的。试想想,正当人们发生信仰危机之时,所发出的“呼唤鲁迅”、“如果鲁迅还活着”、“鲁迅你在哪里”,等等,决不是苍白的空喊。正是民心所向、民魂所在的表现。当然,主观愿望如何与客观实际相统一,相吻合?仍须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六)“民族魂”鲁迅与鲁迅文化传统的社会价值
“民族魂鲁迅”,或曰“民族的象征”,这是历史赋予这位文化巨人的定位。中华民族给自己的骄子鲁迅戴上这样的光环,并使之代表现代文化的传统与方向,其意义是深远的。但时至当今,却有人在来自各方面没完没了的干扰中困惑。甚至有意无意的淡化这个“民族魂”,想抛弃这份文化传统,派生“魂不附体”的怪胎,或重演“传统失传”的悲剧。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最担心的是,在此大潮那大潮的冲击下,什么“民族魂”、“中国心”;连同社会公德都可以只字不提了,唯金钱是万能,金钱最干净。如果社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鲁迅自然可有可无,甚至真的远去了。如果说悲剧,这便是目不忍睹的一幕。所以,我们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宣传鲁迅,决不只是做做学问,当作一种职业、一项任务,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人心目中树立鲁迅的伟大形象,招回崇高的国魂,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唯其如此,才算负起我们真正的历史使命。舍此而求他,薄此而厚彼,本末倒置,去钻牛角尖,去攻冷门,专作花样文章,甚至搞所谓“钱文交易”、“名利生意”,以研究当“敲门砖”,岂有什么价值可言?当然,我们并不反对鲁迅研究工作者兼顾其他。相反,研究鲁迅是不能脱离历史的,尤其不能无视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我们说鲁迅象征“民族魂”,代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并非“独尊”鲁迅。开创中国新文化的功劳,是他与其广大战友并肩战斗的结果。但历史地看问题,鲁迅的“主帅”地位谁也难以取而代之,其社会价值也是毫无疑问的。
二
再说“误区”。
由于政治运动干扰,思想上的忽左忽右,长期来我国鲁研界受害非浅。即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鲁迅的误导、误读、误解仍然不少。当然,“误区”与“禁区”确有差异。“禁区”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有胆识、有勇气便可冲破、逾越,而“误区”常常蒙着一层迷雾,要用足智慧与眼光才能识别,其难度是较大的。
(一)“全能”的鲁迅与“过时”的鲁迅
国人爱走极端。在对待鲁迅的态度上也时有波动,时有偏激。要么把鲁迅捧为神仙,可以包打天下,包治百病。为了配合什么运动,什么中心,总“利用”他老先生出来说教,为自己辩护,或者根本就不敢正视鲁迅的精神与思想,想当然地胡诌一通。这是对鲁迅的一种亵渎与侮辱。要举的例子可真多。“文革”时的荒唐就不必说了。之后,不是有人说鲁迅是计划生育的好典型吗?不是有人主张以鲁迅与许广平自由恋爱为榜样,用“同居”来代替结婚吗?更甚者,有人根本不理解鲁迅“个性主义”、“启蒙主义”的背景与本意,而生搬硬套于今天的道德规范与思想教育工作,以为照鲁迅的办法便可解决问题。再有,当我们在拨乱反正中,批了极“左”的思潮与实用主义,又有人突然炒起陈旧的“过时”论,以为鲁迅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已失去历史光彩,不合时代潮流了。鲁研事业也变成供人观赏的“小摆设”。甚至有人公然声称:“鲁迅没有什么好研究的!”“鲁迅没有前途!”其实,说穿了,不论是“捧”还是“贬”,总根在于“利用”价值的高低。名人最可悲的是被“利用”。鲁迅早就预见在先。把人引入这个“误区”的人,恐怕并没有真正读过鲁迅的书,不知道鲁迅如是说,不然,他们怎么会如此露骨,连一块遮丑布都没有呢?但愿我们的鲁研界能真正保持一片净土,万勿被污染,被利用了。一旦生出“利用”的旧念头,研究就不成为研究,其产品当然是不合格的蹩脚货。
(二)从“神化”到“鬼化”
这是一种更卑劣、下作的手段。“文革”时把鲁迅捧上“神坛”,但后来,有些人为了贬损鲁迅,又若于无从下手,只好肆意丑化、“鬼化”鲁迅,时而说他忘恩负义,领国民党的薪水来骂国民党。时而说他极“左”,专会骂人整人,说什么中国新文坛许多“精英”是被他骂倒骂臭,以致永世不得翻身的。时而诬他“反党”,甚至是日本特务包养起来的“汉奸”。至于生活作风方面,就更加离谱,如说他与弟媳羽太信子有染,与女作家肖红有暧昧关系。总之,鲁迅在某些人心目中简直成为坏人、罪人了。稍有一点良心、一点责任感的人,都不会如此信口雌黄。对鲁迅的人格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把握,置鲁迅特殊处境于不顾,连做学问的普通常识都没有,又怎么能认识鲁迅呢?再这样的“化”下去,鲁迅真的要从中国历史上消失。连王朔都可以取代他,甚至公开发表文章骂他,说他一无是处。有人还视之为眼中钉,非清算他不可。否则,周作人、梁实秋等又如何能走红?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任怎么把捏,也不会叫“周氏兄弟”的是非黑白颠倒过来。梁实秋还是那个梁实秋,他能在中国文坛上改唱红脸吗?
(三)“重评”与“还原”的背后
在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一股热潮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重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重大而又素有争议的人与事,其中当然也包括还原鲁迅本来面目,给予重新评价的问题。如果坚持真理而又采取科学的态度,这未尝不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而且据说已有一些可喜的成绩。但观其事态的变化却不容乐观。因为有人要搞“否定之否定”,非把历史彻底翻过来不可,即按他们的逻辑推理,凡被鲁迅批评过的都是好的,鲁迅及其战友则毫无疑问,全错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帅也该易位了,当年的三、四流作家不分红脸黑脸,均可粉墨登场,鲁迅研究甚至要变成鲁迅批判。一部鲁迅研究史更要重写乃至全盘否定。这不是我在小题大作,耸人听闻。只要你略为关心一下前阶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等),便不难嗅到一种从外面吹进来久已未闻的腥怪味。幸而已有不少同志撰文反驳,或予以澄清某些混淆视听的传闻。在此,就不必赘述了。本来在某些人的“重评”与“还原”背后,埋藏着“私货”(包括“历史误会”与“个人恩怨”),路人皆知。但由于旗号打得冠冕堂皇,加上一股潮流的影响,这种误导的确使某些缺乏独立思考而比较幼稚的人,神经颤抖好一阵子。现在,该是时候了。我们要冷静地吸取这些教训,正确理解、运作“重评”与“还原”,使之纳入实事求是的正常转道。
(四)想象与臆造
与上边某些观点和作法同出一辙。有些人无视历史,也根本不要历史,专靠一个乖巧的脑瓜子,去凭空想象、推理乃至臆造,说什么鲁迅在上海反对周扬就是“反共”,鲁迅劝个别朋友不要参加某个团体组织,就是有意叫人不要参加中国共产党。有的还反复写文章,说鲁迅与毛泽东见过面(也有的传媒盲目地一再转摘了)。有的还通过“回忆”,说他与鲁迅有亲密关系,并以此作为“落实政策”的资本。有人看到鲁迅故居墙上挂两幅裸体画,便由此大彻大悟,说鲁迅内心有两个相反的世界,或说鲁迅有两副面孔。有些鲁迅研究工作者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与动机,对此反而发生浓厚的兴趣,以讹传讹,甚至添油加醋,以为发现什么“新大陆”。问题由此而复杂化。不明真相的人或别有用心者都跟着起哄,唯恐天下不乱,大树不倒。诚然,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天真幼稚,人云亦云;一是心理太阴暗。最需警惕的是后面这种人。他们当然不是真正的鲁迅研究家,或由于立场、世界观使然,或出于自己的什么利益,对鲁迅有成见有偏见,采取敌视的态度(如:苏雪林、郑学稼等辈的“反鲁”专家),是不难理解的。问题在于我们鲁研界的一些同行、朋友,有时也出现这样那样不该有的偏差与失误。说是有意吧,似乎不会。说是无意,倒也费解。因为,毕竟都是有文化有头脑的学术研究者,可不能轻易被误而又随便误人啊。科学研究不能凭想象,更不容臆造。面对一个严肃的重要课题,研究者的责任感与科学态度是不可缺少的。
(五)“宗教化”的鲁迅
鲁迅对宗教(特别是道教)发表过一些精辟的见解。但他关注宗教不是什么信仰,更不是要当什么教徒,而完全是为了研究历史,研究文化,从而切入研究中国。正如他所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但有些同志可能从个人角度与兴趣出发,硬要把鲁迅拉进混沌的宗教圈里面,以为鲁迅本人与作品时时弥漫着宗教味,好像鲁迅作品的字里行间全都充满着宗教思想,他的一切行动都与宗教有关。一个严肃而高尚的人的鲁迅,被弄得神乎其神了。我们认为可以从宗教角度研究鲁迅,但决不能将鲁迅“宗教化”。你可以选定《鲁迅与宗教》这个题目作文章,但切勿引起误会,以为鲁迅一生与宗教密切相关,别的什么信仰、理想一概可以淡化,甚至能否称之为共产主义者,都值得怀疑。特别是在当今“文化热”的影响下,“泛文化”的涵盖面无边无际。有人潜心从文化角度(包括宗教文化)研究鲁迅,并取得成果,是可喜的。但“文化”的内涵丰富毕竟不同于“泛文化”(譬如“厕所文化”、“垃圾文化”之外,又有“烟文化”、“酒文化”、“赌文化”、“毒文化”乃至“妓女文化”等等)。宗教仅仅属于文化一个小小的方面。文化巨人鲁迅怎么能用“宗教”来概而括之?况且,突然掀起“宗教热”毕竟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与鲁迅研究当然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果非让鲁迅就范“宗教”不可,那就属于另一码事了,能奈他何?!反正,我们鲁研界是难以接受的。
(六)鲁迅的“名人效应”
在人们热衷推崇“轰动效应”的时候,“名人效应”是最叫座的一种。中国名人知多少,所产生的“效应”自然不可低估。但对于越来越劲的“鲁迅热”或别的什么“热”,我们却要冷静地审视,不可被某些表面现象所迷惑。譬如,争着编辑、出版新的《鲁迅全集》,有值得高兴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也夹杂着借鲁迅赚钱的私货。正同鲁迅故乡乃至全国各地一下子涌出那么多私营“三味书屋”、“阿Q商店”、“孔乙己公司”、“咸亨酒店”、“华老栓药店”一样,其生意之红火,就是鲁迅的“名人效应”所致。我们可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或一口咬定:中国人又空前热爱自己的“民族魂”鲁迅了。要进行一番具体分析才好。四川不是有家酒店打着地主恶霸“刘文彩”的招牌吗?面对这样的“效应”,我们应该沉痛地想到什么?如此突然“热”起来,是否别有原因?鲁迅研究作为一门社会学科,只要不搞政治运动,总不能忽冷忽热,自有它的发展规律在。对于某些人为造成的这个“热”那个“热”,吹这股“风”那股“风”,我们始终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盲目地跟着嚷嚷,起码是不成熟、不稳重的表现。何况我们的研究对象正是中国现代文坛最伟大的名人。只要老老实实地研究得好,成果显著,其“效应”自然会大,不需强加什么“包装”之类。至于社会上有人借鲁迅之名来达到某一种目的,明眼人是容易识破的。研究者应该独立思考,不轻易受影响才对。
(七)从打标签到朦胧论
鲁迅研究易走极端,久已闻名。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学术研究过于政治化,爱给鲁迅戴上许多桂冠,终极评价达到吓人的程度。其实,那都是给历史人物打标签罢了,根本没有客观的论证、分析,谈不上什么研究。而到后来,由于吃洋不化,或一味引进外国新名词新术语,硬堆到鲁迅身上,因而出现一些令人费解的鲁迅研究朦胧论,不但学贯中西的老专家看不懂,中青年学者望而生畏,连作者本人也只是昏昏瞑瞑,懵懵懂懂,半天说不出一点所以然来。此类文章动辄洋洋万言,或者一抛就是砖头似的一大本,文字严重欧化、洋化,不知哪里断句,甚至不时插入“蒙太奇”、“意识流”之类,以别人看不懂来炫耀自己学问的高深渊博。可惜鲁迅早已作古,不然,他老先生是要出来抗议的。至少不敢承认那是“研究”他的文章或著作。我们有些喝几口洋墨水的年青人,不首先把功夫用在鲁迅的文本上,又不懂得多少“国学”,反而津津乐道欧美这个“派”那个“派”的思潮,抓到洋人某些片言只语,如获至宝,便匆匆忙忙、生生硬硬往鲁迅那里套,到鲁迅作品中钻牛角,找证据,然后对号入座,说鲁迅的文学创作是与西方某家某派一脉相承的。甚至“引经据典”,大作其“六经注我”的宏篇巨著。结果,研究他的论著要比中小学生读懂鲁迅原作困难得多,辛苦得多。所以,称之为“朦胧论”还是比较客气了的。大概这也是世纪末的一种时髦病吧,鲁迅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就对此时代通病使用过解剖刀,今天的鲁迅研究工作者难道能对眼前这种时弊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