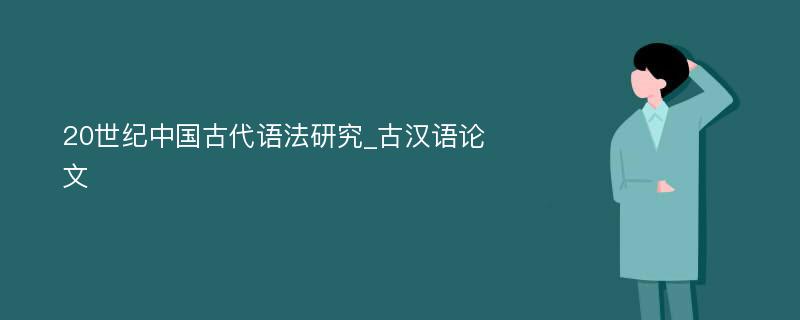
二十世纪的古汉语语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世纪论文,语法论文,古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重视理论,在描写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释
这个时期,在古汉语语法研究中特别重视理论,力求在描写的基础上寻求解释的学者,我们以为应该首推朱德熙。朱氏本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晚年他力主要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同古汉语语法研究以及方言语法研究结合起来。他的《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方言》1期,1983), 就是这方面的典范文章之一。文章的基本观点是:语言中的两种基本形式是指称形式和陈述形式,指称形式在语法上对应体词性成分,陈述形式对应谓词性成分。指称和陈述可以互相转化。文章把句法成分提取的理论运用于汉语研究,指出在陈述转化为指称的过程中,提取了与主要动词相关的名词性成分即为转指,反之即为自指。指出“者字除了转指功能之外,还有自指功能”,“所字只有转指功能,没有自指功能”(1989:60页),文章还指出“‘N之V’表示自指”(1989:82页)。朱氏对“者、所、之”指称化功能作出的理论解释对于古汉语语法研究,特别是对于“活用”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表明,就事论事只能触及现象,理论才能揭示本质。这篇文章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审视古今汉语中的“名物化”问题,涉及到了汉语的本质特点。朱氏的《汉语方言里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期,1985 )分析了南北朝时期选择问句的几种形式以及反复问句同选择问句的关系,指出“‘可VP’型反复问句产生的时代要比‘VP不VP’型晚得多”(1989:104页)。 文章在分析比较各地方言和《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五部文献的反复问句的基础上,得出了如下结论:“‘可VP’和‘VP不VP’两种反复问句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始终互相排斥,不在同一种方言里共存。”(1989:113 页)这是一篇描写研究与理论解释密切结合的汉语语法史论文。
郭锡良也是重视理论解释的,他在《古汉语语法研究刍议》(《语文导报》9期,1986)中指出“研究古汉语语法的人, 容易钻进古书堆,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对西方语言学的新进展不大过问,这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王力先生多次提出过古今中外熔为一炉的指导性意见,我们研究古汉语语法就是要采取古今中外熔为一炉的态度。”(1997:40—41页)在《四十年来古汉语语法研究述评》(《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中再次指出“理论和材料是科学研究的两个翅膀,就古汉语语法研究来说,目前是理论这个翅膀太弱,应该大力加强。”(1997:129页)他曾在各种不同的场合, 对古汉语语法研究领域里以传统训诂学的方法(训释的方法)和翻译的方法研究古汉语语法的倾向展开了尖锐的、持久的批评,这一批评在古汉语语法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许多论文也力图作出理论解释,例如他的《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9),在对先秦主要古籍中指示代词的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紧紧抓住指示代词的地域性、时间性以及各个代词间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的差异性,旗帜鲜明地提出先秦指示代词不是分成近指、远指两类,而是分为五组(即“泛指和特指、近指和中指、远指、无定、谓词性指代”)。文章引证了一些指示代词非近远二分的语言和方言,并且论证了甲骨文中的指示代词不分远近,以此说明指示代词的体系因时间和地域而不同。文章强调指出“在我们考察语言现象时,一定要有历史发展观点,千万不可以今律古”(1997:79页)。文章运用大量的材料论证了上古各个指示代词的语法意义和语法作用,并作出了总结:“上古汉语众多的指示代词在语音方面表现了相当整齐的系统,又在语法意义、语法作用方面体现了自己独特的体系,我们需要从上古汉语本身来考察、理解它的独特的体系”(1997:95页)。应该说,《体系》一文不仅对上古汉语的指示代词提出了全新的看法,同时还具有理论方法上的价值。他的《先秦语气词新探》(《古汉语研究》创刊号,1988)讨论了“什么是语气”、“语气的分类”、“语气的表达手段”、“语气词的起源”等理论问题,着重分析探讨了“常用语气词所表示的语气”,并且明确提出了“语气词的作用是单功能的”这一论点,从而扬弃了语气词多功能的传统看法。
梅祖麟更是重视理论解释的学者,他的《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语言研究》,1981),强调研究问题不能只停留在正确的描写上,而需要有可信的解释。“所谓解释,一则是要把需要解释的现象和其他的类似的现象连贯起来,二则是要说明以前没有的结构怎么会在那时产生”。针对汉语语法史研究中偏重于虚词演变而对结构演变重视不够的倾向,梅氏提出要同时注意词汇兴替和结构变化。尽管对完成貌句式具体演变过程的解释,梅氏自己后来也作了修正,但是他提出的要重视解释,要把词汇兴替和结构变化结合起来考察的意见,却无疑有助于汉语语法史研究向纵深发展。梅氏的《汉语语法史中几个反复出现的演变方式》(《古汉语语法论集》,语文出版社,1998),更是企图为历史语法学提供“管用的解释原则”,因而他“收集一些同类型的语法演变”现象,想“归纳出来一些通则”。文章讨论了三类现象:(1)“正反两式的平衡”,结论是:不平衡就要填补空当。(2)“被、会、解、没等动词的虚化”,结论是:这些动词虚化为助动词、兼语动词是由于汉语句子构造原则和词组构造原则一致。(3 )“虚化过程中的一和多”,结论是:在没有完全虚化前可以存在多个同义成分互换的现象,虚化后就由多并于一。尽管梅氏的某些引例不一定恰当(例如论述正反两式平衡问题中的引例),但是这种寻求理论解释的思想和实践无疑是可贵的。这一思想是在描写研究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标志着古汉语语法研究特别是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对自身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屈承熹的《历史语法学理论与汉语历史语法》(朱文俊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是一部理论色彩浓厚的汉语历史语法著作。 薛凤生的《试论连词“而”的语义与语法功能》(《语言研究》, 1991)也是很重视理论解释的文章,论述具有新意。
为了加强古汉语语法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北京古汉语学术沙龙曾于1986年先后两次举行了“古汉语语法研究方法”专题研讨会。重视理论;在描写的基础上追求解释,已经成为当前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潮流,尽管以理论解释为主的理论性著作还不多见,但是描写同解释已经开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例如:周生亚的《试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中国语文》2期,1980)从古今、 方言和语法功能三个方面解释了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王克仲的《古汉语动宾语义关系的制约因素》(《中国语文》1期,1986), 运用语义学和语用学方法深入分析了动词和宾语的语义关系。李佐丰的《谈〈左传〉三类复合使动式》(《内蒙古大学学报》4期,1983)运用语义分析方法, 分化了三类复合使动式,揭示了三类使动式的差别。张玉金的《甲骨卜辞中“惠”和“唯”的研究》(《古汉语研究》创刊号,1988)用分布理论、语用分析方法对“惠”“唯”两个虚词的语法作用作出了较为准确地区分。姚振武的《关于自指和转指》(《古汉语研究》1期,1994)、 《现代汉语的“N的V”与上古汉语的“N之V”》(《语文研究》2—3期,1995)深入讨论了朱德熙提出的“自指和转指”的观点,并在某些方面作出了补充和修正。唐钰明的《上古汉语‘动之名’结构的变换分析》(《中国语文》3期,1994)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文章, 是古汉语语法研究运用变换分析的有益的尝试。宋绍年的《结果补语式起源再探讨》(《古汉语研究》2期,1994 )提出用相关组合的频率变化作为认定使成式产生的形式标志,并指出:纯句法(分布)的形式标志往往滞后于新结构的诞生,“当某种句法结构开始转变为一种新结构的时候,在形式上往往不会发生变化,而是人们的社会心理对原结构进行了一次重新分析,新旧两种结构在不同的时间层次上形成了同形异构”,从语义和语用入手才能够及时地把新产生的结构从旧有的形式中分离出来;《古代汉语谓词性成分的指称化和名词化》(《古汉语语法论集》,语文出版社,1998)提出了在汉语里指称化不应该等同于名词化,汉语语法研究中要严格区分指称化和名词化这两个概念。董琨的《〈墨子〉称代系统论隅》(《古汉语语法论集》语文出版社,1998)提出可以用词汇扩散理论对某些“语法现象加以一定的解释”。大西克也(日)的《秦汉以前古汉语中的“主之谓”结构及其历史演变》(《第一届国际先秦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4)和《并列连词“及”“与”在出土文献中的分布及上古汉语方言语法》(《古汉语语法论集》语文出版社,1998)两篇论文对出土的秦简、楚简和汉简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提出了先秦汉语存在两大方言的论点,从而解释了“主之谓”结构演变过程中的复杂情况和并列连词“及”“与”分布不一致的现象。在本时期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刘坚、曹广顺、吴福祥的《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国语文》3期,1995), 蒋绍愚的《内部构拟法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中国语文》3期,1995)、 《把字句略论:兼论功能扩展》(《中国语文》4期,1997), 贝罗贝(法)的《早期把字句的几个问题》(《语文研究》1期,1989), 孙朝奋的《再论助词“着”的来源及其用法》(《古汉语语法论集》,语文出版社,1998)等论文,是注重理论解释的代表性论著。
肆.结束语
回顾一百多年来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历程,其中充满了借鉴、融会、批评、修正和创新,这个过程还将不断地继续下去。古汉语语法研究早已走出了国门,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从1881年德国学者加贝伦兹(Ga-belentz)发表《汉文经纬》以来,高本汉、马伯乐等著名西方汉学家都关注过古汉语语法研究,此后,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进入了古汉语语法研究领域。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重庆出版社,1991)和志村良治的《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1995)已经在我国翻译出版。但是,国外学者大量有价值的古汉语语法著作至今还没有汉语译本(例如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页欧洲语言学家的一些著作,以及当代日本及欧美一些著名语言学家的著作),已有的译本还远远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求,我们应该把积极译介国外有价值的古汉语语法著作作为一项基本的学术建设,长期地坚持下去。本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一批国际知名学者的积极推动下,已经举行了三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会议分别在瑞士苏黎世(1994)、中国北京(1996)和法国巴黎(1998)召开,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1996年的北京会议有近百名学者与会,这是古汉语语法学界的一大盛事,从此,古汉语语法学这一与世纪同龄的学科更加生机勃勃。人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二十一世纪的古汉语语法研究将展现出自己更加辉煌壮丽的图景。
标签:古汉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