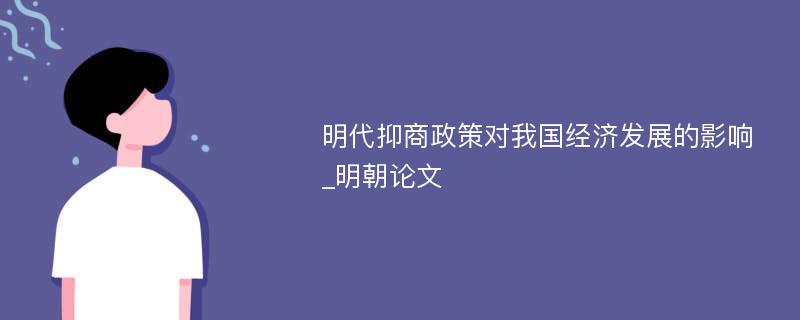
明代抑商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2)01-0125-07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朝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转机。然而,正是在此期间,一个具有悠久文明、长期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经济发展的步伐却呈现出滞缓状态,进入17世纪,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已出现明显差距,到了近代,这种差距居然越来越大,以致今日仍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一现实存在,引起人们的沉思。本文拟就明代抑商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以探讨。
一、抑商政策的制定及其内容
明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蒙古贵族在中国的统治。为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重建社会新秩序,新朝缔造者朱元璋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早在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就提出:“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杜末,则国计可恒纾。”[1](卷三《理财》,P228)洪武十九年三月,在谕户部臣时又阐述了这一主张:“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樽节用度,自有余饶。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不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积蓄富盛”[2](卷三,P462)。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抑末思想贯彻在明初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之中。
1.严禁去农从商。明朝开国后,强调以农为本,士、农、工、商务安其业,从确保农业劳动力出发,抑制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禁止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洪武十八年,朱元璋谕户部:“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庶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3](卷一七五,洪武十八年九月戊子,P2663)同时加强商人管理,规定行商须领取官府印制的路引,才可外出经营。洪武年间制定的《大明律》里规定:“凡无引文私渡关津者,杖八十。”[4](卷一五《兵律三·关津·私越冒渡关津》,P1175)又规定出行在百里外,没有路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津论。嘉靖时丘浚说:“凡商贾赍货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关券。”[5](卷三十《征榷之税》,P385)没有路引而进行商业活动者,视为非法经营,按游民处理,“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6)](验商引物第五,P796),对于在城镇开店经营的坐商,则要求在所在城镇办理入户登记手续,名叫占籍。“非占商籍不许坐市廛”[7](卷九《政事志》,P294)。无籍者,不许在城留居和营业。而取得占籍,又有种种规定,诸如“凡外郡商贾,有置业产而愿受者,悉许其占籍坊里”[8](卷三八《农事》,P143)。这也就是说,在本地没有置产业的商贾,不许在本地占籍;而且取得占籍后,还要交纳商税和门摊税,承担名目繁多的摊派,致使占籍者富者必贫,贫者被迫迁徙。
2.商人地位低下。明代虽然肯定商人是四业之民的组成部分,认为“商贾以通有无”,不可或缺,同时又认为商人的经营和收入是不正当的。在朱元璋看来,尽力求利,是商贾之所为。“平时射利,高价以售”,其弊百端,为害滋甚。[9](卷三,P66)因此,明代立法以贱商为指导思想。洪武二十年规定:“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10](卷二《我朝服制》,P110-111)何孟春曾经指出:“国家于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11]卷一,P3)武宗正德元年,“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12](卷六七《舆服志》,P1650)。这里将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作为同一等次。后又规定“商贾、技艺家器皿不许用银”,也是为了将商贾与庶民加以区别,表明商贾地位低于庶民。由于上述政策的贯彻实施,使得这种贱商观念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之中。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是总结我国农工商业生产技术的专著,书中编目顺次前后排列,将五谷排于前,金玉置于卷末,崇祯七年他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说“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13](《天工开物序》,P1),可见这一思想影响之深。明代的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治安管理,没有给商人私有财产及人身安全以可靠的保障,商人在运作过程中,遭到抢劫的比比皆是。《拍案惊奇》中描写徽州府商人程元玉,“专一走川、陕,做客贩货,大得利息”。一日,收了货钱行囊丰满,在返回途中,遇劫,行囊所有财物,被劫一空[14](第四回,P70)。这便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写照。
3.实行海禁。海禁就是禁止商民同海外各国和地区进行贸易。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诏“仍禁濒海居民不得私出海”。九天之后,告谕大都督府臣:“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近闻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则滨海军卫岂无知彼所为者乎?苟不禁戒,则人皆趋利而陷于刑宪矣。尔其遣人谕之。有犯者,论如律”[3](卷七○,洪武四年十二月乙未,P1307-1308)。《大明律·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驼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只并入官。于内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由于沿海居民有禁不止,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再次宣布“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以重法”[3](卷二三一,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P3374)。甚至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从禁止居民下海捕渔,到将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甚至后来又废县徙民。洪武以后,海禁时驰时严,总的来说,一直持续了下来。成祖永乐二年正月,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15](卷二七,永乐二年正月辛酉,P498)。宣宗宣德六年四月,针对并海居民有私下诸番贸易及出境与夷人交通,“命行在都察院揭榜禁辑”[16](卷七八,宣德六年四月丙辰,P1813)。景帝景泰三年六月,命刑出榜禁约福建沿海居民毋得收贩中国货物。[17](卷二六《市粜二》,P3027)穆宗隆庆元年,调整对外贸易政策,放宽海禁,“准贩东西二洋”[18](卷七《饷税者》,P207),允许中国商人到东、西二洋国家贸易,但对出海贸易船只的数量限制极严。正如许孚远所指出的那样:“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19](卷四,P4332)其禁,一是不许与日本国进行贸易,二是严格限制出洋贸易船只。万历十七年,定为东西二洋各限船只44只,后增加为115只,但仍不许对日进行贸易。
4.重征商税。以商税来抑制商业发展,是明代商业政策的基本点。明初,为恢复战争创伤,鼓励商人的正当经营,商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三十取一的税率。洪武十九年重申:“三十分中,定例税一,岂有重叠再取者!今后敢有如此者,虽赦不宥。”[20](巡栏害民第二十,P907)直至正统十二年,仍强调“每三十分而取其一”的商税制度。同时对有些商品实行免税。洪武十三年诏令军民婚丧嫁娶丧祭所用物品,舟车丝布之类免征。永乐元年下令免征军民常用杂物等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商税名目逐渐增加,税率也在不断提高。仁宗洪熙元年,增加市肆门摊税。宣德四年,顺天、浙江、福建、湖广、江西、河南、山东、山西、四川33府州县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加五倍。不久,又颁布了塌房、店舍收税条例;进而,在运河沿线设立钞关,对过往客商载货船只征收税钞。商税征收由轻到重。据弘治年间礼部尚书倪岳述称:户部官员出理商税,“往往以增课为能事,以严刻为风烈,筹算至骨,不遣锱珠。常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苛求,客商船只,号哭水次,见者兴怜”[21](卷一三《钞关》,P163)。万历二十八年正式改定商税税率为十分之一,较明初税率提高了3倍。隆庆以后,商税征取之令,密如牛毛,一切鄙微,无不税及。应朝卿在奏疏中曾经指出:“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22](《食货典》卷二三一《杂税部》,P84862)户部尚书赵尚卿所说尤为具体:京东通州河西务,先年布店计160余名,今止30余家矣。临清,往年伙商38人,今止存2人;向来缎店30家,今闭门21家;布店73座,今闭门45家;杂货店65家,今闭门41家[23](卷三七六,万历三十年九月丙予,P7038)。继之天启年间,又有关税、盐税加派和杂项征收,北新关原额4万,天启元年另增2万两,五年加增2万,共8万两。浒墅关原额45000两,天启二年加增22500两,五年又加2万两,共87500两。如此接踵继起的苛重商税,迫使一些商户倒闭或将商业资本转向购置土地。
5.强取掠夺。政府和皇室用品,包括国家一些兴建用品在内,本应通过购买来解决。虽然洪武二年也明确规定“官司身用之物,照依时值对物,两平收买。”[24](卷十八《市籴一》,P1858-1859)实际上,官府向商家购买物品并不按时付给,也不照价给值,名为和买,实为白拿。洪熙元年,副都御史弋谦奏称:“朝廷买办诸色物料,有司给价,十不及一,况展转克减,上下靡费,至于物主,所得几何?名称买办,无异白取”[16](卷三,宣德二年七月戊寅,P88)。嘉靖二年四月,给事中汪应轸亦说:“今和买不给值,独累京城,以片根本,其不善尤甚矣。”[25](卷二五,嘉靖二年四月甲寅,P72)更有甚者,在光天化日之下,依势强取。成化四年七月,兵科给事中陈钺说:“近光禄寺遣人于街坊市场,不复计值,概以强取,虽称赴官领钞,未必皆得。纵有得者,钞皆破烂不可用。负贩不幸遇之,辄号呼痛哭,如劫掠然。”[26](卷五六,成化四年七月丙戌,P156)时至明后期,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就连明神宗也无法否认官府“刑逼威伤,致令逃死者相继”[23](卷四一八,万历三十四年二月丙午,P7911)的事实。如此强取掠夺,使得明代中后期商业无法持续发展。
6.倡导节俭。明政府在“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的思想支配下,把节俭作为抑商的手段,力图紧缩内需,从源头上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众所周知,商品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市场需求的扩大。国内市场的需求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众的购买力,一是政府的购买力。各国经济发展表明,政府的购买力是国内市场需求的重要部分。明代政府购买力包括国家机关所需用的各种物品和皇室用品。朱元璋早年家境困顿,即位称帝后,大力倡导节俭以省浮费,并以身先节俭的行动,来引导臣民特别是百官的消费趋向。对于皇宫中各类人员的消费观念及消费情况,也极为关注。一次退朝回宫,他看见二个内侍穿着靴在雨地行走,当即进行斥责,令左右杖打,并下令百官今后上朝遇到天雨,要穿雨衣。同时官吏实行低俸,薪俸支付方式,实物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些做法,压缩了政府的购买力。广大农民由于收入有限,生活穷困,购买力低下。这种低标准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使中国广大民众长期习惯于过极为简朴的生活,很少与市场发生联系,时人陆楫曾说:“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27](P400)。
二、朝贡贸易使明朝在经济上得不偿失
明朝建国之初,在对外关系上,明政府以宗主国自居,将外国使臣来华访问称之为朝贡。这种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既是一种外交活动,同时又是一种经贸活动。人们通常称这种经贸活动为朝贡贸易。对此,明政府的基本的态度是厚往薄来。洪武四年,朱元璋谕中书臣说;“西洋琐里,世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计其年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3](卷七一,洪武五年年正月壬予,P1314)。所谓厚往薄来,不仅给予来华使臣盛情款待,并以优厚的赏赐作为回报;同时还包括对于外国使臣带来非贡品的其他货物,实行给价收买和免征货物进口税。《诸司职掌》规定朝贡国使臣所带来不系贡献之货物,“照依官例具奏,给钞锭酬其值”[28](卷一○○《礼部五九给赐一》,P910)。这种收购给价,不是根据市场价格支付,而是付给高于其所值几倍乃至数十倍。景泰四年礼部一份报告中说:日本国王有附进物及使臣自进物,其所给值,“比旧俱增数十倍。盖缘旧日获利而去,故今倍数而来……计其贡物,时价甚廉,给之太厚”[29](卷五四,景泰四年十二月甲申,P5140)。洪武年间,收买外国的货物,储之于库,从永乐开始,由官府专买于民间,后允许在市舶司主持下通过牙行进行贸易。免征进口税,始于洪武四年,“谕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货物皆免征,以示怀柔之意”[24](卷三一《市舶互市》,P1885)。永乐九年,西洋琐里及刺泥等国船舶,满载本国胡椒等产品,前来互市。有司就此问题奏请朝廷,提出征收进口税。成祖批示:“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例?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22](《食货典》卷二三一《杂税部》,P84382)非但如此,明政府从维护宗主国的尊严出发,对朝贡贸易作出种种限制。
其一,限制国家。洪武年间,准予朝贡的国家,有朝鲜、真腊、苏门答腊、锡兰山、暹罗、安南、占城、苏禄、古里、古麻刺、爪哇、柯枝、满六甲、日本、三佛齐等17个国家。成祖即位后,通过郑和七下西洋、出访亚非国家,朝贡国家增加到60多个。对于许朝贡的国家,明政府发给勘合,一式两份,一份交朝贡国,一份存于明礼部。勘合注明朝贡时间、人数和船只数,要求按照勘合规定前来朝贡。
其二,限制时间和人数。关于朝贡国家来华朝贡的时间,以其与明友好关系的情况,多数定为三年一贡。洪武九年谕中书省臣:“番夷外国,当守常制,三年一贡,无更烦数。”日本因倭寇骚扰沿海地区,规定十年一贡。对于前来朝贡的人数也有限制,“来朝使臣亦惟三五人而止”。日本国十年一次,人数200,船2艘,后增至人数300,船3艘。非贡期而至者,或超过勘合规定人数和船只者,不许入境。正德九年,“令抚按等官禁约番船非贡期而至者即阻回”[30](卷一一三,正德九年六月丁酉,P2297)。
其三,限制活动范围。对于朝贡国使臣及其随行人员,其在华活动范围也有严格限制。弘治十四年重申:“旧例各处夷人朝贡到馆,五日一次放出。余日不许擅自出入。惟朝鲜、琉球二国使臣,听其出外贸易,不在五日数。”[31](卷一七○,弘治十四年正月壬申,P3086)
其四,限制贸易地点。鉴于朝贡国使臣多附带货物而来,明政府允许其附带货物在华贸易,同时规定必须在中国官员主持下在指定地点内进行;在北京,由会同馆负责此项工作;在广东、浙江、福建地区,由当地市舶司负责组织实施,“止集舶所,不许入城。通番者有厉禁”[32](第29册《广东下·杂蛮》,P105)。隆庆元年开放海禁,但对来华外国商人的上述原则并没有改变。
其五,限制商品出口。在对外贸易上,明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利用之物,不可有资于外国者也”[3](卷一五《关津》纂注,P1199)。从这一思想出发,重在防范,对出口贸易物品作出诸多限制。如明确规定不许马、牛、军需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等物品出口,洪武二十四年,下令“禁番使勿得以麻、铁出境。仍命榜揭海上,使咸知之”[2](卷一八一,洪武二十年四月庚寅,P2735)。二十三年户部申令中国金、银、铜钱、缎匹、兵器等物,不许出番。“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3](卷二○五,洪武二十三年十月乙酉,P3067)正统十四年,禁约两京、陕西、河南、湖广、甘肃、大同、辽东镇店军民客商人等,“不许私将白地青花瓷器皿卖与外夷使臣”[33](卷一五八,正统十二年九月戊戌,P3077)。后在历经修订的《问刑条例》中依然规定下海出洋船只,“将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响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这一规定,限制了本国手工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朝贡贸易既然是经济交往,理应遵循经济规律运作,按照互利互惠原则进行。这与政治上友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明政府对朝贡国实行厚往薄来的方针,只讲天朝大国风度,不讲贸易的经济效益,坚持国家垄断对外贸易,不许海商私下贸易,将管理的重点放在防范外商与中国商民接触与打击中国商民出海贸易上。这一做法,在明初的百余年间,换取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宗主国地位的承认,对密切明朝与朝贡国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就经济效果而言,它给明朝经济带来的并不是福音,而是不大不小的损失。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明穆宗隆庆改元。对于明朝方方面面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三、抑商政策的实施使中国丧失了发展经济的机遇
明代抑商政策及其措施,已如上述。将它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它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1.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的发展,一靠生产技术的进步,一靠国家政策的支持。历史证明,保护支持商业的发展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是至关重要的。朱元璋及其继承者面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固守崇本抑末的传统观念,鄙视技术为奇技淫巧,将商人作为抑制的对象,商人地位低下,即使在洪武年间,广开财路,大力选拔一技之长的人才时,也没有把善于经营的商家包括在内。抑商不仅造成有些地区商人数量下降,还使多数商人本小利微,生活水平低下。据吕坤的估计,在万历后期,小工商业者有几百万人,过着“以求升合之利,以养妻奴”[34](卷二《辨洪主事参疏公本》,P14)的生活;他们没有或少有文化,墨守成规,习惯于家族式的经营;经营方式落后,零售商多,批发商少;资金分散,无力扩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即使少数商人能够致富,在经济上相当富有,由于立法贱商、商人社会地位低下,他们也不以从商为荣,往往用钱买官,几乎毫不例外地让其子孙业儒,求取功名,以改变门庭。同时由于商业经营风险较大,为司马迁所说的“以末致财,以本守之”[35](卷一二九《货殖列传》P321)的经营模式,依然深入人心。富商大贾深知所得钱财难于长守,一次战争,甚至一次突发性抢劫,或者一次天灾,即可使其万贯家产化为乌有,为保持其得来不易的钱财,往往转向购买土地,向地主经济倾斜。《醒世恒言》里描写商人阿寄说:“凡贩的货物,定获厚利。一连做了几帐,长有二千余金。看看捱着残年,算计道:‘我一个孤身老儿,带着许多财物,不是耍处。倘有差跌,前功尽弃。况且年近岁逼,家中必然悬望,不如回去,商议置买些田产,做了根本,将余下的再出来运弄’。”[36](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P790)更有一些富商,将家中铜钱、银子埋于地下,使商业资本与市场绝缘。明朝政府的贱商立法与政治干预,严重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2.阻止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沿海地区的地理位置为其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条件。明代中国的货物,在日本、东南亚以至欧洲各地,拥有广阔的市场。嘉靖年间,浙江海盐人姚士麟据其所见说:“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37](卷上,P3525)。崇祯年间傅元初称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而江西瓷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稍后,屈大均也说:“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38](卷一五《货语·纱段》,P427)从事这些经营的利润也是可观的。据中方资料所载:满剌甲不产五谷,“故一物之价,五倍于华也。”[39](卷上,P120)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东南亚)得价二倍。闽广商人与番商贸易,“牟利恒百余倍”[40](卷三,P2944),以是富甲天下者,不乏其人。来自西方国家资料记载,1565年,在中国国内1担湖州丝大约值银100两,到菲律宾就能卖出2倍的价钱。一旦人们在市场上争先购买,湖州丝的售价猛涨,每斤售价为5两,1担就是500两。由西班牙番船输送到美洲的中国丝绸,在马尼拉大约值100比索(1比索等于1西班牙银元),或者更多些。若这些物品运到墨西哥售卖,则可超过200万比索[41](P261、265)。博克塞(C.R.Boxer)在描写澳门—日本贸易的一些文件里,载葡萄牙一艘大船运入日本货物18种,比照当时广州价格和日本价格,其中各色丝线,利润率为164-187%,各色绸缎为111-127%,白铅粉为155-160%,棉线为128-175%,水银为125-130%,茯苓为300-354%,白糖为100-130%,黑糖为1000%。[42](P28-29)正是这种贸易,推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关于此,屈大均曾经有过说明:“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林、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40](卷一四《食语·谷》,P408)随着这种贸易的发展,中国的手工业品远销于世界各地。福之丝绸,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胜计”[43](P12)。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因此“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44](卷四:《江南诸省》),P84)。面对这种生机勃勃的局面,明朝当局生怕内外反明势力结合给政权带来威胁,把管理工作的重点放在如何防范外商与中国人的接触上,放在如何监督中国商民上。种种苛刻的禁令和举措,旨在遏止沿海商民下海贸易。其结果,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因禁海而得不到发展,不仅遏制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出口产品滞销,使得沿海地区正在发展中的外销商业因此而遭破产,同时也使国家税收减少。广东巡抚林富说:“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12](卷三二五《外国六》,P8432)王沄也说:“自海禁严,而闽贫矣。”[45](卷一《闽游》,P4)与此同时,沿海地区的社会秩序也随之而动荡不安。兵部尚书赵文华曾说:“滨海细民,本借采捕为生,后缘海禁过严,以致资生无策,相煽从盗。”[25](卷四四二,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癸卯,P7563)
3.丧失了经济发展的机遇。14-17世纪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也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机遇面前,各国都是平等的。谁能抓住机遇就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正是在此期间,欧洲一些地区和国家,致力于发展新路子的探讨,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在国内鼓励工商业发展,保护关税,限制进口,奖励出口,希求更多的金银进口;大力支持商人,开辟国外市场。对外贸易被视为经济生命线。商业资本在海外运作,使经营者取得了丰厚的利润,加快了国内手工业发展的步伐,并使欧洲经济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而在中国则是另一番情景。进入14-15世纪,凭借传统的素称发达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诸多手工业品闻名于世,具有广阔的市场。整个贸易格局,对明代经济发展极为有利。可惜的是,明朝当局考虑的不是如何发展经济,而是如何巩固政权统治。从加强防范出发,坚持抑商、锁国、禁海,限制去农从商,通过“征商贾以抑逐末之人”[46](《明职·税课司之职》,P7),使中国商人没有实力从事新的产业,也没有条件进入欧洲市场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商业竞争,从而丢弃了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丢弃了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时至16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没有取得突破性的发展,中西技术力量对比的天平,已向西方倾斜。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据其所见说:“(中国)缫丝业规模如此之大,很容易与欧洲产品竞争,虽然后者或许质量更好一些。”又说中国人不懂怎样把羊毛织成料子做衣服穿,中国的吹制玻璃工艺“远逊于我们在本国所看到的”,这里生产最好的纸也远不如我们自己生产的许多产品[47](第三章,P13、14、15、17)。
抑商是明代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诚然,人们对明朝当局作出抑商的决策,可以作出种种解释,列出明代抑商与先前相比,有诸多不同。但是,有明一代,商人的下贱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明代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地位的下落,也是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丧失机遇,就会落后。长期居于世界先进地位的中国,所以在17世纪与世界先进国家出现差距,明政府决策上的这一失误是一个重要的内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明代的抑商政策,禁锢了中国的经济活力,使中国在关键时刻,丢掉了一次发展的大好时机。
收稿日期:2001-0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