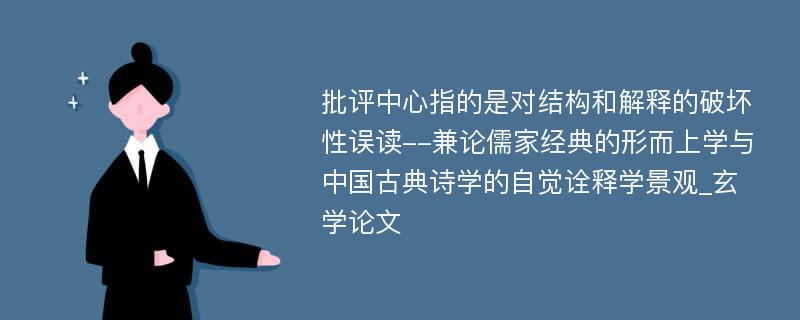
批评的中心指涉结构与阐释的破坏性误读——论经学的玄学化与中国古典诗学走向自觉的阐释学景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涉论文,经学论文,诗学论文,玄学论文,误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对于儒家诗学一统于两汉文学批评的权力话语,可以说,浸淫儒家经典文本且制导其文本意义生成的原初视域起着重要的功能作用。保罗·利科在《从文本到行动》一书中曾这样回答关于“文本是什么”的设问:“我们说文本就是通过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话语。根据这样一个界说,通过书写而形成的固定式是文本自身的构成。但是通过书写究竟固定了什么?”[①a]保罗·利科以为书写在最初的物理与精神形式中通过语音表达固定了书写主体的所有话语。保罗·利科的回答未免太宽泛,但至少对于儒家诗学主体来说,“六经”作为书写的文体形式则固定了儒家诗学的最高道德伦理原则。从孔子到思孟学派、荀子学派对原始儒家的承继性传递,再到两汉今文经学大师与古文经学大师在相互攻讦中对儒家经典文本的建构性阐释,儒家经典文本作为能指在对应于所指的意义关系网络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能指与所指相对恒定的中心指涉结构。因此,儒家经典文本超越了一般历史典籍,成为汉代官方制定各项政策的法典,这也正如班固于《汉书·儒林传序》所言:“‘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②a]由于儒家经典文本总是在学术宗教的神圣地位上,以不可侵犯的、冷酷的法典性质执行着为芸芸众生“立法”的宗教功能,所以,其中心指涉结构呈现出对文学批评指导的理论先验性。
上篇
索绪尔在界分语言结构的能指与所指时,认为是语音与意义两者之间的网络关系确定了语言的结构:“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③a]索绪尔把“语音”界说为能指符号,构成他的形而上学的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而儒家诗学与两汉经学对于“语言”与“阐释”的潜在理论思考不同于索绪尔的语音中心主义,儒家诗学与两汉经学把书写的语言——儒家经典文本认同为能指,在阐释学的本体论上崇尚书写的语言中心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儒家士人主体在经学的学术宗教地位上极力张扬文本中心主义,同时也是为什么儒家诗学在对文学现象进行阐释时无法回避经学中心主义的根本原因。儒家经典以冷酷的法典性质为芸芸众生“立法”,表现在阐释学的理论上,这就是从儒家经典文本的中心指涉结构摄取先验的道德理性原则,给这个本无意义的此在世界铺设意义。也就是说,这个此在世界的意义是儒家经典文本的中心指涉结构赋予的。如果说,这个此在世界就是接受意义而得以澄明显现自我的物化载体,那么,意义与这个被意义命名的此在世界共同构成了与能指——儒家经典文本相对应的所指。
在两汉时期,由于儒家思想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对文化中心地带的占据,从儒家经典文本的中心指涉结构审度,这个此在世界在本质上已经被中心指涉结构的意义先验地界定了。因此,这个此在世界充其量也就是儒家经典文本受限生成的原初视域及其文化语境的反照和投影而已。其实,史学大师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经解》对上述理论现象导源于经学的威压已有粗浅的悟解:“然所指专言‘六经’,则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①b]在两汉时期,当这个此在世界在受限的界定中遮蔽于儒家经典文本中心指涉结构的意义之下,也充分地迎合了汉代皇权政治的“大一统”需要。《公羊传》在阐释《春秋·隐公元年》的“元年,春,王正月”一句时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②b]从而为汉武帝一统天下的占有欲和征服欲尊定了理论依据。而汉儒通经致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③b],从经典文本的中心指涉结构摄取既定的最高道德理性原则覆盖了整个人文世界,使此在的人文世界于屈服中既定地“意义化”了,从而最终完成了对两汉芸芸众生从精神到肉体的彻底占有和彻底征服。在两汉时期,儒家诗学为什么总是从儒家经典文本的中心指涉结构摄取先验的最高道德理性原则,去阐释、批评、规范和囚禁生生不息的文学现象?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学现象的生成与发展从先秦向两汉的延伸,其面对着儒家诗学所遭际的悲惨厄运往往就是在还没有进入具体的批评和阐释之前,于价值取向上,就已经被儒家诗学及其范畴在儒家经典文本的中心指涉结构中摄取的恒定原则先验地界定和“意义化”了。这也是先秦两汉时期儒家诗学的原初视域对同期文学现象进行“意义化”覆盖的必然性。
雷纳·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讨论西方诗学的新古典主义和时代的新趋向时,指出新古典主义诗学理论总是力图发现和挖掘一种“规则”,认为新古典主义对文学现象的阐释和批评总是以“规则”在理论上“假定存在着一种稳定的人性心理,作品本身具有一套基本模式,人(阐述主体)的感受性与智力有着统一的活动……得出适用于一切艺术和一切文学的结论”[④b]。可以说,这个“适用于一切艺术和一切文学的结论”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是一元封闭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出,雷纳·韦勒克对新古典主义一元论的封闭性诗学批评观是一种描述,实际上,在描述的表象下潜设的理论如同儒家诗学理论的阐释价值取向一样,两者都是企图以一元的“规则”使多元的文学艺术现象在封闭的阐释中走向既定的“意义化”。这也如同儒家诗学主体在对作品的解读和批评时,首先把灵魂从自身的躯壳抽回,然后再把这个失去主体性的灵魂抵押给儒家经典文本的中心指涉结构,在阐释中使灵魂失身为傀儡,从中心指涉结构起步达向作品文本,最终使文本既定地“意义化”。我们可以发现,从西汉初始期的《诗大序》到东汉终结期郑玄的《诗谱序》,儒家诗学正是在这样一个纵跨两汉文化的历程中,受限于原初视域,在儒家经典文本的中心指涉结构约束下解读着、批评着文学作品。
那么,在两汉时期,儒家经典文本中心指涉结构的一元价值取向及其内涵又怎样被认同,且怎样向儒家诗学转向呢?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引孔子言:“‘六艺’之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⑤b]的确,“六经”兑现于“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中,正是固执“一也”的一元价值取向“节人”、“发和”、“道事”、“达意”、“神化”、“道义”,从而把六个层面的内涵转化为道德理性,同时铺向两汉的人文世界,逼使这个此在的人文世界沿着儒家经典的一元价值取向既定地“意义化”了。如果说,关于中心指涉结构的内涵,《史记》载孔子所言还是在偏向伦理学和哲学的层面上运作,而《礼记·经解篇》便佯托“孔子之言”把儒家经典文本中心指涉结构全然推向了诗学的理论表达:“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①c]这就是从儒家经典文本中心指涉结构中升华出来的儒家诗教。也就是说,儒家诗学从儒家经典文本中心指涉结构摄取的最高道德理性原则,从“善”的道德理性价值判断面向文学的审美空间取向,最终转型为诗学的理论表达。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儒家诗教已经开始走出纯粹道德理性的理论表达方式,但无论如何,在两汉时期,儒家诗学还是无法摆脱皈依于儒家经典文本中心指涉结构对文学现象进行“意义化”的伦理规范。关于这一点,东汉的文学和经学大师张衡在《思玄赋》,曾给予最真诚而诗意的表白:“文章焕以粲烂兮,美纷纭以从风,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②c]因此,最终儒家诗学在对文学现象的阐释与批评中,仍于道德的功利价值取向上突兀为三个方面:即政治教化、美刺讽谕及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最高审美原则,并且最终儒家诗学还是把最高审美原则在阐释和批评中铺向文学现象,逼使文学规范于儒家经典的价值取向,跌落于既定的“意义化”中。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悟透了儒家诗学在两汉时期的经典表达。《诗大序》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③c]这就是儒家诗学在两汉时期推崇“情志”说的经典表达。“志”作为儒家诗学范畴是对经典文本《尚书·舜典》“诗言志,歌咏言”的思路承传[④c],是指涉道德理性规范的思想志向,“情”是指涉主体“血气心知之性”的哀怨喜乐[⑤c]。《诗大序》从中心指涉结构中承继了一切,主张诗“发乎情,止乎礼义”[⑥c],最终逼使“情”在道德理性的规范下安息于“温柔敦厚”的审美原则,仅在这个意义的层面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⑦c]。如果说,《诗大序》是儒家诗学在汉初为儒家诗教张本的宣言书,那么,调和今古文学的经学大师——郑玄,其《诗谱序》则是儒家诗学在汉末败落前的最后一次总结了。儒家诗学在郑玄这里的理论表达把诗的功能阐释为“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⑧c]。从《诗大序》的“宣言”到《诗谱序》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儒家诗学在两汉的理论演奏是严格遵循儒家经典文本中心指涉结构的总谱而行进的。但无论如何,郑玄《诗谱序》的诗学理论表达是儒家诗学在汉末的最后一次深沉的演奏了,它带着一切行将结束的落日辉煌,期待着末日的到来。
但无论如何,这是儒家诗学在汉末的“曲终雅奏”。
可以说,阐释主体与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遭遇都应该是灵魂深入文本的艰难探险。但是,两汉时期的儒家诗学主体与各种文体形式的每一次遭遇,都是使文学作品在既定的“意义化”中兑现的执行。让我们的视野投注两汉的文学空间。“赋”是两汉文学的代表文体,而儒家诗学从中心指涉结构起步的阐释和批评逼使班固把“赋”读解为“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⑨c]不啻如此,儒家诗学的中心指涉结构又逼使在道家诗学的“无为”中静养自身的淮南王刘安把南方楚骚的审美意义比附于北方的《诗经》:“《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①d];又逼使王逸把中心指涉结构的“意义”覆盖于屈原的《离骚》,以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②d];再逼使扬雄批评司马迁的《史记》“不与对人同,是非颇谬于经”[③d]。也就是这样,两汉的三类文学体式——赋体文本、骚体文本和纪传体文本统统在儒家诗学的中心指涉结构覆盖下既定地“意义化”了。这就是南朝的一代诗学大师——“内儒外道”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透露出的真知灼见:“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列膏腴。”[④d]把刘勰诗学理论所言的“奥区”植入西方诗学的参照系层面给予理论的自觉,其实“奥区”就是儒家诗学“取资”不尽、用之不竭的中心指涉结构。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思考西方诗学的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时,曾借卡尔弗威尔之口把文本的既定“意义化”之罪过追溯到柏拉图主义者的灵魂深处。在柏拉图主义者那里,阐释主体——人的精神仅是主的蜡烛,在阐释中,主体与文本的遭遇、对话仅是以主的智慧之灯(主之精神蜡烛的光亮)装饰、美化作品文本描述及构造的下界而已,并且在理念本体的崇拜意义上,主的智慧之灯将伴随着人们对它莫名其妙的赞誉和敬仰而永世长期:“这就使得柏拉图主义者将人的精神视为主(the lord)的蜡烛,用以照亮各种客体,它投射在这些客体上的光多于从它们身上得到的光……事实上,他或许也会将这些植入观念,肉眼之中这些光的种子,误当作心灵的眼睛中的基本原则(Seminal Principles)……”[⑤d]。这是多么精致而诗意的阐释学理论表达啊!艾布拉姆斯在他的浪漫主义诗学思考中借柏拉图诗学理念本体论的向日式隐喻,把思路铺向了作品文本阐释的中枢神经——中心指涉结构,也就是刘勰诗学理论的那个意义深邃的“奥区”,把作品文本阐释的中枢神经——中心指涉结构诗意地隐喻为“主的智慧之灯”。于是,阐释主体与文本的遭遇、对话仅仅是主的智慧之灯透过人的精神视域而烛照文本,使文本遵循“心灵的眼睛中的基本原则”失落于既定的“意义化”而已。因此,儒家诗学的中心指涉结构——“奥区”与西方诗学的“主的智慧之灯”(即本体论的向日式隐喻),在阐释的价值天平上永远等值。当我们思考到这里时,我们不禁设问:“镜与灯”在西方浪漫主义诗学那里的基本命题究竟是什么?
艾布拉姆斯在回答中诗意地让自己的理论表达全然从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那里起步:“柯勒律治第一次听别人朗诵《序曲》之后,立刻采用了华兹华斯所喜爱的光彩以隐喻来描述它的主题——虽然他同时并用了两个隐喻,即把心灵喻为灯,同时把外界喻为镜……”[⑥d]。多么精巧的隐喻!这实际上是阐释学的浪漫主义诗学理论表达。倘若把“心灵为灯”与“外界为镜”的隐喻转化为阐释学的理论公式,那就是“‘奥区’是灯”与“文本是镜”,阐释主体仅是“‘奥区’之灯”透向“文本之镜”的视域中介而已。因为在西方形而上学的诗学体系中,阐释主体的心灵已经被“奥区”——中心指涉结构在本体论上分享和占有完毕。因此,阐释主体心灵之灯就是从“奥区”——中心指涉结构之域引来的洞照作品文本的“主之精神蜡烛的光亮”。实际上,诗学的阐释就是诗之文本在“主之精神蜡烛”的洞照之下的既定“意义化”,于是在阐释中,如果说诗之文本仅是“主之精神蜡烛光亮”的全然反照之“镜”,不如说“可以把理解(understanding)视为镜子,‘镜子如实地接受的全部色彩,再把这些色彩忠实反射出去。因此柏拉图主义者是值得赞美的,他们把人的心灵视为主的蜡烛,虽然蜡烛被点燃时他们却遭到了欺骗’”[⑦d]。
其实,艾布拉姆斯已经认识到浪漫主义诗学理论关于“镜与灯”的思考再精巧,最终没有逃避诗学形而上学本体论其中心指涉结构的威压。可以说,浪漫主义诗学理论表达者在张扬西方诗学的浪漫主义诗性之际,不自觉地以“奥区”贬损阐释主体与文本的价值地位,为达向读解的终极目标而铺路,最终,在主体迈向文本读解的终极目标背后,遗落下一条主体性全然缺失的阐释之足跋涉过的泥泞之道。为什么?因为,“主之精神蜡烛”,在本体的格位上诗意地燃烧着!它以精神之光烛照着这条泥泞的阐释之道,使诗学主体在主体性失落于一无所有的赤裸裸下全然不惮于前行,以此慰藉那些蒙上思想的眼睛,在阐释的黑暗与寂寞中遵循“奥区”之教义读解文学现象的“猛士”。这也如同儒家诗学把经典文本供奉于神圣的学术宗教地位,在“宗经”、“征圣”、“原道”的诗教信仰下与西方诗学的“主”在本体的格位上平起平坐,为阐释主体对诗之美的审判设定了中心指涉结构。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对儒家诗学那么迷恋般的心灵独白:“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研思之士,无惭匠古矣。赞曰: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皓如江海,郁若昆邓。文梓共采,琼珠交赠。用人若己,古来无懵。”[①e]
一言以蔽之,在儒家诗学体系中,“研思之士”作为阐释主体,“经典文本”是他们评判诗之审美的唯一指导法典。当儒家诗学主体涉足于诗之文本阐释的湍流,走向意义的探险时,阐释主体总是跌失于“用‘经’若己”的信心实足,在“古来无懵”的清醒中庇荫于儒家经典文本的“原初视域”下,最终使诗之文本在阐释与批评中跌失于既定的“意义化”而愚懵自己和一个时代。
下篇
魏晋时期,经学的玄学化导致了中国古典诗学在理论形态上和文化地位上的巨大转型。从方法论上审度,经学的玄学化在理论层面上的运作还是中国古典阐释学的视域融合与意义让位的问题,正是魏晋的玄学大师——何晏、王弼、向秀与郭象,从不同的阐释视点对儒家经典文本进行破坏性误读(Misreading),逼使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从二元的冲突走向了互补的整合。顾易生在《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中讨论汉代“第一个文论高潮”时曾以为:“……两汉是经学统治的时代,而经学家多重教化,忽视了文艺的特征,因而窒息了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发展。”[②e]顾易生也企图从经学的视角追问两汉文学理论贫困的历史原因。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使自己站在“语言”和“阐释”的理论高度上,使自己的追问在思考和理论上深化下去。因为,经学作为学术宗教压迫于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终极问题还是“语言”与“阐释”的问题。魏晋玄学大师也正是洞视到了这一点,使自己的思考从“语言”与“阐释”逼向儒家经典文本的裂缝——“不定点”与“空白点”,最终在儒道两方视域的融合中逼迫儒家经典文本的中心指涉结构铺设给两汉文化语境的意义让位于道家。体现在中国古典诗学空间中,这就是在“语言”与“阐释”(破坏性误读)下的“视域融合”,及“视域融合”所造就的魏晋时期经学的玄学化和道家诗学对儒家诗学的放逐。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古典诗学也正是在儒道的“视域融合”中摆脱了规范于“善”的道德理性,走向了审美形态的自觉与理论思辨的自觉。
“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是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讨论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时推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关于“视域”这个概念在美学与诗学理论中的存在,伽达默尔认为最早从尼采和胡塞尔以来就明显地应用于他们的理论术语中,并指出:“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Gesichtskreis),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把这(概念)运用于思维着的意识……以此来标示思想与其有限规定性的联系以及扩展看视范围的步骤规则。”[③e]从伽达默尔对“视域”的阐释,我们可以理解为“视域”即是指涉主体受限于某一历史“地平线”而投出的思想视野,及这个受限的思想视野所展开的文化语境。也就是说,文本主体与阐释主体两者各自的思想视野均受限于自己生成与存在的那方文化语境,我们把限制文本主体思想视野投射的那方“文化语境”称之为“原初视域”,把限制阐释主体思想视野投射的这方“文化语境”称之为“当下视域”。历史的代际传递运动把原初视域与当下视域分向历史的纵向坐标系的两端,从而在原初视域与当下视域两方文化语境之间构成了一种时空距离的价值紧张;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解就是对这种时空距离的价值紧张的缓解。在理解的进程中,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总是受限于自身存在的当下视域而启动,然后达向对文本的理解,而文本又总是记忆着以限制文本主体存在的原初视域恭候阐释主体理解的进入,因此得以使文本主体的原初视域与阐释主体的当下视域在历史时空距离的价值紧张中走向缓解,最终归向了两方视域的融合,视域融合的结果即是各自均超越了自身受限的文化语境,获取了另一方意义崭新的视域。倘若,我们把思考的走向从伽达默尔那里折回中国古典阐释学的魏晋时代,就可以看出那些玄学大师对儒家经典文本的破坏性误读也正是在视域融合的理论意义上完成的。
在中国古典阐释学的经学玄学化阶段,原初视域是指从孔子删“六经”历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郑玄在阐释学的方法论上调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这一历史时期,浸淫于儒家经典文本且制导其文本意义生成的那方文化语境,就是从先秦的原始儒家思想到以获取经学的学术宗教地位而占据文化中心的先秦两汉儒家思想的总成。当下视域是指从两汉来沉寂于文化边缘,于魏晋时期向文化中心复归的道家思想及道家思想营造的那方文化语境。在魏晋时期,玄学大师作为阐释主体,他们对儒家经典文本进行破坏性阐释的思想视野受限于崛起的道家思想,而把道家思想作为自身存在且使其理解得以启动、运作的文化语境。在中国古典阐释学的发展历程中,魏晋时期的“经学的玄学化”体现在文化语境中,就是指涉儒家经典文本意义受限生成的原初视域与玄学大师受限对其进行破坏性误读的当下视域的融合。说到底,“经学的玄学化”这一命题表述的理论深层意义就是玄学大师对儒家经典文本从“语言”到“阐释”的破坏性误读问题。
人的终极关怀总是诱逼着人在信仰上皈依一个恒定不变的本体,儒家诗学把自我的灵魂与审美价值取向宗教般地命定于“经”的本体格位上,在“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的命题下完成了对两汉人文世界的精神独占。这种“精神独占”作为诗学现象的彰显,归返于阐释的理念本体上,就是儒家诗学主体遵命于《彀梁传》对《春秋经》读解的宣言:“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①f]而在汉魏文化转型之际,于儒家诗学阐释逻辑的反其道而行之中,道家诗学遵循“谁破坏语言,谁就拥有世界”的反价值命题,以《庄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②f]为生存信念和破坏性阐释的宣言,把儒家诗学的“奥区”——中心指涉结构颠覆于意义的支离破碎中,从而消解得一无所有。也正是在“奥区”意义支离破碎的表象背后,儒家诗学从文化中心悄然颓唐地向文化边缘退却,而道家诗学在玄学大师的清谈中从文化边缘向文化中心复归。值得注意的是,“退却”与“复归”的文化转型是以魏晋玄学大师对儒家经典文本的破坏性误读为内在推动力,在诗学与阐释学的现象学上则表现为视域的融合与意义的让位。
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在汉魏时期从二元悖立归向互补的整合,浓缩为哲学阐释学的理论表达方式就是“经学的玄学化”。如果我们从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阐释学理论比较和拆解这一理论表达的内涵,“经学的玄学化”其理论的重量正是以“经学”与“玄学”这两条显赫的学脉,简洁地照示了儒家诗学受限生存的文化语境与道家诗学受限生存的文化语境这两方视域的融合。道家诗学在本体论的猜想中把命定的终极——“道”归属于“无”,以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③f],尽管老子在“玄览”的神秘直观中从“无”推衍出整个彼在宇宙和整个此在世界,但是道家诗学主体的阐释行为却不可能从那个渺远而彼在的“无”起步而达向对此在文本的理解。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讨论“领会与解释”的意蕴时,曾以为此在主体的理解活动不可能从虚无的清明状态达向文本,此在主体总是处在它所受限的“先在”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下得以启动理解。可以说,老子从“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一无所有”[①g]中推出了“所有道家文化总成”,形成了阐释的语境,也正是这个阐释语境构成了道家诗学主体及玄学大师无可回避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这个“前理解”就是魏晋玄学大师在遭遇儒家经典文本时得以启动阐释的当下视域。那么在这个意义层面的另一端,儒家经典文本受限生存的文化语境构成了文本接受阐释主体得以进入的原初视域。倘若我们倒溯历史的逻辑程序,儒家经典文本的原初视域与玄学大师启动阐释的当下视域,两者共同作为文化语境的生成在历史中基本上是同期的,正因为“经学的玄学化”是魏晋玄学大师驻足于道家诗学生存的文化语境对儒家经典文本进行破坏性误读,那么儒家经典文本生存的文化语境成为接受阐释进入的原初视域,而道家诗学生存的文化语境则成为阐释受限启动的当下视域。
可以说,“经学的玄学化”就是儒家经典文本生存的原初视域与玄学大师进行破坏性误读的当下视域的融合,这是中国古典阐释学历程上的一个儒道视域融合的命题。因此,“视域融合”作为西方阐释学的概念植入中国古典诗学,在魏晋这一特定的历史景观下,其理论的意蕴就是指涉儒道诗学从冲突的悖立走向互补的整合。
在魏晋时期,儒家经典文本的中心指涉结构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性颠覆,这种破坏性颠覆的阐释学理论实质,就是玄学大师浸润于道家思想复归文化中心而营造的当下视域,以阐释从这方当下视域对儒家经典文本的原初视域进行侵入。在这里,“侵入”就是思想在阐释中交锋的破坏性误读。道家诗学从文化边缘向中心的复归彰显在阐释学上的一个最醒目的表征,就是玄学大师对《老子》文本和《庄子》文本的读解进入了时代的主流阐释。我们可以说,文本及其思想的生命只有置放于阐释中才能复活。因此,文本能否进入一个时代的主流阐释有着极为重要的生存价值意义。在欧陆的中世纪,《圣经》作为主流文化进入基督教神学的经典阐释空间,它标志着经院哲学与经院诗学的鼎盛及对这个时代景观的意义覆盖,当《圣经》从阐释空间退出,也标志着中世纪的惨淡终结及覆盖这个时代景观之意义的让位。两汉经学的鼎盛作为中国古典阐释学历程上的一块重要界标,它存在的哲学意义就在于标志着儒家经典文本进入这个时代的主流阐释,经学大师在“皓首穷经”的阐释中再度激活了栖居于经典文本中心指涉结构的意义,因此儒家诗学在意义的复活中得以制导着文学现象的发展,而《老子》文本与《庄子》文本在两汉经学的鼎盛期,是以退出阐释空间而忍受着难耐的孤独和死一般的寂寞。然而历史是公平的,《老子》文本和《庄子》文本进入魏晋时代的主流阐释,这标志着儒家经典文本在汉末最终从主流阐释的退却。何晏曾注《老子》而撰《道德论》,王弼注《老子》而撰《老子指略》,向秀与郭象注《庄子》。玄学大师对《老子》和《庄子》的阐释在魏晋蔚为文化大观。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魏晋玄学大师的阐释中重新激活老庄文本的意义,是让道家思想携带着复苏的生命力覆盖于这个人文世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玄风狂炽的主流文化景观下,玄学大师走向了对儒家经典文本的破坏性阐释。何晏撰《论语集解》,王弼撰《周易注》、《周易略例》和《论语释疑》,向秀与郭象从儒家经典文本的中心指涉结构摄取意义阐释《庄子》,使中心指涉结构的“意义”融解于《庄子》文本中,这实际上是从一个反向的视角在《庄子》的文本读解中拆解儒家经典文本的中心指涉结构。海德格尔把理解认定为“此在”的人把握自身存在的方式,把理解置放在生命存在的本体论高度,玄学大师正是对儒家经典文本的破坏性误读中以结束一个经学阐释学的独断时代,从而证明了自我的存在。
在西方,阐释学的发展曾在海德格尔思考的左右下完成了一次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巨大转向。海德格尔把理解认同为“此在”的人把握自身存在的方式,把理解置放在生命存在的本体论高度。但海德格尔又没有把企图在理解中证明自身存在的“此在”的人——阐释主体设定为理解的起点,而是把理解的起点铺设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这个起点就是海德格尔的“前理解”。“前理解”这个概念的容量是巨大的,它以“先有”(Vorhabe)、“先见”(Vorsicht)和“先知”(Vorgriff)三个层面,涵摄了历史、文化、语言、意识、心理等人类一切从逝去到当下的精神和精神物化物。海德格尔以为,主体只要在阐释中进入“前理解”,就被既定的文化、历史、语言、意识、心理所侵占,因此,主体绝对不可能再是一个通体透明的文化处女;正因此,主体也绝对不可能在贞洁的文化状态下不带任何失贞的偏见追寻文本的原初意义。伽达默尔正是在海德格尔“前理解”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理解的“偏见”。集合海德格尔的“前理解”与伽达默尔的“偏见”,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概念有一个共在的理论特点,即指“文化的先在”对阐释主体的浸淫,使主体阐释视野的受限是在文化的无意识渗透中完成的,正如德里达在《纪念保罗·德·曼》中的一句无意之言:“我们只能是先于我们知识景观下的我们。”[①h]在西方现代阐释学理论中,伽达默尔与德里达无论在思想中有着怎样的冲突,其实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认同“文化的先在”——“前理解”对主体生存的浸淫。因此,阐释主体对文本的误差性读解往往是在非自觉的状态下本能地行进。而魏晋玄学大师把道家复归文化中心的语境作为阐释受限启动的“前理解”,对儒家经典文本进行破坏性阐释而形成的偏见是在自觉的心理状态下肇始完成的。这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篇》所言:“正始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之倡也。”[②h]从阐释学的方法论来看,魏晋的玄学大师对儒家经典文本的阐释不同于两汉的经学大师,玄学大师是以自觉的破坏性阐释而颠覆儒家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使能指与所指分离而逼使意义让位。经学大师是以建构性阐释维护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使能指与所指在永恒的契合中维护儒家诗学的话语权力。因此,我们可以说,玄学大师对儒家经典文本的破坏性阐释就是自觉的误读。
玄学大师对儒家经典文本的破坏性误读是从道德观、圣人观、本体观这三个维面侵入的,可以说这三个维面的意义覆盖了儒家诗学整个中心指涉结构的全部内涵,即从孔子的“立言”历经荀子、扬雄到刘勰《文心雕龙》举倡的“原道”、“征圣”、“宗经”其全部的诗学价值取向。虽然玄学大师对儒家经典文本进行破坏性误读的具体操作往往是从一个范畴、一句语言的表达方式或一个文本段落入手的,但从道德观、圣人观、本体观这三个维面的侵入却足以逼使儒家经典文本跌入了整体意义让位的困境,从而导致了儒家诗学从文化中心地位的全面退却,而为中国古典诗学在这一时期走向自觉提供了阐释学的文化景观。玄学大师对儒家经典文本的破坏性误读,实质上就是儒家经典文本的原初视域与玄学大师启动阐释的当下视域——道家语境的融合,视域融合的结果就是原初意义作为所指悖离能指——经典文本,让位于当下意义。误读的思想力量是巨大的,是震撼人心的。玄学大师正是凭借误读的力量一羽拨千斤,轻而易举地“读破”了两汉经学大师殚精竭虑凝铸的那方“大一统”的精神世界,逼使儒家诗学让位于道家诗学。这实际上是彰显在汉魏转型时期文化景观上的文学批评权力话语的争夺现象。这种文学批评权力话语的争夺反照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中,其内在的残酷性绝对不亚于那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对国家权力之争的血腥屠戮。但是,道家诗学恰恰是背靠于清谈的误读,在诗意的表象中剥夺了儒家诗学的内在权力话语表达,这就是玄学大师在阐释——误读中玩尽的从容与潇洒。
注释:
①a Paul Ricoeur,From Text to Acti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1,p.106.
②a 《前汉书》,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书店1986年影印乾隆四年武英殿本,第696页。
③a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8页。
①b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94、110页。
②b 《春秋公羊传注疏》,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世界书局阮元校刻本,第2196页。
③b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0页。
④b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⑤b 《史记》,见《二十五史》,第348页。
①c 《礼记正义》,见《十三经注疏》,第1609页。
②c 张衡:《思玄赋》,见《二十五史·后汉书》,第973页。
③c 《诗大序》,见《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269页。
④c 《尚书正义》,见《十三经注疏》,第131页。
⑤c 《礼记·乐记·乐言》,见《十三经注疏》,第1535页。
⑥c 《诗大序》,见《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272页。
⑦c 同上,第270—271页。
⑧c 郑玄:《诗谱序》,见《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262页。
⑨c 班固:《两都赋序》,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页。
①d 刘安:《离骚传》,见《二十五史·史记·屈原列传》,第280页。
②d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页。
③d 《前汉书》,见《二十五史》,第696页。
④d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页。
⑤d M.H.Abrams,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Oxt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53,p.59.
⑥d 同上书,P.60.
⑦d 同上书,P.60.
①e 《文心雕龙校注》,第250页。
②e 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版,第351页。
③e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88页。
①f 《春秋彀梁传注疏》,见《十三经注疏》,第2400页。
②f 《庄子》,见《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缩印浙江书局光绪初年汇刻本,第61页。
③f 《老子》,见《二十二子》,第5页。
①g 《老子本义》,见《诸子集成》第三卷,上海书店1980年影印世界书局版,第1页。
①h Jacques Derrida,Memories for Paul de Ma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6,p.34.
②h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家刻本,第1012页。
标签:玄学论文; 儒家论文; 经学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语境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语言表达论文; 读书论文; 诗大序论文; 国学论文; 学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