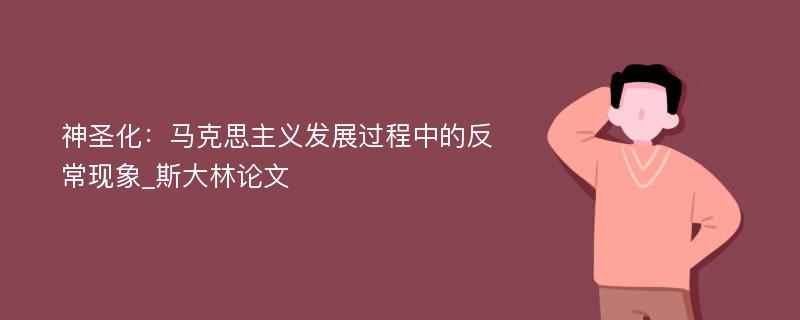
神圣化: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畸形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畸形论文,过程中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的理论曾有过理论上的蓬勃发展、实践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但是也经历过被扭曲、被神圣化的不幸。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化本身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和发展,而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极端表现,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危害都不容忽视。
一、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被神圣化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曾有效地摧毁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在反对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形而上学观点的同时,也反对来自共产党阵营内部和不能准确把握他们理论的青年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宗教化倾向。在他们晚年大量的通信当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力图掌握自己理论的命运。1885年4月23日恩格斯在伦敦写了一封寄给俄国人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在信中他对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完整地接受马克思的伟大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感到自豪,并且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①。当年岁末,恩格斯又批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说:“他们面临一个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强大而出色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②恩格斯实际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不允许把一种科学的理论变成神圣的教条,化作能医人间百病的灵丹妙药。革命导师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所取得的胜利,就是对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的重重一击。试想,如果盲从照搬马克思恩格斯所讲过的话,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会在当时落后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曾针对“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③他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没有写的就不能讲,不能做,那是荒谬的。在谈到1921年苏联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以多样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问题时,列宁批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马克思恩格斯书本里找注释和根据,以攻击新经济政策的做法。他说:“没有一本书提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对这一点也只字未提。没有留下一段可以引证的确切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④列宁认为不能让书本上的条条束缚自己的手脚,“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并且与之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由于经典作家本人的努力,他们在世的时候,任何对其理论所采取的教条态度以及神圣化的做法都不能形成气候,造成大的危害。
但是,从斯大林开始,马克思主义开始被神圣化。在长达29年(1924-1953)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作为前苏联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有历史的丰功伟绩。然而,他是一个带有专制色彩的领袖人物。我们看到,除了绝对的权力外,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斯大林一人垄断着解释权和发展权。他打击异己,排除异端。联共(布)党史和三十年代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许多地方都能看到斯大林唯己唯是的痕迹。例如,对马克思主义的概括说明,必须要符合斯大林的观点。事实上,斯大林领导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虽然在理论的普及和宣传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却开始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神圣化,在国际共运史上,各国共产党都不同程度地迷信过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模式。理论上的照抄导致了实践上的照搬。这使具有不同国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吃了些苦头。
在这里,无需对斯大林进行全面的历史功过评价。我们只是说,神圣化,这一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畸形现象,是在列宁以后从斯大林那里蔓延开来的。斯大林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化是极少数人(主要是有一定地位的权威政治家和理论家)在没有被有效抵制的情况下,通过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强制手法,利用广大民众对理论的陌生感和紧迫需要而一手制造的宗教化的马克思主义。神圣化给马克思主义穿上一层神秘的外衣,涂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
二、神圣化的表现
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神圣化,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总的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理论上的垄断。“垄断”是从经济学中借用的一个概念。它表示对某种东西的“把持”和“独占”。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是指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和发展权的把持和独占。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以著作、论文、通信等文字形式留传后世的,它不可能象实证科学的公式和图表那样清晰明白,需要在翻译的基础上进行注解和阐述。而翻译和注解都属于解释的范畴。按照解释学的原理,任何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失真。因此,就产生了元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有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除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外,还没有别的解决方法。然而,长期以来,总有少数人利用强制手段或者其在理论上的权威地位,来封其他人的嘴,制造一种声音,达到在理论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效果。
诚然,权威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见多识广,处在解释和发展理论的有利地位。但他们并不必然代表真理一方。领袖是人不是神,他们也会犯错误,这就需要批评和反批评。而如果理论的发言权被垄断了,就没有批评和反批评,就没有理论上的民主空气。而没有民主的理论气氛,就不会产生真正科学的理论。
正象政治上的专制并不象征专制者的权力地位是巩固的一样,理论上的垄断也不意味着垄断者的强大。而只能说明他们的虚弱,因为垄断把马克思主义“贵族化”,其结果必然导致垄断者的孤立。
第二,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对领袖人物的爱戴和尊敬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它把领袖变成神,把领袖的话当作神的谕言,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的最典型表现。试想,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领袖都封为神,把他们的话当作神旨,他们的思想还有什么研究和发展可言呢?在神学的迷雾里,人民群众只好听天由命了。这种看起来荒唐十足的对领袖及其理论的崇拜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候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斯大林的独是独尊,“文化大革命”中“最高指示”满天飞就是明证。当然,在科学和文明日益昌盛的今天,再也不会有人公开地造神了。但这并不等于就没有变相的个人崇拜。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毒,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唯命是从、唯上唯是,太缺乏怀疑和批判的科学精神,所以,就容易把领袖们的每一句话,直接当成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第三,宗教仪式化。宗教仪式是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通过一套严肃的礼节和程序,在客观上起着巩固宗教信条,维护宗教信仰的作用。十年浩劫中,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实施了类似于宗教的仪式。例如,人们穿一样的服装,留一种发式,拿一种语录本,高喊同一句口号或“最高指示”,大家必须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等等。
第四,教条化。教条化是指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裁剪现实,不是把客观实际当作研究和行动的出发点。事实上,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的任何做法,都与教条化有关。教条化主要表现有:①理论和实践都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找到对应的指示或根据。凡是在经典著作中找不到根据的东西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②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天衣无缝、绝对正确,勿需发展。面对丰富多采的现实“贴标签”。③任何理论和实践是非,都可以在唯一的参照系中得到判明。这个参照系来自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词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王明的教条论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四人帮”的教条论(当然他们不只是教条主义的问题)差不多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到了死亡线上。“两个凡是”论,曾一度束缚了人们的头脑。直到今天,头脑僵化,麻木不仁者不是还大有人在吗?这种人怀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神圣的宗教感情,不大习惯新生事物,而对早已过时的条条框框有滋有味、津津乐道。君不知,有人在参观了深圳特区后,竟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辛辛苦苦五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说什么如此搞法,他们将无脸见马克思。其实,从根本上说,任何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宗教化而不是当成发展的理论和行动指南的人,都不配见马克思。
第五,万能化,万能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灵丹妙药包医百病。它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教条化的一个变种,其思想基础是理想化。以为马克思主义包罗万象,什么都有,能够解决人与自然和社会的一切问题,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也。其做法是:①依据先被理想化的理论教条,只管开“药方”,而不论“病大病小,病死病活”。②公式解题,套话连篇。如对许多社会现象、复杂事变的解释经常用诸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抽象原理去简单说明。似乎所有的事件都可以用某一原理或同一原理去解释,证实或证否。在实际生活中,马列主义老太太之类的人格扭曲的人就太多了。他们拿着马克思主义的万能公式,可以把简单化成繁杂,也可以把繁杂化为简单。从不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理论上的精心探索,把一种科学的理论弄成了贫乏枯槁的片言只语。
总之,神圣化的种种表现完全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初衷,因为他们曾经谆谆告诫:“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⑦。
那末,既然马克思恩格斯有言在先,多次坚决反对对他们所创造的科学的理论采取非科学的态度,那么为什么还是出现了其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畸形现象呢?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被神圣化这一畸形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历史误会,而是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上的根源。这正是需进一步探讨的。
三、神圣化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被神圣化呢?一种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理论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被扭曲变形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运为什么有悖于创始人的初衷有时被弄得面目全非呢?
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找到马克思主义被神圣化的根源。
首先是历史根源。马克思主义的落脚点和理论目的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及全人类的解放。一百多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的是可以逐步实现的。1848年欧洲革命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使得正处在斗争激流中的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从此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的指引下,无产阶级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进行了一次次卓有成效的革命战斗。1871年,巴黎公社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巴黎公社虽然只存活了72天,最后失败了,但毕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运动富有成效的一次尝试。人们日益懂得,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只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就能够推翻旧世界。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很难设想,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会有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思想体系能够象马克思主义那样如此地改变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
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取得实践上的伟大成就,赢得理论上的巨大声誉的同时,也给自身带来了副产品:有人以为马克思主义是济世救民的万应灵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神圣化。事实上,1924年1月,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立刻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化身。他所主持的共产国际开始了“反右倾”斗争,苏联的经验被神圣化,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人的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受到扼杀。所以我们说,基于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取得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功,斯大林等人制造的个人崇拜和苏维埃崇拜,是它能够被神圣化的历史根源。
其次是社会根源。大工业无产阶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主体,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产生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推动现实的革命运动。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又会提出新的课题,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又能够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前进和深入开展。但是,从逻辑顺序上看,是先有无产阶级的存在,后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没有早期资产阶级摧毁封建制度的革命,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就不会有无产阶级及其队伍的发展壮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大机器工业文明才能打破封建社会小生产的规模和狭隘的农民意识,才有人与人之间日益广泛的联系和不断扩大的眼界。可见,马克思主义是有着自己深刻的社会生产力背景的。这说明了物质因素、经济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制约作用。同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质量也受到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的影响。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先后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经济不发达,小生产者似汪洋大海的国家取得胜利的,作为共产主义政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就必然遭到腐朽的封建残余思想和落后的小农意识的“包围和侵蚀”。虽然党内的优秀分子能比较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但广大的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对这个理论是陌生的。他们不可能自发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先进的理论,而必须依靠灌输。而灌输就容易导致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神圣化。特别是在某些政治领袖有意识地制造或默认个人崇拜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肯定会相应地被从地上捧上天国。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毛泽东,虽然创建了丰功伟业,但都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沐浴下彻底地铲除潜意识深层的封建意识,倒是在小生产充斥的国度先后制造了罕见的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马克思主义也曾一度被教条化、神圣化。所以,我们认为,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大量小生产者的存在以及封建的小农意识是马克思主义被神圣化的气候、土壤,即社会根源。
最后是认识根源。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的认识成果,其本身也是认识的客体。①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作为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大家,其理论著作之丰富,理论体系之宏大,涉及问题之广泛,方法和逻辑之精深严密,都是其他理论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但是,这也形成了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困难。因为不经过艰苦的阅读和理解过程就随用随取,很容易肢解马克思主义。②马克思主义是理论思维的科学成果,要把握它,除了用“抽象”这样一种思维方法外,至今还没有更好的直接认识手段,而理论的抽象是非常容易走向谬误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片面引证,随意解释,假设前提大作文章以及夸大真理,危言耸听,偷换概念,不顾逻辑等等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非科学态度和行为。诚然,谬误终归是谬误,但是,发生在理论研究领域的是是非非并不能象某些严整的科学实验一样短期内就能对所得到的结论彻底地证实或证伪。③任何阶级、政党和个人都有着自己特定的认识立场和认识背景。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样一门阶级性很强的学说,人们不会有绝对的超功利态度。认识主体的各种主观因素难免渗透到认识过程和结论中去。“文革”中的语录大战以及用同一个理论为两种相反的思想政治路线作辩护就是明证。总之,认识主体的主观性以及认识手段的抽象的游离性,就是马克思主义被神圣化的认识论根源。
四、神圣化的恶果
神圣化虽然只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畸形现象,但它对马克思主义有机体本身和亿万人民的实践活动却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危害。表面上看来,神圣化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实际上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降低了它的威信,削弱了它的功能,最终使之由于贫血和缺乏养料而窒息。具体来看,神圣化的恶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不到真正的发展。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通过人民群众和他们的实践活动而获得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可是,神圣化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主体之间设置了障碍。马克思主义由于神圣化而被封闭在至高无上的圈子里失去了紧扣时代主题和扎根群众实践的活力。这样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它本质上要求不断发展的权利,剥夺上它生命的活性因子。
第二,理论研究在神圣化的氛围中形不成真正的民主气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发展从来就不是极个别人的事,它需要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和理论爱好者大军的共同努力。这就需要理论研究的民主气氛。而神圣化恰好否定了理论研究的民主本性。在我们建国以后的历史上,扼杀理论民主的教训是惨痛的。粉碎“四人帮”后,虽经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但直到现在,理论研究的民主气氛仍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第三,神圣化培养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宗教感情而不是科学的态度。长期以来“左”的东西之所以长盛不衰,其中理论上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一些人囿于某些神圣教条所划定的框框和模式,理论视野狭窄,理论境界很低。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人用被神圣化而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去裁决理论是非,对新概念、新观点、新理论采取不予承认或扼杀的态度和手法。
第四,神圣化使整个社会活力减少,而且导致“信仰危机”。众所周知,社会活力的大小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准之一。社会充满活力还是缺乏活力,这主要看组成社会的个体是否充满活力。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化在理论上和社会实践中都制造一种声音,一种色调,一种思维。结果必然是人们应该具有的批判精神和开拓意识的缺乏,社会活力的缺乏。应该看到,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爆发和蔓延的悲剧的土壤之一。两极总是相通的,一极如果是神圣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极肯定就是“神圣的危机”。因为,一种被扭曲的思想体系不可能从根本上说服人。
第五,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有可能断送我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大业的远大前程。因为,作为执政的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一旦被扭曲,就可能导致理论和实践上的方向性错误。我们在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不能说不深刻。此外,我国正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步伐,力图抓住前所未有的振兴中华民族的大好机遇,需要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发挥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精神。然而,被神圣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给予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真正的理论武器。在神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氛围当中,人们必然被僵化的思想观点牢牢捆住手脚,失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本来具有的胆和识,哪里还谈得上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呢?
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⑧的确,并不玄奥、很朴实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它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它与神圣化的马克思主义有着质的不同,我们需要的就是朴实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神圣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不但要分析马克思主义被神圣化的现象、根源,认识其危害,而且还要创设多种条件以防止马克思主义在其未来的发展中神圣化的东西故态复萌。为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都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思想观念领域努力清除封建残余思想。因为封建意识不仅不可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而且为神圣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温床。由于我国曾经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残余思想根深蒂固,所以,反封建的任务一直很艰巨。
第二,培养全社会的科学理性。“神圣化”是反科学的,科学的理性是优化社会主体素质的重要一环,它包括追求真理的勇气、批判和怀疑的精神以及科学的思维和态度等。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培养起越来越强大的科学理性,任何个人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都是极为不易的。
第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只有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不断增长才能为我们科学理性的培养、反封建任务的完成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使我们最终彻底铲除“神圣化”这一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畸形现象成为可能。
注释:
①②③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0、458-459、460、472页。
③④⑤《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626、626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