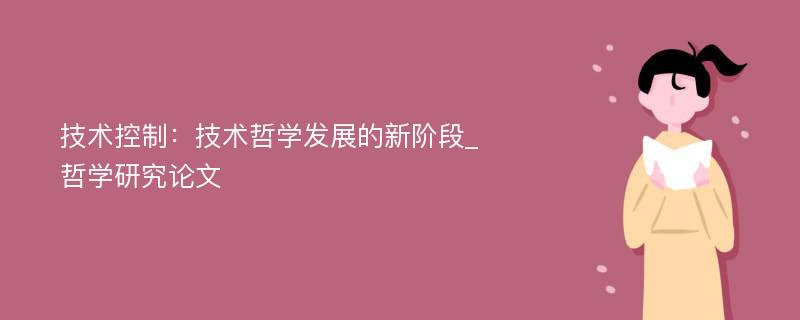
技术控制主义:技术哲学发展的新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论文,新阶段论文,哲学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7)05-0036-07
技术控制主义(technological appropriateness)是在现代技术革命中逐渐形成或正在形成的一种技术理念,是对技术无政府主义、技术乐观主义以及技术悲观主义的辩证综合和发展,是人们关于技术、人类和世界之间相互关系的更加成熟的认识,是人的主体性和价值理性复归的表现,也反映了人类对自身未来命运的关注而采取的积极态度。
控制的技术思想要求我们在从事技术的开发、应用与发展或在运用传统技术之前,必须反思我们的目的和价值,必须有效地控制技术,使之成为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一种恰当工具;在控制理念基础上发展技术的哲学思想,是社会的进步力量。技术控制主义的重要意义是它提示我们能够向技术本身提出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人类和技术的关系、应如何规定技术等等。一旦这些基本问题受到我们的注意,并在理论上得到合理的和科学的解释,必将有助于我们清楚地评价现行政策,并根据人类的要求制订切实可行的战略;而且被控制的技术也将帮助我们促进社会创造力的进步,在从整体上深刻反思人类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确定良好的价值尺度。[1]
一 技术控制主义的基本内涵
美国学者德雷奇森(Alan R.Drengson)撰文指出,在西方人关于技术的一般哲学观念中,存在着四种明显的对待技术的哲学传统,它们是技术无政府主义、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恐惧主义和技术控制主义,并且技术控制主义是技术哲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或技术哲学的第四种形态。[2]
技术控制主义将道德和生态价值引入技术的设计和应用过程当中,强调在技术、工具和人类以及道德之间追求一种正当的、巧妙的匹配。这种观点主张抛开过度集中的技术,转而去应用那种能够保存社会共同体价值的、分散的、具有人性尺度的技术,即赋予简单技术以价值。它要求人们在开发新技术或继续使用旧技术之前要反思技术的价值,主张将技术看成是一种实现人们自由选择的目标与价值的工具而加以控制。很显然,这种观点认为技术没有超出人类的控制范围。在技术控制主义者看来,技术并不是一种超越人类理性选择的异己力量。技术控制主义认为技术中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保证着选择的开放性,人们不应该都依赖同样的技术。就生态角度而言,技术控制主义提倡在人类、机器和生物圈之间保持一种良性的、共生的相互作用,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协调生态系统法则,考虑一切代价(可测度的和不可测度的)。
技术控制主义并不像技术悲观主义那样排斥技术,相反,它认为通过技术的运用可以促进人类的发展。在技术控制主义者看来,技术的使用成了提高生活质量的一部分,劳动成了一种有意义的事。技术的设计将充分考虑并提高人的个体的价值、生态的完整性以及文化的健康性。
技术控制主义强调在尊重自然内在价值的基础上使用技术,与自然共事,而不是将强大的技术强加于自然之上并试图控制和征服自然。它要求对人类社会的技术进行一定的控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手段,控制其发展、应用负面效应等等,同时,它要求不应当将技术作为终极目标,而应该成为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有效手段。因此,人类必须适当地发展和应用技术。
技术控制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舒马赫(E.F.Schumacher)、弗洛姆(Erich Fromm)、星野芳郎、克拉克(Robin Clarke)、科林(David Colling)、米歇尔·巴勒姆(Michael Baram)、汉斯·萨克塞(Hans Sachsse)、杰里米·里夫金、特得·霍华德以及技术替代论者、技术生态论者、绿色组织成员、技术的民主控制论者、技术的社会控制论者以及罗马俱乐部的成员等等。
二 技术控制主义产生的必然性
技术控制主义之所以成为当代技术哲学中正在形成的一种技术理念,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同时任何一种技术理念的产生也都不是凭空突然出现的,都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依据。
首先,技术控制主义的产生是技术观念发展的一种新形态。19世纪工业极大发展时期以前,技术无政府主义(technological anarchy)是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对待技术的思潮。它将技术看成是一种获得财富、权力和驯服自然的工具,主张政府机构对技术及市场情况尽量少加规定和限制而任其发展。这种技术无政府主义状态无疑会有助于技术发展的多样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技术的迅速发展。但当作为满足社会需求而追求的那种“能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技术趋向于其自身的终结的时候,技术无政府主义也就失去了影响力。技术乐观主义(technophilla)是在近代两次技术革命中形成的一种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技术理念。它对技术的发展及其后果持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只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未来总是美好的;而且技术乐观主义者对技术的副作用也持乐观的态度,认为由技术而引发的消极后果最终将由技术的发展来消除。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由技术而引起的全球性问题的凸显,技术的发展没有解决由技术而引起的问题,反而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使得技术悲观主义开始在全球蔓延。而且,这种把技术发展的后果完全归结于技术本身并只凭单纯的技术手段就能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的看法也是过于简单化了的。技术恐惧(悲观)主义(technophobia)是随着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技术理念。它认为技术造成了人类的不幸,人类不可能依靠科学技术摆脱贫困而获得幸福,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为了挽救人类、消除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应该阻止技术的发展。技术悲观主义引发了人类对自身前途命运等方面的诸多深入思考不无合理的层面,它意识到了在使用技术的时候需要一种自觉的反思与批判的方式,但把问题都归因于技术本身又是片面的。
但是,在面对环境、资源、生态等等日益恶化的全球性问题时,人们发觉放任技术自由发展是不现实的,盲目的乐观也是自欺欺人,消极悲观更是于事无补。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要改变世界就得面对世界,正视问题,采取实际的行动。这时,对技术进行控制就成为人们思考的一个重点,由人创造的技术而产生的问题最后还得由人采取行动来解决。在把技术当作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中介、手段和工具的同时,还需要把技术当作控制的对象。技术控制主义由此而成为技术哲学观念发展的新阶段。
其次,技术控制主义的产生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向。一般而言,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并将要经历敬畏、征服与和谐相处三个阶段。在人类历史上的整个农业文明时代,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局限,人类对自然是崇拜、敬畏和顺从,正如培根所讲的“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首先在英国,继之在法国、美国、德国爆发了工业革命,这是以技术革命为中心内容的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它迎来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时代——机器大工业时代。工业文明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得到极大膨胀,人自我标榜式地成了自然界的主人。这正是康德所谓的“人为自然立法”阶段;自20世纪30~4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一个信息化时代,这时,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开始凸显,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已经成为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对几乎是万能的技术进行反思并积极控制技术的负面效应。这就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阶段。要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就必须把人类用以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手段与工具的技术纳入到人类的控制范围,遏制技术的过度滥用现象,还自然以相对自然的状态,还自然以一个适合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状态;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摆脱自己所面临的困境,还必须靠主体性的发挥来创造解决问题所需的各种社会条件,其中,将技术纳入到人的控制范围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和必然选择。正如恩格斯所言,整个自然界是一个具有连续性和相互依赖性的综合体,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一起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
再次,技术控制主义的产生,更是对人类自身生存状况的关切和对人类未来前途命运的关注。技术使人类脱离了原始的幼稚状态和野蛮状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增强了人类在自然中的生存能力。但是,由于工具性技术与机器性技术之间差别的存在,在工业时代以前的各个文明社会中,技术所起的作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当时的技术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组织人们生活的方式。而在世界机器模式里,技术已成了组织一切生命活动的方式。[3] 这种技术性的生活方式,已经给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后果,恶化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威胁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生存和发展。这是与人类发展技术的初衷背道而驰的。对此,人们从人类未来命运的角度出发关注对技术进行控制的问题就成为很自然的了。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认为,人类再也不能从技术中解脱而回到他诞生的状态去;同时技术不仅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机会,而且也带来了无可估量的危险,技术已成为独立而猛烈的力量,这时,由技术实行对技术祸害的技术控制,可能会增加祸害。绝对的技术统治对它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把用技术手段消灭技术看作是完全能实现的任务,就意味着将开辟通往灾难的新道路。狭隘判断的狂热,为了一种所谓的技术而放弃了技术的可能性。但是问题在于怎样对已主宰人类的技术施加影响。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他为自己的生存而控制技术后果的方式。[4]
这种关注,在罗马俱乐部成员的研究报告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他们对不加思考地接受技术的好处表示反对,也对不加思索地拒绝技术的好处感到遗憾,他们希望社会接受每一项新的技术进步,但在广泛采用这项技术以前,要对三个问题做出回答,其中之一就是:如果大规模引进这种发展,会有什么物质上和社会上的副作用?思索这样的问题的目的,就是要对技术进行必要的控制。[5] 米萨诺维克在《人类处在转折点》一书中更明确地从人类未来命运的角度表达了对技术进行控制的必要性,他认为:现在,我们正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第一次感到限制的必要性,必须限制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或者至少改变其发展道路。我们的子子孙孙要求我们与受苦受难的人同甘苦共患难,这不是出于慈善,而是出于必要。现实要求人类致力于在整个世界系统内实现有组织的增长。[6]
三 技术控制主义构想的控制手段
技术控制主义者们在倡导对技术进行控制的同时,为了达到有效的控制效果,给出了种种对技术进行控制的手段和途径。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在《技术的社会》一书中就曾提出“适当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概念,强调技术发展应该增加个人对自由和人权的关心;英国罗宾·克拉克倡导的“替代技术(alternative technology)”论,强调最小限度地使用不可再生的资源,最小限度地干扰环境,在地区或小区域自给自足,消除人类的异化和剥削;日本技术论学者星野芳郎主张“多样性的技术”,反对单一类型的技术,不管是小型的还是巨型的技术,以适应自然生态环境多样性要求和人类能力多方面发展的趋势。他还提出依靠整个技术体系的历史性转变来解决人类生态环境问题。[7] 弗洛姆更是提出要发展一种“人性化的技术”来替代目前这种非人性化的技术,还技术服务于人类的本来面目。[8] 米歇尔·巴勒姆指出要对科学和技术实行自始至终的符合人道的社会控制。
德国H·波塞[9] 在分析技术及其社会责任问题时就认为:责任总是要考虑价值因素或者代价而与行动的后果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行动包含耽搁,只要什么都不做,当然一切都不成问题。不过,只要开始进行区别,诸困难就出现了,如责任机关、要承担责任的东西、责任的主体、为什么而承担责任等等。其中,就责任主体而言,波塞认为这同样是复杂的:可能谁都负责,但结果没有谁肯负责任。这就如同做自我检查,大家都说要为一切负责任一样。波塞所设想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共同责任模型——为了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有必要确立一个完全改变了的模型以取代上述思想,这个模型就是一个共同责任(mitverantwortung)模型,它将恰好按照每个人对于系统所能起到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来分配他相应的责任。美国学者玛乔丽·C·米勒[10] 认为,公民社会对技术的某种控制既可能又正当。米勒所认为的公民社会模式强调有关技术变化的决策乃是政治谈判而非技术过程。这种模式是多元的,不能将公民社会置于单一的固定不变的实体中;而且在这样一个持续产生着的公民社会中,技术变化必须得到通过复杂的政治过程产生的决策的评估和指导。远德玉和陈昌曙认为:对技术发展的控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个人微观层次,主要指发明家和工程技术工作者个人和研究单位;二是社会中观层次,主要是企业和公司;三是社会宏观层次,指国家政府。……对技术的发展和控制还应有第四个层次,即全球社会。[11] 美国前国会议员阿尔·戈尔也认为:我们怎样才能共同努力拯救环境呢?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必须签订国际协定,在全球范围约束我们的行为。[12]
德国经济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沃纳(Sombart Werner)著有《技术的控制》(Diezahmng der Technin)一书。在该书中,沃纳认为应当从国家或社会的角度,对技术的发展予以计划和控制。[13] 美国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对技术进行控制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一个新领域。他在《后工业社会》一书中概括了后工业社会的五大特征,其中的第四个特征就是:“技术的控制与评价”。贝尔认为,随着新的技术预测方式的出现,后工业社会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社会变化领域——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计划和控制的领域。因为在一个越来越依赖技术和创新的社会会产生危险的不确定性,而新的预测和“筹划方法”的发展,标志着经济历史将出现一个新时期——有意识、有计划地控制技术变化,以便缩短未来经济中的不确定性阶段的时期。贝尔认为,新的预测方法和预测技术(如直观技术、探索技术、规范技术以及反馈技术等)的开发和应用,标志着人类已经有能力科学地规划技术的发展及其结果。在贝尔看来,利用技术预测可以规划技术的发展,促进新技术的产生,并加快技术在经济中的传播与应用等。在贝尔看来,尽管技术进步具有有害的副作用,具有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并且完全出乎意外的二级、三级后果,但如果在应用之前对那些技术加以“评估”,那么本来是可以考虑采用其他技术或做出其他安排的,也就是说能对技术做出合理的选择与控制。技术评估作为一种控制技术发展的手段,有助于人们了解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有助于人们通过对目标的评估而提高人类的预见能力,从而控制技术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后果。而技术评估是可以做到的,其前提是需要一种允许进行这类研究、并有助于制定技术控制标准的政治机制。[14]
技术的民主控制思想主张通过社会民主的手段来控制技术,即技术的民主控制(democratic control of technology)。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温纳(Langdon Winner)、斯克罗夫(Richard E.Sclove)、伯格曼(Albert Borgmann)等人认为可以通过民主的手段来控制技术。费恩伯格对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改变控制所在,将技术发展从产业利益中消除,从而走向社会控制的更为民主化的制度;温纳倡导民主技术的塑造以及民主社会的建构来恢复因科学和技术精英权力的发展致使遭到破坏了的市民对决策制定的参与;伯格曼认为,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强大而有效的工具,就社会秩序而言,我们有责任致力于技术选择。技术的民主控制思想期望通过对技术的民主设计、民主参与来达到对技术进行控制的目的。美国学者詹姆士·凯洛尔(James Carroll)提出一种“分享技术”制度,他指出,人们参与发展、实施和管理技术的社会和技术过程……他们要在技术的发展……和实施中起到重要的和合法的分享作用。他还列举了控制技术的三种主要方式——公民诉讼、技术评价和个人与集团从事的各种特别活动。凯洛尔认为,有了分享技术以后,凡是在技术的复杂性面前感到无能为力的个人,均可以通过这三种手段来获得表达他们观点的渠道。H.费雷(Wilbert H.Ferry)则认为,在美国,控制技术的唯一出路是修改宪法。在他看来,过去制定的政治制度和理论,对解决现代问题是毫无用处的,这些现代问题只能靠根本不同的新制度来处理。他认为美国是一个技术化的社会,因此必须修改宪法,以保护公民脱离技术造成的危险,应确使技术朝着有利于人类幸福的方向发展。[15]
从各种控制技术的手段运用来看,无外乎两类,一是用技术的手段控制;一是用社会的手段来控制技术。通常情况下,在技术努力和社会努力之间,原则上谁也取代不了谁,但谁也离不开谁,因此提高技术水平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许多社会因素的社会问题……我们在社会条件改善上若无重大的进展,技术的发展状况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观。[16]
用技术的手段来控制技术,仅仅表明技术系统本身在技术结构、技术后果、技术功能等方面的可控;正如英国学者C.P.斯托弗所言,科学家、工程师所能支配、并且真正能够设想到的,不过是他本行技术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其硕大无比的全貌,则非他所能企及。[17] 但技术是社会行为和结构的特殊形式,技术的发展就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的不同群体的利益、文化上的选择、价值上的取向和权力的割据等都决定着技术的轨迹和状况。而且,在狭隘的自我中心的价值观和近视的国家制度的框架中实行的“技术性修补”,无补于世界问题的解决,并且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从科学发现到应用性研究和技术性开发,再到大规模生产,这个周期相当长。[18] 正如美国学者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所指出的,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技术或进步本身,而在于我们必须从中做出选择的各种可能的技术和进步途径;[19] 而且,芬伯格也认为技术遵从有意识的社会控制。在他看来,现代技术体现了提升阶层分化和统治支配方面的政治价值,而社会建构主义者的研究表明一项根本不同的、民主化的技术是可能存在的。如果更多的社会团体参与技术选择以及如果技术的发展因此而受到民主的控制,那么这种可供选择的技术就是可能存在的。所以,用技术的手段来控制技术,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为了达到更加有效的控制效果,还需要运用社会的手段。在两种控制手段的交替配合使用中达到最佳的控制效果。
四 技术控制主义的未来
技术控制主义抛弃了技术无政府主义、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单纯将问题集中于技术本身的片面观念,强调了社会因素在控制技术中的作用并设计了对技术进行控制的多种社会手段。而这些社会手段所控制的直接对象并不是技术而是人。也就是说,在技术控制主义者看来,技术并不是什么独立发展的客体,而是存在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产物。技术既不是一种自行,也不形成命定般的形而上学发展的结果,它只不过是人的一种行为。人在技术中不是被迫屈从于某种异己的东西,实际上遇到的是自己本身。[20] 因此,要控制技术,最终还得控制人,正如英国物理学家彼德·狄拉克(Peter Dirac)所言:在最后的分析中,这肯定意味着技术是被人所掌握的。如果它们之中有哪一个要受到责备的话,那么绝不应该是工具,而应该是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21] 美国学者欧文·拉格兹也认为,人类面临着一个严峻却得不到广泛认识的问题,即决定人类存亡的不是外部极限,而是内在限度;不是地球的有限性或脆弱导致的物质极限,而是人和社会内在的心理、文化尤其是政治的局限。这种局限表现为个人和集体的管理不当、不负责任和鼠目寸光,并导致了其他许多世界问题……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不是因人而起,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通过改善人的行为得到解决。[22] 因此,在技术控制主义者看来,技术不是自主发展的,也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相反,任何技术都应该受到并能受到人类的控制。这充分发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主体地位,表明由人自身所带来的问题最后还得由人自己去解决。
技术控制主义一改以往几种技术理念对技术无所作为的态度(技术无政府主义强调对技术的发展不施加任何人为的干涉,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仅仅是面对技术发表感慨而已,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把人的实践和行动带入对技术的思考当中,强调了人和社会对技术的积极干预。
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经验转向也为技术控制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1998年,荷兰技术哲学家卡罗斯(Peter Kroes)与梅耶斯(Anthonie Meijers)最先提出《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经验转向》的研究纲领问题,并经荷兰技术哲学家阿克特惠斯(Hans Achterhuis)等人的倡导,最后认为当今全球技术哲学研究正在发生着所谓的“经验转向”(the empirical turn)。[23]技术哲学研究中的这种经验转向,表明经典技术哲学研究中将技术看成是抽象的和整体的而忽视技术本身的缺陷开始凸显并被认识。也就是说,经典技术哲学只注重对技术进行形而上的分析,却忽视了对技术人工物这一基本的物质存在的研究。因此,主张“经验转向”的技术哲学家们强调,技术哲学应该更多地集中于阐述应用工程科学和研究技术的经验科学的基本概念之上,而较少地集中在无法确证其与现实如何联系的、抽象的神话和臆想之上,即对技术的哲学反思应该基于反映现代技术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经验式充分描述之上。也就是说,要“打开技术黑箱”。这是因为,现代技术是一个历史成长起来的、高度复杂化的和差异化的现象。要认识到现代技术的这个特点,只有通过从整体水平上的分析转换到局部层面上的分析才可能。技术的丰富性只有通过对现代技术进行放大镜式的观察才能显现出来。技术哲学研究中的这种经验转向为技术控制主义所倡导的控制的理念提供了一种从技术层面来说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论和认识基础。如果说以前技术控制主义所追求的对技术进行控制是从总体上进行的,那么,技术哲学研究中的这种经验转向则为其提供了对具体的技术进行有效控制的方法和可能。因为“技术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见”(让·戈菲),离开具体的技术人工物而抽象地来谈对技术进行控制会最终因为没有具体的控制对象而使控制行为失之于空谈。所以,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经验转向有利于具体控制技术的行为,从而实现技术控制主义所追求的目标。
总体而言,技术哲学研究中的技术控制主义反映了技术时代人们期望对待技术的精神状况,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对人类未来的关注,决定着技术控制主义有着美好的未来发展。但是,由于它是一种正在形成的技术理念,因此,存在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从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其有生命力和发展空间),而这些问题解决的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着技术控制主义未来发展(尽管哲学只提出问题而不解决问题,但哲学的指导性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例如,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来避免由机械论世界观所导致的技术的滥用而产生的各种技术性的全球问题?如何解决当前针对各种技术问题而产生的能够控制却不加控制的情形?如何解决因对技术不加控制而导致的人类自由的丧失与因对技术进行控制而实行的集中计划和管理所导致的个人自由的可能丧失之间的困境?如何确立技术过程当中各个环节的责任主体及其相应的责任而避免出现谁都负责最后谁都不负责的情况的出现?等等。
注释:
[1]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人民出版社,2002,第7~9页。
[2]Alan R.Drengson,Four philosophies of Technology,Technology as a Human Affair,Edited and with introduction by Lary A.Hickman,New York:McGraw Hill,1990,p.28.
[3]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74页。
[4]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第141~142页。
[5]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116~117页。
[6]米哈依罗·米萨诺维克:《人类处在转折点》,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第128页。
[7][日]星野芳郎:《未来文明的原点》,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85。
[8]Erich Fromn,The Revolution of Hope:Towards a Humanised Technology,New York:Harper&Row 1968,p41.
[9][德]H·波塞:《技术及其社会责任》,《世界哲学》2003年第6期。
[10][美]玛乔丽·C·米勒:《技术与公民社会:控制问题》,《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
[11]远德玉,陈昌曙:《论技术》,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第284页。
[12][美]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第270页。
[13]转引自姜振寰:《技术社会史引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第105页。
[14][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第9~10页。
[15][美]J·T·哈迪:《科学、技术和环境》,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第200~202页。
[16]肖峰:《技术发展的社会形成》,人民出版社,2002,第350~351页。
[17][21]邹珊刚:《技术与技术哲学》,知识出版社,1987,第37页;第40页。
[18][22][美]欧文·拉格兹:《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异端的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6页;第5页。
[19][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页。
[20]奥特弗利德·赫费:《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220页。
[23]Peter Kroes & Anthonie Meijers,The 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Amsterdam:Elsever Science Ltd.,2000.Hans Achterhuis,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The Empirical Turn,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