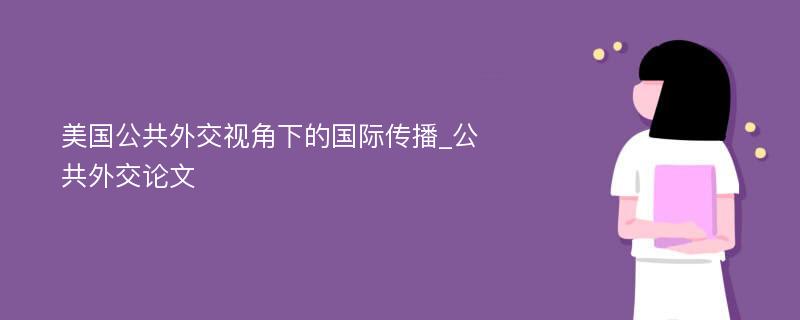
从美国的公共外交认识国际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外交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
【主持人语】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世界逐渐平面化的时代,这个平面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以信息的增长和流量为特征的过程。按照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新闻信息的生产和流动可以转化为社会治理的民主手段,如美国学者舒德森所归纳,新闻业在保障与促进民主方面可以有7项功用:即信息提供、调查报道、分析评论、社会同情、公共论坛、社会动员、宣传代议制民主。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全面普及,如何建构社会主体的关系取决于信息传播的行为效益。传播权力的社会化增长与中国的社会进步同步,不管是基于建构和谐社会的网络问政,还是各种以信息网络为组织形态的社会团体的公共参与,甚至是无数自发的网络反讽和抱怨,都从不同路径在参与某种意义上的媒体公民社会的建构。显然,信息博弈正在中国形成一种旨在建构社会共同体的叙事。一种真实有力的社会叙事,必然要在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追求有理想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性,在推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的现实进程中有所作为。不仅以物质产品,而且以非物质产品的形式为世界的和谐进步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从而赢得应有的尊严和自信。
陈卫星
在经历了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之春关于拉萨民族分离主义骚乱的“真相”传播和守卫“奥运圣火”海外传递的紧张政治斗争之后,国际传播和争取国际传播的“话语权”成为中国主流思想舆论关注的焦点。面对以媒体战呈现的“中西对立”,中国国际传播意识的觉醒呈现两种倾向性的策论思路:一是具有传统国际政治论战经验基因的强攻型,即揭批西方“某些老爷们”的反华本质;①二是与时俱进的技巧型,认为中国遇到了“涉外公关危机”,需要研究如何提高传播、沟通、说服等形式的公关能力,培养“跨国公关人才”。②强攻型的本质主义论者批判说: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具有偏执的反华“病态”,没有资格评论中国。技巧型的形式主义论者则认为:需要对西方知识界和社会公众开展有技巧的“公关”努力,如“推出国家形象广告”、发动“魅力攻势”之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立的理解,前者当然地要求西方先去“治病”再来谈中国,国际传播就是互相不能说服因此难免需要使用贬斥语言的英雄论战;而作为形式主义的传播学分析,后者乐于反求诸己去主动疏通关系,着眼于让更多外国人“愿为中国说话”以克服“涉外公关危机”,国际传播也就是一种笼络或迷惑人心的怀柔术了,似乎近于美国的公共外交。
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英雄论战曾经被毛泽东、邓小平反思为“放大炮”和“讲空话”。③很显然,作为国际传播的“放大炮”和“讲空话”是徒然加剧感情对立的无效传播。那么,“推出国家形象广告”之类的“国际公关”或展开“魅力攻势”的怀柔术会是有效的国际传播吗?为了指出这种简单想象、闭门造车的误解和草率,我们把在西方有代表性的美国公共外交作为比较研究对象,通过具体的国际传播行为来认识什么是可能、有效的国际传播。
一、美国的公共外交
根据法国学者阿芒·马特拉的研究,西方所谓的国际传播从来就是“一种战斗话语”,服务于战争和冷战。④2,102比较于上述“原生态”的概念体会,中国学者望文生义为“超越国界的传播”就显得简单、麻木和隔膜。而作为国际传播的公共外交,虽然可以理解为以现代传播技术手段克服国家间政治壁垒和文化间交流障碍、通过与对象国公众的沟通而影响其政府对外政策的国际政治形态,但它的“战斗性”仍然没有获得必要的理解。很显然,这种理解有待于对美国公共外交的政策文本或政治行为作出实证分析。
美国有着悠久的公共外交传统,比如世界大战时期的战争宣传、冷战时期对苏联阵营的国际广播和文化教育交流项目等等。在冷战以美国的胜利告终后的一个时期,公共外交的战略地位下降,机构被合并、经费枯竭;但随着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力集团在新世纪之初发动对美国的大规模恐怖袭击,美国政府在组织军事反恐战争的同时,重新对公共外交进行强有力的组织和大量经费支持。
关于新世纪的美国公共外交,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格拉斯曼(James K.Glassman)在2008年10月28日做了一次国务院专题简报会,介绍情况并回答提问。他说:我们的政府外交(official diplomacy)以外国政府官员为目标,而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则针对外国公众即美国官员、公众与别国的公众打交道。公共外交与美国政府其他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行为主体拥有共同的目标,即减少对美国的威胁和推动自由。“在公共外交中,我们通过了解(understanding)、报告(informing)、吸纳(engaging)和影响(influencing)外国公众来达成目标。我们所使用的工具是图像(images)、语言(words)和事迹(deeds)。”公共外交的工作分成三类:一是讲美国故事;二是从事被证明有效的文化和教育交流项目,如富布赖特项目;三是打观念战争。所谓“讲美国故事”,就是关于我们自己;交流,是关于我们和他们;观念战争则主要是关于“他们”。“在观念战争中,我们的中心任务不在于修正外国人对美国的理解,而是孤立和减少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当然不是用炸弹和子弹,而是用图像、语言和事迹。”冷战时期我们非常擅长观念战争,但在90年代柏林墙倒塌后,两极模式的观念战争被解除了。现在我们已经重组了机构:战略传播政策协调委员会(PCC)由国务院领导,新成立的跨机构组织全球战略拓展中心(GSEC)由国务院、国防部、情报部门的人员组成,是我们的日常战略和行动中心。我们在全球从事大量的项目,利用驻外使馆和公馆网来评估当地的需求。“我们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清楚我们的任务:创造一个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全球环境。”我们主要以两种方式完成任务:一是与支持和激发暴力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作斗争并摧毁它们;二是引导年轻人远离暴力极端主义道路,切断他们招募人员的链条。“比如在巴基斯坦,我们最近在那里完成了一场新的观念战争,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我们以跨机构团队的形式完成了任务。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巴基斯坦政府关于恐怖主义威胁很严重并且已成为现实这一信息,告诉世界反恐战争就是巴基斯坦的战争,正如巴总统说过的那样。”在巴基斯坦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项目,比如我们帮助当地学校改革,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诸如宽容等普世价值。我们还搞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项目,就是进行小说式广播,让年轻人播音,用一些小故事解释重要价值观念。在这两个十分简单的项目中,我们都支持非政府组织(NGO)的工作,而我们自己并不直接参与到这种“工作”中去。我们为“中东的未来”项目做后盾,该项目集中了中东地区最优秀的头脑形成一个主流智库。我们在坦桑尼亚资助了一个电话交流广播节目,宣传主流阿訇的形象。另一个观念战争的主战场是欧洲,有2000万穆斯林居住在西欧,我们着力于增强主流穆斯林的声音以压制暴力极端主义,并且在年轻穆斯林技术工程师和实业家中建立联合组织,为欧洲的年轻穆斯林提供正面选择。而许多传统的公共外交手段在观念战争中也起到了作用,英语教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事实上,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人们都希望学英语,但“教英语不单是传授词汇,更多的是思想”。
在回答提问时,格拉斯曼还把“观念战争”称为“全球意识形态拓展”。关于公共外交和观念战争的效果,他指出:“支持本·拉登和穆斯林国家以及自杀式爆炸的舆论直线下降,成为近几年来最大的变化。”这些态度以及其后的行为变化正是我们寻求改变所要达到的目标。对于观念战争来说,支持暴力极端主义的舆论渐弱比支持美国的舆论渐强更加重要。而且在事实上,最近的全球态度调查项目结果显示,对美国的好感在世界80%的国家有所上升。我们并不能完全控制局面,但我们需要对话,花了大量时间扮演推动者和召集人的角色。我们鼓励对话,“因为我们有信心相信到最后,人们会朝着我们认为的普世价值方向走”。我们通过人际交流改善美国的形象,例如富布赖特计划,我们每年让50000人到美国来。也利用网络技术例如“数字延伸团队”,这个团队以为国务院服务的身份工作,使用外语上网,进入聊天室,访问受欢迎的网站,有时候登陆博客,讨论美国政策,修正错误,指导人们回到反映事实的文献。总之,对于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我们在其中的作用谈得越多越好,越透明越好。“我们自己在公共外交中试图不去命令别人,不进行说教,而是鼓励更广泛的对话。”⑤
二、思考国际传播学:美国与中国
对于美国公共外交的成功,中国学者和舆论多有临渊羡鱼的赞叹,甚至间或发誓也要“输出价值观”、搞“政治观念竞争”以证明“大国崛起”。但是,“输出”、“竞争”不能靠闭门造车的一厢情愿幻想;作为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我们有必要思考美国公共外交的国际传播学意义及其对中国的镜鉴。
从美国的政策设计和国际政治实践来看,公共外交之所以能够成功,首先是因为它具有明确的传播者定位自觉:坚定的民族国家政治主体性、清醒的跨文化交流意识、积极的思想斗争精神和明确的利益目标指向。
所谓民族国家政治主体性,是指在国际政治中主动认识世界、努力控制国际关系发展进程的能动性。美国公共外交认识到现代大众社会对于国家政策的决定性或牵制能力,了解人们对知识力量、思想尊严和价值理性追求的一般性,因此能够作出以外国公众为对象和以提供知识系统、思想资源和价值论证为内容的国际传播设计。这种公共外交,既不是传播生吞活剥的意识形态教条,也不是发展某种把国家间政治作人情化想象的所谓“友好”,而是在国际交流过程中建构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分享多元化进程话语权的文化公共空间,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文化公共空间中开拓美国利益的可能性。很显然,民族国家政治主体性同时也就决定了公共外交的思想斗争精神和追求外交利益的目标指向。
所谓跨文化交流意识,就是使国际传播具有文化间性的自觉和主体间性的形式,即尊重传播对象的认识主体地位,以共同知识起点、共有思想过程和共享价值意义来克服民族国家间的政治壁垒和文化障碍。有了这种跨文化交流意识,公共外交就是建设对话、交流的社会性参与平台,而社会性参与平台就成为国际文化公共空间的生长点。与单向输出、忽视反馈而坚持传播者本位的本质主义批判或对外宣传相比,公共外交的国际传播学意义在于建立主体间共识的有效性,而有效的主体间共识必然会成为共同政治行动的指针,因此也就达致了所预期的国际政治利益目的。可以说,形成主体间共识是最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和最有政治能力的传播关系证明。
其次,作为国际传播的美国公共外交在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的设计上体现了知识思想系统的传播,而不是简单的政治政策话语宣传,更不是玩弄与人们所关心的事实、知识、思想无关的唯美符号和伪美仪式。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知识思想系统是以自我阐释为起点来展开世界阐释的。在国际传播中,如果传播者不能有效地自我阐释本国的历史与政策,即不能有根据地说明“我是谁”、“我为什么这样”,那么它对世界的解释也必然荒唐,整个传播都是陌生、可疑因此是无效的。美国的公共外交把讲“关于我们自己”的“美国故事”置于首位,就是建立能够自我阐释的“美国知识”体系、“美国思想”逻辑和“美国价值”论证;如果这种知识、思想和价值系统在传播过程中能够有效成立,国际传播的国家信用便确立起来,从而使传播具有了可持续传播的传播者权威和受众继续传播的扩散动力,它对世界的阐释也就获得了积极的受众。而其所谓“关于我们和他们”的“文化教育交流项目”,目的是在传播对象国家建立传播中转的本土“主流智库”;建立这种智库的目的就是利用本土的知识思想权威在对象国家进行低成本的继续传播。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学者库特·列温通过实验发现:尽管美国政府鼓励公众食用动物内脏,但除非家庭主妇决定让它进入餐桌,她的家人是不可能接受的。由此列温在传播学中提出了“把关人”的概念。⑥72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借用本土权威实现有效传播的思想灵感。在公共外交的传播结构设计中,对象国的本土知识思想权威类似于“家庭主妇”,对象国的一般受众基于对“把关人”权威的习惯性信赖而乐于接受其中转信息,因此传播者通过与本土“主流智库”的交流关系可以比较顺利地实现知识系统的平移和传播者、传播媒介的本土化或隐蔽化。而有了知识系统的植入和传播者、传播媒介本土化的转换或阐释配合,以“图像、语言和事迹”展开的“观念战争”就能够与本土的知识思想体系对接而形成有效的战斗力了;这种战斗力体现在受众对国际传播的知识信赖、思想理解和价值服从。
基于上述分析来看关于中国国际传播的“魅力攻势”说和“国际公关”论,它虽然与复活“文革”式语言来批判西方的技术思路相反,但其丧失尊严的作伪嫌疑和提供利益的贿赂取向已经宣告它不是具有政治主体性和知识思想传播功能的国际传播学,而是一种低俗、懒惰的人际关系学。试想,在世界主要国家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关于中国问题的情报收集、学术研究高度发展的当代,如果以为对外传播可以用形式主义的仪式和工具主义的技巧塑造国家形象,如果以为载歌载舞、涂脂抹粉的“魅力攻势”和巧言令色、投机钻营的“国际公关”能够赢得国际政治认同和国家利益尊重,不是低估了外部世界的认知能力吗?如果中国的对外传播所提供的只是教条宣传性的政策陈述、浪漫传奇化的文化叙事或徒具形式的美人美景,而不是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可靠知识体系和具有价值论证能力的理论思维,能塑造有国际尊严的“中国观”吗?总之,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自欺欺人因此有可能遭到捉弄或蔑视的国际“公共”技巧,而是探索既有学术思想内涵又有工具技术形式的传播外交。
三、建设适应时代需要的中国国际传播
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传播技术的变革和学术、教育国际化的迅速发展,知识生产、思想传播已经上升到关系国家利益的情报学战略层次。现代社会的国际情报战通常已经不是以情报工作者获取对方的高层核心机密来了解其政策决定,而是以学术工作者的知识生产、思想传播和外交谈判者的话语能力引导、决定对方的行动,即作为政治学的学术建设与国际传播。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世界性不仅表现在它们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关系上,也表现在它们对发达国家从学术资金、课题设定到知识生产、思想提供的精神依附关系上;而精神依附更加深了经济依附——没有自主的知识、思想生产,导致不能准确地认识外部世界和判断自身的利益。因此,中国欲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间竞争中取得有尊严的利益,就必须能够有效地传播自主观察世界、有效解释自我的知识与思想,建立起国际传播的交流平衡,而努力避免处于被围观、被解释的反传播地位。比如,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之发达,甚至发达到连西方出版的中国革命领袖传记和中国历史著作也能够在中国流行的程度;比较于中国的美国研究、日本研究或者欧洲研究,西方中国学对中国造成的知识思想倒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话。因为中国处于国际学术和国际传播格局的低位,所以难免不断受到西方“中国观”的知识灌输、思想诊断、政治批评甚至媒体攻击;而这种国际文化生态也使得中国很难实现有效的国际传播。
以上述时代认识和问题把握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国际传播还处在不能适应全球化挑战的状况:表现在外交理解和传播实践中,低水平重复的传播形式与技巧往往受到突出的强调;表现在国际传播的学术研究中,形式主义分析和工具主义目的理解居于主流。这种状况与中国学术的荒疏有关——不仅指国际传播学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思考,更包括对中国历史和“问题”特别是“问题历史”的系统实证研究。比如,如果现代中国政治领袖的传记和专业的历史研究也都是外国著作在中国流行,何谈观察世界、解释自我的文化主体性?我们能想象中国学者的美国政治家传记或日本历史研究在海外流行吗?再比如西藏发生骚乱、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及其西方支持者阻击奥运火炬传递之后,中国的主流媒体播放了历史文献纪录片,新闻节目也公布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但国际传播是国际舆论建构的日常性过程竞争,而不是单在危机传播时刻的应急辩解和亡羊补牢。因此,中国必须一方面切实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以改变中国知识思想供给滞后或贫困化造成的对外传播的知识思想空洞化状况;一方面加强国际传播学科的建设,以把握中国问题、了解世界经验,从而建立中国的传播外交能够有效成立的知识思想基础。这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需要,也是中国学术重建知识主权进而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需要。
注释:
①隗静:《西方一些人眼疾、失忆、偏执》,《环球时报》2008年4月11日,国际论坛版。
②吴旭:《让更多老外愿为中国说话》,《环球时报》2008年3月25日;郝平:《培养专业人才,应对国际媒体危机》,《环球时报》2008年4月11日,国际论坛版。
③毛泽东在1972年2月21日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而邓小平在1989年5月16日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更恳切地谈到:中苏论战“讲了许多空话”,“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④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⑤格拉斯曼:关于美国公共外交和观念战争的简报(2008年10月28日),美国国务院网站(http://www.state.gov/r/us/2008/111372.htm),2008年11月16日访阅。
⑥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