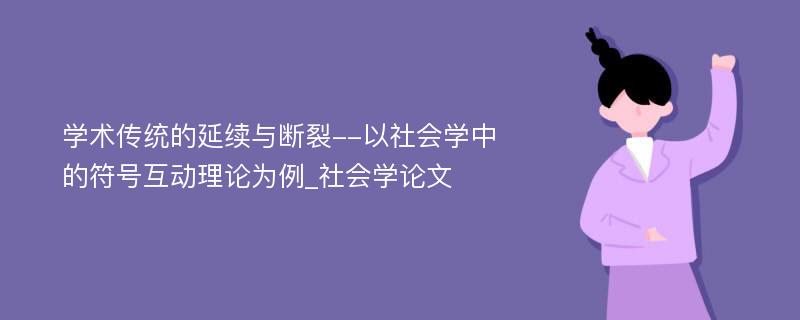
学术传统的延续与断裂——以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为例论文,符号论文,学中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学的社会学及科学社会学的历史上,1962年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出版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这一著作中,库恩向先前流行的那种有关科学是通过循序渐进的积累方式发展起来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按照库恩的说法,科学不是按进化的方式发展的,它的发展是通过一系列革命的方式实现的。在解释这种“革命”的过程中,库恩使用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用来指“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注:Kuhn,Thomas 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econd Edition,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0,p.175.)。科学的进步体现为不同范式间的嬗递的观点,不再像先前那样强调科学及学术发展中的积累因素,而是开始强调断裂与超越。这一思想提出之后,在“范式”概念流行于社会学界的同时,也促使许多社会学家与社会理论家思考社会学或社会理论内部的成长过程。布莱恩·S·特纳发现,在港汊纵横的各种社会学传统内部,几乎很少有什么明显的理论积累,社会理论更为鲜明地表现出的是时尚与分裂,而不是什么连续性的成长(注:Turner,Bryan S.,"Some Reflections on Cumulative Theo-rizing in Sociology",in Turner,J.H.(ed.),Theory Building inSociology,Newbury Park:Sage,1989,pp.131-147.);欧文·斯帕伯更是通过对一系列社会理论家的分析指出,社会科学界的意见领袖是通过对科学时尚的操纵登上舞台的中心的,而一种流行的社会学模式作为一种特定的集体行为方式对理解某一科学家共同体是基本的路径(注:Sperber,Irwin,Fashions in Science,Opinion Leaders andCollective Behavior in the Social Sciences,Minneapolis:Universityof Minnesota Press,1990.)。
尽管学术传统尤其是社会理论传统体现出明显的断裂态势,但是包括布莱恩·S·特纳在内的许多社会学家还是公认,符号互动论和理性选择论这两种理论的成长也许算是例外。“在这两个领域里有着连贯的研究传统,相对而言没怎么受到重大范式或内在分歧和异见的打断”(注:布赖恩·特纳编:《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鉴于一篇论文的篇幅有限,在这里我们仅就符号互动论(The theor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的成长过程,来讨论学术传统的这种延续与断裂现象。
一、符号互动论:一种传统的形成与确立
尽管自布鲁默之后,社会理论家们都公认,符号互动论的鼻祖是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将乔治·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但它的学术渊源却一直可以追溯到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尤其是美国本身的实用主义传统中去(注: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1页。)。就第一种传统而言,导源于黑格尔、康德,经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发扬光大的历史主义传统,有效地阻碍了英法两国盛行的实证主义,这为后来德国解释社会学的出现作了良好的铺垫。基于齐美尔思想对早期美国芝加哥社会学的影响(注:See Faris,Robert E.L.,Chicago Sociology:1920-1932,SanFrancisco: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1967,p.48,p.108;另见布赖恩·特纳编《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第49页。),历史主义传统在符号互动论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作用。不过,正如科林斯所说,尽管受到德国传统的浸淫,但是在詹姆斯、鲍德温尤其是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美国符号互动论取得的成就还是远远大于单纯的模仿。具体说来,在这一传统的延续中,“虽然德国的哲学是一种刺激,但正是美国人自己由此而创造出了纯粹的社会学理论”(注:Collins,Randall,Four Sociological Tradi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44.)。
在符号互动论的萌芽阶段,密执安大学的查尔斯·库利(Charles Cooley)起到了“起锚”的作用。库利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创用了后来享誉社会学界的“镜中我”、“初级群体”等概念,而且在于他主动继承了早期美国社会学家研究主观社会生活的兴趣,“接受了将社会心理学理论系统化的挑战”(注:萨哈金:《社会心理学历史与体系》,周晓虹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这一挑战的新颖之处在对个体和微观层次的社会互动过程的关注,正是这种关注后来直接影响到以米德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传统在美国的发展。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米德是符号互动论的导航人,但是芝加哥大学尤其是其所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无论对米德的个人思想还是对整个符号互动论的形成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1894年,当米德随自己的好友杜威前往后来成为实用主义大本营的芝加哥大学哲学系任教时,社会学系在A·斯莫尔手中已经建立起来了两年。很快,这个迅速发展的社会学系,为米德率先开设的社会心理学课程提供了大批的学术阅听人——哲学系以外的许多学生,尤其是社会学系和心理学系的青年才俊们活跃在他的课堂上,其中包括后来因创设行为主义而名垂青史的心理学家约翰·华生(John Watson),以及在米德之后举起了符号互动论之帅旗的社会学家赫伯特·布鲁默(Hebert Blumer)。
布莱恩·S·特纳曾根据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理论提出,“成功的学派或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一些适宜的制度条件,比如职业社团的发展,一种卓有成效的资助体制的创立,专业杂志的组织以及其他出版渠道”(注:布赖恩·特纳编:《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在社会学发展的160余年中,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一共只产生了两个学派:以埃米尔·迪尔凯姆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和我们这里讨论的美国芝加哥学派,而这两大学派的出现基本都具备上述制度性条件。单从符号互动论的思想摇篮——芝加哥大学而言,从1890年建校伊始,在有着实业界的“强盗大王”和虔诚的浸礼教徒双重身份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老板洛克菲勒的全力支持下,这所大学在经济上就从来没有窘迫过。加之19世纪之后,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移民的聚集,这个1833年还仅有数千居民的原木贸易站,凭借当时开通不久贯穿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和1893年为纪念发现美洲400周年而召开的世界博览会,100年后即到了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时期成了拥有350万人口、仅次于纽约的全美第二大城市。当资本主义在芝加哥获得近乎野蛮的发展的同时,那里的贫困、人口拥挤和犯罪逐渐变得和伦敦、曼切斯特一样显著。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决定社会学在美国的最初发展的骰子为什么最后掷向了芝加哥。
斯莫尔就是在这样一个需要社会学的时代和需要社会学的城市,在当时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珀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尽管斯莫尔的学术乏善可陈,但他在担任系主任的33年的行政生涯中为芝加哥学派乃至整个美国社会学奠定的学术制度体系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其一,1892年,斯莫尔建立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这不仅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而且到斯莫尔退休之时,既是芝加哥大学中的一个大系,也是全美培养博士最多、开设课程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学系;其二,1895年,先于法国人迪尔凯姆创办《社会学年鉴》前一年,斯莫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并且担任主编达30年之久;其三,1905年,以斯莫尔为主创办了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这是至今仍然统治着美国社会学界的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前身。这三大贡献不仅在相当时间内影响到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而且从根本上奠定了符号互动论栖身的摇篮——芝加哥学派在早期美国社会学中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注:周晓虹:《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贡献与局限》,《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6期。)。
尽管符号互动论与芝加哥学派有着亲缘上的关系,但客观地说,与社会心理学关系更为密切的符号互动论并不是芝加哥社会学的唯一子嗣,起码在1930年代之前它的“长子”要算以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因为将学术兴趣直接导向经验研究层面,因为成功地将芝加哥这个充满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现代都市视作社会学研究的巨大实验场,帕克,这个50岁才迈人社会学门槛的新闻记者,10年后就成了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
其他资料似乎也能证实米德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在最初的芝加哥学派中的相对边缘地位。刘易斯和斯密斯两位社会学家通过对早期芝加哥社会学系的课程注册、论文和著作中引述的次数,以及其他资料的计算和分析,企图说明“米德并不是芝加哥社会学程序中的中心人物”(注:See Lewis,David L.,& Smith,Richard,American Sociologyand Pragmatism:Mead,Chicago Sociology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这里的史料应该不会是错误的,起码在当时有两个关键的因素造就了米德在早期芝加哥学派中的边缘地位:其一,他一直在哲学系任职,对社会学系的师生至少没有任何行政上的影响力;其二,有鉴于芝加哥社会学鲜明的经验品质,米德哲学意味浓郁的社会行为主义和互动论思想对学生的学业影响只能是间接的。
不过,193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此时米德已经撒手西去。造成变化的背景是,从社会因素上说,在经历了最初的工业化浪潮之后,此时的美国移民潮已经回落,城市已经多少变得井然有序,人的边际性也开始减少;从学科角度说,包括社会学力量在其他学校尤其是东部的哈佛和哥伦比亚的崛起,它们在理论(帕森斯/默顿)和定量技术(拉扎斯费尔德/斯托弗)两方面的建树彰显出早期芝加哥社会学的粗鄙。这些变化,加之芝加哥社会学的内部矛盾(教师间的不和和优秀师生的出走),导致了学派和芝加哥社会学系地位的衰落。
如果说在上面变化面前,原先由帕克领衔的有关社会无序的社会生态学视角已经式微,那么面对帕森斯这个直接引发芝加哥社会学大厦坍塌的“伟大的年轻人”(注:Merton,Robert K.,"Remembering the Young Talcott Par-sons",American Sociologist,1980,15:68-71.),唯一有能力进行面对面的抗衡的就是此时芝加哥社会学的中坚——罗伯特·布鲁默,而他能够既娴熟借用又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泾渭分明的理论资源,只能是乔治·米德的传统。这样,在1937年帕森斯出版《社会行动的结构》的同时,布鲁默也在“社会心理学”一文中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将米德的传统称之为“符号互动论”。布鲁默的举动极富象征意义:它不仅标志着符号互动论对结构功能论的“反叛”和“挑战”的正面回应,而且规划了符号互动论未来的走向,并且直接导致了战后芝加哥传统的“复兴”。尽管1960年代以后,由于各种原因,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再度衰落(注:有关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发展,参见Fine,GaryAlan(ed.),A Second Chicago School?The Development of a PostwarAmerican Soc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但是符号互动论的思想此后却绵延不断。
二、符号互动论的基本思想
阐释符号互动论的基本思想自然要回到米德的理论轨迹中去。就思想来源而言,米德的思想直接与我们上面提及的三位美国思想家有关,这就是他在哈佛时的老师詹姆斯、在密执安大学任教时的好友哲学家杜威,以及社会学家库利。借用乔纳森·特纳的话说,“这几位学者每人都为米德的理论综合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概念”(注:Tumer,Jonathan H.,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Fourth Edition,Jaipur:Rawat Publications,2002,p.310.)。显然,从詹姆斯那里,米德获得的是“自我”这一概念,它说明人类具有将自己视为客体看待的能力;在詹姆斯之后,库利完善了“自我”这一概念,论述了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对对方姿势(gesture,这一概念最早是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创用的,米德在德国留学时就受到过它的影响)的理解,以及个人是如何根据他人的看法认识自己的——这最后一点,即库利的“镜中我”,为米德提出“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的概念提供了温床;最后,杜威所提出的“精神”(mind)在社会环境中产生并在互动中发展的理论,同样对米德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米德的理论在其生前被称为“社会行为主义”,这一术语的使用具有偶然性,但它却极为准确地反应了米德思想的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基础。他不同意由他先前的学生华生提出的行为主义全盘否定精神或意识的作法,认为行为主义忽视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即忽视了人的社会性。他坚持认为人对外部世界的适应是通过符号化的沟通过程实现的,这与生物有机体对环境刺激的简单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正好相反。因此,在他那里,符号互动论关注的问题是极其明确的,那就是日常生活中符号意义的创造与交换。可以说,这一传统所以没有出现过明显的断裂,表现出了鲜明的理论增进,就在于从米德起,一直到布鲁默、休斯、贝克尔、戈夫曼、里斯曼、曼夫德·库恩乃至当代符号互动论者止,他们所讨论的核心主题都没有偏离这一轨迹。“更精确地说,它关注的是为互动这一概念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说明,从而就自我的社会性质、社会互动的维持,以及关于越轨行为的种种问题,创造出一系列很有意思的概念和思路。”(注:布赖恩·特纳编:《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第9页。)
贯穿米德的主要著作《精神、自我与社会》的基本假设有二:其一,人类有机体在生理上的脆弱迫使他们相互合作,以群体生活的方式求得生存;其二,存在于有机体之间的那些有利于合作并最终也有利于生存与适应的特性和行为将保存下来,包括精神、自我在内的各种人类特征是人类在生存斗争中逐渐形成的“生存能力”,米德就欲图通过对这种生存能力的论述来讨论社会及其建构。社会代表着个体之间组织化的、模式化的互动,而这种互动既有赖于个体扮演角色和想象各种行动方案的精神(mind)能力,也有赖于从概化他人的观点来评价自身的自我(self)能力。显然,社会塑造了精神和自我,但社会和社会组织本身又是凭借精神和自我而得以建构和延续的。如此,“社会制度是可塑的、不断进步的,并且是益于个人发展的”(注:Mead,George H.,Mind,Self and Society: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4,p.262.)。
尽管我们交代,在芝加哥社会学系的行政体系中,米德处在边际状态,但他的社会心理学课程从1900-1930年一气开设了30年,其影响怎样低估都是巨大的。在米德的全部学生中,1927年从他手中获得博士学位,1931年接替他的教席的罗伯特·布鲁默对这一学术传统的传承意义重大。他不仅继承米德的思想遗产,而且还立志将这笔“遗产”盘活。因此,虽然布鲁默对米德的思想尤其是方法论不太满意,但他却一直恪守米德所主张的互动过程是持续进行的这一基本观点。在布鲁默看来,人们正是通过互动过程,对自己周围的环境和相互间的关系做出解释,并对当时的情境加以共同的定义的。
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表达布鲁默对结构与行为或互动的关系。在布鲁默眼中,社会结构或文化的可变性,只是在它们影响人们在其中活动的情境时,或人们在主观上解释或定义情境时考虑到它们,才会影响互动过程。因此,社会制度不能够离开人们的主观定义而保持他们的作用;显然,更为重要的是,当人们的主观定义和解释在大范围内发生变化时,社会制度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由于布鲁默强调人类行为的选择性、创造性和非决定性,强调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行为科学的独特性,认为人类行为的研究者应该进入行动者的世界,他们的“注意中心应该永远是经验世界”(注:Blumer,Hebert,Symbolic Interaction:Perspective andMethod,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9,p.17.),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布鲁默自然会反对操作主义定义、反对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采用测验、量表、实验等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方法。他强调指出,“通向经验有效性的道路并不存在于玩弄探讨方法之中,而在于对经验世界的考察中。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靠追赶自然科学的先进程序,不能靠采用最新的数学或统计学方案,或创造新的概念,也不能靠发展精密的定量技术或坚持某种调查统计的规则。……需要的是走向经验的社会”。(注:Ibid.,p.34.)由此,他沿着芝加哥的传统,提出了由探索和检验组成的对社会现象直接考察的方式,并提倡积极使用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日记、信件、非结构性访谈和参与观察等一系列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
在193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里,布鲁默所遭遇的压力是巨大的:在外部,他必须抵制来自东部的“反叛”,在内部他又必须面对自1935年起连续担任了15年系主任的定量主义者威廉姆·奥格本对芝加哥传统的改弦易辙。在维护芝加哥的传统方面,他获得了罗伯特·帕克的学生、他现在的同事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始终如一的支持。这也使得后来当1952年在芝加哥呆了27个年头的布鲁默转任加州伯克利分校后,符号互动论传统在芝加哥仍然延续了近10年的发展。
布鲁默离去之后,在芝加哥内部,真正继承符号互动论传统的还是芝加哥自己培养的两位博士——霍华德·贝克尔和欧文·戈夫曼。贝克尔的贡献在于,通过符号互动论的思路,他对越轨行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验研究。他质疑那种将越轨视为由社会系统中的结构性压力造成的观点,并提出了后来闻名遐迩的“社会标签理论”的雏型。在贝克尔看来,单单根据越轨者的行为或社会结构是无法理解越轨的,只有认识到越轨行为也像其他行为一样涉及互动关系,我们才能用社会学的方法去分析它。换言之,越轨既非与生俱来的品质,也非后天教化的产物,而是社会反应、他人定义的结果。在“成为大麻服用者”一文中,他成功地解释了通过社会互动和他人定义,那些最终被“标定”为越轨者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过程(注:贝克尔的最初论文《成为大麻服用者》,后来成为其代表作《圈外人》的第三章。 See Becker,Howard S.,Outsiders,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3。)。
和贝克尔一样,此时的戈夫曼不仅坚持了符号互动论的立场,而且与贝克尔一道将这一立场推进到各种经验研究中去,这使得早期芝加哥社会学的两种路径——由米德体现的理论兴趣和由帕克代表的现实(经验)关怀开始了某种程度的融合。1956年,戈夫曼在其硕士期间完成的社会阶层研究和博士期间完成的有关设得兰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上的社区生活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一书。戈夫曼关心的基本主题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是如何用各种复杂的方式在他人心目中塑造自己的形象的?通过大量的经验资料,尤其通过对各种戏剧学理论和概念(如前台、后台和剧班等)的借用,戈夫曼成功地描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面对面的互动过程(注:Goffman,Erving,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Garden City,N.Y.:Anchor,1959.)。用库佐尔特的话说,“在戈夫曼的著作中关于人类事件的报告比许多具有大量定量数据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更富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注:Cuzzort,R.P.,Humanity and Modem Sociological Thought,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Inc.,1969,p.191.)。
其实,尽管在符号互动论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知识增进和连续性过程,但也不是说在丰富的理论积累中就没有任何歧义。比如,当布鲁默在芝加哥学派积极推进符号互动论时,另一位互动论者曼夫德·库恩在衣阿华大学则发展出了另一种独具特色的互动论。这两种符号互动论的区别很多,其中包括对互动本质的理解不同:布鲁默主张把自我视为“主我”(I)和“客我”(M)相互作用的过程,互动是在实行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因此他着重互动的创造性和建构性;库恩则强调自我在互动中的力量,以及制约互动的群体环境,因此在他那里互动是从结构中被释放出来的。不过,这被称之为“过程互动论”和“结构互动论”的两种亚型彼此间的差异并不大,起码他们都认同社会学理论必须解释互动过程。而且在现实的研究中,相互间的融合也是显而易见的,连库恩本人都认为,经过充分的争论,符号互动论“大部分被分离的亚理论会重新整合”(注:Kuhn,M.H.,"Major Trend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in the Past Twenty Five Years",Sociological Quarterly,1964,5:84.)。
三、制度化机制的断裂与思想的扩散
我们已经用了较长的篇幅,讨论了符号互动论的知识增进过程和基本观点。在这一叙述过程中,能够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尽管作为符号互动论的大本营的芝加哥社会学派两度断裂,但似乎都没有直接损害符号互动论的健康发展。相反,我们甚至看到,符号互动论真正成为一种理论直面世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成功地“颠覆”了芝加哥在社会学中的霸主地位的“东部新秀们”揭去其“面纱”的。就像亚历山大所说,“互动理论只是在向帕森斯的统治地位挑战的过程中才被看作是主要的理论传统的”(注: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这里,我们先简单地回顾一下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两次断裂,接着讨论这种断裂为什么没有殃及符号互动论的发展。众所周知,第一次衰落发生在1930年代中期。有关这次衰落的社会背景我们前面已有简单交待,而从学术界内部的因素来说,原因也十分复杂。此时,随着社会学主流范式的转换,社会学已经从原先盛行的齐美尔的人道主义和解释性传统,转向高度定量化和统计性的;另外,美国社会学家对芝加哥社会学家普遍怀有的社会心理学兴趣也开始下降(注:据统计,1930年,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1832名会员中,37%的人是社会心理学家;而到了1959年,这个比例在6345名会员中下降到25%(参见Riley,Mathilda White,1960,"Membership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1950-1959",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5:914-926.)。)。当然,在这些因素之外,当年逼迫芝加哥社会学“禅让”的直接事件,是1935年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稍前于此,包括帕森斯在内的东部主要的几个常春藤联盟大学中的社会学才俊组成了一个青年社会学家团体。这个团体在思想上脱离了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社会学传统,在制度上则脱离了芝加哥的组织约束。(注: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第160页。)。1936年,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们创立了我们前面提及的《美国社会学评论》(AJS),借以与长期由芝加哥社会学掌控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SR)相抗衡,它象征着东部新的强势集团颠覆了芝加哥的“霸主”地位。
当然,衰落归衰落,但此前一直独领风骚的芝加哥社会学并没有就此土崩瓦解。不仅在此之后美国社会学会的领导职务多次再回到芝加哥人手中,而且就像我们已经叙述的那样,在帕森斯、默顿以及拉扎斯费尔德等人的压力下,赫伯特·布鲁默及其他芝加哥学人,通过整合后的“符号互动论”积极地回应了前者的挑战。考虑到布鲁默不但是乔治·米德的学生、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教师,而且是帕森斯参与的1935年的“反叛”的直接“牺牲品”(这一“反叛”导致了布鲁默被解除了担任多年的美国社会学会秘书长一职),你就能够知道这场“厮杀”不但是不同范式间的较量,甚至也是一场罗杰斯所说的“政治运动”(注: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其实,无论对结构功能主义还是对符号互动论而言,这场“厮杀”的结果都是积极的:尽管前者自此之后建立了在美国社会学界的强势地位,后者也在对抗中整合了米德的精神遗产,并且形成了以布鲁默为核心的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在这个学派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秉承了符号互动论传统的学者,其中活跃的包括前面提及的布鲁默、休斯、戈夫曼、贝克尔,以及未提及的大卫·里斯曼和沃纳等人。虽然这第二个芝加哥学派延续的时间并不长(1946-1960年),但它的存在及由其倡导的符号互动论,起码使欲图一统“天下”的帕森斯不那么顺心。当然,自上世纪50年代初以后,芝加哥学派再一次发生“断裂”。从表面上看,断裂的原因与1952年和1956年连续发生的两次“系主任争夺战”(Chairmanship Battle)(注:1951年,布鲁默的“克星”奥格本退休后,在芝加哥已经如日中天的布鲁默接班的呼声很高,但最终却是休斯获得了任命(一种可能的原因是,校方为了调和定性主义者布鲁默和定量主义者豪泽之间的对立,选择了相对温和的休斯),这直接导致了翌年布鲁默转任加州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1958年休斯卸任后,竞争发生在此时已经凭借《孤独的人群》名扬天下的大卫·里斯曼和豪泽之间,最终豪泽获得了任命(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定量传统的胜利),而里斯曼则“出走”哈佛大学,戈夫曼也追随布鲁默去了加州伯克利(See Abbott,Andrew & Gaziano,Emanuel,"Transition and Tradition:Department Faculty in the Era of the Second Chicago School",inFine,Gary Alan(ed.),op.cit.,pp.221-272)。)有关;但从本质上说,造成芝加哥学派在此再次断裂的原因还是日渐强大的定量主义取向最终战胜了芝加哥的定性主义传统。自1936年信奉“科学社会学”的威廉姆·奥格本人主芝加哥后,这匹“特洛伊木马”就酿就了定量方法与芝加哥原有的定性传统间的冲突,“在研讨会和午餐会上,统计学和个案研究方法之间也常常会展开争论”(注:Faris,Robert E.L.,op.cit.,p.114.),而两次“系主任争夺战正”是这种冲突达到水火不容程度的象征。
不过,尽管芝加哥学派再一次衰落,但从这里发展起来的符号互动论却已经像燎原烈火,在1962年以后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在它通过越来越多的大学社会学系的讲台传播出去的同时,其主要的学术旨趣和研究内容基本上都没有发生偏移。换言之,符号互动论表现出了布莱恩·特纳所说的连续的成长或理论的积累。那么,造成这种特定结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促成这种学术增进或积累的第一个原因,恐怕与抵御来自外部尤其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挑战有关。我们已经讨论到,尽管米德已经为符号互动论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意蕴,但是作为一种鲜明的社会学理论学派提出,是帕森斯等“东部才俊”向芝加哥原先的“霸主”地位挑战的直接结果。其实,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也是为了面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强大不断的理论压力,所有的互动论者(即使他们已经不在芝加哥了)才能够在维护自己的立场方面旗帜鲜明。这种“旗帜鲜明”不但是为了打破帕森斯的影响垄断社会学界的状况,而且是为了通过符号互动论这种颇具个体主义色彩的理论,对抗帕森斯的抽象的有关“结构”的一般图式。
紧接着的第二个原因,显然与符号互动论的“中层”性质有关。和社会理论领域中诸多以宏大叙事为特征的流派不同,无论是符号互动论还是我们这里没有讨论的理性选择理论,它们关注的问题相对说来都简单明了——都是一种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问题有联系的中层关怀。用布莱恩·特纳的话说,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就是从最佳利益或自我利益之类概念的角度来看待理性行动的性质;而我们已经说明,符号互动论的根本问题就是日常生活中符号意义的创造与交换。我以为,这样一种理论的“中层”性质,一方面比较容易将学者团结或局限在某种既定的“论域”之中(比如,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革命变迁的经济条件,而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则将注意力转向文化分析,这种范式的转型不仅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同样与马克思主义论域的宏观性质有关),另一方面也容易将理论的运用与丰富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我们已经看到,尽管符号互动论的“鼻主”乔治·米德还属于“扶手椅”中的社会学家,但符号互动论后来的发展却与芝加哥学派的经验品质十分吻合。
最后,需要申明的是,我们无论是谈论理论知识的增进还是断裂,都不关涉与优劣或高下相关的价值判断。这是因为,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延续还是断裂,都是理论发展的不同形式。我们只是想通过符号互动论的发展,来说明促成理论传统延续或断裂的那些基本因素究竟是什么。
标签:社会学论文; 芝加哥学派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社会心理学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米德论文; 布鲁论文;
